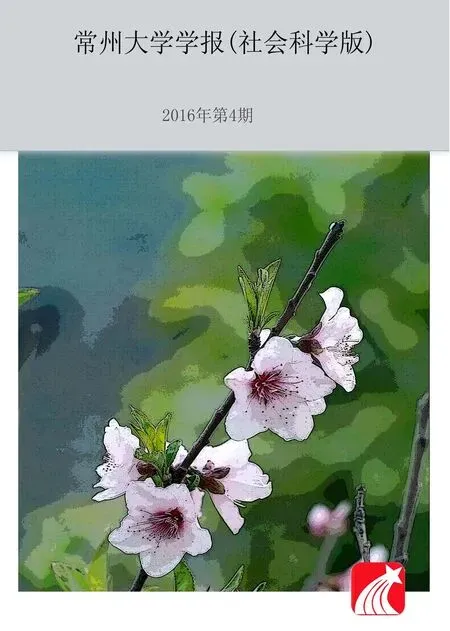奥克肖特、庄子与“中国问题”
——从奥克肖特文本中的几处引文谈起
赵 淼
奥克肖特、庄子与“中国问题”
——从奥克肖特文本中的几处引文谈起
赵淼
在其洋洋洒洒的政治哲学著述中,奥克肖特多次引用中国古代典籍特别是《庄子》中的生动故事,以配合其分析诊断现代西方政治的病理。本文拈出奥克肖特文本中对《庄子》的几处引用,在重温和领略中国经典穿越时空的力道之同时,试图以现代性语境中“中国问题”的疏解为目标,通过对思想界几种理论主张的解析以及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性诠释,在古与今、中与西的比较互鉴中,寻求中国政治抵近传统、中道平和的可能方向。
奥克肖特;庄子;现代性;中国问题
有汉学家曾言: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在相当程度上是个“域外异国”,“我们要么‘妖魔化’中国,要么‘浪漫化’中国”。[1]无法确切推断英国思想家奥克肖特于何时接触到中国古代典籍并对之进行研读,不过,其文本多次引用了中国先贤的话语或故事,可以肯定,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了解甚至可能颇为熟稔*海德格尔的例子常常作为西方思想家受到中国古典文化影响的例子。张祥龙推测海德格尔在1930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就已经认真阅读过《庄子》《老子》,并与之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海德格尔曾在1946年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译过《老子》,而奥克肖特引用中国典籍的几篇重要文章也写作于40年代。硝烟过后,两位思想家都将目光投向中国文化,这或许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参见张祥龙著《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2007年版。。而就奥克肖特的引文来看,他当属于“浪漫化”中国的一脉。奥克肖特引用中国典籍,是为了阐明自己的政治观,反省现代性条件下西方政治文明的弊端。我们阅读奥克肖特,则是为了直面现代性条件下的“中国问题”,思考可能的进路与方向。本文拈出奥克肖特文本中对《庄子》的几处引用,对之稍作讨论,目的不是从西方视野之外印证奥克肖特的政治运思,而在于将奥克肖特与庄子跨越时空的相遇置诸当下中国语境,从中探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中国政治的有益启迪。
一、奥克肖特笔下的《庄子》与诗意的中国
在奥克肖特的文本中,中国古代思想典籍被直接引用或作为注释出现的主要是《论语》和《庄子》,他还提到过朱熹,不过引得最多,且与他的思想颇有契合的,还是《庄子》。这些引用散布在他的数篇论文之中,在他批判政治中的理性主义,探讨政治或国家的非工具性、非目的性时,奥克肖特视野中的中国政治作为一种对比而呈现。在奥克肖特看来,与西方过分理性化、功利化的政治相比,在中国这个历史悠远的东方国度,政治洋溢着独特而迷人的诗意。
引文之一:“轮扁斫轮”与政治知识的传习
奥克肖特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文论及政治活动所包含的知识类型时,引用了《庄子·天道》里的桓公与轮扁的故事[2]9-10。故事讲,某日,桓公在堂上读书,工匠轮扁在堂下做车轮。轮扁见桓公读得入神,便放下手头的锥凿,上前问桓公所读何书,桓公答曰:圣人之言。轮扁又问:圣人还在吗?桓公答:圣人已死。轮扁于是就讲桓公读的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桓公恼怒,要轮扁给出一个说法,否则处死。轮扁便以自己的职业举例:车轮的制作快了或者慢了都不好,而是要不快不慢,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这种技艺口不能传,只能靠不断地观摩学习才能领会。古人以及他们难以言传的经验都已经死去,所以桓公读到的只能是古人留下来的糟粕。
奥克肖特引用这个故事,意在说明:在政治活动中,书本上罗列的“技术知识”无法与具体运用的“实践知识”分开,更不能代替“实践知识”。现代西方政治将政治知识等同于“技术”,把它看作是书本上的文字与教条,可以进行简单的教与学,可以进行机械的应用,这是对政治活动的严重误解。政治中的“真知”或者说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可能毫无妨碍地通过言谈与书写就可以获得和传习,而是要在实践中,通过“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的途径去达到。政治活动的展开并非以某位老师的教导或书本上的条条框框作为前提,以某个固定的政治形态作为样板,毋宁是,照搬书本上的政治知识根本就是对政治的“无知”。
奥克肖特在《庄子》的世界里看到,好的工匠都是艺术家,他们的“方法”就是“无”法,正如《庄子·达生》里的那个“削木为鐻”的鲁国木匠,达到一种忘我之境,才成就了高超的“艺术家”*奥克肖特在另一个地方提到了这个叫梓庆的木匠,Michael Oakeshott:“The Voice of Poetry in the Conversation of Mankind”,in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1962,p.238.。政治也是一门“艺术”。在奥克肖特看来,东方的中国文化没有拘泥于所谓的“方法”与“原则”,人类世界的“诗意”反而没有像在西方那样被遮蔽和遗忘。奥克肖特认为,没有纯粹作为一种“技术”的政治,技术性的政治知识总是蕴含于活生生的政治实践。换言之,政治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不二法门,譬如“民主”或“法治”,它们都不可能有现成的教科书,惟有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在历经时日沿袭下来的政治传统中去揣摩和体会。
引文之二:“其钓莫钓”与政治活动的展开
奥克肖特认为,真正的政治不是为了实质性的目的与追求,而是在政治世界中舒展个性、体验人生、磨砺品德,人们无需通过一个外在的标准去评判政治的优劣,而是尽情享受参与政治本身所具有的“欢愉”。在《论保守》一文中,奥克肖特引用了《庄子·田子方》周文王遇到姜太公的故事[2]177。这个故事说的是文王游览藏地,见到一位老人在垂钓,不过却是钓而非钓,不是为了钓到“鱼”,而仅仅为了享受“钓”的乐趣。文王想委之以重任,又担心朝野的反对,就此作罢,又不忍天下人不能得此良才。后假借先王托梦,授其朝政,三年时间,天下大治。
奥克肖特承认有些人钓鱼是为了捕捉到鱼。如果目的是“鱼”,那么,你会明智地寻求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你要找出最好的渔具,放弃那些证明是不成功的做法,你不会无益地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而,奥克肖特指出:“钓鱼可以是一种不为了钓鱼的利益,而是为了其自身的缘故而从事的活动;渔夫可以晚上空手而归却同样心满意足。”[4] 178此时,“钓鱼”成为一种仪式,意在“钓”的享受而不在“鱼”的获取。如果不在乎能不能钓到鱼,就不会刻意寻求“最好的”渔具,不会以鱼的多寡来衡量“钓鱼”的成败,不会计划多支几根鱼竿扩大钓鱼的规模,不会构想将钓到的鱼独自拥有或分予别人以及怎么分,更不会因为自己喜欢而硬拉别人同自己一样垂钓。此时,只要鱼竿是“熟悉的”,拿在手里没有觉得不合适,便可以在任何有水的地方,独自感受与品味内心的恬静与怡然。
钓鱼如此,政治亦然。在奥克肖特看来,政府不是要统领民众去捕捉“希望”与“理想”的大鱼,而只须提供一个安全的处所,维系一套熟悉的秩序,任由每个人用他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进行自己的“垂钓”。无为而治,放任自由,“无”包蕴了“有”,这个“有”在奥克肖特的视野中便是“自由”。针对西方过于功利化的政治现实,奥克肖特将那位老人的垂钓解读为仅仅为着“愉悦自我”(to amuse himself),这种“浪漫化”的理解自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太公钓的何尝是普通的鱼,这“鱼”也许是文王,是治理天下的机缘*倒是庄子自己钓于濮水,婉拒楚王“愿以境内累矣!”的请求,愿如楚地之龟“曳尾涂中”,却逍遥自在。参见《庄子·秋水》。。在中国古代先贤的眼中,无为而治,并非“纯粹的无为”。孔子讲:“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无为而治,并不是“消极的”放任不管,而是强调“为政以德”,统治合乎“天道”,顺乎自然。朱熹有云:“圣人所谓无为者,未尝不为。”*儒、道、法诸家皆有“无为”之说,“无为”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观念。参见叶坦著“儒家‘无为”说—从郭店楚简谈开去”,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4期。这个道理,身处异域的奥克肖特,怕是不易体会。
引文之三:“相忘于江湖”与政治世界的诗化
在给《利维坦》所撰长篇导言中,奥克肖特在篇末如此写道:“人类注定只能在飞逝的时光中,将对完美的追寻寄托于未来的某一刻,对于这样的族类,它的最高德性是培养对于行为后果的敏锐感知,它最需要的是摆脱幻觉的迷惑。”紧接着这段文字,奥克肖特引用《庄子·大宗师》里的故事结束全文:泉水干涸,那被困在陆上水洼的鱼儿,互相以湿气、口沫滋润对方,此情此景,不如在江河湖水中自在游曳,忘却彼此。[3]79
这个故事,人们常常用来形容男女之间的情感:困境中的相互扶持、“相濡以沫”固然令人感动,“相忘于江湖”则是另一种境界,更能成就彼此的幸福。奥克肖特将其置于“《利维坦》导言”的结尾,却另有一番深意。这篇导言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进行了细致的诠释,奥克肖特指出:“政治哲学是对公民结合体与永恒之间关系的思考。国家被构想为意识到需要解救的人的解救。”在霍布斯那里,“利维坦”就是一个“用以保护和解救自然人”的“人造人”[3]78-79。然而,霍布斯本人十分清楚,国家与“解救”分不开,但它是比“解救”本身低的东西,只不过提供了与人的“得救”有相关价值的某种东西,那就是和平。寄予国家太多的梦想与希望,将“利维坦”想象为一个天国,实际上可能会使之成为一个地狱。“利维坦”一经建立,便应退居幕后,不似那陆上的水洼,将原本自由的鱼群拘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时时饱受身体磨蹭的痛楚。
在奥克肖特看来,“相濡以沫”即便不是一种幻觉,也绝不是可以长久维持的状态,而“相忘于江湖”,则给予每一个个体充分的自由,给予他们自我选择的机会,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求取他“一直所想要的那些东西”,去解救他自己。李泽厚评说庄子的思想是“道是无情却有情,外表上讲了许多超脱、冷酷的话,实际上却透露出对人生、生命、感性的眷恋和爱护”[4]。奥克肖特之所以不时引用《庄子》,正是因为在这个东方哲人的思想世界里,他发现了对于鲜活的生命个体本身的关怀,这种关怀摆脱了世俗的功名利禄羁绊,没有将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寄托于某种理想主义的政治愿景。
不过,庄子在这个故事里还接着讲了这句奥克肖特没有引用的话:“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世间对尧的贤明与桀的残暴多有公论,庄子却主张把谁是谁非统统抛开,化于大道。在奥克肖特的视野中,自由与专制、个人与国家、理想与现实始终处在并立的位置,他的政治哲学试图折中调和,却又不能抛开这种基本的二元结构。庄子的思想则不拘束于这种二元体系,跳出主客之分、有无之别,塑造了一种纯真自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大道之境。庄子的“江湖”,在奥克肖特读来,比水洼宽广,却仍然是一个有限的政治空间。对于那个“人生天地之间”的通透境界,在另一种文化氛围中浸润成长的奥克肖特,到底还是隔了一层*当然,奥克肖特也不必非得如此这般地理解。“解释”不可能抵达绝对的真理,换一种立场,这种通透的境界很难说不是一种“神秘主义”,虚无缥缈,“普通人”根本不能去把握和体会,由此,“自由”的理想落实下来倒成了保障“天生不平等”的自由。。
二、现代性条件下的“中国问题”与思想分殊
从前述对奥克肖特文本中几处引文的讨论可以看出,奥克肖特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政治面临的时代困境,那就是理性的霸权、技术的桎梏,随之而来的是对诗意生活的遗弃,政治世界“只剩下满是尘砂的干枯残余”。奥克肖特在《庄子》的故事中读出一个诗意的政治世界:政治知识的师徒传承,政治统治的无为为政,个体自由的纯真质朴。这种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浪漫化”想象在西方知识阶层并不罕见,“从欧洲与中国最初接触开始,就有不少知识分子,从18世纪和19世纪的莱布尼兹和伏尔泰,直至今天,一直为中国文化所深深吸引”[1]3。虽然奥克肖特不是汉学家,他也没有专文讨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但通过其引文,我们可以窥见一个西方学者出于对现代政治的不满与疑虑,间或将目光投向一种异质的文化,以寻找可能的突破与补救。奥克肖特带着西方的问题阅读中国的先贤,我们阅读奥克肖特,同样是为了反思自己的问题。
近代以降,中国以一种痛苦的方式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被西方现代化的潮流所裹挟,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成为“一个跨世纪的、至今未完成的方案”[5]。如果说历史上从未有过什么“中国问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每一次的革新甚至是改朝换代却都没有走得太远,“一朝天子一朝臣”,基本的政治制度架构与文化支撑却还是大抵延续原来的那套,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进入19世纪,面临亡国灭族的危险,面对前所未有的陌生而强大的西方文化之逼迫与冲击,天朝上国素来的自信不得不接受最为严峻的考验,国人惊惶之余不得不去认真思量:我们该如何对待西方?这是中西之争的问题;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这是古今之争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无法分开,或者说它们本质上就是同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中国未来的道路在何方?究竟哪一种生活方式与政治秩序才是正当而值得追求的?这一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问题”或隐或显,贯穿百余年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历程,直至今日的政治思想论争,仍是绕不开的中心话题。面向“中国问题”的疏解,抛开“左”或“右”的简单标识,下面对几种代表性的思想主张略作举隅和分析。
在不少自由主义学者看来,国家要生存和发展,最好以西方为榜样,不管是渐进的变革还是直接的制度移植,政治发展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的“现代化”,就是实现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与法律制度。“传统”被看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要么把它抛弃、踢开,要么把它搅碎、重组,融进西化的洪流之中。就在西方思想家不忘反省其社会中的理性主义政治之弊端的时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固执地接受西方现代性的普世逻辑,在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忘记了中国自身的主体性建构,在盲目的知识引进中失落了自己的独立品格*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对“中国法学”所作的批判与检讨,也适用于“中国政治学”。参见邓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早年殷海光先生曾经给自由主义者归纳了六个特征:抨孔;提倡科学;追求民主;好尚自由;倾向进步;用白话文。张汝伦认为这与奥克肖特所归纳的理性主义者的特征有着“明显的家族相似”[6]。吊诡的是,奥克肖特批判的理性主义者“唯理性至上”,以“理性”来反对和剔除“传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则是直接把西方的历史经验或现代性价值作为标尺,用它来衡量和排挤中国自己的“传统”。奥克肖特批判理性主义政治却从未否认“理性”的作用,中国自由主义者追逐“理性”却在一定程度上连“理性”的边都懒得去挨。奥克肖特讲:“政治是参加一群人的一般安排的活动”,之所以是“参加安排”,而不是“做安排”,是因为“该活动决不是一块蕴含无限可能性的空白之地。任何一代,即便是最革命的一代,他们已然享有的安排总是远远超过那些人们认为需要做出的安排”[2]112。就此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倒真该倾听一下奥克肖特的政治灼见:“在政治上,每件事情都是作为结果发生的事情,都是追求,但不是追求梦想或一般原则,而是追求一种暗示(intimation)。”[2]113
如果说自由主义者以“传统-现代”范式作为前提,心甘情愿承纳 “现代”而拒斥“传统”,那么,与之相反,以儒学复兴为己任的当代新儒家则是力图回归“传统”,返古开新。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有的东西,比如自由民主、分权制衡,我们的传统也有,或者说即便传统中没有,老“内圣”也可以开出新“外王”;西方没有的东西,比如天人合一、忠恕之道,我们世代传承,可以弥补西方政治文明的缺陷与不足。儒家的基本精神非但与西方的现代政治文明不相冲突,倒是可以在相互对话中创构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儒家文明新样态。且不说新儒家将中国之传统仅仅局限于儒学一家有以偏概全之嫌,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儒家试图摆脱西方的现代性话语,但他们将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嫁接的做法,实际上已经隐然接受了西方现代性的逻辑前提:虽然只有西方的宗教伦理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本身却是普世的[7]。由此,新儒家强调中国的“传统”,强调自己国情与文化的特殊性,但最终仍不得不首先接受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价值的普世性,再试图于“传统”中开释出“现代”价值。换言之,新儒家貌似与自由主义南辕北辙,实则思考的路向是一样的。
在一些学者看来,对西方现代性的主动(如自由主义)或者被动的(如新儒家)迎合,结果都是深化而不可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与殖民化运动的扩张与宰制。中国要摆脱这种西方现代性的宰制,就要发掘出未被“现代”所束缚的文化价值与精神资源。蒋庆觉察到“当代新儒家有‘变相西化’之嫌,当代儒学则有沦为‘西学附庸’之虞”,提出要重构“政治儒学”,以扭转对儒学的“诸多误解与歪曲”[8]。有汉学家断定儒教已经“博物馆化”,只不过是一具仅供观赏凭吊的文物[9]。蒋庆则明确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主张“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实现“政教合一”。蒋庆一方面将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为批判对象,断然否定政治儒学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相通性;另一方面,他所提出的“儒教议会三院制”却明显脱胎于西方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思想,与儒家的圣王理想实在相去甚远[10]。晚近“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围绕牟宗三与康有为、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儒学与现代性、儒教文明与核心国家、国家国族建构与儒学实践等主题争议不断,呈现出两岸学者对当代中国问题的不同理解以及对未来出路的不同期待*2016年1月,在成都杜甫草堂举办了“两岸新儒家会讲”,陈明、李明辉等两岸儒学代表人物同堂切磋,却远未达成共识。会讲内容参见《天府新论》2016年第2期。。将儒学简单区分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分别贴上“港台”和“大陆”的地域标签,并高举所谓“大陆新儒家”旗帜的做法,实际上是将“道统”与“政统”相切割,已然偏离儒家的思想传统,囿于门户之见而阻滞了对于中国社会的共同关切与介入。
另有学者以中国崛起为背景,以古代中国对世界的“天下主义”想象依托,利用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天下”观重构中国的历史脉络与内外秩序,断言这种“新天下主义”是“一种来自于古代传统、又重新加以现代性解释的轴心文明智慧”,是适合全人类的普世文明[11]。赵汀阳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就是仿效和构建西方模式的民族国家,忘记了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与政治经验。在他看来,西方政治哲学的立足点是个人,主要考虑如何界定和维护个人权利,在这个基础上建构的民族国家则强调主权的绝对和神圣不可侵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有明确的边界,互为“异己”,西方政治哲学的弊端就是只有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缺乏一种政治意义上的“世界理论”来化解和消弥“主体间”的诸多问题与冲突,没有形成一种以世界利益为重的政治世界观。与西方的政治思路不同,中国政治是从世界问题开始的,这种思路就是周朝开创的“天下”政治观,“天下”是一个“自然地理、社会心理和政治制度三者合一的‘世界’,是一个饱满的世界概念”。天下理论包含的“天下-国-家”的政治秩序与“家-国-天下”的道德伦理互为论证,“天下之家容纳一切,再无外人,每人每家每国都变成天下之家的内部成员,天下成为所有人的利益共同体,天下之公(共同利益)有利于每个人之私(个人利益),两种的一致性成为可能”[12]。赵汀阳自信“所有的政治问题,无论是世界政治、国际政治还是国家政治,都可以在天下理论的框架内统一的分析”,然而,他却没有对周之后天下体系的崩溃这个事实做出合理的辩护,也未正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王朝体系在同西方民族国家遭遇时一路败退的糟糕现实。
三、中国道路的实践特质与理性期待
当我们思考“中国问题”的政治方案抑或中国道路该往何处去时,面对时下充满分歧与争议的思想主张,如何寻得并持守一种中道和平衡的政治观念,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转圜取舍而不走向极端?奥克肖特可以在《庄子》中发现一个现代西方政治所忽视的诗意的世界,我们也可以通过阅读奥克肖特,于其中体验到另一种或许迥异却不无启发的政治景观。奥克肖特的著作多处引用中国典籍,其代表作《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对《庄子》的引用多达五次。本文将奥克肖特的三处引文呈现出来,直接的因由是为了加深对奥克肖特思想本身的理解,同时也重温和感受中国经典穿越历史的力道,更为深切的关怀则是:奥克肖特与庄子的隔空相遇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中国政治有何裨益?
如上所述,自由主义者主张拥抱“现代”,舍弃“传统”,新儒家主张拒斥“西方”,回归“中国”。如果说以蒋庆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其政治理想是以传统中的政治儒学抗拒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的话,赵汀阳等“新天下主义”者则是发掘传统中的敞开、和谐的天下观以化解和容纳西方封闭、冲突的国家观。他们都注意到了西方现代政治存在的诸多问题,认为中国不能对西方亦步亦趋,而是要走一条本属于自己却同样具有普世性的“中国道路”。这种政治思考本身是有意义的,至少他们不迷信某种政治模式可以作为样板来模仿和移植。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传统,却把传统看作是保存在“过去”的特殊礼物,并且只截取了传统中的某一个面相,将之判定为具有正当性与普遍性:虽然我们经历了失败,但我们的东西确实比西方的好,值得别人“自愿来学”*蒋庆相信“王道通三”、“政教合一”能够摆脱西方民主“多数人暴政”的困境,赵汀阳断定“无论天下体系还存在什么尚未克服的技术性问题,它仍然是一种最具有潜力的政治理想”,这是当前中国思想界比较有代表性的“回归传统”的两种思考路向,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确实过于“自信”了。。对此,奥克肖特对传统的解释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传统是“稳定的,因为它虽然运动,却不是完全运动;它平静,却不是完全静止。任何属于它的东西不会完全消失;我们总是会转回去,从它甚至最久远的时刻恢复某些东西,并使之成为当下话题”,然而,关键的是“没什么能长期不变”[2]128。奥克肖特将人类活动理解为过去、现在与未来都融入其中的“对话”,传统将三者合而为一,它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客观存在,而是不断变化的具体实践过程。传统是一个开放的传承、接纳与创新系统,奥克肖特视野中的传统,实质上就是“当下”。同时,传统首先是一种行为传统,它是人类在面对无数的偶然状况时逐渐累积起来的实践经验,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必然的、叫做“传统”的东西摆放在那儿,等着人们去瞻仰或者取用。因此,传统即为实践,既无法舍弃,也无所谓回归。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对传统的追寻始终“在路上”。
正是在此意义上,奥克肖特反省西方现代政治的理性主义迷思时,敏锐地注意到了《庄子》中的“轮扁斫轮”。郭象曾对《庄子》此节如此作注:“古不在今,今事已变,故绝学任性,与时变化,而后至焉。”[13]辩证地看,“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对立的两个极端,“中国”与“西方”同样不是。面对“中国问题”,中国思想界的政治思考将焦点投射到“西方”或“传统”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当下中国活生生的政治现实。当日严复讲,“今日政治惟一要义,其对外能强,其对内能治,所用方法,则皆其次”。在特殊的处境中,有用的就是正当的,所以严复要为袁世凯复辟帝制辩护[14]。而至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军事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一个崭新的正当性根基已然树立,那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以“人民”为轴心,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追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既是一个规范性的政治理想,也是一个实实在在进行着的政治实践过程,并且已经化作“中国传统”之不可剥离的重要内容。
当下中国所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路。这里的“中国”既不能建构为某个西方国家的翻版,也不能大而化之地构想为所谓的“圣王”之国或者“天下”;这里的“特色”也不是“西方普遍主义道路的特殊化落实”,从而“悄无声息地深化与加剧”西方中心主义[15],而是立足于自我的继承以及同他者的比较和借鉴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政治文明之道。在当下的中国,拘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固然不当,然而,把“民族”与“国家”弃若敝履,似是而非地地讲“中国在上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格局”[16],或者奢谈“走向绝对的精神,而非西方或中国的精神”[17]。即便出于真诚的愿望而非有意的误导,这样的论调也不免有失公允:它对于百余年来中华民族谋生存、求发展的苦难与奋斗历程,对于好不容易达到的国家安定繁荣与人民生活极大改善的历史事实缺乏一种“同情之理解”。
质言之,纵然政治现实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否认或者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视而不见,试图证明中国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在别处”,将其生硬地比附为“西方”或者我们古老的“传统”中早就有了的东西,都难免失之偏颇。事实上,西方有西方的问题,譬如奥克肖特所言之理性主义政治的病理,因此,奥克肖特希望政治知识的传习与政治实践的展开沿袭保守的倾向或气质,有如《庄子·田子方》中的钓鱼者“聊以寄此逍遥”而无所求。然而,政府的“有为”与“无为”哪能如此泾渭分明;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譬如对个体自由的长期忽视与压制,虽然奥克肖特在《论人类行为》中所构想的“公民联合体”几近于《庄子》中“相忘于江湖”的自由之境,但回溯中国历史,自由的理想与不自由的现实之间反差如此之大,庄子思想虽不曾消失,但何曾主导过中国的政治实践。就此而言,在中国语境中阅读奥克肖特,回望奥克肖特笔下的《庄子》,目的并不在于参照奥氏的政治理论去塑造一套中国版的政治现代化方案,更不是弃置参与政治生活的责任伦理而醉心于“逍遥游”,而在于捕捉奥氏与庄子相遇时擦出的火花,学习他理解现代政治时的那种看似消极实则积极、看似平淡无奇实则直指要害的怀疑态度与批判精神。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合理期待是:一方面,我们要走出对西方现代政治的迷恋与崇拜;另一方面,切不可把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政治文明的批判性思考视为对东方文化的服膺,满目皆是西方世界的弊病而忘记了自己曾经的黑暗与蒙昧。换言之,沉迷于西方现代性的浪漫幻象,试图从西人那里寻找某种普适“模式”,或为令人神往的诗意中国所吸引,苦心从古人那里撷取某种“传统”,诚意与勇气固然可嘉,但若脱离鲜活的政治现实,且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则有可能南辕北辙,恰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该成为何物的种种错误意识。”[18]或许,更难堪的境地是:身受“错误意识”的牵引,不知批判与自省,却沉溺于自欺欺人。
[1]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M].何刚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3.
[2]MICHAEL 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M].London:Methuen & Co.Ltd,1962.
[3]MICHAEL OAKESHOTT.Hobbes on civil association[M].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75.
[4]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90.
[5]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
[6]张汝伦.奥克肖特和中国自由主义[M]∥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7]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8]蒋庆.政治儒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3.
[9]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37-343.
[10]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J].中国儒教研究通讯,2005(1).
[11]许纪霖.新天下主义:重建中国的内外秩序[M]//中国知识分子论丛:第1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2]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76-124.
[13]郭象.庄子注疏[M].成玄英,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266.
[14]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51.
[15]陈赟.现时代的精神生活[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120.
[16]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N].21世纪经济报道,2003-12-29.
[17]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5.
Oakeshott,Zhuang-Tzu and “the Problem of China”—On the Quotations from Zhuang-Tzu in Oakeshott’s Writings
Zhao Miao
In his profound writing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Oakeshott cited the ancient classics of China especially “Chuang Tzu” many times while he considered the pathology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s.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a few quotations from Zhuang-Tzu in Oakeshott’s writings,on one hand to understand Oakeshott and Chuang Tzu more thoroughly,on the other had,it is more important to help confront “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Through analyzing current trends of domestic political thoughts and backtracking the political tradition of China in 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a moderate and balanced “Chinese Way” is worth pursuing in mutual comparison and interpre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or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Oakeshott;Zhuang-Tzu;modernity;the problem of China
赵淼,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教授、博士。
D091;D092;D61
ADoi:10.3969/j.issn.2095-042X.2016.04.001
2016-06-20;责任编辑:朱世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