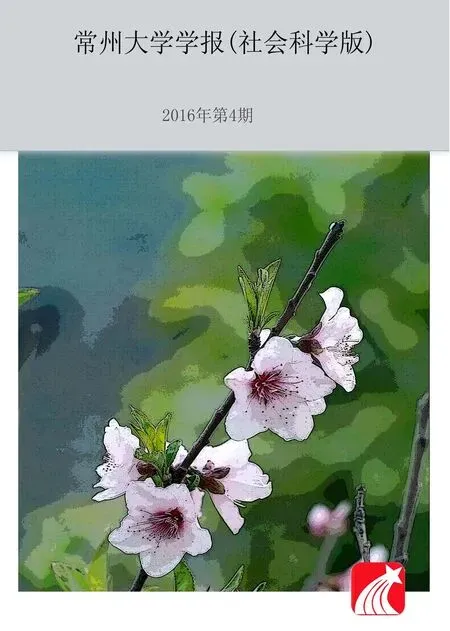城管综合执法的治理转型
高国梁,周京中
城管综合执法的治理转型
高国梁,周京中
城管综合执法改革已经成为新时期国家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传统的管制思维对于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制度设计、体制安排和执法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这种管制思维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城市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的需要,现行的城管综合执法制度也陷入诸病缠身、进退失据的窘境。要摆脱这种窘境,首先要实现从管制思维向治理理念的转型,树立城管综合执法中的多主体合作共治的理念、多元价值和利益平衡的理念、依法行政和正当程序的理念。同时,要在治理理念的指导下实现城管综合执法的制度创新,主要包括管理体制的法定化与协调化、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职能的社会化、执法程序的规范化与裁量标准的明细化。
城管综合执法; 管制思维;治理理念; 制度创新
我国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制度经过近二十年的试验和推行,在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始终伴随着各种质疑和指责,在社会关系重大变迁和国家治理方式转型的背景下,传统的城管执法理念和执法模式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挑战,为此亟待对其进行理念反思和制度创新。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公报中关于“推进综合执法,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的决定为这种反思和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管制思维之下的城管综合执法困境
我国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在法律上的源起是1996年《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授权,此后以1997年北京市宣武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改革为开端,逐渐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城市普遍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实践,这些实践缓解了我国过去在城市管理中存在的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冲突和执法扰民的乱象,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集中统一地行使多项行政执法权,提高了执法效率,较为有效地维护了城市社会经济秩序,满足了民众基本的秩序需求。而城市经济社会事务的快速发展和高度复杂化,以及社会利益关系的日益多元化也给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带来了重大挑战。为了应对管理事务日益增多的挑战,各地也赋予了城管机构越来越多的管理和执法权限,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三百多种。管理和执法权限的膨胀也伴随着机构和人员的膨胀,很多城市为弥补人员和经费的不足,开始招收大量临时工进入城管队伍。但人员、机构和权限的膨胀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执法效果的提高,反而引发了众多的城管人员野蛮执法、暴力执法、执法腐败等事件,有的事件给执法相对人带来人身、财产的重大损害,甚至引发暴力反抗和群体性事件,给社会带来极为负面的观感,并引起了人们对于城管制度本身正当性的反思和质疑。*如2013年在湖南临武发生的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用秤砣打死瓜农邓正加,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死者的极大同情,以及对执法人员的极大愤慨和对城管制度的广泛质疑。这些质疑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城管综合执法制度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方面:先天不足主要体现在该制度的法律依据不足,职权界限模糊、运行程序及裁量标准缺失等方面,而后天失调主要体现在城管部门的管理和协调机制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不足以及城管人员的法律素养不高、执法能力低下等方面。
这些问题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提出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进综合执法,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加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建设,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这些决定的出台有望进一步推动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制度的改革。但是在改革不应仅仅局限于对具体法律条文的修改,而应站在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角度,反思城管制度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并在新的现代国家治理理念的指导下完成城管综合执法制度的改革与转型。
我国城管综合执法制度之所以出现一系列问题,并被人们广泛诟病,固然有着诸如制度、体制、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原因,但如果从现代治理理念的角度来反思,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的管制思维对于制度设计、体制安排和执法活动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这种管制思维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城市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的需要,使得现行的城管综合执法制度也陷入诸病缠身、进退失据的窘境。所以要反思和改革城管制度,首先须对城市管理的管制思维进行反思。
具体而言,城市管理中的管制思维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在城市管理的价值取向上重秩序、轻权利。管制思维延续了我国传统的等级秩序和计划经济的惯性,把维护城市市容市貌整洁、交通秩序通畅和官方命令的权威性等秩序性价值看作最高追求。在这些秩序性追求的背后难免会夹杂着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等因素的考量,为此城管机构往往把流动商贩、强拆对象等视为捣乱或破坏分子,忽视这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财产权甚至人身权,倾向于采取强力手段维护管理秩序。其次,在对城市管理的主体和依靠力量的认识上重官方、轻民间。 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强政府-弱社会”格局,也型塑了管制性思维的认知惯性。在这种思维之下,政府被视为管理城市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唯一中心,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而民众和各类社会组织仅仅被视为管理的对象和客体,被排斥在管理和参与的渠道之外,知情和参与的权利难以得到实现,对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监督和制约更是无从谈起。再次,在城市管理的执法依据上重长官意志、轻法律规则。由于城管综合执法的法律依据存在着“先天不足”,其职权范围、权力行使程序及执法裁量标准缺乏法律法规的明确规范和有效制约,而更多受到地方政府和长官意志的左右,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在地方政府和官员追求政绩的驱动下,可以轻易地突破法律底线,侵犯到民众的权利。最后,在城市管理执法方式上重强制执行、轻说服教育。基于管理理念的偏差、权力的傲慢及对管制效率的追求,一些城管机构在执法中往往没有耐心去与执法对象进行平等的沟通协商和说服教育,而是偏好和沉迷于简单粗暴的高压和暴力手段,使城管人员成为执法对象的“天敌”和恐惧逃避的对象。
管制思维支配下的城管综合执法活动引发了一系列消极后果。首先是造成了大量的民众人身权、财产权和生存权利受到侵犯,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官民冲突。暴力执法会激起执法对象的反弹和反抗,酿成一些导致执法对象和城管人员死伤的悲剧性事件,其中著名的事件有2013年发生的湖南临武城管执法人员打死瓜农事件、2006年发生的北京小贩崔英杰刺死城管执法人员李志强事件、2009年发生的沈阳小贩夏俊峰刺死两名城管队员的事件等。有些暴力执法事件甚至使更多的社会群体卷入其中,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会严重威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即使暴力事件没有发生,但城管的秩序通过强力方式得以维持,在这种零和博弈的管制方式下,一些弱势群体的生存权还是受到了抑制或牺牲,这为其他领域的社会矛盾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其次,城管执法中的法律资源不足和权力意志膨胀会导致管理权力的寻租和滥用,破坏法治秩序。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法律制约的乏力为城管的权力腐败提供了便利。近年来已经有部分地区爆出城管官员因向管理对象收受贿赂而被查处的丑闻,这些也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另外城管权力边界的模糊、执法程序和裁量标准的缺位也为地方政府采取一些法外举措提供了便利,影响依法行政的实现。最后,过度依赖政府的力量和资源进行城市管理和执法活动,一方面会导致城管机构职权和人员膨胀,执法人员素质难以保障,并加大财政的负担;另一方面政府管理和执法活动难以完全贴近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实际,难以实现与民众多元化需求有效对接,也难以及时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关系,造成执法资源浪费和执法效果不佳。
这些问题说明,管制思维支配下的城管综合执法活动与城市管理事务日益丰富和复杂、民众的权利意识觉醒,以及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的现实格格不入,也与我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大趋势背道而驰,亟需实现治理理念的转型和治理制度的重构。
二、城管综合执法中的治理理念转型
管制思维支配下的城管综合执法活动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已经难以为继,而从西方兴起并为我国所引进和借鉴的治理理论,可以为城管综合执法走出管制思维的束缚并形成新的城市治理理念提供一定的启发和指导。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并逐渐向全球扩展的治理理念的核心就是要摆脱国家作为公共治理的唯一中心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对抗关系的传统做法,更多地强调多元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和民主协商的治理方式。“治理是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1]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从国家层面推动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转型,试图摆脱传统的统治思维和维稳思维,并向着国际主流的现代化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迈进。“从统治、管理到治理,言辞微变之下涌动的,是一场国家、社会公民从着眼于对立对抗到侧重于交互联动再到致力于合作共赢善治的思想革命;是一次政府、市场、社会从配置的结构性变化引发现实的功能性变化再到最终的主体性变化的国家实验;是一个改革、发展、稳定从避免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严格限缩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再到追求和谐互惠的正和博弈的伟大尝试。”[2]城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需要在新的国家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完成城市治理理念的转型。具体到城管综合执法制度改革,在新的形势下,应确立以下基本的理念:
(一)多主体合作共治的理念
城管机构一家独专和强力执法的逻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已经显得格格不入和处处碰壁,“那种压制或是消灭异己的野蛮手段根本行不通,代之而起的是和解的和合作的逻辑,是不同见解、不同利益、不同群体多元共存的逻辑。”[3]城管综合执法涉及到多项行政法律法规的执行和多项行政管理权力的行使,同时也涉及多方社会主体的切身利害关系,如果没有其他行政机关的配合和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城管部门不仅面临着执法资源不足的严重制约,也影响到了执法效果的实效性及其与社会多元需求的契合性。在新的治理理念下,城管执法应将相关的行政机关、社会公益组织、执法对象及其他利益相关群体都纳入治理的主体范围,并与这些主体形成良性的合作共治关系。由于城管执法体制尚未理顺,城管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在条块之间的协调配合不到位,出现了在违建执法等领域的“孤岛现象”,“条条关系中的孤岛现象,反映了违建执法手段的综合化需求与执法机构单一化职能之间的矛盾,而条块关系中的孤岛现象,则反映了执法体系末端的无力,以及执法职能在最基层的缺位。”[4]为此,城管机构需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协调与配合。城管综合执法中同时应充分发挥社会公益组织和自治组织的协同治理作用,以弥补城管部门执法资源的不足,同时发挥这些民间组织对执法对象在需求掌握、意见沟通和日常监督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把部分监督和服务的职能通过契约化的机制转移给这些民间组织,在提高监督和服务效率的同时保持对民间组织法律上的最终控制权。在管理规范的制定、管理区域的分类设置、利益冲突的协调、执法行为的配合等方面与相关主体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平等的协商,以便凝聚共识,达成互信,争取相关主体的理解、支持与配合,这样就会为减少执法活动中的冲突和对抗、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的城市社会关系提供有利条件。
(二)多元价值和利益平衡的理念
城市管理活动中涉及到多元的价值选择及利益冲突的关系。城管执法机构往往把执行法律法规和上级指令、维护城市的市容环境和交通秩序等秩序性价值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并通过城管执法活动尽量满足上级领导和部门的各种考核指标和政绩要求,即使不能获得晋升,最起码也能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城管的执法对象往往是在经济和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可能缺乏有竞争力的生存就业手段和能力,也无力在正规的店铺从事经营活动,只能通过摆摊设点、流动贩卖等手段维持生计。当城管人员通过暴力强制执法没收了这些社会成员的商品和工具、损害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安全时,不仅使他们的财产和人身权利受到侵犯,也威胁到他们基本的生存权利,所以很容易激起他们的暴力反抗。当然也有部分执法对象并不存在生计之忧,但想通过一些违规行为谋取不当利益,这又另当别论。而城市居民一方面可能会从一些流动商贩等执法对象那里获得相对廉价和便利的生活服务,另一方面又可能受到交通不畅、噪音扰民、环境脏乱、食品安全等问题的困扰。所以城管综合执法中存在着城市管理秩序与执法对象之间的权利自由的冲突,也存在着城市居民与城管机构之间、城市居民与流动摊贩等执法对象之间的利益冲突。城管执法机构应树立基本权利高于秩序的理念,尊重和平衡多元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在维持基本的城市管理秩序的同时,充分尊重执法对象的各项基本权利,兼顾市民生活便利的需要,与其他政府机构共同规划和制定出兼顾多方利益管理方案,才能取得良好的执法效果。
(三)依法行政和正当程序的理念
法律制度是行政管理机关执法活动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多元利益主体进行合作和博弈的重要基点。只有在相关法律对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职责权限进行了公平合理和清晰明确的界定,且法律能够得到严格和稳定的执行时,国家治理的相关参与主体才能够对彼此的行为选择形成明确的预期,从而进行更好的合作治理。法律制度也是规范和约束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保护民众各项基本权利,以及防止公权力暴虐和滥权的重要手段。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大背景下,城管机构摒弃人治思维,确立严格依法行政的理念,对于重塑政府形象、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形成城管执法多元主体共治格局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城管机构所行使的职权众多,法律授权粗疏,裁量标准模糊不清,又随时面临着执法现场中各种复杂多变的特殊情势,想要通过事先的实体法规则进行规范与约束难度很大,所以树立正当程序理念,通过正当的执法程序来规范城管机关的执法行为就具有重要作用。正当的执法程序可以让执法对象有较为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申诉抗辩权,让民众感受到城管执法中的“看得见的正义”,既可以对城管执法机关形成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也有利于双方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达成谅解和共识,减少执法阻力和成本,提高执法效率。
三、城管综合执法中的治理制度创新
(一)管理体制的法定化与协调化
由于目前的城管管理体制是由《行政处罚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工作的决定》等少数几个法律文件通过笼统而粗疏的法律授权形成的,城管机构的上位法依据并不充分,具体行使哪些权力由各地方立法甚至长官意志自行决定,有较大的随意性,且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职权界限模糊,也缺少一个统一的协调和实施机制,致使城管部门在执法中出现了条块关系中的“孤岛现象”。这些现象既违背了职权法定、依法行政等法治原则,也不利与各部门形成合力进行协调高效的执法,造成了执法资源的损耗和执法效果的打折,因此实现城管管理体制的法定化和协调化成为当务之急。有必要制定一部全国性的法律,对城管机构的法律定位、职责权限、执法程序、国家主管机关及协调机构等予以明确,使城管执法中的法律依据不足和职权冲突的问题在更高的层面得到解决。同时考虑到目前的城管机构职权过于庞杂以及执法专业化的需要,可以把一部分专业性较强的职权分离出来,由其他专业执法部门行使,以减少城管机构的负担及滥权的可能性。因中国各地城市的发展状况差异很大,全国性的立法可以为地方的探索和改革留下一定的空间,但地方的城管改革方案也必须是建立在立法先行的基础之上。《立法法》的新修订赋予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权限包括了“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这些事项不同程度上都与城管的职权有一定的关联,这就为地方城管制度改革的法治化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职能的社会化
实现城管综合执法多元主体共治最主要是如何有效地吸纳社会主体的参与。目前社会主体的参与除了受制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外,参与渠道狭窄、参与机制缺乏法律保障也是重要障碍,民众难以获得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各类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源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利用。为此,可借鉴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通过地方立法设定城市管理规范制定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和民众参与程序。政府部门在制定城区规划方案和城管执法规范时应借助于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各种媒体进行充分的信息公开,广泛地征求民众意见,必要时可以组织听证会和专家论证会,以便形成反映城市多元利益主体普遍共识的管理规范,并对各方的意见要给予及时的反馈以接受社会的监督,这样就有利于民众形成对城管执法方案的认同、接受和自愿配合。同时探索部分城管职能社会化的途径,培育和孵化一些社会组织协助执法部门从事一些日常的管理、服务和监督活动。城管部门通过招标、采购、委托等方式与这些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让它们提供更为便捷和高效的服务。同时可以通过追究违约责任、解除合作关系等法律手段防控社会组织的违约或违规行为。对于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项,也可以由城管部门与社区居委会建立合作关系,让其分担部分日常管理职能。对于相同类型的执法对象,如流动摊贩等,也可以引导他们建立诸如流动摊贩联盟等自治性组织,便于其行使自治、自律以及与政府部门博弈互动等职能。“流动摊贩联盟不仅是实现摊贩自我管理的重要形式和载体,作为自治组织,它也是流动摊贩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参与方,代表摊贩们利益与其他参与者进行谈判、沟通、合作。流动摊贩组织起来,有利于摆脱个人被边缘化的境地, 加强自己维权和参与治理的能力。”[5]
(三)执法程序的规范化与裁量标准的明细化
城管综合执法虽然有一些基本的程序法和实体法可以作为依据,但是给执法人员留下了较大的选择和裁量空间。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场状况和对立情绪严重的执法对象,如何在依法行使职权的同时做到避免矛盾激化,争取执法对象的理解和配合,公平对待每个当事人,裁量不畸轻畸重,并把对执法对象损害的降低到最低限度,这些仅仅靠粗线条的法律是难以做到的。为此,需要通过城管机构及有关主管部门在总结执法经验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多方意见,在不违反上位法的前提下制定有利于执法程序规范化与裁量标准明细化的管理规范或内部操作规则。这些规则虽然不具有直接的外部法律效力,但通过规范和约束执法人员的行为而产生相应的外部效应。一般而言,在制定程序性规则时,要充分尊重执法对象的人身权、财产权、知情权、参与权、申诉和抗辩权,优先使用沟通和说服教育的方式,严格限制强制措施的适用情形和适用等级,严禁非法的暴力执法。在行政机关的内部考核中,应把文明执法、规范执法、无暴力冲突事件等列为重要的指标。在细化裁量标准时,应注意遵循平等对待和比例原则,要统一执法标准,减少执法人员任意裁量的空间,同时让执法对象得到合法合理及人性化的对待。这些原则和标准会对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提出较大的挑战,而在大量临时聘用人员担任城管执法任务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为此需要在优化执法人员的结构和素质、加强教育培训以及提高执法人员工作待遇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进。
[1]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
[2]江必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光明日报,2013-11-15(A01).
[3]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1.
[4]陈柏峰.城镇规划区违建执法困境及其解释——国家能力的视角[J].法学研究,2015(1):28.
[5]张国平,章灿钢.城市流动摊贩管理: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实现条件[J].晋阳学刊,2008(5):54.
The Governance Transition of Comprehensive LawEnforcement in Urban Administration
Gao Guoliang,Zhou Jingzhong
The reformation of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 in urban administr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reformation in the new period, but the traditional control thinking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and restrict to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 in urban administration in the aspects of system desig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 the control thinking increasingly cannot adapt to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leg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ties, and has made the current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 in urban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the disease -ridden, equally difficult to go on or retreat dilemma. To get rid of this dilemma, first of all, we shoul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ontrol thinking to the conception of governance, and establish the conceptions of multi-agent cooperation, multi-value and interests balance, law-based administration and due process in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 in urban administr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system innovation of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 in urban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mainly including legal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management system, diversification of participating subject and socialization of management functions, standardization of law enforcement procedure and the detail of discretion standard.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 in urban administration; control thinking; concep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innovation
高国梁,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周京中,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副庭长。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710048);常州大学青年发展基金项目(2014QN04)。
DF31
ADoi:10.3969/j.issn.2095-042X.2016.04.004
2015-12-10;责任编辑:朱世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