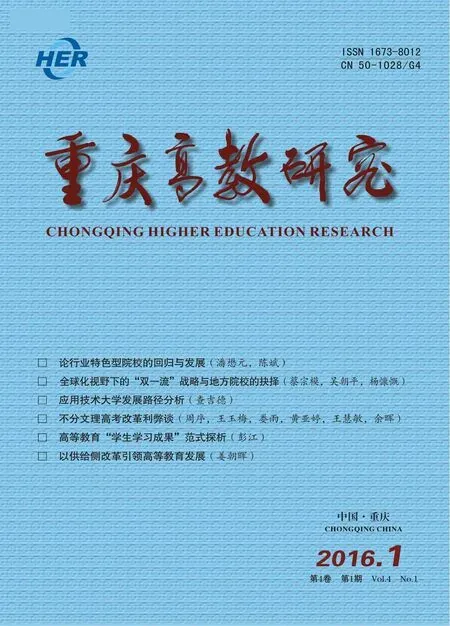宋代重庆书院探析
吴洪成,王培培,王亚平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 西部高教论坛
宋代重庆书院探析
吴洪成,王培培,王亚平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宋代重庆有14所书院,宋代重庆书院具有多种特点:一是发展处于全国书院的前列;二是时间和地域分布不均,北宋书院较少而南宋书院较多,且集中分布在重庆周边沿长江流域地区;三是以官办书院为主。分析宋代重庆书院的教学和管理,可以发现:在教学目的方面,宋代重庆书院的教学旨在探究学问,为传播理学思想而培养人才,教学目的中强调“学而致用”;在教学内容方面,多以理学思想为指导来制订教学计划和安排教学内容,注重理学的传承与发展,但兼涉文史学科知识及其他学派思想;在教学方法方面,提倡“教学相长”的自由教学,以讲授法为主,辅以讨论法和自学,并适时采取“论辩问难”的教学方法;在师生关系方面,受到书院聘任的教师特别注重身教,以“人师”自勉自任,注重口传身教、人格垂范、精神感化、情怀熏陶,学习氛围开放、宽松、活跃,师生间的关系亲近和谐、民主平等;在教学管理方面,主要实行学业水平考试的考课制度;在办学经费方面,宋代重庆书院开创了一种官办民助的办学与管理模式,既克服了官办书院的层层束缚,又解决了民办书院办学经费不足的桎梏。宋代重庆书院有研究性办学、主体性教育的新理念,对现代教育教学仍有重要启示:一是师生淡泊名利的思想,对于转变当前教育界“重名利、轻学术”的错误认识,积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有重要启示;二是选聘教师以“择优而教”为主要标准值得现代教育关注;三是“教学相长”的自由教学理念以及和谐的师生关系与现代教育观念不谋而合。
关键词:宋代;重庆;书院教育;北岩书院;理学
作为一座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源地。隋文帝时设置了渝州,重庆的简称“渝”即由此而来。
宋初沿袭隋唐时期的行政区划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十道,重庆处于剑南道夔州都督府辖区。至道三年(997)废道置路,将全国划分为十五路,重庆属夔州路管辖。道与路,类似于现在的省。之后,宋代的路制行政区域多次变动,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合称为“川峡四路”,即“四川路”。至此,宋代重庆明确隶属于四川的行政辖区内。本文所探析的宋代重庆书院,其地理位置与行政范围不局限于两宋时期重庆府的管辖范围,而是以1997年重庆直辖市所属的区县为准。具体而言,除了直辖以前的重庆区县外,还包括涪陵、黔江、万县(现万州)地区。重庆一名始于宋,有“双重喜庆”之意,赋予了重庆以吉祥、美满的喜庆荣光。而考诸教育历史,唐末五代书院萌芽,北宋以讲学为主的书院日渐增多,南宋理学的发展促使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两者真可谓天缘巧合,不期而遇。
宋朝(960—1279)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重要王朝,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正是在宋代特定的社会场域制约下,重庆书院拉开了历史帷幕,并上演了精彩的剧目。首先,宋王朝由唐末五代战乱、兵戈不宁的离乱时期重新走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社会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政府崇尚儒术科举,加强文官政治以及书画人文艺术的建设,同时重视民间办学,这些都为书院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契机。重庆也在宋代进入区域历史的第一个高峰。自唐末以后,四川的社会经济逐渐往川东三峡地区转移,无论是农业、商业以及手工业的部门经济走向,还是在贸易流通与资本市场方面,均呈现出兴盛活跃的景象。其次,北宋王朝立国之初,国力未振,官学重创,学校荒废,学者缺乏适当的求学之所,加之崇文教、抑武备的教育政策逐渐确立,士人乃至官宦继承唐末五代“读书山林”风习,而开办书院来满足世人读书求学的需要。再次,受佛教禅林的影响,唐末五代,士儒效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择胜地而立精舍”,宣讲授徒,书院应运而生。重庆依山傍水、幽静清雅,自然吸引了大批名流智者来此创办书院,教书育人。最后,印刷业的进步有效地刺激了书院办学活动的开展。宋代的四川、重庆有“人文之盛,莫胜于蜀”之称,其文化事业兴盛繁荣促进了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蜀地的布头笺、麻纸、竹纸等都闻名于世,这些都促进了书院的教育活动。宋代重庆书院勃兴,并在教学、组织和管理方面带有鲜明特点,这就赋予了本选题的独特意义。
一、宋代重庆书院概述
宋代重庆先后建有14所书院,分别为:五举书院、南山经堂(书院)、五峰书院、静晖书院、北岩书院、庹子书院、凤山书院、瑞应山房(濂溪书院、合宗书院)、竹林书院、南阳书院、少陵书院、宏文书院、龙门书院、五桂楼书院。相对于近邻四川在唐末出现的遂宁张九宗书院而言,重庆具有讲学育才性质的书院是在北宋发展起来的,南宋书院建制较为完备。各所书院具体的创办时间、地点、创办人以及书院性质等信息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宋代重庆书院具有多种特点:

表1 宋代重庆书院一览表[1]10

续表
(一)处于全国书院发展的前列
从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元年(960)立国至宋帝昺祥兴二年(1278)终止,宋代统治共历318年。3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重庆出现了14所书院。乍一看数量,或许会嫌其并不出众,但如果考虑重庆的区域范围,并与全国的整体状况相比较,就不能不让我们为之动容或感到惊讶了。如表2[2]354-355所示,宋代四川书院共计31所,数量排名全国第6,名列前茅。其中宋代重庆书院为14所,约占当时四川全境书院数量的一半,而所辖区域的面积仅为四川的四分之一左右。由此可知,宋代重庆书院处于全国书院发展的前列。

表2 宋代全国书院分布状况一览表(共711所)
注:表中四川省含重庆在内。
(二)时空分布不均衡
1.从建立时间看,北宋书院较少,南宋书院居多
在书院的发展史上,北宋虽有6大书院的建设,但就其数量及社会影响力而言,终究是有限的。由于理学是南宋确立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理学家主讲书院,并推动书院的兴建。理学大师朱熹、张栻、陆九渊与吕祖谦等均主讲书院,成为著名的书院教育家。由此,理学的教育、祭祀、藏书等思想文化都印刻在书院机构中,在书院的运行中扮演着功能角色。一时之间书院的学术水平攀升,教育质量提高,社会影响加大,且这三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也就是数理测评中的正相关,由此造就了第一次书院高潮。在重庆14所宋代书院中,除少陵书院、龙门书院、五桂楼书院的创建时间无法判断属于南宋还是北宋外,其余11所书院中,江津五举书院、南山经堂和五峰书院为北宋建立,其他8所书院皆于南宋时期创建。
南宋重庆书院的复兴和发达,与朱熹重振白鹿洞书院有着密切的联系。朱熹于1179年修复江西星子县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亲订《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天下书院共同参照的章程,其后20余年各地大兴书院,重庆亦然。从创办于宋孝宗年间(1163—1189)的静晖书院到创办于咸淳年间的宏文书院,期间经历了约百年的岁月,直到南宋,重庆书院才开始形成制度并达到一定规模[1]82-83。从中得知,书院教育制度在重庆从生根发芽到抽枝散叶,这一历程是艰辛曲折的,同时也昭示出其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2.从地理分布看,集中分布在重庆周边沿长江流域内
从地理位置上看,宋代重庆地区的14所书院主要集中在重庆周边沿嘉陵江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三峡地区。这些地区在宋代时期经济比较繁荣,交通较为便利。这说明在宋代,重庆地区的教育文化状况受经济、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大。以三峡腹心地段刘备托孤的白帝城及“竹枝词”摇篮为中心的夔州府(今重庆奉节)书院更显密集,以静晖、竹林、南阳和少陵著称的书院群占宋代重庆书院总量的近三分之一。比邻合川,地处嘉陵江支流的铜梁县建有庹子书院和龙门书院。这样,上述两地便占据了此时重庆书院的半壁江山。此外,江津县、涪州(今涪陵)、忠县、大宁县(今巫溪)、合州(今合川)、大足县各建有书院1所。重庆除此8府县之外,其他广大地域内再无书院可寻。
(三)以官办书院为主
宋代重庆的14所书院中,北岩、濂溪、五举、静晖、竹林、南阳、宏文等7所书院为官办书院。这7所书院的创办者均是在任地方官吏,在这些官员的倡导之下,地方政府出资修建书院,并且对书院中大小事宜严加管理。庹子、龙门、南山书院是根据已有资料得以考证的民办书院,剩余4所书院即五峰、少陵、凤山和五桂楼,因现存资料有限,属于官办还是民办尚难以判断,存此待考。从中获悉宋代重庆所建的书院以地方政府出资举办为主。这种情况与当时全国书院整体发展的趋势是相悖的。
书院本是由民间兴起,因此两宋时期的书院多为民办书院,官府对书院只予以精神上的支持与肯定,不过多干涉。而在重庆却出现了与此相异的图谱实态。对此可以从办学主体力量的因素加以剖析:就官方而言,官学的衰退失去了往日在人才培养中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势下,重庆府州县任期内官员积极筹谋创设书院,振兴地方教育,以图提升为官任内考评政绩,获得更好的仕途升迁机会。此外,“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3] 661,这种儒学教育观在内陆腹心地带的重庆影响至深,某种程度上成为重庆各级官员更为积极建设书院的精神支柱。加之宋代重庆地区的商贸物流繁盛,官府税收丰盈,这也是宋代重庆官办书院占据优势地位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宋代重庆民间经济实力较弱,难以自行筹集经费创办书院,是民办书院较少的最重要原因。
二、宋代重庆的著名书院
本文若要对宋代各时段重庆14所书院逐一详细介绍,比较繁琐,故此处以最能够代表宋代重庆的书院办学水平及组织管理特点的北岩书院与濂溪书院为例,加以剖析。
(一)北岩书院
北岩书院,后名“钩深书院”,原址在涪州(今涪陵)北岩山[4]62。涪陵位于今重庆市的中东部,因其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吸引了古今文人墨客来此,或感叹它的秀丽,或吟唱它的巍峨,或讲学著书于此。悠久的巴渝历史曾记录过它的不凡文明,书写着它“人杰地灵”的传奇。明代四川巡按李廷龙曾题诗《登北岩》称赞北岩:“北崖交耸向谁开,云际偕登目八垓……坐语不知尘界回,恍疑踪迹是蓬莱。”
北岩书院被世人誉为“理学圣地”“伊洛渊源”[5]39。两宋时期的书院多承载讲学、崇祀、藏书等职能。南宋绍兴五年(1135),涪州知州李赡主持修建伊川先生祠堂,供奉程颐塑像。程颐当年注《易》之所点易洞尚存,有对联称:“洛水溯渊源,诚意正心,一代宗师推北宋;涪江流薮泽,承先启后,千秋俎豆换西川。”据说,此联为知州范仲武于1208年所作,概因年代久远字迹不清,又于光绪二年(1876)重刻。清末“新政”时期,政府推行“废科兴学”的教育政策,而改书院为学堂便是其中重要内容。于是,该书院转型为近代师范学堂——涪州官立师范学堂,并逐渐走向制度化建设,按照清末“新学制”法规《奏定师范学堂》的方案及要求组织管理。1906年后改为中学堂。民国年间,先后为省立四中、县立乡村师范学校、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校地。1950年以后,涪陵师范校、涪陵十三中亦开办于此[6]。

1.程颐、谯定
程颐(1033—1107),世称伊川先生。程颐一生竭尽全力传道授业,由于长期讲学于洛阳,其所形成的学派以其出生地河南洛阳伊川县而冠名,被称为“洛学”。北岩书院与“洛学”结下不解之缘,因程颐而存在,因理学而闻名。
北宋中期,时年65岁的程颐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革职,编管涪州。谯定曾到洛阳跟随程颐问学。据记载:“谯定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遂得闻精义,造诣愈至,浩然而归。”[7]得知其业师遭贬来涪州之后,谯定“于颐前朝夕聆教”[8]121。并共同于北岩注易,使北岩成为中国理学思想的重要传播地之一而蜚声中外。一时名人慕访,贤徒踵至,人文荟萃,光耀北岩。
谯定(1023—?),字天授,号达微,涪州乐温县人,是程门理学在重庆、四川地区的传播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谯定曾隐居于青城大面山(今四川万源),即今之“谯岩”。他饱读诗书,博学多才却隐处不仕,人称“涪陵先生”、谯夫子,著有《谯子易传》。建炎初年(1127—1128),宋高宗授其“通直郎致仕”的名号。由于与当局意见本有不合,又恰逢金兵攻城,维扬(今扬州)失守后,谯定转而回到老家涪州研究理学,传道授业。北岩书院由此而成为“涪陵学派”的大本营,对涪陵教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成为重庆乃至四川地区重要的书院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程颐在北岩书院(当时名“钩深堂”)的讲学形成了巨大的力量,使理学在巴蜀发展传播势不可挡。程颐及其学生谯定对重庆地区尤其是北岩区域的学术文化影响巨大。

南宋时期,程颐所开创的洛学和以谯定为代表的涪陵学派思想,被朱熹加以继承和发展,同时融入释、道各家思想,并形成一个庞大的、严密的理学体系。朱熹(1130—1200),宋朝著名的理学家、儒学集大成者,一生为人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南宋淳熙年间,他亲自订立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对宋代书院教育以及后世教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0]357。
作为程颐的再传弟子,朱熹拜读《伊川易传》后,慕名来到北岩,于点易洞研究《易》学,以承先师。他作“题壁”称:“渺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具此中。”[11]此后,朱熹又特作《与周卿书》:“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谓学者,舍是无有别用力处矣。”[12]11文字虽不多,却深刻地道出朱熹格物致知、读书明理的认识论及学思结合、自我体验的学习论。朱熹振兴书院的建设促使宋代各地书院蓬勃兴起,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重庆亦然。
朱熹与北岩书院的渊源主要是因为师从谯定一脉,之后又由其学生将理学精神继续传播于北岩书院。

图1 朱熹与二程理学渊源(表示曾在北岩书院讲学)
如图1所示,二程理学与朱熹渊源颇深。二程理学是指以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为首的理学派别,因他们是洛阳人,故又名洛学。程颢的《识仁篇》《定性书》和程颐的《伊川易传》奠定了理学的理论基础。他们提出以“理”或“天理”为宇宙本源,“万物皆是一理”,又继承张载人性观点,分性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首创“性即理”说,完成了由儒学向理学之转变。程颢观点为南宋陆九渊、明代王守仁继承发展,形成“陆王学派”,程颐观点为南宋朱熹继承发展,形成“程朱学派”。朱熹理学思想受程颐影响的途径主要在三方面:第一,家学渊源。朱熹之父朱松为程颐三传弟子,与李侗同拜师于杨龟山(时)的门人罗从彦。因此,朱松“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独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于是益自刻厉,痛刮浮生,以趋本实”[13]4。河洛之学,即二程的洛学。其中,罗从彦曾于北岩书院讲学任教。如此而来,朱熹受其父家学教诲,理学思想由罗从彦、杨时,溯其源于程颐。第二,少年受教于建安三先生。绍兴十三年,朱熹之父朱松病逝,临终前写信请屏山刘子翚、白水刘勉之、绩溪胡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朱松死后,朱熹谨遵父命,受学于三先生之门。刘勉之、胡宪为谯定门人,又都是罗从彦的学生,均承程颐之学,进而说明在朱熹舞勺之年受到了程门理学思想的滋养。第三,南宋绍兴二十三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学于李侗。自此朱熹不但承袭二程的“洛学”和谯定的“涪陵学派”思想,并综合了北宋各大家思想,奠定了他一生学术的基础。



(二)瑞应山房(濂溪书院、合宗书院)
瑞应山房是濂溪书院、合宗书院的前身,院址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南津街合州州学之侧。合川位于重庆西北部,因南宋末年钓鱼城之役使号称“纵横天下无敌手”的蒙古帝国大汗蒙哥丧命于此,而被誉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处”。
周敦颐(1017—1073),宋代理学家,世称濂溪先生。南宋丞相文天祥曾撰《侍郎公墓志铭》称其为“百代绝学之倡”。就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论,周敦颐在书院教育及理学传播方面的成就远远突破重庆及西南的区域范围,而流布于全国,遍布大江南北,以濂溪为名或祀周敦颐的书院不可胜数。朱熹在《韶州濂溪先生祠记》中对周敦颐的“功勋”有极为尊崇的评述[14]83。
程颐曾于少年时期受学于周敦颐,便以师礼侍之,但实为学友。嘉祐元年(1056),周敦颐置合州判官。他在合州为官期间,勤政爱民,传道授业,从学者甚众。但同时他也通过汲取四川、重庆学者的思想,提升了自己的学术水平及涵养。合州百姓对周子的功德心悦诚服,在本地设祠堂以示纪念,时至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增设学馆,即为濂溪书院。理学教育家魏了翁著有《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记》。该文收录在《鹤山集》卷四十四中,其中有言:“予为移书太府少卿安癸仲,得官屋于州冈前……匾曰瑞应山房,以祠先生,配以二程子。郡少府又馀法用,即张氏故址为养心堂,以馆学徒……”这里的张氏即指当年从学于周敦颐的合州人张宗范。由此可知,理宗绍定年间应是瑞应山房及后续濂溪书院的修建之年。
濂溪书院后毁圮。明成化中,知州唐珣等复兴,称为“合宗书院”。书院堂前名“寻乐”后名“天余”“光霁”。院后掘池种莲,建亭于上,亭名“观莲”,概因周子《爱莲说》的流传及影响。明末兵毁,亭、房、院、堂荡然无存。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知州蔡之芳重建。教学、祭祀及藏书活动绵延不绝。濂溪书院的兴衰沉浮状况是古代书院史曲折艰难历程的一个侧影,毁而又建、废而又兴的情形又昭示出包括濂溪书院在内的古代一大批书院的顽强生命力与蓬勃精神力量。
三、宋代重庆书院的教学和管理
现代哲学家、教育家胡适曾高度评价宋代的书院制度。他认为,宋代讲学之盛,古所未有……听讲时大半笔记,不用书籍,如《朱子语录》,即学生所做的笔记。教法亦大半采佛家问答领悟之法,至于讲学之风,迨南宋时可谓“登峰造极”[15]194-195。尤其是南宋时期的书院教育,更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模式的典范。以后的元明清历朝书院,虽在数量和规模上有可能超过宋代,但其教育水平已远不及南宋书院,办学模式也没有超出南宋书院的框架[16]215。北宋初期,重庆书院尚处于初建时期,书院各方面的功能、设施并不完善。至南宋时期,重庆书院才终于得到了真正的完善。宋代时,书院在重庆的出现恰当而又适时地弥补了官学和私学的不足,以一种更昂扬积极的姿态担负起了教书育人、传承文化的重任。宋代重庆书院的许多管理经验,至今仍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以下就宋代重庆书院的教学和管理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教学目的
教学目的对整个教学活动起着统贯全局的作用[17]64。宋代官学虽经范仲淹、胡瑗、王安石等经世派的改革,但无力解决科举与学校的矛盾,官学教育弊端日显,完全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无法担任“立学教人”的重任。鉴于此,理学家们高度重视书院教育,并将书院讲学与传播理学结合起来,立志通过创办书院来实现教育改革的宏愿。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地方官吏也注重倡导并积极设立官办书院。如此一来,宋代书院既是理学教育思想实践的教育基地,又是研究理学思想、教育思想的学术基地。宋代重庆书院的教学亦旨在探究学问,为传播理学思想而培养人才,进而改造社会。
作为宋代重庆书院的代表,北岩书院的教育教学目的深受程颐及其弟子、再传弟子的理学思想及教育实践的影响。程颐认为,书院的存在是为了提供教育,然后通过教育的途径,培养出一批学圣至道的封建“卫道”人才,进而通过学生参与政治,来实现其政治意图和思想传播。他在教育学生过程中始终奉行“学而致用”。此外,南宋名臣李曾伯在《竹林书院记》中曾记载书院讲学情景:“相与聚辩讲习,以存心养性,以砥节砺行,将见英才辈出,文风日趋于盛矣!”[18]333这些足以说明宋代重庆的竹林书院不仅是士子们讲学论道的场所,同时也是他们修身养性之地,其教学绝非一般官学可比。因此,宋代重庆书院同当时社会整体形势保持一致,其教学目的是通过日常教学为地方社会培养大量的“学而致用”之才,而这些人才或造福家乡,或为朝廷所用,或为他人之师传道授业。
(二)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实现教育教学目的的手段,因此有什么样的教学目的就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内容和教材,这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要求所决定的[16]120。宋代重庆书院的山长和教师多数是由理学家担任的,以理学思想为指导来制订教学计划,安排教学内容。书院的教学内容多是以理学著作或语录为核心的儒家典籍,兼涉文史学科知识及其他学派思想。书院主讲者乐于把自己的著作作为书院的教材,讲述独到的学术见解,与学生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一点,北岩书院表现得尤为明显。
宋代北岩书院受程颐与其众弟子讲学的影响,以《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认为“为学治经最好”[19],“六经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20]。程颐主张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教材,这就是新的教材体系——“四书”“五经”和新的知识结构,即“义理道统”[16]120。时至朱熹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后,该书便成为宋代重庆书院的主要教材,其地位也超过了《诗》《书》《礼》《易》《春秋》等传统儒家经典。此外,程颐于北岩书院讲学时,也曾专门讲述自己的著作《伊川易传》。值得一提的是,宋代重庆书院的教学内容还包含历史的学习。程颐有言:“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其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21]232
在教学内容的设计及实际影响方面,北岩书院独树一帜,突出表现为理学的传承与发展。北岩书院自创办时便承载着传承历史文化的重担,通过教学来培养出一代代的智者名士,使得他们在思想上传承理学,发展学术。程颐是易理学的开创者,亦是宋代巴蜀理学四大学派之一“涪陵学派”形成的启蒙人物。程门众多弟子纷纷来涪授学,将程颐一脉的思想与学术发扬和传承,为程朱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谯定师从程颐,学于北岩,承传《易经》,之后深得易学之精髓,自成“涪学”。朱熹亦师从程门,受其理学思想与学术传承,开创程朱理学。至此,北岩书院孕育了南宋以后中国六百余年的官统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归根溯源,是北岩书院这片沃土,滋养了程门理学的成长与壮大,使其教学传承数百年,遍及华夏。
(三)教学方法
宋代书院的办学采取民主管理、教学与研究统一、讲学“门户开放”、学生自学讨论与质疑问难结合的方式,被赞誉为中国古代具有大学精神与现代西方学术研究风格的高等教育机构。重庆书院在这种活泼、自由的教学理念与体制的引领之下,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教学模式和方法。
1.“教学相长”的自由教学。宋代重庆书院作为高层次的私学,已经脱离了简单的教师宣讲、学生接受的教学模式,而倾向于师生之间的互动。在这种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质疑教师的观点,老师也可以从学生的思想中汲取新的灵感。在这样自由和平等的环境中,师生互相促进、提高,正所谓“教学相长”。宋代重庆书院中,最早开启“教学相长”自由教学的当属北宋末期的易理学大师程颐与其弟子谯定。师徒二人探讨易理,亦师亦友,教学相长。后又联袂讲《易》于北山之穴,即今“点易洞”,并共同注解《周易》,史称“北山有岩,师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读《易》洞”[7]。元符二年(1099)撰著《伊川易传》。这部易学名著、理学佳作,恰是程颐与谯定师徒“教学相长”的成果,更是二人积累、探究、学《易经》的心得结晶,堪称程朱理学的经典。

此外,宋代重庆书院还会采取“论辩问难”的教学方法。“论辩”是指在讲学时融入自由讨论学术的教学方式,使师生可以直接论辩交流,共同研习学问,较之于官学教育的枯燥乏味的背书而言,更能吸引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问难”则是教师讲课时采取提问式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别出心裁,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这些都是一般官学所不具备的,比官学中呆板的死记硬背要科学和有效得多。这是继承了孔子在《论语·子罕第九》所记录“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灵活教学艺术风格与“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的启发诱导精神。程颐在北岩书院授学传道时,就主张经典中的义理不应和盘托出,而是只讲“七分”,余下得由学生“自行体究”,灵活构造、生成与开发。这说明程颐在讲学之时,注重对学生适时引导,启发学生思考与探究,而不是一味地机械般灌输知识。这无疑是一种符合当代教学改革精神的教学方法。
(四)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学校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办学特征的表现,涉及教学与管理的诸多问题。书院教育中师生关系的民主、互动及学术探究特性是其获得有效高质办学业绩的内在机制之一,重庆的书院也是如此。书院对选聘教师的条件较高,以保障办学质量并维系书院声望长盛不衰。同时,教师的聘金、薪资及其他待遇也颇为丰盈,让人称羡。受到书院聘任的教师自身特别注重身教,以“人师”自勉自任[24]263。此外,书院教师还具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名师主讲课程,启发诱导,指引弟子读书,且具教育教学的热情与精神,有助于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平,并能够在地方形成威信,有积极的社会效应。同时,能够吸引大量的优秀生源来书院学习,不断扩大影响。涪州州牧范仲武扩建“钩深堂”为北岩书院,名儒讲学,言传身教,道德感化,人格熏陶,使北岩曾为长江上游与乌江交汇结合部的学术文化中心。孟珙主持修建竹林、南阳书院亦是如此,亲为书院“择文学行义之士,众所推服者以师表之”[2]34。
两宋时期,重庆书院中的学习氛围比较开放、宽松、活跃,师生间的关系也亲近和谐,而不是冷漠紧张。这是因为重庆书院的教师在讲学过程中注重口传身授、人格垂范、精神感化、情怀熏陶,师生之间亦可互相探讨,尊师重道,关怀学生,营造了一种和谐亲切、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如《四川通志》卷七十九记载,五峰书院中的学习气氛开放、活跃,师生之间亦师亦友,“以为士友讲会之所”。又如,乾道元年(1165)至三年,王十朋在任夔州(今奉节)知州时创建了静晖书院。为了便于师生之间的学习交流,除在书院开展正式讲学外,王十朋还以静晖书院为基础,举办以诗文为中心的各项活动,如诗义会讲、以诗会友等,进而促使书院的学习氛围更为浓厚。一时为学界所吟诵传播的诗句“明朝怅望仙舟远,百尺高楼上静晖”,便是他在静晖书院与学生吟诗交流中所创作的。由此可见,静晖书院当时的师生关系融洽和谐,教学气氛“生动活泼,不固守教条”。这种良好的师生关系既是重庆书院办学秩序协调稳定的条件,也是书院有效管理的目标内容。
(五)考课制度
宋代因受到官府奖励,以讲学为主的书院遂日渐兴盛,规制愈益完备,这是书院确立自身的办学宗旨和特色的一个重要手段[16]219。其中,考课制度作为教学管理的一种,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学业成绩考核,具有教学测评的价值。
考课制度是书院教学管理的重要制度,宋代时已开始实行。宋代书院主要以两种考课制度为主:一种是仿王安石的“三舍法”,通过考核积分以便升级学习;另一种是成绩水平考试。成绩水平考试是宋代书院采取的主要考课制度。例如,朱熹曾“诣学升堂,以百数签抽八斋,每斋一人出位,讲《大学》一章”,以抽签的方式来考核学生对《大学》的学习与理解状况。书院的考课制度,宋代仅为草创,时至明清得以发展。不过,此时已发展成为明清科举的预备考试制度,其教学考核意义已有所下降,反不如宋代书院考课测评的学术价值。如夔州府(今重庆奉节)南阳书院规定“以堂长,季试而旬课之”[18]333,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书院教学管理体制。
(六)办学经费
日常办学活动的运作都需要经费作为物质基础,这也是教育的经济制约性。正因为如此,办学经费的相关论题向为教育教学管理中的核心领域,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概莫能外。宋代较唐末五代而言,经济发展较好,多数地区的民间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进行书院建设。受特定地理环境、人口居住方式以及传统经营管理模式等因素限制,较之长江中下游及江南地区,宋代重庆的民间经济实力薄弱,故民众难以筹集经费来独立创办书院。因而宋代重庆书院多为官办书院,办学经费多来自于官府赐给田地钱粮,“租入附于学库收支,董于佥幕”。例如,竹林书院和南阳书院,主要经费来源便是官府赐予的学田和山林川泽的收入。《公安书院记》卷四记载:“公安凡六十楹……南阳余六十余楹,田租岁入六千石有奇,山泽渔征之利为钱四百万,养士百有四十人。”[25]207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公安书院就是重庆奉节的竹林书院。“(孟珙)度地于公安邑东,辟书院,取莱公竹遗迹,扁曰‘竹林’,置田拨钱以给廪用,乞赐额于朝。六年夏,上亲洒宸翰,赐名‘公安书院’。”[26]又如,合州瑞应山房由地方官员建养心亭“以馆生徒”,“创田以供粢盛饩廪”[27]。
然而,书院的办学模式在宋代的其他区域主要表现为民办性质,重庆虽然以官办书院为主,但书院办学不同于官学的科举教育,其思想理念受官方主流意识控制相对较少,而带有一定的民主性及学术探究的特点。因此,在书院的管理上,宋代重庆书院显现出自身的与众不同。譬如孟珙所办的公安、南阳两书院,不同于当时单一性质的官办或民办书院,而采用一种官办民助的新式办学模式。孟珙曾在上奏宋理宗的奏折中解释道:“襄、蜀荡析,士无所归,蜀士聚于公安,襄士聚于郢渚。臣作公安、南阳两书院,以没入田庐隶之,使有所教养。”[28]由此可见,公安与南阳书院因所占田土、房屋为官方给予,在办学上首先属于官办公立书院。另一方面,公安、南阳两书院又伴有民办私学的性质。由于时值蒙古军进攻夔州,孟珙担负着京湖地区防御重任,自然不能同平日的文人政客那般亲自主持书院,言传身教。受战争影响,宋廷未对公安、南阳两书院指派教授, 也未将其完全纳入官学中,而是择选当地“有学行者为山长”,负责书院的教学与管理。此外,公安、南阳两书院的学生主要为襄蜀两地的“无所归”之士,教师也非朝廷命官而是由孟珙选聘的著名学者,不受朝廷管束。由此可见,公安、南阳两所书院在生源和择师上具备了民办私学的特点。这就使得这两所书院在管理上比当时其他官办书院更具有民办私学的自主性。
综合看来,公安与南阳书院在宋代重庆的特定环境下,开辟了一种官办民助的办学与管理模式,既克服了官办书院的层层束缚,又解决了民办书院办学经费不足的桎梏,进而使得宋代重庆书院在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书院中显得尤为标新立异。
四、宋代重庆书院的发展对现代的启示
宋代重庆书院的办学实践虽然发生在封建社会中期,属古代与官学教育、私学教育并列的教育类型之一,却仍具有普遍意义,对当代的教育发展有一定启示。
首先,宋代重庆书院的教育目的虽以培养统治阶级的合格官吏、封建道德维护与实践者的卫道士为主,但传播思想文化、探究学术方面值得现代教育思考。如作为重庆“理学圣地”的北岩书院,其师生大多淡泊名利,一心研究易文化,使得易学传承绵延不绝,这与其学术性的初衷有极大关联。对比看来,现代教育过于应试化,其中充斥着“为考试而学、为工作而教”的教育观念,而对于教育的真正目的即探究学问、充实人生的理性与道德,为社会培养具有综合素质能力的多层次人才等方面并未落实。基于此,当代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应该从宋代重庆书院的发展中汲取经验,转变“重名利、轻学术”的错误认识,积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以促进当代教育在学术探求及创造力方面的突破。
其次,宋代重庆书院“教学相长”的自由教学与现代教育观念不谋而合,“开堂讲说”的教学方法也较为接近现代的教学方式。在宋代重庆书院的教学中,“教学相长”的观念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以教师为主导”的单向性、灌输式教学活动,而是更趋向于现代意义上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探究式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强调教学是师生、生生之间的多边教学探究活动,其意义在于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自主性,使学习效率得以提高,学生的独特性与创造力也得以发展。现代学校教学中虽大力倡导启发式教学,即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实践中,但往往流于形式,难以推行。究其缘由,应与现代教育的师生关系有关。在这一方面,宋代重庆书院和谐的师生关系也是值得借鉴的。许多宋代重庆书院中的师生亦师亦友,和谐礼让。如竹林书院的师生“相与聚辩讲习,以存心养性,以砥节砺行”[18]333的讲学之景,再如北岩书院师生交相论《易》于点易洞中的桃李之情。想来身处这样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其教学效果也会事半功倍。对于当代学校教育而言,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其教学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保障。因此,教师在组织实施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应注重民主平等、合作互动,进而营造和谐融洽的课堂气氛。
再次,宋代重庆书院选聘教师以“择优而教”为主要标准也值得现代教育关注。宋代重庆书院要求教师不仅有较高的学术造诣,更对教师自身的道德、心理及教学能力等素质要求甚严。如书院教师选聘应有精湛的学术造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高尚的德行及较高的社会威信等必要条件。从现代教育的视角来看,这些要求恰恰也是当今教育对教师职业素质能力的要求,如当代教师应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文化素养、道德素养、能力素养等。总之,教师的选聘影响着教育活动的成败优劣,因此在此环节上应对教师任职资格严格把关,宁缺毋滥,以促进教育活动达到预设的目标及理想效果。
五、结语
宋代重庆书院的教育有现代研究性办学、主体性教育的新理念,尤其是在教学理念及活动领域更蕴含了宝贵经验,需要我们珍视并认真总结汲取。譬如北岩书院对程颐理学的继承与探究,师生之间教学相长的互动学习以及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无怪乎教育史学家不断探究书院的办学精神,西方学者称中国书院是中国古代具有学术研究特征的研究性大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研究宋代重庆书院的发展,探讨其办学与管理方面的表现及蕴涵的主要特点,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希望能从中寻得借鉴,尽可能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来回答当今教育改革中出现的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1]张阔.重庆书院的古代发展及其近代改制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07.
[2]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3]杨荣春.先秦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4]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第8卷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5]孙由德.涪陵地区历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6]张正武.走进北岩胜境[N].巴渝都市报,2014-11-01(4).
[7]宋史:第38册 [M].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459列传第218隐逸下13460.
[8]徐世群.巴蜀文化大典:上[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9]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宋代文化研究:(第13、14辑)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10]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11]王鑑清,施纪云.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20[A].1928(民国十七年)铅印本.
[12]蒲国树.北岩名胜志:内部资料[A].涪陵市旅游局编印,1996.
[13]杨金鑫.朱熹与岳麓书院[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4]吴洪成.宋代重庆书院与学术文化的发展[J].重庆社会科学,2006(11):79-84.
[15]白吉庵,刘燕云.胡适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16]王炳照,李国钧,阎国华.中国教育通史·宋辽金元卷(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7]田慧生,李如密.教学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18]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40册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9]胡广.性理大全[M].1597(万历二十五年)吴勉学师古斋刻本:卷54.
[20]杨时.杨龟山先生集[M].1883(光绪九年)刻本:卷25.
[21]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第18伊川先生语四.
[22]祝穆.方舆纪胜:孔氏雪狱楼影钞本[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
[23]孟宪承,孙培青.中国古代教育文选[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4]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25]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6]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卷143.
[27]董新策.民国合川县志:第26卷[M].1921(民国十年)刻本.
[28]宋史:第35册 [M].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412列传第171杜杲12380.
(责任编辑吴朝平平和光)
Analysis on the Chongqing Academies in the Song Dynasty
WU Hongcheng, WANG Peipei, WANG Yaping
(School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071002, China)
Abstract:There are 14 academies of Chongqing in Song dynasty, having many features: firstly, the deve-lopment is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secondly, with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time and geography, there are more academies in the south than the north, most of which are concentrated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near the Chongqing region; thirdly, the official academies are 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of Chongqing academies in Song dynasty, it can be found that in view of the teaching purpose, the academies in Chongqing focu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knowledge, in order to spread the Confucianism to cultivate talents, emphasis on the learning and practice; in view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the Confucianism thought was used to guide and establish the teaching plan and arrange the teaching content, attention to th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also to the subject of history, literature and other thoughts of school; in view of the teaching methods,the free teaching that to teach is to learn is advocated, priority given to the teaching, with discussion and self-learning as the complementary; in terms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lationship, the employed teacher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self-practice as the teaching, self-encouragement and appointment as the teachers, attention to the oral teaching, practice themselves, spirit encouragement, emotional enlightenment, open, relaxed and active learning atmosphere, with close, harmonious and 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erms of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the performance level examination in the system of evaluation was applied; in terms of the operational funds, the Chongqing academies in Song dynasty started the running school and management mode combined with official running and private assistance, overcoming the deep bondage of official academy, and solving the shortage of the running funds. The Chongqing academies in Song dynasties have the new idea of research running school and subjectivity education, which still has important inspirations on the moder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firstly, the thought of indifference the fame and wealth has great inspirations to change the wrong recognition of “weight on the fame and wealth, lightening on the scholarship” in the present education circle, and to actively create the better atmosphere for the academic research; secondly, the main standard to select the excellent as the teachers is worth to be paid attention in the modern education; thirdly, the free teaching concept that teaching and learning benefit from each other and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ll match with the modern education thought.
Key words:Song dynasty; Chongqing; academy education; Northern Rock Academy; Confucianism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16)01-0033-11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16.01.006
作者简介:吴洪成(1963—),男,浙江金华人,河北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07-25
王培培(1990—),女,河北沧州人,河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王亚平(1991—),女,河北邯郸人,河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引用格式:吴洪成,王培培,王亚平.宋代重庆书院探析[J].重庆高教研究,2016,4(1):33-43.
Citation format:WU Hongcheng, WANG Peipei, WANG Yaping. Analysis on the Chongqing academies in the Song dynasty[J].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16,4(1):3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