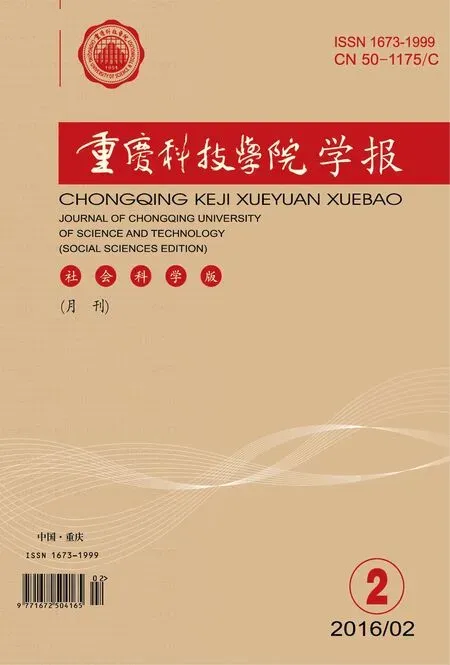论对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
耿 亮
论对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
耿亮
摘要:通过梳理我国针对网络谣言犯罪的刑事立法发展过程,分析了有关网络谣言犯罪的刑法规制特点。联系网络谣言犯罪的特点和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需要,对改进网络谣言犯罪的刑事规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刑法;网络犯罪;网络谣言犯罪;言论自由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应用的普及,人们在网络上的交流日益频繁。网络改变了人们的交流和交往方式。但是,网络也在被一些违法犯罪分子所利用,他们借助网络传播谣言,欺骗公众,侵犯他人权利,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依法打击网络谣言犯罪,需要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对网络谣言进行刑法规制。
一、针对网络谣言犯罪的刑事立法概况
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对谣言犯罪行为进行了规制,比如第103条第2款、第105条第2款、第181条第2款、第221条、第246条、第287条、第378条和第433条的规定,都涉及到了制造与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但是,尚未明确提到网络谣言,因为在那个时候,互联网的应用在我国才刚刚开始。
2000年12月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已经明确提到“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和“利用互联网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扰乱金融秩序的虚假信息”以及“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等行为。
199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对“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行为的规制进行了修改。2001年12月29日公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三)》将“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纳入了刑法规制的范围。2013 年9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刑法》第246条规定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情形进行了界定,同时对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情形及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进行了细化。《解释》还规定,对“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他人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法“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2015年8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补充完善了对于网络谣言犯罪的规制。网络诽谤被害人提供证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安全管理义务,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的,实行单独定罪处罚。对于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的,单独设定罪名和法定刑。对于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的,单独设定罪名和法定刑。对于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网络上传播,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也设定了单独的法定刑。总体上看,修正后的新《刑法》扩大了网络谣言犯罪的主体范围,拓展了打击范围,增加了打击力度。
二、有关网络谣言犯罪的刑法规制特点
(一)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
新《刑法》第287条之一规定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将犯罪的预备行为(设立网站、通讯群组)实行行为化。对于为实施网络谣言犯罪而进行准备的行为,自然也要适用此条规定。网络谣言具有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控制难度大、破坏性强等特点,一旦实施,造成的后果是难以挽救的。此外,网络谣言犯罪需要相当的技术,预备行为对实行行为能否成功具有关键性作用。规制预备行为,防患于未然,可以有效预防网络谣言犯罪。这反映了立法对于以网络为工具实施相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高度重视[1]。然而,对造成严重后果的网络谣言犯罪,仍然适用传统的谣言犯罪罪名的法定刑,这可能导致罪刑不均衡。与传统的谣言犯罪相比,网络谣言犯罪的影响范围和社会危害性更大。
(二)帮助行为正犯化
新《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将帮助行为正犯化,单独定罪。这种做法有先例,如对“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规定,就是将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帮助行为正犯化。对此,有的论者认为这是“为了防止处刑过轻,打击不力”[2];有的论者认为这是因为在组织卖淫中总是存在“协助组织”的行为[3]。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单独定罪,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为了突出打击重点。就网络谣言犯罪而言,传统犯罪中的主次分工在这里已经发生异化,形式上具有共犯性质的“技术帮助行为”已成为主行为。如果没有人提供帮助,有的行为人是无法实施网络谣言犯罪的,所以应当重点打击这种帮助行为。
(三)入罪标准趋向量化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 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构成诽谤罪。对此量化入罪标准,有人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由他人的行为”来决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诽谤罪,不仅违反了犯罪构成的基本原理,也违反了罪刑相当、罪责自负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4]。如果诽谤信息在与被诽谤者生活或者工作不太相关的社区或城市传播开来,则其影响相对较小,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没有影响[5]。也有学者认为,采用量化标准,符合网络犯罪实际,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也是未来司法解释的努力方向[6]。在应对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的行为特殊性方面,这种量化标准无疑有利于增加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有利于规范执法。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网民大国”,这个标准会不会使得入罪门槛降低,导致打击面过宽,不利于保护公民言论自由?
(四)刑法介入范围扩大
新《刑法》第286条之一“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的刑事责任。从保护法益的角度看,这肯定有利于打击此类犯罪[7]。将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纳入犯罪圈,也有利于保证处罚程序的公正性。因为按照刑事案件来处理,无论是一般程序还是简易程序,都对犯罪人的权利保障给予了认真的考虑,有利于避免在行政处罚时可能出现的任意性[8]。不过,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不作为纳入犯罪圈中给予刑事处罚,与民事法上的赔偿损失和行政法上的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相比,孰优孰劣,还有待实践检验。
网络谣言犯罪的主体范围不断被扩大。第一,对自然人主体范围进行了扩充。比如《解释》指出:“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情节恶劣的,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论。”显然,这就扩大了犯罪主体中的自然人主体范围。有学者认为,该款解释已经超出刑法的原意,且不具有国民预测性,属于以解释之名行类推之实[9]。那么。司法解释在对传统犯罪罪状术语赋予符合网络时代的新解时,是否已经超出“术语”的语义射程范围?第二,增加了单位犯罪主体。新《刑法》第286条之一和第287条之一、之二,都规定了对单位实施网络谣言犯罪的处罚。单位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只有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才负刑事责任。增加单位犯罪主体,是适应网络谣言犯罪发展情况而作出的正确选择,有利于全面规制网络谣言犯罪。
三、对改进网络谣言犯罪刑事规制的思考
(一)刑事规制兼顾保护言论自由
刑法规制网络谣言,存在一个如何与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相互平衡的问题。网络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现实愿望,是彰显民意的重要渠道。压制网络言论,极易侵犯网民的言论自由[10]。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刑法是“最后法”,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处罚措施,一旦使用不当,将严重影响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行使[11]。因此,在立法时必须认真考量增设的新罪名和增加的规制款项,是否会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司法解释不能超越权限,以扩大解释为名行类推解释之实,不当扩大对网络言论的打击范围。法官应当严格适用法律。如果法官能够坚守法律底线,遵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合理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立法中即使存在瑕疵,实践中也是可以被克服的。
(二)技术防护与刑事规制相结合
网络谣言犯罪是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应用而出现的。预防和惩治网络谣言犯罪,不能忽视技术防护的作用。有人认为,通过法律和规范来控制法律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情,而技术校正技术却更为有效。例如:法律制度很难禁止色情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而过滤色情信息的屏蔽软件则有良好的效果[12]。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有的技术现象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能力范围,而且人类越来越依赖技术,逐渐成为被技术奴役的对象。因此,仅仅靠以技术校正技术也是行不通的。当然,我们不能忽略技术防护的作用,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1997年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不断地对网络谣言犯罪的规制进行细化和明确化,但网络谣言犯罪案件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没有技术手段的配合,规则也就仅存在于纸面上。预防和惩治网络谣言犯罪,必须坚持技术防护与刑事规制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要了解和把握网络技术的发展态势,从网络技术的专业角度出发,开展具有前瞻性的立法工作;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网络技术在防控网络谣言犯罪方面的作用。对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一开始就应注意培养管控其被不当利用的能力,一旦发生技术滥用,则可以直接对其进行阻止和治理。这样,不仅为刑法规制网络谣言的范围提供了标准,即在管控能力不足时刑法才介入,而且也能及时减少网络谣言犯罪的社会危害。
(三)赋予传统犯罪罪状术语新内涵
立法中对网络谣言犯罪的规制,大多采用了传统犯罪的罪状术语。网络谣言犯罪日益猖獗,而刑事立法滞后,将传统罪名体系延伸适用于网络空间,这也是一种必需的选择。因此,也需要对传统犯罪罪状术语进行扩大解释,赋予新的内涵。扩大解释不等于类推解释,不应超出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而应与刑法条文本身的含义,与一般国民的理解保持一致[13]。网络谣言犯罪的基本类型有2种:一是将网络作为犯罪工具的网络谣言犯罪;二是将网络作为犯罪空间的网络谣言犯罪。针对第一种网络谣言犯罪,对传统犯罪罪状术语的解释,应当突出网络作为犯罪工具的特性,在术语语义射程的范围内,结合网络作为犯罪工具的特点予以解释。超出语义射程范围的解释,不仅有越权之嫌,而且也会超出国民预测,最终会损害公民言论自由。第二种网络谣言犯罪,其全部犯罪过程可能都发生于网络空间,也可以同时发生于现实社会空间,不仅扰乱网络秩序,也破坏现实社会秩序,这就需要刑事规制能够适用于两个空间。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将在网络上散布网络谣言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以寻衅滋事罪论处。将网络空间认定为公共场所,将网络空间秩序认定为公共秩序,这是符合信息社会特点的。随着人们对网络依赖程度的逐步增强,网络虚拟空间与社会现实空间已经越来越难以明确区分。当然,二者始终拥有各自的独立性,存在一定的差异。对罪状术语进行的解释,应当能被一般公众所接受,要使其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生活中的含义协调一致。
(四)完善网络谣言犯罪法定刑的配置
刑法对网络谣言犯罪的规制大多是适用传统的谣言犯罪罪名和法定刑,而且有些新增条款设置的法定刑相对较低。比如新《刑法》第291条的新增条款: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原来该条第1款设置的法定刑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新增条款设置的法定刑比较低。与传统的谣言犯罪相比,网络谣言犯罪由于是利用网络实施或在网络空间实施的,谣言传播对象不特定,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因此也就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笔者以为,对一些网络谣言犯罪,在目前的法定刑基础上,应当增加“可以从重处罚”的规定,以便实现罪刑均衡。当然,实践中应当根据具体案情来适用“从重处罚”,不能“一刀切”。另外,适用于网络谣言犯罪的刑种只有徒刑、拘役、管制以及罚金等附加刑是不够的,还应该增加资格刑。比如对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犯罪主体中的严重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就应当同时处以资格刑。
四、结语
目前,我国对网络谣言的刑事规制具有刑法介入提前、介入范围扩大等特点。对网络谣言犯罪的规制有可能妨碍公民的言论自由,因此需要合理地确定一个“度”。在赋予传统犯罪罪状术语以时代新解时,要注意处理惩治谣言犯罪与保护言论自由的关系。“徒法不足以自行”,防止网络谣言犯罪需要刑法、行政法规、民事法律以及技术防护措施等一起发挥作用。不宜过分扩大网络谣言犯罪的犯罪圈,刑法作为“最后法”,在迫不得已时才可以适用。
参考文献:
[1]于冲.网络犯罪罪名体系的立法完善与发展思路:从97年刑法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4).
[2]郑伟.就这样动摇了共同犯罪的根基:论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怪异切分[J].法学,2009(12).
[3]茹士春.论帮助行为单独定罪:以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的切分为例[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1).
[4]李晓明.诽谤行为是否构成诽谤罪不应由他人的行为来决定:评“网络诽谤”司法解释[J].政法论坛,2014(1).
[5]李会彬.网络言论的刑法规制范围[J].法治研究,2014(3).
[6]于志刚.“双层社会”中传统刑法的适用空间[J].法学,2013(10).
[7]刘仁文.中国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J].食品工业科技,2012 (22).
[8]刘强.我国适当扩大犯罪圈的必要性及思路[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4(5).
[9]高明暄,张海梅.网络诽谤构成诽谤罪之要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4).
[10]于冲.网络诽谤刑法处置模式的体系化思考:以网络水军为切入点[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3).
[11]陈小彪,佘杰新.网络谣言刑法治理的基本立场[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12]理查德·斯皮内洛.铁笼,还是乌托邦:网络空间的道德与法律[M].李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13]张明楷.刑法学[M].第4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45-46.
(编辑:米盛)
基金项目: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研究”(FXY2014004)。
收稿日期:2015-11-07
作者简介:耿亮(1990-),男,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1120)法学院刑法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2-0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