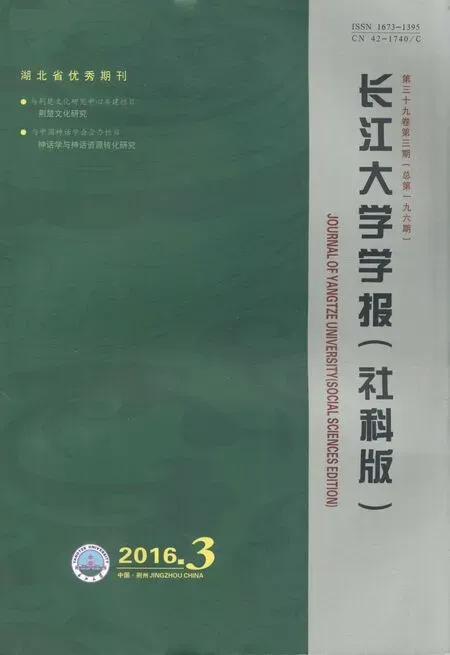20世纪20年代学界对梁漱溟直觉文化观的批评
曾小珍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德育教研室,广东广州510515)
20世纪20年代学界对梁漱溟直觉文化观的批评
曾小珍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德育教研室,广东广州510515)
摘 要: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构建了以直觉为基础的中国文化观。从向善的性质来看,其直觉相当于儒家的本体仁;同时,其直觉又是唯一能通达本体的方法。梁漱溟的这一中国文化观,在20世纪20年代引发了众多学者的批评。人们认为,梁漱溟没有厘清直觉概念及其内涵,只是基于性善论的假定之上,且其太重视直觉的作用,忽略了理智的价值,没有处理好直觉与理智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直觉;中国文化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把孔学当作儒家文化的典型并以之为着手点,运用直觉这一概念,从一个更为原始的道德情感角度出发,重新架构了中国文化。直觉这一概念,承载着梁漱溟从个人生活体验中所得出的结论。他认为,直觉是能够通达本体的唯一方法,这个本体即儒家的仁,“要晓得感觉与我们内里的生命是无干的,相干的是附于感觉的理智;理智与我们内里的生命是无干的,相干的是附于理智的直觉。我们内里与外面通气的,只是这直觉的窗户”[1](P146)。如此,直觉就成为唯一能够与生命本体对话的工具。在梁漱溟那里,直觉本身就是本体,“这个知和能,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的仁”。[1](P130~131)如此,直觉又成为儒学中最高的道德本体。梁漱溟便藉此完成了方法与本体的一体化,也就是本体即方法,方法即本体。这也就是其直觉的内涵。
直觉这一概念与佛教的非量密切相关,但梁漱溟认为,佛教的非量是消极的,直觉则是主观而富于情感的,它“所认识的只是一种意味精神、趋势或倾向”[1](P80),所以它有积极意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就是建立在直觉之上的儒家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庸的,任自然流行,是未来世界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我们能发现,由于受到泰州自然主义、柏格森生命哲学、西方心理学等的影响,梁漱溟对直觉的阐释,并不是那么清晰,其在概念和边界上的模糊化,很容易致使读者对其直觉这一概念的确切性以及在直觉基础上的关于中国的文化观产生怀疑,后来学者对其的批评,皆源于此。
一、直觉内涵厘定不清
梁漱溟认为直觉“任自然流行”,这与泰州自然主义密切相关。泰州自然主义偏于从本能、自然的维度来理解道德,梁漱溟在吸收这一派观点的时候,也将这一点纳入进来,再加上其又吸收了西方心理学、生物学以及生命哲学派的一些观点,故其将生命哲学中的直觉,直接等同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范畴中的无意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其直觉又与本能、欲望相当。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作为本能的直觉根本就无法承担起儒家道德本体的角色,也不能成为梁漱溟所构建文化观的基石,更不能作为人类生命的道德和价值源泉,更不用说担任起复兴世界文化的责任了。梁漱溟没有对“直觉”、“任自然流行”、“本能”,以及他所激烈反对的“欲望”这几个概念进行清楚的解释,也没有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至少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来看,他是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同时,梁漱溟认为,孔子的直觉就是仁,而敏锐的感情也就是仁。因此,其直觉内涵虽然很丰富,范围也很广,但是他却未能将其确切地定义出来。这种概念界限的不明确性,给梁漱溟的文化建构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也必然为其带来更多的批评。比如梁漱溟在论述直觉与道德时,认为真正的道德是由直觉而发的,“非完全自由活动,则直觉不能敏锐而强有力,故一入习惯就呆定麻痹,而根本把道德摧残了”[1](P136)。对此,杨明斋指出:“我们请他先把‘美德’‘道德’‘直觉’‘完全自由’这几件东西讲明白下个定义,然后再讲什么美德要真自内发的直觉而来等等的话,若是不把美德、道德、直觉、完全自由这些名词下个定义讲明白了,则其言虽成千万,唯有一团糊涂罢了。”[2](P76)张君劢也认为,梁漱溟将佛教中的概念等同于西方的理智、直觉是不可取的,而且他将直觉、理智的适用范围扩展得过于宽泛,致使直觉、理智等词义模糊混淆。在建构其直觉文化观时,梁漱溟缺乏对概念范畴的必要解释和应有限定,而且使用随意,不够严谨,这也是其为众多学者所诟病之处。
此外,梁漱溟把直觉作为解释孔学的唯一出发点,认为孔子的仁是在直觉之下的一种自得之乐,将直觉作为孔学的唯一面目,这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非议。他们认为,梁漱溟只看到孔学的直觉是不全面的,“梁先生又引孔子之言‘仁’,言‘中庸’,‘吾与点也’之语,以证孔家之自得之乐,以为出于直觉。所谓自得之乐,是否孔子唯一面目,已是问题”[2](P76)。
二、直觉是居于性善论的假定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以直觉为着手点阐述儒家文化时,也是基于儒家最原本的观点——性善论进行论述和解释的。梁漱溟认为,孔子的路是全凭直觉来走的,因为直觉的向善力,直觉的随感而应,所以现在我们选择的是最适当最妥帖的路。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得益于西方生物学、心理学的发展,人们对性善论的讨论越来越深入,当时的学者如严既澄,就对梁漱溟以性善为基础的自然流行观持怀疑态度:“我细绎梁君所说,全部都以性善的假定为根基”,这个假定,“据近世心理学说来,似乎已不能立足”,“大概善恶的趋向,总得要人明白了人事,通晓了计较才养成的,恐怕不能咬定人性是善”。[2](P76)冯友兰也认为:“梁先生讲的孔家思想,对于人类情感预先存在的调和,对于人性本善,都假定得太多了。”[3]
在梁漱溟看来,道德意识的建立,是直觉自然流行的结果,故其强调主体自身的道德情感因素,认为主体自身的情感因素才是道德最根本的驱动力。但是,由于梁漱溟并没有严格区分道德本能和生理欲望本能,其所肯定的主体自身的道德情感中,就必然包容着道德的与非道德的因素,因此,其在这种视野之下所看到的中国文化,也必然会带有消极的一面。归根结底,梁漱溟强调自然的道德思想,其实是对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功夫即道”思想的发挥。这种将道德本体推向日常生活层面的做法,有其积极意义,但由于界限的模糊性,以及缺乏必要的道德判断标准,故其也存在歪曲道德甚至断送道德的可能。所以,当梁漱溟看到直觉之下的儒家文化始终有道德标榜的作用和号召力时,当时致力主张西化的学者,却从生活世界里,看到了与梁漱溟所描述的截然不同的生活景象。于是,他们纷纷从事实出发,批评梁漱溟的这一观点。针对梁漱溟所认为的中国人的自然混融的样子,以及醇厚礼让的生活态度,严既澄便提出了质疑,认为梁漱溟过分恭维了中国人的道德自律意识。与此同时,胡适也在《读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严厉地指出,并不是中国文化中的所有东西都是好的,“梁先生难道不睁眼看看古往今来的多妻制度,娼妓制度,整千整万的提倡醉酒的诗……这种东西是不是代表一个知足安分寡欲摄生的民族文化?”[4](P91)另外,梁漱溟这种直觉之下的道德的建立,全凭道德主体自身的直觉和随感而应,因此,其现实可能性也是值得怀疑的。按照梁漱溟自己的论证,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连孔子这样的圣人都要到70岁才能达到全凭直觉而“不逾矩”的境界,一般人就更难了,因此,其直觉之下的道德自律并不适用于一般的主体,故其缺乏必要的现实可能性。
三、直觉与理智之矛盾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全凭直觉,自然流行,是一种调和的不认定的态度,孔子对认识对象的把握,也是凭借直觉这一工具的。这种一任直觉的认识虽无方向性,但因为直觉本身同时又具有善、敏锐的特性,故其又得以成为具备方向性的准则和道德标准。梁漱溟认为,这个直觉即孔子的仁,中国文化之所以呈现出其自有的特点,也是因为直觉。在强调直觉的同时,梁漱溟在一定程度上排斥理智。在他看来,墨子的功利主义观将理智发挥到了极处,一味地计较算账,完全排斥了直觉与情趣,这与孔子的直觉是完全对立的。不过,梁漱溟也意识到,要保证始终走一条“得中、调和”之路,仅有直觉是不够的,于是,他又将理智纳入进来,建构了由理智和直觉所构成的调和平衡的中庸之路。这样一条路,“(一)似可说是由乎内的,一任直觉的,直对前境的,自然流行而求中的,只是一往的;(二)似可说是兼顾外的,兼用理智的,离开前境的,有所拣择而求中的,一往一返的”。梁漱溟认为,理智可以纠正直觉本身之偏,故其将理智作为直觉的补充;但这却又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否定了其所谓的直觉的向善能力,造成了其理论体系的自相矛盾。
对此,一些赞同梁漱溟直觉主义观的学者,也认为梁漱溟这一做法不可取,如袁家骅认为,梁漱溟在仁中明确理智的作用,其实是“在直觉之外,添设理智一条路,以为走双的路,就可得到个调和平衡,即令这样的说法是对的,也未免落于第二义,何况是在涂改孔家的真面目”[5]。袁家骅认为,中庸、调和、平衡之类,也是直觉的作用,是一种自然流行,不是人意安排的死标准或固定概念,而梁漱溟这样另立一条中庸的路,是违背任直觉自然流行之本义的,因为真正的仁的生活没有内外之别,没有往返行迹,只是单纯统一的直觉,而梁漱溟把一元变为二元,走出了两条路,这就不可能得到中庸之义了。而胡适、严既澄、杨明斋等人,则直接质疑其以直觉将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合法性和合理之处。杨明斋认为,梁漱溟这种重直觉轻理智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其理由如下:第一,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并不只依靠直觉,尚需理智的参与,“孔子的正名分别同异辨上下倡五伦寓褒贬别善恶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这些事都是全凭直觉去做,能办到么!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要有礼而不乱不绞等,又岂是直觉可以做到么”[2](P63);第二,梁漱溟之所以排斥理智,是因为在其看来,理智之下发端的都是趋利避害,功利算计,而直觉则发端于儒家文化的“鲜功利之习”,但事实上,趋利避害是人的生理本能,中国人也并非全然“鲜功利”,“我们自古就有名利富贵贫贱相连之分”,“几乎公开而有时公开的卖官鬻爵,上下交相舞弊,争名夺利之风,传统了二千余年”[2](P78),且“理智为人类时刻不可离的。反思创造大事业的人,无论他所创是关于道德的或经济政治方面的,也无论他所用的方法是科学推理,或是直觉的,然而非有极高的理智之明是不会成功的。例如释迦、孔子、耶稣等之创造宗教,哲学家之创造哲理,经济学家之创造经济,没有一个不是理智高之人。老实说,人类若离开理智只有盲目的情感,与禽兽无异。所以人若没有理智的训练功夫,莫说直觉之悟不能有什么高尚的,就是感觉也不灵通”[2](P78)。
梁漱溟试图以直觉为基础,重新解释儒家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但由于其在构建其文化观时存有纰漏,故招致了当时学者对其的批评。这些不同的声音,不仅促使人们不断地反思中国文化,且对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M].合肥:黄山书社,2008.
[3]严既澄.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J].民铎,1922(3).
[4]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M].合肥:黄山书社,2008.
[5]袁家骅.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J].学灯,1922(6).
责任编辑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Academic Criticism of Liang Shuming’s Intuition Culture in the 1920s
Zeng Xiaozhen
(Department of Moral Education,Guangdong Tourism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Guangzhou 510515)
Abstract:Liang Shuming constructed the Chinese cultural outlook based on intuition in the book The Oriental&Western Culture and its Philosophy.He put the Confucian cultur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culture,Judging from the nature of intuition,intuition is equivalent to the ontology of Confucian benevolence,at the same time,as a tool intuition is the only way to access ontology.This view attracted numerous scholars criticized in the 1920 s.It is believed that Liang Shuming did not clarify the concept of intuition and its connotation,it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the theory of nature,at the same time,Liang Shuming too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intuition,And he ignore the value of reason,didn’t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uition and reason.
Key words:intuition;the Chinese cultural outlook;The Oriental&Western Culture and its philosophy
文献标识码:分类号:B26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6)03—0074—03
收稿日期:2016-01-15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GD14YZX01)
作者简介:曾小珍(1987—),男,江西吉安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