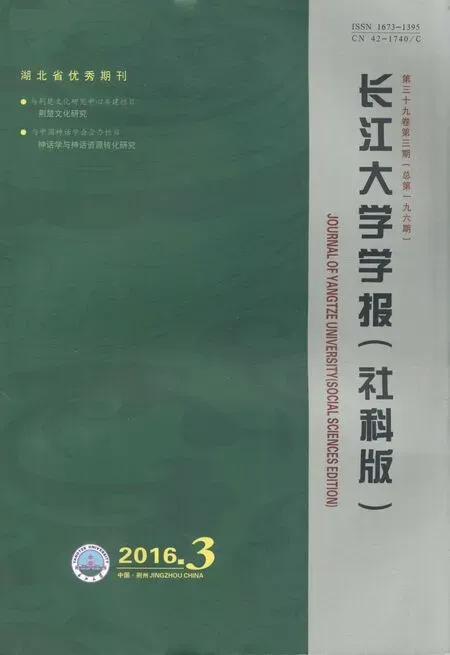论戈迪默小说《邂逅者》中的生态美学意识
胡忠青
(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北荆州434020)
论戈迪默小说《邂逅者》中的生态美学意识
胡忠青
(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北荆州434020)
摘 要:纳丁·戈迪默的长篇小说以反映南非本土的社会现实著称。《邂逅者》则以全球化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移民故事。成长于南非都市的富有白人女孩朱莉毅然跟随非法入境的黑人贫民阿卜杜远走他国,重建自己的梦想家园,而阿卜杜却不辞辛劳地要移民到别国去寻找自己心仪的生活。简单的故事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人与自然的关系疏远隔离,人类普遍失去了“在家感”,精神生态处于失衡状态。只有与自然建立亲密的共生关系,人才能摆脱“无家可归感”,最终达到精神生态平衡。
关键词:纳丁·戈迪默;邂逅者;自然生态;精神生态
生态美学是后现代语境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美学概念,即“生态文明”时代的产物。1994年,李欣复教授发表《论生态美学》,自此开启了中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历程,研究生态美学的学者越来越多,成果也越来越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徐恒醇《生态美学》、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陈望衡《环境美学》、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彭锋《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和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生态美学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生态美学重点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审美关系;广义的生态美学研究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以及人与社会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存在论美学观。李欣复教授认为,人类生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源于自然,又反作用于自然,必须将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结合研究,看到它们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找到正确的途径与方法来维护、调整和修补地球生态平衡。[1]
南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丁·戈迪默的作品以反映南非现实著称。以1991年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为分界线,其前期小说主要以社会现实主义手法揭露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诸多罪行,控诉种族隔离制度对人的生理和心理造成的创伤;后期作品则采用预言现实主义的手法,以极具前瞻性的眼光,对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出现的社会问题做了理性而深入的思考。她于2001年出版的《邂逅者》则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移民故事。成长于南非都市的富有白人女孩朱莉毅然跟随非法入境的黑人贫民阿卜杜远走他国,去重建自己的梦想家园,而阿卜杜却不辞辛劳地要移民到别国去寻找自己心仪的生活。简单的故事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导致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疏远隔离,远离自然的人们在享受着城市生活便利的同时,却普遍失去了“在家感”,精神生态处于失衡状态。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相互依托、相互作用。笔者拟从生态美学视角出发,以《邂逅者》为例,从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两个维度来探讨戈迪默的生态美学意识。
一、自然生态之维
自然生态是生态文明的根基,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都来自于自然。离开了自然生态,一切事物都将是空中楼阁。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人类在实现和自然的分离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人类自然属性的丧失。同时,经济形态的变化与发展导致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泛滥。人类享受着驾驭自然、掠取自然的虚假胜利,走进了人类文明越发展、生态破坏越严重的“二律背反”的怪圈。因此,关于自然生态的各种研究不胜枚举,更有大量的生态主义作家致力于通过文学作品来反映自然生态现状,呼吁人们关注自然生态的维护与发展。
戈迪默不是生态作家,但是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她同样具有强烈的生态敏感性。她的众多作品中始终都有关于自然生态的大量描述。《自然资源论者》、《大自然的游戏》直接以自然作为小说的主题,讲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七月的人民》中,无家可归的白人斯迈尔斯一家,因为内战,不得不逃离到黑人聚居的村庄,在特定的自然生存环境中,人物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生》中,故事就从一个生态保护主义者生病开始。故事的冲突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发展,人与他人关系的疏离与回归也取决于人的生态价值取向。可以说,自然环境对小说中人物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邂逅者》中人物不多,情节简单,自然生态同样成为人物思想变化和情节发展的诱因。
(一)人与自然的疏离
《邂逅者》以全球化为背景,特定的背景注定了这个故事并不轻松、美好。飞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一方面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人对自然的无知。在故事的开端,朱莉的车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街上抛锚。作者把围观的人群形容为,“一群捕食者围着猎物。中间有一个小车和一个年轻女人。”[2](P3)“她感觉到了冰冷的鼻子,呼出的热气还有闪光的牙齿就在她的脸旁。”[2](P6)作者采用自然纪录片一样的表现手法来描述此时的场景,反映了南非的自然生态现实。南非自然资源丰富,大面积的荒野及其生态发展使其成为各种生态研究的首选目的地。而在该作品中,作者更想表明的是朱莉孤立无援、没有归属的生存境地,同时暗示着南非社会并不是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朱莉认识阿卜杜并爱上他,把他当成了充满异域气质的东方王子,把自己对东方的神秘幻想投射到了阿卜杜身上。“棕榈树,骆驼,悬挂着地毯和铜制器皿的小街小巷。阿拉伯三角帆船,海鸟船。”[2](P25)朱莉对阿卜杜家乡的想象充满了旖旎的伊斯兰风情。她对阿卜杜的爱,更多的是源自于她对异域风情的向往。把对陌生环境的向往转化为对一个人的感情,不得不说朱莉所谓的爱情是盲目且肤浅的。同样的肤浅也体现在她的日常生活中。阿卜杜和朱莉的朋友曾经一起出外野营。他们选择在靠近高速公路的地方扎营,尽管不远处奔流不息的汽车时时传来噪音,朱莉和朋友们却自得其乐。对此,阿卜杜有自己的想法,“对他来说,这不是寂静。车流噪音是朱莉的摇篮曲。寂静是荒野,是沙漠。”[2](P34)阿卜杜的现实主义反衬了朱莉及其朋友的肤浅,也暗示着,在这里,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宁静。由此可以看出,身处都市的年轻人对自然的无知以及人与自然疏离后的无奈。
(二)人与自然的亲近
“人类既是他的环境的创造物,又是他的环境的塑造者,环境给予人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并给他提供了在智力、道德、社会和精神等方面获得发展的机会。”[3](P23)对于身份差异巨大的一对恋人来说,唯有自然,才能让他们真正有平等的时空。在朱莉的朋友圈中,阿卜杜一直都是一位处于失语状态的聆听者。和阿卜杜在一起时,朱莉时刻注意不让阿卜杜感觉到他们之间的身份差异。“她尽量不走在这个汽车修理工的前面,就像他是一个仆人一样。”[2](P7)刻意维持的表面的平等并没有真正改变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两人的交流更多的是生理上的,而不是心理上的。但是,在阿卜杜的家乡,两个人的相处状态发生了变化。每逢周末,阿卜杜都会带着朱莉去田野,去荒原。荒野是“被边缘化了的空间,介于纯粹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之间的边界地带,是人与自然及社会双向关系的纽带,既是最富于张力的空间地带,也是最容易产生新质的空间。”[4]在荒野上,他们抛弃了宗教戒律和身份差异,相互分享过往生活的点点滴滴,享受着难得的亲密时光。自此,二人开始对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在心理上相互靠近。旷野这样一个既不在此又不在彼的阈限空间,成了二人存在的理想空间。正如Dana所言,“绿地给两个爱人一个抛弃城市差异的机会,也暗示着新的平等的可能性。”[5]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认为,“荒野自然是人与自然的交会之地,我们不是要走到那里去行动,而是要到那里去沉思;不是把它纳入我们的存在秩序中,而是把我们自己纳入它的存在秩序中。”[6](P53~54)朱莉对沙漠的迷恋与决意改变,也正是因为她真正走向了荒野自然,体会到了荒野自然带给她的力量。初到异乡的朱莉兴致勃勃地想去这个小国的首都,去满足她对这个中东小国的好奇心,但是旷野的沉静让她很快就没了那种好奇的冲动。二人惬意地躺在草地上,“朱莉把手随意地放在他平滑的脖子上,惊讶地说:‘听!寂静!我们从来没有体会到过。’”[2](P34)朱莉的惊讶回应了她先前对寂静的无知。在这个无名小国里,朱莉用心体会到了“荒野概念”,“以及(荒野带给她的)一种全新的、本土的,人与地球和谐共处的希望”[7](P66)。在沙漠里,朱莉体验到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宁静。这种宁静的沉醉使得朱莉不能自已。她喜欢一个人在清晨和黄昏散步到沙漠。沙漠“不分枯荣之季。只有昼夜无尽的交替。游离于时间之外……难以用空间衡量……天空与地面浑然一体,沙漠是永恒。”[2](P172)她之所以选择在清晨与黄昏,即黑夜与白天交替的时间点去沙漠,是因为沙漠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不存在真正的分野,它是时间性和空间性交融的存在。“在荒野,时间沉重,时间滞缓,时间静止,时间消失——时间就是空间,空间就是时间,时间和空间也因此获得了永恒。”[8](P65)也正因为如此,朱莉在空间上寻找荒野,在情感中体验荒野。在时间的维度中,荒野是人类生命的根系,是来路,也是归宿。在一个阈限时间去往一个阈限空间,特殊的时空给了朱莉冥想的机会,她要告别过去的自己,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归属。
(三)人与自然的融合
戈迪默通过朱莉表达了自己对沙漠之美的欣赏,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仅仅是一个有着“荒漠情结”的沙漠爱好者。无名的小国,无名的沙漠,这个环境恶劣的国家可以是任何国家,这片沙漠也可以是任何地方的沙漠。她在引导人们重识沙漠的同时,也在呼吁改变。朱莉沉醉于沙漠带给她内心的宁静,却也只能驻足沙漠边缘,远观沙漠的美。让她惊讶不已的是,她偶遇了一个从沙漠中心走出来的放羊的贝都因妇女。朱莉之所以惊讶,不是因为猎奇,而是因为那个并不惧怕沙漠的女人的顽强的生存方式。她本以为沙漠带给人的是内心的宁静,没想到沙漠还可以这样被利用。沙漠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它的存在不是偶然,而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结果。人类在接受其存在的同时应该思考如何利用以及如何改变。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空里,朱莉决定告别过去的自我,开启新的人生。对阿卜杜亲戚的一次拜访,让她对沙漠利用有了更加明晰的计划。她要在沙漠中种植水稻,改善当地的经济和自然环境,实现自己的绿色家园梦想。这正说明了“位置、身体与环境是相互融合的;那些地方包容一切,包括事物、想法和特别的记忆”[9]。
一个外来的富裕白人因为自己的绿色家园梦想而要改变当地的自然环境,但朱莉并不懂沙漠生态和农业经济,她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叔叔的帮忙争取某国的基金支持。“对绿色的陶醉……一大群鸟儿在稻田上空呢喃盘旋,妇女消失在绿色的稻田里。”[2](P210)绿色是大地的本色,代表了生命、生态和生长,象征着未来和希望。朱莉的绿色梦想简单而美好。对于绿色家园梦想的追求,既是对自然家园的坚守,也是对精神家园的坚守。因为“自然家园是精神家园的物质基础。自然家园如果毁于一旦,精神家园也就不复存在”[10]。然而,阿卜杜的话给她的绿色家园梦想蒙上了一层阴影。“不是稻谷赚钱。”[2](P216)亲戚家的稻田实际上是武器走私的掩护。当地人种植水稻不是出于发展经济和维护生态的目的,而且种植的成本也是无法估量的。阿卜杜对朱莉绿色梦想的否定,其实是质疑建设沙漠绿洲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朱莉仍然坚持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退步了,那就什么都做不了。就种水稻。”[2](P217)她坚持认为这是改善当地自然生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正确途径。诚如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的最后所说:“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态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11](P213)
二、精神生态之维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2](P92)自然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础,自然生态的平衡是精神生态平衡的基础。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是人之存在的本源性关系,是各种伦理关系的核心内容。人对自然的态度反映了人的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的错误取向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进而导致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即人的精神生态的失衡。精神生态失衡的人有家,却感到“无家可归”。然而,这种失去家园的茫然无措不是故事中主人公的个体感受,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自然环境破坏和精神焦虑加剧带给人类的共同感受。
纵览戈迪默的所有长篇小说,所有故事的结局都是开放式的。开放式的结局并不仅仅因为作者想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只能满足读者对完美生活的乌托邦想象,却并不能帮助全面异化的人真正走出困境。正因如此,她的小说没有一部让人读来是欢快愉悦的,小说呈现的故事总能让人感受到各种人物的迷茫与挣扎,而故事中的几乎所有家庭也都在最终走向解体或者发生变故。浮沉命运中的人们总在不断寻找着真正属于自己的理想的家。以戈迪默中后期的作品为例。《七月的人民》中,富有白人斯迈尔斯一家因为内战无家可归,不得不寄居在自己曾经的仆人家,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我儿子的故事》中,索尼最后落得妻离子散、形单影只的下场。《无人伴随我》中,维拉与家人关系冷漠,儿子离婚,女儿是同性恋,而她最终也同丈夫离婚。离婚后前夫与儿子同住,她则卖掉房子,寄居在朋友家,继续追寻自我。琳赛夫妻关系因为二人政治权力的反转而渐渐疏离。其女儿也因为爱上有妇之夫,怀孕并流产。《家藏的枪》中,邓肯由于杀人入狱,其父母哈拉德夫妇也终日忧心忡忡。《新生》中,保罗罹患癌症,虽然最终痊愈,其父亲阿德里安却在外出旅游时爱上年轻导游,客死他乡,母亲则因此饱受煎熬。《空前时代》中,革命功臣斯蒂夫夫妇在革命成功后回国,在郊区买了新房子,以为从此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却不想看到了种种黑暗的社会现实。接受不了社会顽疾的他们最终决定移民澳大利亚,在那里建造他们的新家。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最终能否真正拥有完美的家尚未可知,相似的情感结构同样出现在《邂逅者》中,白人女孩朱莉和黑人青年阿卜杜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家。
(一)优势主体的家园梦
1.失去“在家感”
朱莉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亲生母亲远嫁他国,父亲与继母住在豪宅里,家里出入的人非富即贵。衣食无忧的她却选择租住在别人用来堆放杂物的小房子里,很少回父亲的家,也甚少与父母联系。她有着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为明星们安排活动,高薪且清闲。此外,她还有一大帮朋友。所以她每天的生活除了上班,剩下的时间都是在一个叫做L.A. Café的咖啡馆里度过。惺惺相惜的一帮年轻人常常聚在那里谈天说地,消磨时间。富裕的家庭没能给她归属感,她只能和一帮朋友依偎取暖。但是,在朋友那里,她也没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家的温暖。如Emma Hunt所言,“在全球化的城市里,尽管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与他人产生交集,人与他人之间却失去了一种联系感。”[13]与家人交流的缺失导致亲人间关系的疏远,从朋友处获得的也只是表面的温暖,这种浅层化的安慰反而使人更加孤独。朱莉陷入了一种“在家”却又“无家可归”,精神生态失衡的境地。
“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里,人与包括自然万物的世界——本真的‘在家’关系被扭曲,人们处于一种‘畏’的茫然失其所在的‘非在家’状态。”[14](P326)“畏”说明“无家可归”是一种异化社会中的本源性存在,是人与生俱来的。在现代社会各种因素的统治与冲击之下,这种“无家可归”之感就会显得愈加强烈。因此,海德格尔认为,“无家可归指在世的基本方式,只是这种方式日常被掩蔽着。”[15](P318)如何帮助人们重建“家园意识”,从而摆脱“无家可归”之感?海德格尔的建议是“泰然处之”。他认为应该树立生态整体观,牢牢立足于大地之上。同时,应该在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技术对象。[16](P1234~1235)故事中的朱莉正沿着这个方向走向她的家园重建之路。
2.重获“位置感”
朱莉在修车时意外邂逅了阿卜杜,但是阿卜杜却因为非法入境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尴尬现实。在各种努力未果后,朱莉决心抛弃舒适的生活,和阿卜杜一起回到他的家乡。在阿卜杜一心想要逃离的小村庄里,朱莉慢慢找到了她想要的归属感。她沉醉于当地的沙漠和旷野。永恒的沙漠和空旷的荒野带给朱莉前所未有的平静,在冥想中,她找到了自我,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她想要在这个小村庄重建家园。伊文登(Neil Evernden)认为,重建家园的情感与美学意义的“位置感”密切相关。位置感是指对一特殊地区的认识和归属感。[17](P100)这种情感源于“空间亲密感、认知理解、情感依恋以及责任与关怀伦理”[18](P33),是地理认同和精神皈依的合二为一。朱莉对于阿卜杜家人给二人安排的狭小住房没有任何不悦,也欣然接受了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她努力融入这个新家,慢慢获得了阿卜杜家人的认同和接受。不仅如此,朱莉还通过教授英语、参加妇女聚会等方式加强了和当地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她用自己对这个村庄生态环境的认同和主动的人文交流行动表达了她对这个沙漠村庄的认知和亲近感。
3.重建“在家感”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自觉自由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它能丰富人的生活,发挥人的潜力,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9](P55)异化劳动使得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20](P273)。人们体会不到劳动的快乐,把劳动当成了谋生的手段。因此,梦想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大有人在。成为人人追捧的明星更是很多人的终极梦想。朱莉的工作恰恰和明星有关,她的工作是为明星安排各种演出活动。然而朱莉却并不向往明星光鲜亮丽的生活,反而逃离了这种浮华生活,因为她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归属,也找不到工作的快乐。相反,在这个小村庄,她重新找回了劳动的快乐。“她从来没有像这样毫无保留地劳动过。总是乐意尝试各种事情,也很清楚在什么时候她可以去哪里做什么事情。并不是为了让人满意。像只快乐忙碌的蚂蚁。”[2](P195)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了朱莉自觉自愿的事情。
朱莉走出了异化劳动导致的自我迷失,开始重建“在家感”,她的精神生态趋向平衡。而她想要在沙漠中种植水稻的愿望更加体现了她的生态整体观。“我把自己居住的那处风景定义为我的家。这种‘兴趣’导致我关心它的完整、稳定和美丽。”[21](P167)她完全融入了这个新家,并且想要它变得更好。因为她知道,一个人想要重建家园,就必须植根大地,与大地建立亲密的共生关系。正如约翰·彼德·海贝尔所说,“我们是植物,不管我们愿意承认与否,必须连根从大地中成长起来,为的是能够在天穹中开花结果。”[16](P1305)即便是阿卜杜努力移民到了美国,朱莉依然选择留在小村庄,继续自己的梦想。
(二)劣势他者的帝国梦
1.逃离本土
在朱莉的精神生态走向平衡的同时,她的丈夫阿卜杜却仍然在自我迷失中寻找他所谓的理想家园。阿卜杜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经济学学位。但是,他并没有留在自己的祖国,利用自己的学识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而是非法移民到南非。在约翰内斯堡这个大都市里,他只能在一个修车厂做修车工人,从事体力劳动,赚取微薄的薪水。他居住在修车行里用木板隔出来的一个角落,狭小的空间仅够他勉强躺下。即便如此,他仍然要想方设法地留在南非。为了逃避移民机构的检查,他不惜改名换姓,蓄意割裂和改造了过去的身份。他的本名为“易卜拉欣”(Ibrahim,意味“先知”),为了留在南非,他把名字改为“阿卜杜”(Abdu,意味“上帝的仆人”),把自己由寓意上的主导身份降为从属身份,实际上是把自我他者化了。
“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群体关系恶化……人们的相互关系失去了道德义务感和情感特征,从而变得靠单一的经济利益来维持。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基于物质利益。”[22](P26)一个不名一文的贫穷黑人获得了一个衣食无忧的白种女人的青睐。一方面,这有助于提升他的主体地位,让他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因为“人家把我当作白人来爱”[23](P46);另一方面,这对于阿卜杜而言是一个改变命运的绝佳机会。朱莉富裕的家庭、舒适轻松的工作和朋友圈子都令他羡慕不已,但是朱莉有权有势的富裕家庭却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任何改观,他没能因此获得留在南非的合法身份,他想要通过和朱莉结婚来获取居留权的想法也破灭了。一切未果后,朱莉抛弃一切,追随他回到他的贫穷小国。对此,他很愤怒。他的愤怒更多的是他想要利用这个白种女人获取经济利益却遭遇失败的失望感。同时,他觉得朱莉太天真,因为他的出逃就是源于忍受不了他的国家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落后,一个养尊处优的白种女人更加不会安于呆在那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2.逐梦帝国
和朱莉一起回国后,阿卜杜重新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易卜拉欣。但是,称谓的恢复并没有带给他自我意识的回归,他依然不辞辛劳地努力申请移民到其他国家。本来可以在叔叔的修理厂工作,并且极有可能继承这个厂的经营权,易卜拉欣却拒绝了。在朱莉继父的帮助下,他最终如愿获得了去往美国的签证。“被殖民者尤其因为把宗主国的文化价值变为自己的,而更要逃离他的穷乡僻壤了。他越是抛弃自己的黑皮肤、穷乡僻壤,便越是白人。”[23](P9)他再次选择逃离本土,追逐帝国文化,寄希望于到一个富裕的大国去建立自己理想的家园。他的努力注定是西西弗斯式的努力。伯林特认为,“如果我们的邻近地区获得同一性,并让我们感到具有个性的温馨,它就成为了我们归属其中的场所,并让我们感到自在和惬意。”[24](P66)然而,易卜拉欣在美国的生活不会是温馨的,也不会让他有归属其中的“在家感”。朱莉已经预想到了他在美国的生活。他会寄居在亲戚租住的地下室里,从事着给摩天大楼清洗外墙的危险工作。和他在南非的遭遇一样,他会再次遭受帝国文化的排斥,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缺乏与本土文明相互联系的“位置感”。人只有与本土文明相融相生,才能获得“在家”的归属感。易卜拉欣的盲目追求注定他仍将“无家可归”,精神生态依然失衡。
在故事的结尾,尽管作者没有告诉读者易卜拉欣是否在美国找到了他想要的生活,其结果却不言而喻;开放式的结局也不得不让人思考朱莉绿色梦想实现的可能性。尽管如此,“田园梦想的‘乌托邦维度’展望了一种社会和谐、生态和谐的美好未来。同时,它也激发了人们对美好过去的回忆。”[5]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精神生态平衡的“过去”也是人们为
之奋斗的美好未来。从生态美学视角解读戈迪默的《邂逅者》,我们窥见了戈迪默淳朴的生态美学思考:人类“应该结合本土来关注个体与社区。这样可以帮助克服现代社会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全球化带来的矛盾”[18](P28~29),最终帮助人类走出精神生态失衡的生存困境。
参考文献:
[1]李欣复.论生态美学[J].南京社会科学,1994(12).
[2]Nadine Gordimer.The Pickup[M].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1.
[3]刘彦顺.生态美学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颜红菲.叙事理论的新视角:评科特的《现代小说的地点与空间》[J].外国文学研究,2012(3).
[5]Dana C.Mount.Playing at Home:An Ecocritical Reading of Nadine Gordimer’s The Pickup[J].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2014(3).
[6](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Greg Garaard.Ecocriticism[M].New York:Routledge,2004.
[8]王惠.论荒野的美学价值[A].中国美学研究[C].上海:三联书店,2006.
[9]Arturo Escobar.Culture Sits in Places:Reflections on Globalism and Subaltern Strategies of Localization[J].Political Geography,2008(25).
[10]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J].文艺研究,2002(5).
[11](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Emma Hunt.Pos-Apartheid Johannesburg and Global Mobility in Nadine Gordimer’s The Pickup and Phaswane Mpe’s Welcome to Our Hillbrow[J].Ariel,2006(4).
[14]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5](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16]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C].上海:三联书店,1996.
[17]Neil Evernden.Beyond Ecology:Self,Place,and the Pathetic Fallacy[A].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C].Athens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
[18]Ursula K.Heise.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1](美)阿诺德·伯林特.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M].刘悦笛,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22]蒋承勇.现代文化视野中的西方文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23](法)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M].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24](美)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M].武小西,张宜,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On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s in Gordimer’s Novel The Pickup
Hu Zhongqing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Yangtze University College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Jingzhou 434020)
Abstract:Nadine Gordimer’s long novels are known for their disclosure of the reality in South Africa,while The Pickup tells an immigration story with globalization as its background.In the story,white beautiful rich girl Julie abandoned her comfortable life and chose to reconstruct her dream home in her poor black boyfriend,Abdu’s country,while Abdu chose to seek his dream life in another country.The story does not only emphasize people’s indifference and ignorance to nature,but also uncover the imbalance of spiritual ecology resulted from people’s alienation from nature.Therefore,only if by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can people get rid of the feeling of“homeless”and achieve the balance of spiritual ecology.
Key words:Nadine Gordimer;The Pickup;natural ecology;spiritual ecology
文献标识码:分类号:I106.4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6)03—0017—06
收稿日期:2015-1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WW075)
作者简介:胡忠青(1980—),女,湖北竹溪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