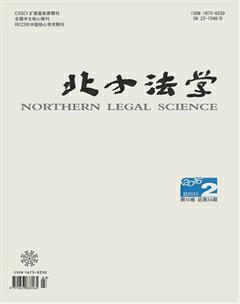清代州县官的司法追求与躬践
梁凤荣 杨鲲鹏
摘 要::有清一代,州县官对地方司法的有效运作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官员队伍中的一个群体,其中不乏庸碌或贪渎之辈,但也确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为官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追求司法中的“秩序”、“仁恕”、“道德”文章。这种追求与其长期被儒家文化的浸润密切关联。清代州县官结合自身职能与任职所在环境,力图通过司法活动达到“使民无讼”、“情罪相协”的效果,为此致力于“哀矜折狱”的实践。
关键词:清代 官僚 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2-0145-16
清代的官僚运作体系和以往的朝代一样,以皇权运作为中心,在自上而下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trapezoid-structure)。 ①州县处于这个结构的最底层,其数目始终保持在1200~1300个之间,这就意味着州县衙署的主官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本质上为清廷所雇佣与豢养,维持着偏私政府的本性,但是出于地方实体治理的需要,他们也在努力形成一种“精英治理的环境(elite administrative milieu)”, ②共同交流和探讨州县官在自我律求和处理庶务中应奉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因领域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措词表达,诸如爱民、敬民、和谐、仁恕、教化、清廉、慎重、勤勉等。不同的措词集合成了“父母官”的标签,体现着地方官员儒家化的政治理想。那么,在司法领域,清代州县官追求的是哪些价值?他们是怎样践行自己的司法追求的?这些司法追求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笔者不揣浅陋,拟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对了解清代州县司法情况有所裨益。
一、州县官司法追求之目的
清代州县官看起来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有人将其喻为“阎罗天子”, ③也有人称之为“治国精英”;法国汉学家魏丕信认为,把清代州县官员的司法活动一概理解为“冷漠和贪婪”似乎是一种误解:“我一直很难相信以下说法:把书呆子气的、不实干的和懒惰的文人,与邪恶的、狡诈的和不顾道德廉耻的胥吏结合起来,就能够颇有效率地统治巨大的中华帝国,使之在相对长的时期内和在巨大的制约和困难中,保持一种相对不错的状态。”魏氏进一步分析:“当我将研究兴趣转向地方治理的其他领域(如司法等)时,以下情况对我来说就更清楚了:支持这整个制度的,时期组织和运作手续的极端老练与灵活,与一个由非常专门和干练的官员组成的活跃的小群体所具有的进取精神。这个活跃的小群体,我称之为‘治国精英(administrative elite)”。前引②。 既有人对州县刑讯之酷烈而为同胞垂泣,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的著作时说,孟氏有“鞑靼种姓虽与南人有刚柔强弱之舒,其为奴隶,则一而已。南人之治其种也,含棰杖无他术,而沙漠之用,则以鞭笞。吾欧精神,自古泊今,恒与此异。凡亚民所谓国法、家法者,自吾人视之,直暴虐侮人而已”之语。严复为之感叹:“孟氏之言如此。向使游于吾都,亲见刑部之所以虐其囚者,与夫州县法官之刑讯,一切牢狱之黑暗无天理,将其说何如?”严复认为州县刑讯与刑部虐囚、牢狱黑暗乃是中国人的甚酷之罚的典型代表,他不禁要“请为同胞垂涕泣而道之。”[法]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63页。 也有人因州县品质之可贵而为理想对象。张伟仁先生通过对有关资料的分析,认为良幕循吏汪辉祖为法制工作者的典范,对其不吝赞美之词:“他是一个十分博洽的人,既懂得法理,又熟悉实务,对于传统文化也有深切体会,因此他对清代社会的价值和导向都有清晰的认识,并且决心以其才能去提升并匡正这些价值和导向,所以他以追寻公平正义为职志,以为民谋福为目标。……所以整体而言,作为一个‘法律人,他给我们的印象,绝不是一个只会搬弄条文的法匠,而是一个博洽通达、忠恕公正,而又和蔼热忱、与人为善的谦谦君子。”张伟仁:《魔镜——法学教育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 大致说来,持正面看法的多属于“官方”的理想表达,持负面看法的多属于“非官方”的实况描绘。“官方”的表达固然有裁剪或缘饰的成分,但其同时也在表明统治阶层所倡导和认同的价值和目的,型塑着统治阶层的理想类型。州县官司法追求的目的涉及到对政治主流意识、法律与其他规范的位阶、司法者与民众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具有典型的“官方”特征。因此接下来的论述将主要从清代官方的主流意识入手,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兹将清代州县官司法追求的目的择要分析如下:
(一)雍睦和谐的治下秩序
博登海默认为,“秩序这一术语将被用来描述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特别是在履行其调整人类事务的任务时运用一般规则、标准和原则的法律倾向。”[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 法律的作用正在于调整人类事务,为社会治理提供一种规则之治。秩序作为法律的形式价值,是法律当然的价值追求,如果与西方稍加对照就会发现,传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社会结构的恒稳,即使偶有失范,也能自我调整,也因之令人惊讶地在人类文明中保持一种“超稳定系统”。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这种稳固的结构被马克思·韦伯称为中国的传统主义,他进而认为这样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法律规范的形式和内容以及司法的性格。[德]马克思·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的确,中国传统司法者身上有着浓郁的秩序情结,法律只是维持秩序所依赖的一种工具。当法律的适用和民众的诉求与秩序相抵牾时,总是退至一旁,沦为秩序的仆役。清代州县官直接面对着平民百姓,是处理民间冲突的第一责任人。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通过惩戒、教化、劝谕、调停的方式消解官司,维护治下秩序的和谐,这也是州县官司法最根本的出发点。
首先,自然秩序的和谐是司法运行的必要前提。按中国传统观念,万物皆有内在的运行机理,春夏草木滋生、秋冬肃杀蛰藏,是宇宙间永远不易的自然秩序,万物皆需与此配合调适,天人之间灵动感应而相互作用。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82—283页。 根据阴阳五行的观点,刑讼代表着“阴”,与秋冬时节的万物凋零、萧瑟、肃杀相关联,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需“承天之道”来“治人之情”,否则就会有上干天和的灾变和祸及子孙的冥遣。韦伯认为,传统中国之所以能维持几千年来牢不可破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秩序,是由于“秩序神”的庇佑,“上天是古老秩序的保护者,也是合乎理性规范的统治所保证的安宁的保护者,而不是非理性命运急转的根源”,[德]马克思·韦伯:《韦伯作品集Ⅷ·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天乃秩序之神。在中国,天也被称作“百神之大君”、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十五,《郊义篇》,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02页。 “群物之祖”。《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67页。 由于天的“无所不在、高岸邈邈”,夏勇:《民本与民权:中国权力话语的历史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州县官的司法行为就绝不简单是作出事实判断和司法裁决,它内含着抽象化和神秘化的天道,若刑讼宽恕,则顺天之道,福报深厚;若刑讼苛重,则违天之道,有损阴德。犯罪行为的出现意味着自然秩序遭受破坏,州县官自然要对这样的犯罪行为进行惩戒,不能滥施法外之仁,使杀人者幸逃法网;但又需念及“民有王法,幽有鬼神”的阴鸷观念,多会清理狱讼、救济人命、疑罪从赦。
其次,王权秩序的和谐是司法运行的根本保障。在中国专制集权的中央政治体系之下,法为王者治天下之具,整个官僚体制的首要目的就是维护王权秩序的稳定,司法作为行政之一环,必须服膺于稳定王权秩序的需要。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在中国,法出现以后,它却既不维护传统的宗教价值,也不保护私有财产,它的基本任务是政治性的,对社会施以更加严格的政治控制。”[美]D.布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而到清代,这种对社会秩序的控制更加严密。清王朝对威胁自身统治的谋反、叛逆和严重危害王权秩序的杀人、强奸、劫盗案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因为这些案件的出现意味着王权秩序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冲击。州县官作为帝国权力体系中最低的组成,同时也是整个官僚集团在民众面前的代理人,需要对这类严重刑事犯罪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最大限度地克制恣意,以便自己的决定和态度能够符合维护王权秩序的要求。州县官作为整个司法的起点,其扬善抑恶、惩奸警愚的主要目的也在于维持王权秩序的稳定,促使“公”道得行。
最后,民间秩序的和谐是司法运行的重要考量。关于中国传统的社会控制,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皇权弥漫于社会的每个角落,清代“连坐”、“逃人法”等制度的存在,更会使个人往往由不可归因于己的原因而转相攀染,致使人们无可逃于皇权编制的罗网之中。但事实上,支配传统中国的是一种“有限的官僚制”,马克思·韦伯曾提出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降低,乃至消失。”参见[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国家权力仅及于州县一级,州县以下的广袤区域则主要依靠民众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情理、习俗、村规、族约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形成了一种靠地方性知识维系的非正式秩序。由于“官”、“民”两元社会的对立,州县官对民间秩序的维护以“民自相安”为最大信条,对于户婚田土等民事案件或者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与严重破坏王权秩序的命盗重案迥然有别。此外,这种追求的形成也与当时“居官安静”的官场风气有关。清代政府考察一个地方官的政绩,关键是看其辖区内的治安状况,无讼则安。如果一个州县官“好收受词讼”,则说明该官员性喜多事,搅扰地方安静,这显然与官员“政简刑清”的理想背道而驰。在这样的一种文化影响和政治风气下,追求民间秩序的和谐自然成为州县官们在司法中的共同意识。
(二)道德教化的裁判意旨
德国法学家耶林曾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比作是法学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够征服其中的危险,就再无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了。[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但是,传统中国的法律与道德互为表里,相互纠缠,始终没有摆脱在法律中的倾没之虞。古代中国并不确定法律的救败之功,而是相信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道德教化的力量使人知耻而无奸邪之心。前引B10,第310页。 道德问题不待于法律而解决,法律问题却亟于从道德中吸取力量。“德刑并用,常典也。”(汉)荀悦:《申鉴·时事》,吴道传校,载《诸子集成》(第七册),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10页。 司法本为辅助教化而设,教化的目的是推行德治,从而实现“教化流行、德泽大洽”的政治局面。法律为道德所服役,德之所失,刑以治之,倘若德教所及,民风淳厚,人人揖让有序,不令而从,法律自可束之高阁。道德是由内而外的自我提升,而教化提供一种外部的社会氛围,由外而内,推近及远,旨在实现臻至大善的社会氛围,这其实正是礼法社会在司法中的映射。道德与法律的融合正如陈顾远先生所说,“礼以德教为主,法以刑教为务,四维八德均可于刑律内求得其迹,法律与道德充分显示其同质异态之体相。”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5页。 同样,州县官在司法中也追求道德主义与实用主义的交融与并立,以道德教化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之一。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道德教化是评判司法的价值尺度。在传统中国的德治背景之下,“德主刑辅”的原则不断被强化。“德教者,人君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汉)仲长统:《昌言》,载魏征:《群书治要》(第九册),卷四十五,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89页。 统治者为显治下民众富而好礼,希望通过学校、社会和司法上的教育随时随地“导民于义”,以此提升民众的精神境地。在行政兼理司法的体制下,州县官既是司法的裁决者,又是道德的宣教者,一个理想的司法官员应该举责善之谊、启天良之心,使道德教化寓于司法之中,以达到治世者高远的道德政治理想。康熙帝就认为,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缘由是,法令虽禁于一时,而教化能维于可久,教化不先而徒恃法令,乃是舍本逐末之举。《清实录》(第四册),《圣祖仁皇帝实录一》卷三四,康熙九年九月至十二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第461页。 州县官作为帝国基垣,身负阐化宣风之职,必将道德教化贯注于司法之中,“国家之设县令,不但使之收一方钱粮,断一方词讼,必责以移风易俗之事。”(清)王景贤:《牧民赘语》,义停山馆集本,载《官箴书集成》(第九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650页。 而道德教化作用尤重,“致治之道在正人心,人心正直,则嚣竞自息。而庶绩允釐,人心偏私,则诈伪日生,而习俗滋弊。朝廷崇尚德教,蠲涤烦苛,适于宽大和平之治。”(清)刚毅:《居官镜》,清光绪十八年刊本,载前引B23《官箴书集成》(第九册),第295页。 自然,道德教化就成为评判州县官司法的重要价值尺度,雍正帝就曾要求,“州县官为民父母,上宣朝廷之德化,以移风易俗;次奉朝廷治法令,以劝善惩恶。听讼者所以行法令而施劝惩者也,明是非,剖曲直,锄豪强,安良懦,使善者从风而向化,恶者革面而洗心,则由听讼以驯至无讼,法令行而德化亦与之俱行矣。”(清)田文镜:《钦颁州县事宜》,载郭成伟主编:《官箴书点评与官箴文化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这一训喻既是清代统治者的治道理想之所在,同时也表达了州县官断狱理讼的最高境界。
其二,道德教化是化导诉讼的有效手段。道德教化的核心是以伦理纲常和道德原则作为说教的工具,以此谋求利益平衡和结果妥当。中国传统法律把对诉讼的解决寓于道德教化之中,致力于以一种劝喻性的、非强制性的方式治理来感化民众。州县官需要在司法中尽最大可能唤醒民众心中的良善之心,不能因民众一时的嗜欲蒙蔽而否认其本身仁义礼智的道德人性。司法的公正和权威并不在于法律的准确适用,而在于做到“事通理顺”,谋求道德上的可行性。州县官办案的基本原则是:“人有争讼,必谕以理,启其良心,俾悟而止”,黄溍:《金华黄先生全集》,载《四部全书集部》第1323册,影印清景元抄本,四十三卷。 在司法中应该“随人随事随时随地谆谆教诲”,(清)袁守定:《图民录》,清光绪五年江苏书局重刊本,载《官箴书集成》(第五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218页。 若民众彼此能够是非判、意气平,自然能够达到“案结事息”的目的。因此,“留心教化者,随事随人皆可劝导,如审理案件,就案内人,依傍本案,推广言之,凡孝悦、忠信、礼义、廉耻之行,皆堪触发。”[清]叶镇:《作吏要言》,徐栋辑:《牧令书》卷十六,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载《官箴书集成》(第七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353页。 经由教化,让案内人自觉遵守礼俗,是化导诉讼的最好方式。州县官作为司牧之官,若平时没有一点担忧民众有不善之心,又没有一句劝民为善之语,直待犯事而加刑,“未刑之先如何不至误犯,既刑之后如何不复再犯,均未之计,终非弼教之意。”(清)陈宏谋:《手札节要》,载前引B28《官箴书集成》(第七册)。 如果能以道德教化来解决诉讼,不仅能够平两造之争,亦能耸旁观之听。无论是案内人或者案外人,如果能通过教化看到自身的道德缺失,从而反思自我,就能够逐渐做到明理知性、嚣风渐革,最终恢复州县官所期待的人与人之间和气致祥、厚风美俗的社会。
其三,将道德教化寓于法律之中也有着简约治理的现实考虑。在中国传统“国权不下县”的政治模式之下,国家权力对县以下的区域难以鞭及,传统乡土社会处于和谐、散漫的状态之中。州县官有“一人政府”之称,其管理事务极为庞杂,堪用之人手又颇为有限,这样的政府模式迫使州县官将司法成本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之下。道德贵简而忌繁,其弥散性可济法律之穷,若是运用伦理纲常等道德性的手段来解决纠纷,那么士绅、乡党、宗族等地方精英会自觉地参与到案件中来,从而使大量案件消化于法庭之外,以此俾兴孝悌之行,而厚宗族邻里之恩。即使诉讼到官,州县官也需对受挞之人反复开导,令晓然受挞之故。这样未受挞者也可潜感默化,从而让未讼者可戒,已讼者可息,在处理问题时自然易于接受。如果一个州县官能够在听断之际而摘奸发隐、片言折狱而令人心咸服,使得涉案民众或有所戒惧,或感从而化,就能正本清源,达到息“刑罚清于上,习俗美于下,使人乐为谨愿,而不乐为黠且悍者”(清)路德:《邱叔山府判录存序》,载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847号,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0年版,第4644页。 的社会效果,也会因符合中国传统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而被人称道。因此,我们需要把州县官的司法行为,放置到一个深厚的道德背景下去理解。
(三)敬让博爱的仁道司法
仁是儒家在生命中体会出的理性原则,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是儒家思想的要义所在,仁的思想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逐步扩展为一种政治社会伦理,对传统社会有着深远影响。由于仁具有“微言大义、既实且虚的属性”,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页。 故其涵义不能一语道尽。大致说来,“仁”包含着仁道、仁恩、仁恕、仁义、仁政、仁者之刑、仁爱德让、仁爱忠厚、宽仁之厚、务于宽厚等概念,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也有人称之为中国正义论(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中国正义论(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是生活儒学在伦理学层级上的具体展开,侧重于制度伦理学问题,即探索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一般原理。……儒家的正义论有一个基本结构‘仁→义,即仁爱情感为正义原则奠基。” 参见黄玉顺:《情感与存在及正义问题——生活儒学及中国正义论的情感观念》,资料来源于中国孔子网 http://www.chinakongzi.org/guoxue/lzxd/,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2月10日。 或中国式的同情心。“孔子所谓‘仁之真义,简单的解释,即是一种同情心。所谓仁爱即为此种同情心之表现。因为‘仁之中心点为慈爱,故‘仁为一切伦理之根本,作成我民族之美德。”参见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转引自前引B32,第66页。 仁同时也表明了一种君子精神,马克思·韦伯在《儒士阶层》一书中说道:“儒家中间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将君子精神视为‘仁,仁是一种美好的社会伦理,仁的意识与传统的君子美德溶为一体,成为自我修养的目标。”[德]马克思·韦伯:《儒士阶层》,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18页。 “仁”的思想自孔孟之后便成为中国传统法律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亦是司法者不断倡导的理想化意境,仁的精神体现在清代州县官身上,就是以宽仁之心对待民众,追求敬让博爱的仁道司法。
其一,“仁”是必要的法律素养。根据冯友兰、张岱年的学说,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一种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是一种“求善”的哲学。“求善”反映到司法上,就是追求仁道司法,用法而施以仁者之心。刘熙《释名》谓:“仁,忍也。好生恶杀,善含忍也。”王先谦撰集:《释名疏证补》卷4,《释言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 司法者直接面对的是陷入囹圄的民众,手中握的是很难收到制约的“刀把子”,宽严生死,只是“仁”与“不仁”的一念之间。因此,只有本着“仁者之心”来处理案件,才能体现出裁决者基本的法律素养。朱熹云:“有其心,无其政,是谓徒善;有其政,无其心,是为徒法。”(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七,《离娄章句上》,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57—258页。 这表明有司断案若无仁心,即使严格依律,也难逃“酷吏”之名。只有怀仁心而用仁术,才能如微风之嘘物,泽被长久;若是刚猛余而仁不足,则如疾风之荡物,覆辙多矣。仁也是生者之谓,戴震说:“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页。 司法者就应以生人为念,表达“敬让博爱”的人道主义关怀。由于家国同构的传统政治模式,州县官与民众的关系习惯被表述为一种“谊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体恤”的共存状态,若是有人被卷入官司之中,那往往意味着灾难的开端。一人向隅而泣,为之凄怆于心,为民父母者又何忍再枉用刑罚?也正因为如此,州县官能够以宽仁之心来进行司法也就被寄予了无限厚望。
其二,“仁”是律例的精神之源。陈顾远曾言:“仁道恕道在中国固有道德中占有重要地位,法律上亦极端表现之。”前引B20,第57页。 按照中国传统法文化,仁并非是自外于律例的道德学说,而是通过与律例的融合,内化为律例的精神之源,成为律例获得妥当性的主要力量之一。方孝孺言:“古之人既行仁义之政矣,以为未足以尽天下之变,于是推仁义而寓之于法,使吾之法行而仁义亦阴行其中。”(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深虑论10首》,徐光大校点,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沈家本也曾道:“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清)沈家本、伍廷芳:《删除律例内重法折》,载朱寿彭:《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25页。 可见古人对“仁”在法律中的功用推崇备至。依据官方价值,仁本就蕴含于律例之中,两者并无畛域之别。虽说仁道于律例之中未有明文,且律文繁简不一、卷帙浩繁、难以尽悉,但不能以此否认仁的存在。清人蒋陈锡写道:“仁者执律而断狱,虽罹于死,有一线生路之可求,未尝不求之,求之亦在律耳。”(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怀效锋、刘俊点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对此,袁守定在《图民录》中有妥当的解释:“一部《大清律》损益百王,原本经术,其设为大防,以防民之流,皆圣人不得已之苦心,而节目委曲之中,具见忠厚仁爱之意。” 前引B27,第231页。 如此也能使执法之吏有所把握,培养其好生之心。可见,以仁者之心断狱不仅是司法官员在品格上的自我律求,也是体察律意的一种表现。
其三,“仁”并非不辨是非的妇人之仁。仁者司法追求的不是简单地要求做到慎用刑而不留狱,它还有“生道杀民”的内涵,即在司法之时虽本生人之心谨慎审理,但若是所犯确系罪大恶极、干伦犯义之罪,也需不得已而杀之,切不可有不辨是非、糊里糊涂的妇人之仁。这正如朱熹所云“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其中”,(宋)朱熹:《朱子语类》(第六册),卷七十八,《大禹谟》,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09页。 清人汪辉祖所言“治无成局,以为治者为准,能以爱人之实心,发为爱人之实政,则生人而当谓之仁,杀人而当亦谓之仁”。(清)觉尔乌通阿:《居官日省录》卷二,清咸丰二年刊本,载《官箴书集成》(第八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47页。 儒家一贯主张善善恶恶、是非分明,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在司法中能够以“无偏无颇”的中道思想进行审断,本就是仁之要义所在。苏亦工:《公正及公益的动力——从〈未能信录〉看儒家思想对清代地方官行使公共职能的影响》,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1期。 民众好生恶死,情之所同,仁者固然不忍由民众由生致死,然而死者之含冤,甚于生者之求脱,在于情于理都难容忍的情况下自然需要明正典型以慰亡灵,这才是仁之旨归。裕谦在《救生不救死》一文中言到:“然而圣人制刑,或取生人而致之死,非杀人也,杀其杀人者也。书曰,‘欲并生哉,彼杀人者既逆其情,而不与生者并生,则执法者必据其情,而与死者并死,故曰杀人者死,法之至平也。……至于情真罪当,法无可宽,则必明正典刑,以彰国宪,仁之至也。”(清)裕谦:《救生不救死论》,载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十八,“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847号,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0年版,第4335—4338页。 杀生以慰死,这也是尊重生命的另一种体现。
其四,“仁”是爱民情感的重要体现。孔子创立的仁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爱人,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言到,“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及即人者也……仁以同情心为本,故爱人为仁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这就是说人与人之间要相爱,治民者亦需宽政爱民、刑罚宽省。朱熹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陈来:《朱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 张载云“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宋)张载:《正蒙·中正》,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页。 即说仁本身是以爱为基础而发的情感,是最高的道德。“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八,《性情》,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82页。 仁是以己为基础而成长起来的成熟理性,它要求推己及人,“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00页。 州县官作为民之父母,自然需要以“爱”作为治理百姓的基本信念,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赤子之生,无有知识。然母之者,常先意得其所欲焉。其理无他,诚然而已。诚生爱,爱生智。惟其诚,故爱无不周;惟其爱,故智无不及。吏之于民,与是奚异哉?试有子民之心,则不患其才智不及矣。”(清)瑞常:《官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州县官就要像慈母一样“噢咻抚摩”,化如时雨,惠如春风,与子孙痛痒相关,随呼则应,虑及精微,计及长久。在司法中更是要以庄敬心态碎琐推敲,为百姓通盘筹划,以求公平、仁恕的结果。对于州县官来讲,用法而施以仁恕之心可以达到重视生命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是其居高临下对待自己治下子民的一种道德宣称。他们只有超越制度规范,追求一体之仁,才能上顺天意,下顺民情,保证司法的正当性与合宜性。
二、州县官司法追求之躬践
和西方发达的纯粹理性不同,中国传统法文化是一种特别偏重实际的文化,保留着浓厚的“实践理性”特征。因此,司法者在传统法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追求并非是形式化、抽象化的理论体系,而是切实可行的行为指引。“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9页。 “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前引B54,第151页。 理想价值的提出以实践能够达致为基础,其目的不在抽象原则而在解决具体问题,因此很少作凌空虚蹈的乌托之思。作为传统司法者的典型缩影,清代州县官在司法中身兼法官、检察官、警官、验尸官、典狱长之职,随事推恩,因心出治,堂上朱笔一点可令民间流血千滴,纸上黑烟一污而使家资耗损大半,其对司法价值追求的实践程度实乃是影响地方司法运作极为关键之所在。尽管清代的基层司法制度存在那么多的罅隙,并且因司法者的黑暗无理、贪渎酷虐而使其衙署有“活地狱”之称。然而通过对清代基层司法状况的研究发现,清代州县官并未摆脱其价值观的影响,他们中的“精英阶层”通过书信、官箴书、笔记等形式来探讨和宣扬司法技艺,在司法中积极地对其价值追求作出回应,以其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娴熟法律技巧推动着司法的实际运作,为实现其儒者之刑名的治世理想而将价值追求躬践于行。
(一)本诸政简民淳,致力闾里无讼
由于对和谐秩序的极致追求,州县所辖的乡土社会形成了一种反诉讼的社会,宗族、乡党以表面上的和谐将纠纷消化于内部,州县官也将使民无讼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责之一。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一大特点是家与国同构或者说家国一体化,这种结构导致了清代州县官“治国如治家”的思维模式,在司法中也形成了“父母官诉讼”。因此,处理国民争讼一如排解家庭纠纷,教之以礼,辅之以刑,以求和谐。古代官僚意识形态采取道德主义的立场,喜欢官民之间能有一个良性的互动。既然官府以一种宽仁无为的面貌出现,并且也采取了一种“精简”的治理模式,而且宣称这样是为百姓着想,在官府看来,百姓也需以自己的行动表达对官府“良苦用心”的理解。赋税钱粮固不可减免,诉讼纠纷却能忍让消除。“太平百姓,完赋役,无争讼,便是天堂世界”。(清)余治:《得一录》卷九,《宗祠条规》,清光绪五年森宝阁排印本,载前引B45《官箴书集成》(第八册),第606页。 无讼的出现和田园牧歌的生活是划着等号的,这也符合统治者维持和谐秩序的价值追求。
依照案件的不同进展,州县官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使民无讼。其一,通过劝民告示、词讼条约、劝民歌、忍讼歌及宗谱、乡约等多种形式进行劝民息讼,培养民众的畏讼、惧讼心理,防讼于未然。州县官劝谕民众在面对诉讼时应该忍让为上、各安其分,且不可贸然兴讼,如果不听州县劝导,执意兴讼,那么“一字入公门,九牛拉不回”,最后会因打官司失业废时,难以周全。《宰惠纪略》讲:“劝吾民要息讼,毋为官清,清官断十条路,九条难预定,有理官司尚且输,无理如何能侥幸?”(清)柳堂:《宰惠纪略》卷一,清光绪二十七年笔谏堂刊本,载前引B23《官箴书集成》(第九册),第493页。 即使己方有理、官员清廉,却还有胥吏勒索、差役为难,如果贸然兴讼,很可能落得破家伤身,受无穷之祸。如果善于劝民息讼,使其知难而退,忍忿兴让,则“虽未便使民无讼,亦必有效于民,不无裨益”。前引B27,第196页。
其二,采取农忙停讼的方式来限制诉讼。这主要针对的是田土、户婚、钱债一类案件。在中国农民的眼里,每一粒谷子都是珍贵的,田土问题更是涉及到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一旦涉及,百姓不惜以命相搏。正如清人方大湜所言:“户婚、田土、钱债、偷盗等案,自衙门内视之,皆细故也。自百姓视之,则利害切己,故并不细。”(清)方大湜:《平平言》卷三,《勿忽细故》,清光绪十八年资州官廨刊本,载前引B28《官箴书集成》(第七册),第675页。 但是大多数州县官却认为,百姓如果因为这些鼠牙雀角之类的“细故”而陷入官司之中,甚而耽误农事,无疑是因小失大的愚昧之举。制止的方式当然是在农忙时对这类案件不予受理。很多州县官如黄六鸿一样,主张在农忙停讼期间在衙门前高挂“农忙停讼”牌,申明“非命盗逃人重情,一概不准。”(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农忙停讼》,清康熙三十八年金陵濂溪书屋刊本,载《官箴书集成》(第三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334页。 不过也有例外情况,对“天旱争水、黄熟抢割、争娶打抢、聚众打降等事,停讼之时亦应准理”,不能“以休息农民之举,竟为宫衙偷闲之会”,使农民奔走无据,更添烦乱。陈弘谋指出,“农忙虽有停讼之例,亦有不应停之例。如乾隆二年,北臬司阎熙尧条奏,……州县自理词讼务须分别事情轻重缓急,随时酌准,不得藉称农忙既置民瘼于罔闻。又乾隆四年定例,或因天旱争水、黄熟抢割、争娶打抢、聚众打降等事,停讼之时亦应准理。……总须有一番分别,明白晓谕不可概以停讼自置告案缓急于不问。以休息农民之举,竟为宫衙偷闲之会,且使农民之进退无据奔走伺应更甚于开忙也。”参见(清)徐栋辑:《牧令书》,卷十八,刑名中,《申明农忙分别停讼》,清道光二十八年刊本,前引B45《官箴书集成》(第八册),第399页。
其三,对涉讼的民众进行感化调息。首先是鼓励乡民调息。“闾阎争端,多起薄物细故,凡乡里口角,亟宜邻里自相劝解。即至涉讼公庭,尤以和息为善。……令乡正党政处息讼案得宜。”(清)王德茂:《和息》,载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847号,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0年版,第4573页。 一则乡民和事符合礼制古义,而且乡民耳目之下不同于县官案牍之间,以民所处较在官所断更为公允。袁守定指出,“乡民和事是古义:周礼、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言民有相难之事,为之调和。有伤人者以乡里之民,共和解之也可见乡民和事”。前引B27,第196页。 二则这些乡民在当地或德高望重或稍有名声或身有功名,他们“世居其土,见闻熟悉,则察识易周,出入阊井,情意相孚,则利害相悉”,便于州县指使。三则将纠纷消弭于当地,无需赴县堂而具控,可以省下不少盘缠费用,可以让纠纷之人保全身家,息事宁人。袁守定就建议:“如到一县。徧谘所治士耆之方正者,以折记之。注明某人居某里,以其折囊系于绅。每行乡村,有所得,即补记。遇民来诉,批所知相近之士耆处释即令来诉者持批词给之,立言剀切,足以感人。必有极力排解以副官指者,此或息讼之一端也。”前引B27,第196页。 其次是在亲自对原被两造感化教育,格之以诚,持之以劝。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运用纲常伦理、道德教化便于解决亲属、邻里纠纷,可收到和息止争的效果。
其四,严惩诬告。与州县官渴望清净的心态相反,民间从来不乏“黠且悍者”助长刁健之风。乡土社会有“无谎不成状、无赖不成词”的风气,乡民出于诉诸情感的需要,“或因口角微嫌而驾弥天大谎,或因睚眦小忿而捏无影之词”,(清)吴宏:《纸上经纶》,载《明清公牍秘本五种》,郭成伟、田涛点校整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州县官于此可谓深恶痛绝。对于这些诬告者,州县官无不严惩,一般以“以所告之罪罪之”。陈朝君曾说,“本县下车以来,息讼止争之论,业已言之谆谆,而诬告犹有张应林者,真可骇异。……朝廷法度极严,莫以健讼而轻犯,常怀天理,勿昧良心,倘有捕风捉影,指鹿为马,以陷害良善如张应林者,即以所告之罪罪之。”参见(清)陈朝君:《蒞蒙平政录》,清康熙二十八年刻本,《为申饬诬告以息讼端事》,载《官箴书集成》(第二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781页。 如果确定是诬告,特别是有讼棍参与者,则严加惩处,以罚奸人之心,“如审系原告情虚,则必须依照律例,加等严惩,断断不宜姑息,庶诬告者知畏,而讼日稀矣”。(清)刘衡:《州县须知》,宦海指南本,载《官箴书集成》(第六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13页。 《大清律例》也明确规定:“无论所告虚实、诈赃多寡、已未入手,俱不分首从问拟,发近边充军。仍先在犯事地方枷号三个月示众,满日再行发配。”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校考注·卷三十》,《刑律·诉讼·诬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5页。 如此规定主要也是从实现“无讼”的角度出发。
(二)通乎理法之准,究心情罪相协
在司法实践之中,对道德教化的最好回应就是作出“合乎人情、宜乎世俗”的判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情理至上的诉讼价值观,主张法的生命在于情理:“原夫礼律之兴,益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坠,非从地出也。”(梁)沈约:《宋书》卷五十五,《傅隆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50页。 道德的实现需在情理中求得。对于州县官而言,在判决中表明出情理的妥当性往往可以体现出“父母官”的温情主义,而这需要深厚的修养和高超的技巧。清人俞樾曾言:“通达治体于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皆到,虽老于吏事者,不能易也。”(清)翁传照:《书生初见》,清光绪刊本,载前引B23《官箴书集成》(第九册),第355页。 传统中国的情理与法不是相互对立、不能融合的,而是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两者相互倚重,理出于一。所谓“律设大法,礼顺人情”、(清)汪辉祖:《学治续说》,清同治十年慎问堂刻汪龙庄先生遗言书本,载前引B27《官箴书集成》(第五册),第298页。 “人情所在,法亦在焉”,(元)脱脱:《宋史·贾易传》卷三百五十五,《列传》第一百一十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173页。 在处理法与情理的关系上,应该“听断以法,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借”,(清)汪辉祖:《学治臆说》,载前引B27《官箴书集成》(第五册),第277页。 州县官在司法中践行的是“情罪相协”的处理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情”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含义,而是一些与案件有关的要素的整合,要而言之,州县官在司法中谋求情理之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察情,即察明案件事实。州县官身处基层,其面对的案件诈伪百出、讼情万变,州县官要想谋求案件结果的妥当,首要任务就是仔细研鞫,得出实情。张五纬在《未能信集》中说:“民间讼事不一,讼情不齐。其事不外乎户婚、田土、命盗争斗,其情不外乎负屈含冤,图谋诈骗。听讼者即其事察其情,度之以理,而后决之以法。” 前引B46。 这里所讲的“情”,显然指的是得出案件之情。在案件之情查明的时候,州县官自然可以放心地以道德立论,对案件如何判罚进行斟酌;在案件晦暗不明,也就是出现疑狱的时候,采取情罪相协的方式既是出于慎刑的考虑,也可以减少案件的差错,避免自身的责任。
第二,揆情,即揆诸风俗人情。传统中国法具有情感之法的特征,涉讼民众追求的是一种朴素的实质正义,州县官应尽量使裁决符合民众出于自然情感的价值判断。清代循吏汪辉祖曾言:“幕之为学,读律尚已。其运用之妙,尤在善体人情。盖各处风俗往往不同,必须虚心体问,就其俗尚所宜,随时调剂。”(清)汪辉祖:《佐治药言》,载前引B27《官箴书集成》(第五册),第323页。 虽然强调的是入幕须知,但是用在州县官身上也应适合。道光八年广东发生了一起因兄逃走恐父自尽而自愿代兄顶罪的案件中,县官认为该犯所行情殊可矜,与奸徒受贿顶凶者迥然有别,未便照减正犯二等之例科断。以上处理就是从人情出发,置事之大小,推情之轻重,使纠纷得到一个比较符合中国人情感思维的判断。
第三,准情,即准情而用法。谋求情与罪的均衡,努力做到“律例有依,情理无碍”。清代州县官兼有行政、司法等多重职能,其在作出判决时往往超越法律范围而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考虑情理因素,以满足其职能从法律向社会的延伸。这就要求对社会风俗有一个必要的考虑,如果地方官能够周知民间风俗,则有利于做到事通理顺。但是尊重百姓的风俗习惯并不代表着不遵守法律,这两者是可以变通的,方大湜说:“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但本案情结应用何律何例,必须考究明白,再就风俗准情酌理而变通之,庶不与律例相违背。”(清)方大湜:《平平言》卷二,《本案用何律例须考究明白》,载前引B28《官箴书集成》(第七册),第653页。 也有的州县官在习俗与法律冲突时会弃法用情,例如,清代部分地区的“转房”问题虽为法律所严禁,却被一些州县官所默认。清代州县官在判词中的经典表述是“本应——姑念”、“依律——宽免”等句式,这实则在宣扬本官对律法和人情都有照顾。清人樊增祥曾说:“州县终年听讼,其按律例详办之案,至多不过十余起”,(清)樊增祥:《樊山政书》卷二十,《批拣选知县马象雍等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95页。 他在这里采用的应该是狭义解释,“按律例详办之案”指严格地依律处断,这在州县司法实践中是比较少的,更多的应该还是律例和情理两相照顾,“或移情就例,或择例就情,务求平允而宽厚,则问官与犯人两无所憾。”(清)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十一下,《与次儿论谳狱第二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2243页。 在司法中采取“情罪相协”的方式既符合中国文化的多值逻辑,也可以起到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作用。
(三)阐发律意精微,期孚哀矜折狱
仁恕爱民的价值追求强调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生命意境,亦是具有普适性的道德理想和精神,仁恕爱民落实到司法实践上,突出地表现为以一种哀矜、矜恤的心态来面对卷入官司的陌生民众,努力做到哀矜折狱。哀矜折狱作为一种司法概念,早在先秦儒家经典中就有记载,《尚书·吕刑》记曰,“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其中。……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狱成而孚,输而孚。”《尚书大传·周传》引孔子言作解:“子曰:‘听讼者虽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也。”蔡沈《书传》云:“‘哀敬折狱者,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五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5页。参见梁凤荣:《〈尚书·吕刑〉司法理念与制度管窥》,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10期。 哀矜折狱的思想要求司法者将仁厚之道置于刑罚之先,在面临罪犯时要从容于道德,餍饫于仁义,以臻忠厚之至。袁守定解释:“非口才便给之人,可以折狱,惟温良忠厚之长者,乃能折狱也。”前引B27,第194页。 这也是强调司法者要具有仁厚品行,对涉讼之人有审克恻怛之心。徐宏先在《修律自愧文》中强调官员在读律时,要“总是一片哀矜恻怛之心,不欲轻致民于死之意也”。《皇朝经世文编》卷九十一,《刑正二·律例上》,载魏源:《魏源全集》(第十八册),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31页。 清代有官员将哀矜称之为“律心”,姚文然说:“凡讲论律令,须明律意,兼体作律者之心。律意者,其定律时斟酌其应轻应重之宜也。如秤锤然,有物一斤在此,置之十五两九钱,则锤昂;置之十六两一钱,则锤沈;置之适当,则不昂不沈,锤适居其中央,故曰刑罚中。中者,中也,不轻不重之谓也。此律意也。何谓律心?书曰:‘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曾子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此律心也。譬如一秤锤也,存心宽恕者,则用锤平,且宁于其出也,微失之昂;于其入也,宁失之沈。若存心刻核者,则其用锤也,出必欲其沈,入必欲其昂,此非锤之不平也,用锤者之心不平也。故,用律者亦然。”前引B81,第27页。 以哀矜之心来权衡法之轻重,并且往往表现出对涉狱子民的怜悯和对爱民不足的切责。州县官在司法中的哀矜折狱主要有几点表现:
其一,视民如伤。清代民谚素有“灭门的知县”一说,又有“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之语,可见州县官处于人鬼关头,在断案时毫厘之差,即可令人生死攸系,因此需对涉案百姓多加保全。“惟于当死之罪,求其生而减至配徒,于当配徒之罪,求其轻而减至笞杖,庶寓仁育于义正之中。”前引B27,第92页。 州县官作为民之父母,无论大小之狱,都要尽量做到“以情恕”,不能对涉狱民众的苦痛无动于衷。裕谦主张在断案时,“如一切杂案,愚民误触法网,无杀人之事,而又拟死之条者,哀矜其情,委婉其事,立义于法中,而施仁于法外,使其惩恶有地,迁善有门。”前引B47。
其二,慎用刑戒。“慎”是清代基层司法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传统“慎刑”思想在司法中的反映,州县官在断案时如果能够做到谨而步,慎而趋,不遽用刑杖,才能表明州县官的悯恻之心。清代州县官权专责重,虽说有律例的规定和“审转”制度的约束,然而朝廷礼法并不会对州县官形成有效的约束,用刑慎与不慎仍存乎长官一心。袁守定曾经描述过平民受杖的惨况,“平民一经受杖,则终身玷蔑,虽创既平,扪之犹有余痛。尝见有无辜受杖,其父母妻子相视环泣,虽族邻慰之,终邑邑无色。竟有忧愤成病而卒及自尽者,每念及此,大可畏也。”前引B27,第207页。 棰楚之下,痛昏之中,何求而不得?州县官若轻易用刑,表明其缺乏基本的品质和素质,仗势凌人,欺虐庶民,不合哀矜之道。一个好的州县官应该在案件中“细审明辨”、“慎刑恤民”,实行刑戒。陈弘谋在《从政遗规》中有“五不打”、“三怜不打”
“五不打”即:“老不打(血气已衰,打必致命),幼不打(血气未全,打必致命,且老幼不考讯,已载律文),病不打(血气未平复,打则病剧必死),衣食不继不打(如乞儿穷汉,饥寒切身,打后无人将养,必死),人打我不打(或与人斗殴而来,或被别官已打,又打,则打死之名,独坐于我)”。“三怜不打”即:“盛寒酷暑怜不打(遇有盛寒酷暑,令人无处躲藏,拥毡围垆,散发振襟,犹不能堪,此时岂宜用刑,盖彼方堕指裂肤,烁筋蒸骨,复被刑责,未有不死者),佳辰令节怜不打(如元旦冬至,人人喜庆,宜曲体人愿,颐养天和,即有违犯,怜而恕之),人方伤心怜不打(或新丧父母,丧妻丧子,彼哀泣伤心,正值不幸,再加刑责,鲜不丧生,即有应刑,尚宜姑恕)。”(清)陈弘谋:《从政遗规》卷二,中华书局五种遗规排印本,载《官箴书集成》(第四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253页。 的说法,黄六鸿亦在其《福惠全书》中规定了十七项拷讯禁止条款,这些慎刑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州县官的哀矜心态。
其三,宽严适当。有“律心”之谓的哀矜无疑是抑制虐法的有力道德因素,州县官在断狱中如果能够从宽,可令死者得生、重者得轻,既可避免冤滥,又能保全赤子,何尝不是哀矜折狱的一种表现?刘衡就建议:“州县官审理词讼,如审系被告理曲,但非再犯,其杖笞以下罪名,不妨宽免。只令对众长跪,已足示惩。盖予负者以改过自新之路,即留胜者以有余不尽之情,亦长官造福之一端也。”前引B67,第113页。 但是有的州县官为了表明自己的哀矜恤民之心,或惑于罪福报应之说,多喜出入罪以求福报,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幸免,甚至造成了“救生不就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的“四救先生”。(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姑妄听之(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58页。 清人李渭曾严厉批评了这种现象:“古人言求其生而不得,今俗吏移易狱词,何求生不得之有?然如死者何!此妇寺之仁,非持法之正。”赵尔巽:《清史稿·循吏传》卷四百七十七,《列传》二百六十四,《循吏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18页。 所以正确表达哀矜之心应遵循“宽严”二字,若事有可疑,难以决断则可转重为轻,切不可入轻为重,这正符合“罪疑惟轻”之意。但是更应该注意“宁失出,毋失入”,因为刑罚之事不可儿戏,只有把哀矜寓于义正之中,方能刑罚得当。
三、成因探究
清代州县官处在官和民的紧张点上,被挟裹在一个复杂的传统结构之中。他们的司法行为既有取得良性管理效果的考虑,同时也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深层次的原因。在司法操作缺乏“技术的精细化”的大前提下,州县官在司法中宣示了他们情感化和道德化的司法特质,采用家长式的治理,也符合中国的传统习惯。传统社会的限制黄仁宇先生曾说,“传统的朝代,以大量的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的基础,无从创造一种深奥的法理学,让小民支付律师和法庭的费用,又给专门人员以职业训练,去花费金钱与实践对诉讼作技术上的推敲,况且文官集团的甄选和考察,也要全国一致,一般农民又不识字,于是只好一方面授权于本地血缘关系的威权,减轻衙门的分量,一面以最单纯而简短的法律,密切跟随当时的道德观念,作为管制全国的工具。”这些大致涵盖了传统法律长时间停滞的社会原因,这也是制约清代州县官司法的关键因素。参见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0页。 使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标准苛求古人,如果我们抱着一种“同情式的理解”来探究代州县官的司法追求,或许会发现其中也有一种“不得不然”的历史合理性。大致说来,清代州县官员的知识背景、法律信仰和政治处境都影响或决定了州县官的司法行为,是清代州县官司法追求与躬践的主要成因。兹将此三种成因略为析述如下:
(一)官员的儒学背景使司法追求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
中国是个独尊儒术的国家,其法律的儒家化自汉代已开其端,魏晋进一步发展,至隋唐集于大成。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政治理念越来越深地渗入到法律之中,成为封建法律精神的合法性来源。儒家提倡“德政”,相信在位者的道德教化可以使民气和乐,瞿同祖:《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 而民心则是政制存亡之所系。正如苏亦工教授所言,“儒家认为,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维护必须有赖于人民真心实意地拥护。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德政或仁政以博取民心。”前引B32,第12页。 另一方面,儒家追求的是“人本主义”社会,张伟仁:《中国法文化的发展、起源和特点(上)》,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6期。 反对刑杀,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推崇教化,认为“教化之废,推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途”。前引B19,第3页。 有清一代,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影响不减反增,前几位皇帝都对儒家政治思想多加推崇,仍秉承儒家“敦德化而薄威刑”(汉)王符:《潜夫论笺校正》卷八,德化三十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78页。 理念,将仁义德化挂在嘴边,冀图以此来巩固满清统治。
儒学不仅为整个司法提供了一个大的政治背景,还为个人提供了道德的基本点。儒家注重道德的自我体念,通过自身努力就可以改变周围环境,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前引B54,第73页。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前引B54,第166页。 儒家追求士君子的理想人格,相信通过个人的自我修养就能具有士君子的道德理性。美国学者D.H.比肖普指出:“儒家还有一个本质上是人道主义的认识,它认为真理不是来自上苍的启示,而是在人伦事务之中发现的,是理性在实践或处理实际事物中所知识的。心的职能是双重的,它一方面是自我净化和自我完善,另一方面是认识宇宙或自然界,并且为了人的利益而与它一起劳作。……儒家学说总是反对把知识从知与行、真与善的统一中割裂出来。中国传统式教育的人格主义目标——不是求事实的积累而是求人格的发展——就反映了这个特点。”参见[美] D.H.比肖普:《东西方人道主义:儒家传统与斯多葛传统》,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18页。 余英时先生将中国古典的士看作一个“未定项”,因为儒家对士的要求可以使其立场超越于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之外,即使是“官僚”也会有相对的“自由”。余英时指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一种以道自任的精神……强调士的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为最后的代表。所以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他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他们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起到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自然,这种“自由”的内心冲动来自于其对高度道德化的儒家理想的追求,这种追求体现为不计较个人得失而对整个社会产生深厚关怀。在儒家眼里,法律是一种等而下之的规范,只有具有高度道德品行的君子能担当起弘道的重任,一个社会的有序运行在于士君子而不在于法,荀子言:“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九,《致士篇》第十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1页。 这样,儒家就把法制良窳的关键归结于个人道德情怀的彰显,所以古代的司法者在适用法律之外,还有一种道德教化的职责,这才是立法者真正的用意所在。
清代州县官大多是科举正途出身,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9页。 即令是异途出身,也多为科举不第者,与正途出身的官员有着相同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而儒家思想正是科举考试的核心和关键所在。清代的科举考试主要有诗、表、判、策问、制义诸项,其中唯一涉及法律的就是“判”,它以《大清律例》的门目为题,要求考生自行揣摩律意,前引⑥,第15页。 考察的仍然是一种宏观上的理解,而不涉及具体的法律知识。即便如此,乾隆二十一年也因为判“沿习故套,则举子易于揣摩,何由视其夙学,甚无取也”《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三六,载《清实录》(第十二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第44页。 而将“判”这项考试取消,法律学科在整个帝制中国都没有和士子联系起来。由于儒家和君主都不重视法律,法律在官员的知识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也就微乎其微,所以州县官在审断时对法律知识一个大概的了解,并不会熟练使用。加之,满清皇帝出于统治的需要对科举士子多加钳制,所以士子在应考之时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多讲一些道德性决断,少一些实务方面的判凭。有着儒学教育背景的州县官员在司法中近乎本能地从道德角度来评判,而不根据事实和法律就案论案。清代州县官对司法中道德教化的推崇、对父母官角色意识的期许,根源就在儒学思想,所以州县官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司法过程变成一个服役儒学和表达儒学的工具。
(二)法律的低阶价值使司法追求具有“权变”思维
从法律的地位来看,传统中国的法律始终被认为是一种低阶规范,它的功用是在道德失范时对社会秩序进行补救,是最后不得已的选择。真正的高阶规范是天志、礼仪、道德、情理这些由儒家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具有明确的层级性。这些高阶规范的缺失意味着法律丧失了正当性基础,没有遵循的意义。陈顾远先生对此有颇为深刻的论述:“因儒家重礼轻法之观念深入人心,礼正其始,刑防其失,故除刑名之外,无所谓法也。……故儒家之礼治,不特高居刑律之上,抑且深入刑律之中,使刑律之为礼化也。……不论凡其所特以为礼者,固无一文字之信条而视为法律之源。”陈顾远:《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8—59页。 梁漱溟先生也有类似看法:“法律这种东西,它几乎可说没有。其自古所谓法律,不过是刑律,为礼俗之补充辅助,不得已而用之。”许章润:《梁漱溟论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与法律生活》,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6期。
法律处于一种相对卑下的地位,其结果就是司法官在判决时具有往往具有不确定因素,这就在司法中产生了一种“权变”思维。“权变”以“常情”为前提,是司法达不到儒家所期望的社会影响和效果时的一种“变通”。法律内在的逻辑并没有在古代受到重视,司法中的“弃法”行为因其具有道德合宜性而在操作上存有广阔疆域。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即使司法官在不选择适用法律的情况下,也得找出合适的道德话语,以证明其“权变”的必要性,这样更使得法律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中国传统法律的卑下地位经过中西方对比后显得更为明显。
清代的州县官是清帝国司法中最基础的组成,拥有相当的权力。在法律不符合“常理”时可以进行“权变”。清人陈弘谋言:“随事推恩,听我自便;因心出治,惟我施行。则莫妙于知州知县矣。”前引B86,第249页。 他认为法律只是“辅助之具”,一个州县官的关键在于曲折委婉的表明自己的爱民态度,所谓“本爱民之实心,行惠民之实政,其词曲而畅,其意婉而切。”前引B86,第284页。 同样做过州县官的张五纬在《未能信录》中也谈到了“律例本乎天理人情而定,刑期无刑,辟以止杀,全在官之决断。故狱不贵乎善辩而贵乎能决事理之当;讼不在乎肯问,而在乎能决情理之平。”前引B46。 因此,清代州县官司法理念中广泛蕴含着仁恕、哀矜、情理等表面看来与法无关的规范,法律在适用和实现的过程中总是受这些规范的影响,充满了不确定性。其实在适用法律者看来,这些规范正是法律的来源和精髓,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法律的严格适用,而是决“事理之当”,得“古今之平”,在具有强烈道德化色彩的司法理念中谋求诉讼的解决之道。
(三)皇帝的推崇使司法追求具有“民本”风格
入关之后,清朝统治者尊崇孔子及其儒家道统,把儒家所提倡的“仁政”、“爱民”作为其治术之一端,其目的一是消除华夷之别,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二则是深刻认识到民之安稳关乎其王朝命运的修短,故而“以民为本”就成为朝廷行政的重要出发点。清初,顺治帝在与大学士陈明夏讨论“唐朝家法何以不正”时言道:“人君之有天下,非图逸豫,乃身当孜孜爱民,以一身治天下也。若徒身耽逸乐,又安望天下治平。惟勤劳其身,以茂臻上理,誉流青史,顾不美欤?”《清实录》(第三册),《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十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8页。 另外,在“天人感应”的影响下,贵为“天子”的皇帝也需要与“天道”相合,“天心爱民而付之君,以治斯民,又以不能独治而分任之百职”。(清)徐栋辑:《牧令书》卷一,《治原》,载前引B28《官箴书集成》(第七册),第16页。 “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爱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前引B53,第78页。 这就要求地方官员需“任职则思利民”,这样既可以维护好“天道”,也可贯彻好“君意”,更可履行好“臣责”,如此才能不负“君上命我之意,上天生我之意”。前引B110。 由此可见,清帝国的统治者将传统民本思想贯穿于其统治思想之中,乐于表达自己的爱民情感,并且要求其所统率的臣民能够体谅君主的良苦用心,念切民依,勤求民隐。
清帝国的统治者既然“上有所好”,州县官们自当体会皇帝的“厚泽深仁”,(清)罗迪楚:《停琴余牍》,百甲山堂丛书本,载前引B23《官箴书集成》(第九册),第401页。 在言行之中表达自己的爱民之心。由于清朝专制主义极端强化,历代统治者主张“乾纲独断”,将官员的“爵、禄、废、置、生、杀、予、夺”操于己手,各级官员只是皇帝的家臣、奴仆。处于官僚集团底层的州县官已经了然自身所处的政治生态中充盈着君主所宣扬的“爱民”、“仁政”之语,故而在所辖范围之内大力渲染,力求“上扬圣天子启牖斯民之化、下振众百姓观感自新之风”,前引B25,第111页。 竭力做朝廷良愿美意的传递者。清代整个官僚集团都拘囚锢蔽在皇权君恩之中,把“爱民”作为“忠君”的主要表现,也就成为了州县官在体制条件下经常选择的行为策略,清人袁守定认为“效忠乃臣子常分,非必左右明廷,始可披胸见款。藐茲小臣,君门万里,虽素孕血诚,倾沥无所,只竭力为民,即是效忠也。”前引B27,第182页。 爱民不仅是表达忠心之举,而且也可以仰邀圣恩,为君主分忧,即“承风慨慕,思为天子效任一区”。前引B113,第398页。
孙越生教授把古代官僚政治分为五等,其中最低级的一等就是官员在对帝王和上级负责的同时要做到忠君爱民,而且君主也经常做“仁政爱民”的表面文章。孙越生:《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序言》,载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既然君主想要“勤求民瘼、益广仁恩”,那么州县官自然要尽力迎合,表达忠君爱民之意,证明其并非尸位素餐之辈。《钦颁州县事宜》中的“宣讲圣谕律条”即是一种典型体现,其中提到“悯小民无知犯法,特命刊示律条,使之家喻户晓。庶几革面洗心,仰见皇上保赤之怀,提斯警觉,仁至义尽,有如天己”。前引B25。 这里,州县官把忠君爱民的思想注入司法追求之中,使其呈现出“民本”的风格。由于州县官所处的位置多方压力汇集,州县官在帝国官僚体制中有着微妙而苛刻的政治环境,他们想要取悦皇帝,表达忠心,尽好“臣职之修”,精神奋励地做好这篇“以民为本”的文章是其行政逻辑的应有之义。
余 论
日本学者寺田浩明把明清社会比作“拥挤列车”模型,民众在拥挤的车厢内相互推搡,每个人都不可能如己所愿地伸展自己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该保持一种自肃,实现彼此边界线上的平衡,谋求生存的最佳空间,“拥挤电车型的社会原理,是一个对所有个别主体的利益主张都不给予确定性的论据,或更确切地说,通过将个别主体的利益主张视为‘私域加以制约,从而营造整体秩序的逻辑世界。因而,这样的权利结构必然要超越无数个私的相互竞争的视界,倾向于通过通贯整体的状况,企求其中以为实现当事人的共存为目标的‘公的主体的存在,而且赋予这样的主体以权威。”[日]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 寺田浩明的理论遵循“脆弱平衡下‘私的拥挤——巨大压力下‘人的冲突——利益谋求下‘讼的产生——司法裁断下‘公的权威”的逻辑主线,为我们勾勒出明清社会司法产生的大致路径。遵循这样的路径,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清代州县官正是这种“公的权威”的典型代表:他们致力于谋求整体的均衡和情法的持平,为秩序的和谐稳定而操劳,同时以道德话语对涉讼民众进行教化,让大量的民事纠纷通过调解和乡规族约解决。从这个意义讲,清代州县官的司法追求在整体上符合清帝国统治的根本利益和政治理想。
清代州县官在整个泛道德主义盛行的帝国体制之中,糅合了地方文化意识和儒家道德关怀,其司法追求往往表述为一种独特的道德性话语。在实际司法运行中,这些道德话语仅仅存在于说教或训诫之中,并没有制度上的监督和约束,所以司法追求的实现往往要靠州县官群体中的“精英阶层”的个人素养和阅历来支撑,他们往往被称作“清官”或者“循吏”。例如,汪辉祖、樊增祥、张五纬、黄六鸿、袁守定等人皆是清代州县官的理想代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地方官标准,同时也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要求和期许。
这些要求和期许蕴含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治世理想,尽管高度道德化的表述可能是对封建法制的整饰和美化,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其中的人文和理性使古代冰冷的法律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清代州县官司法追求中的“和谐”、“人道”、“仁爱”、“教化”、“情感”等因子仍然发挥着划时代的灿然光芒。“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中国的传统法律蕴含着支撑现代法律发展的内在力量,如果有人想从法律传统中汲取养分的话,清代州县官的司法追求或许可以提供一种借鉴。
Abstract:In Qing Dynasty, the county magistrate has played a vital role in effective operation of local justice. As one group of officials, besides mediocre or corrupt officials, there are indeed quite a few officials who have deemed “order”, “mercy” and “morality” as their pursuit of justice to some extent. This pursuit has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long-immersed Confucius culture. Based on their official duties and pertinent situations, the county magistrate of Qing Dynasty strive for the effect of “litigation avoidance” and “coordination of mercy and incrimination” in judicial activities and so to perform it in practice.
Key words:Qing Dynasty bureaucrat confuci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