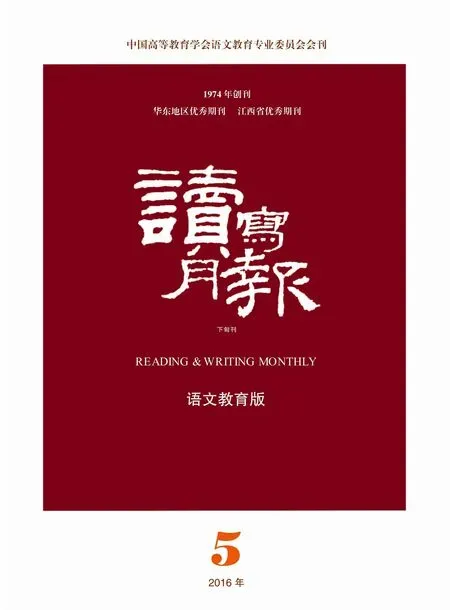“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再辨
宋桂奇
“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再辨
宋桂奇
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序号为笔者所加):
①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②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③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④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⑤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⑥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此中“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一语,苏教版语文必修五注为:“少卿您看我对于妻子儿女又怎样呢?意思是自己并不顾念妻子和儿女。”对此,姚惠萍先生在发表于2015年第3期《语文学习》上的《是“顾妻子”?还是“不顾妻子”?——阅读如何把握“语境义”》(以下简称姚文)一文中持有不同看法:“无论是从人之常情的推理,还是观照司马迁对亲情及生死的价值取向、文章情感发展的特点、语言内部的层递关系,把‘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理解为‘不顾念妻子儿女’都是不合理的。”这个新说虽不无可取之处,但在论述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少错谬,兹不揣浅陋,作辨析如下:
一、“且”之误解
姚文认为,“且勇者不必死节”之 “且”乃“并且、况且”之义,“在语意上应该是承接上文的意思做出的进一步的说明”;而其后得出的结论却又是:“从语法逻辑的关系来看,如果理解为‘不顾念妻子’,是会造成语意层递关系的混乱的。”
且不说“且”是不是“并且、况且”之义,亦不说“说明”与“层递”之间的明显差别;即便按姚文所说,将“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理解为“顾念妻子”,那么,“且”之前后显然都是“不去赴死”之意,如此,又何来“层递关系”呢?
事实上,“且”位于句首,除用作假设或递进连词外,还可以用作语气词。具体到上文,无论将“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一语理解为“不顾念妻子”还是“顾念妻子”,“且”之前后均不存在语意上的递进,已证之“姚文”及上文;至于它不表假设可谓一看即知,不赘;故此中“且”只能是句首语气词。关于“且”的这个用法,虽辞书说法不尽一致——《汉语大词典》:“助词,用在句首,表示提挈,犹夫。”(缩印本215页)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古代汉语虚词词典》:“语气词,用于句首,表示要发表议论,兼有提示作用。可不译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 426 页)杨树达《词诠》:“提起连词。 ”(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0页)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犹‘夫’也。提示之词也。”(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57页)——但考虑到中学语文教学中,习惯上将用于句首的“夫”“盖”称作发语词或句首语气词,故笔者倾向于《古代汉语虚词词典》之说。至于用例,上述著作中多有列举,如:“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当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墨子?非命中》)、“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孟子?公孙丑上》)、“且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史记?魏世家》),等等。
二、匪夷所思的“普通人”
姚文认为,“可以不顾念‘妻子’毅然赴死”的,“要么是‘激于义理者’,要么是‘怯夫’”,而“作者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能知道‘去就之分’的‘普通’人”;这个结论的得出,依据之一是“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之二是“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姚文这一部分论述,可谓问题多多。依据之一和结论之间,除过渡语“从这些内容的表达来看”之外,再不见丝毫理由;而在笔者眼中,“仆虽怯懦”则白纸黑字,说自己是一个怯懦的人,难道这“怯懦的人”和“怯夫”不是同一个意思吗?事实上,司马迁说的非常清楚——“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亦即“慕义”的“怯夫”才会赴死,“姚文”竟置“慕义”于不顾!若顾及“慕义”,这“怯夫(慕义)”与“激于义理者”则为种属关系,又怎能将二者对举?至于依据之二,姚文有解析云:“显然他认为自己是与那些‘死节者’不同的人,只是一个卑微的普通人。当然也就更不是什么‘激于义理者’了。”这个解析明显不合文意:司马迁说的是 “伏法受诛”,而非“受辱”之前,此中的巨大差异,原文第三节已有详述,不赘;又,“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一语,是说“世俗(世人)”不把他与“死节者”相提并论,其言外之意是不是含有——自己对“死节”的艳羡乃至追求?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就算司马迁是一个“普通人”,这“普通人”与“激于义理者”和“怯夫”之间,仍存一种交叉关系:“普通人”因“激于义理”而死,“普通人”中有“怯夫”或“慕义”的“怯夫”,这大概不要举例了吧?若联系文本,“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二语中,“乡党”和“俗人”是不是“普通人”?如果不是,该将他们如何归类?如果是,又为何与司马迁如此隔膜?诸如此类的逻辑混乱,当亦能证明“普通人”之说的匪夷所思。
三、整体把握的偏差
姚文虽肯定“写作《史记》,就是作者活着的目的”,但却又认为:“这个目的是不是一定要排除对‘妻子儿女的顾念’?对司马迁来说,活着是需要理由的,这个理由却不一定是简单的、单一的。”其后还进一步阐释道:“如果理解为‘并不顾念妻子’,作者对于死的选择就可以相对简单了,也不会有那么多痛苦的纠结,这种思想与情感的力量也就不会那么沉重与深厚。”
此论为“普通人”之说的引申,本可弃之不顾,但考虑到它着眼于整个语段以至全篇,故再赘数语,以为“姚文”须“整体把握语境内涵”说之呼应。前引语段中,语意的落脚点在句⑥,可谓一看即知。就全文而言,面对“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样清楚明白的表述,我们好像也没有必要节外生枝。清代学者包世臣在阐释该文主旨时说:“所以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安吴四种》)确实抓住了要领。若由此再进一步,联系司马迁的生死价值取向来看,他忍辱不死的目的亦只能是为了完成 《史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孔子世家》《伯夷列传》两引此语)、“贪夫殉财,烈夫殉名”(《伯夷列传》)、“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伍子胥列传》)、“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太史公自序》),凡此种种,均昭示着司马迁有着追求“不朽”的“重名”思想;故此,他忍受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分裂甚至灵魂的窒息,选择了比死需要更大勇气的生,以践行“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之生死观。若按“姚文”所说,将他选择中的痛苦、活下来的理由部分归因于 “顾念妻子儿女”,不仅不吻合文中语境,而且也削弱了情感力量、矮化了作者思想!
以上错谬,若究其成因,当是“主题先行”(司马迁不可能如此不近人情),以致“六经注我”;这虽让人感到遗憾,但能从“人之常情”这个角度生发疑问,进而指出注释不合情理,无疑仍值得肯定。事实上,课本这个有违人情的注释,确实不合司马迁本意。“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一语,是说“有所不得已”才“不然”,这自意味着,他们本心是“顾妻子”的;若套用孟子名言,便是——“妻子,亦我所欲也;义理,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妻子而取义理者也。”对具有如此崇高理想的志士仁人,我们能说他们没有“人情”吗?明确了这个前提,再看 “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一语,司马迁的本意也就不言而喻了;故课本当改注此语为:“少卿您看我对于妻子儿女又怎样呢?意思是说,自己虽顾念妻子和儿女,但也懂得舍生取义之理。”准此,前引语段的大意便是:遭受奇耻大辱的自己本该去死(①②),之所以忍辱偷生,既不是不明舍生取义(颇识去就之分),也不是因为胆怯怕死(臧获婢妾,犹能引决)(③④⑤),根本原因就是——完成《史记》,以“扬名于后世”(⑥)。若以此验之于全文语境乃至司马迁的思想体系,应该都是符合的吧?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实验中学)
编辑:舍予
责任编辑: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