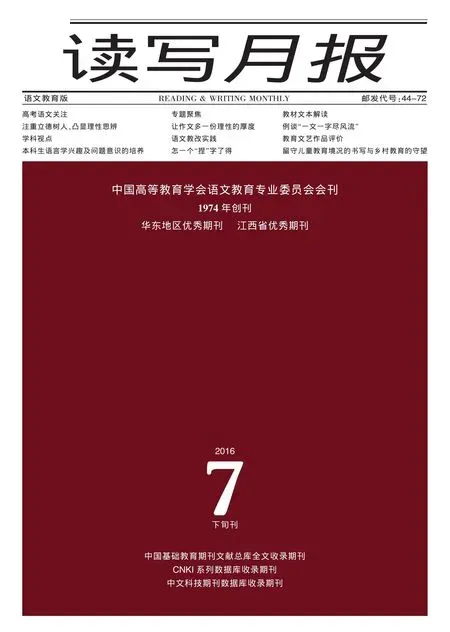留守儿童教育境况的书写与乡村教育的守望
——论海嫫的中篇小说《听风村的孩子们》
徐 畅
留守儿童教育境况的书写与乡村教育的守望
——论海嫫的中篇小说《听风村的孩子们》
徐 畅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格局的不断深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开始呈现日渐加快的态势,人口流动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流动日渐活跃,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封闭的乡村在与城市经济浪潮激烈的碰撞交融中,开始了一轮新的裂变。而与此相伴的是众多社会矛盾的凸显,农村“留守儿童”正是在这一形势之下衍生出来的一类特殊的受教育群体,他们一面茫然地触摸着凝滞封闭的乡村教育的脉搏而沉重呼吸,一面朝着不可知的未来企盼爱的回归,他们正是带着这样双面的特性,跨进这一场巨大的变革之流。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1]并且,这个数据还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而继续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面对如此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数据,反观当代农村教育背后隐藏的现状,如何看待这一类群体的教育问题,如何及时地、较好地使其接受义务教育,已成为我国当今这个时期不容忽视的教育热点话题之一。
海嫫的中篇小说《听风村的孩子们》以农村儿童留守现象为背景,将目光聚焦于远离城市现代文明的封闭乡村,通过讲述一个从城市来乡村支教的新教师安安进入听风村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用现实的笔触观照当代乡村教育现状,书写了留守儿童教育境况,真诚寄寓了她对未来乡村教育热忱与守望。
一、农村留守儿童:封闭乡村中飘摇的小草
“留守儿童”主要指的是一批特殊的儿童群体:他们由于父母双亲或单亲外出打工而造成了与父母短期或长期的离异。由于这些儿童往往正处在人格形成的重要阶段,可现实的因素使他们多方面情感遭遇长期的疏忽,从九十年代开始,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城镇地区,这些“留守儿童”所引发的教育问题已不再鲜见。除了监护人对留守儿童学习介入过少导致的学习问题之外,缺乏亲情的抚慰导致的生活问题,以及缺乏完整家庭教育导致的儿童成长心理问题也日渐凸显。这些农村的留守儿童就如同封闭乡村中飘摇的小草,尽管仍紧紧扎根在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上生长,但似乎已找不到自己的庇护之所,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迷惘地独自生长。
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认为,家庭作为一种结构,每个成员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传统理想型家庭生活模式在时空上是紧密结合型的,亲子之间朝夕相伴,夫妇之间和谐相处,只有这样的家庭结构才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如果有任何一方缺席,都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正如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所说:“夫妇和亲子关系不能相互独立,夫妇关系以亲子关系为前提,亲子关系也以夫妇关系为必要条件,这是三角的三边,不能短缺。”[2]但为了改善家庭生活,为了给家庭的下一代的成长提供更充裕的经济支持,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在经济收入与子女教育的取舍之间,还是选择了离开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到陌生的城市里务工谋生。这使得原来父母的双系结构彻底瓦解,父母的社会化作用缺失,导致孩子的情感生活出现一定程度的缺陷。
海嫫在小说中将目光投向这群 “飘摇的小草”,以诗性平和的语言传达出这些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隐晦之痛。小说一开始就着力塑造了一个单纯天真的留守男孩姚贝贝,后改名为姚雷。他喜欢骑在枫香树的树杈上看从山那边“翻过来”的人或车,喜欢用“神奇”两个字表达他对于外来事物的赞叹,喜欢在卷子上涂满大大小小的象征着“地雷”的墨迹。而就是这样一个单纯天真的小男孩姚雷,却有着一段难言之隐的成长经历。他的母亲因前夫的意外身亡,不堪重负离家出走,所幸来到质朴的听风村与姚家结合,生下了他,可原本生活本该因孩子的出世而平静充实,却又因一场重病与世长辞。“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却各有不同”。[3]在姚雷成长的这个家庭单位之中,除了母亲的爱早早就缺失在姚雷的记忆之中以外,其他构成家庭情感补偿的因素也十分微弱:他的父亲到了城中“找钱”,长期不能陪伴在孩子的身边;他的二叔自年幼起就患上了抽风病,生活难以自理;而他的奶奶年老力衰,加之还有着严重的腿伤,这种隔代监护不但难以担起对孙辈教育管理的重任,而且很难在情感的更深层面给予姚雷爱的关怀。因此,在小说之中,以姚雷为代表的“留守儿童”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源自家庭爱的缺失转而去寻求生活中其他方式爱的补偿的行为尤为明显:他常常会把身子使劲挨紧树杈,紧紧地抱着那棵象征着自己母亲的枫香树,追忆短暂记忆里那些被母亲呵护的日子;他会将新来的支教老师安安幻想成心目中真天使的化身,以求从安安的身上找到爱与美的诗性所在;而小说中多处提及的姚雷改名事件,更是年幼单纯的儿童试图在情感这个层面寻求更为有力的认同与关怀的一种隐性表现。
如果说,以姚雷为代表的留守儿童所作出的行为是在隐性的维度表现内心对爱的渴望与诉求的话,那么以肖雨为代表的留守儿童所表现出的心理特征则更多地反映的是一种情感缺失的外显型表达。肖雨的父母常年在福建打工,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她的性格变得内向孤僻,痛苦和欢乐都在无言中独自体验,不敢对着外部的世界诉说自己的感受。外界的欢乐很难真正进入她的心灵,于是她选择给自己的“真心”戴上一层保护的盔甲,“躺在课桌底下,百无聊赖地慢慢翻滚”[4],“几乎不和别的孩子说话,哪怕是眼神上的交流”,“不时地用手指蘸着塑料包装里的橘色粉末,放到嘴里吮食,似乎周围的喧闹与她一点关系也没有”,即使是肚皮在炉子上烫出了一道长长的水泡,她也隐藏着自己疼痛的感觉,忍着不说。她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所营造的小世界里排演着寂寞的独角戏,然而她心底那份对于家庭之爱的真诚渴望却在见到安安老师及其男朋友林子之后迸发了,她不想再用坚硬冷漠的外表包裹着自己脆弱的心,她也渴望被高大的林子保护,渴望一个不曾得到过的拥抱,渴望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人,所以肖雨才会第一次见到高大的林子就那么执着地哭求得到他的拥抱,才会在安安牵着她上楼的拐角,壮着胆子对安安说“我想喊你妈妈。”因为高大的林子对肖雨而言,是一种男性安全感的象征;而细心的安安能以女性的视角触及肖雨内心情感的变化,是一种女性体贴温柔的象征。这两方因素本该是一个完整家庭父母双方所该给予的最简单的关怀,却因为父母双方家庭教育的缺席,给孩子心灵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
此外,从儿童心理的个性特征来看,留守儿童除了因为“爱”的长期缺失使他们心理产生对于情感或隐或显的强烈渴望之外,还会极端地表现出一系列复杂的心理问题。处于心理过渡期的杨梅子因没有适时得到父母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堕入乡野庸俗之弊的效仿之中,明显地表现出“被异化”的成长,言行偏激、轻狂自大;缺失母亲关怀的姚小丽产生了心理的极度敏感,外表强势,内心脆弱,以“伪成熟”的方式消化自己的孤独与悲伤;从小在奶奶隔代监护的溺爱中成长起来的大良,漠视纪律,在异常的叛逆中寻求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农村的留守儿童就犹如封闭乡村中飘摇的小草,在缺乏家庭教育的无边天际丧失方向地兀自生长。
显然,听风村的留守儿童所反映出的问题并不是个例,它投射出的是庞大留守群体的一个普遍的状况。在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广大农村的这种留守现象一定程度上还将加剧。留守儿童在成长阵痛中所发出的稚嫩童音谁来聆听?又有谁能照亮这些孩子的成长?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教育者思考。
二、农村教育:教育理想信念的失落
除了家庭教育,小说《听风村的孩子们》还展现了农村教育中理想信念的失落。在文本中,听风村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相对封闭的边缘民间,这里的崇山阻隔着外界的讯息。听风村的村主任把村路和小河的命名登上报纸视为“风光”,乡民认为“警车”、“救护车”长了翅膀才能进村,孩童们把网络看作遥远和神秘的新鲜事物,甚至很多家庭竟然都无法提供孩子的户口本。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闭塞的乡村施行教育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
从教学的外部条件来看,以听风村为典型的农村教育面临两重困境。第一,农村的办学条件差且教育质量不高。听风村包括十个组,学校建在较为中心的山坳里,最远的寨的孩子要翻越两座高山才能到达学校,最近的寨的学生也要徒步相当长一段距离。不仅如此,农村办学的质量也不容乐观,正如李子老师在小说中所说:“现在都是招考,有本事考得过的谁愿意来咱这里?没有师资,咱就没有资格办幼儿园。”“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大都只留下老小,不办学前班,大一点的孩子就要退学,回家帮着照顾弟弟妹妹,现在入学率抓得严,从上到下没有好办法。”第二,农村教师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随着生源减少,农村的教学点面临被撤掉的风险,为了维持现状,上级每月对听风村公办教师的考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只要一认真,大家都不合格,去向也就成了问题”,显然,这对于封闭乡村儿童的教育来说将面临更大的麻烦。
从教学师资的内部而言,农村学校不仅面临着教师人手严重不足的困境,教师学历层次偏低,教育教学观念落后,农村教师流失严重,也在制约着农村教育的发展。就小说中听风村这个学校而言,整个学校一共就六名教师,可实际上岗的数量却只有三名。李子老师不但是学校的校长,还兼任四年级的班主任;姚老师虽是三年级班主任,却还代教一年级的语文。更令人堪忧的是,这些农村老师的教育素养整体偏低,更不用说能够掌握正确的教育教学方式了。小覃老师吸烟成瘾,他的瘦脸被烟熏得黝黑中透着红亮,在教学上丝毫不上心,想着靠开辟“学校的后花园”种些蔬菜就近“生财”;李子老师奔忙在大小会议之中,平日的教学方式粗暴落后,常常带着一根竹条“走马上任”,用体罚的方式整治学生,对他而言“都是野惯了的孩子,不凶一点儿,他们就无法无天了”;姚老师思想保守落后,喜欢插科打诨,面对乡村即将引进先进的“网络”,他竟含沙射影地表示出不屑的态度。这些老师们面对失落的农村教育虽也深感无奈,但却得过且过,时时抱着“老和尚撞钟——过一日是一日”的陈腐态度,似乎并没有想要拾起教育理想信念的决心与勇气。如此,农村教育便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这种尴尬的局面更加剧了农村教育的衰败。
此外,农村教育中理想信念的失落在小说里还明显地表现在农村教育的价值观念中,一种“读书无用论”的思想观念在农村悄然蔓延。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显然已经成为个人最重要的发展资本,这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然而,在偏远的农村,也许是出于当下农民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率不断下降所带来的隐忧,也许是出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许多文化程度较为低下的农民出于实利主义的价值观念,认为在当今“金钱至上”的社会,文化的高低对于挣钱似乎不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因而当他们进入到五光十色的城镇,受到物质的强烈刺激时,原本就稀薄的教育理想信念也就随之失落。但更令人后怕的是,这种教育观念不仅存在于年长一代的思维定势里,还更渗入到了农村青少年一代尚不成熟的心灵之中。小说中,安安老师曾给学生布置了一项课堂作业,要求同学们以书信的格式给她写一封关于个人理想的作业。可是,当这些处于花季的学生们听到要“谈谈自己的理想”时,居然一片“嘘”声,露出不情愿的神色。安安问及这些孩子的理想,班级里一片嘈杂,几个孩子竟扯着嗓子喊道“找钱”。面对孩子们异口同声的“回答”,安安深感意外,而她班上年幼的学生姚小丽却在课下十分淡定地告诉安安六年级的覃花已经定亲了。姚小丽的语音语态颇像一个大人,让人想象不出这样一群单纯可爱的孩子竟俨然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个“深谙世故”的“小大人”,早早就抛弃了那些本可以自由放飞的梦想。
的确,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暴露出了很多社会弊病,权力急剧膨胀,特殊利益集团不断滋生,阶层在日益固化,但教育难道因此就要打上实利主义的标签?教育理想信念就应该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之下走下高台?泰戈尔曾说:“教育的目的是向人传递生命的气息。”在今天的城镇教育中,很多学校已经引入了新的教育理念,认为教育不仅应当让学生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教育需要服务于生活,使学生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义。这一点在农村的教育中也不应当被忽视,在落后封闭的农村更需要有人为他们启迪心灵,以让教育真正促进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与“三农”问题的顺利解决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直接关系到农村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如巴赫金所说,“个人的成长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5]。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既来自教育系统的外部,也来源于自身,它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脱节在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一种反映。教育理想信念的失落,必然造成人的生命的失落和异化。教育理想信念作为教育的航标,指引的是孩子们的成长,它不该在农村教育中黯然失色,而应唤起或激发孩子们对于未来的希望。
三、乡村支教教师:用爱唤醒孩子的生命
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真教育”是一种“心心相印的活动”[6]。的确,“爱”是教育的润滑剂,它给人力量,给人智慧,帮助我们去塑造一颗美好的心灵。留守儿童与其他孩子并没有两样,他们之所以要经历更多的成长之殇,是因“留守”二字间的内蕴体验。对于身处在农村教育岗位上的教师而言,只有俯下身来更接近这些留守儿童,在教育中用爱去感染、教化他们,才能真正让教育丰润他们每个人的生命历程,让教育变得更加温暖而有力量。
乡村支教教师安安捧着一颗善良而真诚的心从繁华的大城市走向闭塞的农村,在不断的摸索中探寻教育的真谛。安安初来到听风村的小学,她改变之前当地老师只让学生们机械地反复朗读课文的教学方法为比赛朗读的方法,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她还将“契约学习”的模式引入课堂,跟学生们商定“愿赌服输”的条约:师生比赛,学生赢,上课学生提要求,老师遵守;比赛老师赢,上课老师提要求,学生遵守。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他人、被社会认可的愿望。安安这种新鲜的教学方式运用了激励的方法,让学生充分享受到了学习的乐趣,从而使学生从被动的“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学习主客体之间的转换。
除了教学方式的改变之外,安安还在教育中加入了一些“爱的细节”。譬如说,安安在批改这些留守儿童的练习卷时,因材施教地给每个学生写上了一段特别的评语。在评语中,安安巧妙地运用语言的批评艺术,面对姚雷歪歪斜斜的字迹和大大小小的墨迹,她在卷子的中缝处画了一个头晕的表情,并且写道:“题目做的不错,只是很多字像在跳舞,还有16个‘地雷’,真的好多啊,我已经被‘炸’得头晕眼花啦,可不可以少埋几个地雷呢?”;面对姚美写字丢三落四的缺点,安安画了一个惊讶的表情,并且写道:“哇,好几个字被丢了胳膊、腿呀,它们会很伤心的”;而面对覃小小书写工整的卷子,她则给予真诚的鼓励,期待她“一定会更棒!”……这些与众不同的评语,润物细无声地贴近着孩子的内心,在细微之间流露出对于孩子真诚的爱,让这些平日里缺少家庭之爱的留守儿童找到了归属感,真正感受到了爱的温暖。
安安老师不同于曾经来听风村“考察”的城市人,她不像他们看到农村教育的衰败景象之后就“瞪大双眼,张大嘴,四处感叹,不停追问,最后丢下票子走人”,而是真心实意地走进孩子们的心灵世界,用爱的力量唤醒孩子们的生命:她不忍看到孩子受伤,因而每天放学,她会像母亲一样牵着肖雨的手,把受伤的孩子带回家中,为其抹药;她心疼孩子们辛劳地排长队喝水,因而在午饭前,她会提前烧上开水,挨个给孩子们倒上一杯热水;她担心姚雷奶奶的腿,因而四处联系之后,她会坚持着她的“尽心计划”,每天给姚雷的奶奶清理伤口……安安就这样单纯地践行着自己爱的理想,而这样的行为确实感染到了更多的人,最终听风村的孩子们得到了社会上更多的关注,甚至曾经极力反对她的男朋友林子和女哥们苏苏也都主动为孩子们联系了 “免费午餐”和“慈善义演”的活动。孩子们最终也因为安安播撒的爱,在教育阳光下,重拾起童年的欢乐,变得开朗和活泼。
其实,留守儿童就好比是一个个珍珠蚌,如果我们只是用力地“敲打”,他们会将自己封闭得更紧;而如果我们教育者能变成温柔、缓和的流水,用柔软的触摸悄然进入他们的内心,他们往往会将封闭的蚌壳张开,露出璀璨的珍珠。“敲打”只能给儿童造成心灵的反感和叛逆,而只有这样用爱的方式风和细雨地进入、理解、接受和改变,才能帮助他们勇敢地走出心灵封闭的世界。从失望落寞到绝望气恼,再到兴奋感动,对安安老师而言,她“一路漂泊,也一路憧憬;一路行走,也一路回归”,而在教育中她感触最深的就是用真诚的爱去唤醒孩子的生命。正如她最后在日记本中所写到的那样:
我像任性的孩子,相信过童话;相信一个季节里包含着另一个季节;相信有许多声音被种进土壤里,或者挂在树梢上,只要翻一翻泥土,晃一晃树身就会遇到语言和歌声。
然而,我更相信亲情、友情和善良,而这些正是人生路途中的莲花,你、我只是莲花上的一颗水露,很多时候,可能因为照见,所以晶莹。
这既是安安老师对教育理想的心灵告白,也是小说家对未来乡村教育的真诚守望。或许,教育真应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有教育者用生命去温暖生命,用生命去呵护生命,用生命去润泽生命,用生命去灿烂生命,真心实意地用爱去唤醒孩子的生命之时,生命才会真正显示出它的蓬勃、高贵与尊严。
注释:
[1]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委员会发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
[2]费孝通:《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9页。
[3][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周扬、谢素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5页。
[4]海嫫:《听风村的孩子们》,《山花》,2016 年第 2期,第26页。该作品引文具体出处以下行文不再一一标示。
[5][苏]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2-233页。
[6]方明编:《陶行知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辑:舍予
责任编辑: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