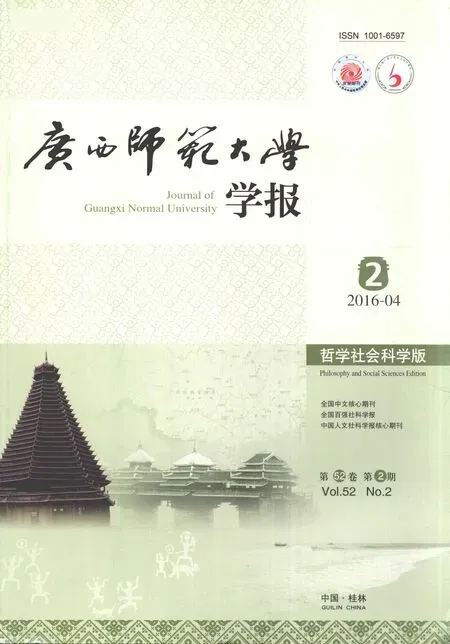新世纪湖北女作家创作的伦理生态阐释
李奇志,漆咏德
(1.武汉轻工大学,湖北武汉430023,2.武汉理工大学,湖北武汉430074)
新世纪湖北女作家创作的伦理生态阐释
李奇志1,漆咏德2
(1.武汉轻工大学,湖北武汉430023,2.武汉理工大学,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新世纪以来,湖北女作家创作呈蓬勃活跃之势,其创作或对人伦关系的悖论进行现实考量,或展示人与社会相处的相依相生状态,或追寻精神品格、编织个体生命经纬,呈现出多元的伦理生态样貌。本文着重从湖北女性创作比较突出的两性书写、城市书写、诗意书写等方面,来探讨其中蕴含的两性伦理生态、社会伦理生态、精神伦理生态的表现和意义。
[关键词]湖北女作家;文学创作;伦理生态
“伦理生态”是创新性的伦理学概念范式和理论视域,主要是指个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达到的一种理性和谐的状态,换言之,其核心要义是人的理性生存样态,是人类发展的“应该的应该之应该”[1]。伦理生态与文学密切相关:文学是一种想象,更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一种实践性的伦理生态构想。文学想象作为现实的超越性存在,对人类的伦理生态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它是人类灵魂追求超越的突破口,一方面,人们可以经由文学想象的伦理生态达到对人类的整体生存状况的洞察和体悟,并进而获得精神空间上的延伸和超越;另一方面,文学想象为人类的精神危机提供了某种消解和弥合的时空,成为人们抱慰个体生命缺憾、探问生活意义、抵御精神失衡的存在方式。新世纪以来,湖北女作家创作呈蓬勃活跃之势,其创作或对人伦关系的悖论进行现实考量,或展示人与社会相处的相依相生状态,或追寻精神品格、编织个体生命经纬,呈现出多元的伦理生态样貌。本文着重从湖北女性创作比较突出的两性书写、城市书写、诗意书写等方面,来探讨其中蕴含的两性伦理生态、社会伦理生态、精神伦理生态的表现和意义。
一
在所有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最根本也是最基本的人伦关系。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发现,两性关系生态总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存在:性别差异从世上有男人、女人起就一直存在,而两性和谐相处又是人类永恒的追求。由此,如何在差异与和谐之间寻找到张力和平衡,则成为文学永远的母题。
就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创作而言,两性关系伦理生态的叙写模式大致呈现出三种态势。一是“对抗批判”式。张洁、张辛欣、铁凝、张抗抗、王安忆等作家是代表,她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揭示了女性在追求自身平等地位、实现自我价值上所走过的艰难而曲折的道路。张洁在当代文学史上被誉为“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先导”和“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旗手”,其要义就在于其女性观念的激进。[2]168她的《方舟》被视为表达女性意识、反叛男权思想的经典文本,小说的题记“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以悲怆的文字表达了其时的女作家对男权文化的极端失望与对抗、控诉与批判。二是“私人自恋”式。时间演进至20世纪90年代,陈染、林白、海男等人的写作潜入女性自身的体验,她们的作品充溢“幽闭”、“幻想”、“镜像”、“女同性恋”、“神秘主义”、“自戕”等元素,女性内部幽暗沉潜的世界得以曝光,与这种开掘深度相伴的却是对繁复外部世界的逃离。三是“多元欲望”式。在以商品经济为核心的新世纪,经济、物质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两性关系生态亦是如此。两性的婚恋与欲望、身体、伦理、道德、人性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成为新语境下女作家们关注的首选话题领域。其中既有张欣式的《掘金时代》、《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的概叹;也有《我为什么不结婚》(童仝),只是因为两性关系是《取暖运动》(盛可以)的棉棉、卫慧式的“身体写作”;更有平实家庭的《清水白菜》(潘向黎),怎能《伴你到黎明》(张欣)的婚姻厌倦……
在上述的两性关系伦理生态表述中,探讨湖北女性创作的两性伦理生态书写就比较有意义了。湖北地处中部的地理位置似乎为湖北女作家的情爱书写导引了“中庸平和”的方向:在两性关系生态中,湖北女性写作少有剑拔弩张的对立意识,并不将男性或是男权社会视为女性世界的“他者”或“压迫者”,她们更乐意让男女两性在文本中互为观照,承认接受两性情爱之间种种复杂的现实态势,营造出两性之间相异又相同的张力生态结构。
郭海燕的小说具有代表性。两性伦理生态书写是郭海燕小说的贯穿性主题,而且她以“理解的同情”的伦理予以观照。郭海燕善于在“男女情事”的叙事模式中细细把玩、体悟和剖析两性之间的情爱梦幻和情爱纠结。李钰(《指尖庄蝶》)、喻言(《如梦令》)、泠渝(《殊途》)和朱玲玲(《掌心里的风》)等女性都有相似的情感经验:不尽如意的婚姻,丈夫的不忠出轨,内心满蕴不平、郁积和无奈,幻想生活会有意外的浪花涌起,于是婚外情成为她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郭海燕的艺术触觉敏锐地抓到了时下女性的情感隐秘处:在描绘她们的情欲心理和情欲行为时,主要把它们归于某种情感困惑和精神困境的外现,所以这种伦理之外的性爱对她们而言就是一种精神和身体的疗救,是对她们对当下生活不满不甘的慰藉和补偿;她们希冀通过梦幻和肉体来找回生活的力量和激情,但一切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缓解,一种不过如此的虚无,最终她们都回归了家庭,在与丈夫那种貌似无趣而实则互为依赖的紧密关系中找到最终的安全感。
姚鄂梅有郭海燕的现实观照,但其小说对人类情爱经验的提炼更加宽广。在她比较成熟的作品中,很少有流行的女性主义写作中的欲望叙事,也很少沉浸在纯粹私人的经验碎片和想象世界中,而往往通过较为完整的故事来传达自己对两性情爱的独特感受。她的《白话雾落》、《妇女节的秘密》、《大路朝天》等作品可以视为女性现代生活问题婚恋的当下读本,一方面姚鄂梅将女性的生存发展、情爱境遇问题并不主要归罪于外部社会环境的作用,另一方面姚鄂梅也从不过分强调女性自身认识的困惑和迷茫。在两性伦理生态之间,她更注重生活的原生态势的平衡力量,多以鲜明的人物性格、命运、形象的对比,以对生活积极向上的色调、可感的当下生活故事情节拟构,导引出女性于绝望处自我救赎的绚丽和光芒。
如果说郭海燕、姚鄂梅对两性关系伦理生态平衡的解决之道具有浓厚的对生活、对内心欲求的妥协、无奈感的话,那么,华姿则让我们看到了更高远的情爱寄托和解决方式。华姿创作的终极所指是“爱”,这种“爱”的个人印迹强烈,是从个人立场表现出来的女性爱、自然爱,还有最能体现她个人特征的宗教爱。《在爱中行走》、《赐我甘露》和《奉你的名》一起,构成华姿的新世纪博爱三部曲,这些散文澄澈、明净、安宁,在“宗教与爱”的范畴中寻找生命存在的精神归属与终极意义,她以女性为基础、母性为中介、神性为导引,在三者的流转中探索男与女、爱和性,“因此,我如果爱,我一定是爱一个人,而不是爱一个男人”。这种智慧品格使其情爱观在现实动荡的情感波澜中有超越,在宗教皈依中有升华,从而为湖北女性创作的情爱书写提供了独特的文本。
上述作品之于中国当下两性关系伦理生态写作的启示意义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两性关系的伦理和谐生态应是两性品质多样化的统一,是两性品质对立面的一致。和谐并不是趋同,恰恰相反,“对立是和谐的前提,和谐是对立的结晶,离开对立无和谐可言, 对立造成多种多样的和谐”[3]54。郭海燕等作家的两性关系伦理生态叙写强调的就是这种相对对立中的趋于和谐,这应是对女性写作的两性“社会问题”小说、“私人话语”小说、“欲望叙事”小说的一种有益补益。其二,正视男女两性婚外情欲的现实性,但又用道德理性进行调控,接受两性婚恋的缺憾性,但又用自我提升和对人性弱点的“理解的同情”来守护完满。两性婚姻的本质是矛盾的,一方面它要求婚姻中的男女相互忠诚,以此维护婚姻的牢固性及其道德底线,另一方面这种忠诚又压抑了人的本性,扼杀了人们对婚姻城堡外的探求欲望。对男女双方而言,既要求对方忠于婚姻,又要放纵自己去寻找婚姻之外的刺激与满足,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事实上,郭海燕等人作品中的女性基本没有了感情洁癖,明了婚姻的约束与人性本身的背离不可能给漫长的婚姻永远洁净的道理,于是在婚姻的无奈与困境中经由精神力量的提升达至了一种平和的状态。基于这两点 我们认为湖北女作家的两性伦理生态小说在中国当代女性写作中是有特殊意义的。
二
“女人天生是属于城市的”[4]156,王安忆此话道出了女性对社会生态环境城市性的偏爱。的确,城市化进程使女性能尽快逃离对她们不利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步入都市空间。都市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为女性的独立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条件和空间。具体到文学而言,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近代以来的小说,从城乡生态区域来看,乡土文学的作者主要是男性,而女作家往往更青睐都市文学。新时期以来,女作家对都市人文生态更是情有独钟,如上海怀旧的代表人物有王安忆、 程乃姗、王晓鹰等,写京城文化气派的有叶广苓、张洁、徐坤等,写广州白领有张欣,叙苏州风情的有范小青等;而武汉的方方、池莉、魏光阎等也提供了汉派小说的典型范本。这些作品依托其生活的城市,汲取城市的文化精髓,形成了独特的城市书写的美学风范。进入新世纪,在文学普遍的城市书写中,湖北女性文学对武汉的书写逐渐呈现出很多不同于往昔的新的城市生态特质。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对城市文化生态关怀意识逐渐强化,特别是作家对生活于其中的城市的文化、心理和生活的依赖和深爱,使湖北许多女作家由对城市的自发书写状态进入自觉状态。方方就是显例。由于城市后来者的原因,方方在20世纪80-90年代对武汉是有抵触和不认可的,近年来,这种倾向已彻底改变,她深深爱着这座城市,甚至说“我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有多么热爱它。”[5]467方方尤其爱武汉深厚的历史底蕴,写出了《阅读武汉》、《汉口的沧桑往事》、《 汉口租界》等描述武汉历史文化的散文集。池莉作为武汉人,对武汉的热爱有加。近年以写汉口著称的姜鸣燕在写小说之余,还撰有写汉阳的《武汉新区的崛起》和《雕塑大武汉》之江汉篇《锦绣江汉》等集子,在她看来,“汉口是我心灵和创作离不开的家园。认识越多,越觉得它蕴涵深厚。而汉口这一名牌及历史人文价值并没充分地体现和挖掘,对作家,尤其是本土作家而言,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6]。总之,这些女作家一直在武汉生活、工作,多以武汉为背景展开创作,武汉之于她们有特殊的意义,她们既是“城的形象创造者,自身又是那个城的创造物”[7]14。
这种对武汉深切的爱,演化为她们小说中的武汉女性,这些女人与武汉互为镜像,互为隐喻,她们是城市生态最和谐最美丽的景观,更是城市生态内蕴的精神价值所在,所以池莉说武汉是“她的城”。《她的城》是武汉女人与城市密不可分的生态体现。小说节奏舒缓,在平和叙事中,将三个女人的汉口往事铺陈开来。三个时代不同、身份不同、性格不同的女人,因着汉口城市空间让她们纠缠在一起。她们都承受着不同的情感创伤和人生磨难,但是她们却都谈笑风生着过日子,对于男性,越来越心平气和、游刃有余:对于丈夫的背叛和不义,她们理性看待,求得平和的解决;对于男人的软弱和无助,有悲悯与怜惜。对于生活,她们泼辣、豪爽、精明、自强。更重要的是,对于生活,对于男人,她们不是臣服,亦不是凌驾,而是安然,是把握自己世界的安然,她们回头看男人,是你在或者不在,我都安然的自信和平和;回望生活,是生活再难,我都刚毅、容忍和善良的从容。 三个女人在彼此理解宽容,相互扶持依赖,像所有汉口女人一般,“坐在大树下,在江边,在汉口,在她们的城市她们的家,说话与哭泣”。
沿着“她的城”的方向,方方、池莉、姜鸣燕等还塑造了一系列的武汉女人来喻指丰满的武汉形象。有底层的“泼辣汉味”、“世俗汉味”的女性生活百态:刘春梅(方方《中北路空无一人》)在毫无希望中的奋力挣扎;何汉晴(方方《出门寻死》) 在无奈生活中的隐忍、善良;李宝莉(方方《万箭穿心》)在亲人背叛与冷漠中的责任、强悍、泼辣。还有知识女性的自我探寻:大学教授华蓉寻爱不得,以湖光山色为情爱寄托的空濛(方方《树树皆秋色》);叶紫屡败屡战、绝不言输的婚恋艰辛路(池莉《所以》)。另外要特别指出的是作家姜鸣燕,其作品专著于汉口,在《汉口的风花雪夜》中咏赞着滋润“汉口的春天”的汉口女人,其女性有汉口租界别样的“温柔汉味”的面貌:云娘、芳芝、宝春(《汉口之春》),这些“女人如同滋养万物、繁花似锦的美丽春天”,她们是作者“丰富文学作品中汉口女人的形象”的成果。[8]4
当然,这些武汉女人是有历史的,是曾经辉煌的,她们与武汉的华美共荣,与武汉的精神同气。方方的“她们”在《水在时间之下》的沧桑中上演着20世纪繁华汉口的故事。水上灯姨妈红玫瑰和水上灯本人就是汉口繁华的一部分,她们与汉口是一体的,红玫瑰即便离开自己的爱人,也不能离开汉口,“她是这片土上的一棵树,挖到别处根本就没法活。……虽说跟着自己所爱的人一起出走,为的是保卫自己的爱情,可是倘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它值不值得呢?”最终,她选择了汉口,与爱人分手。而水上灯在国家需要(宣传抗日)和热爱汉口之间也选择了汉口。整部作品,方方放弃了反压迫、反封建等主题,着重叙写城与女性共同的成长史:水上灯从一个抱养的贫苦人家的女孩,历经养母逝去、养父被凌虐至死、卖身葬父、艰难学戏、遭恶人强奸、与仇家不屈斗争等各种磨难遭遇,终成名角,进而在汉口各方势力的夹缝中求生存,并与几个性格、背景不同的男性产生情爱纠葛,最终在抗战胜利后,在名声最盛之时退离舞台,孤独残生,一代名伶隐没在“时间”之下。而汉口20世纪上半叶的曲折历史就在水上灯的成长史中显映,汉口的繁华与水上灯的红极一时互为映衬,所以,方方借叙事者之口说,水上灯们“曾经一手打造和修饰了汉口”。
更为重要的是,水上灯还是武汉本土文化精神、文化精髓的形象化载体。她是汉剧名角,是汉口光芒万丈的花样年华的表征,而汉剧“这个古老的剧种早先在汉口火爆得不行。说是汉口的店铺,当年但凡有留声机放出来的声音都是汉剧。街上随便抓个人,不是票友便是戏迷”。的确,汉剧是武汉人的集体记忆,是武汉城市文化记忆的符号象征。经由《水在时间之下》的渲染,其作为武汉文化记忆符号的象征意义主要表现有三:一是汉剧是武汉文化传承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小说写道,作为首屈一指的武汉本地大剧种,汉剧是老百姓最主要的庆典、民俗和娱乐方式。作品中有大量汉剧的介绍,比如汉剧的一些经典剧目、唱词,像《宇宙锋》、《挑帘裁衣》、《荥阳城》、《兴汉图》等,此外,还细细讲解了进科班学戏的契约和各种规矩,以及主教老师教戏和艺徒学戏的过程等。其写主教老师徐江莲教水上灯练眼神的一节,尤为细致传神,比如媚眼时,眼珠梭动,目光斜挑;醉眼时,双目微闭,眼神无力;惊眼时,眉心上挑,双目睁起等。二是通过汉剧的贯穿,表现了整个汉口20世纪20-40年代的文化娱乐生态状况。汉剧是整部小说的“文眼”,其作用是组织人物、展开空间、结构框架,最终形成汉口文化生态的诸种表现。人物以水上灯为核心,空间以汉口文化名片“乐园”为典型,结构以水上灯的成长史和汉剧的兴衰为经纬,展现了20世纪20-40年代武汉本土文化的发育和发展。三是汉剧名角与汉剧角色合二为一,淋漓尽致地凸显了武汉城、武汉女人的精神特质。小说中水上灯演得最好的角色是《宇宙锋》中的赵丽蓉,原因在于赵丽蓉的幽微与尖锐、美丽与坚强、曲折与磨难,就是水上灯性格命运的舞台表演,二者的融合,就恰如作品所感叹的:“水上灯,汉口美丽的良心”;“水上灯,汉口高傲的气节”。
上述女性形象构成了当代文学史中武汉女性的画廊,她们是这个城市的“精魂”,有着这个“敞的”城市的气派,精明、泼辣、快意、洒脱和荡气回肠……。“武汉城”代表着武汉女性在物质与精神生存上的双重空间,即一座安身立命的城,一个灵魂寄托的城。经由她们,这个城市的气质品性渐渐充实升腾,它承载着百年风云变幻,氤氲着大江大湖的秉性。所有这些风云秉性,既是女作家所具备的个人气质,也在女性形象的举手投足间流溢和体现。二者互为印证,生于斯长于斯,见证了武汉的沧海桑田,并与城市融为一体;这座城市也以同样的姿态察看着她们的跌宕起伏,品尝着她们的苦辣酸甜,凝视着她们的喜怒哀乐。城市为女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女人又是城市形象的承载者。女性的命运就是城市的命运,城市的变化也就是女性的变化,城市使女性再生,女性又对城市进行新的理解和诠释,这就是新世纪湖北女作家所创造的“城人相谐”的社会伦理生态构想。
三
作为有机体的伦理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本身的伦理生态,其主要内容是人之为人生活的“应该之应该”。而这“个人应该之应该”的伦理生态平衡,除了个人需要处理好一些外在的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凸显作为“个人”的精神伦理生态平衡,也就是要关注个体的内在关系如身心关系的问题、诗意存在与现实存在的关系问题等。
近些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社会的推进,中国人的精神伦理生态正在恶化。在生存伦理的天平上,重经济轻文化、重物质轻精神、重技术轻感情,部分国人的生态境况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导致了精神上的堕落、情感上的冷漠和人格上的沦丧,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危机。文学艺术应该正视这种危机,而这些生存危机也给坚持探索的文学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对象物。新世纪湖北女作家对精神伦理生态的叙写主要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张扬个体的主体诗性理想,表现人类精神追求的超越性,另一方面是对女性幽暗心理的探索,对现存不合理精神生态的剖析。以下分别论述。
(一)寻求诗意栖居生态。
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是姚鄂梅,她的一部分作品力求探索一种与当代社会相和谐的人格、人生和诗性理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姚鄂梅为当代中国人寻求诗意栖居生态的可贵努力,而这恰是其作品的独特意义所在。《像天一样高》是长篇小说,其副标题是“谨以此篇献给8 0 年代”,表明了作者对上世纪80年代人们生活中的诗意生态的无尽追忆和艳羡。由此,小说铺述了小西、 康赛、 阿原等几个纯洁、自由、独立生活的青年诗人的浪漫生活:他们没钱却浪漫快乐,他们清高而不狂妄,他们生在都市,却去新疆寻找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他们“能把贫穷无奈的生活升华成悠闲”, 一边劳作,一边写作,追求“精神的高贵,内心世界的高贵”,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诗歌爱好者”,在新疆那片多情的土地上找到了自由的乐园。尽管,最后这个自由乐园瓦解了,但庆幸的是,小西还在旅途中在寻找那诗意的天空。小说以一种“像天一样高”的心性表达了对诗歌、对心灵自由的期望与信心, 在淡淡的低徊和哀惋后面高扬着对理想的坚守, 是当今文坛不可多得的一曲纯粹的浪漫主义乐章。
如果说《像天一样高》有的是更多的诗意高扬,那么《穿铠甲的人》和《弃权者安息》则更多的是诗意栖居面对现实的无奈和悲剧。农村青年杨青春因为对诗歌的信仰而有了在生活中追逐一切的勇气,诗歌之于他, 犹如铠甲之于士兵。但残酷的现实使得他的铠甲消逝了, 沦落为一个当代的孔乙己。杨青春尚有美好的名字符号象征精神生活的绿洲,而“他”则是干干脆脆的“弃权者”,是无名氏,“他”的诗歌梦只能遗失在自杀的伤痛和缅怀中。即便如此,姚鄂梅仍不妥协于现实,她在“在疼痛的理想中不停地奔跑”,企图通过自己的文章告诉读者,“杨青春的存在,不应该让我们产生虚无感、幻灭感,他的存在对我们应该是一个警示。文学跟现实天生具有不妥协性,进入文学的人也许得有一点牺牲精神,还得有一点斗志”[9]。
姚鄂梅对诗意栖息地的呼唤在池莉那里得到了回响,只不过后者的精神伦理生态视域更为广阔。其作品《托尔斯泰围巾》以一个女作家为叙述视角,以武汉花桥苑为背景,讲述了先做农民工再做“拾荒”者的进城农民老扁担的故事。故事内容的三个关键词是“阅读”、“执着”和“尊严”,三个关键词构成了老扁担这个边缘人零余者,这个被侮辱被嘲弄被损害者的丰饶的精神生活,其情节核心则是托尔斯泰围巾。因为这条围巾,老扁担所有的执着与坚守有了形而上的阐释:“老扁担非常喜欢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有一天他在阅读中了解到,老年的托尔斯泰,最后离家出走,只是围了一条他喜爱的围巾”。通过这条围巾,叙事者女作家由此觉悟到“信”的存在和力量:“我们的宗教在自己心里,无论是一尊黄泥巴菩萨,还是一条托尔斯泰围巾,都是一种信。”整篇小说是池莉给自己,也是给这精神日益枯萎的世界编织的一条坚守理想光华和人文精神的托尔斯泰围巾。
(二)女性幽暗心理的深度掘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中,出现了群体规模的对于女性“自我”驾轻就熟的剖白与言说。苏瓷瓷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其作品在向女性幽暗内部空间敞开的同时,基本上对繁复的外部世界封闭了。苏瓷瓷曾在精神病院做了5年的护士,其体悟是:“我在精神病院可以说是接触到了人类最隐秘的精神角落, 被遗忘、被排斥、被忽视、被侮辱与损害, 可是我深知, 这里存有文学最根本性的命题。”[9]为了探寻文学最根本的命题, 苏瓷瓷小说多以精神病院抑或精神病症为背景,关注个体的情爱经验,小说没有灯红酒绿的生活场景的描绘,更没有具体的情节与完整的故事。其小说人物主要是青年女性,如妙龄白领苏寒、老处女沈郁、女护士丁小菲等等,但这些女子充满了孤独、忧郁、被动、颓废的色彩,缺失该年龄阶段应有的朝气与激情,更丧失一种以群体利益为信仰的理想,她们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幻想并渴望与外界的摩擦与融合。苏瓷瓷对女性心理的深度掘进主要经由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通过疾病来隐喻女性的幽暗曲折的情爱心理。第一篇短篇小说《第九夜》首先作出了这方面的主题呈示:丁小非在男友患精神病后想方设法进了精神病院当护士,意在唤回他俩曾经的爱情,她的所作所为近乎疯狂:恋物、空虚、依赖、自虐、受虐,但其男友已完全不认识她,更谈不上给她爱情了,于是她选择变成男友的同类, 最终二人在阴暗的疯人院里轰轰烈烈地死去。沿着《第九夜》的方向,经由精神疾病来隐喻的情爱心理,是苏瓷瓷不断探索的领域,如《亲爱的弟弟,我爱你》里的姐姐叶绿阴郁、病态、沉寂,而其弟弟则明朗、健康、快乐,弟弟实际上是叶绿所追求的另一个自我的心理隐喻;《伴娘》里马蘅少女时代的疯狂、叛逆,成长后对平凡人生的追寻,其实都是唐凄凄自我追求的隐喻。二是在人物的“常态”与“非常态”的流转中寻求幽暗曲折心理的理解之途。苏瓷瓷的小说比较集中于表现那些“非常态”的幽暗意识之旅,并且作为叙事者她对“非常态”抱有天然的“理解的同情”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她努力让些许“理解之光”——常态的渴求理解的思维、常态的渴求沟通的心愿——照射进“非常态”的幽暗中,以使人类的明白清晰与幽暗曲折心理之间建立沟通理解之桥。总之,苏瓷瓷的小说少有外在的宏大世界的描绘和强烈政治辨析的色彩,但她作品却呈现出这样的价值:引领读者潜入“精神不正常”人的生活和意识,表现出人类幽暗心理的丰富内容和层次,让自认为正常的读者看到他者隐喻,以及与喻体的合二为一的事实。由此,读者会产生疑惑甚至质问,从而可以为稳定的社会文化秩序引入异质因素,使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突然变得陌生,进而引起对既定社会文化生态结构的质疑和新的认识。
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了人类就有了伦理,就有了伦理生态。人类的整个文明史,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乃至人与自身相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消除“冲突对立”、追逐“和谐相依”的奋斗史。但是,无论如何,“和谐”,并且惟有“和谐”,才是生态伦理精神或者生态社会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就此而言,新世纪湖北女作家的创作是颇有意义的,她们经由两性书写、城市书写和诗意书写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两性伦理生态、社会伦理生态、精神伦理生态的某些方面和某些表现形式。这就是她们及其作品存在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张志丹.论伦理生态——关于伦理生态的概念、思想渊源、内容及其价值研究[J].伦理学研究,2010(2).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袁鼎生.西方古代美学思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4]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5]方方.水在时间之下· 后记[M].上海:山海文艺出版社,2008.
[6]欧阳春艳.武汉作家姜燕鸣“绘”汉口之春[N].长江日报,2013-01-07.
[7]赵园.北京——城与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姜鸣燕.汉口之春·序[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
[9]姚鄂梅、马季. 在疼痛的理想中不停地奔跑——姚鄂梅小说创作访谈录[J].朔方,2009(02).
[10]魏英杰,苏瓷瓷. 好小说是在人性内部拓展自己的疆域[J].花城,2006(2).
[责任编辑阳欣]
Interpretation of New Century Works by Hubei Women Writers in Ethical Perspective
LI Qi-zhi1, QI Yong-de2
(1. 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an 430023; 2.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literary works by Hubei women writers have been booming. Their works focus on realistic discussion of the paradox in human ethics and relations, the demonstration of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society, or the pursuit of spiritual quality in developing individual character. Their writings have presented to readers a social condition of multiple ethical standards. This paper focuses on gender writing, urban writing, and poetry writing etc., which is the prominent feature in works of women writers in Hubei, and aim to explore the manifes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gender, social, and spiritual ethics these works contain.
Key words:Hubei women writers; literary works; ethical condition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2.013
[收稿日期]2016-01-10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新世纪湖北女作家创作研究”(2014182)。
[作者简介]李奇志(1963-),女,湖南郴州人,武汉轻工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现当代女性文化文学;漆咏德,男,武汉理工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文学与出版传播。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6)02-008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