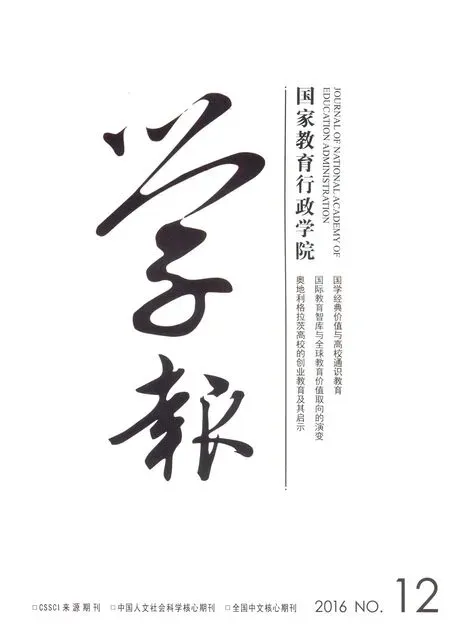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协调与建构
——基于完善内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视角
常亮 李成恩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大连 116024)
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协调与建构
——基于完善内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视角
常亮 李成恩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大连 116024)
建设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是中国高等教育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为破解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体系面临的“权力困境”,建立以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为支撑的权力协调机制,将是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有效途径。为此,以大学中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等权力要素为核心,重构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优化权力运行的制度安排,并选择以“大学事务流”为串联和牵引,进而从认知、结构、机制和文化四个维度,构建以“三权三层三制约”为框架的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
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高校内部权力;协调机制;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种自然反应,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1]为统筹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国务院于2015年11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的出台与实施,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跨越的新常态,而“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实现需要“改革和创新我们的大学治理”。[2]《方案》将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完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权力运行机制,作为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任务;其中,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是推进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使命,而完善大学权力运行机制则是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就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一、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内涵及辨析
1.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逻辑与内涵
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是指在理性思维指导下,由大学领导者、管理者、教职工及学生等共同作用于大学办学及管理活动时充分体现标准化、制度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等现代社会特征的权力结构安排及权力实施方式安排。[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此,构建以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便成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中既包括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权力结构)的优化,也包括实现大学有效治理的制度安排(权力运行机制)。[4]
纵观1949年以来大学治理体系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晰地察觉到中国大学治理演化过程中表现出典型的“中国特色”。[5]那么,在新常态下中国大学如何在“双一流”建设中坚守和彰显“中国特色”呢?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考察期间已对此做出明确阐述:“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也就是说,中国大学的“双一流”建设既要葆有世界眼光、中国情怀,还要坚持按照规律办事,努力实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如此,便成为研究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特征与内涵、探索创新实践路径的基本逻辑。基于上述逻辑,《方案》中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指导思想、核心使命和主旨内涵:“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创造性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蕴含的“中国特色”可被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突出强调党对高校的绝对领导;二是着重强调对基本规律的科学运用;三是特别强调开创大学治理的“中国模式”。
2.中国大学内部权力要素的“特色化”解读
基于权力要素的视角分析便会发现,[6]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实际上是一个“要求相关内部权力在和谐关系中协同治理的权力关系架构”。[7]当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大学内部权力类型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观点,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大学内部权力主要包括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8]也有研究者认为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政治权力是中国大学内部存在的三种主要权力形态,而如何有效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则是推进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挑战。[9]可见,学术界对于我国大学内部权力的理解和认识尚存在分歧,主要集中于“中国语境”下对大学内部政治权力和民主权力的认识和把握上,此时,就需要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启迪智慧,进而对我国大学内部权力要素进行重新审视和再解读。
理论和实践早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最鲜明的特色所在。为此,在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命题下,一般意义上的大学政治权力就特指为“党委权力”,即校、院两级党委及各级党组织对于所在高校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制定和执行学校发展战略、切实做好组织人事干部管理以及学校重大事项安排决策的影响、干预和管辖的权力,[10]党委权利在制度层面上具体表现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大学中的民主权力主要包括师生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11]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中,特指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等群众组织拥有和行使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力。为加强高校党组织对群众组织的支持和领导,《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高校党组织要支持工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依法依规开展工作,领导教职工代表大会并支持其正确行使职权;可见,党委权力和民主权力在核心利益与根本指向上是高度一致的,故而可以将民主权力的基本内涵纳入党委权力概念之中。同样,按照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提出的大学利益相关者划分方法,[12]高校党组织、管理者和教师群体正是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依次对应着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13]因此,本文认为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是构成我国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的基本要素,而协调三种权力的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则是构建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关键。
二、中国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权力困境”及协调机制
1.中国大学内部治理体系面临的“权力困境”
现有研究认为,我国大学内部权力主体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角色的“错位”与“异位”现象,并由此产生了“党政权力同质化”、“学术权力行政化”、“行政主体学者化”和“权力运行碎片化”等问题,是近年来我国高校领域腐败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现实中,由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尚不健全,高校内部的党政权力边界、职能划分不够清晰,容易在制定学校发展战略、重大政策调整和人事机构改革等过程中出现“权力交错”的情况,从而加剧了党委权力和行政权力间的“同质化”倾向。在一些大学中,学校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的常委(成员)经常是一套人马,这就造成了党委权力主体和行政权力主体间事实上的“一体化”,使决策、管理、执行、监督难以有效分开。如此一来,本应独立运行的高校领导权、管理权和决策权被混为一谈,党政权力主体常常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相互扯皮、推诿、不作为和权力寻租现象的出现便难以避免,理想中“决策—管理—执行—监督”样式的权力运行机制便被置换成了“议行合一”的行政化或泛行政化样式的权力运行机制。
当前,大学中存在的“学术权力行政化”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所谓“学术权力行政化”是指通过行政指令或科层制管理等行政化思维和方法行使学术权力的行为,其结果就是学术权力的“行政化”色彩日益浓厚。实际上,“学术权力行政化”问题绝非中国独有,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随着大学规模的巨型化、竞争的市场化,以及大学管理的科层化与专业化,大学行政管理者们自诩的“合理性”不断得到加固,大学组织被不可避免地“官僚化”了;[14]因此,“学术权力行政化”成为困扰国内外大学实现有效治理的顽疾。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行政化思维和“官本位传统”在大学组织和部分教师群体中尚有一定市场;而且,政府在大学外部治理过程中仍以行政方式管辖大学,客观上使得大学中的学术组织也要按照行政化的行为方式与外部进行“对接”;可见,学术权力的去行政化之路仍旧漫长。
事实上,权力主体错位现象不只存在于党政权力之间,也存在于其他类型权力之间。在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一些大学认为让教学科研一线的教授兼任学校主要部门的行政领导就是“教授治学”、“学者治校”;然而,如果教授们既拥有学术权力,又可以发号行政指令,那么,在“结构松散、并以学科和学术为本”的大学组织中,[15]就有可能使大学的“行政化”趋势愈演愈烈,这就是所谓的“行政主体学者化”。在大学权力运行中,当这些行政化了的教授参与学术权力运行的时候,其双重权力身份就会加剧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间的越位、错位,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对此现象,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早有察觉,他指出“既然管理者和教授们自来就在承担的任务和必要的禀赋方面有区别,所以人们最好还是不要让以前的教授们扮演一个凌驾于其他教授之上的监控者或主事者的角色。”[16]那么,如何使那些具有卓越管理才能的教授扮演好行政主管的角色呢?这需要对我国现行的“双肩挑”干部体制进行改革。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教授担任行政负责人的前提是暂时脱离学术身份,在任职期间其身份从学者转为管理者,而当其完成行政使命后可重新回归学者身份,并由学校提供旨在恢复其学术水平的经费与政策补偿。
所谓“权力运行碎片化”是指由于治理主体间缺乏沟通、协调和有效制约,造成了组织内部机构(部门)的割裂,使组织战略目标在分解实施过程中被异化、破碎,最终导致组织内部权力运行效率的低下。从管理学角度来看,同一组织内部应只存在一种指挥决策系统,如此才能保证组织内部运转的通畅;[17]但是,由于缺乏统一规范的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造成了我国大学内部权力运行中的“碎片化”现象较为突出,常表现为不同权力主体在权力运行中出现的各自为政、分工不明、职责不清等情况,加之缺少对权力运行过程的有效制约和监管,权力运行中的随意性较大;[18]因此,这种碎片化的权力分布样态既影响权力的行使,也影响权力运行的效率。面对这种困境,佩里·希克斯(Perry Hicks)和帕却克·登力维(Patrick Dunleavy)认为:“整合和协调是克服碎片化困境的良方”,这为我们解决大学内部权力运行中的“碎片化”问题提供了思路。
2.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协调机制
在推进“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我们越发清楚地意识到,大学内部权力体系的结构和运行是否科学规范、井然有序、廉洁高效,已成为评判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指出:“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超越正义与道德界限的诱惑。”因此,不论何人持有何种权力,在权力运行过程中都需要监督和制约。[19]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总要求,[20]制约与协调、权限与程序、问责与纠错、公开与规范、民主与监督等,[21]已经成为新常态下构建中国特色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体系的关键词。
由上可见,通过体系构建、制度设计实现大学内部主要利益相关者权力、责任和利益的协调与制衡,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顺应高等教育发展潮流、科学规范可操作的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就成为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协调机制。所谓“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是指由若干个对权力主体分配和行使权力的过程进行约束、限制、观察和纠正的机制相互联系形成的一个融合了制度、文化和机制的有机整体。[22]在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中,正确认识党委权力、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内涵与特征、冲突与矛盾、目标与宗旨,有效整合与科学协调三者间的关系,既是构建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基础,也是完善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关键。
三、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逻辑框架及构建途径
1.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逻辑框架
考虑到我国大学内部权力要素的多元性、多样性以及权力运行中的复杂性特征,本文拟围绕“权力要素—权力结构—权力运行”大学内部权力体系构建原则,提出和发展一个以“三权—三层—三制约”体系(简称“三权三层三制约”体系)为核心的逻辑分析框架及大学内部治理架构。
在本文提出的“三权三层三制约”体系中,所谓“三权”是指在我国大学中普遍存在的三类主要权力——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三层”是指我国大学组织中常见的三层级权力结构——学校层面、学校职能部处层面和学部院系层面;“三制约”是指本文选取的三种典型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模式——权力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制度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以及民主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可见,“三权三层三制约”体系是指我国公立大学中的三类主要内部权力,在大学三层级权力结构运行中普遍存在的三种主要类型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模式。因此,“三权三层三制约”体系是一个多主体、多层次、多矢量的复杂动态社会网络。
作为一类社会网络,大学内部主要权力在“三权三层三制约”体系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大量事务信息流的交互、协调与传递,本文将这种存在和运行于大学内部权力结构中的事务信息流定义为“大学事务流”。“大学事务流”可分为“大学核心事务流”和“大学一般事务流”;其中,高等教育涉及的六大政策领域——规划与决策、预算与财政、招生与入学、课程与考试、教学科研人员的聘用、科学研究的决策模式,[23]应被视为“大学核心事务流”,例如大学的基层党建、干部选任、发展规划、学科发展、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机构改革、财务运行、工程基建、后勤保障及招生、采购、招标等。由于“大学核心事务流”事关大学办学质量与效益、声望与尊严,并与师生员工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因此,也是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点环节。“大学一般事务流”泛指维持学校正常运行所需、除去“大学核心事务流”之外的一般性事项;相对而言,“大学一般事务流”更侧重于学校机关和基层单位(组织)对日常性事务的具体落实与规范执行。在本文中,“大学事务流”主要是指“大学核心事务流”。可以说,“大学事务流”的提出和引入,使“三权三层三制约”体系拥有了更加清晰的多维度网络结构和动态可视的系统运行特征。
2.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构建途径
鉴于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系统性与复杂性,本文在已有的“认知、结构、关系”建构路径基础上,[24]提出了以认知、结构、机制和文化四维度为主干的“三权三层三制约”体系构建路径。
第一,认知维度。有效认知是科学实践的前提,也是思想认同的基础。当大学师生的基本价值观念与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大学治理目标和自身利益诉求相一致时,大学内部权力科学配置、协调运行和民主监督的成效就会显著提升,反之,就会影响到大学内部治理的效率和效益。[25]为此,在“前提性认知”层面,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在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语境下,对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的构建理论、思想、原则等进行系统梳理和科学阐释;同时,还应坚持从国际比较、历史反思、案例借鉴三个基本视角,对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的“中国特色”加以体会和把握。在“行动性认知”层面,我国大学在深化推进内部治理体系现代化变革的进程中,应当加强对相关权力主体的教育引导,从而影响和改变他们潜在的价值观念,以形成开放的心态、共同的愿景和更高层次的信用。
第二,结构维度。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大学中的权力主体因其在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及拥有资源的不同,在“三权三层三制约”体系中处于不尽相同的网络位置,这就需要设计出特定的治理结构作为权力交互介质和权力运行空间,并以系统、协调的理念将其“整合”起来,使他们能够为共同的目标更有效率地统筹运转。在“三权三层三制约”体系中,实际上存在着纵横两个方向的结构向量。纵向上,本文认为“学校—职能部处—学部学院”三级权力运行结构,可以分别承担决策、管理和执行职能,较之校院二级权力运行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横向上,本文认为高校中的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同时存在于“学校—职能部处—学部院系”三级纵向权力结构之中,只是表达和实现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为此,在对“三权三层三制约”体系进行横向设计的过程中,应主要解决权力分散、分工、调适以及权力之间的制衡问题。在学校层面,与三种内部权力对应的是党委常委会(全委会)、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而肩负着对三种权力进行监督制约职能的通常为纪委、教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党派、学生会等;因此,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健全党委常委会(全委会)议事规则,完善“校长负责制”下的法人治理结构,并以《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为依据加强学术委员会的职能与规范化建设,就成为“三权三层三制约”体系在校级层面的构建重点。在职能部处层面,三种内权力存在和运行于校内党政职能部门和学术委员会常设机构之间,而对其进行监督制约的则是纪检监察部门、审计部门、机关党委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等;其中,加快学术委员会常设机构及专门委员会建设,推进党政职能部门分工合作,强化职能部门常规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执行,就成为“三权三层三制约”体系在职能部处层面上的构建重点。在学部院系层面,三种内权力具体对应为学部院系党委、党政联席会议和基层学术委员会,对其进行监督制约的主要是党员代表大会、二级纪委、教授会、基层工会、教职工大会等;因此,以强化学部院系党委的组织功能建设为核心,完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创新基层监督制约机制与机构设置形式,就成为“三权三层三制约”体系在学部院系层面上的构建重点。
第三,机制维度。按照《辞海》的解释,机制主要由制度、方法和形式等组成;可见,机制的内涵大于制度,而“制度”作为“机制”一词中“制”的词源,显示出了制度对于机制核心要义的支撑作用。制度体现了机制刚性的一面,而方法和形式则表现出机制弹性的一面;所以,机制具有自组织特征。回到文中,“三权三层三制约”体系的一大特色在于通过系统化设计,全面地将制约和监督整合到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之中;因此,在厘清三种主要内部权力边界的基础上,以制度形式将监督制约整合、固化到权力运行全过程之中,以确保相关权力在规定的范围内有序、高效运行,从而预防和纠正权力运行中偏离学校公共利益的隐患。为此,大学应从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谋求内部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的创新。
第四,文化维度。作为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有序、和谐共荣的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文化,是确保“三权三层三制约”体系在自觉前提下高水准运行的内生动力。以文化制约权力,其作用机理是通过营造良好的制度文化、学术文化和廉政文化,广泛借助于社会舆论机制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文化渠道,使权力主体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自觉产生抵制其滥用权力的欲望与冲动,并在权力主体中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主观意识、思想防线和外部氛围。从大学文化基本构成的角度来看,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文化属于大学制度文化和大学行为文化的交叉范畴;因此,高校在大学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文化建设中,应该坚持以追求真理、倡导学术民主为核心的学术文化,以师德师风建设和“立德树人”使命意识养成为核心的教师文化,以“廉洁从政、遵规守纪、清白做人”为核心的廉政文化,和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着手,打造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中国特色大学权力运行与制约文化。
[1]张炜.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特征与个性特色[J].中国高教研究,2016,(1):61-64.
[2]刘复兴.大学治理与制度创新的逻辑起点[J].教育研究,2015,(11):30-33.
[3][25]甘晖.基于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学治理体系构建[J].高等教育研究,2015,(7):36-41.
[4]刘延东.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努力实现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跨越[J].中国高等教育,2010,(18):4-9.
[5]张德祥.1949年以来中国大学治理的历史变迁——基于政策变革的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6,(2):29-36.
[6][17]谢凌凌.大学学术权力行政化及其治理——基于权力要素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15,36(3):41-45.
[7]秦惠民.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中的权力制衡与协调——对我国大学权力现象的解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9,(8):26-29.
[8][19]刘献君.论大学内部权力的制约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2012,33(3):1-10.
[9]周光礼.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现状、问题与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14,(9):16-25.
[10]时伟.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逻辑、动力与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14,(11):11-14.
[11]李克杰.公民“四权”写入政府报告意义重大[N].中国改革报,2007-3-8(5).
[12]朱家德.大学有效治理:西方经验及其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13,34(6):29-37.
[13]朱玉成.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的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16,(8):16-21.
[14]袁飞.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统一、冲突与平衡[J].高等教育研究,2015,36(7):25-27.
[15]刘献君.高等学校决策的特点、问题与改进[J].高等教育研究,2014,35(6):17-24.
[16]龚放.正确认识大学的运行逻辑与学术权力——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再思考[J].江苏高教,2015,(3):1-7.
[18]赵新亮.论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权力失衡与变革路径——基于权力分配的视角[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5,(5):64-68.
[20]赵洪祝.进一步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N].人民日报,2013-11-27(6).
[21]刘献君,张晓冬,刘皓.高校权力运行制约机制:模式、评价与建议[J].中国高教研究,2013,(6):8-13.
[22]桑学成,周义程,陈蔚.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研究[J].江海学刊,2014,(5):211-218.
[23]左崇良.现代大学的双层治理结构探索[J].中国高教研究,2013,(2):21-25.
[24]董云川,罗志敏.高水平大学建设:一种新框架和路径[J].高等教育研究,2015,36(6):49-55.
(责任编辑 吴潇剑)
Coordin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Syste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Internal Power Operation Restric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
Chang LiangLi Cheng'en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system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The exploring for and establishing of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internal power operation restric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 should be an efficient path to promoting the world first-class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cause of the“power dilemma”of current Chinese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the frame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internal power operation restric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 and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ystem of“three powers,three layers,three restrictions”.It should have at the center Party committee power, administrative power with academic power,and extend to the“university affairs flow”.In the meantime,the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such dimensions as cognition,structure,mechanism and culture.
Chinesecharacteristicuniversityinternalgovernance;universityinternalpower; coordination mechanism;power operation restric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
G647
A
1672-4038(2016)12-0038-07
2016-10-2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880002);2016年度辽宁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2016GXDJ-C001)
常亮,男,大连理工大学物理学院党委书记,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李成恩,男,大连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战略与政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