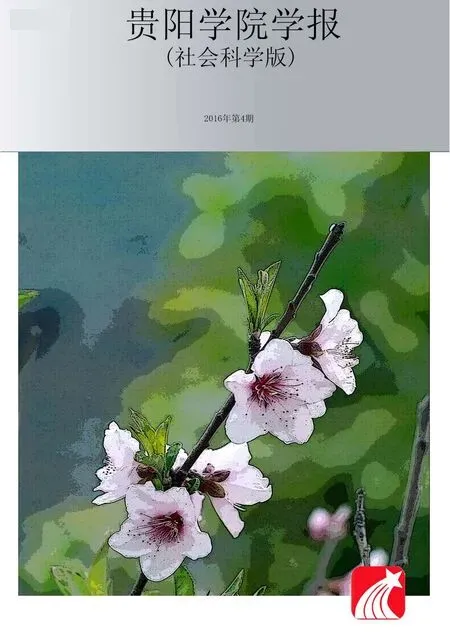论“三言”中“负心汉”形象的悲剧建构
齐婷婷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论“三言”中“负心汉”形象的悲剧建构
齐婷婷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负心汉”主题是传统爱情文学模式中十分重要的一种,“三言”从“负心汉”对“财、色、情、仕”的选择入手,揭示了他们身上罪恶与心灵持续碰撞的悲剧根源,呈现给我们一群“类型化”的可怜人群像。他们大多性格软弱、贪财好色、毫无生气与活力,在“情”、“色”、“财”、“仕”中,往往抛弃“情”选择后者。他们屈服于环境、屈服于欲望,在摧毁别人的同时也摧毁了自己,罪恶与心灵的持续冲突是他们的悲剧性所在。
三言;负心汉;悲剧
爱情是文学作品的母题,男欢女爱、忠贞不渝、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的爱情故事总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爱情文学从一开始就充溢着悲剧的味道,“负心汉”主题从古一直延续至今。这种主题的建构一般包括:爱情婚姻中的女子有恩于男子;男子先落魄、低姿态追求,后飞黄腾达;男子飞黄腾达、得到之后不懂珍惜,抛弃有恩于自己的情人或妻子而另觅新欢,此三要素具备,“负心汉”主题基本就可完成。明清之际这种主题又加上了负心汉遭惩罚的结局,完成了“负心汉”形象的悲剧建构。《诗经·卫风·氓》中那个表面憨厚老实,实则“二三其德”[1]的男子,《诗经·邶风·谷风》中那个喜新厌旧、背信弃义的丈夫,从正面展示了“负心汉”的形象;乐府民歌《白头吟》中有“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2]37-58,《上山采蘼芜》中有“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2]37-58的记载,从侧面描写了“负心汉”形象。“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3]作为展现晚明社会通俗历史画卷的代表,这类“负心汉”形象的刻画尤为生动细致,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性,比如性格懦弱、贪财好色、始乱终弃等,最终造成婚姻爱情的悲剧,也造成人物自身的悲剧。
一、悲剧呈现:“三言”中“负心汉”群像
“三言”中负心汉题材的作品,按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和行为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才子佳人”式爱情里的负心汉
这一类“负心汉”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见钟情”式的风流才子。在这一类故事里,青年男女都是知书达理之人,才貌双全,正值青春妙龄之际,情思奔涌,两人一旦见面相识后就诗书酬答,相互倾诉爱慕相思意,之后便私订终身后花园,你侬我侬,男欢女爱,最终男子背弃约定,另寻新欢,酿成爱情悲剧。在作品《王娇鸾百年长恨》里,起初周廷章与王娇鸾私结良缘,当得知父母安排婚姻的魏女绝美富有后, 就抛弃了王娇鸾,导致王娇鸾悬梁自尽,最终他自己也被上司乱棍打死。此类“负心汉”有美貌,有才气,会舞文弄墨。“好个俊俏郎君!若嫁得此人,也不枉聪明一世”[4]341-355,这是王娇鸾在见到周廷章第一眼时的反应。但这类“负心汉”又很虚伪,会为了金钱、美色、功名背信弃义。周廷章“初时有不愿之意,后访得魏女美色无双,且魏同知十万之富,妆奁甚丰。慕财贪色,遂忘前盟”[4]341-355。在向千金小姐求爱时,这类人都装出一副老实、可怜的模样,低三下四,百般哀求,而当他们一旦骗取了千金小姐的欢心,与她们尽情欢愉,满足了自己的情欲之后,便又忘恩负义,始乱终弃。
2.“荡子良女”式爱情故事里的负心汉
这类“负心汉”属于“荡子成名,必弃糟糠之妻”,或者“只享婚姻之欢,不给婚姻之名”。这类作品中的“负心汉”大多初是落魄的书生,虽也有才貌,但要么科场失意,要么穷困潦倒,正当他们处境凄惨、寂寞空虚之际,女主人公闯入他们的生活。这些女子大都温柔善良,漂亮机智但沦落风尘或处于社会底层,身不由己。为了和命运抗争,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她们就想找个“儿郎格调相称者”,希望与他们永结同好。在书生们困顿失意之时得到这些女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一旦这些男子科场得意,官运亨通,他们便撕毁盟约,将之前有恩于他们的女子抛到九霄云外,然后去攀龙附凤,做名门望族的乘龙快婿。当莫稽人生不如意时入赘金家,期间金玉奴不惜金钱供他吃穿用度,购买古今书籍,请人会文会讲,之后他连科及第,不念妻德,反以为耻。在乌帽官袍加身之后想的竟然是“早知有今日富贵,怕没王侯贵戚招赘为婿,却拜个团头做岳丈,可不是终身之玷!”[5]256-263李甲俊俏风流,在他身无分文、穷困潦倒时,杜十娘又是金钱资助,又是温情关怀,李甲许诺“此情此德,白头不忘也,”[4]320-330但在父亲的干涉和孙富的怂恿下竟以一千两银子将杜十娘转卖,辜负十娘。这里呈现的李甲是懦弱的,他惧怕家族势力,没有抗争精神,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贪财胆小。小说以杜十娘将价值连城的百宝箱沉入湖底结尾,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本来可以人财双收,结果人财两空。
3.通奸故事里的负心汉
“三言”是写市井细民的生活百态,这类负心汉多存在于市井细民的圈子,他们没有翩翩风度、高雅谈吐和浪漫情话,只是贪恋美色、追求刺激,满足自身的欲望。他们心理扭曲,对异性的追求怀着“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6]的观念,放着家里贤惠的妻子不管不顾,在外面寻花问柳,败坏道德。陈大郎是个商人,在外出经商期间,趁蒋兴哥不在,与其妻王三巧勾搭成奸。他心里想的是“家里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5]1-23于是他与牙婆“排成窃玉偷香阵,费尽携云握雨心”,终与王三巧勾搭通奸。
由此可知,“三言”中塑造的“负心汉”具有软弱性、功利性、虚伪性等特征。软弱性主要指性格优柔寡断,毫无反抗精神和自主意识,身上缺乏男子应有的阳刚之气和责任担当。功利性是指为了金钱、身份地位不惜背信弃义,违背诺言。虚伪性是指前恭后倨,表里不一,道德败坏。软弱性在“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里比较多见,比如作品《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周廷章虽然长相漂亮,但却毫无责任心。功利性和虚伪性则在“荡子良女”和通奸式的故事中比较常见,比如莫稽为了攀龙附凤竟要置金玉奴于死地;李甲没有主见,出卖杜十娘;陈大郎勾引人妻并与其通奸,败坏道德。
二、 悲剧归因:财、色、情、仕的选择
1.逐利、重财的社会风气
明中叶以后,随着手工业的兴起,商品流通的进一步扩展,经商的人数的社会覆盖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上到亲王官爵,下到市井百姓都开始从事商品买卖活动,经商的社会风气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以及各阶层的人身上,这大大动摇了一直以来“重农抑商”和商业为末流的思想观念,社会市民的思想认识、道德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李贽等明末的思想家也都纷纷肯定人的私欲存在,李贽就主张:“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7]这从思想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意识信仰。言私重财、崇商逐利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在“三言”所描写的“负心汉”题材的爱情小说里,为了金钱而选择背信弃义的不在少数。周廷章在得知“魏同知十万之富,妆奁甚丰”后,才愿意娶父母安排的魏女,如果魏女的处境是贫困落魄,想必周廷章是不会娶她的。莫稽看到金团头家道富足所以选择入赘,当他后来有可能入赘更富有家庭的时候,他就选择了“趋利”。《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李甲更是以一千两银子将杜十娘卖给了孙富,重财逐利心态可见一斑。在陈大郎看来,要谋得王三巧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只要肯花钱,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所以他利用金钱收买牙婆,上下活动,终于得逞。在这些故事中,对金钱的迷恋和“趋利”心态是造成男子负心,婚姻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
2.“情少”、“色多”的爱情
在现代爱情中,我们谈论精神和肉体,精神和肉体是晚清才兴起的。明清时期,我们称之为“情”与“色”,明人认为“情”多半因“色”而起,因“色”而生。虽然有“无情之色”,但没有“无色之情”,即所谓“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多情”。“无情之色”重在欲,“少男少女,情色相当”是明人十分推崇的观念,明代在男女的情爱关系中“好色”一直是被肯定的。在“负心汉”题材的爱情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对“色”的追求大于“情”是造成爱情悲剧的又一重要原因。作品《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王娇鸾说:“只因有才有貌,所以相爱相怜”。爱情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才貌”基础之上,感情却很不牢固、极难通融。这里“色”是情的基础,王娇鸾的美貌多才,是周廷章最开始喜欢她的必要条件,后来当周廷章“访得魏女美色无双”后,因贪色就将其迎娶,一个“色”字是王娇鸾遭弃的重要原因,如果魏女长相一般或丑陋,恐怕周廷章不会改变主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李甲和杜十娘一见钟情的首要因素是李公子没有遇到过像杜十娘这么美的人,即“未逢美色”,作品中杜十娘则因“那公子俊俏庞儿,温存性儿,又是撒漫的手儿,帮衬的勤儿”[4]320-330,从一开始,两个人在一起的是因“色”,后来李公子没钱了,也是“迷恋十娘颜色,终日延捱。”作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陈大郎与王三巧通奸是典型的“无情之色”,毫无感情可言,关键在于一个“欲”字,色欲熏心是陈大郎负心的主要原因。从一开始,陈大郎想到的就是:“家里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与这些“色”大于“情”的故事相比,如果在爱情中“情”大于“色”,悲剧就很可能避免。作品《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第一次看见花魁娘子时,觉得此女“容频娇丽,体态轻盈,目所未睹,准准的呆子半晌,身子都酥麻了”[8]20-46。心中暗想道:“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8]20-46。男主角最初的动机在今天看来丝毫也算不上高尚,“色”字打头,但这并没有影响它成为中国言情之作的名篇,原因在于卖油郎的痴情,他“一日积一分,三年便成”的至诚,他的不功利,他的情有所寄。对于他情有所寄的对象,既不问得失,也不问成败,只是“情”的付出。所以最后卖油郎和花魁娘子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没有出现爱情悲剧。
在“情”与“色”的选择中,情多情少是爱情婚姻是否成功的关键,婚姻应该是建立在牢固的感情基础之上。
3.身份、地位的改变与追逐
在封建社会,婚姻都讲究门当户对,这里的门当户对不仅指财富方面,更重要的是门第和身份地位。“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和“学而优则仕”的意识在明代文人的潜意识里并没有完全抹去,他们依然重视婚姻门第的观念,入仕依然是他们的人生追求。一旦他们从困顿中走出来,比如考上了进士,做了官等,他们有机会实现传统价值观上面的人生理想时,他们更多地会选择自己的名声和地位。再者,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赋予了男子过多的权利。宋以后,男子可以多妻,女子却要守节;男子可以再娶,女子却不能再嫁;男子可以休妻,女子却不可以离夫。“负心汉”的出现与这种封建社会传统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分不开的。李甲平常与杜十娘你侬我侬时,一心想着杜十娘有多好,而当杜十娘要与他永结同好时,他却认为像杜十娘这样的风尘女子是不会被接受的,不敢给杜十娘妻子之名。孙富的挑拨也用的是封建门第思想,说明他虽然喜欢杜十娘,但在他的潜意识里杜十娘是不能够做他的妻子的。莫稽于困顿中娶金玉奴时,不觉得金玉奴配不上他,还觉得她是个“好女儿”,而当他做官以后便觉得金玉奴出身卑微,拜个团头做岳丈,是自己一生的污点。当男子飞黄腾达,取得身份、地位后就抛弃原配、另结新欢在“三言”中是很普遍的。
三、 悲剧根源:罪恶与心灵的碰撞
“三言”中的“负心汉”大多结局不好,生命都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黑格尔认为:“悲剧的实质就是伦理实体的自我分裂与重新和解,伦理实体的分裂是悲剧冲突产生的根源。在自然的冲突、人与外界的冲突、心灵的自我冲突这三种冲突中,心灵的自我冲突是最高冲突。冲突双方要维护个别化于自身的实体性的伦理力量,就造成了一种两难之境,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种两难之境的解决,就是代表片面伦理力量的人物遭受痛苦或毁灭。”[9]在“三言”中所涉及的“负心汉”,要么与周围所处的环境有冲突,要么有心灵的自我冲突,面对冲突的选择时,他们有的屈服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有的则屈服于自己内心的欲望,因此破坏或放弃了冲突的另一面,使那些与他们相处的女子遭受痛苦或者死亡,酿成爱情婚姻的悲剧。这里我们应当承认:长期的封建思想观念或者说社会文化意识对人有异化作用。我们看到“负心汉”的周围往往充斥着强大的封建力量,不管是封建家长制还是他们自身的潜意识,即内心传统的思想观念,它在某一个时间段就会出现,让当事人陷入一个两难的选择境地。由于周围的力量太过强大,他们不具有最终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们往往会屈从于家庭、社会,而屈从的结果却没有使他们得到真正的幸福,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他们造成与他们相处的女子的悲剧——被抛弃或者死亡,同时也造成了他们自己的悲剧——受到谴责与痛苦的煎熬。作品《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周廷章屈从于自己内心的财色欲望,屈从于家庭的安排另娶新欢,造成王娇鸾含恨而终,他自己最后也被他的上司乱棍打死。“着体处血肉交飞。顷刻之间,化为肉酱。满城人无不称快”。作品《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莫稽为了权势地位,竟然狠心地将金玉奴推入江中,后来同样为了权势地位又遇到金玉奴,遭棒打,落下个薄幸的名声。作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陈大郎最终钱财被洗劫一空,死在路途中。心灵自我冲突人物的典型当属《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李甲。他心里爱杜十娘,但爱得不够大气,因为他所有思考的问题都是从自己出发,当杜十娘看到鸨儿贪财无义,想与他永结同好时,他却优柔寡断,“惧怕老爷,不敢应承”,这是他心里的第一次妥协。面对孙富的挑唆,他又一次妥协,结果落得人财两空,还被众人唾骂为李薄倖,声名受到影响。而他自己在舟中“看了千金,转忆十娘,终日愧悔,郁成狂疾,终身不痊”[4]320-330。这些“负心汉”受制于封建环境、受制于欲望,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加之他们良心发现后的自我折磨,都是他们所体现的悲剧意义。“三言”中的莫稽、李甲、陈大郎最后都对自己进行了自我反思,这是道德反思与“良心发现”的过程,是自我的心灵冲突和自我意识的道德痛苦,他们在没有泯灭的人性和个人欲望中徘徊,在眷情与绝情中冲突,他们的罪恶是永远的,心灵折磨也是永远的,罪恶与心灵的冲突一直延续,这正是“负心汉”形象的悲剧性所在。
“三言”中“负心汉”形象的建构是从他们对“财、色、情、仕”的选择入手,揭示了他们身上的罪恶与心灵持续碰撞的悲剧根源,呈现给我们一群“类型化”的可怜人群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环境、欲望和心灵发生冲突时,一定要追随心灵。人性不能被欲望和社会环境异化,否则会出现类型化的悲剧群体。在对待爱情婚姻时,一定要立足情感基础,将“情”放在第一位,情有所寄,才能避免爱情婚姻的悲剧。
[1]诗经·氓[M].北京:中华书局,2013:169.
[2]乐府诗选[M].余冠英,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朱全福.“三言”“二拍”研究·序[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2.
[4]冯梦龙.警世通言[M].上海:中华书局,2009.
[5]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朱全福.“三言”“二拍”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315.
[7]李贽.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78.
[8]冯梦龙.醒世恒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德)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60.
责任编辑 刘晓华
On the Tragic Construction of “Heartbreaker” Image in theJingshiTongyan
QI Ting-t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China)
The motif of “heartbreaker” is an important kind of traditional love literature models. In theJingshiTongyan, the writer Feng Menglong reveals that the reason for tragedy originates from the continuous conflict between heartbreakers’ crimes and their sou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ney, sex, emotion, fame” , which shows a group of poor typification images. In these four aspects, those heartbreakers with weak, greedy and prurient character and lifeless and vitality prefer pursuing “sex, money and fame” to selecting “emotion”. Submitting to the environment and desire, they destroy other people and themselves; therefore, their tragedy lies in the continuous conflict between crimes and souls.
JingshiTongyan; heartbreaker; tragedy
2016-03-10
齐婷婷(1991-),女,陕西高洛人,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学、宗教。
I206
A
1673-6133(2016)04-005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