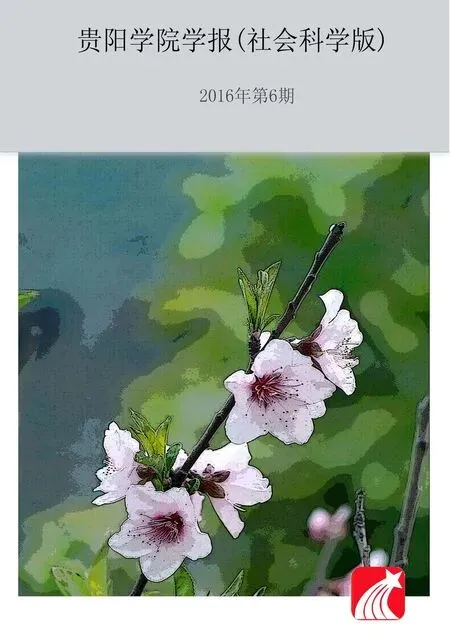杂糅与超越:形象学视域下的考琳·麦卡洛小说《呼唤》之中国缘
邱坚娜
(泉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杂糅与超越:形象学视域下的考琳·麦卡洛小说《呼唤》之中国缘
邱坚娜
(泉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从形象学入手,对澳大利亚女作家考琳·麦卡洛的小说《呼唤》中跨文化语境下充满杂糅性的中国元素进行文本解读,从中透视中西文化的差异、冲突与交融,并期望在全球化语境下实现国家间平等的文化交流。
考琳·麦卡洛;《呼唤》;中国缘;形象学 ;西方中国形象
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英语世界,尽管在语言文学研究体系处于边缘地位的澳大利亚文学,但在英美主流文学的大背景之下从含苞待放到百花齐放,开始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1973年,澳大利亚文学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现代主义文学巨匠帕特里克·怀特开始,澳大利亚小说迈出国门走向世界[1]127,直至澳大利亚亚裔文学的卓越代表布莱恩·卡斯特罗,澳大利亚华人形象跃然纸上。1977年,从大洋洲飞出了一只享誉全球的《荆棘鸟》,该作者便是澳大利亚当代杰出女作家考琳·麦卡洛。时至2003年,她又呕心沥血完成《呼唤》一书,成功再续家世小说与爱情传奇。而小说中所诠释的中国之缘,在充满杂糅性的跨文化语境下耐人寻味,同时又颇具超越性的学术韵味。
毋庸置疑,涉及中国题材的英语小说首推美国
作家赛珍珠,正如尼克松所说,赛珍珠乃沟通中西文化之桥梁。[2]而考琳·麦卡洛即是沟通中澳两国人民友好感情的纽带之一。然而她与作为澳大利亚中国形象研究热点的布莱恩·卡斯特罗有所不同,他们虽均为重树华人形象笔耕不辍,展现澳大利亚华人的苦难历史和奋斗精神,但是对于在“白澳政策”下遭受种族主义者极尽蹂躏的澳大利亚华人,考琳·麦卡洛在《呼唤》一书中进行了全方位的赞美与歌颂[3]5,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引人瞩目并值得探究。
一、形象学与西方中国形象
从形象学入手,必须首先明确该理论涉及的一对基本概念,即“自我”与“他者”。学者巴柔(Daniel H.Pageaux)指出:任何形象都源自两者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4]155按照他的定义,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即是“他者”[4]118。因此,在形象学视域下,笔者研究的是澳大利亚考琳·麦卡洛小说《呼唤》中的异国形象即西方的中国形象。它是西方长期关注并日新月异的一种文化现象,该研究涉及跨语言、跨文化领域。针对形象学研究的模式化倾向,例如:过分僵化于“自我”的主体地位或者忽视“他者”原型的问题,最有效的解决方法便是回归文本,进行个案分析,同时结合作者自身的文化背景与情感因素。
二、考琳·麦卡洛《呼唤》的中国缘及其杂糅性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Bhabha,H.K.)的杂糅性理念认为杂糅意味着两个或两个以上元素的混合,包括性别、阶层、民族、宗教和文化,并提出广大移民可以从“中间区域”获得身份认同的观点。[5]这就是所谓的“第三空间”,超越“自我”与“他者”的边界,从中减少文化的不确定性并达成杂糅的形式。该部分以此杂糅性为视角,一一解析考琳·麦卡洛小说《呼唤》中涉及中国元素的杂糅特征,包括人物身份的杂糅与人物关系的杂糅,多元时空的杂糅与多元文化的杂糅,从中透视中西文化的差异、冲突与交融。
(一)人物形象的杂糅性
小说《呼唤》中出现的中国人物形象屈指可数,但过目难忘,充满杂糅性的人物身份与人物关系令人万般纠结又潸然泪下。其中的代表人物当属男主人公之一的李。他集多种元素于一身,包括错综复杂的身世、辗转反复的经历和恶始善终的爱情。出生于澳大利亚的李是中国人孙楚和澳大利亚人贝茹的私生子,之后他成为孙楚的合伙人、与贝茹真心相爱,却娶十六岁堂妹伊丽莎白为妻、原是苏格兰私生子而后富甲一方的亚历山大的义子。在此期间贝茹与伊丽莎白居然情同手足,三个人过着堪称畸形的生活。他以中国王子的身份留学英国,学成归来后却即刻爱上了比他年长六岁的义母伊丽莎白,但是迫于多重压力、浪迹欧亚,创业伊朗。然而,终究回归澳大利亚的他与爱人伊丽莎白还是发出了压抑十六年的、充满爱的心灵的呼唤,宣告了他们忠贞不渝、感人至深的爱情,而身为义父与丈夫的亚历山大则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深爱他、他也深爱的人们铺平了一条幸福之路。以上陈述囊括了亲情、爱情和友情三个内容,包含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生命伦理三个内涵。尤其李和伊丽莎白的这场旷世奇恋,涉及跨国恋、婚外恋、乃至乱伦主题等诸多因素,凸显了两性关系建构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沉沦与救赎,考琳·麦卡洛无情鞭挞人性之恶、热情讴歌人性之美,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并拥有非凡的气魄,像亚历山大和李一样的英雄人物形象才能够得以升华。
(二)文化背景的杂糅性
从单纯文本出发,作者采用后现代写作策略,对文本的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进行多次转化,导致小说背景上的时空错位及重合,造成多元时空的杂糅,这一点从以上人物形象的杂糅性中得以间接说明。从时代背景着眼,多元文化社会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发展趋势,各国移民的交会、多种宗教的共存和异质文明的并置,造成多元文化的杂糅。小说中的孙楚就是一位由于不满晚清政坛腐败,流落海外淘金的澳大利亚华人移民,因为金矿他同苏格兰人“金山之王”亚历山大结盟创立“天启公司”,言下之意就是上帝的启示,从中表达了对西方基督教与上帝的深切信任。而在深受基督教教义禁锢的伊丽莎白身边却有一位名叫玉的中国女仆,她至死也不愿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作为中澳混血的李,兼具中国传统思想和多元文化的熏陶,从为爱走天涯直至迸发出心灵的呼唤,正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冲突与交融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光辉典范。
三、考琳·麦卡洛《呼唤》的亲善型及其超越性
从考琳·麦卡洛小说《呼唤》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虽然处于西方强势文明和英语世界之下,相较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相对负面的中国形象,她却能够呈现出超越“他者”形象的非“东方主义”范式,高瞻远瞩摒弃前人甚至对同时代人对中国的偏见,而采取了一种友善的观察态度,倾情推出爱的《呼唤》。
(一)亲善型之文本表现
考琳·麦卡洛对中国形象近乎正面的描述,可以归诸于形象学理论中的“亲善型”[6]111-115,亲善顾名思义指亲切而友善,这样的描述在小说中并不鲜见。在她的笔下,中国人具有美丽的心灵甚至外表,兼具勤劳、勇敢、善良、聪慧等优良品德。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医、中药和中餐她也推崇备至。在小说中,一位集智慧、勇气与忠诚于一身的中国女仆玉令人印象深刻。即将被判处绞刑,但是“玉坦然微笑,深棕色的大眼睛里没有丝毫恐惧更没有后悔,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之感。从天而降的雨水似乎一点儿也没有打搅她。她看起来那么安详,没有牧师到场,玉拒绝这种精神上的抚慰。她坚持说,她没有洗礼,不是基督教徒”[3]5。在同情与美化澳大利亚华人的同时,更表明了她对移民政策与环境的控诉。纵观全文,作者企图表达的关于中国人的精神与林语堂先生《吾国吾民》的文化内涵是基本契合的。无论如何,且从亲善型角度出发,对于作品所呈现的中国形象是否完全忠于现实暂且不论,同时承认异质文明之间的形象很难完全摆脱自身的文化逻辑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6]111-115。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大家为何要刻意拒绝或者执意批判,为何不以一种开放的态度与乐观的心态接纳异质文明的亲善之举?
(二)超越性之西方中国形象
1.西方中国形象的误解
相较于考琳·麦卡洛的亲善之举与《呼唤》中近乎正面的中国形象建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内因与外因的合力之下虽然历经变迁仍旧存在着诸多误解,作为一种出现在文学文本或者任何形式文本中的异国形象,学者巴柔(Daniel H.Pageaux)认为,它们是在文学化和社会化的交叉进程中获得的对异国认识的集合。[4]4纵观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用错综复杂、变幻莫测、扑朔迷离十二个字来形容可谓精辟准确,它大体上经历了四种类型的变迁:神话化、理想化、乌托邦化和丑化或妖魔化。[7]其中相对否定和负面的中国形象比比皆是,从国家至国民,从外表至个性。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曾经是香格里拉也是人间地狱,中国人被冠以“中国佬约翰”“异教徒中国佬”“付满楚”“哲人王”“查理·陈”等标签。[8]其中,出神入化地代表当属称“中国是宇宙的中心点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地方”的西班牙教士闵明我;龌龊之至的代表当属英国作家笛福,在他的笔下“中国人不过是一堆贱骨头、一群愚民、龌龊的奴隶,臣服于一个只配管理这种民族的政府之下”;然而最意味深长而又颇具禅意的点评则来自美国作家派克,他说虽然历经磨难,中国人仍旧时常保留神秘的微笑。[9]尽管如此,以《呼唤》为代表的相对正面客观的西方中国形象虽然乏善可陈,但是依旧也必须具有上升的空间和趋势。
2.“东方主义”的超越
西方中国形象之关键,并不在于中国这个“他者”形象本身,也不在于西方究竟从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现实,而在于西方的主观想象,在于西方如何从“他者”形象中认同了“自我”,这就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东方主义”范式的核心所在。[10]换言之,西方中国形象仅仅是作为一种“他者”,以被动的宿命参与到西方文化出于自身需要的自我建构之中。当“自我”不满现状之时,则需要构建一个正面的“他者”形象进行自我超越;当“自我”满怀自信之时,则需要构建一个负面的“他者”形象进行自我肯定。究其原委,一方面是出于对自身的不满或自信;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异域的向往或鄙视。根据东方主义理论,考琳·麦卡洛《呼唤》中的亲善之举可以归结为对于自身的不满或者对于中国的向往,然而这并非本文的意图所在。
综上所述,超越“东方主义”,完善“他者”形象势在必行。问题在于,中国形象由谁塑造与传播?首先,对于他者中国形象的态度应该是不沉默,有度量。如果沉默就意味着从“他者”中国形象中认同了自身,因为不能将别人眼中的中国变成中国人自己眼中的中国。一个有格局的国家,必须拥有包容开放的态度,做到不卑不亢,不偏不倚。同时,从“他者”中国形象中反观自身,汲取参考意见和建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将有助于中国形象的自我反省、自我定位与自我完善。更何况像考琳·麦卡洛与《呼唤》一样充满爱与正能量的作家与作品与日俱增,所以断然不能全盘否定。然而,客观存在并令人费解的问题是,来自异域的“自我”,从注视者的观察视角,尽管努力挣脱“他者”与“自我”关系的枷锁并试图超越“东方主义”,即便主观上怀着客观的态度与美好的意愿包括来自澳大利亚的考琳·麦卡洛,中国人民也选择相信她对中国的美好感情,但是出于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思维局限诸多主客观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都不能也不可能全然超越自身的文化,将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个人与时代的烙印。因此,中国要发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建构超越“他者”形象非“东方主义”范式的中国形象。不做搔首弄姿哗众取宠的自我丑化,正视自己,批判偏见,消除误解乃至整个西方话语霸权;主动而理性地分析中国形象的内涵与外延,与时俱进客观全面地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的卓越雄姿。
四、考琳·麦卡洛《呼唤》的亲善型中国缘之成因
扪心自问,中西文化本是两种不对等的异质文明,处于西方文明世界的考琳·麦卡洛何以能够或者是否真的能够超越“自我”,甚至站在中国和中国人的立场,对“他者”中国采取相对客观正面的态度?让-马克·莫哈指出:一切形象均包含异国的、出自一个文化的、以及一个作家所创造的形象。[4]25以上说明立场中立,鉴于措辞“中国缘”,本文对于《呼唤》中的西方中国形象建构之评价不言而喻。
考琳·麦卡洛在2004年10月30日写给译者的信中向中国人民直接伸出了友好的橄榄枝:“随信寄去的《呼唤》有一个重要情节,介绍了十九世纪中国人在澳大利亚金矿的生产、生活状况,其中一个主要人物是中国人,希望中国读者们喜欢。”[3]5考琳·麦卡洛于1937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一个牧业家庭,从游牧生活四处为家到辗转澳洲、英国、美国求学行医,最终隐退澳洲孤岛,笔耕不辍。多元文化的熏陶以及多舛生活的历练为其拓宽了写作思路与视野;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的多重身份为其触发了多重创作灵感,尤其是她的医学背景,是其在小说《呼唤》中推崇中医、中药的源泉;父母不幸婚姻的心灵创伤以及自身从不婚主义至喜结连理的极度转变,为其爱情传奇的缔造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从情感自觉出发,正如上文所说,《呼唤》属于形象学理论中的“亲善型”,主要在于她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具有一种源自内心的原始的“亲善”态度,从她为促进第三世界神经生理学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令其荣登澳大利亚百名卓越人物榜足以证明。这种情感上的自觉性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令其首先怀着一颗同情之心或了解之情尝试走进中国、走近中国人。在对中国形象相对写实的同时,也蕴含着考琳·麦卡洛所处的西方文明对此形象某种程度上的认可,由此呈现出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文化一种互相了解和认同的趋势和状态。其次,从文化意识入手,基于基督徒的文化身份与仁爱精神,作者见证了西方文明自身的诸多缺陷与不足,努力进行中西文化反思,试图在“他者”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中完善自身,用自我积极进取的正面立场取代出于西方自身需要的负面臆断。或者,根据任何形象全部源于自我意识的理论,植根于人类基本的道德观念,作者的亲善之举单纯表达了对于中国的尊重,这简单却不失厚重的道理才是本文呼唤的主旨所在。
五、结语
从“白澳政策”到1973年澳大利亚政府实施包涵团结、平等、博爱和共同繁荣的多元文化政策[1]295,至2016年中国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协议,澳大利亚将向中国公民提供十年期多次往返签证的利好政策出台。事实证明,澳大利亚华人的苦难史和奋斗史不能忘却,文化母体在空间移位者身份认定中起到的作用不能忽视,但是在以移民为主多元文化政策下的澳洲社会,务必积极探寻并努力建构华人移民身份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简而言之落在实处不外乎八个汉字:互相尊重、彼此融合。这是《呼唤》问世的价值所在,也是远在南天的考琳·麦卡洛的美好期待。最后,再次借助“自我”与“他者”的概念强调,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错综复杂而微妙至极,相互分开又彼此联系,双方的积极互动与诚挚合作才是修补西方中国形象的误解、促进西方中国形象的建构之重点与关键。因为,只有以积极诚恳开放的姿态主动地参与到世界文化平等对话中来,才能为国家间平等互惠的文化交流探寻一条可行之径和长远之策。[11]通过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建设多元文化关系,追求多元文化和谐,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中建构中国形象,这才是一个呼之欲出并且关系到全人类进步的美好课题。
[1]黄源深,彭青龙.澳大利亚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许晓霞.赛珍珠纪念文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9.
[3](澳)考琳·麦卡洛.呼唤[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4]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5]Bhabha,H.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Routledge,1994:12.
[6]王霞.西方中心论语境下的近代中国妇女形象—兼及形象学理论运用的反思 [J].兰州学刊,2012(4).
[7]伍辉.西方中国形象变迁[D].济南:山东大学,2008:6.
[8]姜智芹.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J].国外文学, 2004(1):45-50.
[9](美)史景迁.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0]左燕.权利与话语[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5.
[11]杨波.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论20世纪初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2):90-96.
[责任编辑 刘晓华]
Hybridity and Transcendence: the Chinese Fate in Colleen McCullough’s Novel ”The Tou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ology
QIU Jian-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Fujia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ology,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Chinese elements full of hybridity in intercultural context in The Touch , written by the Australian female writer Colleen McCullough, from which we can see differences ,conflicts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expect to achieve equ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mong nations under globalization.
Colleen McCullough;TheTouch; Chinese elements; imagology; western image of China
2016-09-29
邱坚娜(1979-),女,福建永安人,泉州师范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研究。
I106.4
A
1673-6133(2016)06-01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