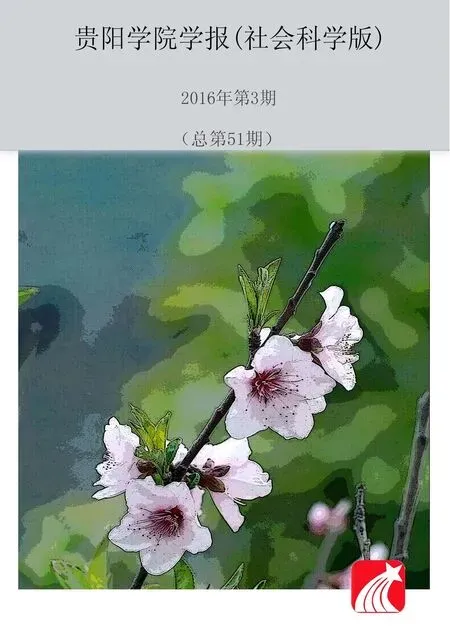论王全安影视作品中女性身体苦难的想象性言说*
刘坤厚
(贵州师范大学 党委宣传部,贵州 贵阳 550001)
论王全安影视作品中女性身体苦难的想象性言说*
刘坤厚
(贵州师范大学 党委宣传部,贵州 贵阳 550001)
身体叙事作为一种突出描写人的身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常用在小说和电影中,尤其是在作为视听艺术存在的“第七艺术”——电影中。在影视文化中随处可见女性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女性的性别和身体都可以参与叙事,而且在影视作品中用身体叙事比用语言更为直接有力,还避免了许多因语言叙述而出现的尴尬和无奈。王全安的电影中有的部分同样也采用了直接以身体来叙述的方式。
王全安;身体叙事;想象
身体叙事也称为身体写作,是女权主义者在较早的时候提倡的一种文学上的创作策略,带有较强的性别政治意味。优美的舞蹈、充满力量的功夫,强健美丽的身体或者羸弱被凌辱的身体等等,身体承担着叙事的功能——既是行为的载体,也是被凝视的客体。大千世界之中的身体没有相同的,因此是不可复制的。当身体积极参与叙事或处于相应状态之中,那么身体就具备了更为复杂的意义和功能:身体是人物行为、思想最为主要、最为直接的载体,也是人物感知世界最根本、最便捷的“媒介”,还是被“他者”凝视的对象(尤其是女性身体,不管是女性娇艳的身体,还是创伤的身体),同时人物身体的存在状态(生老病死伤残等等)也会影响甚至控制人物的行为、思想。也就是说,当人物在进行某种叙述或凝视之时,其身体就已经处于“说”与“被说”的媒介——叙事与自我叙事,也就是身体叙事的核心所在。运用视听语言表达主题思想的影视文本之中,身体参与叙事的状态几乎无处不在,通过身体叙事能够引发人们对自己身体存在的状态、生命的生存状态以及生命意义的思考。尼采认为,“身体的力学乃是审美的根据,正如审美的领域决定于生命的光学一样……在审美的过程中,身体始终是出发点、中心、目的,以其力学和光学创造美学。发挥作用的有感官、肢体、情欲,当然还有思想,亦即审美乃是身体各部分机能(包括‘意志之手’)整体协作的结果,此时感性即是神性,自我肯定的意志贯穿于人所是的身体,自豪、忘情、放纵的快乐充盈于其中,并向世界流溢乃至喷射。”[1]“身体具有文化的意义,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皆被身体所呈现,既可呈现权力的控制,也是自我认同的可见的携带者。”[2]梅洛·庞蒂也指出,“身体是奇特的物体,它把自己的各部分当作世界的一般象征来使用,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得以‘经常接触’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一种意义”。[3]存在主义更是赋予了“身体”极为重要的意义,身体首先“存在”才能在此基础上承载“思想”,身体这一感知世界媒介也赋予了人们思考“存在”本身的意义。“梅洛·庞蒂建立在“身体—主体”基础上的审美体验,既是对人作为精神主体至高无上性的还原,更是对人感知力的拓展。”[4]
叙事是人类描述现实世界和组建意义世界最常用的、最主要的手段。随时代不断发展变迁、艺术理念不断演进、表现手法更加多元,除了传统的舞蹈、戏剧、武术等身体参与叙事形式之外,电影艺术、行为艺术等开始成为新的身体参与叙事形式,身体也承担了更具张力的叙事功能和意义。
王全安虽然是男性电影导演,但是在影片当中他始终偏爱女性,以平等的视角来看待女性、关爱女性。对于男性,王全安没有显示男性的优越和优秀,反而一直尝试揭露男性身体、心理的缺陷,在影片中塑造了胡小兵、姜锁、巴特尔、森格、白嘉轩、白孝文等等一系列的男性人物形象。他们无一例外地或是心理或是生理上有缺陷,而且他们无一例外地对女性人物造成了伤害。也正因为这些有缺陷的男性人物的在场,王全安所建构的具有现实质感的影像世界、关注女性的视角、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等才得以顺利地实现。
一、女性身体苦难展示及其叙事功能
在王全安的最具代表性的两部作品之中,《图雅的婚事》和《纺织姑娘》人物命运的转折都是身体的直接原因。身体的疾病威胁着主人公的生命存在,因而他们在面对生命的危机时必然会思考和反思自己的生活、感情、人生、命运等等问题,这也是导演戳破影片中人物生存的气泡,让他们暴露在身体与社会危机之下的那根“针”。图雅的生活面临着极大的危机,丈夫为了寻求新的水源被砸断了腿,几十公里外他们赖以生存的那口井也慢慢地干涸了,图雅自己也因为长期超负荷劳作面临瘫痪的危险……这些直接的威胁让图雅不得不选择与丈夫离婚。因此,可以说身体创伤的原因是导致图雅当时困境的最直接的原因。而在《纺织姑娘》中,身体原因同样是促使李丽去寻找自己爱情失落、生活不快的真相的最为直接的原因。
1.女性创伤的身体
与图雅和李丽的身体创伤、疾病类似的身体叙事在王全安的其他几部影片中也有运用。在王全安的处女作《月蚀》中,雅男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女性,有自己的工作,但因为心脏病而不得不回归家庭。身体的原因是直接导致雅男远离独立的个人生存状态,而回归到传统的对女性的要求——回归家庭,成为妻子、母亲,成为男人的依附之物。佳娘同样面临着身体疾病的危机,但她依旧乐观,敢于追求自己的梦想。雅男与佳娘在这一点上,事实上形成了对比,同样面临身体的疾病威胁,雅男放弃了工作回归传统要求,而佳娘则在苦苦地寻求实现自己梦想的可能的途径,哪怕被伤害也不后悔。王全安在这里,让雅男和佳娘对比,凸显影片的张力,形成隐喻和反讽。
《惊蛰》中,关二妹一出场就以一个不停忙碌的农村女孩的身份出现,在影片中关二妹很多时候也都是以劳作的姿态出现的,而且她还是可以被“卖”,某种程度上她是被物化了的女性身体。对应于关二妹的丈夫最后被阉割的身体来说,关二妹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主动权。大年夜里带着生病的孩子去县城看病,丈夫酩酊大醉承担不了传统社会意义上男人的职责,关二妹被迫承担起传统意义上男人应该承担的重担,驾驶拖拉机,在漆黑的夜里赶往县城。当太阳再次光临大地时,关二妹正疲惫地驾驶着拖拉机,而丈夫则安静地坐在车斗里,披盖着大花的被子,怀里抱着生病的儿子。此刻传统意义上对男女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男女的社会姿态则完全颠倒,在这里身体参与了叙事,也暗露了导演的态度。
影片中另外一个人物毛女则完全是一个迷失了自我的男人欲望的身体。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虽然毛女早于关二妹来到城市,或许可以完成对关二妹的启蒙,包括生活和性,但是毛女自身就处在迷失的状态,沦为男人的欲望身体,这决定了她对关二妹的启蒙是不会成功的。
2.女性娇艳的身体
《白鹿原》虽然是一部厚重的史诗般的民族历史剧作,但在影片中王全安更加突出了身体的叙事。如果说白嘉轩是白鹿原上最后矗立的一根干裂的木棍,那么田小娥则是初来乍到的一株新鲜娇媚的罂粟花。田小娥最初出现在影片中就是以男性欲望的身体出现的,即一个心理和生理无法得到满足的娇艳美妾,她对男人有着致命的诱惑。对正处在青春期对女人更为好奇的黑娃来说,田小娥的身体的诱惑更是不可抗拒。
田小娥对自己处在男人欲望对象的地位无法作出自己的选择,然而她处在男人欲望对象的位置上,连生理的满足都无法获得,因而黑娃的出现让她至少满足生理的欲望。虽然还是处在男人欲望对象的位置上,但田小娥选择了跟贫贱的黑娃一起回到白鹿原上,希望自己从此摆脱男人欲望的对象的身份,哪怕仅仅是名份上的。她的美丽让白鹿原黯然失色,让白鹿原上的男人们躁动不安,白嘉轩、鹿子霖、鹿三、白孝文无不如此,连痴傻的狗娃都蠢蠢欲动。跟随黑娃来到白鹿原并没有让田小娥摆脱男人欲望对象的命运,反而陷入了更大更多的男人欲望的陷阱中。因为曾经的不容于传统道德的身份,道学家白嘉轩坚决不肯认同田小娥新的身份——黑娃的妻子。虽然不被白鹿原承认,也没有锦衣玉食,但至少黑娃能够满足她的部分生理和心理需求,田小娥在白鹿原上安定了下来。社会大环境的动乱裹挟着普通的民众,田小娥也无法置身事外。为了救出犯事被抓的黑娃,田小娥向鹿子霖寻求帮助,却给鹿子霖提供了借口,成为了他的欲望对象。为了报复白嘉轩而勾引白孝文,却真正激起了白孝文的男性功能。白孝文为了跟田小娥在一起,与家庭反目成仇,自己也倾家荡产,最后卖身投军。跟白孝文在一起让田小娥获得了片刻的欢愉,但最后被鹿三刺死,死后又被白嘉轩做主埋在六角塔下。
田小娥的一生都是男人的欲望对象,不管活着还是死去。她从来没有被当作一个真正的人来对待,即使是死去之后也不被原谅。然而讽刺的是,白孝文这个传统道德培养的接班人却是被田小娥唤起了男性的功能,最后不顾一切地与之生活在一起。
二、强化身体苦难与建构现实性
古往今来的许多文本中,“文人墨客”都塑造了许多鲜活而伟大的女性,这些女性往往被迫走上自愿自我牺牲的“神坛”进行“伟大”的献祭。“文人墨客”正是通过讴歌女性“伟大”的自愿自我牺牲来掩盖女性被伤害、被牺牲的状态。更甚者,女性的“自愿自我牺牲”往往成为用来黏合阶层鸿沟、掩盖底层群体苦难与某些社会制度缺失的迷雾。波伏娃指出:“于是,神话思想使唯一的、不变的,永恒的女性,同现实女人之分散的,偶然的,多样化的存在相对立。”[5]当代中国底层影像在自觉不自觉间试图揭示女性“自愿自我牺牲”“伟大”神话的残忍与蒙蔽。《图雅的婚事》讲述了蒙古族普通妇女图雅试图通过自我牺牲的方式来拯救家庭的苦难故事。“嫁夫养夫”的女性通常都会被称赞“有情有义”,而成为展现民俗奇观和女性牺牲神话的叙事场域。导演有意识地用影片前半段“牺牲女人或女人牺牲” 暧昧不清的色彩掩盖重压在图雅身上的整个家庭的生存压力。王全安没有再继续采用俗套而隐蔽的女性“自愿自我牺牲”的神话来叙述图雅的艰辛与苦难,从而满足观众观赏民俗奇观、称赞女性伟大欲望。在影片的结尾,图雅最终答应了森格的求婚,除了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个男人之外,更重要的是格森同意接受前夫。然而,在婚礼上前夫与格森却大打出手,让图雅心灰意冷,喊出了:“你们都是混蛋”。图雅的这一声怒吼事实上宣告了女性牺牲神话的虚无。图雅——这位普通而坚韧的蒙古女人想要“卖掉”自己来拯救家庭,然而事实上她柔弱的肩膀无法挑起改变生存现状的艰难。而且,曲折的叙事和伦理表达之下隐藏着更为宏达的叙事,蒙古族人民当下艰辛生存的现场在女性“自愿自我牺牲”神话被打破之后浮出地表。
王全安特别关注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女性。他将镜头聚焦到底层女性的情感、生存、命运中,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下她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以期在历史语境之中揭露女性自我牺牲神话所竭力遮蔽的性别与阶层的鸿沟。他感叹:“《月蚀》和《惊蛰》是一个主题,就是梦的破裂,是一种生命历程。我们看到的是无奈,就是不得不回到规则里,而这种破裂的梦,是奠定在真实基础上的。艺术最大的魅力就在于真实。如果不真实就等于失去了他最重要的品质,即使在商业片里也离不开真实。也就是说,你应该跟生活保持一致。电影的真实,其实就是感情的真实,我个人认为这种品质非常重要,而且这种品质在中国的电影里面很严重地缺失了,很影响我们电影未来走的路。所以,不管是文化电影、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真实是基础,是起点。艺术华丽高深的渲染,其实都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6]
三、结语
通过分析王全安的电影作品我们发现,王全安所坚守的真实是强化、拼贴现实的结果,尤其是在影片中对女性身体苦难地强化和建构。在《月蚀》《纺织姑娘》《团圆》(未公映)《惊蛰》《图雅的婚事》《白鹿原》等等影片中,身体的苦难都被刻意地强化了。如果雅男的心脏病没有触发、李丽没有患血癌、二妹的爷爷没有去世、巴特尔和图雅身体不被瘫痪威胁等等,很难想象到王全安所坚持的影片中真实性或者说现实性该怎样展现,影片又该怎样推进。
[1]王晓华.身体美学:回归身体主体的美学—以西方美学史为例[J].江海学刊,2005(3):5.
[2]林树明.身体叙事及色情文学的性别倾向批判[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7):87.
[3]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02.
[4]杨经建.身体叙事——一种存在主义的文学创作症候[J].文学评论,2009(2):118.
[5]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06.
[6]文韵.王全安:关注女性,关注小人物[J].大江周刊(生活),2010(4):16.
责任编辑 何志玉
On the imaginary speech of female physical suffering in Wang Quanan's films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LIU Kun-hou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Publicity Department, Guiyang,550001,Guizhou,China)
Body Narrative is an artistic expression in describing the human body, which often used in novels and movies, especially in the audio-visual art as "the seventh art" - the movie. Women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audio-visual culture. Both female’s gender and body can participate in the narrative. Not only body narrative is more powerful and direct than the language in the films, but also avoids the embarrassment and frustration caused by the languages. Body narrative is also used in some parts of Wang Quan's films.
Wang Quanan; Body Narrative; Imagine
2016-03-22
刘坤厚(1985-),男,河南信阳人, 贵州师范大学教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美学、电影美学。
J905
A
1673-6133(2016)03-0090-03
——以电影《图雅的婚事》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