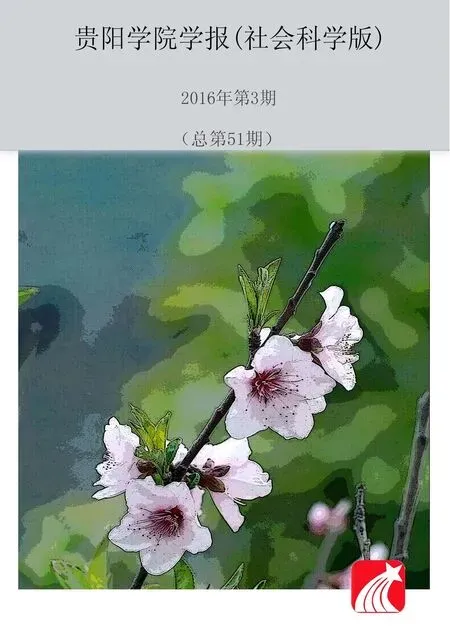中国当代推理小说创作特色研究——以呼延云系列推理小说为例*
王美雨,李 娟
(1.临沂大学 文学院,山东 临沂 276012;2.东营市委宣传部,山东 东营 257100)
中国当代推理小说创作特色研究
——以呼延云系列推理小说为例*
王美雨,李 娟
(1.临沂大学 文学院,山东 临沂 276012;2.东营市委宣传部,山东 东营 257100)
在国外推理小说模式成熟、艺术风格多样化的背景下,已有的推理模式架构下的内容已经不足以满足受众的需求,创建新的推理模式及内容就成为国内推理小说家不得不面对的任务。国内新锐推理小说家呼延云的系列小说可以称作是其中建构新推理模式、内容的成功代表。呼延云系列推理小说更加注重对文化、社会及人性的关注,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建构起一种众人参与推理、依托传统文化、观照社会现实、重视情感的新模式,给受众带来一种在文化、现实、情感中感受推理乐趣的新鲜的审美愉悦感。
推理小说;呼延云;创作特色
从公案小说到当代推理小说,从由冤魂暗中提供线索到冤魂退出、办案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寻觅线索,中国的侦探类小说经过了漫长的历史。严格来讲,公案小说是本土小说,推理小说是外来探案模式,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探案模式、人物塑造方式。然而,当推理小说这种外来探案模式一经融入到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显示出了与其他国家同类小说不同的特点,即在中国的推理小说中多采用传统文化、鬼魂等和推理模式相结合的方式。
推理小说一直不为文学界、评论界认为是正统文学作品,就连大学的现当代文学教材中也很少涉及推理小说。在现有针对推理小说的研究中,大多是对国外著名的推理小说家如东野圭吾、松本清张、爱伦·坡、约瑟芬·铁伊、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进行研究,极少对国内的推理小说开展研究,尽管国内也有“侦探推理小说发展研讨会”,但由于先入为主经验以及中国推理小说本身的确存在着一定问题,因此,并没有引起学界对国内侦探推理小说的足够重视,偶尔涉及也是以批判居多。然而,一种文学形式不会因为文学界、评论界的不认同、不关注就会停止发展的脚步,随着国内推理小说形式的成熟及内容的广度性逐渐增强,它必定会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国外推理小说模式成熟、艺术风格多样化的背景下,已有的推理模式架构下的内容已经不足以满足受众的需求,建构新的推理模式及内容就成为国内推理小说家不得不面对的任务。国内新锐推理小说家呼延云的系列小说可以称作是其中建构新推理模式、内容的成功代表。
呼延云系列推理小说中所建构的推理小说模式和内容发生了富有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变化,这一点完全不同于美国的硬汉派、日本的社会派,也与新本格派注重谜团的富丽堂皇、案件的扑朔迷离等不同。呼延云系列推理小说更加注重对文化、社会及人性的关注,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建构起一种众人参与推理、依托传统文化、观照社会现实、重视情感的新模式,给受众带来一种在文化、现实、情感中感受推理乐趣的新鲜的审美愉悦感。
一、众人参与式推理模式
推理小说也可叫做侦探小说,存世接近200年,最初是依靠作者刻画的名侦探一个人的力量,用缜密的推理、分析,破获案件。江户川乱步指出:本格派的特点在于“运用推理逐次拨开疑云迷雾,去疑解惑,描写侦破犯罪案件的过程,并以情节引人入胜。”在作家蜂拥创作推理小说的年代,受众的期待视野也逐渐提高,对文学的陌生化要求更高,由此,案件的设置必定更加的繁复、技术含量更高,如此,单靠一个人推理整个案件的故事情节显然已经满足不了受众的审美需求。
我们知道,推理小说与公安小说、警匪小说等相近体裁的文学作品最大的不同在于推理小说注重民间力量的参与,公安小说、警匪小说等则主要是正面刻画公安干警形象。这种体裁特点以及推理小说发展的需求,促使众人参与推理模式的出现,即小说中每个人物形象从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认知角度出发自觉推理案件,从不同的角度互相印证、补充,最终将之归于一名人物形象,完成推理。在呼延云的笔下,法制日报记者、法医、侦探社、警察、推理家等几乎所有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都被他一同拉进了推理模式中,这些人物形象众多,但都血肉丰满、性格分明地处在案件的逻辑推理中。
因为提倡众人推理模式,所以呼延云在书中设置的密室往往是多重的,如果说“本格推理是先造一间密室,然后把人杀死在里面;新本格则是先把人杀死,然后在尸体的四周造一间密室”[1],那么呼延云的小说就是综合了这两者的特点,建构了双重密室,然后众人积极参与、互助推理,最终一层一层去掉密室,在《不可能幸存》中的眼泪湖畔旅店发生的凶杀案正是属于这种双重密室。
作为系列小说,呼延云在书中设置的主要人物是固定的,他深刻地意识到尽管这些人物都能够参与案件的推理,但是数量依然有限,于是在众人参与推理的模式中,他又设置了国内四大顶级推理咨询机构,来固化他所提倡的众人参与推理模式。这种固化,无形中又体现出一种江湖帮派的感觉,这一点在《黄帝的咒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呼延云能够建构起这种众人参与式的推理模式在于他独特的写作理念。他认为,“侦探小说需要变革,但这种变革不应该建立在血腥、恐怖的基础上,不能‘谜团一万,巧合八千’,而是要恪守侦探小说的基本原则,即用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设置谜面,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解开谜底,只有这样,读者才能在阅读中体验到‘智慧的乐趣’。”[2]正因如此,所以呼延云在每一部书设置的故事情节都非常的复杂离奇,也更便于众人参与推理模式的建构。
二、多重预设
推理小说离不开预设,预设是推理能够找到依托的基点。呼延云擅于使用多重预设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预设是为了保证其后情节的合理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不合理因素的出现。呼延云之所以能够成功使用多重预设,与他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运用有关。以《乌盆记》为例,其第一重预设即是以中国历史上最恐怖的罪案之一《乌盆记》为出发点,并将古今《乌盆记》放置在同一发生地点。为营造一种真实性的氛围,在楔子中,呼延云将历史上《乌盆记》的恐怖及其在以往历史中的社会反响做了研究并进行了详细地展现,为进一步营造这种真实恐怖的氛围,就连古今《乌盆记》罪案中的主要人物“赵大”的名字都一样。这个预设无形中就为接下来的故事营造了真实恐怖的气氛。当然,作者还是觉得不够,于是继续使用其他预设来加深受众对《乌盆记》故事真实性的认知。这种情节及气氛有案件制造者本身的原因,也有见证者或是来自正义一方的谎言,相较于案件制造者本身而言,来自见证者或是来自正义一方的谎言更易让人产生困惑,甚至凭空给故事本身制造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而这正是作者设置的第二重预设。曾为警察的马海伟最初告诉所有的人“当我从床底下拿出这个乌盆的一刻,我浑身的血都要凝固了,我相信我的梦是真的了!”[3]81这种谎言将所有的人拉进了乌盆记的恐怖氛围中,为整个推理过程作了一个虚假却是致命的预设,从而引导着所有人的思路脱离了正确的轨道。由于设置合理,所以这种脱离正确轨道的做法并没有给人突兀的感觉,因为作者抓住人们“三人成虎”的心理,会设置很多预设促使这种脱离成为“真实”。第三个预设是小卖部店主的话:“咱们这县里的传统,乌盆搁在床底下,找个人躺上去睡一夜,乌盆里的冤魂就钻到睡觉的那个人身上去了,就不会找害死它的人报仇了。”[3]92-93这个预设有第一个预设做铺垫,让人感觉不到任何的违和感。为让大家相信乌盆中含有冤魂的存在,呼延云做的第四个预设是看守花房的老头说的一席话:“这床可不能随便躺,床板分成好几种,全看上面浮着什么颜色:金黄色的最多,那叫柴床,谁睡都行;乳白色的叫奶床,身子骨虚的睡了容易落下病;青色的叫水床,夏天睡消暑解闷儿,冬天睡不得,睡了会冻坏五脏六腑;还有红色的叫囚床,火力足,肝火旺的人睡了容易打架出人命……还有就是黑色的,叫作疠床,不是刚刚有人死在上面,就是附近摆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睡上去容易鬼上身呢!”[3]96文化意蕴如此丰富的床知识由一个打工几十年的老头说出,由不得你不信。四重预设,层层推进,既同为预设又互为验证,顺利地将整个推理故事推向了高潮,也彻底把受众带进了惊悚、离奇的世界。
荀子在谈到人的欲望时指出:“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追求利益几乎就是人的本性,追逐方式不同,就主动会有罪案的产生。纵观所有侦探小说中描述的罪案,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大部分都是源于财、情,且其手段极其恶劣,超出了人类心理所能承受的能力。
三、依托传统文化
人类的任何行为都基于一定的动机,为达成一定的目的而形式各异。当这种行为的形式模式化、内容雷同化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这种行为收效甚微的时候。放置于推理小说亦是如此。悬疑小说的形式是设置谜题、以推理方式解谜、揭晓匪夷所思的谜底。这样的形式已经为受众所熟悉,如何在不能更改的形式下创新内容,是当代推理小说家应该注意的问题。呼延云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每部小说都选取一部或者一种传统文化作为基点构建内容。如《黄帝的咒语》选取的是《黄帝内经》《洗冤录》中的文化,还有来自扁鹊、张仲景等人的丰富医学知识;《镜殇》选取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有特色的镜子文化;《不可能幸存》选取的是八卦阴阳文化;《乌盆记》选取的是在中国轰动一时的罪案并被演绎成各种形式的《乌盆记》。如此种种,将历史和现实、文化和推理完美地结合,不经意间,创造了推理小说的经典。
随着人们获取信息方式的改变以及信息量的平面化,“艺术的接受不是被动的消费,而是在接受过程中显示赞同与拒绝、参与读者个人审美趣味和思想见解的审美活动。”[4]这种审美活动必然要求推理小说家要展现出来的不仅仅只是推理,还有其他诸多的知识。呼延云是一个医学知识、刑侦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都非常丰富的推理小说家,《黄帝的咒语》中为我们展现了大量的医学知识:“一个人死亡1小时后就会出现尸斑,如不及时检验就有可能和生前损伤形成的皮下出血混淆;4个小时后会出现四肢肌肉僵硬,如不及时保存将无法考证死者死亡时的体位和姿势,8小时后苍蝇产下的第一批虫卵开始孵化,如果不抓紧时间尸检,产生的蛆虫将无情地破坏尸体上的伤口。”[5]37如此精准的时间计算和分析,没有一点医学基础恐难做到。星象学知识是一种比较难懂的传统文化,呼延云在书中却是信手拈来:“在星象学中,最重要的是看两个星球的变化:一个是木星,木星又叫‘岁星’,11.86年行一周天,古人取约数12年,以其位置来纪年,视其进退左右以占妖祥;另一个是太阳,每朝每代的皇帝都是被吹嘘为‘授命于天’的天子,所以‘日蚀则帝危’”[5]50。如此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知识融合在推理知识中,实现了文化和推理的完美结合,既满足了受众对推理小说的期待视野,无形中又学到了大量的知识。
四、批判社会现实
任何题材的小说都必须基于一定的现实,完全脱离现实的小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任何的生命力。评论界之所以认为呼延云的系列推理小说“开拓出推理小说的全新时代”,在于他将本格派和社会派结合。在缜密的逻辑推理、张力恰到好处又不失水准的故事情节背后,是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感。《嬗变:杀戮者与推理者的顶级较量》中隐含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问题;《黄帝的咒语》中贩卖活人器官的贩子、地铁上如行尸走肉般的乘客;《乌盆记》中的黑窑厂、窑奴、富二代;《不可能幸存》中的老人保健品等等,无一不是这个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僵化的教育体制容不得学生做教科书之外的事情,对敢于描写社会阴暗面的学生,老师的评价是:“那只能说明,你的视线是偏激的、狭隘的!”[6]128毫不留情的驳斥,抽走了学生心中拥有的最后一根对教育充满渴望的稻草。所以他不在乎老师说什么,在他看来:“沉重的课业负担、僵化的教育体制,学生们早就被家长、老师以及整个社会,捆缚进了蚕室,一刀阉掉灵魂上的阳具,从此除了吃饭睡觉做功课,就是扑克台球游戏厅,即便偶尔感到两腿之间有点空虚,只要叼起烟卷,那些空虚就与烟雾一并缭绕到九霄云外去了。”[6]128这种揭露无疑给了当前的教育体制狠狠一击,然而推理小说家的这种击打能否真地触动当前的教育体制,却是不可而知。再看行尸走肉般的表情背后是深深的孤独、人性的冷漠。推理小说的本质就是去伪存真,而任何作品即便离开人这个具象也无法脱离人的思想,同样,推理小说自然会对人性进行剖析,在推理中将人性假的一面慢慢剥离,将其真实性的一面呈现。黑窑厂背后是对现实中黑窑厂的控诉;保健品是对中国混乱的保健品市场的谴责,这种混乱已经到了连媒体都无底线地协助的地步:“随便在街上买一份报纸,上面刊登的广告有多少是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虚假保健品!又有几篇曾经批评过它们的虚假宣传,揭发过它们的骗人伎俩?!”[7]276一个被标榜能治愈百病的五行阴阳镜,检测结果却是“为玻璃、灯泡、电线和水,接通电源后会产生光和热,大约可以理解成一个表面雕刻了八卦图的暖手宝……绝对不会对人体构成任何辐射性伤害。”[7]280对人体没有任何辐射,却对人体也没有任何功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这样被不良商家利用、糟蹋,而买单的却是销售终端的消费者。
精神危机、信任危机等已经成为当代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呼延云小说中揭示的这些问题从肉体、精神、社会等层面出发,从各个角度解剖着当代人的精神危机、信任危机。这种解剖,虽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至少是个警醒。
呼延云的小说中除揭露社会阴暗面之外,还有对底层人们的深切关注,《黄帝的咒语》中的黄静风、高大伦,《不可能幸存》中的张大山、陈少琳等有理想有抱负,却因种种原因而失败,最终走向绝望。张大山说:“老人们总爱说:黑夜过去就是白天。这里面有个盼头的意思,可是我知道我的命,我没白天的……。”[7]这种对自己命运的判决,不是到了山穷水尽、毫无希望的地步,是不会如此的。
美学家伊泽尔在谈到文本和读者的关系时,曾指出:“文本和读者的相会使文学作品真正进入存在,但这种相会决不可能被准确地定位,当它既不等于文本的实现,又不等于读者的个别意向时,它总会留下有待填补的空白部分。”[8]既然任何案件都有漏洞,都有别人推理解决的可能,那么解决这个案件的推理过程自然也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是作者留下的空白,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所以,尽管目前国内的推理小说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也是摆脱国外推理小说影响,构建本土特色推理小说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在推理小说家不停地探索中,中国的推理小说必将展现出更多的特色,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
[1]绫辻行人.十角馆杀人预告[M].黄晓燕,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27.
[2]白明.侦探小说的恪守与变革[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02-21(07).
[3]呼延云.乌盆记[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
[4]李绍庆.接受美学视角下的约瑟芬·铁伊推理小说[D].杭州:浙江大学,2011:5.
[5]呼延云.黄帝的咒语[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6]呼延云.嬗变:杀戮者与推理者的顶级较量[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128.
[7]呼延云.不可能幸存[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
[8]蒋孔阳,等.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309.
责任编辑 刘晓华
Research on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detective fiction——Take HuYan-yun's series of detective novels as an example
WANG Mei-yu,LI Juan
(1.Faculty of arts of Linyi University,Linyi 276012,Shandong,China;2.Dongyi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propaganda department,Dongying 257100,Shandong,China)
Foreign crime fictions have matured and various patterns, and in this background these patterns can’t meet what readers want. Chinese reasoning novelists have to create new inferential model. Chinese brand-new reasoning novelist Huyan-yun’s series can be regarded as a successful delegate. Focusing more on the culture, society and humanity, Huyan-yun’s series base 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stablish a new mode that contains participation, dependence, social reality and emotion. Readers can enjoy these new modes through reading detective fictions.
Mystery novels;Hu Yan-yun;Characteristics of creation
2016-02-25
王美雨(1978-),女,山东临沂人,临沂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汉语,中国文学。李 娟(1980-),女,山东临沂人,东营市委宣传部群众文化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文学,群众文化工作。
I207.42
A
1673-6133(2016)03-008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