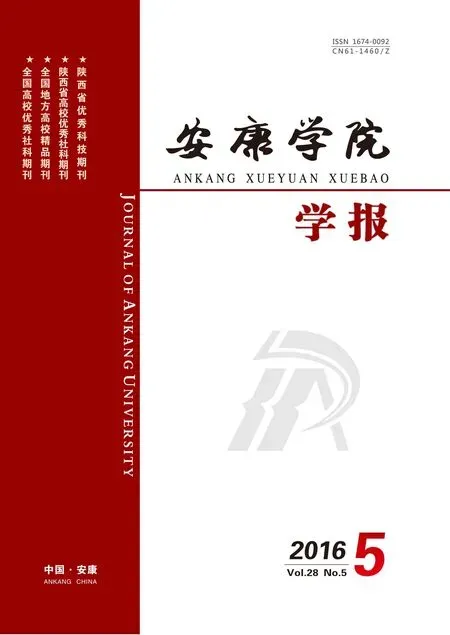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论安娜·卡列尼娜的幸福伦理
李霞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论安娜·卡列尼娜的幸福伦理
李霞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安娜·卡列尼娜》作为一部优秀的叙事伦理作品,叙述了主人公安娜由寻求幸福生活到自我毁灭的过程。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不可调和性最终导致了安娜的悲剧。叙事不仅体现在叙述故事的可能性,还注重探求某种伦理的可能性。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即是幸福,而幸福的终极目的就是伦理目的的乌托邦。然而,取消了伦理目的的乌托邦是不存在的,安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安娜在人性生成的过程中,由自我——本我——超我,完成了自我伦理上的救赎。
安娜·卡列尼娜;自我与他者;可能性;幸福伦理;自我救赎
王国维根据叔本华的观点,将悲剧分成三类:“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1]。安娜就属于第三种悲剧。伦理学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幸福”,即“每个人的生活动力”。无论是从托尔斯泰写作的动机出发,还是从叙事故事背后传达出的道德与伦理意义而言,都在说明托尔斯泰想通过安娜这一角色的设置表达他内心对道德与伦理的某种诉求。叙事是一种虚构的艺术,其虚构性在于探求人类生活的种种可能性。幸福与不幸福也只是对生活可能性的一种摹写。对一种生活可能性的摹写,往往也是一种人心秩序与观念的生成过程。詹姆逊曾经把叙事定义为“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也明确表示:“小说具备伦理意义。人类生活最终的伦理目的是乌托邦,亦即意义与生活不再分割,人与世界相一致的世界”[2]35。安娜对幸福寻求的过程,即是对内心乌托邦世界的构建过程,体现的也正是人心秩序的一个建构过程。然而,乌托邦不仅仅只是乌托邦,它还必须具备伦理意义,一旦取消了伦理,乌托邦也将无法存在。
一、个人幸福与他者幸福的关系
“现代小说的社会——历史——文化源动力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即个体从政治、伦理的客体演变成自主性的自我或主体”,也就是一种主体性的生成过程。安娜与沃伦斯基在他们欲望的驱使下,终于走向欲望的火炉。然而,他们所期许的幸福生活却只是一种取消伦理目的的乌托邦,这样的幸福生活在托尔斯泰看来是行不通的。每一部叙事作品,无论其背后传达出怎样的伦理意义,它始终有自己的立场。约翰·霍华德曾说过,观看一个事件的角度,就决定了事件本身的意义。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中,非常清晰地指明了他的伦理立场。这也即是我们所说的作者与隐含作者对叙事的一种干预,这种干预往往是通过作者、叙述者或隐含作者来进行传达的。关于这一点文中也有表现:
安娜垂着头,摸弄着头巾的穗子走进来。她红光满面,但这容光不是快乐的光彩,而是夜里可怕的大火。
托尔斯泰对安娜初次幸福的叙述,是担忧与恐惧的,对安娜出轨于沃伦斯基的“幸福生活的可能性”给以否定的态度。托尔斯泰认为,安娜与沃伦斯基的幸福生活根本不可能,一方面来自于宗教与世俗伦理的强大压力,另一则是安娜内心伦理与道德符号的隐形施压;所以,安娜面对着沃伦斯基的强烈追求,她是既幸福又恐惧的。她既贪恋于沃伦斯基的爱情,同时又用理性与道德伦理极力规束着自己。让她在歆享幸福生活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他者诸多因素的纠缠与折磨。安娜的幸福已不仅仅只是属于她个人的幸福,而是与周边的各种关系密切联系着。从叙事伦理学角度分析即是伦理学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伦理学有三个基本要素,即“价值中心”“价值判断”“其主张是如何处理人际互动关系问题”。伦理本指心态气质,也就是个人的内心秩序,发展到后来,伦理一词包含了伦理规则和心性。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关系调整在伦理中是至关重要的。关系调整当然包括自我调整(德行伦理),但最主要的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根据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理解与处理方式的不同,区分为伦理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主要调整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安娜自我的德行伦理。安娜同沃伦斯基之间的爱情,深深地与当时的社会伦理与道德纠缠联系;作为爱情幸福生活主体的安娜与沃伦斯基在面对双方各自欲望与幸福的实现上,又是他者与自我的关系;另则,作为叙事故事主体人物的安娜,在面对自己幸福生活的同时也面对卡列宁这个他者的干扰与阻碍。
(一)双方爱情幸福与他者的关系
这个欲望,对安娜来说原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怕的,因而也就格外使人销魂、神往……
“安娜!安娜!”他颤声地说,“安娜,看在上帝的份上!”
“上帝呀!饶恕我吧!”她呜咽着说,把他的手紧压在自己的胸口上。
……一想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付出羞愧难当的代价,她的心里不由得感到又可怕又可憎。
安娜与沃伦斯基的幸福,受到来自社会道德与宗教的种种干扰与阻碍。这让他们在幸福的同时,也饱受伦理与道德的规束与鞭打。社会这个隐形的他者,原是他们俩无论怎样逃避与取消,都无法回避的。安娜承受着比沃伦斯基更为沉重的伦理与道德的枷锁与压制。作为妻子,她出轨于沃伦斯基,虽然卡列宁从来没有给以她爱的滋养,但是这也不足以支撑她出轨的合法性;在世俗伦理方面,她同时还是一位母亲,这种抛家离子严重背离道德与伦理的个人利己主义行径,势必会将安娜推向社会伦理与道德的绞刑架上。作为幸福生活探求的另一方沃伦斯基,他也无法逃脱世俗伦理与社会道德秩序的约束与拷打。因此,开始幸福生活的两人,最初体会到的不是爱情的甜蜜与幸福,而是世俗伦理与道德在精神与肉体上对双方的双重折磨。这种欲望满足后的自我内心道德伦理制约,让他们无法安心歆享幸福生活的可能。面对社会这个强大隐形的他者,他们不但纠缠于其中,甚至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人面对着迎面而来的不同道德自治,不存在一种没有对手的强大社会力量,能够(或者希望能够)把在知识上基础牢固的普遍原理锻造成普遍行为的有效标准。相反,存在许多社会力量和社会标准,他们的存在把个体抛入了道德的不确定状态,在这种情形下,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出口。”[2]186-187然而,行为一旦开始,就无法否认他的不存在性,他们的爱情与幸福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的凄美,没有安全出口。甚至,他们自己一开始对道德与伦理抱着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正是这种不确定状态让他们一步步走向“他者”,即地狱的深渊。
在行文中,托尔斯泰并没有直接的情节叙述,主要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与人物自身内在本性的发展过程来展开叙事。欲望的萌发,欲望满足的恐惧与形神的双重受难,人性(本性)的自我复归亦即是自我德行伦理的调整,最后走向悲剧。用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理论即由“自我”——“本我”——“超我”,人性是不断生长的过程。叙事伦理本身就是对一种生活可能性的摹写,现实生活有多少可能性,那么叙事也就有多少种可能,叙事背后的伦理也就有多少种可能。正如马尔克斯曾说过的那样,人们并非在他们母亲分娩的那一天就此降生了,而生活迫使他们赋予了自己的生命。安娜的生活就是这样,是她自己所处的位置与关系,决定了她个体生命如此的生活窘境与悲剧性。但是,情感在强大的社会他者面前,只能就这样屈膝服从?其实,作为社会个体的人,是可以通过理性不断地去调和、协调,也即是两者通过协商与对话可以将两者的关系调整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理性就像人的本性一样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产物,它的合理与理想性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托尔斯泰正在通过安娜这一形象的塑造去探求一种叙事伦理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是绝望与悲剧的,但正是这个人物的绝望与悲剧性最终真正地传达出了叙事背后深刻的伦理旨趣。人类生活的最终目的就是寻找一种幸福的可能性,一种伦理目的的乌托邦,如果这种幸福的符号取消掉伦理目的,那么我们所谓的幸福也就随之崩塌。
卡列宁作为安娜与沃伦斯基幸福生活的他者,他也在有形无形中将爱情双方逼上了悲剧的绝路。卡列宁不但窒息了安娜的幸福,同时他始终以一个支配者的身份,控制着安娜,这包括他对安娜人生自主权的占有与支配。当安娜向卡列宁坦诚她对沃伦斯基的感情要求离婚时,卡列宁始终没有给安娜应有的婚姻自由权和人生自主权。如果说欲望是人身体的自然本能,那么权力是人的欲望的延伸,正如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所提出的,身体就是权力意志本身,“动物性是身体化的,也就是说,它是充溢着压倒性冲动的身体,身体这个词指的是在所有冲动、驱力和激情中的宰制结构中的显著整体,这些冲动、驱力和激情都具有生命意志,因为动物性的生存仅仅是身体化的,它就是权力意志”[3]。卡列宁对政治权力的热笃让他几乎癫狂,最基本的表现就是他对安娜精神上的折磨。卡列宁是一个典型的权力欲望膨胀者,任何阻碍他权力的因素,他均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清扫,甚至去摧毁。他把安娜的生命权力意志死死地攥在自己手中,一方面在身体与意志方面支配着安娜,另一方面又将安娜推向了世俗伦理与道德风口浪尖之处。安娜向他坦诚以后,他竟厚颜无耻地在给安娜的一封信封里装了一些没折叠的钞票,并写道:“我为你的回来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丝毫不在意安娜的痛苦与意志,完全是排他的利己主义者的形象。他在给安娜的信中写道:“您自己一定也能预见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怎样。我们的生活应当像过去一样继续下去吧!”卡列宁对安娜人身与自由的支配欲,一下子将安娜逼上了伦理与道德的风口处。安娜的处境反而更糟糕了,“她哭,因为她想把自己地位肯定下来的幻想从此破灭了”。这样,安娜与卡列宁这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调和与协商已无可能,因为安娜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她的精神虽是自由的,但这也使得她肉体与精神反而更受折磨。因为卡列宁处在两人关系的支配地位、主动位置,安娜幸福生活的可能性也就在此时一步步走向破灭。在福柯那里,话语处在权力的控制之中,并成为权力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形式,即如他所言:“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4]。卡列宁在话语权方面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他的一切权力的实施正是通过他对安娜在话语上的强暴与控制来进行的,卡列宁面对妻子的出轨,不但没有予以指责与行动,反而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在话语上抢占了优先地位。他正是通过话语将安娜的权力与自由紧紧地攥在自己手中,继而通过这些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与发挥功能,达到他在权力上对安娜的控制与支配。同时,福柯也指出:“权力不应该被看作是所有权,而应该被称为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动作”[5]28。其实,在这里我们也看出了一贯热枕于政治与权力的卡列宁对权力与政治的一种通达与熟练。他首先在话语上抢占先机,让犯了罪的妻子不但在话语与权力上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同时也正是通过这种话语与权力的策略,让妻子在内心与精神上饱受伦理与道德的规训与惩罚。在世俗社会伦理道德层面,他抢占了先机;同时他使犯罪者(安娜)在自己内在德行伦理的规训与惩罚下处于更为劣势的地位。抢占话语,只是他对安娜实施人身与权力控制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犯罪者处在了社会道德与世俗伦理的绞刑架上,被遮蔽的状态被慢慢地解了开来,使她不得不面临着自己内心伦理德行的时时规训与惩罚。这样,卡列宁实现了自己对安娜在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控制与惩罚。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努力,并不期望于挽救自己的家庭,而是保证妻子的“纯良”不撼动自己一生致力于的权力与地位的稳固。其次,卡列宁又是一个严苛的基督教徒,他对妻子“纯良”的看法应该比世俗道德与伦理更为注重,但是为了稳固他已建立起的权力地位,他依然将自己的宗教置于权力之下。
在福柯的理论中,身体与权力的关系占据核心地位:今天社会的惩罚,最终涉及的总是身体,即身体极其力量,他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在他看来,“历史摧毁身体”“身体处在被动处境”,这样的身体是被奴役、被控制和被蹂躏的身体,备受社会的惩罚与规训,这样的身体与权力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关系[5]27。同时,福柯一再强调权力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种关系,是各种势力关系的复合体,是这些势力关系通过持续不断地相互抗争改变、增强或颠覆它们的过程[6]。安娜与卡列宁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个人伦理幸福与他者的关系,卡列宁一系列的话语与行动的实施无非就是在这场安娜“自我”与“他者”卡列宁之间的一场关系视域下的权力的角逐。善良并情感至上的安娜又怎么能够在这场“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权力角逐中获胜呢?所以,等待她与沃伦斯基的注定是一场悲剧。因为,无论是在社会伦理与道德的“他者”场域中,还是在面对丈夫卡列宁这一个体“他者”的场域中,安娜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处于被支配、被奴役与被惩罚的地位。当属于她的权力被置于“他者”视域之下时,安娜的处境正如福柯所言,“身体处在被动处境”,这样的身体是被奴役、被控制和被蹂躏的身体,备受社会的惩罚与规训,这样的身体与权力也就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关系。安娜正在一步步走向伦理与道德的绞刑架,这伦理与道德一方面来自于“他者”,另一方面更来自于她的内心,亦即一种灵活的、不受拘束的“良心的声音”。
(二)双方互为的“自我”(安娜)与“他者”(沃伦斯基)关系
在双方互相构成的爱情场域中,沃伦斯基与安娜的爱情与幸福与社会以及卡列宁构成了一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同时作为个体幸福与欲望的主体,双方又互为“自我”与“他者”。这里的“自我”以安娜为主体,安娜是“自我”与“他者”关系中一组比较重要的个人与他者的关系。沃伦斯基在欲望上唤醒了安娜,两者在个体幸福与他者幸福关系的维度上,始终保持着“他者”伦理学中的温和型致思路线,即“自我”安娜与“他者”沃伦斯基是一种异质性存在,但相互关怀和对话。但是,“他者”在整个人类传统意识中,一直作为边缘的代名词。它表明,由于自我主体性地位的绝对强势,他者总是同一化的对象,它存在,但并不具备存在的意义。用西方的思维结构就是一组二元化论,二元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二元论暗含着等级制,也就是说其中的一项总是支配着另一项。安娜的悲剧固然主要来自于社会与卡列宁这一组他者关系在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施压与惩罚,实则真正将安娜直接推向绞刑架上的却是沃伦斯基这一“他者”。并不是沃伦斯基本身对安娜的权力意志有多大的控制与支配力,而是他是压死安娜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德勒兹曾经这样说过:“界定身体的正是这种支配与被支配之间的关系,每种力的关系都构成一个身体——无论是化学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7]被卡列宁窒息着生命气息的安娜由于沃伦斯基的出现,从而恢复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在与沃伦斯基的这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安娜是被动的。她特殊的社会地位与尴尬的身份处境,在本质上已经使她部分上丧失了拥有爱情与幸福的自主权。作为出轨的妻子,她在爱情与幸福方面与沃伦斯基又绝对的对立,直接决定了她处于两者关系的劣势地位。因此,在个人与他者的场域中,安娜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她的身体与意志在环境与语境中处处受制于作为他者的沃伦斯基。尼采曾说:“身体这个词指的是所有的冲动、驱力与激情都具有生命意志。”[8]安娜无论是身体还是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沃伦斯基,处于两者关系的劣势地位。安娜对沃伦斯基的求爱,既惧怕又自觉幸福。她对沃伦斯基的惧怕来自于内心自我德行伦理的规训与惩戒,另一则是对他者的不信任性。正如丹麦神学家、道德家与哲学家诺德·E·朗斯特里普断言的:“人类生活的一特征就是我们彼此信任……只是因为一些特殊的环境我们不再预先信任一陌生人……起初我们相信彼此的话,起初我们彼此信任。”[2]183安娜对沃伦斯基的情感与信任就是这样。她由惧怕爱情到接受爱情,甚至为自己的不道德做辩护。
安娜对沃伦斯基开始是抵抗与克制的,她内心的自我德行伦理在此时还处于优势地位,并没有被欲望冲昏头脑。但是随着沃伦斯基不断地狂热追求,她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个有生气需要爱情的女人,“我是一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既然把我造出来了,我就需要爱情,需要生活”[9]。这个时候的安娜在心理和精神上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最后选择了用“爱”来代替“意志”,这也正是托尔斯泰在叙事中强调的一点。安娜已经从自我伦理德行的窠臼中解放出来,欲望在她的生命里彰显了主导地位。但是,她的内心却始终无法逃脱伦理与世俗道德的规训与惩罚。后来,她几乎每天都要借助药物才能安然入睡,但即便如此,她的睡眠质量也是十分有限的。她开始猜疑,甚至人每天也变得恍惚。此时的沃伦斯基和安娜都由于目前的艰难处境在彼此抱怨对方,安娜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这种压力让她对沃伦斯基的爱情充满猜疑,这种猜疑让他们两者更无法对话。但是,沃伦斯基作为安娜最后唯一可以依靠的行动者,他对安娜的爱与要求,反而比处在精神崩溃边缘的安娜更多。其实,沃伦斯基对安娜的关怀与理解愈来愈少,他甚至把她当作将自己陷入如此不堪处境的罪人,在心理与精神上,他并没有给安娜一个和自己一样平等的地位,而是把安娜看成是自己不幸因素的根源,束缚他幸福与自由的包袱。他对她已经不再捧在手心,而是当作可以供他把玩与发泄的情感工具。这个时候,两者就充满了对立,以至于后来两人闹到公开性的感情冷淡。安娜自杀前的最后一句话“那里,倒在正中心,我要惩罚他……”[10]705说明此时的安娜已经完全走向人性的复归之路。她已经由“本我”向“超我”迈进。同时,也向沃伦斯基喊出了自己作为“自我”与“他者”幸福的不可调和性。而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性,并不是一开始就激化与对立的,而是随着人物情感与处境、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升级变化的。
二、自我伦理的救赎
“人性同理性一样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从安娜自我德行伦理本身角度讲,安娜是一个自我本性不断生成的过程。”[11]用弗洛伊德的三重性格理论分析,就是一个由“自我”——“本我”——“超我”的发展过程。作为故事主体的安娜,正是通过自我主体性不断生成的过程,从而完成自我人性的一种锻造。人性的生成总是有代价的,安娜的悲剧意识不仅在于她自身的一种人性锻造过程,而且更多的也是上面所论述的社会与他者关系处理不当的一种悲剧。安娜的悲剧正是由于她自己本身的位置与关系使然。安娜的悲剧如果是从她遇见沃伦斯基开始,那么就注定是一场伦理与反抗者的角逐。然而,关于叙事作品的立场,在叙事的开篇,托尔斯泰就引用了《圣经》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原意是:人间的罪孽只有上帝可以裁判,世人是无权评论的。关于这个题词,托尔斯泰曾回答魏烈萨耶夫说:“我选用这个题词,正如我解释过的,只不过是为了表达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人们所做的坏事有其痛苦的后果,这不来自于人,而来自于上帝;安娜·卡列尼娜就亲身体验了这一点”[10]3。因此,安娜的悲剧意识除了上面论述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冲突与对立之外,更多还是安娜自我内在德行伦理的规训与惩罚。安娜作为主体不断地生成,亦即不断地在人性与非人性的两向维度上徘徊与挣扎,直到最后面临欲望满足后的空虚感与罪恶感,她选择摆脱。这不仅仅是一场叙事伦理可能性的摹写过程,还是自我伦理的救赎过程。托尔斯泰一再强调,安娜作为故事主体对自我伦理德行的一种内在规训与惩罚,他特别强调这样的一句话:“是的,我很烦恼,但天赋理智就是为了摆脱烦恼;因此,一定要摆脱烦恼。既然再没有什么可看,既然什么都叫人讨厌,为什么不把那蜡烛灭掉呢?可是怎么灭掉呢?”
受到他者与自我内在德行伦理的双重惩罚与折磨,安娜已经向解脱迈去。这个解脱就意味着真正的摆脱,没有任何他者,那就是死亡。安娜用死亡去结束自己已无法背负的沉重肉身与伦理枷锁。这是一个人的自由与伦理幸福与现实生活无法调和的主体毁灭过程。叙事伦理不仅仅在叙事故事的可能性,实则也是在探求某种伦理的可能性。作为虚构故事世界的伦理乌托邦,伦理目的才是乌托邦寄身的最终归宿。安娜或许到死都没有悟出,但托尔斯泰却通过安娜这一角色的设置把这种伦理目的乌托邦给真实地传达了出来。在死亡来临的瞬间,安娜把自己推向了赎罪的界域。
面向死亡前,“她画了十字”“仿佛立刻想起什么,但又扑通一声跪下了。甚至连她自己都为自己的这一行动大吃一惊”,直到死她嘴边依然念叨的是:“上帝呀,饶恕我吧!”安娜主体意识的觉醒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确。安娜自我德行伦理的内在惩罚,让她的生活与内心充满负罪感,因此她最后死的姿势就是一个宗教教徒在向上帝请求宽恕的姿态,这就是叙事伦理学中的自我伦理的救赎。犯罪与宗教的内在规训与惩罚让安娜时时为活着的每一秒都充满负罪感,生活对她而言已生无可恋,唯有摆脱。摆脱别人,也摆脱自己,才能让她那饱受伦理与道德惩罚的肉身与精神彻底摆脱烦恼。这是安娜作为一个主体性的人,对自我人性的一种认知过程,一种在行动上的生成过程。虽然,最后的代价是死亡,但惟有死亡才真正地从“生”的意义上赋予安娜深刻的道德与伦理两个维度上的价值意义。此时的安娜已经由弗洛伊德的“本我”走向了“超我”,在伦理与道德的维度上永远地把生存的意义真实而深刻地传达了出来。
欲望固然是人类生存的内在动力,但人类一旦为欲望左右,终究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真正的幸福。人类一直努力追求的终极目的即是幸福,而幸福的终极目的就是伦理目的的乌托邦世界,取消了伦理目的的乌托邦是不可能存在的。安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有句古话:“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在自我人性生长的过程中,欲望的膨胀与过度追求肯定会让人性在世俗的窠臼中走向迷途。但是,如果伦理的意义只在于说教或是对对抗者的绞杀,那么伦理又怎能为人类的终极幸福寻找一方真正的乌托邦世界?叙事伦理之所以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就是因为伦理一方对人类的德行与伦理进行着集体契约式的规训与惩罚,同时它也能够作为一种“善”与“道德伦理秩序”的标尺引导迷失者复归人性的自我。这就是伦理叙事的社会效应之一——自我伦理的救赎。人性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自我——本我——超我,正是世俗伦理与道德的参与才让人不断向善靠近。
“要是善有原因,它就不是善;要是善有结果——奖赏。那也不是善。因此,善是超越因果关系的。”[10]732那么,作为社会伦理与道德标尺的德行伦理取消掉因果关系,社会整体的德行与伦理秩序又将走向何方?叙事伦理一直在强调伦理的可能性与实际的践行度,但是转向现代语境下的伦理与德行是否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伦理德行标尺?如果存在这样的标尺,我们人类最终追求的伦理目的的乌托邦是否有个标准可以衡量?尤其是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个体性极度膨胀,德行伦理面临着被欲望与异化所取消的处境。当然,我们可以对触犯社会公约与伦理者予以惩罚,但在谴责与同情的两向维度之间我们自身的德行伦理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诚然,善与恶是德行与伦理的两个极端,但是人们普遍习惯于善与恶的中间状态,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一个怎样的伦理世界?现代伦理与道德秩序又将走向何方?若是整个社会的伦理与道德秩序陷入了“善”与“恶”的模棱两可状态,伦理救赎——人性的生成过程将永远只是过去式或虚拟式。
[1]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1182.
[2]伍茂国.从叙事走向伦理——叙事伦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3]齐格蒙特·鲍曼,蒂姆·梅.社会学之思[M].李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03.
[4]米歇尔·福柯.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M].罗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28.
[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6]刘伟.反抗“父亲”——空间、身体话语权力视域下的周氏兄弟失和[J].鲁迅研究月刊,2014(9):16-27.
[7]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M].周颖,刘玉宇,译.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1:59.
[8]尼采.苏鲁支语录[M].徐梵澄,译.北京:商务图书馆,1997:218.
[9]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杨楠,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8.
[10]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草婴,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11]耿占春.自我的变形记[J].大家,2015(1):52-54.
【责任编校朱云】
On the Happinesse Ethics of Anna karenina w ith the Theor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the O ther
LI Xia
(College of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475000,Henan,China)
As an excellent works of narrative ethics,“Anna Karenina”which describes the heroine——Anna who sought for the happiness and made herself destroyed finally.Personal and relationship of irreconcilable eventually led to the tragedy of Anna.Not only does the narrative story describe the possibility of narrative ethics,but also the narrative stor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possibility of ethics.However,cancelling the ethical purpose of utopia doesn’t exist.Anna is a typical examp le.Human nature is a process of constantly generating,so does Anna.She by ego—id—superego to comp leted herself redemption ofethics.
Anna karenina;selfand theother;possibility;ethicsofhappiness;self-salvation
I106.4
A
1674-0092(2016)05-0064-06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5.014
2016-03-19
李霞,女,河南驻马店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文论、文学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