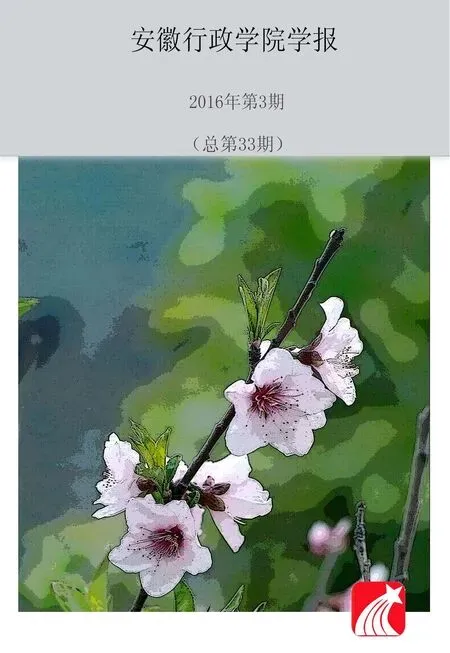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
——来自“保护规范理论”的启示
丁雯雯(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300071)
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
——来自“保护规范理论”的启示
丁雯雯
(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300071)
2014年新《行政诉讼法》首次引入“利害关系”的概念,将其从之前的“司法解释”上升到了法律层面,明确规定原告不仅包括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还包括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但是如何判断起诉人是否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现实中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这就为实践操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与混乱。域外的“保护规范理论”在解决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问题上可以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在分析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现状的基础上,结合“保护规范理论”,旨在为我国行政诉讼的实践与发展作有益的尝试。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利害关系;保护规范理论
一、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现状
(一)现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
2015年5月1日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我国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主要是以“利害关系”为标准。此前,在2000年的司法解释颁布之后,学界以及实务界在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方面,也主要是以“利害关系”为标准,那如何理解“利害关系”的内涵呢?结合2000年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我们可以将“利害关系”理解为行政行为是否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的影响,如果能够产生实际的影响,则具有利害关系,如果不产生实际影响,则不具有利害关系,也就是说行政行为与权利义务的减损是否有因果关系。在实践中,大多数法院也是据此来确定起诉人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和案件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
例如,在“魏永高、陈守志诉来安县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案”①中,安徽省高院认为:“本案中,来安县人民政府作出批复后,来安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没有制作并送达对外发生效力的法律文书,即直接交来安县土地储备中心根据该批复实施拆迁补偿安置行为,对原土地使用权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在“陈秀玲诉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行政强制案”②中,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解除对第三人事故车辆的强制措施,并未损害起诉人的合法权益,对起诉人的权利和义务并未产生实际影响,因此起诉人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在“徐信邦不服萧县房地产管理局行政撤销案”③中,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萧县房地产管理局作出的萧房字〔2002〕12号文件没有侵犯原告徐信邦的合法权益,原告徐信邦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
在这几个案例中,法院都是从行政行为是否对起诉人的权利义务或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来认定“利害关系”,从而确定起诉人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新《行政诉讼法》中增加了“利害关系”的规定,与行政相对人进行了区分,并在司法解释中删除了之前“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规定,但是在实质上与之前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标准没有太大的区别,就目前来看,以行政行为是否对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来判断其是否具有原告资格,仍是大多数法院的惯常做法,同时也为多数学者所支持。
虽然“利害关系”标准已经为学界及实务界所认可,但是如何认定“利害关系”,如何判断权利义务是否受到了行政行为的实际影响,学者们存在不同的看法。尽管如此,在这些学者的观点中也存在共同之处,就是“合法权益”要素和“因果关系”要素。即在认定是否具有“利害关系”时,首先要判断是否存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可能受到侵害的事实,其次判断合法权益受到的这种不利影响是否与行政行为有因果关系。故“合法权益”和“因果关系”是目前公认的“利害关系”认定标准的要素。
(二)目前原告资格认定存在的问题
1.“合法权益”与“因果关系”难以把握
从上文中,我们知道要判断是否具有“利害关系”,根据目前通用的做法,必须要对“合法权益”和“因果关系”这两个要素进行判断。而“合法权益”与“因果关系”这两个概念同样具有不确定性,什么属于合法权益,合法权益的外延是什么,如何判断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了行政行为实际的影响,“实际影响”的范围和深度是什么,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什么程度的联系才构成因果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具有不确定性,而且法学中的因果关系,不仅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作为法律问题,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1],所以在实际操作时,类似的案件可能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处理结果,这样极不利于我国法治的统一。
2.无法将反射利益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
反射利益是指法律基于保护公共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目的,要求行政机关作为或不作为,个人因此在事实上所享受到的利益。他所享受的这种利益实际上只是一种事实上的期待与机会,所以,法律未赋予他有对行政机关这种作为或者不作为在公法上的请求权[2]。例如,甲因居住于小学附近而有就近上学的便利,政府决定小学迁址使得丧失了这种便利,据此不能提起诉讼;失业人员获得的低保惠及他所赡养的或抚养的人,这种“惠及利益”仅属于反射利益。
根据通说,当事人是不能以反射利益受到侵害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但是根据目前的判断“利害关系”的标准,只要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可能受到侵害,并且这种侵害与行政行为有因果关系,当事人就具有原告资格,可以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反射利益也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当事人的反射利益受到侵害往往是由于行政行为,那么根据当前的标准,当反射利益受到侵害时,当事人也能够到法院起诉,与通说不符。
二、“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如果仅用当前的“利害关系”标准来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话,在实践操作中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决定“利害关系”的“合法权益”要素和“因果关系”要素都不是一个含义确定的概念,所以为了解决我国目前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所面临的困境,有必要借鉴域外经验,引入“保护规范理论”。
(一)保护规范理论概述
公权利是指人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基于公法(行政法)的规定,享有的请求国家作为、不作为或容忍的权利。公权利的实践意义在于司法救济。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任何一个主观权利遭受公权力侵害的公民都可以诉诸法律途径(司法途径)。也只有在这时,公民才可以向法院起诉,主张其“主观权利”受到侵害[3]。也就是说,起诉人只有具有公法上的权利,才能提起行政诉讼,即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这就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转换为公法上权利的判断。
反射利益是指法律基于保护公共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目的,要求行政机关作为或不作为,个人因此在事实上所享受到的利益。
行政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因此有时人民可能会因公法上的规定,会因公法上任务的执行而获得利益与好处,但是这种“利益均沾”的反射利益并不等同于公权利,因为公权利是立法者专门为特定范围内的人民所设定的法律上的利益,而为特定范围内的人民所独有。那么如何判断行政法上规定的权益是否为特定范围内的人民所独有,换言之,即人民在何种情况下才具有公权利(原告资格),进而提起行政诉讼呢?
在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主流的学说就是“保护规范理论”,又称“保护目的理论”、“公权理论”等。德国学者毛雷尔认为:“主观公权利理论即以此为根据,认为:如果有效的法律规定(行政的法律义务即由此而来)不仅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且——至少也——是为了公民个人的利益,就应当肯定主观权利”[3];杨建顺在其所著的《日本行政法通论》中提到,“传统学说认为,当法律为私人特别规定保护其一定利益时,该利益称为‘法律保护的利益',该利益由于行政权的违法作为或不作为遭受损害时,当事人享有排除行政违法行为的权利(法律上的利益),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排除违法行为(违法排除请求权),或者要求合法地行使行政权(行政介人请求权)”[4];陈敏在其所著的《行政法总论》中说:“在学说上发展出所谓的‘保护规范理论',经由法律之解释,探求其保护目的,从而界定一项利益之为反射利益或权利”[5]。李建良认为:“如何判定何种利益为特定范围人民所独享而为法律所保护,学说见解不一。目前较多学者主张,且已成为主流见解的是‘保护规范理论'”[6]。
那么究竟什么是保护规范理论呢?保护规范理论是指,公法权利的确认,应从探求相关法律的规范意旨着手,若该法规的规范目的,除保护公共利益之外,同时兼及保护个人的利益,则受保护的个人即因该法规而享有公法上的权利[6]。依“保护规范理论”,对公权力主体课以义务的行政法规,经由解释,其目的如在于,或至少同时在于承认及保护特定个人的利益,使其得为自己而予以实现时,即存在人民的公权利;反之,行政法规如仅为一般或特别的公共利益,设定公行政特定行为义务,人民虽因而获有利益,此一利益并非法律的目的所在,或仅偶然发生者,则为反射利益,而非公权利[5]。
(二)保护规范理论基本判别步骤
根据“保护规范理论”,主观公权利的成立主要涉及如下两个问题[3]:
(l)是否存在规定行政机关应当采取特定行为(行政的法律义务)的法律规定?
(2)该法律规定是否——至少也——以保护个人利益为目的(个人利益)?
所以在根据保护规范理论进行个案认定时,笔者认为可依照以下三个步骤进行:
(1)首先找出行政争议所涉及的法律规范,即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时的法律依据;
(2)判断系争的法律规范是否属于“保护规范”,也就是说该法规的规范目的,除了保护公共利益以外,是否还兼及保护特定范围或可得特定范围内的个人的利益;
(3)判断提起诉讼的当事人是否属于系争法规所保护的对象范围。
如果系争的法规属于“保护规范”,并且系争的当事人属于系争法规所保护的对象,那么提起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即具有原告资格。
(三)“保护规范”的认定
从上文,我们可知在运用“保护规范理论”判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时,具体可分为三个步骤,其中第一步“找出系争的法律规范”和第三步“判断起诉人是否属于系争法规的保护对象”相对容易,其核心就在于第二步“探求法规的规范目的”,而探求目的的关键是对系争法规范的解释,所以法院在根据“保护规范理论”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时,既要特别注意对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还要考虑整个法律制度设立的目的以及对各方利益进行权衡与考量。日本2004年修改的《行政事件诉讼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规定,即“法院在就处分或者裁决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进行判断时,不能只是根据该处分或者裁决所依据的法令规定的文本,还应当考虑该法令的宗旨和目的以及(行政机关)在该处分中应当考虑的利益的内容和性质。在考虑该法令的宗旨和目的时,与该法令有着共通目的的相关法令存在的,还应当斟酌相关法令的宗旨和目的;在考虑该利益的内容和性质时,还应斟酌该处分或者裁决违反其所依据的法令时所蒙受侵害的利益的内容和性质以及侵害的形态和程度。”
笔者认为,我国在“如何解释法规以探求规范目的”的问题上,可以参考借鉴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的规定。即在“探求法规范的目的”时,首先要对系争的法规范进行解释。在解释时,不应仅限于立法原意,也就是说不应只探求立法者的目的,以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的目的为准,而应该还包括对客观意旨的探求,从当下社会环境与制度出发,综合各种立法因素。这就要求法官综合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综合考虑整个法律的立法目的、适用对象、公共政策以及一般价值观念,以确定法规范的保护目的;其次,法院还需要考量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涉及相对人比较重要的权利并可以做多种解释时,可以采纳对相对人权益有利的解释。
(四)保护规范理论的启示
基于保护规范理论,在判断人民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时,关键是探求系争法规的规范目的,这种思路抛弃了之前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而将其转化为对行政争议涉及法的规范目的的解释,笔者认为,通过探求法规的规范目的来确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这种方式,相较之前认定合法权益与行政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具有可操作性,能够更好的保护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具体而言:
1.“保护规范理论”与新《行政诉讼法》的“立案登记制”相契合
为了解决“立案难”的问题,新《行政诉讼法》改之前的“审查登记制”为“立案登记制”,施行宽松立案,对起诉条件进行形式审查,就算有实质审查也是很浅程度的审查。在根据“保护规范理论”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时,只是探求系争法律规范的目的以及判断起诉人是否属于规范的保护对象,这并不涉及对案情情况的实质审查,只是在形式上进行审查,不仅与新《行政诉讼法》确立的“立案登记制”的立法精神相契合,而且能够更加充分地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同时可以缓解目前行政诉讼“立案难”的现状。
2.法规的规范目的更易于把握
保护规范理论的运用主要是对系争法规的目的进行解释,而对行政争议涉及的法律规范进行解释刚好符合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职能的发挥,与认定利害关系中的因果关系相比,法院更擅长对法律规范进行解释,因为法院本身的职能就是适用法律与解决争议,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免不了要对法律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4条规定:“在裁判案件中解释法律规范,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门”,因此对法规的规范目的进行解释,可以减少法院在认定原告资格时的任意性,从而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保护规范理论”能够更好的保障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
正如上文所述,决定是否具有利害关系的“合法权益”和“因果关系”要素均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在范围和程度上很难能够对“利害关系”进行全面的把握,而与之相比,系争法规的规范目的更易于把握,从而可以减少在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时的不确定性和任意性,全面保护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
与目前通说“利害关系说”相比,“保护规范理论”在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时更具有优越性,能够更好的保障起诉人尤其是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笔者认为,在实务界,法院应该在运用“利害关系说”的基础上,结合“保护规范理论”综合判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做到全面、公正的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三、结语
“保护规范理论”将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审查的重心由“判断利害关系”转为“探求法规的规范目的”,不仅可以缓解目前利害关系标准模糊、难以把握的现状,而且与新《行政诉讼法》中确立的“立案登记制”的精神相契合,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尤其是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符合《行政诉讼法》“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目的。笔者认为,“保护规范理论”在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问题上可以为我国提供很好的借鉴,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实务中,都可以在“利害关系说”的基础上结合“保护规范理论”,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进行相对全面的把握。
注释
①具体参见指导性案例22号,http://www.chinacourt.org/ article/detail/2013/11/id/1150468.shtml。
②http://www.pkulaw.cn/case/pfnl_1970324839988899.html?keywords=%E9%99%88%E7%A7%80%E7%8E% B2&match=Exact,载于北大法宝。
③http://www.pkulaw.cn/case/pfnl_1970324837330215.html?keywords=%E5%BE%90%E4%BF%A1%E9%82% A6&match=Exact,载于北大法宝。
[1]范志勇.立案登记制下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J].法学杂志,2015(8):124-131.
[2]章剑生.现代行政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29.
[3]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53-155.
[4]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199.
[5]陈敏.行政法总论[M].香港:神州图书出版公司,2003:256.
[6]李建良.行政法基本十讲[M].台北:元照出版社,2011:198.
[责任编辑:张兵]
Identifying the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From Enlightenment of the“Protection Norm Theory”
DING Wen-wen
(School of Law,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The new"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was promulgated in 2014.It firs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interest" and expressly provides that the plaintiffs include not only the person opposing administrative acts,but also other citizens,legal person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with an interest in administrative actions.But in reality,there is no established standar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rosecutor has an interest with administrative acts,so this brings some difficulties and confusion for the practical operation.The"Protection Norm Theory"from abroad can provide useful lessons for China about identifying the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about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plaintiff qualification,and combined with"Protection Norm Theory",it i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plaintiff qualification;interest;Protection Norm Theory
D925.3
A
1674-8638(2016)03-0089-05
10.13454/j.issn.1674-8638.2016.03.017
2016-02-27
丁雯雯(1993-),女,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学,行政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