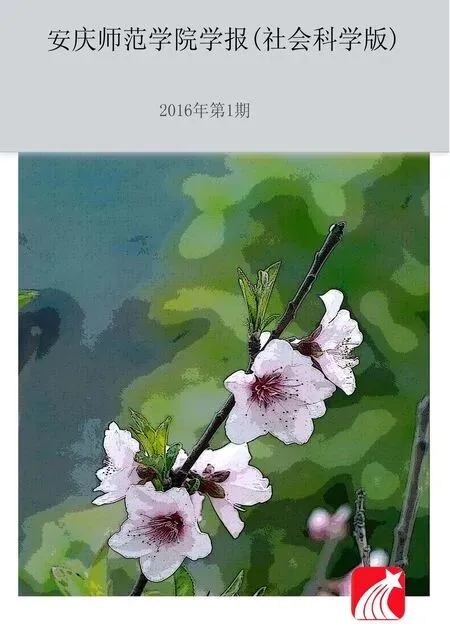快感·颓废·逸乐
——柏桦诗歌的身体美学初探
李 商 雨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快感·颓废·逸乐
——柏桦诗歌的身体美学初探
李 商 雨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安徽芜湖241002)
摘要:诗人柏桦的写作从80年代初开始,即已显示出身体性的美学特征。他诗歌中的身体性,是基于尼采的身体哲学和透视主义方法,也是他诗歌美学的出发点和所有秘密。柏桦诗歌的身体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快感、颓废和逸乐,三者的结合,构成了柏桦写作的美学风景和当代汉语诗歌中独特的后现代景观。
关键词:身体;透视主义;快感;颓废;逸乐
身体是个大的美学和哲学问题,长期以来,还没有人从身体的角度来认识和探讨柏桦的诗歌。事实,身体性是柏桦写作的起点,正如“尼采的口号是,一切从身体出发”[1],柏桦的写作正是从身体出发上路的;同时,也意味着身体是他写作的生成性源头,也即身体是他的落脚点,因身体性而生成其文本色情学。这从他的成名作《表达》一诗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另外,从其自传性的《左边》一书中,也可以证实这个看法。《左边》第一卷《忆少年》,从“蛋糕”开始,柏桦强调了“三块蛋糕的意义”,“那个下午是决定我前途的下午,也是注定了我要歌唱的下午”[2],请注意,由于此处时间性词汇“下午”的引导,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多注意到“下午”在柏桦诗歌中的价值,却忽视了另一个因素——身体的痛苦——在他诗歌中的重要性。
在其早期的诗歌中,痛苦,是一个关键词,只要留心一下,便会发现他的诗歌中的身体性因素。比较明显的如《冬日的男孩》、《美人》、《琼斯敦》、《恨》,这些诗,人们讨论的时候,往往着意于它的白热化的速度、下午的美学,但很少强调痛苦、神经质的另一面。即便在相对较为轻逸的诗,如《夏天还很远》中,身体之痛也成为一种生成性因素。“左手也疲倦/暗地里一直往左边/偏僻又深入”三句,源于柏桦的左臂一种类似神经痛的存在,这种痛的来源不明,时隐时现;2011年,柏桦曾说,他胳膊的痛从80年代就开始了,他也是因此将这种痛写入《夏天还很远》一诗,这种痛,是这首诗的发动机。在很多读者看来,这几行写身体感觉的诗的确很难解释。我们这里研究的着眼点在于“身体性”,淡化其早期诗歌中的痛苦,主要分析柏桦诗歌中的快感、颓废和逸乐;“快感·颓废·逸乐”,是柏桦身体美学的具体形态,也是柏桦文本色情学得以生成的基础。
一、快感
本文无意就“主体-身体”问题作无谓的论战式的讨论,而是基于柏桦的文本自身,作出一个解释。正如尼采说的:“解释,而非认识。”[3]109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柏桦的文本生产。用尼采的另一句话说得更清楚一些:“解释,而非说明。没有什么事实,一切都是流动的、不可把握的、退缩性的;最持久的东西还是我们的意见。”[3]119柏桦是个事实上的尼采主义者,而尼采的出发点是身体,身体是其准绳,他的价值是快乐和不快乐,他的解释方法是透视。众所周知,尼采反对柏拉图以来,尤其是笛卡尔以来的知识和理性,瓦解了主体性,从古代希腊的酒神秘仪中,找回了身体。他认为,人的天性中有一种极为强烈的冲动,这种冲动的本质在于“个体化原理崩溃之时从人的最内在基础即天性中升起的充满幸福的狂喜。”[4]尼采将这种“狂喜”谓之“醉”;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研究的“狂欢”,罗兰·巴特在《文之悦》中所谓的“Jouissance”,应该属于同一范畴。尼采曾说,在这种“醉”中,“(个体化原理)被彻底打破,面对汹涌而至的普遍人性和普遍自然性的巨大力量,主体性完全消失。”[5]在此意义上,身体也成为快感的身体。当身体遭受惩罚,快感被压抑,也便有了痛苦。因此,可以将柏桦早期诗歌理解为身体的快感被压抑或遭受惩罚的痛苦;他完全是以身体的视角来透视世界。在早期诗歌中,他的快感在文本中,呈现为一种白热化的速度,这一点广为人知;同时,这也有狂欢的性质,如《美人》一诗中,他写道:
整整一个秋天,美人
我目睹了你
你驱赶了、淹死了
我们清洁的上升的热血[6]79
如此的状态,即是一种狂欢,是一种醉。更为人所知的是《琼斯敦》,速度也更快,更白热;现在我们需要从身体的角度来看:
从春季到秋季
性急与失望四处蔓延
示威的牙齿啃着难挨的时日
男孩们胸中的军火渴望爆炸
孤僻的禁忌咬着眼泪
看那残食的群众已经发动
一个女孩在演习自杀
她因疯狂而趋于激烈的秀发
多么亲切地披在无助的肩上
那是十七岁的标志
唯一的标志[6]80-81
不过,相对于柏桦后来文本中跃现的那种狂欢,早期诗歌更像是一个征兆。也就是说,他的写作是一以贯之的,他没有改变,只有程度的加深,只有某种方式的全面展开。张枣曾这样说这一时期的柏桦:“虽然八十年代初的政治压力仍然相当浓重,这些诗人……在写作中却基本上没有选择正面的对抗,而是沉湎于发明一种新颓废,来点染写作冲动和青春的苦闷。”[7]作为柏桦写作生涯的同路人,张枣的话印证了一个问题:柏桦从80年代写作开始,即是以狂欢(“沉湎于发明一种新颓废”)来写作的。相对于朦胧诗,柏桦的写作,意味着一种新的美学,在当时叫做“后朦胧诗”,但今天如果单就柏桦写作而言,他没有选择朦胧诗对抗美学,可能是天性(身体)使然。而其早期的那种热血与速度,也不排除受到北岛的影响;这也是因缘际会,在当时整个时代的美学趣味中,柏桦之所以写出那样的诗,这本身就是身体的力量,也是尼采所说的权力(也译为“强力”)。这种力量从不曾消失,因为他来自身体;这是与生俱来的。故而,当时代发生变化(中国的文学代际更迭非常快,通常认为,英国的诗歌二十年为一代,中国则五年即为一代),诗歌的范式也会随之改变。进入21世纪,由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变化,柏桦的写作,相对于自己而言,也出现了新的范式,早期的痛苦渐渐隐匿,从而真正、彻底地沉溺于文本的快感。有意思的是,这与后期的罗兰·巴特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暗合。
站在后现代的立场考察快感,自从尼采对它进行改造以后,使其摆脱了柏拉图和启蒙理性的束缚,这个词汇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低俗、淫荡、无耻、浅薄的代名词,而是有了新的特殊价值,成为文本生产的原点和理想之境的追求。自然,身体被唤醒,性的因素占据了核心地位,当然并不是全部。罗兰·巴特将之用之于文本理论,也算是一个创举。巴特顺着尼采的方向,把文学的快感分为阅读性和写作性两种类型,前者为悦,后者为醉:
我一方面需要一种普泛的“悦”,我便随时可谈及文的超越,谈及其中对任何(社会)功能和(结构)运作的超越;另一方面,我需要一种特定的“悦”,一种作为整体之“悦”的纯粹面,我就随时要将欣快、满足、适意(文化顺当地插进之际的畅美感)与(醉、销魂说特有的)撼摇、恍惚、迷失区分开来。[8]26
这恰恰可以理解为,是从文本的角度,对柏桦的写作做了最好的注释;性在文本中的存在从来不应被忽略,更不应戴着启蒙理性的眼镜去观察。本文论及的柏桦身体美学特征中的快感,也因而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尼采出发,在他的观念里,明显地体现出身体性趣味,以及伴随身体性而出现的“醉” 的沉溺,柏桦以身体作为透视点进行价值甄别;二是,与罗兰·巴特一致,在具体的文本生产的意义上,呈现为销魂的特征,或者说,柏桦写作,实际上是快乐写作,是以快感为基础的销魂、极乐,文本中言语杂多、相互嬉戏。
其实,对柏桦的这种快感美学进行价值判断时,也并非一定要单纯从西方的视角,比如它对柏拉图和启蒙理性的敌意。如若从中国语境进行分析,也未尝不可;正如上文张枣所言,柏桦“沉湎于发明一种新颓废”,是“没有选择正面的对抗”;可以这么理解:柏桦的这种快感写作,还不仅仅是不选择正面对抗,它也可以被认为是另一种对抗,是倡导,是极权主义语境下的二元性因素,是制造一种不和谐,是有意失去节拍。
我们可以往传统中去寻找这种有意失去节拍的传统。这种传统还相当源远流长,因而并非必须用是否对抗现实的思维来理解快感。姑且不拿“郑声淫”来作为早期案例了,就从白居易说起。白居易的“中隐”思想里,明显地包含有快感成分,而在白居易的及时行乐的文本里,也呈现出一种销魂的醉态。“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显然见出这样的快感。同样,这种具有及时行乐特点的快感思想,在中国一直以来也是被边缘化的,所以它非常另类,以至于白居易竟有“诗魔”之称,虽然“诗魔”一词出于白诗,但将这个词从中挑出来称谓诗人,就成了一个有所指的符号,其中的话语色彩不言自明。白居易之后,这种与主流的儒释道美学——尤其是儒家诗学传统——呈现极大偏移的美学,多有人承袭,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如张岱、李渔、沈复等人的文本。
不得不再次提及的是日本平安朝时代的《枕草子》,清少纳言在这本书中开创了一个有别于物哀的日本美学的传统,其源头固然可以追溯到白居易,重要的是,这也成为柏桦快感思想的一个来路。也许,80年代早期,柏桦还没有真正接触到《枕草子》,所以他写作的个人的范式没有成为现在的样子;仿佛一切都在等待,东西方的快感,以及柏桦自身的身体原因(如罗兰·巴特在谈及自己的时候,热衷于自己日常琐细的爱好,他认为身体与身体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才有了现在的柏桦的写作。
尼采曾提问说“人类如何患上了上帝病,与这个人疏远了”(引文着重号为原书所有——本文作者按)[3]75;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为什么身体和快感在传统里遭遇到抵触?为什么要贬斥身体和快感,以为低俗?在当代中国,似乎直到柏桦,汉语新诗才真正地与“这个人”亲近了。不是吗?放眼当世,有多少诗人没有“上帝病”呢?从身体的快感开始,柏桦的美学自然而然走向了与当代诗歌主流美学思想相异的选择:由快感,而生出了沉湎于日常细节的颓废,以及以颓废为标志的逸乐。
二、颓废
需要强调的是,“颓废”一词,从后现代的意义上,它并非是一个否定意义的词;之所以被否定,乃因对它进行了社会学解读,其中加入了不洁的主体性的道德判断;颓废与身体有不可分裂的联系,是从身体生出来的。正如社会普遍道德认可一种往上爬的努力,颓废便成为一个不合节拍的“刺点”(罗兰·巴特在《明室》中的说法)。因此,对颓废的指责,便是从启蒙理性的、社会学的和功利主义角度出发的;但因为与身体相联系,“颓废”纯然是非功利的,更接近唯美主义。中国的文学自五四时期以来,一直没有出现过大面积的非功利主义的写作,拿李欧梵的话说,“它从未转向那种‘纯粹的唯美主义’的cul-de-sac(绝境)”[9]240。
汉语中原本没有“颓废”一词,这个词是从英语单词decadence翻译。李欧梵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一文中指出:颓废原本是一个西洋文学的概念,二三十年代,有人译为“颓加荡”。“颓废”一词,从字面考察,有坍塌荒废的意思。李欧梵说,他更喜欢“颓加荡”的翻译,以为音义兼收:“颓和荡加在一起,颓废之外还加添了放荡、荡妇,甚至淫荡的言外之意。”又说,“荡妇在卫道者的眼中当然属于坏女人的类型,然而我觉得也可以和古文中所谓的尤物相呼应”[9]137。李欧梵的这种直觉,应该很容易得到广泛认可,江弱水在《古典诗的现代性》一书中,便使用了“颓加荡”而不是“颓废”,这可以看做是对前者的偏爱。关于“颓废”的概念问题,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从英语词源学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和界定,读者自可参阅[10]32。李欧梵的荡妇说与尤物说,更接近身体的含义。
颓废与身体性发生联系的地方在于它的非功利性、唯美性,在于它与以性为核心的身体因素相联系。这里也呼应了尼采的那个问题“人类如何患上了上帝病,与这个人疏远了”;颓废,正是要亲近这个人。人类生命个体的差异性,便有了相对主义。亲近“这个人”,即意味着亲近身体,亲近以身体为中心的日常琐事。因此,这引发了个人话语和历史话语对立的问题。李欧梵认为张爱玲小说为“颓废艺术”,基本论点是:“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是把艺术人生和历史对立的。”[10]164我因此认为,柏桦的写作也是如此。并非说,我们在柏桦的诗歌中找不到历史话语,而是他的诗歌中更多的关注个人,关注身体;为此,他不惜与宏大历史话语对立,完全出于琐屑的身体书写,没有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而仅仅是个人的身体话语。这也难怪,他对张爱玲的激赏,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也因此,柏桦的写作意味着朝小,而不是大的方向去。此处的“小”,便是细节;耽于身边琐事、小事,哪怕大的话题,也往小处写。比如柏桦有一首单行的诗《温暖的事》:
初冬,食指甲缝里有一点污垢,是温暖的;而拇指甲脏的人不懂冬天。[11]226
又如一首两行短诗《中日对比》:
我们爱吃煮老的鸡蛋,
日本人爱吃生的鱼。[11]226
颓废与身体的连接处有两个要素:一是“小”,即细小、琐屑;二是身体,以性为核心,身体和生理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视为身体性。但这二者绝非割裂,而是天然地融合在一起的;它意味着这是一种与主体性话语对立的身体话语,是尼采式的解释世界的透视方式。透视是什么?作为一种美学的方法论,它出自尼采,以之取代传统的认识论;但尼采并未对“透视”进行界定。据西北大学段建军教授的研究总结,作了一个大致理解,认为透视“是为区别于柏拉图传统的辩证法而提出的,以权力意志为本体的生命哲学的认识方法”,以身体为视线,“对一切实物价值或文本,作不同角度的审视、评估、解释和批判”,它“具有多元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不是纯粹的逻辑思辨和概念定义,认识人性的追问之路,是诗性的沉思方法”[12]。在这个大致界定中,“以身体为视线”,和“不同角度”是理解的关键。透视的根本是指向“以权力意志为本体的生命”,是一种反认识论的解释方法。如果从透视的角度研究柏桦的颓废,它作为一个基本的方法,其根本的一点就是耽溺于与身体和生命有关的细小之物。
如果要找例子,这种例子在柏桦的诗作中俯拾皆是,随手拈来一首,《一点墨》第588《古风》:
蹈虎尾,涉春水:南宋油条
小萝卜鸭舌煨汤。
鸳鸯乎,蝴蝶乎
吴门周瘦鹃,江都李涵秋。
大陆青砖,台湾红砖
虱子亦写成蚤子。
炖得稀烂之猪头并非古风
古风是鹅肉和鹅油。[11]254
单从颓废的角度看,我们来考察柏桦这个文本是如何沉湎于细小之物的。透视作为一种身体视角的美学方法,它对细小之物的关注,并非从认识论角度,而是从身体的角度与世界交流;那么,“古风”是什么?让身体说话,让生命说话,让快感说话:“蹈虎尾,涉春水”为什么就是古风?“大陆青砖”而不是红砖就是古风?“炖得稀烂之猪头”为什么并非古风,而“鹅肉和鹅油”却是?这显然无法用认识论解释,而且,一旦认识论发生作用,即意味着主体介入;但身体性与主体性根本就是不相容的,非此即彼的。另外,从柏桦的这首诗里,可以明显见出一种耽溺的快乐,耽溺于“小”的快乐。声音、词语、句式,这在技术层面上的操练的诗之为诗的形式要素,也是服从身体的。颓废是身体沉溺于快感的状态;文本中各种言语在嬉戏,它们是非理性,和反逻各斯的。
颓废之所以为某种主流话语贬斥,原因是它的反传统道德,反认识论;它的从身体出发沉浸于快感的透视,与文学中的社会学(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发生了根本性抵牾,但这恰恰是使文学走向非功利主义的“纯粹的唯美主义’的cul-de-sac(绝境)”之途。柏桦的诗,事实上,从很早的时候就呈现了这种态势:他写于90年代中期的《山水手记》,已经分明地出现了这种透视主义的颓废。“他有着黎明式的精神,但准时是他忧伤的表现。”“好听的地名是南京、汉城、名古屋。”“年轻人烧指甲是会发疯的呀。”“星期天,一个中年女教师/在无休止地打一条狗。”[6]151-153……这些俳句式的诗,并不包含有理性、道德和认识论的判断,完全是一种身体的透视,是一种快乐的沉浸,是一种张枣谓之的“发明一种新颓废”。这其中,柏桦一面是颓废,一面是在玩味——用透视主义对身体的玩味,一种与传统的启蒙理性发生偏差的身体享乐,是属于汉语新诗里的独特的享乐主义。这种独特的享乐主义,包含柏桦的尼采主义的解释世界,他将这称为“逸乐”,一种他从传统借助的美的方法。
三、逸乐
“逸乐”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的《古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安逸快乐”。所谓“安逸”,其中不言自明地包含有安乐、闲适之意;这就是说,它其实意味着一种“慢”的节奏,相对于快节奏,它是漂移和错位。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的看法与这里的逸乐颇有相通之处: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13]
张爱玲此文,是为对迅雨(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对其写作的指责而进行的回击;傅雷的文章发表在1944年5月《万象》第三卷第十一期。事实上,傅雷的批评,有其老派文学的标准,但是他以自己的标准给新派的张爱玲套紧箍咒,是颇为不妥的。关于这个话题,是另一篇文章,仍然回到柏桦这里。2008年,柏桦《水绘仙侣》的出版,成为诗坛上一个事件。这本书的出版,算是一个“快感·颓废·逸乐”的宣言,以非对抗性实现对当今主流诗歌美学的偏离。这本奇特的书,是由一首较长的诗(不是长诗)《水绘仙侣——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和对这首诗的注释组成的。从美学的角度看,整本书无异于就是宣称这是一种新的美;它就是以身体为出发点的新的写作,这种写作一反主体性,而强调了快感、颓废和逸乐。以下从书中抽出的这段话,代表了全书的风貌:
这好大的人世,有风花啼鸟的趣味,亦有鸡犬相闻的乐趣,繁华受得,寂寞耐得,各自有各自的好处。河清海晏,那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亮丽想头;花开花落,岁序不言,那是民间人家的想头,虽然不是大江大涌,却也风日无猜,细水长流。[14]
在另一个地方,柏桦撰文,称“年轻时喜欢呐喊(即痛苦),如今爱上了逸乐,……逸乐作为一种价值观或文学观理应得到人的尊重”,又称“逸乐作为一种合情理的价值观或文学观长期遭受道德律令的压抑,我仅期望这个文本能使读者重新思考和理解逸乐的价值,并将它与个人真实的生命联系在一起”[15]。需要注意的是,柏桦这里说话使用了一种温和的祈使语气,这说明,在当今的文坛上,这种“与个人真实生命联系在一起”的逸乐之美的被压抑的真实话语语境。而柏桦所说的“个人真实生命”,其实就是指“以权力意志为本体的生命”——身体,以及与身体相联系的快感、颓废和逸乐。
反过来,当回到身体性这个话题的时候,不难发现尼采身体哲学和透视主义的题中即已包含享乐,“快乐与不快乃是一切价值判断的最古老征兆”[3]33;不妨把话题稍稍延伸至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人类本然地有着趋乐避苦的天性。这种天性,也不止于弗洛伊德作如是观,它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佛教所谓的各种感官——眼、耳、鼻、舌、身、意——与外界接触产生的欲望,其实也是快感,只是,它要求将这些欲望止息。从后现代角度对尼采的身体哲学观察,很容易导出享乐主义的结论,虽然尼采以强力意志来对其进行修正,本文亦不打算从强力意志这个话题岔开。无疑,透视的结果,就是快感和享乐的合法性。值得辨析的是,作为柏桦提出的一个写作的美学观,逸乐与享乐有着细微分别,虽然二者很难区分。享乐,可以完全出于身体,但逸乐除了身体以外,它自身包含的安乐、闲适的趣味,使其更多了一道玩味的风景:它的时间性、它的慢节奏、它的现实的物质主义。由是,并不能将柏桦的写作断为单纯享乐主义写作;而且,这也不仅是由于柏桦说了什么,他的文本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比如,《一点墨》一共六百四十六则,犹如一个逸乐的大观园,身体、快感、颓废,以及词语的交欢,应有尽有。如题为《纸》的诗,第二节:“紧张?不。乌力波(Oulipo)?不。/天井里,青苔/欲上人衣来。一种回忆录,中唐的/Bunin?/不。但死有一个好处,躺着。”[11]183为什么会这样写?为什么“欲上人衣来”与“一种回忆录”并置,两种言语犹如人体交合?笔者以为,柏桦以这样的文本,来为他的逸乐之美提供一种写作的典范,并对启蒙理性之后,或者现代之后文学是什么作出回答:去除及物的写作,完全沉浸在颓废的逸乐,词语的嬉戏,抛弃道德,抛弃真理,抛弃人道主义。
那么,在柏桦的写作里,自然,也就不会主动触及一些大的事物,而是沉迷于“小”。这个“小”,乃是,乃与日常生活有关;这些日常生活的小,构成了他的身体美学里的人世的风景。柏桦的“小”,必定是在人世中的小。柏桦在一篇文字里这样写道:
在通常的唐诗选本里,也许不会出现上述的这首(白居易的)《舟行》。因为从内容上来看,它描写的只是一次琐碎的日常饮食活动,与那种代表崇高的或者至少正经的忧国思想、感遇心态截然不同。这类诗歌有着某种浓烈的个人气味,甚至颓废气息,即它过于专注享受、品味,而不是讲求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就将这类诗文仅仅看作是一种单纯的贪图享乐、放纵生活,“逸乐”作为一种生命形态,它不仅可以是文学作品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价值。[16]
无疑,这段话,可以视为“逸乐”的通俗化表达。因此,柏桦的“逸乐”,从而与快感和颓废,共同构成了他的身体美学。
身体性,也即表现在这三者的结合:首先是基于身体的快感,这是一个前提;其次乃为颓废,也即玩味和沉溺于“小”与精致;逸乐则作为对快感和颓废的升华,成为一种人世的风景。在此基础上,柏桦构建了自己的写作生产机制:一种独特的文本色情学。这是一种与罗兰·巴特的文本思想实现了高度暗合的文本学,在生产的层面上,将文本也视为身体,词语相互嬉戏,“种种群体语言(langages)的同居,交臂迭股”[8]4,这些构成了文本的身体性。如罗兰·巴特自问:“什么样的身体呢?”他说,是这样的身体:“一种醉的身体,纯粹由性欲关系构成。……文具人的形式么,是身体的某种象征、重排(anagramme)么?是的,然而是我们的可引动情欲之身体的某种象征、重排。”[8]21因之,柏桦的身体美学具有两重性;文本的生产,或文本的色情学,是柏桦写作的落脚点。当我们谛视柏桦文本时,不应忘记李欧梵解释“颓废”时的“荡妇”说和“尤物”说,这是柏桦的身体文本的重要特征;它是要强调文本的妖媚属性。文本的身体,是妖艳、妩媚和狎邪的身体,犹如美艳的妇人;如陈叔宝诗“映户凝娇乍不进”、“妖姬脸似花含露”,非常妥帖。
在这个意义上说,柏桦的写作,基于尼采的身体哲学和透视主义方法,是他的写作的出发点,文本的色情学,是他的写作的落脚点。早期,痛苦——也即他自己所说的“呐喊”——是驱动力;经过十多年停笔,自《水绘仙侣》开始,另一种身体表现形态——逸乐——在其诗中大面积跃现。然而无论痛苦还是逸乐,实质上是统一的,正如他在《现实》一诗中写的:“而冬天也可能正是夏天/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柏桦的写作自80年代以来,在美学上,一以贯之,且有着逐渐成熟、全面展开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汪民安.尼采与身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61.
[2]柏桦.左边[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12.
[3]尼采.权力与意志:上卷[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8.
[5]尼采.酒神的世界观[M].周国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22.
[6]柏桦.山水手记[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2011.
[7]张枣.张枣随笔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8.
[8]罗兰·巴特.文之悦[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9]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10]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M].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柏桦.一点墨[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
[12]段建军,彭智.透视与身体——尼采后现代美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7.
[13]张爱玲.流言[M]// 张爱玲.张爱玲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85.
[14]柏桦.水绘仙侣[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42.
[15]柏桦.逸乐也是一种文学观[J].星星诗刊(上半月刊),2008(2).
[16]柏桦.日日新——我的唐诗生活与阅读[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78.
责任编校:汪长林
Pleasure, Decadence and Delight: Somaesthetics in BAI Hua’s Poetry
LI Shang-yu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Anhui, China)
Abstract:From the early 1980s, BAI Hua, a poet, began to compose poetry with somaesthetic features, which were based on Nietzsche’s body philosophy and perspectivism and constituted the starting point and secret of his poetry aesthetics. Pleasure, decadence and delight, three aspects of somaesthetics in BAI Hua’s poetry, form the aesthetic view of his writing and a unique post-modern view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Key words:body; perspectivism; pleasure,; decadence; delight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6)01-0061-06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1.014
作者简介:李商雨,男,安徽太和人,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收稿日期:2014-12-18
网络出版时间:2016-03-09 13:49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60309.1349.0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