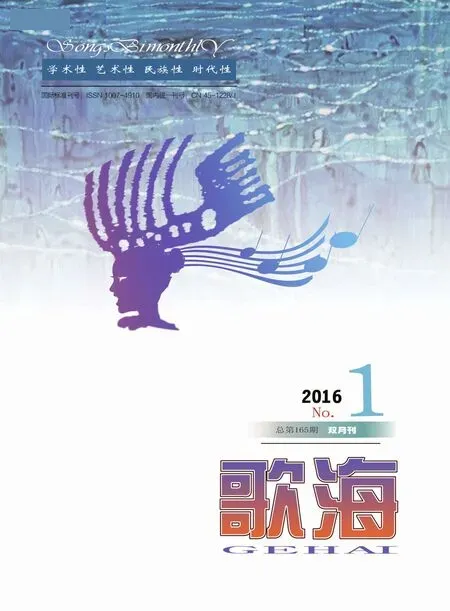民俗“迎老爷”中潮州大锣鼓存在现状考察与文化解读*——以潮州市两个社区的游神活动为个案
●潘妍娜
民俗“迎老爷”中潮州大锣鼓存在现状考察与文化解读*——以潮州市两个社区的游神活动为个案
●潘妍娜
*本文系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项目“高校本土传统音乐教育的‘话语转换’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2A033)阶段性研究成果;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项目“岭南本土传统音乐资源在高校音乐教育课程中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11TJK160)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潮州民俗“迎老爷”活动是潮州大锣鼓的原生环境,考察这一民俗空间与当代大锣鼓的存在关系,对潮州市两个区域意溪镇下地段和磷溪镇埔涵村的“迎老爷”活动及其中的大锣鼓表演进行调研,可以对潮州大锣鼓在这一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独特的文化含义进行解读。
[关键词]“迎老爷”;潮州大锣鼓;祭祀;宗族社会
潮州大锣鼓是流传于粤东地区的传统吹打乐,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地方乐种,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民俗实用功能,其存在涵盖着中国传统音乐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目前对于潮州大锣鼓的研究主要是对其音乐形态的研究,较少对其形态背后的人文、历史、社会因素进行探索。当传统面对现代化剧烈的冲击时,探讨传统在当下的保护必然需要从其活态的原生环境与音乐的关系进行研究,在这一背景之下,仅仅进行形态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关注音乐的原生状态,理解潮州大锣鼓的社会价值与文化内涵,将有利于这一民间乐种在当下的继承与发展。为了考察潮州大锣鼓在当下的活态存在,笔者于2012年正月初五至初九(1月28日至31日)前往潮州对“迎老爷”活动中的大锣鼓进行了考察。本次考察选取了潮州市两个社区的“迎老爷”活动作为考察对象,分别是正月初六意溪镇下地段的“迎老爷”和正月初八磷溪镇埔涵村的“迎老爷”,笔者想通过对两个民俗活动的比较性考察,较为全面的把握潮州大锣鼓在当代农村生存的真实状况。
一、潮州大锣鼓与民俗“迎老爷”
在传统的潮州社会中,大锣鼓只在传统民俗游神活动中演出,潮州的游神多在正月和二月间,也称“迎老爷”。潮州地区不论城乡,岁时祭祀与游神习俗多,村民有定期的祀奉活动。每年一到规定的日子,村民就将村中所信奉的神像从庙中抬出,到街巷游行,在这个过程中,重点就在于大锣鼓。在当地民间认为,“迎老爷”游神必须有锣鼓队,如果没有锣鼓队为神灵护驾,游神便无法进行。可以说,地方信仰为潮州大锣鼓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因此,传统的潮州社会中,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锣鼓队都是一种必须的存在。
意溪镇下地段和磷溪镇埔涵村两个社区的“迎老爷”所供奉的神灵均为三山国王。三山国王是粤东地区普遍信仰的本土神灵,崇奉三山国王的庙宇遍布城乡农社,三山指的是揭阳市揭西县河婆镇北面的独山、西南面的明山和东面的巾山,三山国王为三座山的山神。相传北宋时,三位山神因助宋太宗征北汉刘继元有功,宋太宗“诏封明山为清化盛德报国王、巾山为助政明肃宁国王、独山为惠威宏应丰国王”,并赐庙额曰:明贶,并敕增广庙宇,岁时合祭,从此,三山神便被统称为三山国王。①陈春声:《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三山国王信仰与后土信仰相结合,每逢立春举行春祭之时村民便将神像从神庙中抬出游行,其目的就在于祈求来年境内风调雨顺、人畜平安。
这一活动过程不仅是一场祭祀也是一个众人娱乐的过程,一个游神赛会的仪式队伍中,由标旗、彩景、醒狮、歌舞、大锣鼓队各个并不固定的部分组成,由于社区具体情况不同,仪仗队的规模有一定的差别。其中意溪镇下地段的游神活动由长和居委(部分)、坝街居委、寨内居委和东洋塭村几个社区在一起游行,该区域为居民与农民混居,因位于镇上,参加的人较多,规模较大,也更为热闹。而埔涵村由埔上、涵井二个自然村组成,规模远不及意溪镇,也不如意溪镇游行形式的多样化。虽然规模不同,但从信仰氛围来看,两个社区的游神活动都充分展示了观赏和娱乐的性质。
二、“迎老爷”活动流程与祭祀特点
(一)活动流程
据笔者考察,尽管两个社区游神规模不同,但从游神程序来看,埔涵村与意溪镇并没有太大区别,都包括了“请神——游神——送神”这一程序。请神仪式大约在上午8点进行,由游神赛会仪式活动组织者燃香,潮州大锣鼓队在神庙前奏乐,组织者在庙内进行相应的请神仪式,拜请三山国王宫内的诸神坐上神轿,开始游行。三山灵庙中供奉的“老爷”除了三山国王,还有国王的“大夫人”“二夫人”“三太子”以及“土地公”“土地婆”等神祇,三山国王在前,一众神祇被抬出神庙,随着“老爷”起身,众锣鼓队也整理队伍,按照事先排好的顺序开始游行。之后游行队伍按照固定不变的路线进行游行,游行队伍每到一处斗脚或祠堂,“老爷”需稍作停留,接受本地域人们的礼拜上香,由于游行时间所限,每一处斗脚或祠堂停留时间不超过十分钟。这一程序被当地人称为“老爷坐位”,当地人认为,老爷在本地域内坐位,煞气就能驱走,为本地域带来平安好运。①张璇:《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观众态度研究》,星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游神在中午十二点左右结束,在锣鼓声中,“老爷”被送回了神庙中。
(二)两个社区不同的祭祀特点
人类学在研究村落社会祭祀范围的过程中,提出了“祭祀圈”的概念,“祭祀圈”是研究村落地域团体或家族团体的重要方法,最初由日本学者冈田谦所提出,一般是指以一个主祭神为中心,信徒共同举行祭祀活动所属的地域单位。在这一区域内,人们透过共同神明信仰,举行共同祭祀活动,将地方上人群整合起来,维系一体的意识与感情。在潮州的迎老爷活动中,“祭祀圈”的范围以宗族为基本单位形成单一村落和多村落祭祀的不同类型,在本文所涉及的两个祭祀社区中,埔涵村的“迎老爷”以村内大姓丁氏宗族为主,由丁氏宗族组织,张、施、林诸姓一同参与,从而构成了一个立足于自然村落区划的“祭祀圈”。其区域内的人们共同供奉的是坐落于村东南方的三山国王神庙,村落中村民共同出资筹备本村的游神,由于村中丁姓宗族为主要的居民,游行的路线以丁氏各房支的祠堂为主要的点,同时也兼顾其他小姓例如同村的张姓、施姓、林姓的祠堂,可以说,埔涵村“迎老爷”具有单一村落单一宗族为主的乡村型祭祀类型的体现。
而在意溪镇长和、坝街、寨内三个居委和东洋塭村所构成的“下地段”②意溪镇上这一天的游行又根据不同的社区(上下地段)而分为两个时间段,上午是下地段的长和(部分)、坝街和、东寨洋内塭村游行,下午是上地段的长和(部分)、橡埔村、团三村几个社区一起游行,这样的划分自古已有。祭祀区域内,人们共同供奉的是位于寨内居委的三山国王神庙,以三山国王信仰为核心,根据地域区划,构成了意溪镇下地段的祭祀圈。初六上午的祭祀,由该区域内的各宗族共同出资筹备,“迎老爷”游行的路线,便是以这一区域内的祠堂、神社为祭祀点。与埔涵村单一村落单一宗族的祭祀类型不同,在“下地段”这一社区中,因位于镇上,经济较为发达,人口较多,宗族较为复杂,并不像埔涵村以丁姓宗族为主,而是一个多宗族的区域。该区域内的宗族构成为:长和社区以钟、黄、林姓为主;坝街社区以张、卢姓为主;寨内居委以蔡、陈、林姓为主;东洋塭村以翁、黄、张、潘为主。“清朝中期,保甲制度推行,把原本作为一个乡村建制的意溪按姓氏和区域,编成了十五个‘社’,分别是东关社、南关社、西关社、北关社、坝街社、敦厚堂、潘厝、翁厝、周厝、赖厝、黄厝围、石门斗社、蔡厝、长和社、连邑社。除坝街两社和寨内四社是杂姓之外,其余各社均是一姓。”③张璇:《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观众态度研究》,星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十五个“社”④“社”这一祭祀单位在潮州意溪镇的保留,体现了古老中原文化在潮州地区的遗存,也验证了该地区族群作为中原移民和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共同供奉位于寨内居委的三山灵庙,但同时每社斗脚建有小型神庙,作为三山灵庙的“分治点”,同时供奉土地神。因此游行队伍每到各“社”神庙之前,都要停下来打一段锣鼓,之后又继续前进。延续自古已有的游行路线,完成一年一度的神灵巡境仪式。因此,意溪镇下地段的“迎老爷”活动体现了多村落多宗族的综合型城镇型祭祀特点。
三、游行中的大锣鼓
(一)曲目
在“游神”这一过程中,大锣鼓所演奏的套路和曲目根据游神程序而分为“游行锣鼓”和“驻场锣鼓”两类,其中“游行锣鼓”的曲目称为“长行套”,“长行套”是在行进中用一般曲牌配上锣鼓演奏,根据路途的远近可长可短,套曲简单、灵活,也较通俗化、大众化。游行中较常使用的长行套包括二板长行套和三板长行套,常用曲牌有[过江龙]、[小梁州]、[一粒星]、[北山茶]和[闹江州]等。牌子套由同宫音系统的牌子曲联缀而成,多数来自正字戏的音乐、唱腔,为游行到斗脚、祠堂之时演奏。常用牌子套有[六国封相]、[关公过三关]、[十仙蟠桃会]等。两个社区从演奏曲目来看,都是《六国封相》《秦琼倒铜旗》《八仙庆寿》《关公过三关》等传统曲目,尽管当下新创作的锣鼓曲有不少,但是在潮州乡村中,在迎老爷这一传统民俗活动中,传统曲目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锣鼓队乐队配置
大锣鼓的乐器分成打击乐部分和管弦乐部分,其中打击乐的乐器包括鼓、斗锣、深波、大小钹等,管弦乐的乐器包括笛子、唢呐、扬琴、椰胡、三弦等,其中鼓作为领奏乐器是整个演出过程的核心。
两个社区的乐队配置也较为相似。游行中的锣鼓队由村民组成,一支锣鼓队30人左右,一般的配置为:鼓1人,斗锣8-12人,大钹2-4人,小钹2人,月锣、钦仔、亢锣、深波、苏锣各1人,笛子4-6人,唢呐2-4人,扬琴1人,三弦1-2人,月琴1人,二胡1-2人,椰胡1-2人,乐队成员年龄构成较为多样化,上至古稀老人,下至黄口小儿,都可以作为乐队成员参与游行,其中打击乐部分主要由青少年担任,是锣鼓队的主要力量。
(三)流派风格
两个社区在大锣鼓的传承与发展上都有一定历史积淀,但分属不同的流派。潮州大锣鼓分为“文、武”派,埔涵村的大锣鼓风格为“文派”锣鼓,“文派”锣鼓是建国前民间打鼓艺人邱猴尚发展出来,其特点在于鼓点密集均匀、文雅细腻、力度适中。埔涵村上一代打鼓师傅丁钦才正是师承于邱猴尚,据说多年前邱猴尚常年在埔涵村教习锣鼓,可见埔涵村的锣鼓队是有一定历史的。而意溪镇的大锣鼓以“武派”锣鼓见长,“武派”锣鼓是建国前民间打鼓艺人许裕兴发展出来的一种打鼓风格,讲究手法多样、气势豪放。许裕兴为意溪长和木厝池人,当年就在长和社区中“老万顺”锣鼓馆主持和传授大锣鼓,如今当地的司鼓师傅或直接或间接都师承于他。意溪镇在国家文化部组织开展的2011—201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评审活动中,以“大锣鼓”和“金漆木雕”两个项目进行申报,在2011年的时候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意溪镇的大锣鼓随之成为潮州大锣鼓的代表。
四、民俗“迎老爷”中潮州大锣鼓的文化解读
(一)祭祀活动中神圣的音声
重视土地和农业决定了潮州社会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乡土社会基质,也形成了传统潮州社会对于土地神信仰的昌盛。土地神被作为镇土之神而受到潮州人的供奉,不但村头地界都建有土地庙,而且在其他神灵的神庙中也有土地神的位置。这些土地神名称不同,既有我们一般意义上所称呼的“土地公”“土地婆”,还包括三山国王、安济圣王、双忠公等地方神灵,神灵虽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但无不是以守护所辖地区江河水利,保境内平安的身份存在。而正是因为重农业、信鬼神,因此潮州地区不论城乡,岁时祭祀与游神习俗颇多,尤其是春耕时节的祭祀活动最具典型,正月的“迎老爷”就是这种信仰的体现,这同时为潮州大锣鼓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音乐与仪式的关系在于:“作为仪式行为的一部分,音声(音乐)对仪式的参与者来说,是增强和延续仪式行为及气氛的一个主要媒体及手段,通过它带出了仪式的灵验性。”①曹本冶:《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从这一角度来看,仪式中的音声可以说是潮州大锣鼓在这一民俗活动中的本质,潮州当地民间认为,以震耳的锣鼓乐献祭“老爷”,既可以显示神灵出巡的威严,又可以驱邪祈福,如果没有锣鼓队为神灵护驾,游神便无法进行。虽然整体来看,埔涵村规模远不及意溪镇,也不如意溪镇游行形式的多样化,但从信仰氛围来看,埔涵村对于三山国王的信仰之虔诚却又较意溪镇更让人印象深刻,游行队伍到每个祠堂路口之时,便有人开始放鞭炮,大批的信众手持香柱迎到路口,见到“老爷”纷纷下跪,壮观的场面与大锣鼓喧闹的音声重叠在一起,营造出一个神圣的世界,让笔者一个局外人都能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二)民俗活动中的娱乐、竞技与狂欢
正如很多中国的传统节日与祭祀之间紧密的关系,长期以来形成的祭祀传统以及在“迎老爷”这一过程中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使得这一天已经不仅是一次普通的祭祀活动,而演化为一场民俗狂欢。清朝嘉庆年间的潮州府海阳县文人郑昌时在《韩江闻见录》记述其所经历过的崇奉三山国王的情况,“三山国王,潮福神也。城市乡村,莫不祀之。有如古者之立社,春日赛神行傩礼。胙饮酣嬉,助以管弦戏剧,有太平乐丰年象焉”①郑昌时:《三山国王》,载《韩江闻见录》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这一段话正道明了传统潮州地区“迎老爷”这一活动作为一个民俗化的祭祀仪式,其历史的悠久,活动内容的丰富性:不仅有神圣的祭祀环节,还有戏剧、音乐以及其他民俗事项。正如一本书中提到的:“音乐和舞蹈在祭祀仪式中并非仅仅是为了取悦神灵,它们也是仪式参与者自我娱乐的一种方式。”②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锣鼓在整个祭祀活动中不仅具有神圣性,还为整个仪式的参与者营造了节日的气氛。考察中笔者发现两个社区的祭祀活动相比较,埔涵村由于是单一宗族为主的祭祀,规模较小,较多的保留了这一活动祭神的本质,而意溪镇作为多村落多宗族的联合祭祀,则更具“娱人”的特点。这一点可以从游神时锣鼓队数量和表演来看,当天一共有五支锣鼓队参加了游神,五支锣鼓队分属“下地段”所属的四个社区,每个社区出一支锣鼓队,加上意溪镇上的民间音乐组织“鳄渚民间音乐组”,分别是:
东洋塭村锣鼓队
坝街石门斗社茂兴锣鼓队
长和喜灯社鼓乐社
寨内敦厚堂潮州琴园曲艺园
鳄渚民间音乐组
五支锣鼓队一起游行,规模尤为盛大,形式多样丰富,而其中来自不同社区的锣鼓队彼此之间存在的互相斗乐,使得这一祭祀活动更像是一场锣鼓乐的竞技盛宴,竞技性与娱乐性也正是潮州大锣鼓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更为成熟的体现。
(三)宗族社会族群认同的凝聚力
在本次考察的两个社区中,无论是单宗族为主的埔涵村,还是多宗族共同祭祀的意溪镇下地段,在迎老爷这一民俗活动中,可以确定“宗族”作为一个祭祀的基本单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具有“家族祭祀”的特点。葛学博在1925年出版的《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中提出“家族主义”这一概念,他认为在华南地区潮人乡村社会中,人们的行为、规范都以家族为核心。在其记述中,把“迎老爷”这类仪式归结为一个目的,即满足家族主义的功能。他区分了人间与神灵社区,自然与宗教家庭。所谓神灵社区即是去世的祖先,宗教家庭即指一个祭祀单位。他认为各种仪式成为两种社区联结的媒介。③周大鸣:《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在笔者观察到的整个“迎老爷”活动中,从活动的策划、组织到游行的路线的确定,宗族制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体现于:其一,村中宗族的族长和各房支的房头组成村落领导集团是每年游神赛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二,“迎老爷”活动和宗族组织的维护与祭拜相融合,以“房”“支”为祭祀单位,游行队伍每到各“房”“支”祠堂前都要停留祭拜。
以宗族制度为基础的潮州乡村社会进一步成为了支撑潮州大锣鼓存在的社会力量,反过来看,潮州大锣鼓也为维系、加强、凝聚宗族社会的群体认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学习潮州大锣鼓是宗族教育的重要手段。迎老爷是全村民都必须参与的一项活动,进入到锣鼓队中学习打锣鼓和演奏乐器是村中青少年成长中的一个重要过程,
例如埔涵村多年来形成了一个传统,每家的男孩到十四五岁就要送到锣鼓队中学习打锣鼓。据笔者了解到,每年的暑假,在潮州的乡村中的公房或广场中,大批的青少年被集中起来,聘请打鼓师傅到村中集中进行教授。这些孩子的父母们认为,参与村中的锣鼓队并服务于“迎老爷”活动既是作为宗族成员的一种社会责任,同时也可以避免孩子因为暑假无所事事而沉迷于网络或学坏。其二,演奏大锣鼓成为社区间宗族认同、交流、竞争的工具。尤其是城镇作为多宗族混居的区域,在这一区域内,不同的宗族、村落在更大的社区中协调、整合同时彼此竞争,游神赛会就是宗族的合作与竞争的体现。多宗族村落共同筹办这一区域的游行,说明在更大的社区中,原有的宗族权力被削弱,但同时游神赛会也成为各宗族炫耀财力、物力的一个场所,而锣鼓队及其表演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这种炫耀的工具,这也无怪乎在笔者的调查个案意溪镇游神中不同社区的五支锣鼓队一同游行所呈现出来的竞技性。而在传统的潮州乡村中,各宗族因为游神赛会发生械斗事件比比皆是,锣鼓队则往往成为了导火索,周大鸣在《凤凰村的变迁》分析凤凰村与周边村落关系时候就提到潮州归湖镇白叶村内徐、吴两姓,平日里友好相处,但每逢正月十五日游神两方出锣鼓队,互相攀比争脸面而造成械斗的例子。①周大鸣:《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这正说明在多宗族混居的社区的游神活动中,不同宗族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以及大锣鼓作为宗族荣誉所具有的社会地位。
五、结语
民俗化的祭祀活动和宗族社会无疑是支撑潮州大锣鼓得以运行至今的重要生态,服务于游神这一功能性需求也造就了这一环境中潮州大锣鼓实用性和临时性的特点:乐器的公有化(全村人共同出资购买)、乐队的非固定性(锣鼓队只有在春节前才集中起来进行排练,平日里乐队成员都各自为生活而奔波)和音乐曲目的单一性(传统曲目)。只有理解了潮州大锣鼓这一特定的生存土壤,我们才更能理解为什么在传统的潮州社会中,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锣鼓队都是一种必须的存在,进而理解潮州大锣鼓对于潮州传统社会的独特的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探讨传统音乐的活态保护这一问题也就变得更有意义。
作者简介:潘妍娜,女,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