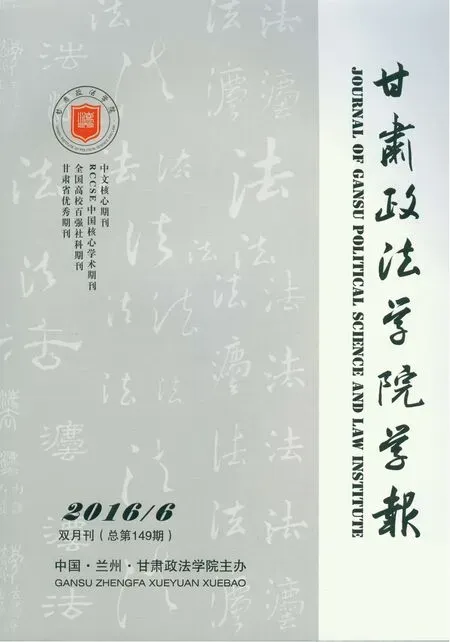论我国宪法中的国家义务理论渊源及其本位
崔寒玉
论我国宪法中的国家义务理论渊源及其本位
崔寒玉*
在国家与公民关系问题中,已有研究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过分关注使其忽视了国家权力的暴力性在保障公民权利时的弱化作用,并同时没有意识到国家义务在社会权问题凸显的今天所体现的价值和作用。正确理解国家义务理论的渊源及其本位,认清国家义务理论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的理论基础,以及其在宪法中的具体表现,从而针对性的采取对策运用进而实现国家义务,是现代宪法实施所应当秉持的价值内涵之一。在权利要求日渐丰富的今日,正视国家义务理论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符合法治的要求。
国家义务;社会本位;社会权
人类社会近两个世纪都在为寻找对国家权力施加法律约束的有效手段而奋争。从个人主义到社会主义,法学家都在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提出不同的理论主张。在国家之上是否存在一个高于国家的法律来对国家进行义务性限制这一问题,就成了公法的基本问题。
在国内,国家义务论的研究也是在最近几年被学界所开始重视的议题。一直以来,公法问题中国家与公民的对应,对于公民权利的研究随着人权思想热潮而较早的提上日程,相对应的国家理论观念并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此之前,国家与公民这一公法的中轴性问题,仅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角度进行论述,然而,国家权力是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机器来实现其意志和巩固统治的力量,其本身就具有强制和暴力的特征,从权力角度出发,这一对公民权利有着压制性作用的理论是否真正对公民权利起到保障的作用也不得而知。因此,对国家义务理论理论渊源的探索与研究开始得到学界的重视。*例如孙世彦:《论国际人权法下国家的义务》,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陈醇:《论国家的义务》,载《法学》2002年第8期;高鹏程:《国家义务析论》,载《理论探讨》2004年第1期;邓成明、蒋银华:《论国家义务的人本基础》,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杜承铭:《基本权利的国家义务——理论基础、机构形式和中国实践》,2008年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徐钢:《论宪法上国家义务的序列与范围——以劳动权为例的规范分析》,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柳华文:《论国家在〈经济、社会好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义务的不对称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参见龚向和:《国家义务是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国家与公民关系新视角》,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4期。
国家观的演变使国家义务观念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丰富的不同阶段。从总体上来说,国家义务观念的产生是为了消解国家权力概念所造成的对于威权的恐惧而产生的对公民权利概念的忽视,以义务观对应公民权利,是以公法中的相互关系保证公民权利的真正实现,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和建立有限政府是现代国家义务的主要体现,而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理论渊源的演变随着不同时期对国家概念的不同理解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
一、国家义务理论渊源:形而上学国家观
形而上学国家观也称个人主义国家观,主张国家作为主权者存在的目的就是保护个人权利。1793年的《人权宣言》写到:“社会的目的是共同福利。政府是为保护个人享有其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目的而成立的。”个人主义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其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受干涉,反对权威等对个人的压迫。个人主义国家观倡导天赋人权,以单个的人为本,主张国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因而萌生了国家义务的概念,用以限制国家权力,并主张国家拥有权力并负有义务去压制和惩罚所有侵犯他人自治性的个人行为。*[法]莱昂·狄骥:《法律与国家》,冷静、郑戈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个人主义国家观不是最早出现的对国家观念进行系统论述的理论,但是第一个将国家理论中融入国家义务相关内涵的国家观,个人主义国家观旨在平衡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关系,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和秩序的维持都是为了保护个人财产的安全。个人主义国家观的预设是人类在为满足自身利益而产生奋争,在逐渐对混乱和普遍的敌对感到疲惫之际,“人们通过经验获致了渐进的进步,其中包括对法律的服从。”*[爱尔兰]约翰·莫里斯·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霍布斯提出,人类生活为了克服自身私欲导致的如丛林般的社会生活,需要一个巨大的“利维坦”以其权威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防止个人欲望对他人财产的侵害,国家的形成始于“一大群人互相订立信约、每个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32页。在此意义上的国家,基本上对社会福利等问题是漠不关心的,仅消极地以国家权力的威慑力来保证社会成员之间不相互侵害。霍布斯意义上的国家,其虽在目的上与洛克是一致的,旨在建立一种秩序以保证人民权利得以实现,但他理论中的国家更多的是在行使权力而非履行义务。
洛克的思想相对较为和缓,其为了保护个人权利的实现,为国家权力设定了边界,认为人民不能将全部权利让渡给同一主体,而应当由不同的人行使立法权和执行权,以防止权力的专断对权利的侵害,但其理论意义上也没有将国家义务的内涵有所扩展。这一理论后为实证主义法学派继承,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边沁。在边沁看来,人类的基本规律就应是避苦求乐,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的主要内涵即,“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少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我说的是无论什么行动,因而不仅是私人的每项行动,而且是政府的每项措施。”*[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版,第58页。国家的义务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如果组成社会的个人是幸福的,那么国家就是繁荣的。他认为,“一切行为的共同目标……就是幸福。任何行动中导向幸福的趋向性我们称之为它的功利;其中的背离的倾向则称之为祸害……因此,我们便把功利视为一种原则。”*[英]边沁;《政府片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15-116页。这一理论促成国家的一切事务的实行必须以个人的幸福这一功利的标准进行。
个人主义国家观本身的内涵也有发生变化,其在初期,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为了以一种威慑的力量保证个人之间的不相互侵犯,但权力运用亦有可能造成对个体权利的侵害,从而可能违背国家建立的初衷。因而,为了更好的保障个体权利,个人主义国家观才转而运用洛克的思想,利用分权来解决权力过大对个体可能产生的威胁。但是,个人主义国家观下,国家的义务依然仅仅被限定在对个人权利的认同和不予干涉,以及对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进行惩罚的职能,没有将对公民权利相对应的积极义务加以考虑,也就认为国家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对公民有救助、满足其就业和受教育的权利。个人主义国家观所对应的人权保护还仅仅限定在消极义务的层面上,并且个人享有要求国家如何行为的绝对权利,为保护这种权利的行使,国家机构进行分权设置,立法权以保证个人权利实现为界限,司法和行政权以维护个人权利不受侵犯为目的。个人主义国家观的这种个人权利至上理论发展到极端,就发展出了以暴力反抗压迫的绝对抵抗权,即个人有权采取暴力手段推翻作为权利侵犯者的政府。 因而,个人主义的个人权利至上很容易使国家的主权陷入困境之中。
毋庸置疑,个人主义国家观的觉醒为国家权力的正当存在设定了义务,从而以义务来牵制国家权力的正确运行,在当时,对国家权力的暴力统治有着积极的制约作用。然而,其理论自身有着一定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现代自然法研究当中,出于经验的、或是出于形式上对人的研究都以彼此孤立的主体存在为基础,共同体也不过是孤立个体的集合形式。个人主义学说将个人视为在自然状态下区别于其他人的孤立的自然人,人类行为方式是孤立个体的行为过程,在此种意义下的人类共同体其内涵也不过是牵强附会的形式相加。*就此,黑格尔对自然法的经验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评析,认为其原理只要是从关于人性的虚构定义或者人类学定义出发,以便在此基础上借助更进一步的虚设,提出的社会集体生活的合理组织方案,它们就是经验的,由此将人类共同体想象成为孤立主体的组合。参见[德]黑格尔:《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Jenaer Schriften,载《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475页。引自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曹卫东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此种理论以康德与费希特为代表,其将伦理行为与人性当中的一切经验的内容和倾向剔除开来,只看做是理性活动的产物。然而,亚里士多德起就已提出人性中与共同体相联系的本质,基于此人类社会化的自然基础应当是假定一个主体间共存的前提。“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本质不同就在于人类天然有为公民社会的倾向。”*同前引〔3〕,第15页。独立存在于社会中的人是不存在权利概念的,人不能孤立于社会之外而存在。权利概念是在人进入社会后,融入社会生活中在国家体制下而存在的、与他人互相交往之间存在的,人在进入社会之前拥有的应当称之为能力,而非权利。个人主义国家观强调国家义务是个人权利的对立面,但国家义务不是在国家出现之时就同步产生的,而是在国家与个人关系发展变化中逐渐衍生而来的。此种观点中预设了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个人权利的不受侵害,这也是一种个人本位的国家义务观,在此种价值观中,忽视了国家存在的目的不应仅仅是倡导以个人自我为中心,而是应该正视人类是融于社会的“政治动物”这一事实。
人不能以天赋人权理论主张其在进入社会之后才享有的权利。德国魏玛时期的法学家赫尔曼·黑勒也曾认为,自由法治国并无法对公民进行普遍的保护,因而提出了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要求人民对国家的普遍认可。民主主义者托克维尔说过,“政府的目的,是给组成这一整体的每一个人以最多的福利, 使他们免受贫困。这种以平等作为社会准则、 民主作为国家特点的社会, 同时也是以最大多数人的福利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这是一种以繁荣和安宁为目的的社会, 是一种人们所称的小康社会。”*[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页。尽管他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也对个人主义的观点予以驳斥,认为国家以每个人的和谐共存为目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与最大多数人的福利为目标的社会准则背道而驰。涂尔干认为, “在个人主义社会里, 首要的问题在于保持最低限度的集体意识, 即共同的信仰和道德准则, 否则社会有分崩离析的危险。”*同前引〔9〕。这就揭示了,在个人主义社会中最可能出现的问题,即没有了集体意识,社会就会分崩离析,因而,个人的权利也就没有了保障的依托环境。但同时,这种集体意识也一定是最低限度的,因为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里,不可能形成集体意识为主导的思想。极端的个人主义学说将个人的独立性对立于国家的权力使其不相容的陷入了两难状态,即要么支持个人权利至上的无政府主义,要么否认个人自由陷入专制。
二、国家义务理论之演变:社会契约国家观
为了避免个人权利至上对国家主权的破坏,社会契约论的倡导者则提出,在保障个人权利自治的前提下,也给予国家主权以独立的地位。主权的存在不会对公民个人权利有任何侵害,因为主权是由具有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的民族共同体组成的,即卢梭所说的公意,公意是全体人民的意志,是全体人民对自身意志所施加的限制。社会契约的主旨就在于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和谐并存。将个人意志融入国家主权,因而在个人意志得到充分尊重的情况下,主权也就得到增强。
社会契约论的国家思想也见诸于康德和黑格尔的论述中,他们的基本观点也是一致的,即“个人只有借助于国家,而且只有作为国家的成员才能获得自由,国家的全能性不仅可以使个人的自治性得到完整的保留,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个人的自治性。”*同前引〔2〕,第46页。为了避免出现同个人主义者一样的二重危机,社会契约论者试图将个人与国家的二元关系融于一体,将社会矛盾的根源寓于一个普遍承认的社会契约之中,澄清了国家存在的目的与方式,为国家存在的正当性提供了新的依据,因而指明由此建立起来的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对个人权利有效保护的共同体状态。
社会契约国家观中,权利与自由是现代政治国家存在的前提,人们出于对权利的保障而主动与彼此签订契约组成国家。但人们签订契约的原因也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权利的不受侵害,这种契约观念的产生受当时古罗马的政治民主化倾向,人们盼望通过社会契约建立一个理想的城邦政体以谋求权利与生活的保障,社会契约的建立既为国家的政治权威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也为政治权力的实行范围做出了限定。卢梭指出,“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页。
天赋人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契约国家观的形成提供了价值基础,社会契约论在早期的出发点就在于人将其先天享有的权利让渡给国家而寻求其权利得到真正的保护。但社会契约国家观同天赋人权理论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国家观不同的是,在社会契约的前提下,国家被视为“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同前引〔12〕,第21页。。它不是个人意志的简单相加,而是“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前引〔12〕,第20页。。因而,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的主要义务就不仅仅是维护单独个人的权利,而应当是维护全体共同体内部所有成员的利益。只有当个人意志符合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时,才是受到国家保护的和真正获得自由的。社会契约论国家观将一个全体人民的意志引入国家的概念之中,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公意的桥梁连接起来,国家的存在不是只为保护个人的全部利益而存在,而是保护每一个人的平等生活的权利不受侵害,只有当个人利益服从于全体人民利益的时候,国家才有义务对其权利进行保护。“国家不要对公民的正面福利做任何关照,除了保障他们对付自身和对付外敌所需的安全外,不再向前迈一步。”*[德]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林荣远、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社会契约论国家观较之个人主义国家观注意到了人并非独立存在于社会的动物,将个人看成客体孤立于社会存在是无法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的。因而,相互结合的人们互相信任地通过契约将权利让渡给一个代表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即公意。在公意之下,个人意志必须服从公共意志的要求,当个人意志与公意不一致时,就要迫使个人意志服从公意并使其真正得到自由,在这种状态下,公意有着最高权力,其思想把国家概念神化为一个伟大的公意的执行者,个人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实现自我。因而,社会契约下的国家观,相较个人主义国家观虽看到了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相互联系,却愈发将国家塑造成了一个极权主义者。国家理性足以保障其作出对全体人民有利的行为,因为这是公意的行使。与公意相对的就是个人意志,个人意志就有私利性,不能作为主权行使的前提,只有公意是至高无上的,不可能犯错的,因而,以公意作出的国家行为才是对公民最为有利的。然而,社会契约下的国家观所构想的国家观念虽是完美无缺的,但又是不切实际的。公意的现实可能性一直是卢梭观念的软肋,其所设想的公意的实现在现实生活中是寄托于一个全知全能的主体,期待其能做出对社会共同体全部有利的决断,但实际上,公意的产生和实行都是缺乏现实基础的,虽然卢梭希望通过“公共利益”的概念将公意的内涵实在化,但公意本身是没有实现能力的,还是需要借由其他动力,他称之为立法权和行政权。*同前引〔11〕,第72页。立法权属于人民并将永远属于人民,而行政权将成为公意的执行者。那么,公意能否以公共利益的形式体现出来,需要依靠行政权的行使,即便行政权能够最大程度上的实现公意的要求,“公意的权威性仍使得个人自由的施展失去了一个适度的空间。”*张龑:《没有社会的社会契约——对卢梭公意理论与传统民意观的批判性考察》,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
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考察发现,他所期待的契约合意并不等同于现代社会即公民社会的契约,而是缺乏社会层面的形而上的理论建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明确区分了公意与众意的区别,旨在说明其公意不是个体意志的简单相加——而此正是众意的基本特征,公意因异于此种粗糙性而具有了一种理想性特征,只有在真正公意的指导下,共同体才能向着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向发展,然而公意的可行性显然不能如众意那般简单,众意本身因其实存与个体意志的相加因而固然有着现实性的依托,从而在现实生活中指导和维护政体有效运行的前提大部分是众意的直接体现,然而,卢梭却要断然抛弃这种简单的可行的众意,而去寻找一个理想主义的公意,原因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众意下的国家,在现实生活中的依托表现为一个民主政体,然而民主政体也是有其缺陷的,不合理的民主或者不加限制的民主极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专制,这就是卢梭所说的众意。同时,众意还包含的一层特征就是个体性的意志,因为众意是不加区分的个体意志的简单相加,因而个体性的私欲又可能成为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敌人,这种众意又极可能做出违反真正公共意志的行为。但众意因其是一个已经经过个体意志共同达成统一意见的过程,众意相对于简单个体意见,有了一个统一性的制约,所以它可能不是必然客观上正确的,但也不能排除其主观上的正确性,不过这种主观正确性不能给国家正当性提供任何帮助。众意不像公意,不是绝对必然的善的意志,因而卢梭就要断然抛弃这种并非全善的意志对人民的统治,但这种完全正确的公意卢梭却也未能给其应然性找到一个实然的依存。卢梭虽然将公意的实现转化为公共利益的形式,但是公共利益本身与意志之间的差异也是无法忽视的,行动的意志亦仍需行动的力量得以维持,悬于空中的公意的落实,必然需要立法权与执行权这样的国家机器得以维持,因此,卢梭似乎为公意的行使找到了一个实然的依存,一个绝对客观正确性的行政权主体。公意将其意志委托于此,因而使其代表其利益而为意志找到一个行动的力量。可以洞见,卢梭如此处心积虑的希望为公意找到一个正当性存在的基础,以保障全体人民的权利都得以实现,但其理论的未能自洽也使其构建未能实现如此伟大的设想。
但是,不可否认,卢梭这一尝试是国家理论的一个飞跃,其将个人主义国家观的个体本位观念加以合理化,证成了国家权力正当性存在的理论基础在于对全体人民的全部利益的保护,此种公意是抛弃了私利的具有绝对客观正确性的理论。在这种客观正确性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其存在合理性可以被完美无缺的阐释出来。但是,卢梭的国家理论还是差了那么一小步,因而常常被人称作是集权主义的代言人,他在为公意找到一个行动力量时,将全部权利委托于一个行政权,并且将公意至上设定为社会契约的根本原则,在此种公意之下的个人自由相对于以往的个人主义国家观下的个人自由,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假定公意是可以帮助个人实现真正自由的预设与实际权力的委托行使之间的断裂,公意对个人自由的真正保障缺乏一个绝对有效的保障机制,因而在此基础上的个体自由保护又可能受制于权力行使的制约,使其自由意志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保护和发展。
社会契约国家观下的国家义务理念,旨在为全体人民的全部权利为根本出发点和目的,国家就此采取立法和执行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但是由人类这一向往社会的自然本能所导致的有意识的集体行动依然需要一个现实的行动力量,社会契约论者没有给这一权力的有效行使安放一个恰当的位置,因而可能会使这一委托面临失效的可能,虽然在此后,卢梭又提出以人民集会的形式对政体的腐化加以推翻,但是不断革命论也不是一个正常政治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妥善处理好政府与人民主权的连比例关系相对于公意如何实现这一主要问题来说,就成了后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当人权发展不断推进,人权需求从个体自由权已经渐渐推进到社会福利权,在此更看到了社会权在现代社会人权保护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当社会权已成为新一代人权,并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单纯的社会契约学说及契约观念对于保护社会权并没能提供最好的帮助。
三、现代国家义务理论:社会连带主义国家观
黑格尔提出,“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确立的存在,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8页。黑格尔不是社会连带理论的创始,但从他的哲学思想开始,社会就已成为个人与国家问题思辨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定律中,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于国家之中,认为 “国家极权非但不会侵害个人权利和市民社会的利益,反而会因为其自身的不断增强而促进个人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同前引〔2〕,第72页。社会无可否认地成为了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公共生活空间。政治共同体的社会一体化过程以从社会成员得到习惯支持为前提,而此种习惯“又与他们相互交往的方式紧密相关。”*[德]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曹卫东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在此种相互以承认为前提的条件下,结成共同体。人们“为了实现其内在本质而必须依存于政治共同体的社会构架。”*同引〔20〕,第11页。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说的公共性生活,而对于公共性概念,阿伦特曾指出公共性概念表征着共同性,“‘公共’一词表明了世界本身……这一世界就像一件中间物品一样,在把人类联系起来的同时,又将其分隔开来。”*[德]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公共性是市民社会的特点,也是社会与个体生活的界限,在公共生活中,人们通过语言的对话、交流而达成一致的共识,形成一种面向所有人的、激进包容的普遍主义的团结观,在此主体间性的公共活动中,寻求个人自主和团结性认同的协调,在这种协调一致中形成了个人与社会的连带关系。
狄骥将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以及涂尔干的社会连带主义理论引入法学体系中,在自由资本主义兴起之际,其理论为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打造了新的盔甲。其研究将国家置于法律之下,以合作国家观念替代权力国家观念等观点多少有些有失偏颇,但其将社会理论引入法学框架下探讨国家和个人问题,其功勋不可磨灭。人民逐渐认识到国家权力的享有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且认识到权力的行使必须与义务的履行相辅相成,公务概念的含义就是显而易见的了。”*[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冷静、郑戈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国家逐渐被看成具有双重人格的主体,在一定情况下行使权力,一定情况下履行义务。在此之后,国家理论的变化和发展开始动摇了主权国家和无错政府的观念,而行政权的行使仅仅是一个“顺从的哑奴”。*引自L’Humanité,Ierféverier,1906。参见[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冷静、郑戈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自此主流的国家学说开始宣扬国家角色从社会契约倡导的“最小国家”转变为认可社会干预和有效控制的政治统一体。在此后的学者们都在试图将主权概念中融入公共权力的内涵,主权的内涵已不同往昔。
自由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出于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资本家们期待和拥护着自由的国家观,希望国家在提供国防、治安等服务外,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采取放任的态度,当然,这种期待并非现代意识的体现,事实证明,包括资本在内,国家干预之手在各个层面都未曾将公共事务视为私事而置之不理。每一场变革都使社会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使各成员之间因其不同的需求而组成一个具有相同意识的民族共同体。因而,公共服务的内涵就随着时代的变迁被定义为,“任何因其与社会团结的实现与促进不可分割、而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规范和控制的活动,就是一项公共服务,只要它具有除非通过政府干预,否则便不能得到保障的特征。”*同前引〔23〕,第45页。就此可以看出公共服务内涵蕴含了新一代国家义务的相关特征,一是与社会团结的实现和促进密不可分,二是需要国家权力以规范性的行为对社会事务加以控制,此两项特征,体现了现代国家义务内外的两个面向,即对内要求国家权力行使的规范化控制,对外要求以促进社会团结为目标。
狄骥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论问题上,一直主张将主权问题由公务概念来替代,反对建立在主观权利至上的国家主权,排斥主权观念,其主要目的是要防止主权概念对主观权利的压迫,认为这个压迫永远无法解决,因而应当抛弃主权概念。在权利与权力问题无法调和的状态下,狄骥选择了抛弃主权观念而追求权利的实现,这似乎有些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笔者自然不会走的比他更远,单纯就其公共服务的国家观来看,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权力的行使和压制而在于公共服务这一立论是值得肯定的。因国家其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人格意志和主观权利,而其存在目的是立足于公共服务,那么在抛弃了主权观念、排除了权力对权利造成威胁之后,狄骥就将其国家存在的义务来源归因于对权利的服务和保障,但他所提出的权利内涵和自由主义国家观定义下的权利不同,其有着深刻的社会连带法则内涵其中。狄骥所提出的社会连带性大致等同于社会相互关联性,即“人们相互有连带关系,即他们有共同的需要,只能共同地加以满足,他们有不同的才能和需要,只有通过互相服务才能使自己得到满足,因而,如果人们想要生存,就必须遵循连带关系的社会法则。连带关系不是行为规则,它是一个事实,一切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法]狄骥:《国家、客观法和实在法》(选录),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建立在这种社会关联性下的国家,其公民的基本权利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在社会体系框架下人民为着共同的需要而相互合作形成的具有同质性的权利体系。因而,国家应当为促进公民之间的相互合作的社会连带关系而存在,国家权力的行使应当以保护弱者的权利得到更多的保护为目的。因此,政府不应当仅仅是一个权力机构,还应当是一个公共福利机构。
狄骥声称连带关系不是“行为规则”而是“事实”这一观点不免和柏克关于国家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连带关系是实存的而不是单纯的理论设计的产物,源于国家制度之根源在于民族价值与历史并与之共同成长,这种社会关联性是实然而非应然,因此其本身就不会像社会契约论一样借助一个超验的公意价值来为政治统一体的正当性加以证成。
社会连带理论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来界定国家义务的范围,从社会本位才能将国家义务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从单纯的自由权扩展到社会权的保障体系,社会本位理论对于拓宽国家义务的范围具有积极的作用,将公民权利融为一体,国家义务所保障的权利才不是片面的、私的,而是全面的、公的。现代社会的多元化使得其出现了分化性与非同质性等特点,而社会连带理论其目标就是防止这种多元对社会造成的分化作用以促进和发展社会团结,保证共同体的协调性和统一性,但是这种统一不是专制主义的,而只是以制度规范化为手段的有限的统一性与多样化的包容。团结的公民社会使得个人的参与意识、责任意识得到增强,最终回归到国家维护个人不断提出的权利要求。基于社会连带而要求的国家义务可以将有效保障社会个体成员利益的同时,促进集体的相互交流与相互承认,可以减少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消极因素,从而实现社会道德的进步。只有在人们之间自由联合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才可能催生出一种民主的与开放的社会共同体。
同样还需说明的是,现代国家义务学说,仅以个体自由维度限制国家权力干涉、或以福利国家思想为基础仅仅主张国家对公民的经济社会权利保护等都没有从完整维度上解读国家履行其职责的内在根据。社会连带主义同社会契约共同目的都是试图调和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内在关系,而社会契约却在给个人权利寻找最有利根基的基础上可能产生了集权主义的危机。相对而言,社会连带的取舍可能更加有利于维护好个人权利、集体利益与国家三者之间的有机协调。社会连带没有像个人主义那样忽视人类共同体生存的社会维度,也没有像社会契约论那样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没有社会的契约,个人与全体统一于国家,缺少了社会维度的个人权利失去了自由发展的空间。社会连带采用不那么极端的方式,将个人、社会与国家相统一,在公共空间中给予个人权利的发展以自由的空间,又以一种连带的社会团结将全体人民的权利得以统一于国家体制之下,就此在不忽视差异存在的同时,保证统一性得以维持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
当然,只从以上三种不同观点出发探讨国家义务虽然不够全面也有失偏颇,但由此角度出发可以审视国家权力、国家义务和公民权利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变化:随着现代权利的发展,国家的地位和职责也在随之不断变化,伊始于主张国家权力至上和无限制,到为抑制国家权力对权利的侵害而进行的分权,再到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相互调和的一系列理论变化中,可以看出,国家理论正在从消极忽视人民权利转向积极保护公共利益的轨道上来。
综上所述,国家义务观念得到重视发端于基本权利保障问题,基于历史与现实的需要并伴随基本权利的时代内涵而不断增加和发展,国家义务的理论基础随着其权利需要和社会现实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利用新的学说为其证成正当性,权利的内涵影响着义务所容纳和对应的事物也相应的发生变化,如国家义务对应的义务内容已不再仅仅是对自由权的保护,而是包含社会权在内的公共权利和利益;国家义务对应的义务相对人也不再仅仅是单一的个人或团体,而是共同体的全部成员。
四、国家义务理论在我国宪法中的体现及其本位
国家义务理论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奏与发展使其内涵随之日益更新,国家义务的内容随着从自由权保护向社会权保护的转向而由最初的消极义务扩展到积极义务层面,义务理论的发展伴随着人权理念不断拓展的历史而演进,而后出于规范化研究的便利,将对应于不同人权需求的国家义务做出了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的划分。
广义上讲,法律是国家履行其义务的手段,那么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全部内容都可以划归为国家义务的实践基础。从狭义上讲,国家与个人关系问题上表现为双重属性,一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而需作为的义务主体,二是为了实现治理而运用社会调整手段的权力主体。那么国家在法律中的体现就内涵了权力与义务两重属性的规范性内容。从狭义角度看待现有法律体系有关国家义务的相关内容,国家义务的基础规范体现在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中,因而,有关人权保护的条款是国家义务寻找其法律基础的起点。
(一)国家义务理论在我国宪法中的体现
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其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所体现的国家义务具有总括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宪法的内容包含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和国旗国徽首都五个部分,从篇名上可以看出,宪法的第二章是规定公民权利的主要核心部分,通过对公民权利在宪法上的确认,保证国家义务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
宪法中的权利本质上就是由宪法规定的国家不可侵犯且有义务保护的一种能力或资格,宪法将个人权利与国家义务统一的连接在一起,国家义务蕴含于宪法中的价值目标,旨在寻求平衡和协调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以实现共同体内部在保障自由与多元化的前提下每个公民权的真正享有。因而宪法中的国家义务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公民私人权利的保障,第二部分是有关公民社会权利的保障。
与公民私人权利相对应的国家义务体现在宪法对公民平等权、选举权、表达自由、宗教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权与通信自由*参见《宪法》第33、40条。的规定。国家义务对公民私人权利的规定在宪法上表现为以上8种基本权利,这也是个人主义国家观所遵循和赖以维护的八项基本权利,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不是不受限制的,相反,法律对权利的限制也是绝对必要的。这8种权利是对公民权利保护的第一个层次,即国家在私人权利保护中的义务责任体现在维护个体之间权利行使中相对平衡,并对一切侵犯到个人权利行使的行为加以限制和惩戒,同时也体现了国家自身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这就在体制层面上为国家权力的行使划定了界限,一切不利于公民个人权利行使的无论是其他组织还是国家自身的行为都应该得到禁止。可以说,从这一点来看,前8项权利是对公民消极权利的宪法规定,是对公民自由能力的宪法确认,那么以下几项内容就是宪法对公民社会权利的保障。
对公民社会权利的明文规定也体现在《宪法》第二章之中,其中包含了劳动权、休息权、退休制度、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学术自由权、男女平等权、婚姻家庭制度和华侨、归侨的权益保障*参见《宪法》第41、50条。等。积极权利是随第二代人权在后工业化的福利时代开始兴起,社会权的规定为人们提供了更多自由的可能性,但在自由扩大的同时,“提供者”也享有了更多控制和干预自由的方式,因而国家义务本质上又赋予了国家巨大的权力来实现和满足新的自由,为了防止这种自由转化成政府控制下的奴役就需要一种正确的国家义务理论导向作为基础,在此就需要一个原则性的规定来加以明确。因此,《宪法》第二章以公民的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两部分规定了我国保护人权的基本内容之外,宪法第33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权利的原则性条款,确认了国家义务对人权保障的总原则,即将权利理论建立于义务之上而非将权力凌驾于权利之上,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国家权力本身长期内含着对公民权利侵略性的危险,也无法解释社会权扩大的正当性,只有在平衡了国家权力、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三者关系之后才能为宪法之人权保障的实现形成一个有效的运行机制,对此的详解笔者将在下文予以阐明。总而言之,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是国家义务的根本起点,以尊重和保障为前提力图实现有限政府的法治是国家义务正确的、有效的实现方式。
当然,宪法对国家义务的规范还不仅仅体现在第二章中,有关国家义务的指向性规范也能在宪法序言中窥见一二。宪法序言是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着丰富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内涵,我国宪法序言的内容大致上反应了两个方面的问题,既包含了对革命建国历史的确认,还规定了立宪建国后的国家根本任务和根本原则。对革命建国史的确认保证了国家建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对建国后的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则是在实现从非常政治时期向日常政治时期转型以促进法治宪政的实现。在这其中国家义务的体现和其所针对的对象不再是单独的公民个人本身,而是面向建立主权国家的全体人民共同体,这也就表明了单纯从个体角度探讨的国家义务是没有办法容纳宪法中社会权和国家根本任务等问题的法理学依据的。宪法序言体现了宪法的政治性,而政治性是与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又不能欠缺历史维度的,宪法序言的政治现实主义也在不断的向规范主义演进,不同国家的宪法序言都体现了该国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理想世界。我国宪法序言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其规定了国家履行其义务的根本内容,而是因其确立了国家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也为国家义务的行使明确了方向并划定了界限。我国“八二宪法”及其修正案的确立,体现为一个政治宪法向法律宪法的转型过程,*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与嬗变》,载《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宪法的不断完善亦是在将政策决议上升到法律规范的框架之下,一个基于武力的国家正义必须转化为能动性的执政力量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抉择的稳固。因而,具有政治现实性的宪法序言必然包含了国家义务在现阶段的主要内容,此内容并不单以公民权利保护的形式表现,同时仍体现在立宪建国后的国家根本任务之中。
最后,在宪法的总纲和其他部分也分别对国家义务进行了列举,从公民个人角度,宪法的第13条规定了对公民合法财产权和继承权的保护;其余部分则是从国家或社会群体角度对国家义务予以规范化,如对自然资源、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的支持和发展。如果说宪法第二章是从公民角度去规范国家义务的基本内涵,那么宪法总纲则是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角度,为国家义务所应该包含的基本内容给了一个明确的总括性的表述。从宪法第四条民族政策开始至总纲结束,国家一直是宪法中各项政策的执行者,宪法有关于民族政策、国民经济、自然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科学、医疗卫生与体育事业的保障、鼓励、发展、推广的规定,可以看出这样的规范并不是在为国家权力或强制力服务,也并非从个体角度来约束国家权力的行使,而是从整体上明确一个国家为其运行和发展所要实施的一系列举措,而这一要求可以被理解为广义上的国家义务。这也就表明,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现实规范方面,国家义务的内涵都不可能仅仅限定在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和维护上,狭义的国家义务的解读既不能在应然的意义上站住脚,也绝不是实然的写照。
(二)国家权力与国家义务的辩证关系
国家权力和国家义务一向是当国家被视为人格性主体后的同一主体的两面性。权力的运用是政治统一体得以存续的根本动力,在权力的运作下国家才能以其能力和权威保证统一体不分崩离析。国家义务一向是在公民权利的相对面提出,旨在主张国家义务使公民权利得以保障和实施。
在国家义务概念出现之前,权力一直和公民权利站在相反的对立面,对于国家权力有着两种极端的看法:一是将国家当作全能者,其权力行使必须服从。康德认为,个人进入社会并未抛弃任何权力,而仅仅是抛弃了那种粗野的无法律状态的自由,“只是在形式上进入了一种彼此相依的,受社会控制的社会秩序。而从主权者法律是具有神性的出发,那么服从当前的立法权力所指定的法律是一种义务,无论他的来源是什么,即不问他的行为与目的取向的无条件的服从。结果是,一个国家中的最高权力,对臣民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同前引〔2〕,第62页。主张国家的全能性使得人民对于国家的错误行为,只能申诉和反对不能积极反抗。与此相反的另外一种极端观点是认为权力的行使永远是对公民权利的压制,要想真正实现公民权利,唯一的办法就是限制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压迫,以保证公民权利自由而充分的实现。向国家权力施加法律限制的根本原则与国家主权原则存在着致命的冲突,国家权力只能以一种有限的和相对的方式而存在,而卢梭是给人民套上链锁的同时又宣称人民享有无上的权威,并且在强迫人民保持沉默的同时又以人民的名义来说话。主权是需受到限制的,国家权力更需要受到限制,世界上没有哪种权威是不受限制的。而这一主权原则建立在那些正义和个人权利来进行确定的限制之上。*Benjamin Constant,Cours de politique constitutionnelle,I,pp.187~188.参见[法]狄骥:《法律与国家》,冷静、郑戈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实际上,在国家义务概念出现的很长时间内,国家法理论研究者依然将国家义务概念与国家权力放在制衡的位置上,认为对公民保护只能强调国家义务以克制国家权力的实行,国家义务作为克制国家权力的手段来制约着其对公民权利的暴力性攻击。
看到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保护起到积极性作用是在国家义务概念内涵逐渐演化的过程中发生的。当国家义务的内涵被划定为消极的尊重和保护义务时,不要求国家对公民权利做出任何积极行为的时候,国家权力应当消极被动的对待公民权利的时候,对其限制和分权为主要的方式。当国家义务内涵逐渐变成积极主动的要求国家履行给付义务时,国家权力的威力对权利保障的正面作用才渐渐体现出来。“一项法律义务并不是一项要求人们去做某件本身是好的事情的义务,而是一项去做具有社会价值的事情的义务。”*同前引〔2〕,第217页。现代法治将国家权力发展成国家义务的工具,国家义务成为国家权力的目的,国家义务为国家权力的存在提供正当性。二者之间有着辩证的逻辑关系。首先,宪法是国家权力的授予者也是国家权力的制约者,其制约就体现于宪法中的国家义务。宪法中国家义务内涵的不断扩展使国家权力行使的边界得到明确而清晰的界定,在权力界限之外行使的权力就是对权利的侵犯和义务的违反。主观权利需要客观法来保证,国家义务的规范是明确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国家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履行其义务,其中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就是一种普遍的方式,因而,对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也是一种履行义务的手段,权力的分散可防止其强大而导致暴力,。其次,国家义务的履行需要国家权力的存在。没有执行力保障的义务是无法履行的,正如无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没有办法签订有效的契约一样,没有行为能力的国家也没有办法履行其国家义务,而国家的行为能力的体现就在于国家权力的有效行使。缺乏了强大执行力的国家只能被认为是一项并不持久的事业,因而“在劫难逃”。*[美]哈维·C·曼斯菲尔德:《驯化君主》,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体现国家权力积极性的执行权,被许多人抱怨其灾难性的强大力量,最终将其与专制同日而语。这是他们在没有发现这一被掩盖的事实——即国家权力积极行使的必要性——之前对国家权力的无故抨击。国家权力本身所有的强制力和威权为国家义务的履行提供了保障。因此,国家权力对国家义务的履行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在权力存在的前提下,义务才能得到完整而充分的履行,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和保障,义务就像无根之木一样,对权利的实现根本束手无策。以义务性为导向的国家权力行使才能从根本上将权力与权利二者之间相互平衡,以权力为导向可能造成对公民权利的忽视,并且义务的指向性可以规范权力的相对自由性,因而从规范意义上来制约国家权力的不当行使。现代公法背后应该蕴含这一个命题,即“那些事实上掌握着权力的人并不享有行使公共权力的主观权利,他们负有使用其手中的权力来组织公共服务,并保障和支配公共服务的进行的义务。”*同前引〔2〕,第221页。
(三)国家义务的社会本位
正如前文提出,现代法律中的国家义务已不能简单的限定在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方面,在社会层面,作为人民共同体,国家对其也有着相应的保护责任,如果我们将其最终目的推及到国家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实现个人权利的保障,那我们就陷入了个人主义国家观论证的怪圈,个人主义下的国家理论虽然可以将一切权力的行使等问题归结为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但是其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没有给国家权力的积极行使一个正当的地位,而将权力视为个人权利自由的最危险的敌人,因而要求国家权力对此应当以分权来控制,以个人权利至上为核心。
自中世纪后期人类理性觉醒以来,以天赋人权来反对统治者对个人压迫的思想家们无不发现,单独个体理论和力量不足以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行,个人本身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社会本能与个人本能在家庭里得到混合并相互调节,家庭和社会各有其职责,但目的是一致的。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目的并在不知不觉中相互合作着,这种合作是社会得以产生的根源。”*[法]孔德:《实证主义概论》,转引自张宏生、谷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页。人类在这种相互联合下才能保证其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中,家庭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单位,而保证人从出生到死亡,在其没有行为能力和行为能力减弱的时候,都能在这个社会中得以生存。人无法脱离社会,最基础的原因是人无法脱离于家庭而存在,在家庭之中,人才能在出生开始得到其生存最基本的供给和需要,而又在其老去时得到最基本的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存在,为人类生活提供了一个相互合作的环境,人们依靠着这种社会连带关系得以生存,这种从家庭开始的连带关系,在融入社会之中渐渐被注重实际的法律制度所取代。这也是涂尔干在其社会分工论中所提出的机械连带向有机连带的一种转化。*《社会分工论》中指出,人类社会有两种连带关系:机械连带和有机连带。机械连带是建立在相同的价值判断、共同的社会约束、对共同传统的尊重之上的;它就象分子构成结晶体一样,个人被并入一个大的单位;它主要存在于只有简单劳动分工的社会中。有机连带是建立在专业和劳动分工的高度发展、各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的相互依赖之上的;它就像有机体一样.个人、群体是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它主要存在于现代文明社会中。参见[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3~92页。人们的生活逐渐由简单的家庭与传统约束向社会群体的相互依赖和劳动分工而转变。当社会连带融入法律规范之中,其社会行为就有了国家强制力的约束和保障,在法律框架下的社会行为已不再是单纯的家庭生活,而是一个社会整体的合作与协调,那么相互联系的人们之间处于各取所需的意图而合作,在此国家就有了协调和分配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责任。这种联合使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而不至于崩溃,也使社会得以有序的运行。那么在此连带关系下,国家就被赋予了保障共同体内部成员生存和发展权利得以实现的义务,也即体现了国家义务的社会本位。
以社会为本位的国家义务,其内涵就不仅仅包括尊重和保护义务,而且包含着给付义务,这也是以社会本位的国家义务观对自由主义国家观的修正。尊重义务和保护义务都产生于自由主义盛行时期,对自由的崇尚以及认为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但权力本身而仍对个人权利的实现产生威胁,并且否认国家对个人生存财产的积极义务。尊重义务的内涵限定于对公民权利的不得干涉。因而此种意义上的国家义务对应着公民的一种防御权,“基本权赋予人民一种法的地位,于国家侵犯其受基本权所保护的法益时,得直接根据基本权规定,请示国家停止其侵害,籍以达到防卫受基本权利所保护的法益,使免于遭受国家恣意干预的目的。”*许宗力:《基本权利的功能与司法审查》,载《宪法与法治国行政》,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56页。尊重义务大部分是通过立法的行使得以实现,通过法律的形式宣示公民权利的不可侵犯。保护的义务则要求在国家自控的基础上,对他人的权利侵害行为的阻止,这种阻止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其他有效的救济来进行。如果说尊重义务中国家处于相对较为消极的不侵犯角色之中,那么保护义务中国家对人民自由的保障行为已转变为一种救济,即以一定的制度设计与实施来促进个人权利的实现,即以立法为核心,司法与行政相互配合。保护义务以积极态度承认并对公民权利进行相应的保护,但这样保护仅限于个体自由与防止第三方侵害方面,并没有将社会福利等纳入公民保护的范围内。
社会契约国家理论下的政府因其本身内涵的人民性,因而人民在此既充当了主权者的位置,又成为了享有权利的个人。全体人民为自己的权利得到实现而行使全部权力来调控国家行政手段,这无疑为国家理论提供了一个最为保障自由的新的方式,但是庞大的权力行使不能要求每一次的抉择都由所有人民出场,仍需要一个可以代表全体权利人的执行机构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谋取福利,在社会契约下虽然发展出了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基础,但是并没有给权力的积极行使提供任何机会和理论上的要求。给付义务的产生也是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在宪政国家职能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给付义务是“国家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为公民提供某种利益的义务。”*张翔:《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从基本权利分析框架的革新开始》,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给付义务的履行旨在所有个人能够获得保障其生存的最低条件,帮助和促进人民享有幸福生活。给付义务作为一种国家的积极义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国家的消极义务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给付义务能动的将国家权力用于创造权利行使的条件和环境,让平等享有权利成为可能,在此处的平等不是唯一的权利形式,而是权利实现的一种方式,也只有平等的、实质享有的权利才是法治国家所追求的最根本的目标。
国家形态逐渐从自由法治国转型社会法治国,德国成为实现国家能动主义的先驱,为了调和资本主义的劳资冲突矛盾,国家在经济调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调控作用,主要表现在一系列社会保险法案的颁布。在法案颁布其后,1918年德国魏玛宪法亦对部分社会性权利加以基本法上的确认,这一系列立法行为将给付义务以规范的形式确立了下来。给付义务与以往的保护和尊重相比较,改变了以往消极的不干涉方式,相应地增加了积极地推进社会政策等手段,而不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给付义务的产生离不开宪政国家转型时期的社会思潮,除了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会连带主义国家观的形成亦为国家给付义务提供了正当性的来源。社会连带主义国家观下个人与社会密切相关,“国家职能从本质上说,除了消极地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使公民获得私人利益外,还应当积极地扩展范围,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公共利益。换言之,国家除了给个人提供消极权利,即因国家无所作为得到的利益外,还应该为个人提供积极的权利,即由于国家的积极作为而得到的利益。”*俞可平:《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在此意义上的国家与个人本身并不是相互制约的关系,也不仅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国家的繁荣与个人的权利实现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共同进步、相互促进。
从自由权到社会权——权利内涵的不断扩大,给付义务总是涉及一个最低标准的问题,即国家义务的最低限度,联合国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提出“每个缔约国都有责任承担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以确保使每项权利的实现均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水平。”*Committee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e Rights,General Comment No 3 1990,In HRJ/GEN/I/Rev,6,12 May 2003,p.16.给付义务后于尊重和保障义务出现在宪法的规范中,但在后期发展中成为国家权力行使的目标,相对于具体落实性的公民个人权利原则,给付义务包含了一种从应然向实然转化的过程,也可以说,给付义务在规范中的表现包含着可变性,这种可变性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即在不同国家对于给付义务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它并不像尊重义务和保障义务在不同国家可以适当的形成价值趋向等量的标准,给付义务却可能随不同国家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标准。相对于尊重义务和保障义务的立法权威保障,给付义务的实现则需要依赖于行政权的行使。行政机关的给付行为既是出于积极义务的履行目的,也是给付义务的实现方式,给付义务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行政权的行使方向和力度。
当然,通过传统权利类型划分来对应国家义务的基本内容没有办法包含现代国家义务的全部内涵,在当今的宪法理论与实践中,基本权利的分类之间出现了相互重叠,*see, Henry Shue,“Rights in the Light of Duties, in Hum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eter G. Brave & Douglas Maclean (eds),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79, p263-264. Henry Shue观察到了一关于基本权利的“双重二分”(Double Dichotomy)的现象并且认为应当寻找“更好的思考权利问题的概念框架“(a better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inking about rights)。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国家的给付义务——从基本权利分析框架的革新开始》,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因而基本权利的性质也并非单一化。国家义务的根本内容也不能因为权利类型的单一性而忽视其内涵的复杂性。国家义务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其内涵日渐丰富。以社会为本位的国家义务,在历经个人本位注重尊重和保护义务后,扩延至积极的给付义务,国家在社会与个人的作用中已不再是一个消极的角色,而是一个积极的社会资源的调控者。
结语
国家义务内涵如此广阔,是否能容纳一切国家行为,或者是否会出现以国家义务为幌子而实施的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如果没有给国家义务划定一个边界那么公法之手也可能会伸延到危害私法范围下的公民生活自主性。从国家义务这一概念和内涵的演进来看,国家义务是依附于国家权力而运行的,国家权力的存在才能推动国家义务得以履行。但国家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强力可能会对权利造成压迫,因而应当划定国家义务的范围,以防止国家借用其权力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首先,这就要求国家以其理性对其权力的行使进行划分,以保障基本权利的优先性。国家以其理性行为实现权力和利益的均衡,限制国家权力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方式之一,也是有效履行国家义务的宪政手段。其次,虽然公民基本权利类型化对应的国家义务不能包含其全部内涵,但在一定程度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也为国家义务的具体化提供了划定边界的依据。但是,国家义务“边界没有先验的模式,必须动态地回应社会和经济情势变迁,确定边界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工程,而是个相对静止但却具有‘回应型’、‘开放式’特征的过程。”*袁立:《公民基本权利视野下国家义务的边界》,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1期。规则的规定是僵硬的,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国家义务的界限仍需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来加以限定,权利的行使要受到法律的限定,那么权利的边界也就决定了义务的边界。并且,为了防止国家权力与人民利益之间产生冲突,应当要求法律的行使都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原则,在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国家行为需要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问题进行理性的安排,以保证基本权利不会丧失其生存空间,对其实现尽可能的保护。这就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要客观、适度并合乎理性。国家权力的能动行使首先不能逾越法律的框架,那么就需要立法权为国家权力提供一个合理范围,要衡量公共利益目标与个人合法权益的适度比例,权力措施的实现必须以实现其目的为导向,至少应有助于实现其目的。“权力往往以所谓目的之正当来为一切不正当的行为狡辩,致使权力的腐败变质是如此容易,而且又是如此不知不觉,如此不易被察觉。”*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48页。为了防止权力行使的裁量如同戴雪所言之“专断”的代名词,但又不能将权力的行使控制的毫无生命力,这就需要为此提供一个合理性边界,那么除了比例原则之外,权力行使的司法救济也不为是今日之所需。
总而言之,国家最终无法吞没个人与家庭,国家的能动行为应容许自由和不悖于公共利益。以义务为导向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强调会吞噬了自由的空间,但无限制的义务行为所倚仗的能动性也可能让期望实现的自由消失殆尽。对国家义务的强调不等于宣扬全能主义的国家模式,一切极端主义的做法都会削减其权威和效率,而无法促进个人的自由与幸福。国家治理就是在放眼历史与经验中寻找影响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在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关怀的作用下,协调现存制度结构的冲突,找到一个国家进步的进化之道、改革之道与民本之道。
崔寒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