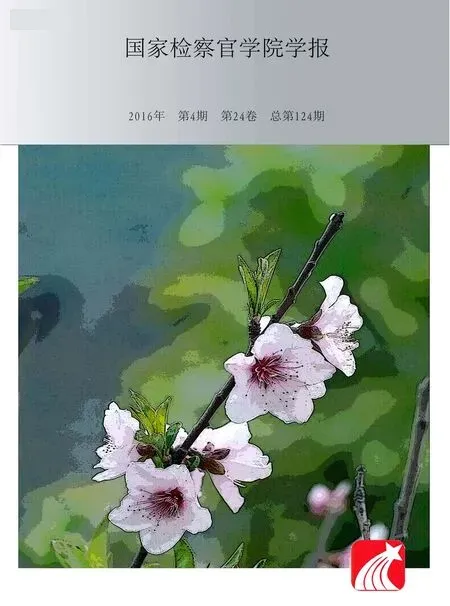法国“机关”犯罪立法述评及其启示
康均心 郑 佳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法国“机关”犯罪立法述评及其启示
康均心郑佳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法国“机关”犯罪理论研究和立法规定不仅具有开创性,而且在司法实践获得成功。法国新刑法典将“机关”犯罪的犯罪主体限定为“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将入罪条件确定为“在进行‘可签订公共服务委托协议’的活动中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立法安排不仅绕开了“国家主权原则”的难题,对于减少司法适用的不确定性也发挥了积极的效用。然而,我国“机关”犯罪立法之初就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机关”犯罪立法和实践的矛盾日显突出。因此,对法国“机关”犯罪立法经验加以总结和借鉴,对于完善我国“机关”犯罪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机关犯罪公共服务行政合同刑事责任
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并没有法人犯罪的相关规定。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法人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攀升,法人在商事、经济活动中的严重违法行为逐渐增多,法人刑事责任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20世纪七十年代起,法国开始了对刑法典的全面修订工作,法国刑法典修改委员会随即提出应当在广泛的范围内承认法人犯罪。然而在修正案的拟订过程中,法人犯罪主体的范围却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其中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机关”应否成为犯罪的主体。经过近10年的权力博弈和不断修订,法国在最终形成的新刑法典中,对“机关”犯罪主体以及“机关”犯罪的归责条件做出了不同于任何国家的立法安排,开创了大陆法系的先例,实现了重大的立法突破。
鉴于我国“机关”为牟取暴利进行走私犯罪活动十分猖獗的现实情况,1987年1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在《海关法》第47条明确将“机关”规定为走私罪的主体。此后,在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中“机关”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得以明确。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丹东、烟台、海南的汽车走私案,还是引起广泛关注的新疆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乌铁中院)受贿案最终都因追究涉案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会引起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放弃了将该机关作为刑事被告人,转而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司法实践无法贯彻立法规定的事实至少说明了相关立法的合理性存疑。本文从法国“机关”犯罪主体的厘定出发,对法国“机关”犯罪的成立条件进行理论剖析及实证研究,希望以问题意识为思维导向,以法国“机关”犯罪立法的中国化为视角,为我国机关犯罪立法完善和发展提供可兹借鉴的经验。
一、法国“机关”犯罪主体的厘定
法国刑法典将“机关”作为犯罪主体置于刑事司法之下的规定是长期酝酿的结果。根据法国国民议会的提议,刑法典修改委员会曾在最初的刑法典修改草案中提出法人不论性质如何均可受到刑事责任追究。不过国务委员会随后根据权力分立原则的要求,以行政权不应置于司法权之下为由否定了“机关”的刑事可罚性。经过十余年的博弈,国民议会与国务委员会达成妥协,在最终形成的新刑法典中以附条件的形式确认了“机关”的刑事责任。准确界定“机关”犯罪主体的内涵以及分析“机关”犯罪立法背后的理论基础是进一步剖析“机关”犯罪成立条件的前提。
(一)“机关”犯罪的主体范围厘清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机关”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但我国学界对于“机关”犯罪的主体范围则一直众说纷纭,总的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支持广义论的学者认为,作为犯罪主体的“机关”包括国家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以及执政党的机关;而支持狭义论的学者则认为,作为犯罪主体的“机关”主要是指行政机关,一般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我国学者在“机关”犯罪的主体范围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我国的刑法规定“言而不明”。这种不明确的立法规定既不利于公众形成确定行为预期,也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反观法国新刑法典的规定,立法机关在规定“机关”犯罪的犯罪主体时使用了 “l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et leurs groupements”的表述,即“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笔者认为,法国刑法将“机关”犯罪的主体范围明确限定为地方行政部门的立法选择与我国狭义论者的观点相契合。此外,对于“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的建制相关法令也有明确的规定。具体来讲,根据1982年3月2日法国国会通过的Loi n° 82-213 relative aux droits et libertés des communes,des départements et des régions ( 第82-213号《有关市镇、省和大区的权力和自由法案》)*法案全文载法国参议院网https://www.senat.fr/application-des-lois/a8081010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月20日。的规定,地方行政机关(l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的建制包括市镇、省、大区以及海外领土(根据法国1958年10月4日生效的《宪法》第72条的规定,法属海外领土也属于法国的地方行政机关,包括4个海外省、4个海外领地以及2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地方行政区) 。*A.LEVY,S.BLOCH,J.BLOCH,La responsabilité pénale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de leurs élus,de leurs agents,LITEC,1995,pp.11.同时,根据该“法案”第164-1条、第165条、第167条以及第168条的规定,地方行政机关的联合团体(les groupements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包括县(C.communes,art.L.164-1 et s.)、城市共同体、市镇共同体、城郊共同体以及市镇自治会。其中市镇自治会又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单一行业自治会(Syndicat de Commune à Vocation Unique);另一种是多行业自治会(Syndicat de Commune à Vocations Multiples) 。*E.FORTIS,La responsabilité pénale des personnes morales de droit public: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et établissements publics,RSC,2004,pp.341.综上,法国“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由上述具有法人性质的行政单位构成。因此法国新刑法典中规定的“机关”犯罪的主体范围应当是包括上述所有行政单位在内的机关组织。
(二)“机关”入罪的立法逻辑
一般认为,法国新刑法典将“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作为“机关”犯罪的主体纳入刑法规制的立法规定是权力角力后的产物,从功利主义的价值导向出发,这种立法安排既能够满足遏制犯罪的现实需要,也能够规避基于“公权力特殊性”的反对之声,具有现实意义。其立法逻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性。
1.“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具有类市场主体属性
与立法、司法等机关的行为只具有公共权力专属性不同,尽管“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在行政执法或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行政行为也具有公权力专属性,但除此之外,其另外一项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如果某项公共服务能够以订立行政合同的方式委托给私法法人 ,那么这种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便可视为类似于私法法人的经营管理行为,提供公共服务的“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便可视为具有类市场主体属性。因此,当“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在提供上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实施了犯罪行为时,由于其行为并不具有公权力专属性,不享有刑事豁免权,所以应当为其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这种犯罪行为进行定罪处罚,无涉国家主权原则,亦无碍于权力分立原则。
2.“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入罪体现平等对待原则
平等对待原则是当今市场经济规律的属性,是现代法制的基本准则。尽管在地方行政部门进行具有公共权力专属性的活动时应当享有刑事责任豁免权,但当“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在从事私法领域的活动时,其角色应当视同私法法人,当其实施犯罪行为时当然应当与私法法人一样承担刑事责任,这是法律的平等适用原则的内在要求。因此法国在新刑法典中将“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规定为法人犯罪的犯罪主体,避免了使公法法人和私法法人受到差别对待,遵循了平等对待的法律原则,立法意图正当且纯粹。*陈萍:《法国“机关法人”刑事责任述评及其借镜》,《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1期。
二、法国“机关”入罪条件的剖析
从《法国新刑法典》第121-2条的规定来看,立法机关一方面认可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又将刑事责任的范围限制在犯罪行为发生在“从事可以订立公共服务委托协议的活动时”的条件之下。因此,地方行政部门在犯罪行为发生时是否亲自在经营某项可以委托的公共服务,以及涉案活动本身是否存在订立委托协议的可能性是判断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的重要标准。
(一)“公共服务”理念的兴起
19世纪的法国经济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获得巨大发展,国家逐渐突破“守夜人”式的政府模式,日益积极地介入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领域,包括建设铁路、公路网路、设立大量公立教育机构以及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机制等。*参见 Jacques Chevalier,Le service public,9ème édition,PUF 2012,pp.10-11.国家在实施此活动时的行为手段也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强权命令行为,相反采用了大量类似于私人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这些行为一般被称为公共经营管理行为 (la gestion publique),显然,此时国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公共服务”理念逐渐形成。此理念确信行政机关对公共服务的经营管理相比于私人企业更富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私人企业被视为只追求利润,而公共组织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机体的需求;一方是自私自利和牟利的精神,另一方则是利他主义与大公无私的精神。”*参见Jacques Chevalier,précité,pp.40-41.同时,行政机关对公共服务的经营管理相比于私人企业经营管理在社会保障层面具有更高的效率,因为其保障“每个人的平等享用,并一最低的成本运作,公共服务最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减少社会的不平等。”*同前注[6],第41页。因此在这一时期,“公共服务”专门由行政机关提供,没有委托给第三方私法法人的可能性。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国家的“公共服务理念”也随着市场竞争观念的渗入逐渐发生了转变。事实上,一切公共服务的经营管理专属于行政机关的模式缺乏竞争机制,容易使得行政机关怠于作为或效率低下;反之,公开透明的良性竞争环境不仅有利于规范“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行为,而且有利于保障“公共服务”的质量,因此,在一定范围内放开“公共服务”经营管理,使其面向市场中的经济运营商,使 “公共服务” 从传统的封闭式到兼具竞争性是这一时期 “公共服务”理念的重要转型 。
(二)“公共服务”可委托性的认定标准
法国国务委员会在最初的阶段仅仅采取列举的方式确定了若干可以进行委托的公共服务活动,比如公共交通、学校食堂、生活垃圾回收、供水、废水回收和利用、港口和机场基建、停车场、失物认领处和市场摊位的管理以及议会中心和展览场所的经营。*参见Rep.Min n.32824:JUAN Q,4 mars 1996,p.1194.到2002年,法国最高法院刑事法庭以个案确认的方式对公共服务的可委托性作出了规定:在相关判例中,法庭在确认了跨市的公共屠宰场*参见Cass.crim.,23 mai 2000,Bull.crim.n°200,Rapp.C.Cass.2000,p.444.、滑雪场*参见Cass.crim.,14 mars 2000,Bull.crim.n° 114.以及市剧院*参见Cass.crim.,3 avr 2002,Bull.crim.n°77,Rapp.C.Cass.2002,p.586.RJDA 2002,n°1012.的管理活动是可以委托的同时,也确认了课外发现课堂*参见Cass.crim.12 déc.2000,affaire du Drac,Bull.crim.n° 371,cette Revue 2001.157,obs.Y.MAYAUDET,p.372,obs.B.BOULOC,2001,n° 43,obs.M.VÉRON.、公共教育服务*参见Cass.crim.11 déc.2001,D.2002.IR.373 ; cette revue 2002,p.321,obs.B.BOULOC.是不可委托的。
随着类似判例的数量逐渐增多,刑事法官认为逐案评估地方行政部门的公共服务活动是否具有可委托性效率不高,因此,他们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即清晰界定涉及公共权力活动的范围,所有涉及公共权力的活动都是不可委托的。除此以外,其他活动被认为是可以委托的公共服务。据此,地方行政部门将涉及公共权力的不可委托的活动归纳如下:
(1)地方行政部门以国家名义、为国家利益而实施的活动无不可委托。例如,户籍管理、组织选举、发放驾照等。这与《法国刑法典》第121-2条第1款关于国家刑事责任例外的规定相契合。
(2)涉及公共权力特殊性的活动不可委托。例如,犯罪侦查活动*参见CE,1er avr.1994,commune de Menton,Leb.p.176.和公共道路中的监视活动*参见CE,19 déc.1997,commune d’Ostricourt,req.n° 170606.。
(3)法律明确规定专门授权给地方行政部门的公共服务管理活动不可委托。比如法国《地方行政部门一般法》中规定,太平间、消防、地区档案的管理都属于这类活动。这些活动虽然也属于公共服务活动,不具有公共权力特殊性,但因法律的特别规定而不可委托。
显然,对于发生在上述不可委托的活动中的犯罪行为,“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不负刑事责任;除此以外,“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应当为发生在提供可进行委托的公共服务过程中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三)“公共服务委托协议”市场竞争属性的标志
在法国,“公共服务委托协议”的概念最早见诸于行政法,一般理解为行政机关订立的行政合同。行政合同是公法合同,在到达刑事领域之前,不由私法支配,而是适用行政法的规则,诉讼关系由行政法院管辖。可以说行政合同是法国行政法上富有特色的一种制度。*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190页。
但从法律规定的层面上来看,行政法并未就“公共服务委托协议”的含义给出具体的定义。因此有观点认为《法国新刑法典》在第121-2条第2款中规定的“公共服务委托协议”的指向不明确,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可能性。*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曾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适用《法国新刑法典》第121-2条第1款的规定,因规定中的“公共服务委托协议”的概念不够明确,可能涉嫌违反《法国宪法》第61-1条的规定,而致案件的审理暂停。同时,第121-2条第1款关于“公共服务委托协议”的规定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也被提交至宪法委员会,称为宪法优先性问题(QPC,Question Prioritaire Constitutionnelle)。参见Cass.crim.,11 juin 2010,n°09-87.884 QPC:JurisData n°2010-008735; Dr.pén.2010,comm.111,obs.M.Véron.该问题被提交至宪法委员会进行裁决。尽管最终宪法委员会判定,根据已有的法院判例,足以让人了解“公共服务委托协议的”内涵和外延,不认为刑法典第121-2条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参见Frédéric Desportes et Francis Le Gunehec,droit pénal général,ECONOMICA,2012,p.556.但可以明确的是,此聚讼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服务委托协议”的概念没有成文化和法定化。
最终,法国第2001-1168号《经济及金融紧急措施法(Loi MURCEF)》解决了上述问题,终结了长期以来“公共服务委托协议”没有成文法定义的历史。具体来说该法引进了《地方行政部门一般法》第1411-1条的规定并结合此前的相关判例,将“公共服务委托协议”界定为“公法人将其负责的公共服务管理活动委托给另一公法人或私法人的协议,其中受托人所获报酬应基本与其服务经营状况相一致。”*参见l’article 3 de la loi MURCEF,载法兰西法律网http://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cidTexte=JORFTEXT000000221912&dateTexte=&categorieLien=id,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2月5日。该定义强调受托人所获报酬与其提供服务应具有对等性,并将其作为判断行政协议是否可以视同私法人间的平等协议的标准,以及进一步判断地方行政部门的行为可否视同私法人的行为的前提。不难看出,立法者从市场竞争的理念出发,将需要服从于公开透明与强制竞争规则的合同特征引入行政合同之中,是地方行政机关在提供可委托的公共服务时具有市场主体性的标志。
(四)入罪条件的司法考察
司法实践是立法实施情况的客观反应,是检验立法可行性的关键。 法国刑法典改革距今已有二十余年。尽管在法国最高法院公布的刑事判决中,对“机关”提起控告的案例并不多见,但从对这些案例的分析中可知,最终判定“机关”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的焦点在于“犯罪行为”是否发生在可归属于“地方行政机关”的活动期间以及该活动的性质是否属于“可委托的公共服务”,这是判断犯罪行为应否归咎于“地方行政机关”的关键。对此在法国司法实践中关于橘园、剧场管理和公共教育服务的经典案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在橘园案中,斯特拉斯堡市(La Ville de Strasbourg)自行承担管理和维护坐落在该市某一橘园的责任。同时允许游人自由出入该橘园。当橘园内的老树因安全管理不善从高处倒塌造成一名未成年人受重伤的案件发生时,法院对于能否根据《刑法》第221-6条非故意伤害生命罪追究市政府的刑事责任的问题给出了肯定答案。首先,市政府对橘园的管理活动属于公共服务管理活动。其次,该活动不在法律或者法规规定禁止委托的范围之列,因此可以由私法法人参与。由于该橘园的经营管理权转让给有资格的受托人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阻碍,因此从本质上来讲,该市政府对于橘园的管理和维护属于可订立委托协议的公共服务。据此,法国最高法院刑事法庭的最终判决是,该市政府对于橘园中发生的事故存在疏于管理的过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参见Cass.crim,7 sept.n°10-82.119:Dr.pén :2011,comm.32,obs.M.Véron.
与此案类似,在比耶夫尔-利耶尔镇上( La Communauté de Communes du ays de Bièvre-Liers)*比耶夫尔-利耶尔市镇,位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市(La Ville de Grenoble)。,一头奶牛在一个陈旧且安全措施不完善的屠宰场内被追逐引起交通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判定应当根据《刑法》第221-6条非故意伤害生命罪追究该镇政府的刑事责任。其判决理由是,该镇政府对屠宰场的经营管理活动在性质上属于提供公共服务,与橘园案相似,该公共服务活动也未被法律或者法规规定禁止委托,因此对于屠宰场的经营管理也可以交由私法法人执行。由于该镇政府对屠宰场的经营管理权可以自由转让给其他的受托人,因此从本质上来讲,该镇政府对屠宰场的经营管理也属于可订立委托协议的公共服务,可以认为该起人员伤亡事件正是由于该镇政府没有派出管理人员对屠宰场的安全隐患进行修缮所致。该镇政府在案件中存在漫怠疏忽的过失,因此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参见Cass.crim.,14 déc.2010, n°10-80.591:Dr.pén.2011,comm.32,obs.M.Véron.
但在Drac河惨案中,格勒诺布尔市6位小学生由于Drac河水位陡然上升而不幸溺水身亡。事发当时,小学生们正由学校教师和一位由格勒诺布尔市市政府聘用的活动组织专业人员陪同,在Drac河河床上进行“发现课堂”活动。案件发生后,两位涉案自然人均受到刑事处罚。但对于格勒诺布尔市市政府是否应当接受刑事处罚的问题却产生了巨大争议。格勒诺布尔市轻罪法庭和上诉法庭都认为“发现课堂”作为教育服务也可以由私法法人提供,从本质和法律上来讲该活动都是可进行委托的,因此应当追究市政府的刑事责任。但是,最高法院刑事法庭却在最终判决中认定市政府不承担刑事责任。其理由是:法律明确规定专门授权给地方行政部门的公共服务管理活动虽然也属于公共服务活动,不具有公共权力特殊性,但由于《法国教育法典》明确将公共教育服务活动授权给各级地方行政部门,因此从性质上来说该活动是不可委托的。由此可见该案中,“机关”成立犯罪主体必须符合的法定入罪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法国最高法院刑事法庭判定在“发现课堂”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格勒诺布尔市市政府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参见Cass.crim,12 déc.2000:Bull.Inf.C.cass.2000,n°529,p.3,rapp.Mme FERRARI,concl.Mme COMMARET; Bull.Crim.,n°371.
由此可见,法国“机关”犯罪的刑事立法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良好运行的关键在于法国刑事法院对于“机关”入罪的法定条件——“犯罪行为发生在提供‘可签订委托协议的公共服务’的活动时”的认定已经基于现有的判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简而言之,笔者认为法国刑事法院判断刑事责任是否归属于“机关”时,会从具体案件是否发生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公共服务是否可以进行委托以及委托协议是否具有等价有偿性三个层面逐一考察。
三、法国“机关”犯罪立法的启示
立法的完善总是会历经“现有立法——理论研究——反思立法——立法改革”的过程。自97刑法以来,我国将“机关”列为单位犯罪主体的立法规定在刑法学界引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对于我国“机关”犯罪立法中犯罪主体不清、成立条件不明的缺陷,我国学者间也达成了初步的共识。有的学者认为应当肯定包括国家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以及执政党的机关在内的所有机关的刑事责任,但该观点难以逾越“国家主权原则”这座大山;有的学者建议将“机关”直接解释为“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却忽略了立法采用的是“机关” 这一一般性称谓,如果径自将其限制成“地方国家行政机关”似乎又不够谨慎;还有的学者建议将“机关”从单位犯罪的犯罪主体中剔除,却忽略了“机关”犯罪的现实性,也不利于融入先进国家将“机关”纳入刑法规制的立法环境。因此,这些学术观点都无法完全从理论上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对法国“机关”犯罪立法的研究过程中,笔者深刻意识到,尽管从立法结果来看,法国在“机关”犯罪的立法问题上是以抗制和预防犯罪的功利价值目标为导向,但其立法的理论基础不可谓不夯实,同时法国刑法典对“机关”犯罪的犯罪主体和“机关”入罪的法定条件的明确规定,也使得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能够有序衔接。因此法国在“机关”犯罪问题上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对于我国“机关”犯罪的理论研究和立法修正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我国“机关”犯罪立法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国家机关作为市场主体融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由此而产生的权力寻租、权力异化等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将“机关”的犯罪行为纳入刑法规制之下既有利于遏制犯罪行为的蔓延和扩散,也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是一种务实的表现。然而我国刑法的总则部分仅对“机关”犯罪做了概括性的规定,这种笼统的立法模式虽然看似有很强的包容性,实则过于抽象。这种立法上的模糊状态体现在主体范围和入罪条件的认定两个方面,是造成“机关”犯罪的主体范围模糊以及“机关”犯罪的认定条件缺位的直接原因。
1.“机关”犯罪的主体范围模糊
一般认为,“机关”是指以主持、实施、保障、参与国家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以及社会事务的管理为基本职能,由国家财政维持其职能活动,并具有法人资格的特定组织。*李玉成:《单位犯罪中“机关”主体界定的若干问题》,《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我国的国家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以及执政党的机关的职能范围、组织特征和经费来源都与上述定义相吻合,因此“机关”的范畴应当包括上述所有机关在内。 由于刑法在规定“机关”犯罪时未对犯罪主体进行限制性修饰,因此理论上,刑法中“机关”犯罪的主体范畴应与上述“机关”保持一致。
然而从国家机关的职能和功用来看,国家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以及执政党的机关的行为都只具有公权力属性,由于公权力具有特殊性,涉及公权力的行为享有刑事豁免权,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以及执政党的机关都不能成为“机关”犯罪的犯罪主体。我国行政机关的职能具有双重性,他们在行政行为以外的另一项重要职能是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该职能并不具有公权力属性,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的行政机关不能享有刑事豁免权,因此当其在提供公共服务的经营管理活动过程中实施了犯罪行为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换言之,事实上能够成为“机关”犯罪主体的仅有行政机关。不难看出,我国对于“机关”犯罪主体范围的理解在理论和事实两个层面上形成了巨大的鸿沟。此种差异是我国“机关”犯罪立法规定过于粗陋所致。这种情况下的立法规定也失去了指向和导引意义。
2.“机关”犯罪的认定条件缺位
我国刑事立法在“机关”犯罪认定条件的问题上也并不健全,对于具体判断“机关”的哪些行为能够入罪缺乏统一的规则和标准。
然而,实际上并非“机关”的所有行为都能入罪。从刑法原理的角度来看,刑事诉讼的本质是由一个国家机关居中裁判,由另一个国家机关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控诉的国家活动,它代表的是国家权力对私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如果将这一结构中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替换成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机关,会使得这一国家活动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一个刑事诉讼活动变成一种国家权力与另一国家权力的对抗。而根据宪政原理,包括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内的各国家权力之间应当互相平等,互不干预。因此,国家机关涉及公权力的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调整的对象,不应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参见李晗:《单位犯罪刑事政策研究》,《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据此笔者认为能够归属于“机关”的犯罪行为只有“机关”在其职能范围以内不涉及公权力的行为,如行政机关利用其管理权限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行为。由于我国在“机关”犯罪的立法之初,理论准备不足以及立法过程仓促导致立法结果草率,使得“机关”犯罪的认定条件至今仍处于空白状态,导致司法机关在判断涉案“机关”应否承担刑事责任时难以提供充分有力的法律依据。
(二)法国“机关”犯罪立法中国化的可行性
法国“机关”犯罪的立法模式以限制肯定论为立足点,跨越了理论与现实的鸿沟,尽管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却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值得庆幸的是,同为成文法国家的中法两国,在“机关”的职能权限方面的共通性为我国汲取法国刑法中的有益经验以完善我国“机关”犯罪的立法规定奠定了基础。此外,我国地方行政机关与我国其他“机关”在收入来源方面的差异也使得我国刑事立法将“机关”的刑事责任限定为“地方行政机关”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现实可行性。
地方行政机关在“行政行为”之外都存在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两国的地方行政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也都有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形。因此,中法两国将“机关”规定为犯罪主体都是在理论论证以外,基于抗制犯罪的刑事政策的考虑。可以说,两国将“机关”作为犯罪主体进行刑事规制是刑事政策对危害日益严重的“机关”犯罪行为做出反应的体现,是在惩罚犯罪以外同样重视犯罪的预防。
从“机关”职能方面来讲,中法两国具有相似之处。由于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国家权力之间互相平等、互不干涉,因此,中法两国机关涉及公权力的行为不应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法国,除了依照法律行使权力履行职能之外,还能够发挥经济职能,从事经济活动的机关仅限于地方行政机关。由地方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能可知,地方行政机关除了履行公共执法、行政管理等法律规定的权力职能外还可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当地方行政机关因提供公共服务而参与到市场经济的活动中时,其行为可被视同私法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私行为。因此,将我国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以及党的机关排除在刑事责任主体以外,而仅对从事市场行为过程中实施了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的地方行政机关,根据平等对待原则,定罪处罚,既具有可操作性也是刑法谦抑性的体现。*参见刘艳红:《公权力主体犯罪——应然的解说与实然的超越》,《江海学刊》2008年第2期。
其次,从收入来源方面来讲,惩罚地方行政机关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犯罪行为既不会带来国家自我惩罚的理论困境也不会招致罚金刑刑罚处罚的实际无效。从地方行政机关的收入来源看,其他国家机关用于保障机构运行的经费主要依赖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或财政拨款;地方行政机关的收入来源则呈多元化,除了上述收入来源以外,还有地方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以及制度外收入,等等。对地方行政机关判处罚金,可以从地方行政机关的其他收入中执行,其处罚后果并非从“中央来到中央去”,因此也不会招致刑罚的无效。
(三)我国“机关”犯罪立法修正
97刑法对“机关”犯罪的立法规定是立法者高估司法能力的产物。 刑法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而刑法的明确性、协调性、合理性则需要立法者与解释者的共同努力。由此看来,将“机关”犯罪立法的适用交由有权的解释机关,由其对机关犯罪的立法规定做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解释,使得“机关”犯罪的主体范围和入罪条件朝着明确化的方向改革是一种权宜性的修正方式,也不失为一种理性的目标。具体来说,国家立法、司法、军事机关、执政党机关的除罪化和行政机关入罪条件的明晰化应当是解释“机关”犯罪立法规定的两个方向。
首先,如前文所述,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以及执政党机关是享有刑事豁免权,因此刑事立法必须清楚明晰地将其排除在刑事责任主体的范围之外。对于司法实践中那些将“机关”作为犯罪工具,以“为了机关的利益”之名,行个人犯罪之实的机关直接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则应当按照个人犯罪定罪处罚。
其次,进一步转变政府行政职能,把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是当前我国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同时,作为对传统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革新,公共服务民营化能够有效解决公共服务资金短缺以及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重视对地方行政机关提供公共服务活动的约束,特别是通过对机关实施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进行刑事制裁体现刑法对“机关”犯罪的否定态度,对于规范“机关”的行为具有明确的导引作用。
“解释是法律调整机制的必要因素”。*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笔者认为从立法的权威以及后续的执行效果来看,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具有普遍效力的司法解释,将《刑法》第30条中的“机关”解释为从事公共服务的地方行政机关,既能维护立法的权威,也能给司法工作提供明确的依据。
结语
任何立法都有局限性。 尽管从立法背景来看,法国关于“机关”犯罪的立法是各方博弈之后的权宜之计,同时有法国学者指出,刑事立法将最高层的行政法人——国家排除在刑事责任范围以外的差异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却可能产生不平等。具体来说,在地方议员或者地方公务员牵涉到犯罪的情况下,法国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追诉过程中,更多起诉地方行政部门,而非以工作人员的名义起诉个人。然而,在涉及国家公务员时,由于国家不负刑事责任,并不存在前种选择的可能。因此,这就造成了国家公务员与地方公务员之间潜在的不平等。尽管法国关于“机关”犯罪的刑事立法在学界存在上述为人诟病之处,但是它在司法适用中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回顾法国“机关”犯罪的立法规定,可以发现法国的立法模式是一项颇具立法技术的创举,使得理论研究和法律现实之间天堑变通途。当前我国“机关”犯罪立法难以指导司法实践的现状一直为人所诟病,因此我们不妨从法国“机关”犯罪的立法规定中找寻调适立法的灵感。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法律的制定者是人不是神,法律不可能没有缺陷。而将有缺陷的法条解释得没有缺陷正是法律工作者智慧的体现。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司法解释将“机关”解释为实施非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使得“机关”犯罪的立法更具操作性,也是对现行立法的有力补强。
(责任编辑:操宏均)
作者简介:康均心,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佳,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法国巴黎第二大学访问学者。
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28(2016)04-0100-11
*本文受“2014-2015年国家留学基金委高水平公派留学生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