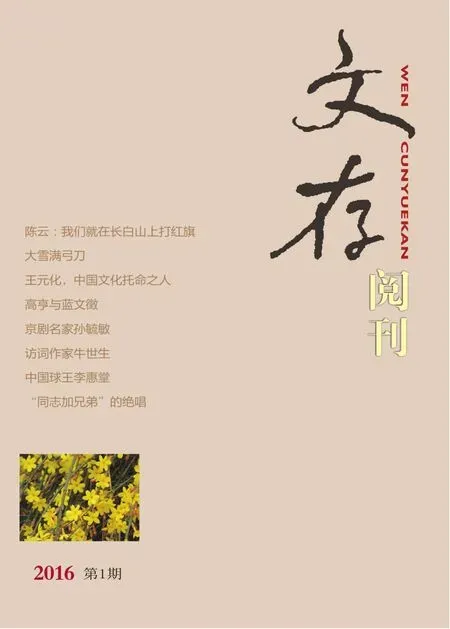花儿、阳光与爱情
花儿、阳光与爱情
冶力关正午的阳光,怎么想都像某种情感,纯净、透亮、简捷、热烈,一往无前、不留退路的倾洒势不可挡。
其实,我心如明镜,知道明媚的阳光有时就如爱情一样美好。但那天我还是撑了一把宽大的遮阳伞,怕只怕突然而至的灼烤会给没有准备的身心留下疼痛的记忆。可是,阳光从树叶、阳伞、以及周边的建筑上滑落之后,竟然就拥有了水的质感,明明亮亮,也汪汪洋洋地流溢在广场的地面,然后又从伞底漫掩或者弹溅上来,复把伞底的人照亮。置身其中,不仅仅感觉到脸庞和衣裳尽染光明,仿佛连脏腑、血液和骨头都被光注满,从里到外的明亮,明亮得没有一丝阴影。
这时,我突然发现,世间最美也最难懂的三样东西,已经在临潭聚齐。
一年一度的“洮州花儿会”,就在眼前演绎得流光溢彩、如火如荼。透亮、激越的歌声如另一种看不见的阳光,以声波的形式,隐秘而又堂皇地扑面而来,一旦遇到耳膜,立即产生强烈的共鸣,其形,如雨水之于土地的久别重逢;其情,如阳光之于花朵的相拥而笑。
每年农历六月初是莲花山洮州花儿会的特定时段。届时,临潭、卓尼、康乐、临夏、临洮、和政、渭源、岷县、兰州等地的数万游客接踵而至,游山赏景,真可谓是人山人海。期间歌手云集,歌声如潮,花儿此起彼伏,昼夜不休。“莲花山,九眼泉,花儿常开水不干,口漫花儿透心甜。”人们如过节一般,身穿鲜艳的服装,欢天喜地赶到莲花山“花儿会”上唱歌野游,沉浸于节日的欢乐和花儿的意境之中。
歌手们唱花儿,用的是甘南方言。对于一个不熟悉地方话的人来说,那些唱词便如阳光和清风一样难懂。好在歌词之外还有曲调和情感,那就任由一曲接一曲花儿的旋律回旋、荡漾,在心头激起莫名的波澜吧。掌声、笑声、喝彩声都属于别人,我则静坐于那些我很难以懂得的事物之中,如一棵树或一株草感受、猜测阳光一样,猜测着那些花儿要表达的意境。
据说,洮州花儿和大部分西北民歌一样,起源和重要功能都与爱情有关,主要用于男女之间唱和、应答,传递思念和渴慕之情。按正常的艺术规律,对于温柔情感的表达,当是细雨在春夜里的行走,嘈嘈切切,委婉沉迷,如慕如诉如怨,柔软的声线扫过心头,则留下一串轻轻浅浅的波纹。而临潭的花儿,却天生一种惊天动地的气势,如强劲的秋风卷着枯叶与飞沙,呼啸而过,在听众的灵魂里犁起一道深沟。先是让人心头一颤,随后便有微微的凄苦和疼痛扩展开来,将整个心灵覆盖。
临潭花儿的唱腔,不论如何是奇异而独特的。那些高亢、激越的曲调听上去总如某种情绪的倾倒,总如抛心抛肺的呼喊,轻而易举就把我带入一种天高地远的意境,让我不得不把探寻的目光投放于那片广阔苍茫的地域和其悲壮、幽深的历史。
公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即晋太康四年至十年(283—289)左右,鲜卑单于涉归庶长子吐谷浑,因与以母贵继单于位的嫡弟慕容廆不和,不得不率所部一千七百户从辽东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背井离乡,向西迁至阴山,后又从阴山南下,经河套南,度陇山,至陇西临夏西北的罕原,并以此为中心,子孙相承,向南、北、西三面拓展,占据了甘肃南部和四川、青海部分地区。原来,这是一片放逐者的土地,三尺黄土之下,自然沉积着难以陈明的悲情。
自古以来,临潭都是“西控番戎,东蔽湟陇,南接生番,北抵石岭之要冲。”但同时也是一个兵家必争、废置多变的动荡之所。自北周武帝保定元年置洮州始,临潭历经了无数战乱和纷争、民族融合和归属变迁。从大明洪武年开始一直到永乐、洪熙,朝廷又陆续令大批平息地方战乱的内地军士留驻洮州,并将他们的妻儿家眷统统迁往此地,伐木造屋,铸剑为犁,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一代代细嫩白净的江南人,就这样在高原风雨、阳光的雕琢下演变成了黑脸膛、粗嗓门的西部农夫。虽然乡关渺远,归期无限,但自“小桥流水,杨柳依依”而来的文化基因却为屯守者们标定了灵魂指向,就是在梦里,也断不了对江南故乡的思念,思念而感伤,感伤而悲戚。渐渐地,这个地域的很多艺术形式都自然而然地染上了丝丝缕缕的愁怨。
然而,这个地域的总体性格,又决定了其表象上必然的刚毅和硬朗。纵有千般万种的愁怨,也要埋藏于情怀深处。很久以前听过一首在西北各省广泛流传的民歌《蓝花花》,歌词是:“五谷里的那个田苗子,数上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数上咱们蓝花花好。”既高调又“阳光”,可那曲调唱出来的时候又似拖着哭腔,不由得让人从心底里生出些许酸楚。想那一介乡间女子,再好能好到哪里,怎么可能在一国之内拔得头筹?只因为喜欢,只因为爱,这些生存于极端环境里的人们就启动了情感中接近极致的运行和表达方式。有一种描述叫“死去活来”。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一切都极致到死去活来。
阳光往死里晒。对于一些没有生命的事物,比如一根雪糕,一个冰块儿,定会在阳光的作用下短时内消融、蒸发;对于土地,如果没有充足的水分涵养滋润,也一定成为寸草不生的焦土。但对于生命来说,这种“狠”,很像那些极致的爱情。一腔的心愿、一腔的热力就那么毫无保留地倾注了,那是来自于生命深处难以掩抑,难以控制的激情,哪里还顾得上问一问你是否适应,是否承受得住。只要你有能力互动,一切自会不同凡响。烈焰熄灭,必有一段安恬静谧的甜黑;燃烧过后,必有一个凉爽、幽深的夜晚,月色温柔如水。光明的手指抚过之后,一切事物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大地上水气汹涌,草木葱茏,瓜果膨胀。云成为一种最飘忽不定的情绪,一会儿阴沉,一会儿明媚,翻来覆去地酝酿着那场雨。如果有人一定要追问,阳光过后我的脸色为什么会暗下来,我并不想说阳光在我的脸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记忆,而只想告诉他,这里的水果特别的甜。
花儿,往死里喊。激烈的表现形式必然对应着激烈的内在需求和内涵。曾经的地广人稀让这里的人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一种独特的理解和诉求,那种一个生命对于另一个或一些生命的呼喊和倾诉,不仅仅缘自空间上的阻隔,更来自于内心长久压抑着的焦渴。于是,我们感受到的便是来自于自然和本真的天籁之声,狂风暴雨或江河呜咽咆哮。最温柔和最热烈的情感都可以采取极端的表达——“拼上我的性命,往哥哥家里跑”;“我见到我的情哥哥哟,有说不完的个话呀,咱们两个死活哟,长在一搭”;“若要我把你丢脱,牛长上牙马长角,河里的石头滚上坡”。如果,每一次的抒发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每一次的表达都不再有机会重来,为什么不倾尽生命里的全部能量,来一次火山喷发,来一次石破天惊!或许,只有爱情,只有那些狂放、热烈的情感才能让灵魂深处的疼痛免于复发,才能让干涩、沉重的生活之轴不再研磨出锥心、刺耳的尖叫。
就这样,既有高原粗犷豪放又兼具江南绵密细腻的临潭,自然成为花儿和爱情的滋生之地,而一切物质与精神、苦涩与甜蜜的积累,又缘于“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当我从飞机上回望甘肃,回望临潭时,却不知是谁已经在那片既苍凉又美丽的土地上一口气种下了万顷白云,连绵起伏如无垠的棉田,不由得从心里发出由衷的感叹:“这地方,好气派!”
(作者/著名作家,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