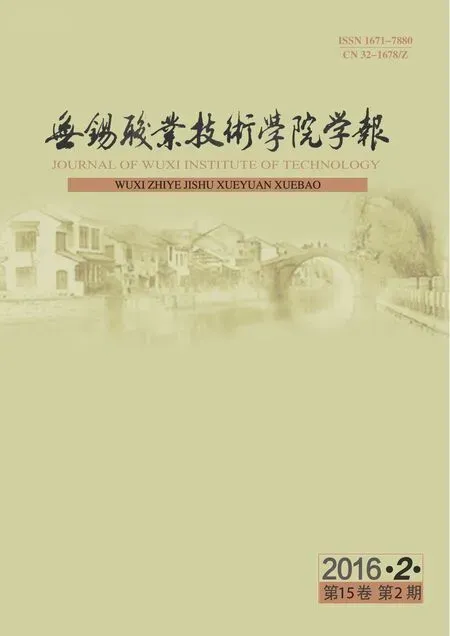城市的原罪,自然和人的灵性
——由霍桑的《胎记》看19世纪美国小说
操 磊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与旅游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1)
城市的原罪,自然和人的灵性
——由霍桑的《胎记》看19世纪美国小说
操磊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与旅游学院, 江苏无锡214121)
十九世纪美国城市化的飞跃发展带来物质生活的极大繁荣及奢华,然而这难以掩盖城市中人内心的空虚,浮躁与迷茫。本文旨在通过对霍桑短篇小说《胎记》的解读,透视城市的集成单一以及不可逆的构建对人的心灵带来的束缚,压抑与扭曲。文中首先解读城市化的文学内涵;其次剖析霍桑小说《胎记》中对现代文明产物——城市的“原罪”控诉;最后纵观十九世纪美国小说的历时统一主题:对城市及现代文明的批判及反思,以及对自然和人灵性的回归。
《胎记》; 19世纪美国小说; 城市; 原罪
1 19世纪美国城市化小说的内涵
19世纪初美国开始了早期的工业化,随之而来的西进运动催生了城市化的萌芽。19世纪中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进一步加速了美国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实现了美国在经济、技术、人口、文化等方面的集大成式的发展与跃进。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在文学方面的突破式发展。
英国作为老牌殖民帝国,其城市化呈现浸润式发展。而后起之秀的美国则凸显出膨胀式的城市化特点。城市化的急剧发展也使得美国文学尤其是美国小说生发出纷繁丰茂、日新月异的主题。因此,城市的多层次、集成式发展使得人们的情感有了多元化的文学表达。
19世纪的美国小说基本呈现出两大主流倾向:前期的浪漫主义倾向和后期的现实主义倾向。浪漫派的小说家代表有华盛顿·欧文、爱伦·坡、纳撒尼尔·霍桑、赫尔曼·麦尔维尔,而现实派的小说家主要包括马克·吐温、威·迪·豪威尔斯、亨利·詹姆斯。而霍桑作为19世纪杰出小说家以及浪漫派的终结者,继承了浪漫派的瑰丽想象和主观抒发,同时也开启了深刻批判城市畸变现象的现实派风潮。
本文以19世纪转折性小说家霍桑的短篇小说《胎记》一文为例,分析男主人公阿尔默试图通过文明的医药手段去除女主人公乔治亚娜脸上与生俱来的胎记,结果却导致乔治亚娜殒命的悲剧。这一看似对完美容颜追求的人性悲剧本质上是对经济科技进步带来的城市文明及城市化审美的无声控诉。而这一控诉式的主题也不鲜见于19世纪美国其他作家的小说中。
2 霍桑《胎记》对城市原罪的控诉
城市从其诞生之初就被推向了乡村的对立面,与乡村的自然、闲散、自由、古朴不同,城市是文明、整齐、统一、现代的。同样,城市文学也与乡村文学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局面。城市文学的主题多为对城市生活及人群的冷漠、机械、异化的抨击。虽然乡村文学也揭露乡村惯有的贫穷,无知和落后。但是乡村作为大自然代言人,为城市文学以及乡村文学提供了无可争议的文学主题。乡村所象征的诗意、乡愁、怀旧、归隐是城市文学永恒向往和歌颂的对象。
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理论下,城市带着与生俱来的原罪,正如Jie Lu在 Rewriting Bejing: A Spetacular City in Qiu Huadong’s Urban Fiction一文中提到的,城市生成了碎片化的杂乱无章,令人生畏的孤立无援以及对历史自然的无情遗忘。在19世纪的美国,城市化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这种原罪的释放更为充分典型以及毫无保留。在霍桑的短篇小说《胎记》一文中,这种原罪被无限地曝光及放大。
小说一开始介绍说:“那年头,电及其他大自然的奥秘刚被发现,仿佛打开了进入奇异世界的条条途径。人们热爱科学。”电的发明,科学技术的进步催化了城市化的萌芽。男主人公阿尔默作为一名极具智慧的科学家,痴迷并推动知识与技术的进步。他崇尚智慧、科学、理性,怀抱“征服大自然的信心”,可以称之为城市文明的化身。女主人公也就是阿尔默的妻子——乔治亚娜,脸上有块独特的胎记,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这块胎记深植于乔治亚娜的脸颊中,并且随着女主人公的情绪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这种颜色的变化暗合了生命的活力与生机。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胎记像一只小小的人手,这不免让人联想起上帝之手以及自然之手。这样的颜色变换和手形形状无一不昭示着生着这样一块胎记的乔治亚娜就是大自然的代言人。
悲剧始于阿尔默对科学研究毫无保留的激情和献身,出于科学家对完美及进步的追求,他表示出了对这块胎记的不满,并对她的爱妻说:“亲爱的乔治亚娜,大自然把你造得几乎尽善尽美,所以这一点点瑕疵——我吃不准该叫它缺憾还是美丽——也令人震惊,因为它是人间遗憾的明显标记。”造物主的自然产物在阿尔默看来并不美丽,而是令人震惊的人间遗憾。城市文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已经完全湮没大自然的魅力,以及对大自然“不完美”之处的接纳。这种城市文明至上的思想作为城市化的产物,疏远了人与自然的亲近关系,甚至导致了人对大自然的遗忘、孤立、背叛与蔑视。
城市文明以及城市文明催生出的畸形病态的审美观冲击并颠覆了传统的自然审美观。尊崇自然,以自然为美的的价值观被城市化无情湮没。城市化的急剧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便利优越使人们迷失在城市文明的繁荣虚华中,并陷入对城市审美的极端完美追求中。
在19世纪美国城市化发展的蓬勃时期,对自然的审美臣服于对城市文明及技术的推崇。这在人类城市文明刚刚起步的时期似乎无可厚非,因为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发展及嬗变,人类由对自然的无知恐惧和被动依赖变成对城市文明的主动构建和自主规划,迈出了人类在集聚方面的自我改造和前进的一大步。而文学家们敏感的笔触总能最早感知到城市文明蓬勃之下的危机及险象,19世纪美国小说家们更是如此,在对城市文明的喝彩和追捧中,他们独辟蹊径,直击城市人群及城市文明背后的虚妄、伪善、疏远、孤独。
3 美国小说的城市化现象
Robert Park在其著作《城市》一书中曾经提到,“城市不仅仅是人和社会基础设施如街道、灯光,电车和电话的聚集,也不仅仅是机构部门和行政设施如法院、医院、学校,警察以及各种官员的集成,而是思想的邦国,习俗和传统的载体,以及既成态度和情感的表征。” 人的悲剧即是城市的悲剧。 以霍桑为代表的一系列美国小说家包括华盛顿·欧文、爱伦·坡、赫尔曼·麦尔维尔、马克·吐温、威廉·迪安·豪威尔斯、亨利·詹姆斯等人开始通过异常敏感的关注,极其细腻的笔触再现高度城市化下的生活风貌和人物万象。他们抑或浪漫色彩,抑或象征手法,抑或现实格调,抑或自然主义的艺术创作风格无一不勾画着城市理性之外的人物情感及自然灵性。
前文提到,19世纪的美国小说由前期的浪漫主义转向后期的现实主义。然而这一创作流派的变化依然围绕当时城市化及城市文明发展的大氛围,同质化地抒写着同一个主题。他们由个人转向社会,由单一到复杂,由浪漫到现实,都是对城市化的控诉。 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
3.1城市化中的追忆情怀
这一时期的小说对城市与自然关系的描写多从他者的角度,即对古老文明的仰慕,对田园遗风的向往,对小说环境的精心创设,对人物寓意的特意安排等。这类小说并不直接抨击城市的罪恶,而是通过对前城市时期的留恋,城市外空间的歌颂或者对象征意象悲剧的描述来反衬或暗示城市文明的初罪。比如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代表《瑞普·凡·温克尔》和《睡谷的传说》,采用充满浪漫奇幻色彩的传说,描述了发生在穷乡僻壤的奇闻趣事。读者在这种迷离美妙的气氛中,不免对美好的往昔生出无限的遐想以及对现实的遗憾。这种遗憾令人感慨、令人失落,因为城市文明的快速发展和无情的社会节奏碾压了未进入城市之前的闲散惬意和悠哉节奏。 爱伦·坡的小说更是把小说人物置于各种精心创设的极端环境中,弥漫着浓厚的恐怖、孤独,绝望甚至死亡的气息,小说人物也毫无例外地沉浸在悲伤、焦虑、烦恼以及崩溃的情感边缘,死亡一触即发。这种被城市异化的城市环境及人物情感昭示着对某种安全地带的诉求,而这一安全地带就是城市之外的空间,例如:淳良的乡村。 同时期的赫尔曼·麦尔维尔在其代表小说《白鲸》中也象征性地阐明了试图对抗自然将导致灭亡的无情事实,号召人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
3.2城市化中的人文情怀
以霍桑的作品为转折点的19世纪美国小说一改前期的沉郁、内敛、追思特点,不再隐晦地影射城市文明的象征和代表,而开始大胆直白地描述城市社会下的众生万象,并勇敢无畏地抨击城市社会的种种弊端。他们不像19世纪前期小说家们那样顾左右而言他,回避现实而一味迷恋过去的美好,取而代之的是直面现实,尖锐而辛辣地讽刺社会,并从人道主义角度给出合理的改良建议以便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和城市人文。这也得益于当时的城市化极度扩张,当时的美国由早期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扩张,其城市化的脚步已经踏出美国国门,冲向世界各个殖民地。当时的文学幽默批判大师马克·吐温写出了大量小说作品,其思想和创作也表现为从轻快调笑到辛辣讽刺再到悲观厌世的发展阶段,前期以辛辣的讽刺见长,到了后期语言更为暴露激烈。他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尖锐地揭露了美国民主与自由掩盖下的虚伪,批判了美国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社会弊端,诸如种族歧视、拜金主义、封建专制制度、教会的伪善、扩张侵略等,表现了对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生活的向往。亨利·詹姆斯把中篇小说创作的造诣提高到一个前无古人的水平。他的人文主义倾向主要是对城市文明中的道德品质的关注,借此来缓和以及减少城市阶级矛盾和冲突。欧·亨利作为美国19世纪后期的小说家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数量极多,最擅长描写落魄的小人物在艰苦的求生环境中,仍能对他人表现出真诚的爱与关怀这类感人小故事。这种对城市人物美好灵性的赞美让人强烈感受到了城市人文的光辉。
4 结语
19世纪美国经历了城市由萌芽到璀璨的伟大时期,这一伟大并非意味着自然和人类的伟大,相反,自然和人类却因此而备受罹难。不可逆的城市化使人们再也不能够回到城市前的自然文明,不可消灭的城市原罪也只有在对自然和人的灵性的尊重和整合下才能黯然失色,并焕发出焕然一新的光芒,照耀着人,自然与城市的和谐与平衡。
[1]霍桑. 霍桑短篇小说精选[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2:28.
[2]金莉,译.美国十九世纪文学选读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6.
[3]Robert Park,Ernest W. Burgess, Morris Janowitz.The Ci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33.
[4]Jie Lu.“Rewriting Beijing: A Spectacular City in Qiu Huadong’s Urban Fiction”[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4,13(39):323-338.
[5]陈超.文学视域中的“城市化”景观及其反思[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4):134-141.
责任编辑王红岩
Sin of city to sagacity of nature and human beings——A study in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s American fiction by Hawthorne'sBirthmark
CAOLe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Tourism, Wu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xi214121, China)
Throughou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witnessed overwhelming development by industrious revolution. However, urban habitants' inner loss, fickleness and confusion became intensely unveiled by urban vigor and glory. This paper studies urban theme of Hawthorne's short fictionBirthmarkby uncovering constraint and distortion of urban monotony and irreversible construction over human souls. Meanwhile the dynamic and diachronic theme in American fiction of nineteenth century is explored: reflection on urban sin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resort to sagacity of nature and human beings.
Birthmark; American fiction of nineteenth century; city; sin
2015-11-13
操磊(1987—),女,河南信阳人,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10.13750/j.cnki.issn.1671-7880.2016.02.019
I 3-84
A
1671-7880(2016)02-0066-03
项目来源: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PZY2015A086、PPZY2015C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