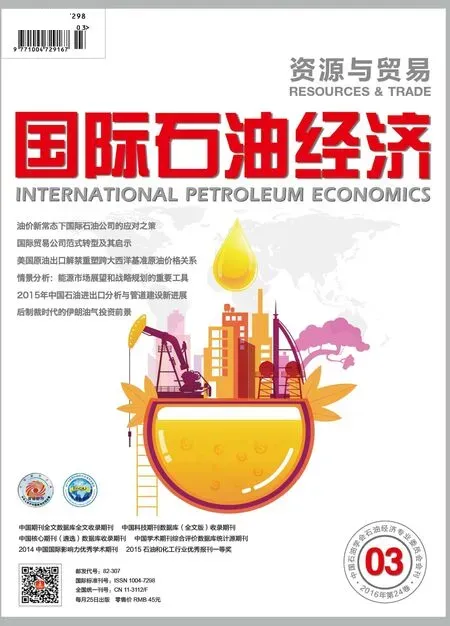国际工程索赔的法理基础
张浩(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伊朗分公司 )
国际工程索赔的法理基础
张浩
(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伊朗分公司 )
摘 要:工程索赔在国际工程领域被公认为是最为复杂、最为棘手、最具有挑战性的法律问题。国际工程索赔的法理基础主要包括合同文本的选择、条款的法律适用、归责原则三个方面。工程索赔首先要看合同文本的风险分配原则,风险分配给谁对于合同当事人来说尤为关键;其次,合同条款是否与准据法或工程所在国法律相冲突,无效的合同条款不能作为合同索赔依据;最后,即使相同的合同条款,在不同国家适用时,由于归责原则不同,法律后果也可能大相径庭。
关键词:国际工程;索赔;法律适用;归责原则;合同文本
国际工程索赔涉及法律法规、技术经济和工程管理等多学科知识,被公认为是国际工程领域最为复杂、最为棘手,也最具有挑战性的法律问题。国内外学者对索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引起索赔的因素、索赔原则、索赔依据、索赔程序、索赔方法、索赔技巧、争议解决方式、组织机构构建、人员素质构成、数据记录、费用计算、工期计算、索赔模型的构建等问题上,对索赔的法理基础研究不足。工程索赔需要先定性分析,再进行定量分析,两分法可使复杂的索赔问题迎刃而解。定性分析主要是指法律分析,判断能否构成索赔;定量分析属于技术性分析,量化索赔费用或者时间。国际工程索赔的法理基础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合同文本的选择,工程项目选择的合同文本中的风险分配规则是构成索赔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因素;二是合同文本具体条款的法律适用,解决合同条款与工程所在国的法律或者准据法存在冲突的问题;三是索赔事件在适用具体法律中或合同中的归责问题。
1 工程索赔的定义与特征
“索赔”在《牛津法律词典》中的定义是:“坚持取得金钱、财产或赔偿等方面的要求。”工程索赔通常是指在履约过程中,合同一方当事人非因自身的原因受到损失后或者权利受到损害后,根据合同、法律或者惯例通过一定的合法程序向对方提出经济或时间补偿要求的一种行为。“索赔的实质是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对合同双方权利与义务作出调整,以达到对发生的损失给予补偿的目的”[1]。索赔有三大法律特征,即补偿性、客观性和合法性。补偿性是指承包商与雇主按照合同约定的风险进行合理调整或再分配,以弥补受损方的损失。国际通用的合同文本对于索赔的范围基本限定为“额外”的工期或者费用,索赔本身不具有经济惩罚的性质。客观性是指索赔必须是在发生实际损失后或权利受到损害后才能向对方提起,无损失则无索赔,而且这种损失必须是能够被证明的法律事实。合法性是指提起索赔必须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既包括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文件,也包括准据法或者工程所在国的法律以及国际惯例。索赔的三大特征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补偿性是索赔的第一属性,是索赔的最本质特征;客观性受合法性制约,但客观性的评价标准在不同法域认定差异很大。
关于“反索赔”的定义,中国国内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承包商向雇主提出的经济补偿或工期延期要求为索赔,而雇主向承包商提出的索赔,对承包商索赔进行的评价或者批评以及否定称为反索赔”[2]。全国建筑施工项目经理培训教材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教材等均采用该观点。这种提法在中国工程界占主流。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反索赔是当事人另一方向索赔方提出的索赔要求进行反驳、反击或阻止对方索赔成功叫反索赔”[3]。《牛津法律词典》中对“反索赔”的定义是:“由被索赔一方发出的对该项索赔进行检查和处理的行为。它不仅是对该项索赔的防卫与反驳,而且是对索赔者提出实质性索赔的一个独立的行动。”[4]该释义是必须针对同一标的提出的相对独立的反索赔请求,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对方的索赔诉求,该项反索赔诉求也能独立存在。如果仅仅是“拒绝”或者“反驳”,则构不成“反索赔”,这与中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关于“反诉”的规定相似。工程索赔具有双向性特征,是法律或者合约赋予双方平等主体间的对等救济权利。上述第一种观点违背了语言逻辑习惯,在国外并没有该种提法。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1999年出版的FIDIC合同条件《设计-采购-施工/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第2.5款规定了雇主索赔的权利:“如果雇主认为,根据本合同任何条款,或合同有关的另外事项,他有权得到任何付款,和(或)缺陷通知期的任何延长,他应向承包商发出通知,说明细节”[5]。在国际工程实践中,雇主的索赔往往没有时效性约束,不需要提交索赔报告和资料,甚至不需要征得承包商的同意,雇主可以从应支付给承包商的工程款中扣抵,或者没收履约保函或质保金保函,其索赔难度与承包商的索赔相比容易得多,又因雇主的索赔频率较少,我们通常见到的是来自于承包商的索赔。但该种提法盛行主要是一些主流教材起了以讹传讹、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种说法虽然揭示了索赔与反索赔的主体双向性特征,但混淆了索赔与索赔抵制、抗拒等行为的区别,是抛开法律语境下的提法。
2 合同文本的风险分配是索赔的前提和基础
国际工程通常采用国际组织编写的标准合同范本(或称合同文件)。合同范本是国际工程界多年工作实践和智慧的总结,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工程建设的惯例[6]。近几年出版的国际工程合同范本主要有FIDIC、ICE和AIA三大系列: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1999年出版的FIDIC合同范本,包括《施工合同条件》(红皮书)、《生产设备与设计-建造合同条件》(黄皮书)、《设计-采购-施工/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银皮书)、《简明合同格式》(绿皮书);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ICE)2005年7月出版的第三版《新工程合同》范本,简称NEC3合同;美国建筑师学会编写的AIA合同范本。总体而言,FIDIC、ICE、AIA合同系列范本基本上代表了当前国际工程总承包领域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最高水平。三大系列合同条件一般被认为是合同性国际惯例,需经过当事人的选择才产生法律效力。FIDIC合同条件在编制之初就着眼于将国际工程领域通行的规则和惯例作为编制依据,弱化不同国家法律法规的差异,充分考虑货币选择、汇率风险以及工程所在国的罢工、暴动、骚乱、政权动荡等因素的影响。NEC3合同范本体现了英国合同体系发展的最新成果,该合同文本在英联邦成员国、南非、香港等区域被广泛采用。AIA合同范本主要在美国国内和美洲地区使用。由于大部分工程所在国不具有美国那样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在社会政治领域,承包商经常面临罢工、暴动、骚乱、政权动荡等风险,美国的AIA合同文本系列不具有应对这些风险的能力,因此“美国总承包商协会和美国施工行业协会倾向于使用以ICE合同第5版为蓝本编制的FIDIC合同条件”[7]。在大陆法系国家,合同权利与义务传统上是以立法的形式调整的,但为了弥补民法典的不足,在借鉴英美国家合同文本的基础上,一些国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合同文本。中国政府在借鉴FIDIC合同文件的基础上,制定了《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试行)》和《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示范文本》。但这两个合同范本为选择性使用文本,没有强制性法律效力。
合同范本的实质就是规范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确定风险责任的分配方式与转移规则。不同的合同范本,承包商与雇主的风险分配原则和方式差异很大,即使同一索赔事件适用不同的合同文本,由于风险分配机制不同,索赔结果也会迥然有异。解决索赔问题的前提是厘清合同文本中风险责任的划分与认定。例如FIDIC银皮书与红皮书对风险分配有不同规定:1)银皮书4.10款规定,承包商负责核实和解释雇主提供的现场地下、水文条件及环境方面的资料,雇主对自己提供的资料准确性、充分性和完整性不承担责任;红皮书规定承包商应能解释此类数据,在可行的范围内,承包商被推定为已取得了了解投标文件或工程产生所风险的必要资料。2)银皮书5.1款规定,明确除四种条件外雇主不对自己要求的任何错误、不准确或遗漏负责;红皮书中规定此类责任完全由雇主负责。3)银皮书4.12款对相关的风险、意外事件等推定承包商已经有充分的准备,其困难和相关费用完全由承包商承担,除非合同有特别约定,否则雇主没有此项义务;红皮书规定承包商可能得到这方面的工期和费用补偿,责任在于雇主方。4)银皮书关于产品质量的设计责任规定由承包商承担,对雇主造成损害后,责任在于承包商;而红皮书中的产品质量责任规定由雇主承担,对于产品质量造成的责任,雇主承担违约或侵权责任。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合同文本风险分配不同会对索赔会产生根本性的颠覆。
3 合同文本条款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
合同的法律适用是指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在因合同而发生争议时,仲裁机构或者法院以何国的实体法作为处理争议的依据。这种冲突规范的援引,用以确定合同当事人权益义务关系的实体法就是合同的准据法。确定准据法的原则是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主,辅以客观标志或最密切关系原则[8]。当代国际社会,基于主权考量,每个国家都以法律形式规定在本国领土范围内进行的一切活动均受本国司法管辖,因此无论是雇主还是承包商都必须遵守工程所在地国家的法律。承包商与雇主通常约定司法管辖区并接受司法管辖区的法律约束。银皮书为此作出规定,第1.4款:“合同应受专用条件中所属国家(或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管辖”,第5.3款规定:“承包商承诺其设计、承包商文件、施工和竣工的工程符合工程所在国的法律”。中国《民法通则》第8条和第14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国际合同条件是合同性的国际惯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条约,因此只有在中国法律或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均出现空白时才可以适用国际工程合同条件。若国际合同条件与中国现行法律发生冲突,则适用中国法律。
研究国际工程合同条款要熟悉英美法系中的默示规则。英美法系合同有明示条款和默示条款。明示条款指构成合同文件的协议书、通用条款、专用条款、技术规范和投标书。默示条款是指合同中没有专门的文字描述,但可以通过某些条款的含义以及签约时当事人的主观意图,推定该合同中隐含的意愿或条件,以公正地解决合同争端。默示条款主要来自于习惯、成文法和法院。成文法例如英国1979年的《货物销售法》,默示了卖方有权销售货物、货物质量需让人满意、凭样品销售的货物需与样品相符等内容。法院的默认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种是“法律的默示”,另外一种是“事实的默示”。英国法建立起来的“默示规则”已经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是较合理、全面、可行的游戏规则。英美合同范本规定了除承包商自身原因造成损失外,均有权根据索赔条款向对方提出索赔。
FIDIC合同条件是以传统的ICE合同文本为蓝本制定的,具有英美法的特色,在普通法系国家法律适用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然而在大陆法系国家适用时,“由于大陆法系民法典中承揽合同规定的理念与FIDIC合同条件下的理念并不完全相同,致使FIDIC合同条件中的一些规定与大陆民法典中的一些强制性规定相抵触”[9]。例如,红皮书和黄皮书中的“工程师”制度,形成了以工程师为中心的专家管理体制,规定工程师拥有广泛的权力,能决定承包商的索赔是否成立,签发付款证书,能够决定工程是否竣工。关于工程师的法律地位,究竟是中间人、设计者、裁决人还是发包人的代理人历来是大陆法系国家争论的焦点。即使红皮书本身,对于“工程师”的地位也不断定位,新红皮书将原来工程师“中间人”的中立地位变更到“发包人人员”中,重新界定为雇主的工作人员或代理人,并将其争议裁决的职权交给了争议裁决委员会。英美法系中赋予了“工程师”很大的权利,但工程师又不承担任何作为与不作为的义务,权利与义务仍由雇主和承包商承担。以大陆法系的视角来看,工程师的法律地位很尴尬,工程师在大陆法系中始终不能成为一个适格的法律主体。例如,在德国承揽合同根本不存在类似于FIDIC条件的“工程师”,虽然雇主的索赔经常通过“建筑师”的协助来完成,但“建筑师”的法律地位是被作为雇主的代理人而发生作用,并不具有英美法中“工程师”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中国工程监理实施的是严格的资质准入和资质等级制度,如果适用红皮书条件,则工程师制度与中国监理工程师制度必然存在冲突,雇主和承包商无权通过自由约定排除监理工程师制度。
银皮书第20条规定,承包商索赔应在察觉或者应已经察觉索赔事件后28天内发出通知,否则承包商不能延长工期或者无权获得补偿,雇主可以凭此免除有关索赔的全部责任。对于分包商索赔逾期28天丧失实体权利的规定是否与中国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相冲突的问题,有观点认为索赔逾期即丧失实体权利的规定无疑是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索赔逾期失权制度违反了中国法律有关诉讼时效的强制性规定;也有观点认为索赔时效与诉讼时效问题不相冲突的情况下产生的“过期作废”问题应具有法律效力,索赔时效与诉讼时效相冲突(尤其是索赔时效短于诉讼时效)的情况下产生的“过期作废”问题,应不具有法律效力[10];还有观点认为合同约定的索赔时限无效。对于国际惯例中的索赔期限制度是否与中国的诉讼时效发生冲突需要做出立法或司法解释。
FIDIC条款规定争端委员会(DAB)的决定对合同当事人有约束力,如果一方不执行,另一方可以向选定的仲裁机构提出申请,而仲裁机构只能进行程序性审查,不能对DAB的决定进行实质性审查。如果未发现DAB在程序上违法,则会裁定维持DAB的决定。AIA合同文本争端解决机制是首先让建筑师对双方之间的索赔作出决定,如果双方对建筑师的决定无异议,则应执行。如果建筑师的决定未能解决纠纷,则需要按照美国仲裁协会的建筑行业条例调停,调停失败后才能提交仲裁。无论是FIDIC还是AIA在纠纷解决机制上都采用提交工程师或建筑师解决。假如上述两个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使用DAB解决机制,仲裁机构是中国某仲裁机构,一方当事人对DAB的决定拒不执行,中国的仲裁机构是否有权对DAB的决定进行实体审查?当事人按照FIDIC条款仲裁制度约定是否与中国的仲裁法存在冲突?对于涉外合同,国际惯例中通行规则是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然而约定是否为中国现行法律所承认?这些如何适用法律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有相应的立法规定或司法解释。
合同范本与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其产生和存在都依赖于特定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法治环境。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同一索赔事件在不同州的法律适用中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因此在选择合同文本时,需注意合同文本中的个别条款是否与准据法或工程所在国法存在冲突。如果工程所在国有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则必须遵守当地法律,对合同条款加以改造。
4 索赔事件的归责原则
归责就是依据一定的法律事实状态确定民事责任的归属,归责原则是指确定责任归属所必须依据的法律准则。“无论一个国家属于哪种法系,总会通过某种特定的制度设计反映其基本的价值理念——无论其是否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公开宣布其一般的归责原则”[11]。归责原则是工程索赔最直接和最根本的法理基础。民事归责制度涉及责任归属和免除两个方面,责任归属方面包括违约与侵权,免除方面主要是指不可抗力。
违约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没有按照合同完全履行义务或没有适当履行义务而应向对方当事人承担的赔偿责任。英美普通法系违约的归责原则基本上采取严格责任原则,大陆法系国家基本上采用过错归责原则。由于近代两大法系出现融合趋势,大陆法系把过错原则作为基本原则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严格责任,而普通法系在采纳严格责任原则时,也没有否定过错因素在确定合同责任方面的意义。FIDIC合同条件根源于英国的ICE合同条件,因此其违约的归责原则采取严格责任。在中国,违约的归责原则通常认为在1999年合同法颁布之前采取过错责任原则,合同法颁布之后采取以严格责任为主、过错责任为补充的原则。合同法总则采用严格过错责任原则,分则中部分实行过错责任原则,而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以及缔约过失责任则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国际工程索赔中诸如自然因素造成的损失等很多事件,并非当事人的过错引起,因此常被误以为是不可归责原因造成的,其实是对归责责任的误解。由于标准合同文本源于英美法系,严格责任下的违约就不要求行为人有过错或过失。违约责任本质上是一种财产责任,其性质是以经济补偿为主,兼有一定程度的惩罚性。在赔偿范围上,英美法系主要包括期待利益、信赖利益和返还利益。违约引起的索赔具有限定性,英美法系主要采取两种形式进行限制:一是约定限制,在合同中约定损害赔偿最高限额;二是法定限制,即由国家以法律形式限制赔偿数额。“常见的限制规则有合理遇见规则、过错相抵规则和损益同销规则”[12]。违约是引起索赔的重要和常见因素,但有违约不一定引起索赔,即使没有违约也会产生索赔。违约责任不一定以发生损失为前提,即使没有发生实际损失,也要承担违约责任;而索赔必须以实际损失或实际延误为前提,没有损失就没有赔偿是索赔的基本原则。
索赔还有可能由侵权引起。大陆法系侵权行为法以法国和德国国内法律为代表。《法国民法典》所采用的是单一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德国法》归责原则采取了过错责任原则为主、特殊侵权危险责任为辅的原则。英美法系国家没有将侵权行为高度抽象化为成文法,仅仅从具体侵权行为的样态进行分类。英美普通法中采取了“事实本身证明”的原则,以避免原告举证困难,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13]。在中国,关于侵权的归责原则学界争议很大,通常归责是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与公平责任等特殊侵权原则为补充。侵权责任的构成方式来源于当事国的法律规定,当事人不能约定,否则无效。
违约与侵权是两大法系的共同归责理由。在同一索赔事件中,可能既存在违约,也同时存在侵权,即出现违约与侵权的竞合。在工程实践中,主要集中在承包商设计产品瑕疵等造成的损害责任。发生侵权与违约竞合,各国处理方式差别很大。以往英国有判例,如果一方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其高于违约的救济金额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按照中国法律,对于责任竞合,守约方可以在违约与侵权中任意选择一个向法院起诉,侵权的赔偿额有时会高于违约的赔偿额。
不可抗力是违约或侵权的共同法定责任解除理由,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解除违约方或侵权方的责任。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源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该法典第1148条规定:“如债务人由于不可抗力或事变而未履行其给付或作为的债务,或违反约定从事禁止的行为时,不发生损害赔偿责任。”[14]除非有特别约定,发生不可抗力后,实行“谁损失、谁承担”的原则。不可抗力在英美法系类似的含义是“履行不能(act of God)”或“合同受阻(frustration)”,它构成了英美法系的免债理由。在英国,不可抗力靠“约定”而成,而“困难”、“不便”以及“金钱损失”都不是合同受阻的理由。美国法认为构成不可抗力的条件必须同时满足客观上履行已经变得“极难实施”、主观上在签订合同时无法预料这两个条件,主要从主观角度对与不可抗力相类似的“履约不能”加以界定。中国《合同法》和《侵权法》规定的不可抗力必须同时满足行为人不能遇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三要件,在理论上采取了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折中抗辩。1999年版的银皮书、红皮书和黄皮书第19条规定了不可抗力制度,在风险分配上,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分配给了雇主,承包商不但可以免责,还可以就其遭受的损失向雇主提出工期延长索赔或经济补偿索赔。在不可抗力的范围认定上,自然原因例如地震、洪水、泥石流、台风等因素,国际社会一般都以法律明文规定为不可抗力。但对于社会原因引起的战争、动乱、罢工、流行病、禁运、市场行情突变、政府干预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各国立法并不一致。各国司法实践中,对于不可抗力的使用有严格限定,并不能排除所有情况下承担责任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工程索赔首先要看合同文本的风险分配原则,风险分配给谁,对于合同当事人来说尤为关键。FIDIC银皮书打破了传统的平衡分配风险原则,把更多的风险转移给分包商。如果忽视合同文本的风险分配而盲目索赔,其索赔必然没有任何法理基础作为支撑。其次,合同条款是否与准据法或工程所在国法律相冲突,无效的合同条款不能作为合同索赔依据。最后,即使相同的合同条款,在不同国家适用时,由于归责原则不同,法律后果也可能大相径庭。中国的工程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企业在走出去时,必须加强涉外工程领域的法律和国际惯例研究,积极参加国际规则制定,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徐守文, 盛继亮. 浅谈国际工程索赔[J]. 人民黄河, 2000(12): 43-44.
[2] 陈勇强, 张水波. 国际工程索赔[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10.
[3] 杨德钦. 索赔的双向性[J]. 建筑经济, 1994(6): 46-49.
[4] WALKER DAVI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227.
[5] 中国工程师咨询协会. 设计采购施工(EPC)/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29.
[6] 仉乐. 国际工程总承包合同范本比较研究[D].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2007.
[7] REG THOMAS. 施工合同索赔[M]. 崔军, 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42.
[8] 张仲伯. 国际司法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70-177.
[9] 闵卫国. FIDIC合同条件适用性问题比较研究[D]. 武汉大学法学院,2013.
[10] 徐江. 新版合同范本三问题剖析与建议[J]. 建筑, 2013(9): 13.
[11] 王利民, 郭明龙. 民事责任归责原则新论[J]. 法学论坛,2006(6): 55-66.
[12] 贺为民. FIDIC合同条件下国际工程索赔的法律研究[D]. 郑州大学法学院,2003: 20-29.
[13] 刘晨光. 民事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论[D]. 安徽大学法学院,2004: 4-8.
[14] 白丽云. 略论“非典”疫情的不可抗力[J]. 陕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3): 23.
改回日期:2016-02-16
编 辑:戚永颖
编 审:张一驰
Legal basis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project claims
ZHANG Hao
(China Petroleum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Abstract:Claim in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project is recognized as the most complex, diffi cult and challenging problem. Legal basis of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project claim mainly includes the choice of contract, the terms of the applicable laws and doctrine of liability fi xation. Risk allocation principle should be the fi rst step in engineering project claims, risk is assigned to who is especially critical for the parties to a contract; second, contract terms should be applicable to proper law or the laws of the host country, the invalid contract terms cannot be taken as the basis of contract claim; last, even if the same terms of the contract, due to different doctrines of liability fi x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legal consequences may also be different.
Key words: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project; claims; applicable of law; doctrine of liability fi xation; contract
收稿日期:2015-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