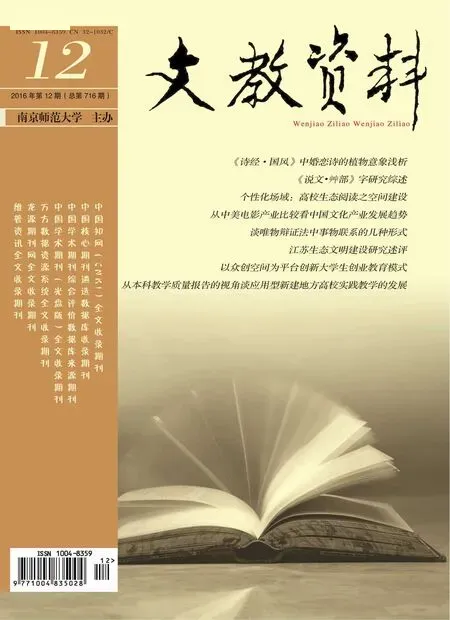《坛经》与中国意境诗论
陈 赟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坛经》与中国意境诗论
陈 赟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摘 要:《坛经》思想深刻影响了唐代以后的意境诗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性本清净”、“刹那顿悟”说与意境论的非功利题旨、非逻辑思维相通;“见性成佛”、“自性自度”说凸显了主体意识、自由精神在意境营中的核心地位;“不假文字”、“出语尽双”启发了诗境表述的言不尽意、若即若离。
关键词:《坛经》 意境诗论 思想影响
钱穆说:“唐代的禅宗,是中国史上的一段‘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禅宗的精神,完全要在现实人生之日常生活中认取,他们一片天机,自由自在,正是从宗教束缚中解放而重新回到现实人生来的第一声。运水担柴,莫非神通;嬉笑怒骂,全成妙道。中国此后文学艺术一切活泼自然、空灵洒脱的境界,论其意趣理致,几乎完全与禅宗精神发生内在而很深微的关系。”①目前关于《坛经》②与中国哲学、美学、文学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但由于《坛经》思想博大深奥,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拟就《坛经》与中国意境诗论的相似、相通之处进行探讨,致敬于钱穆先生。
一、“性本清净”、“刹那顿悟”与意境审美的非功利、非逻辑
在《坛经》的叙述中,惠能以一篇偈言打动了五祖弘忍,击败了博学多才的师兄神秀,获得了弘忍传授的禅宗衣钵。在这篇禅宗史上最为著名的偈言中,惠能提出了 “性本清净”的基本人性预设: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八)
“性本清净”的主张是针对神秀的偈提出的,神秀在偈言中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常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意为人性里总是充斥着七情六欲,就像沾满尘灰的镜子,人若想完善自己、获得佛性,必须像擦掉镜子上的尘灰一样,不断克制世俗的欲望,刻苦清修,才能超越世俗的纷争,提升自我,接近佛性,获取终极解脱。此种观点与印度禅的思想基本一致,但根据《坛经》的记载,弘忍对此偈言的评价是“只到门前,尚未得入”。神秀这一永不停息的“拂拭”苦修意象中,暗含人心永远无法摆脱俗念、永远无法产地成佛的悲哀命运,不仅难以吸引众生,而且无法解决如何由人性过渡到佛性这个理论难题。有鉴于此,惠能大胆地提出了“性本清静”之说,认为人性即佛性,心灵本是道的源头和本质,不需要向外在模仿,顺其自然,即可实现清净。在《坛经》的描述中,此种“清净之心”体现为广阔无边、包容万象又虚空如幻、物我两忘的境界:
“摩诃”者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二四)
善知识,此法门中,坐禅元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言不动。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净,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不见自性本净,起心看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故知看者却是妄也……看心看净,却是障道因缘。(一八)
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本性自净自定,只缘触境,触即乱,离相不乱即定。(一九)
此种与佛性无二的清净天性,与生俱来,人人皆有,只因受外部世界之名利妄念的覆盖和污染,才逐渐滞缚并最终迷失:
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一二)
自性无非、无乱、无痴,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有何可立?(四一)
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森罗,一时皆现。世人性净,犹如青天,惠如日,智如月,知慧常明。于外著境,妄念浮云覆盖,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识开真法,吹却迷妄,内外明澈,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二〇)
因此,“成佛”、“解脱”不再是清苦修炼、压制欲望的不懈努力,也不再是任重道远、上下求索的艰难寻觅,而变成充满温情的回乡之旅,顺其自然的“刹那顿悟”之思:
心明便悟。(二)
此但是顿教,亦名为大乘,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三六)
令学道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三一)
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是佛。(三五)
作为一种论辩策略,“性本清净”之说使禅宗的求道成佛在理论上看起来更乐观和简易,也更符合人性,在方法上与孟子的“性善”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一种精神理想,“清净”本性对物质世界的拒绝和排斥,为心灵打开一扇澄明洁净的窗口,从而破除种种迷妄杂念,“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从文论角度看,“性本清净”让我们想起道家“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涤除”、“玄览”、“心斋”、“坐驰”的审美心境,并与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美学家“无功利关系”的审美态度遥相呼应,王国维“无我之境”受益于此。而“刹那顿悟”说则与“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创作灵感息息相通,直接启发后世“禅道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的注重直觉的诗境创作论。
二、“见性成佛”、“自性自度”与意境营造的主体意识、自由精神
以“性本清净”为前提,《坛经》把修炼重心放在心灵上,提出“见性成佛”、“自性自度”之说。惠能认为,佛教追求的最高目标不是西方净土极乐世界,不是摆脱三世轮回的永恒不灭,也不是看破红尘万事皆空,而是心灵的自然清净。佛经中描述的种种诱人景象不过是心性的象征:
西方净土是人心,慈悲是观音,喜舍是势至,能净是释迦,平直是弥勒,人我是须弥,邪心是大海,烦恼是波浪,毒心是恶龙,尘劳是鱼鳖,虚妄是神鬼,三毒是地狱,愚痴是畜生,十善是天堂。(三五)
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二三)
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惠。(四一)
因此,学佛修道不需要坐禅,不需要诵经,不需要清规戒律,不需外求他人,只需从内心入手,顺其自然,“见性成佛”:
迷念年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三五)
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有迷心,外修觅佛,未悟本性,即是小根人。闻其顿教,不假外修,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烦恼尘劳众生,当时尽悟,犹如大海,纳于众流,小水大水,合为一体,即是见性。(二九)
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一四)
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若外求善知识,无有是处。(三一)
吾见自知,岂代汝迷?汝若自见,亦不代吾迷,何不自修,问吾见否③。(四四)
佛并不存在于身心之外的某个地方,也不存在于记载佛理的诸经之中,甚至在传道师父那里也找不到,“外修”或借助外人的帮助也没用,只能在“自净其心”、“常行直心”中“顿悟”才可以“见性成佛”。此种对自身性情的强调,对自身感悟的强调,大大抬高了心灵在心物之间的地位,人类的主体性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个体心灵成为确认禅道的核心标准,“自性自度”成为修禅的最高目标:“故知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三〇),“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八),归依三身佛变成了“自归依”、“自悟自修”(二〇),四弘大愿“不是惠能度”而是“各于自身自性自度”(二一),忏悔则是“自性若除”(二二);连佛经也被心灵解构了,“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开佛知见转《法华》,开众生知见被《法华》转”(四二),其结果是,“心地常自开佛知见,莫开众生知见”(四二),客观的、普遍的、群体的价值观念被抛弃,个性的、独特的、神秘性的体验得到了重视。此种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背离了印度佛教的教义,与中国先秦庄子对主体精神的推崇更为相近,因此被认为是中国佛学的典型思想。
从诗论上看,“见性成佛、自性自度”之说强化了魏晋庄学影响下的“形似不如神似”的观点,大大提高了主体精神在意境营造中的地位,并把艺术论中的“神”从可感的精神气质引向了神秘的终极理想,为后世诗论中最为复杂丰富的意境论及盛行于唐宋的“以禅喻诗”之批评方法提供了理论资源。
三、“不假文字”、“出语尽双”与意境表述的言不尽意、若即若离
文学以语言文字为基本载体,文学批评必然涉及语言文字研究和讨论。中国古代文论中对语言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炼字、声律、用典等具体技巧层面,产足于语言文字之基本性质与功能的理论探讨不多,在庄子与《周易·系辞》提出著名的“言不尽意”论之后,惠能以更为极端的态度再次介入这一话题。《坛经》多次表达了对语言文字表意功能的不信任:
法以心传心,当令自悟。(九)
自悟修行,不在口诤,若诤先后,即是迷人。(一三)
迷人口念,智者心行。(二五、二六)
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二八)
吾心正定,即是持经。(四二)
惠能认为,禅法的真谛不在语言上,口头的争论或虔诚的诵读都是无益的;文字作为语言之记录符号,能指之能指,自然更无助于理解佛法,因此他要求信徒们“不假文字”、“以心传心”。据《坛经》的记载,惠能并不识字,读经写偈都是央求别人帮忙,但最后却成了弘忍门下继承禅宗衣钵的大师。也许是这种不识字又悟道的经历使他对语言文字的表意缺陷有着比别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语言、文字总是有限的、片面的、僵死的、外在的东西,借助系统的语法与词汇试图认识、描述变动不居的佛道时,反而束缚、阻碍了人们把握。因为禅宗的悟道是个体的、独特的神秘感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是不可言说的、“非思量”的东西。悟道:“不是知识或认识,而是个体对人生谜、生死关的参悟,当然不是通过普遍律则和共同规范所能传授,只有靠个体亲身体验才能获得……通过个体独特性的直觉方式获得。”④
但是,撇开语言文字进行“以心传心”艰难重重,禅宗灯录中记载了拈花示众、当头棒喝等一系列“不产文字,教外别传”的公案故事,绝大多数还是离不开“话头”,并最终由文字记载下来。尽管语言可能模糊、遮蔽乃至扭曲,但已经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思想的工具了。惠能只能回到语言上,主张出语尽双、于相离相,尽量避开语言的陷阱,消解语言与意义的矛盾:
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问法,出语两边,皆取法对,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四五)
外境无情对有五: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暗与明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
语与言对、法与相对有十二对:有为无为对,有色无色对,有相无相对,有漏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长与短对,高与下对。
自性居起用对有十九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崄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慈与害对,喜与嗔对,舍与悭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常与无常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体与用对,性与相对,有情与无亲对。
言语与法相对有十二对,内外境有无五对,三身有三对,都合成三十六对法也。(四六)
如何自性起用三十六对?共人言语,出外于相离相,入内于空离空。著空,即惟长无明;著相,即惟邪见谤法。直言不用文字,既言不用文字,人不合言语,言语即是文字。自性上说空,正语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语言除故。暗不自暗,以明故暗。暗不自暗,以明变暗。以暗显明,来去相因。三十六对,亦复如是。(四六)
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一七)
惠能首先在语言中总结了“三十六对”,通过对产概念的相互牵制消弭对确定性的执著,要求弟子们“出语两边,皆取法对”,提醒他们在明暗、有无、虚实、生死、色空、动静、清浊等问题上辨证理解,不仅知道“以明变暗”、“以暗显明”的对产面相生相成关系,还要知道语言与实体之间不是紧紧相扣的现象与本质,而是若即若离、不离不染的隐喻与象征,“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三一),唯其如此,方能内外不迷,“内外不迷,即离两边。外迷著相,内迷著空。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四二)。
概言之,“出语尽双”是对语言表达的要求,目的在于拆除语言划定的意义籓篱,在语言裂缝中追寻佛法精神;而“于相离相”则更多地着眼于语言的理解方式或态度,可视为对听众、读者的指引,要求读者、听众对语言中呈现的幻象保持应有的距离,做到“内外不迷”。
在“出语尽双”、“于相离相”的影响下,后代禅师中盛行参话头、究公案,用一些自相矛盾、答非所问的句子凸显佛法,无意中实现了佛教的“语言学转向”,“语言从承载意义的符号变成意义”,“宗教语言,渐渐变成文学中的语言艺术和语言游戏”,禅与诗在此种语言艺术和语言游戏中找到了一块共同的领地,拉近了僧人与诗人的距离,促进了禅与诗的交互影响,后世的诗歌意境论从中受益甚多,如王士祯《带经堂诗话》“须如禅家所谓不脱不粘,不即不离,乃为上乘”此类诗论,从理论到词语都深深地打上了禅宗的烙印。
注释:
①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3:166.
②《坛经》主要有四个本子,分别是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流通本)。宗宝本流传最广,而敦煌本时代最早,更接近惠能思想的本来面目。在此以敦煌本(中华书局《坛经校释》)为讨论的依据.
③此段文字出自惠昕本.敦煌本原作:“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惠能见否?吾不自知,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见,代得吾迷,何不自修,问吾见否。”文义晦涩难解,此选惠昕本以昭明其大旨.
④李泽厚.中国思想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208.
⑤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VOL2:93.
本论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项目《岭南文论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GD11XZW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