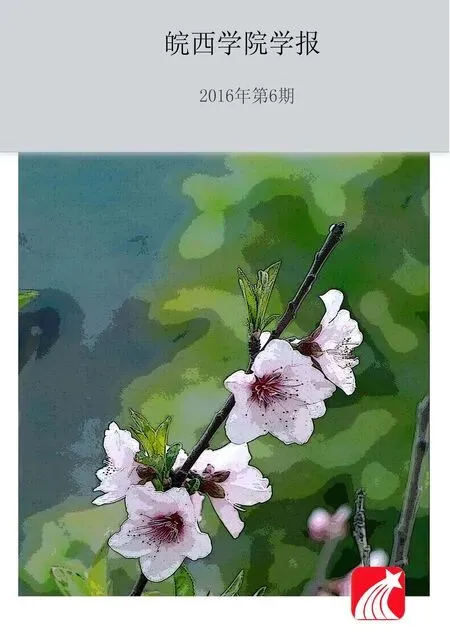安徽舒城方言中的实现体标记“得”
夏 华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安徽舒城方言中的实现体标记“得”
夏 华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舒城方言的实现体标记“得”可以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动作或性状的实现。“得”标记实现义有一定的特殊性,无法足句,对句中的宾语、谓语等语法成分有一定的限制性,经历了由结果动词虚化为体标记的语法化历程,是带有结果补语痕迹的实现体标记。
舒城方言;实现体标记;得
方言是记录地域文化的“活化石”,是人们获得情感共鸣的重要途径。中国地大物博,各地方言像万花筒一样绽放异彩,比如普通话用“了”表示动作的完成或性状的实现,上海话说“仔”,苏州话说“脱”,长沙话说“哒”等等。汉语方言中的实现体标记有着各自的特点,其复杂性给研究带来了难度,也正因如此,它们才引起了语法学界的普遍关注,成为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舒城县地处安徽省中部,大别山东麓,方言属于江淮官话中的洪巢片。舒城话用“得[t0]”来标记动作的实现,从已查阅的文献来看,目前还没有论文专门研究舒城方言中的实现体标记。程瑶(2010)在“舒城方言语法专题研究”这一大的语法框架里提到了舒城方言中的完成体标记“得”,“‘得’用在动词、形容词和动结式后,表示动作完毕、结束和产生了某种消失性结果。”[1]由于篇幅的原因,描写较为简单,不够深入。本文以舒城话里标记实现义的体助词“得”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得”的特殊用法、虚化历程和语法意义,明确“得”带有结果补语痕迹的实现体标记属性。
一、“得”的特殊用法
“得”可以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动作、性状、状态的实现,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了”。“得”没有足句的功能,句中须带数量成分或语气词,“得”对句中动词、形容词的语义有一定的限制性。
(一)N+V+得+C时量
“得”可以出现在“N+V+得+C时量”这样的结构里,“得”的后面是数量补语,强调动作所耗费的时量或者动作所涉及的客体完成的量。
(1)特去北京去得三天。(他去北京去了三天。)
(2)特睡得一个钟头。(他睡了一个钟头。)
(3)地栋路吾们走得四十分钟。(这段路我们走了四十分钟。)
(4)地课书吾念得三遍。(这课书我念了三遍。)
(5)地个戏吾只看得一半。(这个戏我只看了一半。)
如果“得”后面的补语是时量、动量词语,那么句子所表达的含义就是动作从开始到完成的时间的长短、量的多少,标记着动作的实现;如果“得”后面的宾语是时量、动量、物量词语做修饰语,那么句子所表达的含义是动作从开始到时间参照点完成的量的实现,并不表示事件的结束。
用“完成”还是“实现”来界定“得”类虚词,学界颇有争议。左思民(2003)认为完成体与实现体的区别是:“对实现体的最自然的理解是动词所指示的动作等已经成为现实,即由不存在变为存在。对完成体的最自然的理解是动词所指示的动作等已经结束,即由存在变为不存在”。[2]“实现”不强调结束,只要动作成为现实即可,“完成”强调动作的结束。本文参照此观点,认为用“实现体”归纳“得”的属性更具解释力,比如“地个戏吾只看得一半”后面往往还有后续小句“还有另一半没有看”,动作并未结束。
(二)N+V/A+得+(量)+O
助词“得”在本质上是属于“体”的语法范畴的。李讷、石毓智认为鉴别体标记属性的形式判断标准是:a)可以出现在“V+X+O”格式中的“X”的位置上;b)可以出现在“V+C+X+O”的位置上。[3]
(6)一把火烧得四五家房子。(一把火烧了四五家房子。)
(7)街个生意不错,卖得一大半货。(今天生意不错,卖了一大半货。)
(8)吾已经看完得五本书嘞。(我已经看完了五本书了。)
(9)小家伙么赖能吃,中午七完得三碗饭。(小孩子特别能吃,中午吃完了三碗饭。)
(10)第下头孬得好几年了。(这丫头傻了好几年了。)
“N+V/A+得+(量)+O”是“得”字句出现的最典型的句法环境,也是舒城话里最常用到的“得”字句式,参考a标准和b标准,这里的“得”是一个典型的体标记。
(三)N+V/A+得+嘞/喽/之①
(11)恰个钢笔掉得嘞,街个又把书弄掉得嘞。(前天钢笔掉了,今天又把书弄掉了。)
(12)吾看俚第侠子真料得喽。(我看你这个小孩子真完了。)
(13)拜给那贼跑得喽。(不要让那贼跑了。)
(14)雨停得嘞。(雨停了。)
(15)铅笔芯断得喽。(铅笔芯断了。)
(16)衣裳妈妈洗得嘞。(衣服妈妈洗了。)
(17)五道题四道题都错得喽。(五道题四道题都错了。)
(18)一箱苹果都烂得之。(一箱苹果都烂了。)
(19)自行车脚踏子坏得之。(自行车脚踏子坏了。)
(20)四大名著吾都看得之。(四大名著我都看了。)
(21)嗬嗨,关系搞僵得之。(哎呀,关系搞僵了。)
“得”可以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产生结果的实现,但是不能直接用于句末,所以需要与其他词连用,这说明了“得”的虚化程度不高,没有足句的功能。“得”用在句末,除了可以与“喽”、“嘞”连用,还可以与舒城话里另一个实现体标记“之”连用,表示结果的实现。“得”用在静态动词或性质形容词后,表示性质、状态的实现,主体事物从一种状态进入到了另一种状态。
(四)“得”句中动词、形容词的语义特征
1、“得”句中的动词具有[+消失]、[+消极]的语义特征
“得”字句中的动词要具有[+消失]的语义特征,但这只是词汇层面上的,在句式层面上,如果整个句子的语义相对于说话人来说是“消失”的,那么动词本身不具有[+消失]的语义特征,也可以进入“得”字句。
(22)吾打破得一个碗。(我打破了一个碗。)
(23)*吾补好得一个碗。(我补好了一个碗。)
(24)老丝凿个讲错得一道题。(老师昨天讲错了一道题。)
(25)*老丝凿个讲对得十道题。(老师昨天讲对了十道题。)
(26)吾卖得一丝家具。(我卖了一些家具。)
(27)*吾买得一丝家具,麻个就能崩进去了。(我买了一些家具,明天就能搬进去了。)
(28)吾买得一丝家具,还有一丝以后再买。(我买了一些家具,还有一些以后再买。)
(29)吾给得特三斤橘子。(我给了他三斤橘子。)
(30)*特给得吾三斤橘子,吾马上就给得他六块钱。(他给了我三斤橘子,我马上就给了他六块钱。)
(31)特给得吾三斤橘子,还有四斤末给。(他给了我三斤橘子,还有四斤没给。)
(32)*吾补好得一个碗。(我补好了一个碗。)
(33)吾补好得一个碗,还有三个碗没补。(我补好了一个碗,还有三个碗没补。)
“得”对进入句中的动词是有选择性的,表示“损失”的动词可以进入“得”字句,例如“卖家具”;而表示“获得”的动词不能进入“得”字句,例如“买家具”。“得”把控整个句子的语义倾向,同一个动词、同一个动结式,进入句子后如果表示“损失”、“消失”,可以附加“得”,但是如果表示“获得”、“完好”,后面不可以附加“得”,例如“吾给得特三斤橘子”可以说,而“特给得我三斤橘子”却不能说,因为前者表示的是一种损失义,后者表示的是获得义,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参照点就是说话人。
2、“得”句中的形容词具有[+变化]、[+消极]的语义特征
上文已经讨论过,“V得”结构对进入其中的动词的语义特征有着一定的限制性,同样的,对进入“V得”结构的形容词的语义特征也有一定的限制性。
(34)*教室静得很多。(教室静了很多。)
(35)教室亮得很多。(教室亮了很多。)
张国宪(1995)认为“用能否进入‘已经……了’格式和能否用‘没’修饰两项标准可以将形容词分为动态形容词和静态形容词”。[4]符合这两项标准的是动态形容词,表示事物的变化;不符合这两项标准的是静态形容词,表示事物的形状。“V得”结构中的形容词表示变化的结果,“得”表示这种结果的完成或实现,因此,该格式中的形容词是动态形容词,具有[+变化]的语义特征。
(36)电脑坏得好几天了。(电脑坏了好几天了。)
(37)*电脑好得好几天了。(电脑好得好几天了。)
(38)考试特错得好几题。(考试他错了好几题。)
(39)*考试特对得好几题。(考试他对了好几题。)
上文所论述的“得”对动词的语义特征限制在这里对进入“V得”结构中的形容词也同样适用。表示消极意义的,比如坏、傻、暗、错、臭等等,这些形容词可以进入“V得”结构;而表示积极意义的,比如好、聪明、亮、对、香等等,这些形容词不能进入“V得”结构。
二、“得”的虚化历程
“得”在舒城方言中除了有实现体助词的用法,还有结果动词、结果助词的用法。结果补语是实现体标记的一个重要来源,体标记一般是动词经历语法化后的产物,即经历“动词→助动词→体助词”这样一个语法化历程。刘丹青(1996)构拟了结果补语向体标记虚化的几个阶段:能补谓词——唯补词——补语性体标记——纯体助词。舒城方言的“得”是一个补语性的体标记,它的虚化历程在方言的共时层面上还留有明显的痕迹。
(一)“得”可以用作结果动词
(40)七得!/看得!/脱得!/卖得!/扔得!/洗得!/切得!/冲得!/煮得!/ 写得!/做得!叠得!/冲得!
“得”用在动词性非主谓句的句末,语音较强、未弱化,构成“V+得”的结构,表示说话人的命令、意愿,具有劝说义,用于长辈对晚辈、老师对学生、领导对下属等。这里的“得”类似于 “掉”,上面的动词后的“得”均可以用“掉”来替换,意义不变。而且“得”是所在VP的表达中心,说听双方的语义焦点并不在“吃”、“看”、“脱”、“卖”等等这些动词的动作行为上,而是在“得”所传达的动作行为产生的结果上。动词通常是预设,不是新信息,而结果补语才是句子的新信息所在。
“得”作为结果动词不能用于动结式与双音节动词后:
(41)*七完得!/看完得!/脱掉得!/卖掉得!
(42)*研究得!/分析得!/考虑得!/处理得!/介绍得!/准备得!/翻译得!/收集得!
结果动词“得”可以重读,可以作为句子的焦点信息,有一定的词汇意义,不能用在动结式和双音节动词后。由于结果动词“得”具有“V-掉”结构中“掉”的语法特征,因此本文将这里的“得”看作是一个只能作补语的结果动词,不单独作谓语,只能跟在其他动词之后作结果补语,有丢失、达到、结束等表示结果的意义。
(二)“得”可以用作结果助词
用作结果助词的“得”可以用在动词后,其后面有后续小句,特点是其语法意义有了一定程度的虚化,可以用在双音节动词后,也可以用在动结式后,有一定的“实现义”。
(43)吾饭七得再去找你。(我饭吃掉/了再去找你。)
(44)俚作业做得才能去玩。(你作业做完/了才能去玩。)
(45)电影看得吾就回家。(电影看完/了我就回家。)
(46)特们走得吾才能坐哈来做自己的事。(他们走掉/了我才能坐下来做自己的事。)
结果助词“得”出现在紧缩句中,有后续小句。这里的句子所含的意义是前一动作完成后再发生后一动作,或前一动作是后一动作的假设条件。从时制的表达的角度来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件在表达时间信息的时候,它们彼此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得”多用于前景句中,一般不能用于背景句中。结果助词“得”与结果动词“得”相比,性质已有所不同。结果助词“得”的意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虚化,因为与结果动词“得”不能与双音节动词、动结式结合不同,结果助词“得”可以用于双音节动词和动结式后,表示实现某个动作。
(47)俚把资料分析得再来找吾。(你把资料分析掉/了再来找我。)
(48)吾把第丝剩菜处理得才能上街。(我把这些剩菜处理完/了才能上街。)
(49)把新来的同学介绍得就上课。(把新来的同学介绍完/了就上课。)
(50)吾饭七完得再去找你。(我饭吃完了再去找你。)
(51)俚作业做完得才能去玩。(你作业做完了才能去玩。)
有些例句中的“得”已经不能简单地用“掉”来替换,可以直接对应于“了”。结果助词“得”的语音弱化,在句中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不能单独充当谓语,不是充当补语,因此本文不能将它归到实词的范畴里,只能归到虚词的范畴中。但是结果助词“得”又不同于动态助词,因为不能说“吾七得饭再去(我吃了饭再去)”、“俚做得作业才能去玩(你做了作业才能去玩)”,即不能用于动宾之间,因此本文将这里的“得”看作结果助词②。
(三)实现体助词“得”的语法化历程
“得”在舒城方言中有结果动词、结果助词、动态助词这三种用法,三种用法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从共时层面上反映了语言变化的历时轨迹。这说明语言的变化发展并不是“一刀切”的,语言的阶段划分是粗线条的,同一阶段内的成分虚实有差异,同一个词在方言中,有虚化程度高的用法,也有虚化程度低的用法。我们将体助词“得”的虚化历程构拟为[结果动词—→结果助词—→补语性体标记]。实词虚化为体助词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一是句中位置前移,二是语音弱化,三是实义逐渐消失。
三、“得”的语法意义
“得”作为体标记与其他纯体助词不同:它不能用在句末,没有足句的功能;句子的宾语要与数量有关或受数量成分的修饰;进入“得”字句的动词、形容词要么本身具有“消失义”,要么进入句子后整个句子呈现一种“消失义”。因此,本文认为舒城方言的“得”是一个带有结果补语痕迹的实现体标记。其语法意义较为虚的一面体现在:a.可以表示动作的实现、状态的达成。b.在句中的时候,意义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了”,能和“了”互换意义不变。c.可以用在动结式的后面,肯定结果的实现。d.前附性强,语音上,“得”只能跟前面的实词连读,语音较弱。e.语法结构上,没有可能式。这些虚的用法证明“得”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补语了,已经虚化成了体标记。
汉语中的体助词多由补语虚化而来,“得”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面貌,与它的语法化历程息息相关。如上文所述,“得”是由表示“消失义”的动词作补语逐渐虚化而来,因此本文将“得”看成是一个带有结果补语痕迹的补语性体标记。南方方言中,有一些与舒城方言“得”类似的带有结果补语痕迹的实现体标记,比如安徽芜湖清水话的“得”[5]、苏州话的“脱”[6]、江苏常熟练塘话的“开”[7]等等。舒城话“得”[t0]与吴语里的“脱”[t‘5]在语音形式上非常接近,句法分布、语法意义也比较类似。这些相似的体标记的来源可能是一个词,这个词在经历了时间、地理、语言上的种种变化历程后,在各自的方言里留下了不同的语音形式,虽然语音外壳不同,但是它们的语法意义、句法特征、附带的词汇意义有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不过这只是一种猜测,至于它们之间具体的关系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论证,这对于方言类型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喽”、“嘞”是舒城话里比较常见的位于句末的语气词,它们的主要功能是足句,并且可以用于表示变化的句子里。“之”是舒城话里又一特殊的实现体标记,使用范围广泛,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了”。
② “结果动词”、“结果助词”的说法均参考了范晓(1988)的研究成果,范晓在《吴语“V-脱”中的“脱”》一文中提出将吴语中的“脱1”看成是“结果动词”,该文收录于《吾语论丛》[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第217页。
[1]程瑶.舒城方言语法专题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4):48-59.
[2]左思民.上海话中时态助词“仔”的语法意义[A].吴语研究——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香港语文学会编,2003(1):202-206.
[3]李讷,石毓智.论汉语体标记诞生的机制[J].中国语文,1997(2):82-96.
[4]张国宪.现代汉语的动态形容词[J].中国语文,1995(3):221-229.
[5]胡德明.安徽芜湖清水话中对象完成体标记“得”[J].方言,2008(4):325-328.
[6]范晓.吴语“V-脱”中的“脱”[A].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吴语研究室.吴语论丛[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214-222.
[7]王健.江苏常熟练塘话的准体标记“开”——附论“得、过、脱、好”[J].方言,2008(4):318-324.
OnRealized Aspectual Marker “[t0]” in Shucheng Dialect
XIA Hu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llege, Anhui Radio & TV University, Hefei 230022, China)
As a realized aspectual marker in Shucheng dialect, “[t0]” could be used after verbs or adjectives in indicating the realized meaning of an event. There are some particularities when “[t0]” indicates the realized meaning. It could not be set at the end of a sentence and has some restriction for the object or predicate in the sentence. It is a realized aspectual marker with the imprint of result complement, after the grammaticalization from a verb related with results to an aspectual marker.
Shucheng dialect; realized aspectual marker; “[t0]”
2016-03-16
夏华(1987-),女,安徽舒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代汉语。
H172.4
A
1009-9735(2016)06-0025-05
——以舒城县开展精准扶贫为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