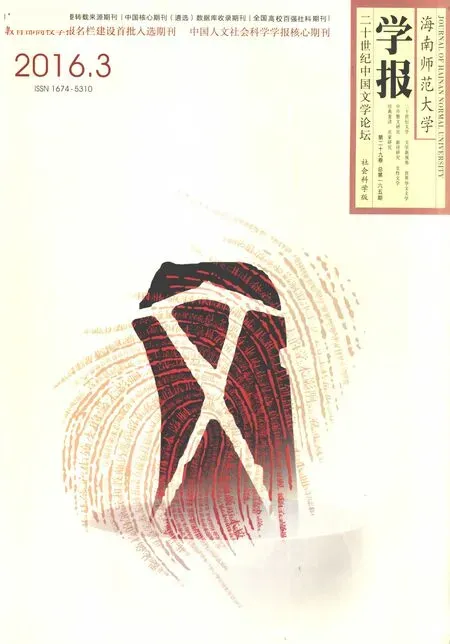从意识流看王蒙的“沉默”和政治情怀
——读《海的梦》兼论王蒙新时期意识流作品
王学森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从意识流看王蒙的“沉默”和政治情怀
——读《海的梦》兼论王蒙新时期意识流作品
王学森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王蒙重回文学界,以意识流的手法在人们眼前一亮。但80年代初的文学场并没有给文学自身留出足够的话语空间,而是处在意识形态纷争的阶段,形成了“伤痕文学”的创作热潮和“去政治化”的文艺思潮。同时占据政治权力的一方又对此充满了警惕和排斥。对于怀有忠诚革命信念的王蒙来说,也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海的梦》抒发了经受“文革”迫害的知识分子缪可言在新时期的内心感触,意识流的手法将这种感触刻画得浓郁而含混。也就是说,以《海的梦》为代表的意识流作品不只是一种文艺形式,更代表了王蒙的一种政治话语模式——“沉默”,他将所有的痛苦揉碎、潜藏在飘荡的文字里,以一种温和、沉闷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话语,并因此而获得到了文学场的重要位置。
关键词:王蒙;《海的梦》;意识流;沉默;政治情怀
20世纪80年代初,王蒙的作品以意识流的手法在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从1979年到1980年,《布礼》《夜的眼》《风筝飘带》《蝴蝶》《春之声》《海的梦》等几篇被称为“意识流”的中短篇小说,如同抛掷的“集束手榴弹”,引起了一场关于文学叙述方式的艺术革命。故事情节的淡化、浓重的心理描写、跳跃的思维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陌生感,也因此引起了一些评论者的不解。
在刚刚“解冻”的新时期,西方现代派的手法和文艺理论大量被译介到中国,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并且很快引起了关于现代派与现实主义的讨论,对王蒙意识流创作的讨论也被列为其中。保守派否定了意识流在小说创作中的非典型性,坚持传统现实主义写作中体现的鲜明的社会功能。“王蒙近两年多来的小说,竭力描写人的情绪、感受和心理,竭力寻找人的意识活动的秘密,在这方面,应当说是有成绩的。但是,王蒙却有意无意地丢掉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李从宗:《王蒙寻找到了什么?——评王蒙近期小说创作的得失》,《思想战线》1998年第2期。尽管如此,由于“1976年底“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文学并未在较大的范围里实现从‘文革文学’的转变。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取材和艺术方法,仍然是‘文革文学’的沿袭”*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0页。,所以,王蒙的出现无疑令人耳目一新,他的“意识流”对传统艺术手法来说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对开启新时期文学的时代具有革命性的作用,他的意识流创作也以创新探索的姿态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赞扬:“王蒙同志以艺术家的睿智和勇气,开拓了艺术的新天地。他的小说创作富有鲜明的时代感,洋溢着强烈而又独特的创新精神。”*陆贵山:《谈王蒙小说创作的创新》,《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因此,在新时期文学的哀怨和诉求声中,王蒙选择了艺术形式的探索作为回归“文学主体”的文化资源,也对文学艺术性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是具有文体先锋意义的。
但是,新时期文学的思潮变动远比单纯地对文学形式的讨论要复杂得多,其中蕴含着权力关系的较量和更新,整体表现为“文学本体”、“人道主义”与“工具论”、“集体主义”、“政治话语”主流置换的现象,处于文学与政治话语重新定位的阶段,形成了“伤痕文学”的创作热潮和“去政治化”的文艺现象,宏观来看还是一场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
在政治权力中心存在着顽固的保守势力,对文学界进行一次次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他们对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政治领域的异化”和“思想领域的异化”充满警惕和怀疑。“朦胧派”诗歌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传入让保守派惊恐不安,他们把“人道主义”看成是价值观的异化,其主要原因是他们仍然秉持着“文艺工具论”,把文学作为政治的宣传语,局限在僵化的教条主义思维中。从左翼文学到“文革”文学,革命文学、政治宣传式文学等书写模式改变了从审美出发的文学艺术性,形成了文学评价的政治标准,书写者和评论者在这漫长的过程中经受政治性文艺理论的灌输,并且从中体会到权力关系的作用,自然地养成了运用权力话语的习性。其次,保守派对“现代派”思想和写作手法排斥是因为“现代派”所代表的是“西方”话语。在“文革”中,“西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成为了语言、思想的禁区,知识分子因其还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即使“文革”结束,他们仍心有余悸。在“文革”结束初期,知识分子仍然是以怀疑、保守的眼光看待一切,自然对“西方”的现代派非常敏感谨慎,时刻要求作品的社会主义意识。尽管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已经呈现出缓和的趋势,权力意志对文学的干预也在减弱,但是,文学作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功能在各大文艺座谈会上仍然是强调的重中之重。而作为文艺革新的一派,在批判“黑八线”的同时,也极力呼吁文学的去政治化,要求回到文学自身,尤其是在“伤痕文学”、“人道主义”以及“现代派”被定义为精神流毒后,这种呼声便更加高涨。1979年1月《戏剧艺术》上发表的《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4月《上海文学》刊登的《为文艺而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等多篇评论都在明确指出要摆脱政治对文学的干预。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对朦胧诗的肯定,在文学审美上也肯定了文学的自主性。因此,这不仅是一个转折的时代,也是一个权力抗争的时代。新时代的开启不如人们的憧憬一般,它遇到了巨大的挑战——政治权力,并且政治话语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写作者,不得不面临着选择和被选择的命运。“除了自然年龄上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由于文学观念和与此相关的创造力原因的分化和更替。因而,在80年代,也出现了如四五十年代之交作家大规模分化和重组的现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32页。在80年代初由于“市场”的缺席,此次重组主要是文艺自身与政治权力的分化、对立。
王蒙固然也面临着这种抉择的。从表面看来他的作品更贴近于艺术手法的探索,王蒙也从政治诗人变成了文学的革命家。然而,从文本内部看,他的意识流作品里蕴含着面对抉择时的态度,并且流露出明显的革命意志。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这样写道,“即便是他后来借助西方现代派创作技巧创作的一批被称为‘意识流’的小说……从创作的主题来看仍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只不过作者创作的姿态与以往相比显出了矛盾性……”*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第412页。“一方面他整个身心被这种意识形态所浸透,他的艺术构思中不由自主地会流露出对为此奉献了他青春、理想和爱情的岁月最真诚的抒情(这种真诚性也使他在对当代社会履行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时抱着宽和的态度),可另方面他也为自己曾经付出过、然而被历史证明是无谓的代价恼怒不已……”*陈思和:《关于乌托邦语言的一点感想——致郜元宝,谈王蒙小说的特色》,《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确实,尤其是在《海的梦》中,这种现象十分明显。
《海的梦》的故事情节并不突出,它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主要是对个人情绪的抒发,对人生的沉思。心理描写的是主人公缪可言经历“文革”后对个人生存的思考,故事情节的淡化为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表达欲望提供了充足的话语空间。“晚了,晚了。生命的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俱往矣,青春,爱情,和海的梦!”*王蒙:《王蒙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缪可言这些直白的感慨之语是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的真实感受!他的青春消耗在被压迫的年代里,现在留给他的只是一副年老的躯体。这与韶光易逝的感慨并不相同,“文革”10年是被偷走的10年,是被掠夺的10年,是被强行切割的10年。“五十岁了,他没有得到爱情,他没有见过海洋,更谈不上飞翔……然而他却几乎被风浪所吞噬。你在哪里呢?年轻勇敢的船长?”“然而,激情在哪里……欢乐和悲伤的眼泪的热度在哪里?”面对着“文革”的结束,缪可言首先体会到的是失落和彷徨。这些疑问,就像一句句的责难、一句句的哭诉,是面对衰老的苦恼和绝望,道出了王蒙和所有知识分子的心声。同时,作品中大量的景物描写,也为作品奠定了沉闷的基调。“是一匹与灰蒙蒙的天空浑成一体,然而比天的灰更深、更亮也更纯的灰色的绸缎。是高高地悬在地平线上的一层乳胶。隐隐约约,开始看到了绸缎的摆拂与乳胶的颤抖,看到了在笔直的水平线上下时隐时现、时聚时分的曲线,看到了昙花一现地生生灭灭的雪白的浪花。这是什么声音?是真的吗?在发动机的嗡嗡与车轮的沙沙声中,他若有若无地开始听到了浪花飞溅的溅溅声响。阴云被高速行驶的汽车越来越抛在后面了。”“他住的疗养所栽着许多花。低头可以赏花,抬头可以望海。可以站在前廊上数过往的帆船的数目。夜间,大家都入睡了以后,他可以清晰地听到大海的潮声,像儿时听到了睡眠着的母亲的呼吸。大海有多悠久,这海的呼吸就有多悠久。大海有多沉着,这海潮的起伏就有多沉着。而当海风骤紧了的时候,他听得到海的咆哮,海的呐喊,海的欢呼,好像是千军万马的厮杀。”海的辽阔、厚重,色彩的昏暗,以及缪可言面对这些景物的沉思、冥想、宁静赋予了作品浓郁的感伤情调。尽管如此,王蒙最终让缪可言在小说的结尾找回了希望,“爱情,青春,自由的波涛,一代又一代地流动着,翻腾着,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淡漠,更永远不会中断。它们永远和海,和月,和风,和天空在一起。”从情感上看,缪可言的内心是矛盾的,饱含幽怨的,但却又不得不表现出一种豁达的心胸。但对于王蒙的书写来说,这正是他面对文学场权力纷争的一种叙事策略。
通过意识流的手法,王蒙实现了内心忧愤的表达,但是意识流的语言是抽象的,它的表达不像传统现实主义手法那样具体、典型,也不像“伤痕”的情感一般声嘶力竭、痛彻心扉。丰富的心理描写和象征手法的运用,以及语言的晦涩、时序的跳转使得痛苦之情变得浓郁而含混。并且故事的结尾,王蒙已然找回了自己的政治热情。因此,王蒙面对曾经的劫难是选择了“沉默”,意识流的手法绕开了“伤痕”式苦难的书写,同时也抒发了知识分子内心的苦闷。这样来看,朱栋霖等所说的“矛盾”也不再成其为矛盾,意识流的文学手法也不只是传统定义中的文学形式的意义,而是赋予了话语策略的价值,它以“沉默”的方式表达出内心的想法。除此之外,对王蒙至关重要的是在“沉默”中坚守了政治情怀,在文学场中赢得了政治话语权威。王蒙的“沉默”是政治情怀的避难所,也是政治书写的另一种方式。“沉默”不只为了逃避抉择的两难,也是对“分化现象”的态度,尤其是对一直秉承的革命书写的延续。
经过了10年“文革”,王蒙对极端主义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既不能左也不能右。很多评论者便将王蒙看成了“中庸主义者”或“犬儒主义者”,但王蒙则将其视为自己的生命哲学。“学术问题上吵吵闹闹,这乃是正常的现象。这种争吵往往并不一定意味着什么阶级斗争,人们所以对一个学术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和各人的不同的社会地位、世界观、知识面、切身感受、思想修养以及个性、习惯和专业造诣等等有关,也和历史的局限、民族的局限有关,呈现了非常错综复杂的状态,完全不必要予以统一、事事搞它个整齐划一。但是我们却已经习惯了一边倒,自以为正确的人也就自以为有权对谬误实行专政,其实,正确和谬误是认识论的概念,而专政、占领则完全不是认识论的概念,把这样的概念引入认识论,实在是奇谈。正确和谬误有时一时分辨不清,有时共存、交织在一个流派、一个人或一篇文章里,有时又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因此,正确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向谬误进行专政的,真理是不需要、也无法对偏见进行专政的,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只能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去解决,这就要实行‘费厄泼赖’。”*王蒙:《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读书》1980年第1期。这段论述显示出王蒙公正、宽容的态度,也明确体现了他对新时期文学争论的立场。这种宏观的言论看似不偏不倚,但是反映了实质性的问题的存在:权力意志对文学依然强加干涉,并且这种干涉具有外部力量强制指挥的性质。而王蒙的智者宽和姿态体现了他的政治话语书写的优越性以及对政治权力的认同感。
在《海的梦》中,王蒙没有竭力去痛批“文革”对整个国家、对几代知识分子的践踏和迫害。小说中只有几笔写到“江青”“号子”等,然后便回到缪可言对青春逝去的感慨上,它并没有耗费大量笔墨去细致地描写被压迫的过程和痛苦。王蒙的这种理性当然也是对“文革”带有批评色彩的,然而这种批评是有局限性的。缪可言也没有止于苦恼,而是超越了个人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层面,对政治生活重新作出了抉择。缪可言从绝望到希望,是通过他对历史的回顾,对自身处境的定位,对现在人们思想的感受,潜移默化中再一次燃起了对生活的热爱和政治的热情。对于这样人物的塑造不只限于缪可言,还有《布礼》中的钟亦成、《蝴蝶》中的张思远、《春之声》中的岳之峰等等都是经历了“文革”迫害,但也都坚守着忠诚的革命信仰。因此,“缪可言们”的塑造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个鲜活的革命人物形象,也可以是一种新时期的选择,是一种政治生活的方式。王蒙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要被超越的,他们对自身的思考远远不及对革命的憧憬。但是在80年代之初,文学争论的矛头是直指政治话语的,作品要打破了样板戏的公式化书写和空想的革命乌托邦世界。80年代初的文艺作品除了“伤痕”还有对爱情、乡土、战事等题材的描写,却很少再有直接表达政治革命热情的作品。而王蒙的这几篇小说都通过对个人命运和理想的思考,来表达对国家民族使命的忠贞不渝,树立起为民众为民族代言的形象。因此,王蒙的意识流手法是革命书写的外衣,是延续政治话语和革命热情的新颖模式。
“还有另一些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识地引入了政治激情。这种丧失知识分子精神操守的行为比起诗人来更值得关注。我这里要说的是小说家和剧作家。他们本来的职责是尽可能客观地描述人的精神运动及其冲突,莎士比亚、莫里哀和巴尔扎克都证明了可以不折不扣地实现它。但是这种职责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为了服务于政治目的而遭到违背,许多当代小说家就是明证。”*[法]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1页。朱利安·班达把对政治热情的迎合看成知识分子的背叛,是丧失了知识分子精神操守的行为。显然这种说法是有偏颇的,陷入了狭隘的本质主义囹圄,艾略特对此也批评道,“我提出这些事情仅仅是为了指出文人们对实际事务中的干预(这就是班达先生所反对的)只是表现了一种普遍的混淆现象。议论世事的公众人物回应的是公众在世事上适度而多变的利益要求。所有这些都太平常不过了,我提出这一点只是为了说明事实上很难在美国式庸俗的学者和兴趣广泛的‘知识分子’之间划出一条界线。而且,把所有被指责越俎代庖或者迎合大众政治激情的知识分子都归为一类,也是错误的。”王蒙政治书写是因为他自身的政治热情,“政治”因素是他创作的源泉,“政治”就是他的生命,而且他对政治的书写并不是以扭曲现实、歪解现实为代价,是真诚的诗性的自我表达。随着文学思潮的丰富,创作手法的多样化,人们对意识形态的书写也越来越少。即使与王蒙同时代的作家,经受了同样的革命理想主义的洗礼也逐渐偏离了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写书方式,如张洁对女性书写的深入探讨、冯骥才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张贤亮向大众文化的转变,而王蒙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书写倾向,无疑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体现了其独特价值。从王蒙的创作历程来看,新时期的作品也必然归属到其革命书写的整体中,并且解读的空间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展开,而对其“意识流”手法的研究也只能从与政治情怀的独特关系挖掘更深入的内在价值。“艺术语言是艺术思维的直接现实。适应着作品的思想感情内容及其艺术表现的需求……”*王振铎:《合乎规律的探索——王蒙小说〈海的梦〉及其它》,《中州学刊》1982年第3期。意识流便是王蒙直接的艺术表达,是合乎规律的表达,对历史劫难的“沉默”抒情正与其政治情怀相得益彰。
(责任编辑:毕光明)
An Interpretation ofADreamoftheSeaand A Discussion on Wang Meng’s Works of Stream-of-Consciousness
WANG Xue-sen
(SchoolofLiberalArts,HainanNormalUniversity,Haikou571158,China)
Abstract:In the early 1980s, Wang Meng was back in the literary world and appeared noticeable due to his use of some stream-of-consciousness techniques in his works. Nevertheless, because of the inadequate space of discourse for literature itself in the then literary arena, there arose the creative boom of “traumatic literature” and the “de-political” literature ideology in the phase of ideological disputes; while the party in possession of political power was fully alert and repulsive towards such a conduct in the literary world. For Wang Meng, a writer loyal to his revolutionary belief, it is impossible for him to be exclusive from such a trend of literary thought at that time. While A Dream of the Sea portrays the inner feelings of Miao Keyan—an intellectual persecuted during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in the new era, the feelings are pictured poignantly but ambiguously by virtue of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That is to say, works of stream-of-consciousness represented by A Dream of the Sea are not only a literary form but also a political discourse pattern of Wang Meng—“silence”, that is, Wang Meng has managed to crumble and conceal all his pain in his words and to express his political discourse in a mild and depressed manner, thereby having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literary world.
Key words:Wang Meng; A Dream of the Sea;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silence; political sentiments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3-0061-04
作者简介:王学森(1990-),男,山东德州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3级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