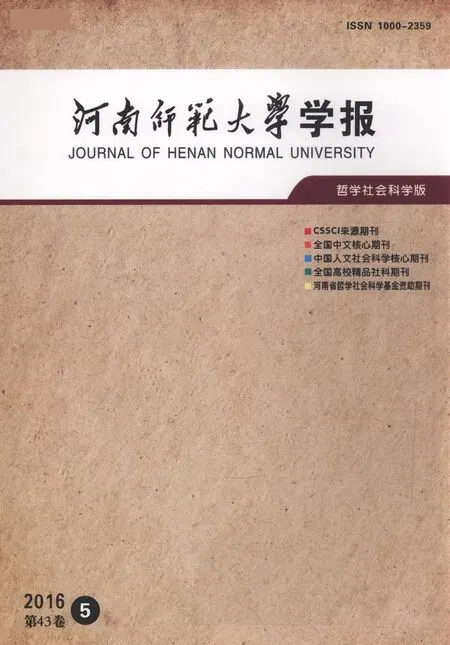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地球中心主义
——生态批评视域下的《瓦尔登湖》及其当代意义
刘 霞
(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地球中心主义
——生态批评视域下的《瓦尔登湖》及其当代意义
刘 霞
(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亨利·戴维·梭罗是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在自然中寻找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生态主义者,是现代生态文学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瓦尔登湖》描述了梭罗对自然的超验主义生活体验,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生共荣的生活画面,梭罗从地球中心主义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出发看待自然界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在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中寻求自我,对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表达了自己的隐忧。《瓦尔登湖》记录了梭罗关于自然的哲学思考,显示了超前的生态意识,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梭罗;《瓦尔登湖》;生态批评;人与自然;当代意义
如果说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是美国超验主义的精神领袖和哲学导师,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1]之一,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创者和民族民主文学的奠基者[2],自认为是爱默生学生的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就是超验主义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在自然中寻找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生态主义者,是现代生态文学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其代表作《瓦尔登湖》(又译为《湖滨散记》)充分体现了超验主义的思想,读者能从中通过对自然的欣赏获得审美愉悦,寻求精神的安慰和宁静,领悟到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附近生长着大片再生林,瓦尔登湖被浓密的树林包围其中,在这里梭罗度过了两年多闲云野鹤般的日子,他把这次经历称为简朴隐居生活的一次尝试,这期间他观察自然界四季变换和各种生命和谐共存,对大自然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美国文学历史中很少有作家能像他一样把毕生时光投身于大自然,探寻回归自然之路。直到20世纪50年代,梭罗的文学作品价值才得到人们的认可,《瓦尔登湖》后来被看作是塑造美国人性格的十部书籍之一,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会追随梭罗的脚步来到他曾经住过的树林和湖畔,极力追崇大自然的单纯与简朴。究其原因,不外乎“人们回归自然的需要和人们对自身环境越来越多的关切”[3]。本文将以生态批评为视域和方法论进一步分析梭罗的《瓦尔登湖》,分析表明梭罗在《瓦尔登湖》湖光山色、动物植物的描写中呈现出一幅人类与自然共存的和谐画面,梭罗以地球中心主义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出发看待人与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关系,对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表达了自己的隐忧。
一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威廉·霍沃思是生态批的主要代表,他认为:“生态批评家是对描绘文化对自然之影响的作品进行评价的人,他赞颂大自然,谴责对自然进行掠夺的人,同时他希望通过采取行动来逆转掠夺者对自然造成的破坏。”[4]国内专治生态文学批评的王诺则认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生态责任、文化批判、生态理想、生态预警和生态审美是其突出特点。”[5]27同时王诺认为生态批评的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审美目的上的自然性原则;审美视域上的整体性原则;审美方法来的交融性原则[6]。在生态批评视域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了全新的诠释,人不再被置于地球的中心,不再被想当然的认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而是由人类中心主义过渡到地球中心主义,由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共存、共生、共待的相对主义观念之下。可见,生态批评的核心是自然,是人类对自然的伦理关系和对待自然的态度,从哲学层面上讲,生态批评仍然是西方文学中几千年来关于人的本质属性的思考,是人类理性主义精神的合理延伸,是更高级的视域之内对人与自然系的重新审视,特洛亚战争结束之后,众英雄踏上了归乡之路,尤利西斯面对大海发出自豪的声音:我是最强大的,没有什么能战胜我,没有谁能把我打跨,从此整个西方世界被置与人与自然对立之中,人在驯服大海、征服自然之中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尤利西斯成了人类智慧的化身和理性的象征,他就是凭借智慧和理性战胜象征自然之强大力量的众多海怪之后最终回到家乡的,从此以后理性及对理性的苦苦追索与坚守就成了人类永久的宿命。但理性在西方人类史上又经历了多么复杂的变迁!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把理性归之于上帝,人成了匍匐在上帝面前的木偶,人成了没有精神主体性的物质躯壳——如果有,也只是宗教神性,文艺复兴把人从宗教牢笼里解救出来,再次张扬人本主义的大纛,却使人陷入感觉主义的泥潭,过分的感官享乐冲跨了理性的堤坝,启蒙主义又把人类的一切文明活动都置于理性观照之下,一切的一切包括上帝都要在理性的天平上去称量一番,凭理性获得其存在或者不存在的理由,在理性的观照之下,人的主体意识得以复苏并空前高涨,有学者认为:“启蒙运动张扬了人的理性,推崇了工具理性,加速了人的主体化和自然的人化,它将解放了的人,纳入形而上学的片面主体性之路,推进了人类与自然、殖民与反殖民、个体与社会、肉体与灵魂、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的矛盾冲突,启动了生态灾变的按钮,成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生发背景与根由。”[7]但启蒙的理性之光并没有照彻欧洲大地,启蒙主义者向往的“理性王国”也没有来到人间,当人们对污浊的城市文明,物质主义的工业文明厌倦了的时候,人们又一次回到自然之中,再一次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希冀从自然中找到失落的人类自我。对自然的向往与描写成为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根本主题,卢梭对原始的、古朴的、未受现代文明污染、未经雕琢的自然的描写达到如痴如醉的地位,华兹华斯在英国西北部湖区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中找到生活的宁静和灵魂安逸,拜伦在对辽远的天空、深邃的大海、苍茫的森林的歌咏中尽情宣泄并升华自己自由意志。卢梭、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等人在欧洲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到爱默生那里借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思想而成为超验主义的哲学观和自然主义的文学观。爱默生是一个清教徒,在他看来宇宙间存在着一种伟大的精神、永恒的神性,这种精神和神性是人之道德本善的根源,它存在于自然的每一角落——一座山丘,一股清泉,一片树叶,一颗小草,这一切都是上帝精神的象征,上帝借美丽的自然而显现,自然是人类与上帝沟通的中介和桥梁,人类的道德至善通过自然与上帝的永恒神性相统一,人的灵魂通过回归自然、融入自然得到净化与升华。但人对这神性的感悟并不通过逻辑推演与理性分析,而是通过直觉与感悟,或者说人的理性就是一种直觉能力,凭借直觉,通过自然,人可以与上帝直接对话,人可以直达对真理的认知,就爱默生的哲学思想而言,有学者认为:“爱默生的哲学思想中保持了唯一神教派强调人的价值的积极成分,又吸收了欧洲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超验主义观点,其基本出发点是反对权威,祟尚直觉;其核心是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2]作为爱默生的学生,梭罗深受其超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同时作为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文学家又与爱默生保持必要的距离,超验主义哲学让梭罗醉心于自然,把他的一生都托付给自然,用他的全部的身心追求自然的多姿多彩、宁静和谐;独立思考让梭罗抛却了爱默生神学观念和神性意识,以工业文明、工具理性给人类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为出发点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瓦尔登湖》记录了梭罗关于自然的哲学思考,描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生体验。梭罗在瓦尔登湖度过的生活是一次内心对大自然的探索旅程,正是在这里他的生态哲学思想得以形成,同时找到了理想生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在爱默生眼里,自然是超验的神秘的和具有神性色彩的“隐喻”,他以一种带有说教性质言辞和与“上帝”对话的目的去描写自然,而梭罗却以一种献身精神和激情去写近乎野性的原始的自然,梭罗完全放弃道德的说教只身投入的自然之中,寻求一种外在简朴、内心富有的生活方式,在瓦尔登湖畔两年多时光里,梭罗见证了那里的一切自然变化,包括人们对湖、周围的树以及树林里的动物所做的一切。在梭罗看来,瓦尔登湖是大自然的缩影,人类在这里的一切活动都代表着对整个大自然的态度。
在天气晴朗的夏天,从不远处看去,湖面呈现蔚蓝色,特别在水波荡漾的时候,而从很远的地方望过去,全是天水一色。赶上暴风雨的天气,水面有的时候呈现深石板色。不过,据说海水在大层中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下,却是今天蓝,明天绿。……瓦尔登湖一会儿蓝,一会绿,哪怕是从同一个视角看过去。瓦尔登位于天地之间,自然具有天地之色。从一个山顶望过去,它映现出蓝天的色彩,而从连岸边的沙子你都看得到的近处看,它却呈现出先是淡黄色,继而淡绿色,同时逐渐加深,终于变成了全湖一致的黛绿色。[8]132
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拜伦、弗·施莱格尔、布莱克、享特等也不断地抒写湖光山色、动物植物,他们的诗作也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不过他们与同属于浪漫主义的梭罗又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他们的湖光山色始终是诗人眼中的景色,他们描写动物植物始终是诗人主观情感的意象性表达,他们的诗作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是作者主体意识的映射,处处显示出作为主人的人的影子,是以人为中心对世界观照,显示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意识和哲学观念,“自然的审美对象仅仅当作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把它们当作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的工具”[6]。而梭罗则认识到人类终究只是自然万物的“一份子”,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相比并不高明多少,也不高级多少,人与自然是平等的,是互为主体的,人与自然从更高的范畴上说是一个完整和谐的整体。“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的文学”[5]24。在梭罗看来,无论动物还是植物,无论是水还是土壤抑或是人都只能是一个共同体中的一员,是自然宇宙公民群体中的一员,全体“公民”“处于同等的地位,有着同等的责任,有着同等的权益,有着相生互发的共生关系”[7]。然而,几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里的平静,这些掘冰人试图砸开湖面的冰块,其中一个不小心跌落水中,然后来到梭罗的小屋取暖,在梭罗看来,这是瓦尔登湖对这些不速之客的惩罚,而小鸟、鱼儿、小虫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自己只是他们的邻居。每天梭罗都会走进树林,来熟悉这些邻居,甚至会把自己小屋里的一只老鼠看作朋友,听任老鼠在自己的屋子里“安家”,每到用午餐时它就会爬到脚下寻觅面包屑,敏捷地越过脚面,并且顺着衣服爬到身上来,他会让老鼠爬到自己手掌上,饶有兴致的观看老鼠吃奶酪的过程,并用生动的文笔描绘他观察到的每一个细节。“小老鼠轻松的就能爬上屋内的墙壁上,如松鼠一般动作轻盈。有一天我如往常般闲坐着,它顺着我的衣袖往上爬,在已经放满了美食的杯子周边游走,我把杯子拉到一旁,故意不让它得逞,逗他玩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我拿起一块儿奶酪,它立刻就爬了过来,窝在我的手上,一点一点的品尝起来美食。”[9]210
梭罗给予多样性的生物与整个人类同样的尊重,觉得它们与人类并无差异,也没有高下等级之分,甚至是完全平等的。畅游在湖面上,看着湖中掠水虫集合在水面,成群的小鲈鱼围在自己小舟四周,在湖水中畅游,他也置身其中不能自拔。而当有人在他离开湖岸开始砍伐木材时,他禁不住心伤起来,伤感的原因是自己无法再像以往徜徉在林中,无法透过树林目睹湖面的美景,连树林也被赋予灵性,感知到这种伤害,林中的动物也无法再鸣叫。梭罗丝毫不觉得受到了打扰,潜水鸟会与他玩耍,有时候还会像淘气的孩子一样嘲笑他,这些可爱的潜水鸟和他一样都是瓦尔登湖大家庭的一员。还有湖里的野鸭,如果不是热爱瓦尔登湖,他们也不会冒着危险游到湖的中心。他的描写轻松而富有诗意,秋高气爽之时,他会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欣赏野鸭如何畅游在湖中心,“如果飞离湖面,则会高高的盘旋在空中,像是在审视着整个林子,关注着别的湖面和小河,时而突然俯冲直下,飞往一个不远处不受惊扰的沼泽”[9]219,但没有多久便又会飞回瓦尔登湖中心来,好像这里才是它们的家,原因可能是和自己一样深爱着这片湖水。梭罗自己也会完全沉浸在自然之中,他常常不愿意把眼前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任何工作,他喜欢给自己留出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独自坐在洒满阳光的小院门口,“出神冥想,置身于松树、山核桃树和漆树丛中,四下里一片孤寂和宁静,唯有鸟儿在近处歌唱,或者悄没声儿地掠过我的小屋,直到夕阳余晖照在我的西窗上”[8]82。在瓦尔登湖,鱼儿就像高贵的隐士,悠闲的潜于湖底;湖面就像大地的眼睛,高山和石崖是大地的眉毛,湖畔的树木是瓦尔登湖的睫毛,梭罗只是众多生物中的一员,梭罗与它们对话、互视、交往,他与它们是同一个苍穹下的一群朋友,自然界中的万物对于梭罗来说不再是陌生的,相反,他抱着一种平等分享的态度与身边的生物相处,视它们为自己的家人,甚至会认为这就是给予他的馈赠。梭罗的心灵是敏感的,梭罗的感官是敏锐的,梭罗的感觉是细腻的,梭罗完全沉醉到瓦尔登诗情画意的景色,他欣喜,他快乐,他与瓦尔登湖、与大地、与天空、与水中的鱼林中的虫和空中的鸟、与大自然的众多的孩子们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他与它们成为了一个完整的整体。
二
挪威著名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提出的深层生态学强调把“人-自然”作为统一整体,重视多样性,包括风格、行为、物种、文化的多样性,且认为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只能以朴素的生活作风为途径。自我实现的取向在梭罗作品中体现的极为充分,梭罗把大自然视为人类的精神家园,认为它能够净化人类灵魂。《瓦尔登湖》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很早以前我丢失了一只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求助咨询过的很多游客也很关心它们的踪迹,我见过两个人,他们说曾听到过猎犬的行踪,见到过斑鸠消失在尘土中,他们似乎很担心这些线索,仿佛是丢失了自己。”[9]14这段描述中的猎犬,一匹栗色马或一只斑鸠,代表的是人们在这个世界中丢失的自我,梭罗追寻的便是自我的完美实现。他把自己看作自然界中的一部分,投身于大自然以期找回一个理想的自我,这个自我需要不断受到大自然的启发来实现,通过与大自然的交流和融合将个体自我与整体自我达成统一。梭罗的自我实现意识充分体现在他对湖畔生活的细节描写中。他在一块田地种下豆子后,整个夏天都在松土除草,还照料湖边的野花野草,对田地里的野草也丝毫不介意,他对豆子和野花的态度表明了对自然的强烈认同感,豆子因自身有价值而值以耕种,而毫无价值的野草也同样有存在的权利,这种权利便是自我实现。某种生物并不能因为对人类没有用途就应该剥夺其存在的权利,作为不同的生物形式,野草和豆子都增加了生物系统的多样性,因此他们的内在价值是一样的。在劳作时,他始终很享受整个过程,无论是松土除草,迎接阳光雨露,还是应对松鼠或土拨鼠的破坏,都不会影响他享受置身大自然的奇妙旅程。
梭罗非常享受在自然界田间的劳作,清早他会赤脚劳动,就像一名艺术家踩在沾有露水的沙子里一般,到了正午,任由阳光灼烧自己的双脚。太阳照在锄头上,阳光缓慢的来回游走在黄沙天地间,在长长的绿树丛中,远处尽头是一片矮矮的橡树林,劳作间隙坐下来歇歇脚,回头看另一端蔓延到了黑莓田边,看上去隐约觉得黑莓的色彩会更浓。“平常我除去田间杂草,在新苗周边围起新土,以便让我种下的禾苗茁壮成长。日复一日,我的工作大抵如此”[9]145。这种栩栩如生的描述不再是简单的把自然万物看作是生活的附属,而是一种与自然完全融合的投入,进而达成自我实现。
梭罗自我实现的核心概念是如何度过充实人生的问题,与自然的密切联系是通向充实人生的一种方式。自然状态的生活,抛弃毫无必要的物质需求便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征得爱默生的同意,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属于后者的土地上建造了一座小木屋,从1845年7月4日起,他在这里生活了26个月,在两年多的时光中,梭罗的大部分时间都融入到自然之中,在湖边漫步,在林边阅读,与松涛对话,与松鼠为伍,与鸟儿嬉戏,与鱼儿私语,为保持基本的生活参加极少的劳动,他想证明的是少量物质消耗,简单的生活方式,缓慢的生活节奏并不是必然带来精神世界的单调乏味,相反,简单质朴的生活反而可以使人“活得幸福快乐,活动更从容、更轻松、更充实、更本真”[5]159。梭罗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描述得淋漓尽致,繁琐的世俗生活几乎耗尽了人们对生活的激情,大自然成了恢复人的感觉,强化人的直觉,美化人的心灵,丰富人的精神,抗击那些疏离社会的异己力量的灵丹妙药,大自然提供了可以让他超越现实存在,重返自然并与之和谐共存的机会,人类由此得以与日益商业化的生活对抗,最终实现自我。在梭罗的笔下,瓦尔登湖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显示出不同的性灵,但不论阳光还是雨露,也无论严寒还是酷暑,那无法用言语描述的大自然的纯净与恩惠总是能带给人们娴雅的生活、美妙的乐趣和怡然自得的精神享受。湖底的水草、湖中的鱼儿、湖畔的小虫都能引发梭罗无限的遐想,同时在阐释对生命、生活的思考时,其语言又是理性、严肃的。
不过,在对自然细腻的感悟、对自我的不断追求中也隐含着梭罗的对环境遭到破坏的隐忧。在《闻籁》一篇中,梭罗一方面静听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美妙的天籁之音,一方面又写到一列火车拖着长长的尾巴,像一颗慧星一样向远方驶去,把从瓦尔登湖畔山泽中获取各种物资运到珊瑚岛、印度洋、热带地区及到整个环球世界,把缅因州的木材源源不断的运到全国各地,人们从大地上过分索取物资,人们对物质享乐的过分依赖,因此造成了自然生态的被破坏,梭罗对此表达了他的不满与隐忧,他表示:“断断乎不会让火车的黑烟、蒸汽和咝咝声污染了我的眼睛与耳朵。”[8]89如果说火车的鸣叫是一种隐忧的话,对工业化造成的生态系统的破坏,对自然的直接干预造成的生物种群的灭绝,梭罗更以激烈的言辞给批评,河鲱是美国本土的一种重要的鱼种,春天逆河而上到河川产卵繁殖,秋天长成的幼鱼又与成鱼一同出川入海,但水坝的建设阻断了鲱鱼上溯产卵的通道,成鱼因此大量死亡,幼鱼数量锐减,梭罗以同情而愤懑的语言批评到:“你既无刀剑作武器又不能击发电流,你只是天真无邪的河鲱,胸怀正义的事业,你那柔软的、哑口无言的嘴只知朝向前方,你的鳞片很容易被剥离。拿我来说,我站在你一边。”然而不可阻止的是鱼为了人类的利益被大批杀死,梭罗喊道:“人类肤浅而自私的博爱主义见鬼去吧!”你们“有谁听见了鱼类的叫喊?”[10]这是鱼类的呐喊,也是如梭罗一样的早期环保主义者和生态平衡倡导者的呐喊,是梭罗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以与动植物平等相等的自然界中一员,以地球中心主义或曰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发出的呐喊,其中蕴含的是梭罗的生态哲学观念:过度的人类索取必将带来可以想像的生态危机与生态灾难——梭罗的超前意识在当代社会可怕地应验了——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人务必放弃自我中心主义,放弃理性精神主导下的狂妄的主体意识,放弃对大自然的控制姿态,在与大自然的亲近亲和中实现自我,因为从最高的意义上看,整个自然界的生态是一个完整的链条,链条的每一环都处在相互关联中,人类同样身处其中。
三
梭罗的名声在进入20世纪后不断攀升,60年代以后“美国人对梭罗的评价越来越高,对他的迷恋日趋增强。成立于1941年的‘梭罗协会’是研究单个美国作家的最大的也是历史最长的组织”[5]160。其著作《瓦尔登湖》也被认为是人们在物质生活中寻求精神食粮的经典文学作品。工业化进程中人类一直把大自然看作是索取的对象,不断地向自然界获取利益造成土地荒芜,土壤沙化,水土流失,草原退化,森林消失,植被破坏,河流干涸,大气污染,物种急剧减少,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自然灾害频发,厄尔尼诺现象成规律性的再现。人类听到的是建筑工地的吵杂声,汽车的呼啸声,铁轨的呻吟声和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声,而不再是水牛、夜莺、野鸡、野鸭、猫头鹰们发出的天籁之音[8]81—89。人类在享用征服大自然的成果的同时,也在承受着大自然的报复性回应所带来的恶果。在《瓦尔登湖》一书行将结束的章节中,梭罗以“春天”命名,生动描述了春天里的瓦尔登湖冰面融化,树林里万物复苏的开端,阳光带来了和煦的微风,一阵阵吹来,带走了雨雾,溶解了岸边的积雪,等到天空一片晴朗,太阳向着风景如画的大地微笑,等风停时,地面上如熏香般的薄雾飘摇起来。结束语中,梭罗说他入住进树林,又离开了树林,那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以何种生活方式生活的试验,对梭罗来说,重要的不是他对这种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坚持了多处,而是从极简主义生活中悟出的道理:“一个人只要充满自信地朝着他梦想指引的主向前进,努力去过他心中想象的那种生活,那他就会获得在平时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会把某些事情置诸脑后,越过一道看不见的界限;在他周围与内心深处会确立一些新的、人人懂得的更加自由的法则来。”[9]235这就是梭罗所追求的完美境界,这应该是他对自己回归自然,超凡脱俗的生活哲学所下的最好注脚。工业时代里,人们在大肆攫取自然资源的同时,渴望有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安抚焦躁不安的社会情绪,基于这种哲学态度创作而成的文学作品迎合了人们的需求,正因为如此,生态创作所焕发的生命力才会愈演愈强。
生态文学创作并非一开始就被人们所接受,但在美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激发了作家们开始文学创作的活力。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认为梭罗关注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与大自然的关系,来探索人类精神世界,并“把自然生态创作推向了全新的阶段—生态文学”[11]。后来的美国生态作家,诸如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和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等接力生态文学创作,直接推动了生态批评兴起。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被推崇为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文学新纪元的开始,在美国和整个世界掀起了一个永不消退的环境意识浪潮。之后,穆尔、艾比、缪尔、斯奈德、斯塔福德、菲利普·布思、薇拉·凯瑟等新兴的环境生态文学作家坚持进行自然书写、荒野书写以及环境文学创作,同时生态批评家威廉·鲁克特、切瑞尔·格罗菲尔蒂、弗雷·德里克瓦格、威廉·霍沃思、哈罗德·弗罗姆、格林·洛夫、帕特里·克默菲等致力于生态文学批评[12],这种文学研究结合工业文明的新进展、科学主义的盛行、哲学思潮的变化进行综合性的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讨论生态文学的概念、定义、性质、类属,梳理生态文学的兴起与发展脉络,研究生态伦理及其意义,分析生态破坏对当代社会造成的震聋发溃的警示意义,生态文学批评与生态文学创作相互影响,形成良性互动之势,推动绿色文学的繁荣,推动我们的生活家园再现葱绿。“绿色文学是世界的绿色需求、作家的绿色创作、读者的绿色阅读、批评家的绿色批评、理论家的绿色思考、社会的绿色实践共生的。绿色文学运动的环路,呈现出如下图式:世界的绿色呼唤——作家的绿色创作——文学的绿色文本——读者的绿色阅读——批评家的绿色批评——理论家的色思考——社会的绿色实践——世界的绿化。在生态批评等等的作用下逐渐恢复绿化的世界,生发了更高的既真且善的绿化要求,形成了更新的绿色呼唤,形成了下一轮绿色文学的绿化运动。如此回环往复,世界不断地走向绿色的复魅人类也就有了绿色的家园,宜生的环境”[7]。梭罗的文学创作是生态文学创作的范本和代表,梭罗的世界是一个生满生命和谐交响乐的绿色的生态世界,对梭罗的生态批评是因全身心投入而达到忘掉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态审美批评。《瓦尔登湖》已经不再是“瓦尔登湖”自身,《瓦尔登湖》的文学价值已经超出了作者对湖畔生活的简单描述,作品更能反映出在当时社会发展状况下作者的哲学思考,梭罗投身瓦尔登湖畔,置身大自然,通过亲身实践向世界展现了“一个人类之外的自然存在,那是最主要的存在,是超越了任何人类成员的存在”[13]。这种生态情怀有着超前意识,也有更强的当代意识和现实意义。
[1]Pritchard,John Paul.Criticism in America[M].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56:43.
[2]张素艳.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对美国文化的影响[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3] 程爱民.论瓦尔登湖的生态学意义——纪念《瓦尔登湖》发表152周年[J].外语研究,2007(4).
[4]Cheryll Glotfelty,Harold Fromm.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 in Literary Ecology[M].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70.
[5]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王诺.生态批评的美学原则[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2).
[7]袁鼎生.生态批评的西方经验[J].鄱阳湖学刊,2011(1).
[8]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9]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10]罗伯特·塞尔.梭罗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31.
[11]Buell,L.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116.
[12]李晓明.美国当代生态批评述评[J].思想战线,2005(4).
[13]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J].文艺研究,2005(3).
[责任编辑 海 林]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5.027
2015-10-18
I106.6
A
1000-2359(2016)05-0155-06
刘霞(1979-),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