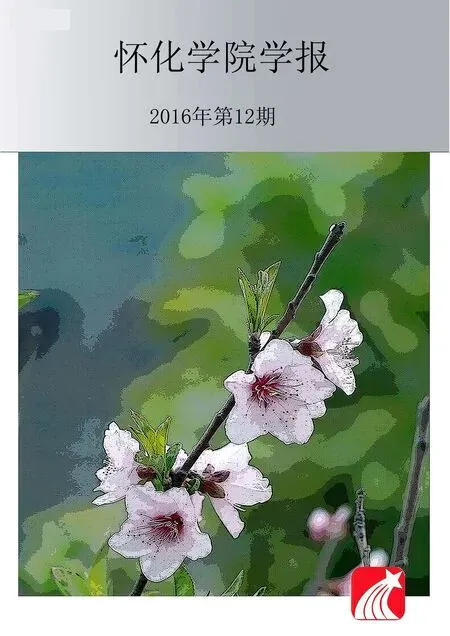侗族民间节会功能研究
吴波
(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怀化418008)
侗族民间节会功能研究
吴波
(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怀化418008)
侗族传统节日是侗族人民世代传承下来的一笔非物质文化遗产,蕴涵着维系和凝聚、规范与约束、推动与促进、传承与发展、调节与融洽五大功能。
民间节会;侗族;功能
民间节会作为某一民族或多个民族之间由民间自发形成、共同恪守以及虔诚赓续的一种仪式或活动,是一个民族传统精神信仰、特殊生产生活方式和多样化文娱活动的集中反映。民间节会作为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鲜明的历史传承性;也因其自身明显的程式化倾向,拥有不可替代的强大功能。功能指的是事物或方法发挥的有利作用。民间节会之所以在侗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与其强大的功能是密不可分的。概而言之,侗族民间节会主要具有五大功能,即维系和凝聚、规范与约束、推动与促进、传承与发展、调节与融洽,这些功能分别作用于侗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
一、政治功能:维系和凝聚、规范与约束
(一)维系和凝聚
一个民族能够繁衍生存,最重要的前提是内部的团结凝聚。而要促进民族的团结凝聚,关键是要增强族民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感,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感是民族团结凝聚最强大的内驱力。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以各种仪式、典礼、活动为载体的民族民间节会恰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就侗族民间节会而言,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的活动来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的。
1.通过对共同祖先“萨岁”的崇拜来增强血缘意识。在众多侗族民间节会中,“祭萨节”是最重要的节会。“萨岁”是侗语的音译。侗语“萨”的意思指的是祖母,也用于尊称老年女性;“岁”有首位、最大等意义。“萨岁”意译过来就是圣祖母的意思。在侗族社会中,对于“萨岁”尽管有各种称呼,神礻氏属性也有不同的说法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她是侗族共同尊奉、至高无上的始祖神。
作为原始母权时代的产物,“萨岁”具有多重身份。她既是公道正派、舍己为民的女酋长,又是充满母爱、母情的原始母亲神;既是劳动神、歌神,又是创世神;既生殖繁衍了侗民,又运用智慧和力量护佑侗民,抗击来自于自然与官府的双重威胁与压迫,使侗民族能够化险为夷,艰难前行。她的身上,集中了侗族祖先勤劳、勇敢、智慧、自强不息、助人为乐、坚忍不拔等优秀品质,寄托着侗族人民美好的愿望,既是侗民心中的灵魂,又是侗族得以延续的精神力量来源。因为其崇高的地位与无可比拟的功德,“萨岁”成为侗民心目中至高无上、尊崇无比的神灵。无论是南侗还是北侗地区,祭萨都是民间节会中最重要的活动。每年的正月初一、十五乃至各种节日,侗民都会自发地前往萨坛开展祭拜活动。其中既有正式庄重肃穆的祭奠仪式,也有简单朴素的祭拜活动。不仅在丰收喜庆时,感恩于“萨岁”的护佑,同时,遇到劫难灾情更要祈求“萨岁”的保佑化险为夷。在“祭萨节”,大家在萨坛前敬茶、唱萨歌、唱萨耶,缅怀萨岁的功绩,十分虔诚恭敬。有的地方正月初六还要用鱼、田螺及白瓜、茹瓜、青菜、豆四种蔬菜加酸水同煮,用一条全鱼煮粥,吃晚饭前,到萨坛前祭萨。为了表示对“萨岁”的崇敬,在设立祭祀坛的时候,还要特别组织背萨队伍前往几百里外的贵州黎平龙额乡的弄堂概背回一些泥土象征引萨到寨,然后用这些泥土及其他一些器物作为埋葬物修成墓葬性质的“然萨”(即祖母屋)和“堂萨”。在侗族的“祭萨节”中,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乐江乡宝赠村的“祭萨节”很有代表性。每年农历二月的第一个卯日,身着民族服饰的侗民,争先恐后地来到萨坛前,为“萨”烧纸上香,各家主妇在萨坛前点燃火把,将萨玛播下的火种带到回家。“款师”在众人的应和中宣讲祖先艰苦创业事迹款词,众人抬着萨玛的塑像巡游。然后,催促人勤春早的春牛舞和除虫消灾、祈祝丰收的草龙舞相继登场,所有的歌舞都与萨玛息息相关。文化活动结束后,众人聚集在一起吃合拢饭,分享节日的快乐。宝赠村的“祭萨节”目前已经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著名的文化品牌和文化符号。“祭萨节”作为侗族民间节会,具有浓郁宗教色彩。族民通过讲唱萨岁的功绩,以及其他形式的祭萨活动,往复地强化着族民对萨岁的感情,使萨岁这一形象得以深入人心,传之久远,产生超越时空的力量。而这种对始祖神的信仰,也自然在族民心中产生了一种基于共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和力,同时也使族民滋生共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强化民族内部的凝聚力。
2.通过祭祖来强化侗民的凝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尊崇祖先、讲究孝道的民族,不管是汉民族,抑或是少数民族,都非常强调对祖宗的祭祀。《史记·礼书》中称:“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祭天地,是报答天地覆载之德;祭祖先,是感谢生命的赐予。通过祭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强化各个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侗族民间节会中的祭祖仪式亦不逾斯矩,如贵州省黎平县茅贡、地扪、登岑、腊洞、罗大等侗族村寨,每年农历正月十一至十五,都要举行名曰“千三”的祭祖活动。祭祖节这天,凡是从地扪村迁出的村寨,都自发地回到地扪村参加“千三”祭祖活动,称“千三”节。相传,上述村寨的祖先最先都落户于地扪,发展到1 300户后才开始分寨居住,其中700户分到茅贡,200户分到腊洞,100户分到罗大,300户留在地扪。节日这天,到萨坛前祭萨,到塘公祠前合歌祭祖,给萨神和祖先献上三牲祭品等。然后踩歌堂、赛芦笙等,场面十分壮观。这些活动的开展,对于凝聚人心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3.通过歌颂民族英雄、弘扬民族英雄的精神以增强民族自豪感,达到凝聚人心的目的。任何民族都有令人敬仰的英雄,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和骄傲。在侗民族的迁徙流变与发展中,同样出现过许多民族英雄:他们或在为改善民族的生存环境与自然斗争中有惊人之举,或者在抗击官府政治强权,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中创造了伟大的业绩,或者为民族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与其他民族一样,侗族也是崇拜英雄的民族。如“侗款”中就专门有“英雄款”一门,其内容就是讲述侗族英雄的事迹,歌颂他们的丰功伟绩。
在侗族民间节会中,以纪念侗族英雄为主要内容的占据了重要的比例。比较典型的如流行于六洞地区的纪堂(农历正月初三)、九洞地区的黄岗(农历正月初七或初八)的民间节会“抬官人”,就是为了纪念斩妖除怪、保卫侗寨平安的“镇南大将军”吴志和。相传吴志和出身九洞黄岗。臂力过人,武艺超群,神通广大,他不仅徒手杀死了为祸四方、祸乱侗民的白蛇精,还单枪匹马与洛寨数名身怀绝技的武士激战,调解了六洞的郎寨与洛香侗寨的山林纠纷。由于吴志和为官正直,锄强扶弱,朝廷封他为“镇南大将军”。“抬官人”就是为了感恩于他而设。
再如,四月八“乌饭节”是纪念古代英雄杨八哥。“侗戏节”是为了纪念侗戏鼻祖吴文彩。据史料记载,侗戏是一种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古老戏剧形式,为黎平戏师吴文彩于1830年左右首创的,迄今已有160余年历史。侗戏在侗族地区广为流传,湘、黔、桂、鄂四省(区)18个侗族县每两年轮流举办一次大规模的四省区侗戏汇演,先后已举办过五届,以纪念侗戏师祖吴文彩,弘扬、发展侗戏。“讲款节”是为了纪念是侗族款组织的款规的创始人六郎,“侗年节”是为了纪念一位杨姓将军等。诸如此类的以纪念民族英雄为主体的民间节会还有不少。
在每个节会中,仪式及习俗的核心内容都围绕英雄们的事迹展开。如“抬官人”,农历正月初三、初七,纪堂及黄岗等侗乡抬着由小孩装扮的“官人”吴志和走街串寨,接受百姓的参拜;农历“三月三,芷江大垅乡龙姓侗民为纪念英雄龙冠保,在三月初一天亮前做好三天的饭菜,初一、二、三禁止生火,不准会客;初三还要进行隆重祭祀。四月初八,侗民为了纪念英雄杨八哥专门烧制“乌饭”等等。通过节会这一群体性、参与性较强的形式,族民追忆和缅怀英雄们的丰功伟绩,激励与鞭策后人,潜移默化地增强民族自豪感以及凝聚不断前进的内驱力。
(二)规范与约束
侗族民间节会是侗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相同地域特征和相同心理结构的稳定社群行为,其具体表现内容和操作方式呈现出鲜明的趋同性和传承性。民间节会趋同的共时发展和历时累积,共同形成了侗族民间节会对族民日常生活行为、道德品质的强大规范与潜在约束。具体到侗族民间节会的规范与约束功能,主要表现在以民间节会为平台“讲款”,以此来宣誓盟约法规,规范和约束公众行为。侗款是“侗族社会集历史、政治、经济、哲理、法制、教育等知识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的传统文化集合体,它是侗族传统文化的精粹和核心”[1]。作为侗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侗款”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其最初的意义是“联成片的、联盟的、聚集的组织”[2]。实际上是一种民间自发的社会组织形态。后来,又在组织联盟的基础上衍化出“款约”、“款词”。“款约”是“村寨内部、村寨之间所订立的规章约法,是维护各款区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共同规约”[3]。“款词”是款首“讲款”时的念词。它“源于原始社会的宗教祭词,款组织出现以后人们常用原始宗教祭词的形式来发布款规款约或叙述历史”,到后来,“款词即变成一种风趣幽默、寓意深刻、投韵相间、典雅清新的表达方式,成为具有一定的严肃性、艺术性的口头文学作品”[4]。在作为社会组织的“款”以及“款约”、“款词”这三个义项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款约”。它实际上是侗族地区的习惯法,是规范和约束族民生产与生活的重要法典,其影响力和作用甚至远远高于当时朝廷的正规法典。在普及“款约”的过程中,家庭的教育传承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是,民间节会起到的重要作用更是不可低估。侗族不仅有专门的讲款节,如湖南通道侗族地区在春秋两季的“三月约青”、“九月约黄”,即在农历三月春耕及九月即将收获时由讲款人聚集众人重申款约条规。告诫大家春天要爱护秧苗,在秋收时要保护劳动成果,否则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等等。而且许多民间节会中,都有讲款的环节。“讲款节”是一个固定讲款的节会。一般以村寨或鼓楼为单位,由经过民主选举出来的德高望重、公道正派的款首、寨老或款师主持,地点一般选在款坪或鼓楼。讲款节有着严密的程序,气氛庄重、威严。首先由款首、寨老或款师背诵款约,众人认真倾听,每讲完一款,众人则高吼“是啊”以应和,表示对这些条款的认同。然后,根据这些款约,对村寨违背款约的人员进行处罚。这叫做“聚款”。其处理的方式,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以“六面阴、六面阳、六面威”为主要内容的所谓“阴阳款”。“六面阴规”主要是针对盗窃耕牛、银钱,绑架杀人、挖坟盗墓等重大违规行为而设立的条款,其处分的方式也是比较严苛的。“六面阳规”主要是针对破坏家庭、弄虚作假、偷放田水、小偷小摸、移动界石、勾鸡引鸽等六种比较轻微的行为而设立的条款,处理的方式主要有罚款、坐吃、喊寨、驱逐出寨等。“六面威规”主要是道德教化方面的条款,旨在劝化寨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要遵规守纪,相互爱护,和睦相处。侗家人十分重视“讲款”这一民间节会,每逢其时,寨民都会自发地聚集在款坪或鼓楼,积极参与各个环节的活动。通过“讲款节”年复一年重复不断的仪式,侗款这一侗族地区的古老“法律”体系已经逐渐为侗民所接受,并内化为一种自觉的意识。侗族地区之所以能够由“古时人间无规矩,父不知怎样教育子女,兄不知道引导弟妹,晚辈不知敬长者,村寨之间少礼仪,兄弟不和睦,社会无秩序,内部不和肇事多,外患侵来祸难息”[5]40的野蛮蒙昧状态发展进化至“男人吹六管,女人善汉音楚歌”(明旷露《赤雅》)的文明程度,与侗款的确立及深入人心、广大侗民自觉遵履显然是分不开的。有学者指出:“节日及其习俗是几千年文化累积的结果,民众习惯用它们来表现自己心中的价值,走过有意义的人生历程。这种价值与文化形式的契合是很难被改变的。”[6]正是这种价值观念与文化形式的契合,侗族民间节会作为特定文化时空中的周期性文化行为,自一开始便烙上了浓郁的集体意识,呈现出鲜明的群体认同、群体享用和群体传承的特质,对于广大族民也拥有与生俱来的规范和约束功能。
三、经济功能:推动与促进
民间节会是展现地域经济发展的良好平台与重要载体。侗族民间节会的举办,对于拉动内需、改善经济结构和发展区域性旅游产业等具有不同寻常的作用。具体而言,侗族民间节会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推动农业生产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等层面。
(一)再现农耕文明,推动农业生产。侗族生活的地域主要是位于湘、黔、桂等边远交界地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目前,尽管科技已经发展到了互联网时代,但是,大部分侗族地区采取的还是比较原始的农耕劳作方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勤劳善良的侗族人民养成了敬畏自然的文化心理。他们遵守大自然的规律,与生灵和谐相处,祈祷风调雨顺。这些朴素的思想意识成为一些民间节会的来源和主要内容。如在立春日,侗族地区就有“闹春牛”的民间节会。是日,侗民要修理牛舍、牛栏,用糯米粑、酒等慰劳耕牛。晚上“送春牛”、“舞春牛”。由两个青年扮演“春牛”,牛头用竹篾纸作成,牛身用布,饰以棉花或皮毛。“春牛”前是两个圆形红灯笼,上书“立春”大字。“春牛”后是青年们所扮演的模仿耕耘、播种、锄草、施肥、收获的农夫农妇。他们载歌载舞,挨家挨户祝福,各家燃炮、献红糖、红包、糍粑,欢迎“春牛”。各户走毕,即以打谷场为农田,作“春牛”舞。周围人还与“春牛”对歌、对话,问答农时、农事。这一民间节会,提醒大家春天已经到来,接下来,关乎族民生存的春耕即将开始,而春耕,最为重要的是耕牛,所以大家通过这一方式,来欢迎“春牛”,希望他不吝力气,奋力耕种,取得好的收成。这些民间节会,完整再现了农耕文明的真实现状,激发出侗民从事劳动生产的热情,也有效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展示民族特色,促进旅游产业发展。近年来,侗族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很快,前往侗族地区旅游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并且势头不减。侗族地区的旅游业之所以火爆,实际上并不在于其自然山水,而在于它那一种古老纯朴自然而又神秘的文化资源。而民间节会,本身既是一种文化,同时又是集合并展示文化的载体。可以不夸张地断言,正是因为数量众多、丰富多彩的民间节会的存在,才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往参观旅游。旅游业的繁荣,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使侗民摆脱了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长期以来,侗族人民受历史、地域特别是观念等因素的制约,长期沿袭的是一种自耕自足的生产生活模式。向土地讨食是唯一的生存方式。旅游业发展起来后,使侗民得到了实惠,寻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充分调动了侗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侗族是一个封闭、乐观自足的民族,广大侗民所追求的是一种恬淡自然的生活状态,小富即安的思想在大多数人的心中不同程度存在着。这一生活模式和思想观念对于经济的发展无疑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旅游的发展,游客的涌入,沉寂已久的侗族山寨活跃起来。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山村的宁静,很多寨民已不满足于小富即安的生活。幸福观的变化,激发了他们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动力。目前,在侗族地区产生的各种旅游模式如参与体验式以及一些全新的管理模式的产生,就是侗民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具体体现,这就是旅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效应。三是旅游业的发展的确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目前,除了极少数进入寨子需要收取门票外(如广西三江的程阳景区),绝大多数侗族旅游是不收取门票的。村寨收入主要来源于游客聚餐的费用。在民间节会筹备时,首先由村寨集体组织寨民交纳部分资金及物品,由村集体统一使用。前来参观旅游的客人进寨以后每人交纳一定的费用,获得入场券。最后,由村集体统一核算,确定收入,年终进行分配。同时,节会常常成为物资交流的集散场所,一些侗民将当地的土特产如稻米、“侗家三宝”及侗锦等手工制作品展示出来,供游客挑选购买。这样既彰显了地方特色,活跃了民间节会的气氛,又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四、文化功能:传承与发展
侗族民间节会既是侗族百姓群体性的文娱活动,也是侗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从文化方面言,主要是传承与发展功能。侗族来源于秦汉时期的“骆越”,是一个古老而相对封闭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勤劳、智慧的侗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文学艺术、饮食、建筑、音乐、舞蹈、服饰、宗教、习俗等各方面均各具特色。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民族融合程度的加剧及现代文明的强势渗透,侗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日益突出,而节会恰恰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一个难以替代的平台与阵地。
民间节会传承与发展侗族文化的方式与途径是多样的,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种形式:一是讲款。如前所述,“款”既有社会组织、盟约寨规之意,也有“款词”之意。所谓讲款,就是讲侗族人民的事情,侗款涵盖的内容极为丰富,凡是与侗族人民的生活有关系的事物都在侗款中有所体现。据有关学者统计,款词按照内容可分为“款坪款词”、“约法款词”、“出征款词”、“英雄款词”、“族源款词”、“创始款词”、“习俗款词”、“祝赞款词”、“请神款词”、“祭祀款词”等十类[6],其中有叙述天地形成和人类起源的,有叙述民族来源和历史迁徙的,有反映生产生活和社会习俗的,也有叙述历史人物英雄事迹,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族民普通生活,都包含其中。节会中的“讲款”,其实质就是讲述侗族的历史,传承侗族的文化。二是各种仪式。仪式指的是“按一定的文化传统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集中起来的安排或程序”[7]135。仪式是侗族民间节会的核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凝聚着侗民的情感和意志。仪式本身既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仪式年复一年的重复,就是传统文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展示和传承方式。三是各种形式的歌舞表演。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音乐舞蹈很有特色。几乎在所有的民间节会中,歌舞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欢乐热烈的歌舞表演中,传统的踩堂歌、吹芦笙、侗族大歌等节目都会得到完整展示,最后众人一起参与的“多耶”将节会气氛推向高潮。这些都是侗族歌舞文化的精华,通过节会这一平台,使侗族歌舞文化得到发扬光大。
五、社会功能:调节与融洽
民间节会作为一种群体性和公共性的社会文化活动,群众参与度高,辐射面广,影响深远。从社会生活方面考量,侗族民间节会还具有调节与融洽功能。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节会中表演的音乐、舞蹈使族民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调节着劳作的紧张与劳累。二是节会中的宗教仪式强化族民的信仰,使族民产生对平安幸福的虚拟式的期待,这是他们战胜自然、克服困难的力量源泉。三是节会中音乐舞蹈的原始元素均来源于生产劳作,是生产劳动的模仿与再现,可唤起和强化族民对劳动生活的热爱。
节会还密切了族民之间的交往,增进彼此之间的互信,融洽了彼此的关系。经常性的相聚交流接触,会产生一种自然的亲和力。贵州省黎平、从江、榕江等县侗族村寨正月初三之后,开始一年一度演侗戏、作戏客活动。戏班先在本寨演上一天,初四之后村寨与村寨之间相互邀请表演和做“戏客”活动,一直到元宵节,甚至正月底。侗族“为也戏”,是一种以演唱侗戏为主的社交活动。甲寨数十人组成一个戏班,一般都是正月初三出门,到邻近一些村寨巡回演出,每到一寨都上演三至五天。东道主热情款待来客,离开时村上姑娘们还给客寨后生们每人赠送一条花巾。次年或过些年,乙寨也要组织戏班进行回访做客。“为也”(侗语:weexyeek)是侗族一种集体交往的方式,外人称其为乡客。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有鸡尾客、芦笙客、戏客、龙灯客等形式。其中鸡尾客最具代表性、古老性和传统性。它多角度地折射出民族的心理素质和群众文化素质。在中国诸多民族中,侗民族素以团结、和谐、幸福指数高而著称,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应该说,这与丰富多彩而又频繁的节会活动不无关系。
总之,侗族民间节会作为侗族族民集体意识的现实表现或艺术呈现,已完全融化进侗族族民的日常习俗、社会交往和政治活动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强大功能。对侗族民间节会的研究,不但能深入了解侗族文化的源远流长与绚丽多彩,也能有效保护和弘扬侗族民间节会与生俱来的强大政治、经济、文化功能,维系中华民族的和谐团结与世界文化的立体多元。
注释:
①根据赵巧燕研究,对萨岁本名或原名比较一致的看法有三种:婢奔或贝芬、杏妮、白石娘娘;而对于神名的翻译和记录则是多种多样,如“萨”、“萨岁”、“萨玛”、“萨柄”、“萨翁”、“萨样”、“萨温”、“萨滕”、
“萨老”、“萨子”、“萨天巴”、“萨巴闷”、“萨玛神”、“大神母”等称呼。对“萨岁”神礻氏属性目前存在冼夫人、孟婆、始祖、女款首、女性神、侗族女娲、女英雄等七种说法。参见赵巧燕:侗族萨岁考辨与研究述评,《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15辑。
[1]张世珊.侗款文化[J].求索,1991(2).
[2]杨进铨.侗族款的名称[J].民族论坛,1990(2).
[3]粟丹.传统侗款的法文化探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8(12).
[4]陈迪,徐晓光.款词与讲款——兼论黔湘桂边区侗族社会口头“普法”形式[J].贵州社会科学,2010(3).
[5]杨锡光.侗款[M].长沙:岳麓书社,1988:40.
[6]高丙中.作为一个过渡礼仪的两个庆典——对元旦与春节关系的表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
[7]陈国强.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135.
A Study on the Function of the Folk Festivals of Dong Nationality
WU B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Huaihua University,Huaihua,Hunan 418008)
Traditional festivals are an important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passed down generation.For Dong people,there are five kinds of functions in their traditional festivals:maintenance and coagulation,standard and constraints,promotion and furtherance,heritage and development,adjustment and harmony.
folk festival;Dong nationality;function
K28
A
1671-9743(2016)12-0001-05
2016-11-08
国家社科基金“侗族民间节会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对策研究”(10BMZ034)。
吴 波,1965年生,男,湖南浏阳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及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