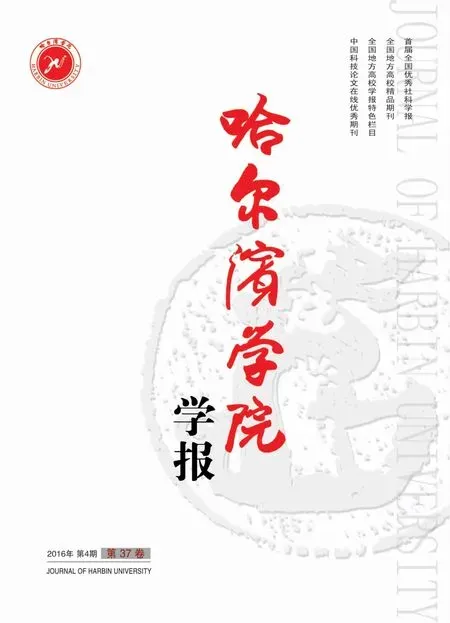国际私法中意思自治原则限制论探析
——兼评《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戴正清
(上海经贸大学,上海 201620)
国际私法中意思自治原则限制论探析
——兼评《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戴正清
(上海经贸大学,上海201620)
[摘要]意思自治作为确定涉外法律关系准据法的一种方式,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理念。但凡自由必有限制,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也不例外。从国际私法的制度和实践来看,均体现了对该原则的限制。这似乎与该原则本身所倡导的自由相抵触,导致理论与实践存在冲突。如何调和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摆脱被限制的困境等问题殊值讨论。文章在对上述现状的剖析过程中,兼评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关键词]意思自治;《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意思自治原则限制论
一、意思自治原则概述
意思自治原则是通过当事人的合意来确定法律关系的准据法,关于涉外法律关系的准据法问题,主要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前者指法律关系的成立及效力的准据法按当事人的意思来决定;后者指法律关系成立及效力的准据法的适用与当事人的意思无关,是依客观连接点来实现。主观主义在国际法上被称为意思自治原则。①;[1]在现代国际私法实践中,意思自治原则已经成为确定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通过意思自治原则赋予当事人自主确定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的法律体系的权能。
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私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上是指国际性的民商事法律关系(即含有涉外因素)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法律所准许的范围内,通过协议选择某一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的法律体系。[2](P261)
意思自治源自于实体法中的契约自由,从国家不干预经济或较少干预经济的角度出发,才得以成立的冲突法规则。意思自治原则是否应该受到限制,不能妄下断言,但从各国实践来看,几乎所有国家都对意思自治原则有所限制,但对其限制的程度有放宽的趋势。澳大利亚的《1992年法律选择法案》中并没有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进行限制。[3](P37)笔者认为,此仅是在“警察法”部分不加限制,而对于公共秩序、直接适用的法等方面,对意思自治原则仍有所限制。采用意思自治原则是一国立法政策的问题,但是只要采用该原则,从理论角度来看,对其限制应是不成立的。以下着重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对该原则限制论进行探讨。
二、制度层面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
(一)识别制度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院在对涉外民商事案件的事实情况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识别时,都必须以某一国家的法律为依据。原则上,各国的实践都以法院地法为识别依据,但也有例外。这就使得当事人无法通过意思自治选择识别问题应适用的法律。
匈牙利1979年《关于国际私法的第13/1979号法令》第3条第1款即明确采用了依据法院地法进行识别的传统方法。但该法第3条第2款亦规定如果某一法律制度为匈牙利所未规定,或虽为匈牙利法所规定,但相对于匈牙利法来说有不同的名称(在内容上也不相同),且依匈牙利法的解释规则无法予以确定,则在进行法律上的分类时,以外国法规定了该法律制度为限,也必须考虑外国法。②《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187条第1款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在确定准据法时,法律概念的解释依据俄罗斯法为之。”但同条第2款规定:“如果在确定准据法时,所须识别的法律概念为俄罗斯法所未规定,或被以不同的字面上的名称或不同的内容加以规定,且这些法律概念不能再依俄罗斯法直接解释的情形下予以确定,则在识别它们时,可以适用外国法。”另外,《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3078条第1款和第2款亦规定依据法院地法进行识别,但有关外国法律制度为法院地法所不知时,可例外考虑外国法。[3](P219)我国《法律适用法》第8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可谓与识别的原则性趋势相符。
虽然在依法院地法进行识别的原则之外,不少学者主张其他的识别依据,如依据准据法识别、比较识别方法、功能性识别等。但除了准据法说之外,不管何种主张都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其实,准据法说会陷入循环矛盾之中因为识别的目的在于对法律关系进行定性,以便确定准据法,法院是在识别之后通过冲突规范指引准据法。而准据法说是先有准据法后依准据法进行识别,显然逻辑矛盾。主张该学说的学者主要是德国国际私法学家马丁·沃尔夫以及法国国际私法学者德斯帕涅。[1](P61)
(二)外国法查明制度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
当事人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外国法时,就涉及到外国法查明的问题。各国司法实践中查明外国法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由法官依职权查明、由当事人提供和法官依职权查明为主当事人提供为辅。但不管采取哪种方式,都不能保证一定能查明外国法。当外国法无法被查明时,就会涉及该纠纷如何解决的问题。
当外国法无法查明时,主要有三种方法处理:其一驳回起诉。如果外国法是事实,一旦外国法无法查明,即事实无法查明,当然驳回起诉。但如果外国法是法律,驳回起诉就意味着拒绝审判,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其二适用法院地法。1978年奥地利《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律》第4条第2款规定:“外国法虽经多方努力仍不能在适当时间内予以查明的,适用奥地利法。”2007年土耳其的《关于国际私法和国际民事程序法的第5718号法律》第2条第2款规定:“虽经一切努力,应适用于案件的外国法的相关规则仍不能予以查明的,适用土耳其法。”2011年波兰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律》第10条第2款规定:“应予以适用的外国法的内容在合理期间内不能予以确定的,适用波兰法。”我国《法律适用法》第10条第2款亦规定当外国法无法查明时适用法院地法。而在我国的实践中却出现没有按照上述规定处理的案例(江苏省轻工业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环球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美国博联国际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4])。在当事人有法律选择但事实上所选法律不存在的情况下,法院最终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解决有关争议,凸显了最密切联系作为意思自治的补充作用。其三适用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1995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外民事关系法》第12条规定:“依照本法的规定应予以适用的法律的内容无法确定的,适用与有关的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法律。”
总之,当被选择的外国的法律无法查明时,自然无其适用的可能。
(三)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
当协议选择的法律满足了公共秩序保留的条件,即无法被适用。公共秩序既然作为排除准据法适用的一种手段,那准据法被排除后,法官应如何处理纠纷,在国际上做法不一,最为常见的就是适用利用法院地法替代被选择的法律,但也有学者主张适用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
适用法院地法的国家有:1978年奥地利《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律》第6条第2款规定:“必要时,奥地利法的相应规定必须取代它们(外国法的规定)而予以适用。”1979年匈牙利《关于国际私法的第13/1979号法令》第7条第3款规定:“必须适用匈牙利法以代替被排除适用的外国法。”我国《法律适用法》第5条亦作了类似规定:“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日本的折茂丰教授认为,国际私法规范适用的外国法是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当外国法的适用违反了法院地国家的公共秩序时,应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次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③
准据法被公共秩序排除适用的结果与外国法无法查明的结果类似,都是无法通过原协议选择的法律来解决纠纷,面临的问题都是如何确定新的准据法,它们在这些方面应具有共性。
(四)强制法制度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
强制法的概念在冲突法上又称之为“直接适用的法”或“警察法”。从“直接适用的法”的字面理解也可得出,该法律的适用不存在当事人选择的可能,必须直接适用。因此,无意思自治存在的可能。
各国法律均对强制适用的规则有所规定。《罗马条例Ⅰ》第9条第1款规定:“强制性法律是被某一国家为了维护其公共利益而认为遵守它乃至关重要,以致要求将之适用于一切进入其适用范围的情势的强制性规定,而不论依本规则以其他方式适用于合同的法律体系为何。”1987年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律》第18条规定:“不论本法所指定的法为何,因其特殊目的而须予适用的瑞士法的强制性规定,应予以保留。”1995年意大利《关于改革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的第218号法律》第17条规定:“尽管被指定的是外国法,鉴于其对象和其目的而必须强制地予以适用意大利法律规则的优先地位,不受以下规定的影响。”我国的《法律适用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中国的外汇管制法、利息限制法、最低劳动工资法、劳动标准法、消费者保护的特别法、因工事故保险法以及承租人保护法都属于“法院地国家直接适用的规则”。[5]最为明显的是《合同法》第126条第2款对在我国境内履行的三类涉外合同适用中国法的规定。就此问题,有学者指出若该三类合同纠纷在国外仲裁时,如何确保中国法能够得到适用?如果未予以适用,作出的仲裁裁决在我国是否应当被承认与执行?[6]由于仲裁系属纠纷解决的民间层面,其意思自治的成分较国家层面的诉讼更多。因此,当涉及到该三类合同纠纷时,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外国法律进行仲裁。而我国又是1958年《纽约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并没有将违反内国强行法作为拒绝承让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依据,但违背被承认与执行国的公共政策时,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而强行法与公共秩序并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一般强行法主要是从公共秩序的角度出发,由国家对纠纷直接干预保护当事人间的实质平等。故依据外国法解决的该三类合同纠纷的仲裁裁决如果不违背公共政策,在我国应该被承认与执行。
在国际私法层面,外国强行法具有直接适用的特性,具有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功能。
三、实践层面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方式限制
在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思表示分为明示和默示两种。[7]明示即以文字或语言明确作出选择法律关系准据法的意思表示,最典型的是事前在文本中约定好准据法的条款。默示即并没有明确规定法律关系应适用的准据法的情况下,通过行为或者其他一些因素来推定当事人已默示同意该法律关系受某一特定国家法律的支配。明示选择的方式为采取意思自治原则的国家所接受的应有之意,然而是否承认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承认当事人以默示方式作出的法律选择,各国态度不一。[8](P38)
有的国家如秘鲁、土耳其等只承认明示选择法律的方式;有的国家如瑞士、法国、美国以及1955年《海牙买卖动产公约》则有限度地承认默示选择法律的方式。美国1971年的《冲突法重述》第187条仅承认一直默示选择法律的方式,即“合同条款中包含了某一州所特有的法律理论或法律上的规定,则可证明合同当事人希望适用该州的法律。”1955年《海牙动产买卖公约》也规定在适用默示选择法律时,应考虑当事人的意图。所考虑的因素仅限于合同中是否包含了某国法律条款或采用了某国格式合同的情况。[9](P224)可见,尽管部分国家承认了默示选择法律的方式,但均对其限度作了要求,尤其限制在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图十分明确的情形下。我国的《法律适用法》第3条也将意思自治原则限定为明示方式。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的司法解释》),第8条第2款规定:“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此可以视为明示选择的一个例外。
对于明示选择,势必涉及到书面和口头,各国法律一般均未作进一步规定。由于国际上对合同形式的要求进一步放宽,如CISG、PICC、PECL以及DCFR都允许口头方式订立合同。因此,在合同领域,口头选择合同的准据法应无障碍。如1980年《罗马公约》和2008年《罗马条例Ⅰ》都未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但是欧盟司法实践中对于采取口头形式的法律条款一般持支持态度。在Derek Oakley vs Ultra Vehicle Design案中当事人口头约定德国法作为合同的准据法,法院将这种口头约定的法律选择视为有效。[10](P40)与书面方式相比,口头方式确实存在举证困难、合同形式有效性等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当事人采取此种方式作出法律选择。
总之,各国对选择法律的方式主要倾向于明示,有些国家兼采有限度的默示。在承认默示方式时,虽然体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但有时可能误解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思,更多是法官个人的意思。正如莫里斯所指出的:“当事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明确表示,当事人可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只能由法院推定其具体意思,即由法院为当事人确定一个公平合理的准据法。”默示情形下准据法的确定主要由法官根据一些因素(主要包括合同条款、性质或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来自由裁量,自由裁量的情形下不免会出现不公正。我们姑且认为所有法官的专业知识都很丰富、职业操守也很高,但法官选择准据法依据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有很大的偶然性,这就不能完全真正代表当事人的意图。默示意思并不能完全达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目的,将违背意思自治原则的本意。[11];[1](P167)
另外,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选择的兜底条款,完全可以弥补意思自治原则缺失下法律适用的问题。而且据以确定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的意思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认定标准相类似。因此,默示标准应无存在的必要。但为了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明示之外,也并不是说不允许其他方式选择法律,但是只有在当事人选择相同法律的事实十分明显的情况下,才能推定当事人有默示选择该法律的意图。如《〈法律适用法〉的司法解释》第8条第2款规定。
总之,意思自治原则的方式应限制在明示和有限度的默示。
(二)意思自治原则的时间限制
当事人在法律关系发生时行使意思自治的权能,应无疑义。有疑义的在于:其一法律关系发生后能否选择法律关系应适用的法律,此又包括两个时间段,即法律关系发生后与此法律关系有关的争议发生前;与此法律关系有关的争议发生后诉讼辩论终结前。其二在法律关系发生后能否通过协议变更法律关系发生时原选择的法律。
对于这两个问题,各国通常考虑是否影响合同形式上的效力或第三人的利益。只有在都不影响的情况下才允许选择法律或变更法律。如1987年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16条第3款规定可以在任何时候作出或修改法律的选择。如果是在合同订立之后作出或修改的,其效力溯及合同成立之时,但不应影响第三人的权利。[9](P225)《土耳其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与国际民事诉讼程序法的第5718号法令》第24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可随时作出或变更法律的选择。在合同订立之后进行的选择,只要不影响第三人的权利,亦属有效。”另外,1994年《墨西哥公约》并没有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作出任何限制。2012年《海牙草案》也允许当事人在任何时候对法律作出选择。[10](P44)《〈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第8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协议选择或者变更选择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可见,我们国家将选择法律和变更法律的时间规定在诉讼辩论终结前,此种做法充分体现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重视,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也体现了《法律适用法》的科学性。
对于选择和变更的法律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上各国态度也不统一。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瑞士等国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了具有溯及力,而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以及国际条约,如《罗马公约》《罗马条例Ⅰ》《墨西哥公约》以及1985年《海牙公约》等均未规定法律选择或法律变更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罗马公约》的草案对此问题也未明确规定,但其报告人明确表示,只要符合当事人的意图,变更法律选择的效力可以具有溯及力。④笔者认为,此种推定亦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不能完全符合当事人的真正意图。因此,法律在规定时应具体明确为妥。
(三)意思自治原则的范围限制
1.空间范围的限制
尽管意思自治原则最为典型地体现在合同领域,但从目前各国立法来看,其已超出合同法领域,逐渐向婚姻家庭、继承、侵权及国际民事管辖权领域拓展。[8](P23);[3](P192)在婚姻家庭领域,1992年的罗马尼亚国际私法第21条允许夫妻双方协议选择支配其婚姻契约的内容与效力的法律。[3](P192)我国《法律适用法》第24条关于夫妻财产关系、第26条协议离婚均允许当事人明示选择应适用的法律体系。在继承领域,美国路易斯安那1991年国际私法第3531条,魁北克1994年国际私法第3098条第2款等均规定被继承人可以选择遗产继承的准据法。在侵权领域,上述国家新的国际私法均允许产品责任的受害者选择所适用的法律,但这种选择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德国1999年国际私法改革法第42条规定,非合同之债据以产生的事件发生后,允许当事人选择应适用的准据法,但不应影响第三人的权利。我国《法律适用法》第44条第2款也规定了关于侵权行为发生后允许当事人的法律选择。另外,《法律适用法》还在第37条关于动产物权适用的法律,第47条关于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适用的法律等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有学者也指出,将意思自治引入物权冲突是正当的,但要受到两项限制:仅适用于动产物权纠纷;不能对抗第三人,除非第三人同意。[12]另外,各国已普遍接受国际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权这一现象。[3](P192)这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管辖权方面的延伸,但其仅在一定范围内排除普通管辖,并受专属管辖的限制。我国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协议管辖仅限于合同及其他财产利益两类案件,且不得违反专属管辖,并符合实际联系原则。随着海牙国际私法会议2005年通过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进一步赋予协议管辖在国际民商事诉讼中的地位。[8](P24)
由以上可知,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虽不断扩张,但仍受到限制,只能说限制有进一步放宽的趋势。因为它在有些领域仍无法涉足,如民事主体。另外,就算扩展到某些领域,仍无法适用于该领域的专属性部分,如婚姻家庭领域的结婚条件、结婚手续等,继承领域的法定继承、遗嘱效力等,物权领域的不动产、权利质权等。意思自治原则在发展过程中,各国立法和私法对其有放松约束的趋势,但不代表其可以扩展到法律关系的任何领域。笔者认为,在其今后的发展中,仍无法突破这些专属领域。
在国际社会中,虽然在消费合同和劳务合同中排除当事人对法律的协议选择,但通过立法赋予消费者、劳动者单方选择对其有更好保护的法律的权利,这就是国际私法中的弱者保护原则,这也与当今的国际私法的立法缺失相吻合。[13]1980年的《罗马公约》第5条、第6条、第7条就倡导了此规则。[14](P101-103)我国《法律适用法》第42条、第43条也有类似规定。在合同领域,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合同的准据法,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冲突法所追求的正义价值目标和效率价值目标。但意思自治原则在特殊合同领域却受到限制,究其根源还在于对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之间的衡平。因为在特殊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处于不平等的谈判地位,强势方可能利用自己优势地位侵害弱势方的利益。鉴于消费者、雇员的弱势地位,在法律适用方面应予以照顾,方能实现实质上的公平。[15](P156)各国在特殊合同领域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方式存在差异,欧盟主要采用当事人不可规避的“强制规则”,而美国则采用“公共政策”来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最终目的都是保证有利于弱者的法律能够适用。
2.实际联系原则的限制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否应与合同有实际联系,这是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围绕法律选择的范围争论不休的话题。[8](P93)对于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是否需与合同有实际联系,我国《〈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第7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以双方协议选择的法律与系争的涉外民事关系没有实际联系为由主张选择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表面上看,我们国家不承认实际联系原则,即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不需要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有实际联系。但是否如此有待进一步讨论。
此条司法解释是针对《法律适用法》第3条作出的,而该第3条属于宣示性条款,仅具有指导意义。而分则中的12条才具有实践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意思自治原则所定的基调是不需要与实际联系相关,但在具体适用方面,所选择的法律还是不能摆脱《法律适用法》第3条“……法律规定……”的窠臼。而法律规定中就存在只允许在实际联系的范围内自由选择。因此,我国的意思自治原则仍受实际联系原则的限制。如在婚姻家庭领域,《法律适用法》将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的范围限定在一方当事人的属人法和主要财产所在地法,表明我国在扩大意思自治原则适用范围的同时,对婚姻家庭领域内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作了一定的限制。[8](P39)此条仍有进步意义,因为它将大陆法系的属人法与英美法系的财产所在地法相互融合,兼顾了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上的法律适用,符合现今两大法系相互融合的趋势。除此之外,还有婚姻家庭领域也需受实际联系的影响。
从其他国家的立法来看,美国也没有完全摆脱实际联系原则。《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187条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受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支配,除非所选择的法律与当事人或交易没有实际联系或者当事人的选择无合理基础。可见,美国对意思自治原则与实际联系的关系持保守态度。但“合理基础”为意思自治原则增添了几分活力。因为如果缺乏实际联系,可基于当事人选择的合理基础加以纠正,如选择的法律发展完善,当事人熟知该法律等,这种“合理基础”在美国的司法判例中得到支持。⑤虽然有此规定,但在美国法院最近几年的判例中,很少以没有实际联系为由否定当事人的法律选择条款的效力。⑥
1980年的《罗马公约》第3条第3款允许纯国内合同选择外国法,这就意味着当事人可自由选择与合同无任何联系国家的法律。1994年《墨西哥公约》第7条第1款也表明当事人可以选择任何国家的法律。2012年《海牙国际合同法律选择原则》也允许当事人选择与纠纷没有任何关系的法律。[16]另外,最近国内立法也表现出这样的趋势,在许多国家立法都没有做出实际联系的限制,如加拿大魁北克、罗马尼亚、德国、俄罗斯、瑞士等。另外,美国统一商法典(以下简称UCC)在2001修订后也废除了实际联系的要求。由此,意思自治原则的发展必将完全摆脱实际联系的限制,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实现涉外民事纠纷公正高效解决。另外,意思自治原则的应有之义是:不要求所选择的法律与合同(或交易)或当事人存在某种特定的联系。[2]
虽然意思自治原则受实际联系的限制越来越宽松,但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仍然可以因国际私法的一些制度而不予适用。
3.效力范围的限制
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的效力范围如何,是适用所涉法律关系的全部还是部分,一直倍受争议。笔者认为,虽然讨论的是协议选择的法律的效力范围,但前文已经论述了法律选择中的“意思”可以看作是冲突规范中的连接点,即通过意思自治选择的准据法与通过其他连接点指引的准据法应类似。因此,此部分关于协议选择的法律的效力范围可以用通过论述准据法的效力范围得出结论。
以合同为例,从范围上说,合同准据法主要适用合同的实质有效性以及因合同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⑦1986年《关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准据法的(海牙)公约》第12条规定合同准据法适用合同解释、当事人权利义务以及合同的履行、买受人开始有权享用货物的产品和孳息、收益的时间、买受人开始承担与货物有关的风险的时间、所有权保留条款当事人之间的有效性及效果、不履行合同的后果、债消灭的不同方式及消灭时效、合同无效或不生效力的后果。《罗马条例Ⅰ》第12条第1款规定合同的准据法适用于合同的解释;因合同发生的义务的履行;在受诉法院的诉讼法所赋予它的权限内,完全或部分地不履行这些义务的后果,包括损害赔偿的评估,但以它是依法律规则进行的为限;债消灭的方式,以及消灭时效和因期间届满而发生的失权;合同无效的后果。此外,同条第2款就履行方式和履行中发生的错误时有待债权人采取的措施而言,应考虑履行发生地国家的法律。我国《法律适用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应适用的准据法。此一规定对准据法的效力范围虽没有明确界定,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它剔除了《民法通则》第145条以及《合同法》第126条第1款中的“争议”,扩大了准据法的适用范围。[8](P42)但对于当事人的缔约能力,合同准据法应无适用的余地。
至于合同当事人双方的缔约能力、合同的形式有效性等事项,分别由单独的冲突规则确定它们的准据法,而后者往往是不同于合同准据法的法律。如缔约方式,一般以适用行为地法为原则,兼采其他连接方式。[8](P42)
至于当事人的缔约能力,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以当事人的属人法为原则,以行为地法为例外。⑧;[1](P113)匈牙利1979年《关于国际私法的第13号法令》第10条第1款规定:“人的权利能力……依其属人法决定。”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的法律冲突采用属人法已成为一项公认的原则,但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指国籍法或本国法,英美法系国家一般指住所地法。我国的《法律适用法》第11条、第12条对于当事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以属人法为原则,只有依据属人法为无行为能力时,才采用行为地法,但该例外不适用于婚姻家庭与继承,对于婚姻家庭以及继承中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应一体适用属人法,以凸显调整人身关系的属人法的稳定性。
其他法律关系中准据法的效力范围可以参照合同。
四、理论层面对意思自治限制论的驳斥
(一)对质的限制论的驳斥
质的限制论指意思自治原则只能局限于任意法的范畴。[17](P150)
但从理论上讲,质的限制论并不能成立。因为只要承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即成为连接点,以此来确定包括任意法和强行法在内的准据法。任意法和强行法的划分只是实体法上的问题。如果承认当事人只能在任意法的范围内选择纠纷的法律的话,那么,当事人选择的就不是准据法。因为当事人的指定不是冲突法的指定,而是实体法的指定。[1](P15)将不得违法的强行法作为纠纷的准据法,就否认了作为冲突规范存在的当事人自治原则。所以,既然承认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就不存在对该原则的限制。
(二)对量的限制论的驳斥
量的限制论是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范围限定在一定范围的国家的法律之内,即强调纠纷与所选择的法律有实际联系。[1](P166)
意思自治原则的目的在于纠纷发生时,为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更好、更快的解决纠纷。如果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与纠纷并没有实际联系,但均为当事人所熟知,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更何况,如果当事人对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法律不了解,硬要当事人在其中选择纠纷解决的准据法,未免不够理性。既然当事人选择了纠纷的准据法,可以说没有充足理由来进行限制,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也就是与纠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另外,我国学者也倾向于否定量的限制论。[18](P41)
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是基于国内法上的契约自由原则,从国家不干预经济或尽少干预经济的角度出发,得以成立的冲突法原则。由上述可知,意思自治原则限制论在理论上并没有说服力,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与否是一国立法政策的问题,但是只要采用该原则,从理论角度出发对该原则的限制不能成立。
五、结语
意思自治原则作为确定纠纷准据法的重要原则,在纠纷解决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原则不仅能快速、便捷、高效的解决纠纷,更重要的是尊重了当事人的意志,符合现今涉外交往的趋势。而对于涉外纠纷,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一国主权、一国国内公共利益。因此,从国家主权、国内公共利益角度出发,不可避免的要对意思自治原则进行限制,以遏制他国域外法治。而理论是没有国别限制的,是以世界法的角度阐释意思自治原则,这就不会考虑到一国国家主权、国内公共利益,也就没有必要基于此对意思自治原则进行限制。只要有法域的存在,在实践中就一定会对意思自治原则进行限制,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其限制的程度可能不断减弱,但不会消失。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法域,自然没有对意思自治限制的必要。但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法域,那法律也就统一了,也就不需要选择纠纷的准据法了。言外之意,意思自治原则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
总之,在实践层面,只要有意思自治原则,就一定有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
注释:
①笔者认为,主观主义下,“意思”应作为连接点,通过“意思”指引的法律应为准据法。因为,准据法指被冲突规范指定用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如果不经过冲突规范而确定的法律不能称之为准据法。
②See Burian,Hungaria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in:Yearbook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Vol.Ⅰ1999。转引自:陈卫佐,《比较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
③折茂丰,《国际私法研究》,有斐阁1992版。转引自:李旺,《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
④Richard Plender,Michael Wilderspin:The Europea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f Obligations (Third Edition),Thomson Reuters 2009。转引自:李凤琴,《国际合同法律适用发展趋势研究——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⑤Steven N.Baker:Foreign Law Between Domestic Commercial Parties:A Party Autonomy Approach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North Carolina Law,Campbell Law Review,2008(30)。转引自:李凤琴,《国际合同法律适用发展趋势研究——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⑥Symeon C.Symeonides:Choices of Law in the American Courts in 2009:Twenty-Third Annual Surve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2009(58):255-261.Choices of Law in the American Courts in 2008:Twenty-Second Annual Surve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2008(57):276-278.Choices of Law in the American Courts in 2007:Twenty-First Annual Surve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2007(56)。转引自:李凤琴,《国际合同法律适用发展趋势研究——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⑦See R.H.Graveson,Comparative Conflicts of Law。转引自:洪莉萍、宗绪志,《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探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⑧See Dicey and Morris:the Conflicts of Law,1980。Chesshine: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1938。转引自:洪莉萍、宗绪志,《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探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
[参考文献]
[1]李旺.国际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陈卫佐.比较国际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3]杜涛.国际私法的现代化进程·中外国际私法改革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武汉海事法院【1999】武海法宁商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Z].
[5]陈卫佐.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立法思考[J].清华法学,2010,(3).
[6]洪莉萍.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评析[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5).
[7]丁伟.限制”意思自治原则”的法律制度探析[J].政治与法律,1996,(1).
[8]洪莉萍,宗绪志.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探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9]刘仁山.国际私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10]李凤琴.国际合同法律适用发展趋势研究——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中心[M].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1]刘仁山.“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适用中的适用限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12]宋晓.意思自治与物权冲突法[J].环球法律评论,2012,(1).
[13]卢峻.国际私法统一化运动的发展和趋向[J].政治与法律,1996,(1).
[14]沈娟.合同准据法理论与解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5]刘想树,江保国.涉外消费合同的法律适用[A].武大国际法律评论:第2卷[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16]刘仁山.国际合同法律适用中“意思自治原则”的晚近发展——《海牙国际合同法律选择原则》述评[J].环球法律评论,2013,(6).
[17]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18]朱怀念.论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及其发展趋势[A].市场经济与中国国际私法立法[M].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李新红
Principle Constraint on the Party Autonomy in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Commenting on “Application of Law”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Party Autonomy
DAI Zheng-qing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Party autonomy,as means of a proper law defining the legal relation concerning foreign affairs,shows the party’s autonomy of will. The constraints can be seen in both system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This may sound contradictory with the principle itself. How to adjust the contradiction is worth discussion.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the “Application of Law for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hip” in China is commented in terms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party autonomy.
Key words:party autonomy;“Application of Law for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hip”;principle constraint on party autonomy
[收稿日期]2015-08-05
[作者简介]戴正清(1991-),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法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4—0028—07
[中图分类号]D997;D9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4.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