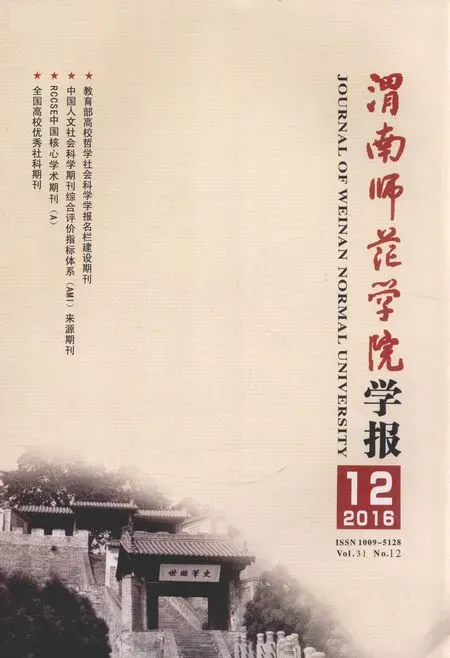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比较研究
——兼论我国农地产权改革
王留鑫,何爱平,何炼成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710127)
【财经与公共管理研究】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比较研究
——兼论我国农地产权改革
王留鑫,何爱平,何炼成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710127)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两个理论体系,在理论基础、研究范式、终极目标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除了价值立场上的本质性差异不可调和外,两者在具体的产权实践中也有着互相借鉴的地方。为此,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改革中,应做到产权的统一与分离相结合、产权的公平与效率相结合、产权的多样与稳定相结合。在进行产权比较和启示的基础上,对我国农地产权改革的路径进行了探讨,农地所有权统一于集体,细化承包权、经营权、流转权,建立成员权下农地承包权的可继承制。在农地征用、流转经营中,要保障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农地所产生的集体公共利益应用于集体公共服务。以法律形式规范农地产权的稳定性,以制度创新发展农地产权的多样性。
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比较研究
1 背景
当下中国正值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时期,但改革的深化始终绕不开一个话题,那就是产权,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土地改革研究中,已到了言必称产权的地步。但部分人自觉不自觉地就完全用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来开中国产权改革的“药方”,以致有些不但不能“对症下药”,甚至还“南辕北辙”,这是无视历史与国情,没有考虑不同制度安排所赖以运行的制度环境所致。我国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在公有制“土壤”上的产权不能按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完全私有化产权理论来指导中国的产权改革实践,而是应在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基础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作出创新,应在对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其可取之处。就此,本文先从两种产权理论不同维度的比较谈起,然后结合两种产权理论,探析对中国产权改革的启示。
2 文献综述
对于两种产权理论,或曰两种产权的分析范式的研究,有从研究产权的方法是个体主义的还是整体主义的,产权体现的是经济关系还是法权关系,产权关系是交易关系还是生产关系,财产权利是自然权利还是历史权利四个方面,林岗、张宇深入剖析了两种产权分析范式。[1]张泽一从产权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层面、产权起源、产权绩效、产权结构和产权变迁等角度比较了两种产权理论。[2]李云海就两种产权理论做了更细化的比较研究,比较了两种产权理论的微观基础,指出两种产权理论的微观基础在其界定范畴、激励方式和变迁动力上不同。[3]吴振球、尹德洪从私有产权的起源和产权制度演进动力视角进行了两者的比较,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私有产权的起源和演进动力来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下产生的社会大分工逐渐形成的,是历史动态的视角。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来源则是劳动力个人产权,私有产权的建立也只是考虑到这种产权制度建立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产权就得以建立。[4]吴易风运用经济哲学的方法论和一般的方法论比较了马克思和科斯的产权理论,指出经济基础中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决定上层建筑中的包括产权在内的法权关系。包括产权关系的法权关系是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产权是所有制关系的法的观念[5]。
除了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产权理论的系统比较之外,也有针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各自的产权理论研究及其著名产权学派的名家思想进行评论研究。叶祥松研究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概述了产权的含义和本质,认为产权是财产主体对财产所拥有的排他性、归属性的关系或权利,其实质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或经济权利;分析了产权的权能,认为产权的权能既是统一的,又可以是分离的。同时,产权也具有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的保障功能。[6]陈霜华评论了科斯的产权理论,批判了其只有私有产权才能推进市场和提高经济效率的观点,认为其违背了分析逻辑和实践发展的要求,指出科斯的分析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分析方法基础之上的,缺少整体主义的方法分析问题。[7]程民选评论了巴泽尔的产权理论,指出对巴泽尔在产权理论研究中认同的基本观点,即产权是相对的,产权也是一种商品,有多种属性且可分的;为了价值最大化,产权也是有约束的;认可个人在产权制度安排中的作用。[8]
产权理论研究众多,观点纷呈,周春云梳理了1997—2006年关于产权理论的研究,发现产权理论的研究随着经济改革实践而不断向前发展,与我国经济社会中产权变革的社会实践相呼应。[9]但观点争鸣中也出现了一些混乱的地方,为此,宗寒指出当前理论界产权研究的误区,一是抽掉所有制与产权关系的内涵,把产权泛化,认为产权就等于私有产权;二是不是客观地分析各类产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必然性和相互关系,而是一味批判公有制,说公有产权违背人性,私有产权符合人性;三是把产权看成一切。[10]白暴力认为现在的产权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以下误区:虚假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就是指所有权,这容易让人认为界定产权就是所有权的私有化;基础层次倒置,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不能反过来说私有制就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私有化理论,认为私有化可以解决一切的产权问题;将“人权”当“产权”的误区,把劳动者物化,仅仅作为生产要素看,而忽视了人是最重要、有生命力的主体。[11]石淑华指出产权问题的认识误区,即产权理论应用范围上出现了错位和泛化,忽视了公营经济的特殊性,把适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产权理论应用于公营经济领域;在产权理解上出现了偏差,即忽视了产权的可分割性和可让渡性,把公营经济的民营化等同于私有化;产权理论与改革实践出现了脱节,导致产权理论创新和发展严重滞后。[12]
以往文献已对产权理论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比较研究,既有从整体上探讨两种产权理论研究范式的根本区别,也有从微观上探讨两种产权理论的来源和动力上的区别;既有对国外产权理论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的评析,也有对国内产权理论研究上的针砭,这些研究以理论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居多,也开始涉足比较研究后所形成的产权理论综合指导产权理论改革实践的研究。但产权作为一组经济权利束,对产权的统一与分离、公平与效率、多样与稳定的研究重视不够,这是因两种产权理论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研究范式和终极目标所致。本文从宏观视角上,在以往产权理论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两种产权理论的精华之处,探究其对我国产权理论改革的启示。
3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比较
3.1两者的理论基础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是建立在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的体系上,其产权理论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基础上产生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不同的生产力阶段,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下的生产方式。以这种范式的逻辑考虑,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就会形成不同的所有权,所有权是最重要和最大的,其他一切权属都是由其衍生的。不同的生产力时期,有不同的主导阶级和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该主导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就会以法律的形式固化这种生产资料占有权利,而使其合法化,这样也就形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产权。马克思采取先研究劳资矛盾后研究供需矛盾的方法,继承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同时把自己的产权理论建立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之上。他利用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按照“天赋人权”理论建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重点论述了这种优先保护资产者非劳动生产要素及其所有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科学地指出了它的历史过渡性。
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以边际效用为核心的分析体系上,其产权理论也是在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上产生的,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用的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把产权的法律属性上升到最高的高度,而故意略去产权的实质和核心,撇开了产权来源的“原罪”,掩盖了对物的所有或占有是怎么来的问题,尽显其唯心主义。
3.2两者的研究范式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定性和规范分析,从生产力的角度,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方式,及其孕育其中的生产关系,而进行的法权分析和阶级分析。谁位于统治阶级的位置,生产资料就归谁所有,也就形成了所有制下的所有权,进而由所有权衍生出使用权、分配权、受益权等等。马克思经济学中所讲的产权是一种生产关系,这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同时不同的生产力决定不同的所有制社会形态,也即不同的社会关系,由此就会产生不同的产权形态,这是一个历史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且马克思经济学中所讲的产权是公有产权,因为这是为了消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下的阶级剥削关系。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而且商品的交换买卖也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着力于经济关系上的法属关系,通过人对物的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从一种社会的、整体的视角来进行的。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依然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范式,强调产权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界定、明晰产权就是为了分清收益与成本。它所讲的产权体现的是一种交易关系,它忽略了生产力及所有制社会形态,仅从功用的角度来阐述产权的交换所能带来的收益。认为为了保障利益相关方权益,明晰产权,就只能实行私有化,过于强调产权的私有属性,其所讲的产权实质是私有产权,主张把产权完全界定到个人,实行私有化,认可产权的私有化是最有效率的。西方经济学中所讲的产权是从法律角度进行权利及制度规范化以减少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及内耗,更好地实现资源的配置,提高市场效率,体现的是一种法律关系。这是从个人主义的、局部的视角来进行的。
3.3产权研究的终极目标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所进行的产权研究是在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进行的。一种所有制战胜另一种所有制,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的,当一种所有制战胜另一种所有制,这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已不能使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而形成产权制度变迁,这最终也是为了论证社会的历史动态演变,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
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研究,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经济社会模式,是站在资本主义及其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其摇旗呐喊,只把成本—收益下的效率作为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力,而绝不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对产权制度变迁的影响和被影响。
4 产权比较对我国产权理论发展的启示
有比较才能有借鉴,在产权理论的发展和实践上,应在继承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中科学合理的部分,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为我国深化改革的实践做出指导。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更多充满了哲学思辨,可做产权理论战略上的指导,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科学合理的产权理论,借助于其在具体事物上的更具实用和可操作性的部分,为我国的产权理论改革贡献力量。在我国的产权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中,应始终坚持“马克思经济学为本,西方经济学为用”的原则,在产权理论的比较研究中,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立场、理论基础、终极目标的前提下,在具体的研究分析方法和视角上借鉴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中可以吸收的部分,丰富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指导中国产权理论改革的实践。
4.1产权的统一与分离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因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一切归“公”,过于强调国家和集体的所有制下的所有权,造成产权过于统一,忽视了个人的经济权利利益,这样致使激励机制缺失,不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对个人经济权利重视起来,改变了过去产权过于统一的局面,产权束依据不同的属性也在不断细分,但也应注意避免矫枉过正,主张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完全私有化的产权理论。产权体现的是一组经济权利束,其中包含有若干权利要素,这些产权既可以统一于一个整体,也可以从中分离出不同的权利要素。
我国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制度的基础,所有的产权讨论都应统一于这个前提之下,同时对相应的权利如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进行细分,在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整体视角下重视产权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生产关系的同时,做到既重视经济利益的生产,又能根据产权的细分,做好经济利益的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对于涉及国家公共利益的部分,产权由国家代理经营,并根据其具体收益情况回馈民众;对于涉及民生经济利益的部分,产权在统一于公有制的前提下,对其余下的权利根据权、责、利对等的原则细分于民众,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交易。
4.2产权的公平与效率相结合
产权的制度安排背后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经济权利及利益关系,涉及人们对某一物的拥有、使用和选择的权利。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会对不同的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可能有人受益而有人受损,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效率和社会的公平。不同的产权界定也会有不同的帕累托效应存在,为做到兼顾公平与效率,应考虑使产权界定达到帕累托效应最优。为此,应界定产权边界,明晰产权归属,分清产权的责任方和受益人,借鉴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中产权的法律属性,运用法律来实施产权的制度安排。
鉴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下的产权制度安排,产权统一于国家主体的层面,任一产权制度的改革变动可能都会影响到相当大部分的群体。有些产权变革,效率提高了,但公平程度却降低了。当然也不能纯粹为了公平,而不讲发展、不要效率,而是在产权改革中借鉴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所提出的效率与产权制度安排相互作用的思想,兼顾公平与效率。
4.3产权的多样与稳定相结合
受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产权理论改革实践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在产权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方面还有着改进的空间,产权的多样意味着经济利益的开发更充分,更多的人能从这种经济利益的权利关系中获益,但前提是产权更明晰,产权的主体方更明确,由此就能降低经济社会运行的外在成本;产权的稳定意味着产权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使人们有一个稳定可信的权利收益预期,这样也可避免出现悖德倾向下的机会主义行为。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国家的终极目标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产权的安排上应发挥其在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在分配制度上,我国现在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支持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应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利用产权的激励作用发挥各生产要素主体的能动作用,在合理、科学的前提下,应允许产权制度安排的灵活多样。同时,产权一经安排,应保持稳定,因为产权体现的就是各利益主体间信用背书下的未来价值预期,应借鉴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中的交易关系、法属关系,完善产权法律保护,维护产权交易市场秩序,因为如果产权不够稳定,不管产权最终归属谁,没有稳定的未来价值预期,这样的产权终归是虚无的。
5 产权比较视角下我国农地产权改革的探讨
5.1地权的统一与分离
地权是权力集合,广义上涵盖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流转权。王露璐对近代我国苏南地区农地的研究,发现当时地权就有田底权和田面权之分,存在着所谓的“一田二主”现象,这是当时工商业发展催化的结果。[13]新中国成立后,农地产权从改革开放后的两权分离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提出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立。农地产权也从统一到分离,不断细化农地产权,根据相应的权利,获得与之相对应的收益。
按照马克思工农业联合发展和产权统一与分离的思想,农地产权统一于集体,集体拥有最终的所有权,通过确权颁证承认其承包权,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放活农地经营权。根据成员权建立农地承包权的继承制,规范农地的承包经营对象和用途;根据经营权,改革农地的相关补贴制度,使农业补贴真正用于农业经营。农地产权的分离中,根据权利的边界建立完善的交易协调机制。
5.2地权的公平与效率
马良灿认为地权是一束权力关系[14],这就把土地问题从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向人与人的关系,在地权的收益中,国家、集体和农民皆有份额,国家份额随着工业反哺农业,农业税费的取消,国家对农业剩余的索取变小,而集体的利益也因税费改革导致的集体组织虚化而不能实现。农民的地权收益得到了法律承认,为保障农民的生存利益,农民可以在保有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进行土地流转。在国家、集体和农民间进行地权的利益划分时,应找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点,在强化农民承包经营权时,实化集体所有权。童列春坚持以成员权进行农村地权利益的分配[15],这样既把农民包含在集体中,增加对集体的认同,也更好实现农地功能资源配置。
马克思经济学所重视的从利益冲突的视角研究地权问题,根据利益结构的变动来兼顾效率和公平。要让农民从土地增值中获益,要让土地成为农民发展的资本。处理好国家、集体与农民三者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在此,程世勇认为应做到程序正义和差别正义[16],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征地中应建立维护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机制,给失地农民合理公正的补偿,并具有可持续性,除了现金补偿外,还应保障发展权。农地征用所产生的利益,应归集体所有,由集体在提取集体公益金的前提下,在成员间进行合理分配,而集体公益金将用于集体公共利益的服务供给。
5.3地权的稳定与多样
有稳定的地权,可以鼓励农民在土地上进行长期投资,如对土地进行的改良,由此可在土地流转中获得级差地租的升值额度。地权不稳定,地权变动的概率直接影响农户土地投资行为,孙杨和罗伯特C.埃里克森认为这会导致对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和减少对土地改良所做的投资。[17-18]我国虽有保持耕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的制度,但因我国地权界定没有在法律中得到明确体现,Peter Ho认为政府由此通过“有意的制度模糊”来为自己留下模糊操作的空白地带[19],就为政府权力和利益团体参与地权利益争夺提供了缝隙,所以,我国的农地产权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为此,在保有农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对每户承包耕地进行确权颁证,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放活农地承包经营权。由村集体组织对流转土地进行登记背书,完善农地的用途监管,防止农地非农化、资本裹挟农地的现象出现。在当前农村人口转移和生育率下降致使农村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应稳定农地的承包权,也应使这种权利在同代间可以流转,在代际间可以继承。
相应的权力带来相应的权益。龙登高对清代地权交易形式的研究发现其有三大类型:债权性融通、产权转让、股权交易出现。而且不发生土地产权最终转移的融通性债权交易形式也呈现多样化,具体有:“押”“典”“当”“抵”。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地权所有者的权益,地权转让与收益补偿的交易形式则有活卖、绝卖、佃权顶退、找价、回赎等[20]。地权交易的多样化形式,在保有地权的同时满足农户的资金融通需求有着极大的作用,促进了土地流转,使生产要素组合和资源配置通过地权交易得到发展。可以借鉴清代的地权交易多样化形式,发展创新我国当代的地权多样化形式,完善农地的抵押、贷款机制,实现农地的融资功能,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当然前提是建立地权的保护机制,不能因地权的多样化形式,造成地权的混乱和无序。
[1] 林岗,张宇.产权分析的两种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1):134-145.
[2] 张泽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2008,(5):13-16.
[3] 李云海.产权理论的微观基础——西方产权理论与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差异分析[J].生产力研究,2010,(11):6-8.
[4] 吴振球,尹德洪.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比较——基于私有产权起源和产权制度演进动力视角[J].经济问题,2007,(11):4-6,57.
[5] 吴易风.产权理论:马克思和科斯的比较[J].中国社会科学,2007,(2):5-18.
[6] 叶祥松.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J].经济经纬,2000,(4):15-18.
[7] 陈霜华.科斯产权理论评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2,(3):25-26.
[8] 程民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产权理论的比较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9):41-45.
[9] 周春云.我国产权理论研究(1997—2006年)的基本情况与态势[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63-68.
[10] 宗寒.产权三论[J].东岳论丛,2005,(3):152-156.
[11] 白暴力.产权理论与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5,(4):5-6.
[12] 石淑华.论产权问题的几个认识误区[J].经济学动态,2009,(1):29-32.
[13] 王露璐.“生存伦理”与“理性意识”的共生与紧张——20 世纪20—40年代苏南乡村地权关系的经济伦理解读[J].江苏社会科学,2007,(6):54-58.
[14] 马良灿.地权是一束权力关系[J].中国农村观察,2009,(2):25-33.
[15] 童列春.中国农村经济实现中的地租机制[J].农业经济问题,2013,(3):25-32.
[16] 程世勇.地价失灵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2010,(7):11-15.
[17] 孙杨.地权影响下的农户土地投资行为和绩效分析[J].农村经济,2011,(11):85-87.
[18] [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复杂地权的代价:以中国的两个制度为例[J].清华法学,2012,(1):5-16.
[19] [荷]何·皮特(Peter Ho).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M].林韵然,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0] 龙登高.清代地权交易形式的多样化发展[J].清史研究,2008,(8):44-58.
【责任编辑马小侠】
Comparative Study on Property Right Theory of Marxist Economics and Western Economics and Comments on the Reform of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WANG Liu-xin,HE Ai-ping,HE Lian-c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ern University,Xi’an 710127,China)
Property theory of Marxist economics and western economics belongs to two theoretical systems. There are large differences on theoretical basis,research paradigm and ultimate goal.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of value standpoint is irreconcilable,while the both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in specific property rights practice. Therefore,in guiding Chines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s,the unity and separation of property rights,the equity and efficiency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diversity and stability of property rights should be integr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arison and revelation of property rights,the path of the reform of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is discussed,to unify land ownership in the collective,to refine contract right,management right and transfer right,and to build the inheritance system of the contract right of rural land along with the member right. In the land requisition and circulation management,the farmers’ right to exist and develop should be protected,and the collective public interest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agricultural land should be applied to collective public services. In legal form the stability of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are regulated,and the system innovation is stressed on developing the d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Marxist economics; western economics; property right theory; comparative study
F091.91;F014.1
A
1009-5128(2016)12-0071-06
2016-04-13
王留鑫(1989—),男,河南南阳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何爱平(1967—),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何炼成(1928—),男,湖南浏阳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劳动价值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