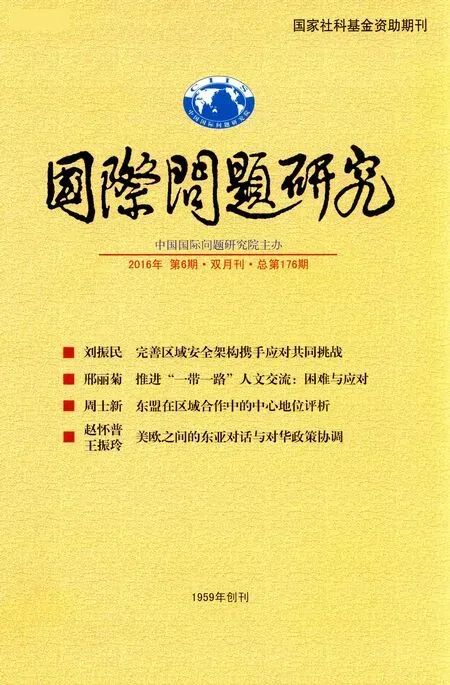美国关于大战略的辩论及其影响*
张学昆
美国关于大战略的辩论及其影响*
张学昆
〔提要〕近年来,为应对变化的战略环境,维持世界领导地位,美国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大战略调整,战略学界也围绕不同战略选项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美国经济能否继续负担‘深度介入’”、“‘深度介入’是否适应当今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变化”、“美国应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扮演何种角色”、“美国是否应致力于推广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大战略总体呈现守势,局部采取攻势,主要表现为在中东、欧洲等地区实施收缩和克制,在亚太地区推行以“再平衡”战略为主要内容的深度介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全球战略收缩势头有可能加强。美国的战略收缩和再布局,并不意味其要放弃全球领导角色,而是试图避免过度扩张和过多干涉,转而以一种平衡和“可持续”的方式实现自身战略目标。
美国大战略、战略收缩、美国外交
近年来,随着战略环境的变化,美国对其长期实施的扩张型大战略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并通过改变战略思维和采取一系列新的战略举措,对其大战略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调整,以维持战略手段与目标的平衡,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在这一进程中,美国战略学界围绕不同的大战略选项及美国介入世界事务的性质和范围等展开了激烈辩论,产生了一定的政策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近年来美国战略环境和实力地位的变化,梳理和剖析美国战略学界的相关辩论,进而探讨美国大战略调整的进程和内容,旨在认清美国大战略的本质特征和发展方向,评估其对国际和地区形势以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美国大战略调整的背景
冷战后,美国作为守成大国,为维护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一直推行一种扩张型大战略,广泛且深度地介入国际事务。然而,进入21世纪,这种战略不但没有带来预期效果,反而造成过度扩张,引发了很多负面效应:削弱了美国领导力、破坏了地区秩序、损害了国际规范。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而同期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则保持崛起势头,致使美国的相对实力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被迫对其大战略进行调整。
(一)美国大战略目标
大战略是关于确定国家核心目标与为实现核心目标可用的各种实力、资源和手段之间的一种匹配关系,它首先要明确国家重要的目标和利益,继而确定实现这些目标和利益面临着哪些挑战或威胁,最终通过选择和推荐特定的政策工具或手段,来应对挑战并实现国家目标。因此,大战略是一种概念上的路线图,描绘了如何确定目标、优先排序,以及把国家资源和国家利益匹配起来。[1]Colin Dueck, The Obama Doctrine: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Tod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4-15.一项有效的大战略必须能确保目标和手段的良好匹配,所做出的承诺不应超出能力范围,否则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甚至风险。
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目标是维护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进而维持美国的安全、繁荣和自由。为此,美国需要达成以下三个目标:塑造外部安全环境以减少对美国安全的中近期威胁;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自由市场经济以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创立并维持促进国际合作且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制度体系。[1]Stephen G. Brooks, G. 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7, No.3, Winter 2012/13, pp.11-12.长期以来,为实现以上目标,美国在世界范围推行扩张型大战略,加强海外的前沿军事存在和对盟友提供安全保证,以优越的军事能力和使用力量的可信意志为基础,宣称要在世界各地促进民主和保护人权。
美国大战略在确保其独霸美洲的前提下,尤为重视欧洲、东亚和中东/波斯湾这三个世界核心区域,并投入了大量资源和战略关注。在欧洲和东亚,美国的主要关切是维持地区均势、防止出现地区霸主,牵制该地区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东/波斯湾地区,美国的目标一是防止出现地区霸主,维持地区石油输出秩序,维护世界和美国经济繁荣;二是保护盟友以色列,确保美国中东战略支点国家安全。总之,美国大战略致力于维持在全球的主导地位,防范在上述核心区域出现潜在的地区霸权。
(二)美国相对实力发生变化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对国际秩序的主导能力相对下降,有关美国开始衰落的论调喧嚣一时。那么,这种论调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呢?大国实力的衰落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绝对衰落,即一国相对于自身鼎盛期的力量衰减;另一种是相对衰落,即一国相对于他国的实力优势缩小。约瑟夫·奈认为,理解“衰落”这个概念,关键在于思考美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重要的是要考虑相对衰落而不是绝对衰落。[2]Joseph S. Nye, Jr., 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他从对外实力和国内衰败两方面进一步澄清了“衰落”这一概念,前者是在国际体系中相对其他国家而言,后者则代表了缺乏把资源转化成实力的内部能力。
首先看美国的对外实力。实力是多维、变动和难以精确测量的,但从长期来看,衡量一国相对于他国实力的大小,最重要的指标是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在经济实力上,美国的优势因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经济实力增长与其差距缩小而减少。2015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为15.5%,相当于美国GDP的63.4%,这一比例较2012年提高了11%。[1]“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国际比较”,国家统计局网站,2016年3月9日,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603/ t20160309_1328611.html。(上网时间:2016年5月16日)在军事实力上,美国仍占有很大优势,其军费开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为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在制海权、制空权乃至在外空、网络空间领域掌握着主导权,军事盟友遍及全球。不过美国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其他国家在军事策略和技术上的变化正在侵蚀美国的优势,反舰巡航导弹使得美国更加难以靠近对手的海岸,先进的地对空导弹使美国维持空中优势的成本增大。此外,近年来美国持续削减军费开支,在2010—2016年期间,美国的防务预算实际下跌14%,占GDP的比例下跌大约30%。[2]Mac Thornberry and Andrew F.Krepinevich, Jr., “Preserving Primacy: A Defense Strategy for the New Administar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6, p.28.其次看美国是否正在经历政治衰败。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美国当前正在经历政治衰败:三权分立的宪法体制、两极分化的党派斗争、财力雄厚的利益集团,共同构成了美国的“否决政治”,造成了阻碍政府做事的局势。[3]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6, p.58.从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不断受到共和党的攻讦和国会的掣肘,以及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所呈现的乱象来看,目前美国的政治体系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败,这显然会对美国把资源转化成实力的内部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单纯的经济规模并不足以衡量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大小,必须把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和军事实力等指标考虑在内。作为国际体系中与美国实力最为接近的国家,同时也被认为是最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中国在这些指标上跟美国的差距还比较大。正如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所指出的,中国的崛起是真实的,它吸引了全球如此多观察家和领导人的关注是有原因的,但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崛起常常被夸大,中国崛起的意义被误读。[4]Thomas J.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W.W. Norton, 2015, p.48.总的来看,美国并未遭遇绝对衰落,只是相对实力发生了一些不利的变化,且这种变化的速度和程度都比较温和。无论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来看,还是从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来衡量,当前美国在国际体系中仍处于优势地位。
(三)美国的过度扩张
“过度扩张”指霸权国对战略目标的追求超出能力范围,以及战略成本超过“成本—收益”的均衡点,导致陷入战略困境。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基于“自由干涉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的战略理念,打着“反恐战争”旗号,将“单边主义”和“干涉主义”发挥到极致,发动了旷日持久且代价高昂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然而,两场战争非但未能把阿富汗和伊拉克打造成中东地区民主政治的样板,反而加剧了地区局势动荡,催生了“伊斯兰国”(ISIS)等恐怖主义势力。美国则陷入过度扩张的状态,巨额军费开支使其不堪重负,国内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进一步加剧,反战情绪日渐高涨,要求美国“回家”(撤离和收缩)的呼声加大。[1]Kurt M.Campbell, The Pivo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 New York: Hachette Book Group, 2016, pp.303-306.美国不仅为两场战争付出了高额账单(据估算高达4万亿到6万亿美元),而且还因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及虐囚等丑闻破坏了形象和声誉,损害其介入国际事务的合法性基础。此外,长期深陷中东泥潭还让美国的全球战略失衡,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入相对不足。随着世界重心从大西洋向亚太地区转移,加之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正在改变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美国需在该地区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关注,以维持地区主导权和影响力。
二、美国关于大战略的辩论
美国在大战略调整中的选项包括两大类:深度介入(deep engagement)和收缩(retrenchment)。前者通过寻求增加资源,比如增加国内税收以补足预算缺口,或要求盟国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在进行适当革新的基础上继续推行扩张型大战略,维持海外前沿军事存在,履行国际安全承诺,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甚至谋求对其他国家进行政权更迭等。“深度介入”政策的支持者(以下简称为“介入派”)认为,“深度介入”是美国追求安全、繁荣和自由等核心利益的有效路径,不应夸大其成本并低估其收益,鉴于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仍将保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继续推行“深度介入”是最好的战略选择。[1]Peter Feaver, eds., Strategic Retrenchment and Renewal i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August 2014, pp.221-242; Stephen G. Brooks, G. 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7, No.3, Winter 2012/13, pp.7-51.与之相反,“收缩”战略的支持者(以下简称为“收缩派”)认为,美国的“深度介入”战略代价高昂,为维持同盟体系和履行安全承诺付出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且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干涉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因此,美国不应再实施扩张性的大战略,解决之道就是对现行战略进行实质性调整,减少在海外的军事存在和对盟友的承诺,通过在全球范围或某些地区缩减承诺、减少支出、降低风险和转移负担等方式,实施战略克制和收缩,把资源和战略关注转向应对更重要的内外挑战,比如振兴国内经济、应对中国崛起。
关于大战略的激烈辩论反映了美国国内对自身所处战略环境以及在这一环境中的利益、目标、角色和手段等不同的认知。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美国经济能否继续负担‘深度介入’的大战略”、“‘深度介入’是否适应当今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变化”、“美国应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扮演何种角色”、“美国是否应致力于推广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等一系列关键问题。
(一)国内预算能否继续负担“深度介入”
“收缩派”认为,在当前和预期的经济形势下,美国将难以负担“深度介入”的高昂成本。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开支压力巨大,加之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都限制了美国的海外行动能力。对于一般国家来说,资源多优先用于交通、教育、养老、医疗等国内项目,对外投入则受到限制。而美国长期以来凭借强大的国力,对外投入并未受到此类限制,但这样的时代正在结束,新的限制性因素要求美国缩减防务和外交开支,把资源转向振兴国内经济。
“介入派”认为,虽然美国面临着严重的预算问题和缓慢的经济复苏,但不能也不应通过大战略收缩来解决财政危机,况且当前水平的防务和外交开支仍然可以负担。他们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财政危机并非源于防务开支的增加,其与国内社会福利支出相较比重很小。例如,2015年美国防务开支占联邦预算的16%,且这一比例还在下降;而同期国内社会福利则占联邦预算的49%,且这一比例还在上升。[1]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Policy Basics: Where Do Our Federal Tax Dollars Go?,” March 4, 2016, http://www.cbpp.org/cms/?fa=view&id=1258.(上网时间:2016年10月5日)从历史来看,冷战时期美国的防务开支远高于当前,1950年到1990年间,美国国防开支占GDP比例年均为7.6%,而冷战后降至5%以下,即便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高峰期间,该比例也并未超过5%。[2]Evan Braden Montgomery, “Contested Primacy in the Western Pacifi c: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U.S. Power Projec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8, No.4, 2014, p.119.因此,当前财政危机的解决之道是改变国内社会福利项目不可持续的趋势。第二,美国通过缩减国际承诺可节省约1%的GDP,但当美国为了核心利益需要派军队重返海外作战时,此前所节省的经费将被更高的支出抵消。[3]Elbridge Colby and Jim Thomas, “The Future of Allian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August 2016, p.37.因此,从经济上来说,相比撤离海外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当前投入资源来维持美国的海外军事存在是合算的。
(二)“深度介入”是否顺应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变化
“收缩派”认为,“深度介入”不适合当前国际体系正在形成的多极结构。美国已不再是多极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重心正从大西洋向亚太地区转移,因此需要对大战略进行调整,在全球层面进行收缩,重新确定美国外交的优先方向。“深度介入”将在国际体系层面激发两种针对美国的阻力:第一,促使其他国家以结盟、内部平衡(把潜力转变成军事能力)、“软制衡”(使用制度、规范或其他非军事手段)等不同形式制衡美国;第二,过度扩张导致霸权衰落,其逻辑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指出的,美国将在霸权的诱惑下走向扩张,由于过度扩张而不堪重负,最终走向衰落。因此,美国应适时进行收缩,避开霸权国的历史宿命。
“介入派”认为,美国仍能在未来几十年维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深度介入”仍是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最好选择。他们并不否认近年来美国在某些领域实力的相对衰落,如经济领域,但强调美国仍维持着在其他多数领域的明显优势,如超强的军事实力、科教实力等,这使得美国能继续在国际体系处于领先地位。“深度介入”并不会激发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因为制衡主要是针对地理上邻近的霸权国或威胁最大国家的行为,这并不适用于美国: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屏障使美国在地理上处于相对超脱地位,美国也没有侵占其他国家领土的野心,这减弱了其他国家对美国威胁的感知程度。
(三)美国应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扮演何种角色
“收缩派”认为,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争夺军事霸权是不明智的,维持均势而非成为主导者应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美国的比较优势在海军和空军,应主要通过加强海空能力维持地区均势,而非把地面部队送到战场。美国应放弃推动政权更迭、改造其他国家的雄心,因为追求意识形态目标会使美国卷入无益于自身利益的十字军东征式战争,这些冲突不仅浪费了本可用于国内振兴的精力和资源,还引发了国际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导致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恐怖袭击,发生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冲突就是例证。[1]Denny Roy, “A More-Selective US Grand Strategy,” June 28, 2016, https://www.csis.org/ analysis/pacnet-53-more-selective-us-grand-strategy.(上网时间:2016年9月26日)扩展民主有时需要实施军事占领,并经常需要干预当地的政治安排,这些做法总会激起当地民族主义者的憎恨,由于民族主义者没有实力与美国直接对抗,因而会转向恐怖主义。美国发起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破坏了中东地区力量平衡,数以千计的美国人付出生命代价,并催生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2]Jacob Heilbrunn, “What is America’s Purpose?,”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15, p.34.奥巴马认为,“几乎每一个伟大的世界大国都曾被过度扩张拖垮,我不认为每当出现问题时就派出军队强行施加秩序是一种聪明的做法。我们不能再那样做了。”[3]Jeffre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The U.S. President Talks through His Hardest Decisions about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The Atlantic, April 2016.总之,在“收缩派”看来,美国应缩减对外承诺,减少海外驻军,只有在地区均势被打破时,才应进行干预以恢复均势。
研究表明,葡萄种植过程中,实施水肥一体化对葡萄的生长起着很大的辅助作用。由于葡萄植株对水肥要求较高,传统的灌溉方法和施肥方式容易受到地域和季节等因素的限制,缺乏一定时效性,面对植株的生长无法发挥最大的效果。水肥一体化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地形和季节对这种技术的影响很小,因而不必担心地形对浇灌的制约,从根本上使得问题得到解决。通过这种定时定量的水肥输送,使得葡萄快速生长,有助于其产量的提高。
“介入派”认为,美国应继续投入资源维持在全球范围的军事存在,以确保能够完成一系列不同任务:保卫国土,确保自由进入海洋、空中、太空乃至网络空间等全球公地,维护欧洲和平,努力在大中东地区建立和平,应对亚太地区新兴大国崛起,等等。美国的军事力量应能威慑敌人和影响可能的侵略者,并让盟友和伙伴相信美国有能力为其提供安全支持。美国在北美、欧洲和东亚等地区建立的安全同盟体系是美国战略优势和影响力的持久来源,并最终加强了美国自身安全,因此应坚定维持对盟友的安全承诺。[1]Elbridge Colby, “Don’t Scrap America’s Alliances, Fix Them,”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ne 29, 2016,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nt-scrap-americas-alliances-fix-them-16788?page=show.(上网时间:2016年8月3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行不应以损害美国在欧洲、中东或其他地区的安全承诺为代价。[2]Luis Simón, “Balancing Priorities in America’s European Strategy,” Parameters, Vol.46, No.1, Spring 2016, p.15.美国的安全承诺和前沿军事部署,不仅可以阻止有区域霸权野心的国家进行扩张,还可以约束盟友和伙伴采取挑衅性行动,从而避免地区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的加剧。
(四)美国是否应致力于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
“收缩派”认为,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偏离了为促进美国利益所应完成的核心使命,美国应放弃这种做法,转而依据切实的国家利益制定政策并开展对外行动。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是可有可无的目标,执著于此会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副作用,在推动其他国家进行所谓的“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这类难以完成的任务上耗费宝贵的资源。美国之所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旷日持久且代价高昂的战争,就是因为试图把自由民主价值观移植到这两个国家,殊不知这是一种错误的理念,造成美国未能在重要的安全利益和边缘性利益之间做出区分。
“介入派”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由民主对于实现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很有必要,且能增加美国的软实力和全球影响力。此外,美国最紧密和可靠的盟友是民主国家,因此,促进民主将扩展能与美国建立持久和紧密关系的国家范围。[3]Hal Brands, “Rethingking Amrican’s Grand Strategy: Insights from the Cold War,” Parameters, Vol.45, No.4, Winter 2015-16, p.12.美国应继续做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有力推动者、人权捍卫者 ,坚决反对任何严重践踏人权的现象。扩展美国的价值观能促进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因而在道德规范上是值得的,此外它也是美国的一项核心安全利益,因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其必然有助于美国的安全。[1]Peter Feaver, ed., Strategic Retrenchment and Renewal i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August 2014, pp.241-242.
三、产生大战略选择分歧的原因
关于大战略的辩论反映了美国国内在大战略选择上的分歧,这主要源于三方面原因。
(一)对美国当前实力地位及变化趋势存在不同认知
持悲观态度者则认为,基于国际政治中的“霸权更替”、“大国兴衰”等理论学说,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霸权的衰落将不可避免,当前美国经济已难以支撑其全球前沿部署的沉重负担,地缘政治影响力将逐渐减弱,因此应重新定位自身的全球角色,通过战略收缩等方式延长霸权时间或者谋求体面的衰落。
不管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他们在观察美国实力地位时都以中国作为重要参照。乐观主义者认为,虽然中美经济总量差距在缩小,但在科技水平和军事实力这两个重要力量指标上差距还非常大,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潜在超级大国,距离赶超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s Ris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s Global Posi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0, No.3, Winter 2015/16, pp.7-53.悲观主义者则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了首要的战略挑战,中国有望在未来10到1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即便今后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上升速度放缓,世界也将在未来数十年间见证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以来全球最大的权力转移。[2]Michael Green,et al., Asia-Pacifi c Rebalance 2025:Capabilities, Presence, and Partnerships,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nuary 2016, pp.10-11,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 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publication/160119_Green_AsiaPacificRebalance2025_Web_0.pdf.(上网时间:2016年7月24日)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是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都是中国崛起的显著例证。对美国实力地位的不同认知和对中国崛起前景的不同判断,成为引发美国国内在大战略选择上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
(二)美国外交战略深受两种不同的传统思想支配
美国外交中存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不同传统,它们对塑造美国大战略具有重要影响。理想主义传统,或称自由主义,是自美国建国伊始就已存在的理念,认为美国肩负着向世界传播民主和自由的天赋使命,负有领导和拯救世界的神圣职责。同时,一个由众多民主国家构成的世界将是和平稳定的,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只有在由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构成的开放世界里才最安全。美国影响世界的方法应是行动主义的“圣战”,有责任在其他国家保护自由和民主价值,推行民主和人权。[3]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这样,理想主义就塑造了一种扩张性的大战略,最终引导美国走向过度扩张和自由帝国主义,引发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干涉主义立场,甚至发动一些本可以避免的对外战争。在当前的大战略辩论中,秉承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观念者认为,美国有道德上和战略上的需求来促进自由和保护人权,扩展民主将在很大程度上使世界摆脱战争和残暴、减轻苦难并维持美国安全。[1]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Case for Offshore Balancing: A Superior U.S.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6, pp.79-80.
现实主义传统始自开国元勋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说,在之后很长时间里表现为孤立主义思潮。二战后,孤立主义在美国几近绝迹。然而近年来,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带给美国人的挫败感,加之金融危机的重创,使孤立主义情绪在美国有所回潮,在当前的大战略辩论中表现为一种现实主义立场。奥巴马自认是现实主义者,上任后多次宣称美国需要专注于国内建设。[2]Kurt M.Campbell, The Pivo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 New York: Hachette Book Group, 2016, p.361.他认为美国应该克制而不是随意对外干涉,只有在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介入外部事务。[3]Anthony H.Cordesman, “Is there an Obama Doctin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10, 2016,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here-obama-doctrine.(上网时间:2016年7月27日)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偏好表现出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并吸引了一大批坚定支持者。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4月所做的一项民调显示,57%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处理自己的问题,让其他国家处理它们的问题。[4]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Case for Offshore Balancing: A Superior U.S.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6, p.70.现实主义者对美国的例外主义及美国在捍卫自由、民主、人权方面的独特领导作用持怀疑态度,认为以武力威胁的方式来扩展民主收效甚微,还会损害美国的形象和声誉,甚至有损自身的价值观。美国应从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现实出发,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外交政策,不应执迷于理想化目标而使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陷入危险之中。
(三)美国国内对如何维护核心利益持不同观点
有观点认为,美国的地缘环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北部和南部的邻国相对弱小,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其东部和西部宽广的大西洋和太平洋,成为美国天然的安全屏障。此外,美国拥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众多充满活力的人口,这使得美国立足本国就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强的军事大国。美国还拥有数千件核武器,也使得其他国家发动对美国本土攻击的可能性极低。因此,无需推行代价高昂的扩张型大战略,美国就能维持自身的强大和安全。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安全、繁荣和自由与开放的国际体系密切相关,而要维持开放的国际体系就必须要有一个霸权国家存在,由它来提供秩序、合作、安全、汇率稳定等公共物品,这就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在他们看来,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并且有意愿为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提供公共物品的国家,为此美国需要实施一种“深度介入”的大战略,甚至在必要时进行对外军事干涉。
四、大战略辩论的影响
大战略辩论为决策者提供了战略选项,也对近年来美国政府的大战略调整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可能继续塑造今后美国的大战略调整。
首先,大战略辩论正在改变美国的舆论倾向,也在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进而影响美国的政策调整。由于金融危机后美国相对实力发生变化,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给美国造成了巨大财力损耗和众多人员伤亡,近年来美国民众对美国介入国际事务的支持度下降。大战略辩论进一步加强了公众舆论呼吁美国减少介入国际事务的呼声,而美国各派政治力量要获得选民的支持,他们的政策主张就需要回应选民的意愿。奥巴马政府顺应形势,对其前任的大战略进行调整和纠偏。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和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张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大战略辩论的影响,他们都认识到民众对政府无休止和不惜代价地介入国际事务感到厌倦,从而竞相提出满足选民意愿的政策主张。
其次,大战略辩论从历史、理论和现实层面厘清了不同选项的利弊得失,为美国政策调整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同时增进了民众对不同选项的深刻理解与认知,进而为美国政策调整提供民意支持。美国的大战略调整需要体现出美国对外战略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些对外战略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只有通过大辩论才能清楚地加以揭示并被人们所认知,进而提出解决方案。
最后,尽管大战略辩论具有政策含义和政策影响,但战略学界的辩论与对外政策制定仍存在一定区隔与分野,其更大的作用在于推动美国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学术研究不断取得理论进展,对具体政策制定产生指导作用。
如前所述,大战略辩论对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时,美国在战略和军事上处于过度扩张状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呈相对衰落之势,这促使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大战略进行调整。打着“变革”旗号上台的奥巴马认为:国内振兴对于任何长期大战略来说都至关重要;美国出现了过度扩张,尤其是在中东地区;小布什政府所犯的错误致使美国国际地位降到前所未有的低点。[1]Daniel W.Drezner, “Does Obama Have a Grand Strategy? Why We Need Doctines in Uncertain Times,” Foreign Affairs, Vol.90, No.4, 2011, p.64.基于这些理念,奥巴马政府把资源和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国内事务上,奉行经济优先原则,干预外部事务的信心和动力减弱;在对外采取行动时更加克制,强调“在背后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重视多边主义和“巧实力”;动员盟友和伙伴采取集体行动,分担风险与责任,这就是所谓的“奥巴马主义”。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大战略包含三项原则。第一,要维持冷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以及这种秩序所依赖的美国领导和首要地位,这在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每一份重要战略文件中都得到了明确表述。第二,要以更聪明、更低成本、更审慎的方式来实施全球领导,尤其是涉及使用武力时,应提高军事介入门槛,尽量避免卷入新的战争。第三,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因为亚太地区可能成为21世纪全球安全竞争和经济增长的中心,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了最大的长期挑战。[1]Hal Brands, “Breaking Down Obama’s Grand Strategy,”The National Interest, June 23,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breaking-down-obamas-grand-strategy-10719?page=show.(上网时间:2016年6月8日)
在政策实践上,奥巴马政府在攸关美国战略利益的三个核心区域分别施策。在中东,美国主要依赖经济、外交和情报在该地区展开行动而非军事介入,把自身的角色限定在提供支持和指导,同时专注于更具战略性的问题,比如在波斯湾地区的导弹防御和核威慑。在欧洲,美国要求北约欧洲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加强人员部署和能力建设,在北约框架下由它们负责欧洲的安全与防务,美国主要扮演战略性角色,比如提供核保护伞以及情报、监视、侦查(ISR)的指挥控制系统。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向欧洲增派军队,并提出了名为“欧洲安全保证倡议”(European Reassurance Initiative)的军事援助计划,重申美国的安全承诺。在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把加强与盟友及伙伴国的关系与扩大军事存在、优化军力部署结合起来,利用东海、南海、朝核等安全议题巩固其东亚地区的同盟体系,应对中国崛起给地区格局带来的冲击。
总的来看,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大战略仍然以维持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为总体目标,同时强调要以更低成本、更为平衡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表现出收缩和克制的特点。这一总体目标和收缩趋势有望继续保持。
五、结语
美国大战略辩论试图为处于转型期的对外政策指明调整方向。在美国相对实力发生变化和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美国的大战略调整旨在维持战略手段与战略目标的平衡,实现以更低成本和“可持续”方式来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因此收缩成为调整的主基调。但收缩并非孤立主义,也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全球领导角色,而是试图避免过度的对外干涉和过多的国际承诺,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转向应对更紧要的挑战。
伴随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共和党人特朗普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美国的大战略调整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从竞选言论来看,特朗普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偏好带有一定孤立主义倾向,认为美国应少干预国际事务,不应充当世界警察角色,主张重新构建美国与盟国关系,要求盟友承担美国海外驻军费用,在移民、穆斯林入境、全球化、自由贸易等许多议题上态度极端,对推广民主人权价值观等议题兴趣不大。但在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上,特朗普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策混乱。他认为目前美军国防开支占GDP比例处于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因此要加大军费开支,恢复美国绝对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与其战略收缩目标相矛盾。通常情况下,竞选言论与当选后的施政会有一定差距。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也将受到共和党建制派影响,这些人曾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过于软弱,致使美国国际影响力衰减,美国利益的外部威胁不断增加。可以预见,特朗普上任后推行的对外政策很可能会引发美国国内有关大战略调整的新一轮激烈辩论。
应对中国崛起是近年来美国大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动因,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和平发展和中美关系造成影响。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可能会出现新调整。但鉴于两国利益高度交融,在全球事务上相互依赖,维持双边关系总体稳定仍将会是美方的战略选择。面对美国的大战略调整,中国一方面应保持战略定力,继续深化国内改革和发展,审时度势地主动塑造周边和国际战略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应继续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利用现有机制平台深化各领域合作,扩大两国利益契合点,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完稿日期:2016-11-9】
【责任编辑:李静】
张学昆,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D871.20
A
0452 8832(2016)6期0074-16
* 本文的写作得到上海交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编号:16JCHY04),同时得到2015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的支持(项目编号:15PJC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