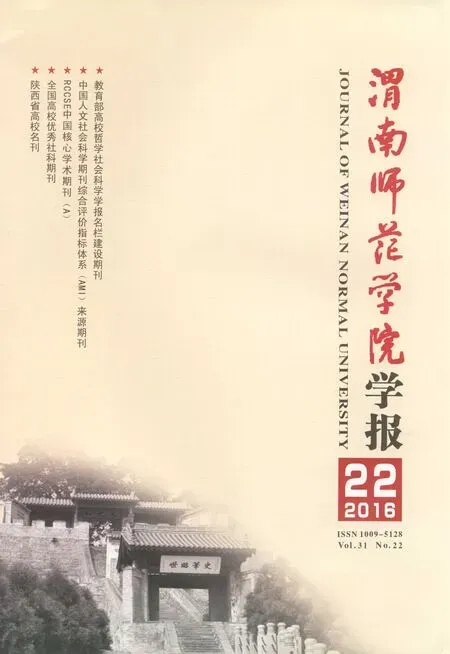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特征管窥
齐 玲,姚妍君
(曲阜师范大学 a.教育科学学院;b.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蓓蕾园地】
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特征管窥
齐 玲a,姚妍君b
(曲阜师范大学 a.教育科学学院;b.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指存在于近代大学场域内的学者或教员人群。它的产生和发展浸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因子,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时代特征,即教师群体来源构成新旧杂糅;教师伦理观逐步形成,大学教师职业获得承认;教师知识结构从单一到多元;教师职业技能由传统单调到灵活趋新。
中西文化冲突;近代大学教师群体;过渡性时代特征
清末民初的大学教师群体不仅在质量和数量上已颇具规模,而且在秉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兼具相当程度的西方文化素养,他们具有一定的近现代政治思想意识,并致力于发展中国近代化教育事业。它的产生和发展浸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因子,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时代特征。具体表现为:教师群体的来源构成新旧杂糅,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教师身份由模糊到明确,教师职业伦理观逐步形成;教师知识结构从单一到多元,系统的现代知识逐渐内聚;教师职业技能由传统单调走向灵活趋新。
一、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 来源构成:新旧杂糅
近代中国国势衰微,变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教育救国”一时被视为一剂救国良方。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和冲突的特殊历史时空下,我国教育的近代化已无法遵循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和连续性,而明显表现为对政治的依附性和同步性。因此,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及其教育不再是我国传统的古代高等教育的自然延伸和发展,而是在西学东渐的时势下“自觉不自愿”进行变革的产物。中国近代大学的产生为大学教师群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平台,作为存在于近代大学场域内的大学教师群体,就其人员构成来看,一方面有基于传统教育底色的历史基因,另一方面又自然地富有 “适世”的时代因子,故“新旧杂糅”成为这一群体来源构成的显著特征。
具体而言,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大致可分为旧式士人以及半新半旧之士、早期归国留学生和外籍传教士三类。旧式士人以及半新半旧之士成功实现身份转型有其必然性和可能性。就必然性而言,科举制的废除,从根本上切断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的“利禄之途”,打破了“学而优则仕”的耕读仕进传统,四民社会逐渐瓦解,士人在政治、文化等领域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成为“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1]。在科举制废除而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尚未建立之际,寻求自身生存依附之道便顺其自然地纳入士人考虑之列。而可能性则源于中国早期建立的独特教育制度,即这种教育制度主要针对上等社会人群受教而非一般民众,正所谓“学在官府”。教育的等级性直接导致知识的垄断性,即便后来私学兴盛以及书院产生,依然很难改变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事实,作为维系正统意识形态和传统儒家道德伦理主要载体的士人自然拥有对知识的掌控和解释,甚至获得了社会对他们“学术地位”的承认,故此类人群成为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近代化以及近代大学教师群体形成的过程中,早期归国留学生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国人的文化自信感面临动摇之际,人们放下自尊开始“礼失而求诸野”。更有人认为,“中国人如果想要保全自己的国家,唯一的道路就是学习西方的知识,而谁能完成这个重任,只有那些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人。”[2]33所以,前至洋务时期,后达民国初年,出现了一批批应国家之需、政府之急而系统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出国留学人员,他们有的求学于欧美,有的留学于东洋,旨在通过潜心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教育,探寻救国良方。 归国后的留学生普遍受到政府重视,或招其入仕委以重任,或自愿从事各行新业,但主要还是以教育行业为鹄的,毕竟作为新晋知识分子,在经过了西方先进教育后,所具有的新知和开阔的视野成为他们的独特优势。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归国留学生日后成了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的中坚力量,并在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中发挥着支柱性作用。
此外,外籍传教士作为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的又一组成部分,是伴随着教会在中国的建立以及教会大学的兴办而形成的。最初的教会多半是为了宣教,传递上帝福音,传教士更多程度上是作为传播西方教会文化的媒介展露世界,而任何异质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都势必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与碰撞,更何况后来的教会和传教士在受到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支持和庇护下,公然打出“中华归主”的旗号,直接从事文化侵略,自然受到国人的厌恶与抗拒。无论是为了更直接地为殖民主义侵略活动服务还是出于对自身传教人员不足的考虑,他们愈发地意识到需要建立自己的教育机构以培养宣教人才,此时的传教士才开始渐渐地有了几分“教师”的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成功实现职业转型成了“纯教师”。毕竟草创时期的教会学校,在多大程度上算是真正的教育机构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和考据。当教会学校内部开始对学校的宗教目的和学术目标何者为第一位展开讨论时,已经预示着教会学校教育功用的必然走向,特别是传教士试图将学校提高到大学水平,强调学校的学术水准,直至教会大学的创立时,教会大学场域内的传教士作为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的一部分已属事实。
从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的来源构成可以看出,他们产生于中西文化冲突下的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现代过渡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革下的教育制度转型和知识个体价值选择的共同产物。他们新旧交织、成分杂糅,却共同汇融于中国近代大学这一场域中,依托外部建制提供的生存空间做庇佑,最终形成了一个中国近代的新职业群体,即大学教师。
二、中国近代大学教师伦理观 的形成:职业承认
1.大学教师群体自身内部承认:忠诚
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职业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最先源于从事本职业内部人员的自身承认。所谓内部人员的自身承认,就是近代大学教师的自我肯定以及同行之间的互认。作为在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的近代中国萌生出的一种新型职业,大学教师职业在其产生后,具有稳定的追随者和从业者便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大学教师职业也就名不副实。而保证大学教师长久从业的根本绝非教师人员一时的兴趣冲动,而是基于大学教师自我认同以及由同行之间彼此互认而产生的自尊。衡量大学教师职业独立和成熟的标志,就是在“前从业者”的持续努力下,由大学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和社会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或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以至于能够引发后继者对大学教师职业的忠诚以及其他相关者的追随,甚至产生职业崇拜。这种强大的职业吸引力逐渐形成大学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同行之间开始彼此互认,且积极展露和标示自己的职业身份,并以此为傲。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阶段,大学教师对自身职业的忠诚程度不同。在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职业萌生初期,从业者甚至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教师职业概念。这一点可以从近代大学教师群体最初来源构成中管窥。作为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组成部分的旧式士人及半新半旧之士,虽然在遭受中西文化剧烈冲突下,着手进行自我调适以期实现身份转型和社会角色定位,但他们尚没有完全脱离封建官僚体制的束缚,也未曾彻底革新自己的思想,此时所谓的教师职业伦理依旧充斥着浓烈的“为官”夙愿,在内心情感上更多的还是对“封建道统”的依附而绝非对教师职业的忠诚。待到中国近代大学的教师从业者对自身职业开始有了清晰的认识并产生强烈的情感依恋以达忠诚时,他们开始渴望得到业外人士的普遍承认,但大学教师自身内部的同行承认无疑是大学教师作为一种新兴职业获得外部承认的前提和基础。
在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形成的过程中,大学教师职业为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提供了维持生活和获得尊严的必要条件,使得近代大学教师确保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收入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促使从业者对大学教师职业的欣然接受,此时大学教师对自身职业的承认与其说是主动地忠诚倒不如说是出于利益考量后的依附。事实上,中国近代大学和大学教师职业成为大学教师从业者的家,大学教师对于本职业的忠诚或者爱在精神上能够产生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另外,大学作为研究高深知识的场所,大学教师对其所从事的高深知识研究会逐渐产生一种职业依赖。这种职业依赖的存在,确保了大学教师从业者群体的稳定性。无论是主动地忠诚还是被动地依附,中国近代大学教师对于本职业的承认都是一种“爱”,即“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源于中国近代大学教师从业者内部职业忠诚或者爱的存在,大学教师才能成为一种职业,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才得以形成。一个职业如果失去了从业者的忠诚,面临的必将是职业的衰落,甚至是最终的分崩离析。
2.不同职业主体间的承认:尊重
近代大学教师自我意识的形成不但需要同行内部间的认同,更取决于不同职业间的互相承认。与近代大学教师职业内部的同行承认相比,来自其他职业的局外人承认方式的提出及其实现,反映了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不同职业间的彼此依赖,同时也体现了近代大学教师主体性的消解以及对不同职业主体间的反思,即“只有当我们反过来认识到必须对他者承担规范义务时,才能把自己理解为权利的承担者。”[3]115其他职业的局外人承认注重的是不同职业主体间彼此身份的认可和肯定,即“竞争者的参与保证了合法性和诚意”[4]33。由此可知,近代大学教师职业地位的提升和职业影响力需要社会上的其他职业的尊重与承认。
然而,不同职业主体间承认有时存在着冲突,任何一种职业试图在社会化分工的职业建制中得到他者的承认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近代大学教师作为一种“职业”亦是如此。导致近代大学教师职业不易被承认的诱因很多,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因素、组织建制的因素,还会有从业标准或认识观念的因素。一旦大学教师职业在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过程中被蔑视,则会成为社会职业分工中的次等职业,有时甚至会因此而面临失去获得大学教师职业独立资格的风险。出于对大学教师职业尊严以及大学教师职业地位的维护,为职业承认而斗争成为近代大学教师试图将大学教师职业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一种选择。然而,获得其他职业从业者的承认绝不是轻易就能实现的,局外人的尊重只会投给职业价值竞争中的胜利者,而且由于局外人承认的不可控性,大学教师职业要想在近代中国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期待那些反对势力自身的逐渐消亡。
虽然近代大学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在产生之初要想获得局外人承认比较困难,但是作为职业承认的一种重要形式,能够获得局外人承认又是近代大学教师成为职业所不可或缺的。事实表明,化解新型职业间冲突的有效渠道就是加强职业彼此间的互动交流和了解。近代大学教师只有通过与其他职业从业者的互动与交往,才能更加激发大学教师内部的归属感和集体感,也才能获得基于彼此平等地位认知基础上的承认和尊重。
3.大学教师职业的社会重视承认:价值
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内部以及其他职业从业者的承认反映的是近代大学教师职业的教育属性,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建制,近代大学教师职业还具有社会属性,而近代大学教师职业的社会属性则需要社会的承认。近代大学教师职业的社会承认以近代大学教师内部的自我承认和其他职业从业者的局外人承认为基础,但不同于情感依附和权利赋予的评判标准,它强调的是近代大学教师职业在整个社会中的价值和贡献。在价值的维度上,不同职业对社会的贡献绝非平等,基于价值原则基础上的社会承认是衡量职业贡献大小的外部标尺。因此,不同的承认形式和不同的承认程度无形中强化了职业地位的差异,即便如此,以重视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承认对于职业地位的“等级”也只能是象征性的暗示。毕竟在理论上,职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等级差异,对于职业平等的追求也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
虽然在社会建制中职业之间没有制度化的“等级性”规定,但实践中在同行承认和局外人承认的基础上,不同职业主体为了能够受到更多重视,获得更大程度的社会承认,以便在社会发展中争取到有利地位,彼此之间依然存在着永恒性的激烈的价值竞争。诚如约翰·齐曼(John Ziman)对“科学”的论述,“由于本质上他们按照同样的标准予以评估,对资助的竞争强化了对科学承认的竞争。”[4]92在争取社会重视和经费资助的过程中,大部分职业会在职业的价值竞争中失败,仅有少数职业最终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重视。暂不论得到社会重视的职业就真的比受到社会蔑视的职业能够拥有多少制度性权力,但他们通过政府部门或社会其他领域所获得的不公平的资源配置和权力赋予着实令其受益良多。社会的重视承认具有高度的象征性,一种职业一旦获得了社会的重视就极有可能走向社会的“中心”,并对社会其他职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和冲突的近代中国,“四民”社会逐渐瓦解,一批新兴职业如雨后春笋般产生,中国近代大学教师顺应 “教育救国”的时代思潮,以近代大学为组织建制依托,凭借社会对从事大学教师工作的人的要求和期待,迅速实现了近代大学教师职业的社会承认。事实表明,中国近代大学教师主动肩负起了教化兴国、开启民智的历史责任。这恰恰是近代大学教师职业获得以价值为原则的社会重视和承认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知识 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中,无论是知识体系还是学科划分,都长时间处于一种混沌状态。中国传统知识以儒家传统经典为中轴,虽有经、史、子、集四部之别,但更多的是对知识使用价值的一种人为区分,而非知识本身逻辑体系基础上的严格有效的学术分类。中国传统知识的划分不是以研究的客体(对象)为标准,而是以研究主体(人)来划分,研究学习的知识范围主要锁定于儒家传统典籍,尤以《四书》《五经》为核心,自然科学知识长期被排斥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之外。特别是在实行科举选官考试制度以后,进一步强化了统治者对教育知识控制的权力,这不仅标志着外部力量对知识人的命运及前途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也意味着知识本身的价值判断也由官方裁决。这一破坏知识自身内在逻辑和价值的行为,将导致知识人忙于对功名的追逐而非对知识,尤其是高深知识本身的探索。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西方学科意义上的“专门之学”,中国学术相对而言更具有“博通”的特点。原因就在于,封建社会中知识是一种奢侈品,无论是居于四民之首的“士”还是德化权威的“师”,都无形中扮演着一种道德圣徒的角色,他们皈依于统治者的德治政策和意识形态下,发挥着连接统治者和普通民众的中介桥梁作用,他们是社会主流思想文化的传递者和传道者。鉴于教师被“圣化”的事实,其除了在伦理道德方面的高标准要求之外,在知识领域也被要求博学多识,他们努力成就自身在知识上的权威地位以达“优入圣域”。诚如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知识人个体而言,在学问上他们竭力追求“会通”,在知识上尽量表现出“渊博”,这也正是前人所谓“一事不知,儒者可耻”的意味所在。然而,在仅限于传统儒家典籍为知识范畴的狭隘认知基础上的“博学会通”,也就必然地导致学人群体在知识结构上的类同和单一。在这种意义上讲,知识结构的单一性更多强调的是社会分工下的知识类别的单一化。所以,近代中国高深知识的资源总量相对来说也就欠缺,知识的种类自然趋于单一和有失偏颇。
而且,近代以来,随着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开始受到挑战,以儒家典籍为知识范畴的读书人在失去儒家制度体系的合法性依据后,开始寻求新的安身之所和谋生之技。他们受西学东渐和新式教育的影响,开始对西学有了普遍的适应性反应,同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弘道和忠君为己任的士人也有了根本区别。特别是西方学科门类的分科性学术和知识体系传入以后,彻底改变了读书人以往的学习内容和知识结构,按知识自身逻辑体系分门别类的学科开始出现。此时,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顺应时势,已经意识到并开始试图打破自身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其实,早在洋务运动早期,西方学术分科观念就已经为士人了解和接受,如郑观应曾云“泰西取士之法有数科,无不先通文理算学,而后听其所好,各专一艺。”[5]29这不仅表明郑氏对西学分科理念的熟识,而且也显示了其对西学“各专一艺”分科立学原则的认同。而后,随着西书翻译以及介绍西学书籍的增多,中国传统读书人开始突破中国固有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和儒学典籍的知识范畴而扩展至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
当然,在新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的确立之初,早期学人的呼吁和宣传固然重要,但外部的制度保证才是根本。所以,从洋务时期的新式学堂到清末民初近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大学的出现,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到分科教学的系列新学制的颁布,无不从制度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保障。自此,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体系开始发生历史性转向——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这种新的“七科”分类及其各专门课程的设置渐渐固化,它们不仅成为中国近代建构起来的新知识系统的分类标准,而且也成为设定大学教员知识边界的标准。[6]161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由此被赋予新的社会角色和身份——知识分子。他们以教书育人为志业,在知识所涉及的领域上不仅兼具旧学,而且广泛接纳新知。他们不需要承担广泛的社会教化和修齐治平的政治责任,也不再是拘泥于儒学知识系统里的“通人”,而是以一己之专长贡献于国家,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各方面“专才”。所以,就近代大学教师个体的知识来说可能更精专,但就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这一“群体”的知识结构而言,已经变得分散和多元,这是近代大学教师作为一种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学术职业在近代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必然结果。
四、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职业技能: 由传统单调到灵活趋新
大学教师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一种专门化职业,它的劳动特点及其职责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从业者要想成为一名称职的大学教师并非易事。中国近代大学教师在产生之初,除了获取职业内外不同形式的承认以及满足自身从业所需的知识结构以外,大学教师的职业技能亦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按照教育心理学的观点,“技能”是指通过练习而巩固下来的迅速、准确、流畅、娴熟地完成某种任务的活动方式。它在总体上分为动作技能和心智(智力)技能两类。[7]300前者主要表现为外显的合乎法则要求的活动方式;后者则是隐形地内化为本体性的认知方式。依据教育心理学关于“技能”的表述,结合大学教师的劳动特点和性质,大学教师职业技能应该是大学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通过练习而巩固下来的迅速、准确、流畅、娴熟地完成大学教学任务的一系列行为及智力活动的总称,它是大学教师为实现一定教育目的、有效组织教学内容、合理控制教学过程所必备的职业素养和方法。
鉴于中国早期近代大学教师的职责主要是以培养人才为主,所以对其职业技能的要求也就主要体现在教学能力、教学态度以及教学方法上。就教学能力而言,早期由传统士人演变而来的近代大学教师多为硕学鸿儒,而归国留学生和教籍人士也多受过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训练,他们在课堂讲授中的语言表达、对知识的解析以及对课堂进程把握都已经具备了不同程度的掌控能力。譬如1916年12月,教育部在视察中国公学大学部时,曾对教师授课情况给出过一份考察报告“教员张廷健讲解尚明,惟少发挥。教员江元亮讲解尚属详明。教员陈传瑚讲文法颇详,教员高孔时讲名词变化,其形恳挚,教员黄旭讲解甚有精神,教员汪郁年讲解少有发挥,教员刘立夫讲解甚晰,惟语气稍嫌急促,教员陈仲沂讲述尚详,教员黄尊三讲解不甚合法,教员费兴仁用英语教授尚畅达,综观该校各科教授,大致尚属认真,讲堂风纪亦甚整齐”。[8]434-435由此可见,虽然早期的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参差不齐,但整体上已能够顺利地完成课堂知识的传授,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是具备相应的教学能力的。
此外,近代大学教师仅有教学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们不仅要能“传”,还应该会“授”。所以,掌握合理有效的施教方法,是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成功完成教学任务、实现人才培养的关键。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大多依托于课堂,以教室为中心,多采用单向的教师讲授(填鸭式)方式进行。在教育目标上,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视能力的培养,学生被视为被动接受灌输的机器。而且中国传统教育强调师道尊严,讲究教师的权威,突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正所谓“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非理性的师生关系必然导致教师权威的绝对化,学生对教师绝对服从,教师把握着整个教学过程的主动权。待到中国近代大学肇始之际,随着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势必要求近代大学教师的教学方法作出相应的变革,如“京师大学堂创办伊始,其教学方法,虽偏重讲演法,但因仕学馆与师范馆学生的年纪多半较大,出身又高,国学根底亦极深厚。因此,在教学方法上特别注重讨论方式,而养成师生之间‘互相讨论,坐而论道’的风气”[9]944。同时,近代大学教师对自身所授课程进度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且对各自所授学科的教学方法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如茅以升 1926 在北洋大学任教时“进行科学研究同时,并精心研究如何改进教授法,启发诱导学生独立思考,深入钻研。如学生提出课程中的问题,老师不能答复,就给学生满分,深受学生欢迎”。[10]136还有叶公超授课时“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挚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11]193-194这种教学方法在保证教师传授基本理论和知识的同时,还启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总之,中西文化冲突下的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职业技能已开始变得灵活多样、整体趋新,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近代大学教师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近代的中国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变革是时代的主旋律。中国近代大学教师应时代社会之变,从最初产生到最终群体形成,一路演绎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无论是近代大学教师群体的构成来源、职业伦理观的形成,还是其自身的知识结构及职业技能的发展,中西文化冲突下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过渡性时代特征构成了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群体的生命维度。事实表明,中国近代大学从无到有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代大学教师群体这一师资力量的迅速崛起和有力支撑,而且中国近代大学教师在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亦发挥了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
[1]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J].二十一世纪,1991,(8):15-25.
[2] Y.C.W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M].Chape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6.
[3]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 [英]约翰·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M].曾国屏,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5] 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上)[M]//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6] 胡金平.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角色困顿——大学教师的社会学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 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M].第2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07.
[8] 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9]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 (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10] 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 [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
[11] 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大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曹 静】
An Analysis o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Modern University Teacher
QI Linga,YAO Yan-junb
(a. Institute of Teacher Education; b.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65,China)
In terms of the group of Chinese modern university teachers, it refers to the scholars or teachers who exist in the field of modern university.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is imbued with the factors of the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With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itional era, namely source of teacher groups constitute the mixture of the new and the old; teachers ethics gradually formed, university teachers’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teachers knowledge structure from single to multiple; teachers’ professional skills from the traditional monotonous flexible new trend.
cultural conflict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modern university teachers group; transitional era characteristics
G645
A
1009-5128(2016)22-0084-06
2016-09-12
齐玲(1990—),女,山东曲阜人,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以大四公费师范生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