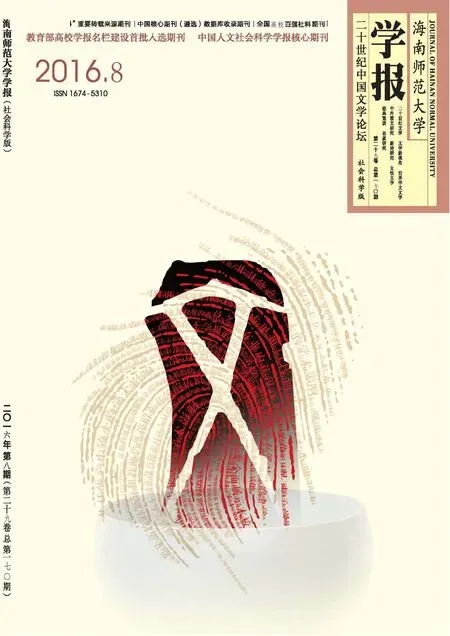以诗修行的先行者
——东荡子和《东荡子的诗》
林馥娜
(《中西诗歌》杂志社, 广东 广州 510630)
以诗修行的先行者
——东荡子和《东荡子的诗》
林馥娜
(《中西诗歌》杂志社, 广东 广州 510630)
因为摒弃了诸多物质的诱惑,诗人得以静下心来倾听万物的声音,从东荡子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自然物象的深切洞察与了解,心灵图境与诗学精神的永恒性,正是一个诗人赖以安心与归宿的土壤。
东荡子;阿斯加;自我挖掘;哲思范式;心灵图境
“朋友离去草地已经很久/他带着他的瓢,去了大海/他要在大海里盗取海水/远方的火焰正把守海水/他带着他的伤/他要在火焰中盗取海水/天暗下来,朋友要一生才能回来”(《朋友》)。①东荡子:《东荡子的诗》,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本文所引此书均出自此版本。东荡子仙行了,朋友们要一生才能与他相见,但同时,他又似乎从未离开,他通过他的诗,一直在朋友圈中来而复往。
一、躬行自明:肉身与心灵的苦修
2004年应东荡子的要求,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诗《黑色》的更正(在某刊刊出的诗与原诗有出入)与评论后,我对批评这个文体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兴趣,因此可以说我走上诗歌批评的道路,是东荡子间接促成的。《黑色》这首诗凝练精悍,所以即使编排上出现一字之差,也会有害诗意,由此可见东荡子在诗歌文本上的严谨与求精。
自东荡子到增城定居后,我与他见面的机会少了,但只要有机会在诗歌活动中相见,几个较常聚的老朋友和诗会上随机偶遇的一些诗友都会聚在他的房间,一起聊天,常常彻夜谈诗论事,有时甚至争论得不可开交。每次说话最多的都是东荡子,他那洪亮的声音伴随着香烟烟柱在空气中荡漾、发散。每次聚会看到他只顾抽烟、喝酒、聊天,我总忍不住要叫他先吃点东西。他却总说:“没关系的,食物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只要一点点就足够。你看我不都一直是这样过来的。”
2004年圣诞节前夕,受汕尾杜青、冷梅之邀,我和东荡子、世宾、老刀,还有开车的姐姐琳娜,一行五人出发去红海湾,一路上东荡子滔滔不绝,像是一个诗歌布道者,一直说着关于诗的话题。乃至到了汕尾,当地的诗友围着他,向他请教诗歌问题,他依然一一解说,仿佛是一台强劲的永动机,不知疲倦。姐姐琳娜作为局外人,对他的印象是有点愤青,有点犟。我想,诗人多少都有点愤世吧。诗人是最敏感的群体,往往具有济世的情怀,对于所洞察到的各种荒谬与残酷,愤怒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眼里掺不进沙子,诗歌便成为诗人含沙成珠的丰盈产物:
一间茅屋要几千年才能变成瓦房/建筑从未中止,但拖延也从未中止/误工和偷工减料、烧毁、坍塌也从未中止/从未中止的还有兵荒马乱和勾心斗角……杀戮将动物的毛皮紧绷在我们的身上/将它们的声带装进我们的喉咙……一颗心却在一夜之间就碎成了粉末/一颗心越来越碎,越来越碎成更多的粉末/它不能回答,它在忙于碎,忙于流血*东荡子:《东荡子的诗》,第48页。(《上帝从不光顾我们的晚餐》)。
当自然法则与天理被潜规则败坏与摧毁,无力抓住某些特权阶层挥舞的刀子——“往来于各个节气/然而在低处,从未见你把刀的爪子抓住”*东荡子:《东荡子的诗》,第12页。(《何等的法则》),当“天空已裂缝”,处于低处的众生只能哀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时,“坍塌便不只是掩没大地的声音”,而是整个人文世界的坍塌。面对“坍塌的世界”,若要在写作上达到自由,在心灵上获得平静,则取决于对这种内心与现实的冲突怎样去进行平衡。东荡子的处理方式是修行,他以苦行僧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不断地做减法——摄取最低限度的生活所需,以最精炼的表达进行诗写,并在精神上驱除侵占心灵旷野的各种黑暗,身体力行,躬行自明。他说:“人和万事万物都是泥巴捏的,要想不再被捏来捏去,只有砍掉或远离那些伸来的手。”*东荡子:《不落下一粒尘埃》,《诗歌与人》专刊2009年4月,第125页。我在为东荡子所作的挽联中有“东士仙行”之语,正是特指他具有“士”的那种修身律己的品格。
因为摒弃了诸多物质的诱惑,诗人得以静下心来倾听万物的声音,从东荡子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自然物象的深切洞察与了解:
在空旷之地,或无人迹的角落/土地和植物悄悄腐熟/你转过身,蘑菇冒出来了/无声无息。却全然不像水泡/当着你的面也会冒出/声响果断,短促而悠远/有时还连续冒出一串/在同一个地方,接着便消失。*东荡子:《东荡子的诗》,第16页。(《水泡》)
这种与自然界的通感与共鸣,把诗人带入一种无欲无求、无功利得失的虚静之境:
那一刻来临,时间在我的周围静止/我的心回到了它自己的祖国,它无限宽阔/思绪由此远去,自由而宁静/留连所有的事物,但并不思想它们/那一刻我不会像往常,处在喧闹的人群/去深入他们和他们的事物中探求/我已失去重量,轻松而任意飞翔/在有些事物上,我会停下来/仿佛风从上面拂过,有时又会悄悄返回//那一刻来临,我已经把我的肉体放在了一边/没有痛、没有感受、世界通体透明/我随意进去,又随意出来,像从未来过/我的朋友、我的亲人、陌生人,甚至伤害我/和被我伤害的人,以及动物和植物,所有奔走/繁忙和吵闹,在我前头闪过,从不打扰/我也不觉得肉体的颤动和心跳。那一刻/所有的一切都孤立,相互连接却并不纠错/时间已忘记了它手中的绳子/鱼儿在永远的水中/我在空中*东荡子:《东荡子的诗》,第77页。(《时间忘记了他手中的绳子》)
这时的诗人,已获得了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极致——领悟了自然规律之道,并从此进入生命的广阔境界——对荣辱生死处之淡然。这时的“我”,已无需结绳为记,在时间的节点上设立为之奔忙的目标。
东荡子与聂小雨结婚后,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来家里看小雨啊”。在一次《人民文学》组织作家到增城采风时,我和张鸿就来到了他家——九雨楼。一进家门,最打眼的是一长排的简易书架和长长的书桌,地板配搭鹅卵石图案的地砖,给人一种简朴和谐的气息。我不禁说,好!很简洁。他满脸得意地说“这都是我自己做的”。作为木匠的儿子,他有这个能力。这时的他,有一种家常的温暖与近乎天真的笑脸。小雨则在旁准备煮水待客,家有娇妻,任是多犟硬的男人,也有温存的一面。我们也发觉,自从有了小雨,东荡子的性格也悄悄发生了转变,不再那么锋芒毕露。因小雨本身也是作家,这对于两者的创作,无疑也是相得益彰的,故他们夫妻双双摘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还记得当时得知获奖消息时是在顺德,我们正一起参加第11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活动,大家纷纷祝贺东荡子时,他还不忘让我致电小雨,告诉她这个消息。心安则性平,正是家给他带来俗世安妥的栖居。
曾经与世宾讨论过东荡子的诗,说起他如果阅读更多的书,视野的宽阔和丰富的心灵体验将会有助他的诗歌达到更加辉煌的境界,也曾和东荡子当面谈论过。但到了后来,也就是“阿斯加”出现在东荡子的诗歌世界那个时段,世宾说,东荡子就这样走下去,继续冥想,继续走向内心,一条道走到底就行了,这路适合他。这似乎不无道理,随着年岁的增长,并不断在写作中反省自我与他者的共同弱点中,东荡子之前外露的锐气已逐渐内化为作品的力量,并发明了“阿斯加”这个诗歌符号,这个既是自我,也是他者的“人”,成为东荡子自由挥舞诗学之剑的载体,也使他的写作得到了更加游刃有余的挥洒。他在向内自我挖掘式的思考中,不少诗歌都附着了自我设问与自我解答的哲思范式,使其诗作具有一种答辩式的自足性。比如《上帝从不光顾我们的晚餐》、《我永不知我会是独自一人》、《信徒》、《何等的法则》等,他的诗也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
二、修辞的力量与精神修炼的共同发力
东荡子的诗歌之所以受人喜爱,当与他赋予作品的思想性(诗学精神)与力量感有关。他与世宾、黄礼孩一同提出的“完整性写作”理论是他为自己的写作树立的坐标。
理论并不是用来指导我们每一首诗的写作,而是我们为自己所归纳和认同的审美方法树立一个信仰般的思想标尺,这把标尺用于防止自己滑向美的反面,同时推动自己无限接近于心中审美理性的标高。
东荡子的诗歌有一种占领感,他以演讲式的、简短有力的诗篇开门直入地抓住了读者。修辞的张力就像是一张拉满的弓,而一旦修辞上的力量与精神指向上的某一主题互相触发,则精神主题的利箭便脱弓射向读者的靶心。像他的《黑色》、《异类》、《让他们去天堂修理栅栏》、《宣读你内心那最后一页》等诗作,都具有直抵人心的、紧崩的力量感。*林馥娜:《旷野淘馥——诗论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年,第59-60页。
我曾在评论专著中解读过东荡子《黑色》这首诗:
我从未遇见过神秘的事物/我从未遇见奇异的光照耀我/或在我身上发出我从未遇见过神/我从未因此而忧伤//可能我是一片真正的黑暗/神也恐惧从不看我/凝成黑色的一团在我和光明之间/神在奔跑模糊一片*东荡子:《东荡子的诗》,第60页。(《黑色》)
从未见过神是大众的体验,神在大众的心目中是高高在上的,谁都没有见过神,而东荡子却用“遇”这个字,把神拉到了与人平等的位置上,他让我们领会到,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遇见神,他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心中。人有时就在神性和人性,甚至是鬼性中穿梭!那既然神可以“遇”,为什么我又没见过神秘事物、没在我身上发出光呢?下半阙的诗告诉了我们——如果“我”心存黑暗,则“神”也“凝成黑色的一团”,我们只有规避人性的黑暗面,奔向光明,才可能与神重合,形成神与我一体的“模糊一片”,这时,我们正走在通向光明的路上,呼应了上半阙末句的“我从未因此而忧伤”,因为我们可以用诗学精神修身,走向神性的超我、能够发出智慧光芒的我。诗学精神是神性的、充满美与爱的精神,这里的神性并非指神话故事中所指的那类“神”,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讲,神其实就是人类心目中用以自律、宽慰、提升灵魂的个人宗教。*林馥娜:《旷野淘馥——诗论卷》,第4-5页。
人在人性、神性乃至鬼性(恶念)中穿梭,诗人需要建构的,正是去除鬼性,拓展人性与神性,让人类的行为(包括写作)及灵魂在不断批判现实、规避黑暗*林馥娜:《旷野淘馥——诗论卷》,第59-60页。(“这里黑暗除了政治的,还必须揽括人类事务的所有领域,包括:人类心理内部的怯懦、无可奈何、人云亦云及一切精神性病症;外部的疾病、战争、灾难、死亡”*世宾:《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诗歌与人》2005年第9期,第19页。)中无限靠近光明和谐的前景。
而东荡子的《世界上只有一个》让我们体会到每个诗人都是诗学精神的追求者,是驱散自身的黑暗与世界黑暗的修行者。所有的诗人都是诗学之塔的一块砖,在修炼自己的同时修炼出诗学精神的高塔,修炼出顶天立地的“大诗人”。在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时代,一个重拾往昔珍贵事物的异类是多么孤单——“我孤身一人,只愿形影相随/叫我异类吧/今天我会走到这田地/并把你们遗弃的,重又拾起”*东荡子:《东荡子的诗》,第27页。(《异类》)——又是多么可贵!就算被世俗的阴影拖下水,“可他仍然冥顽,不在落水中进取/不聚敛岸边的财富”*东荡子:《东荡子的诗》,第19页。(《人为何物》)。这里的“冥顽”,正是一种精神的坚守与人性的修炼。*林馥娜:《旷野淘馥——诗论卷》,第59-60页。
三、心灵图境的永恒性
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诗人在白昼时必须在代表世俗生活的“长着金属的面庞”的“一枚硬币前停下”,但也可以在黑夜里继续前行,不断“创造黑夜,鼓足飞翔的勇气/从此写下轻于鸿毛的诗篇”*东荡子:《东荡子的诗》,第52页。(《在一枚硬币前停下》),以与世人看不见的上帝相见。“上帝一直在我左右/他如唤我,好像他也在躲避/从不跟我讨论我错误的一生/也不愿把我的灵魂放在合适的地方//当我最后离去/我只在秋天的怀里待过一个白昼/上帝却在黑夜的林中,我看不见”*东荡子:《东荡子的诗》,第61页。(《上帝在黑夜的林中》),并通过与黑夜中的上帝——也就是和“超我”(诗性的我)相见——达到驱除“黑暗”,到达光明的境界;使放养的心灵一步步走向更宽广的牧场,从而构筑出自由的心灵图境。
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真的能带给我们幸福吗?当人们由世俗标准裹挟着,一路狂奔在追名逐利的狭路上,而从不停下来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真正合适自己的道路时;当我们忙得没有时间来珍惜身边的所有时;当我们的精神生活一片荒芜而如行尸走肉时;这种同一模式的幸福,无疑是一副副枷锁和镣铐,这种盲目的、想得到和别人一样的成功和幸福、无休止的追逐和轮回,不能不说是人类永劫回归的怪圈。“谁在指使我们/创造光辉的勋章要我们佩戴/我们却往往在同一炉膛打出枷锁和镣铐……也没有人,不愿意不追求幸福/那好,还是让我们/来把幸福的含义全部揭穿/它来自人类/它是人类一场永劫的惩罚”*东荡子:《东荡子的诗》,第110页。(《生存》)。
唯其对人生意义持续的追问和透彻的参悟,才让诗人卸下了困住心灵的枷锁,获得了精神的自由——看淡世事,看轻生死。“他已不再谈论艰辛,就像身子随便挪一挪/把在沙漠上的煎熬,视为手边的劳动”*东荡子:《东荡子的诗》,第38页。(《别怪他不再眷恋》)。“一顶帽子无论怎样变化,即使如夜莺把夜统领/都只是戴在头顶。是的,他就这么看”*东荡子:《东荡子的诗》,第39页。(《他就这么看》)。是的,不管在世俗中拥有多么荣耀的头衔,那都只是一顶暂时戴在头上的帽子,一切终会隐入大地的恒久寂穆中。只有触及灵魂的吟唱依然会在一代代人的共振与时光的淘洗中发出独立的光芒。“我快要死了,一边死我一边说话/有一个东西我仍然深信/它从不围绕任何星体转来转去/倘若它一心发光/死后我又如何怀疑/一个失去声带的人会停止歌唱”*东荡子:《东荡子的诗》,第47页。(《倘若它一心发光》)。我们无法掌握生命的存亡与年轮的长短,但“值得我回味的或许是我已发出自己的声响/像闪电,虽不复现”*东荡子:《东荡子的诗》,第37页。(《不要让这门手艺失传》),闪电所照亮的人生,虽然仍不可操控,但只要诗艺不失传,诗歌精神的光芒依然会照亮更多人行进中的前路。
把一个物件放到一个地方/它的位置在那里/但它的思想不一定在那里/任何永恒的东西都不会在心灵之外/我们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们说:鸟儿,飞/鸟儿就飞走了/鸟儿真的就飞走了吗/我们把碑埋在墓地——不朽啊/我们所看到的人/无非是一个个墓碑的影子/他们孤独地离去。花束留下了/花束又在那里死去/我们再拿什么献在花的墓前/甚至一万年过去/我们仍有许多东西不解/光荣和羞辱/我们应当把它们放在哪里/啊心灵,永恒的尘土/我又一天接近了你/即便你和他们一样/从不把我放在心上*东荡子:《东荡子的诗》,第88页。(《尘土》)
不管是先行者还是后来者,一切终究敌不过时间的磨盘,万物均归于尘土,而又永生于永恒的尘土——心灵图境。
我无知而生存/我盲目地有知而生存得如此热烈/为虚无写下颂辞,为真实而斗争/即使痛苦也得用半生来眷恋……我永不知到达山峰还能继续上升/我永不知那山峰为什么使我前往/我永不知我会疲倦而去像那巨石滚下/我永不知我会是独自一人*东荡子:《东荡子的诗》,第91页。(《我永不知我会是独自一人》)
东荡子独自一人疲倦而去了,唯有心灵的吟唱永远伴随着他,并回旋在亲友中,在更多人群中传诵。反之,心灵图境与诗学精神的永恒性,正是一个诗人赖以安心与归宿的土壤。朋友说,东荡子是天上派来的,现在回去了。是的,东荡子就是诗神派来传道的,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别怪他不再眷恋,他已收获,仿若钻石沉眠”。
(责任编辑:王学振)
Dong Dangzi andDongDangzi’sPoems
LIN Fu-na
(PeriodicalOfficeofChineseandWesternVerse,Guangzhou510510,China)
Thanks to his abandonment of various material temptations, the poet can calm down to give ear to the voice of all things. In Dong Dangzi’s poems can be discerned his deep insight and understanding of natural objects. In short, the mind map and the eternity of the poetic spirit is the very land on and to which the poet can feel at ease and return.
Dong Dangzi; Asgard; self-exploration; philosophical paradigm; the mind map
2016-05-28
林馥娜(1970-),女,广东揭阳人,《中西诗歌》杂志社编辑,主要从事诗歌创作与研究。
I227
A
1674-5310(2016)-08-006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