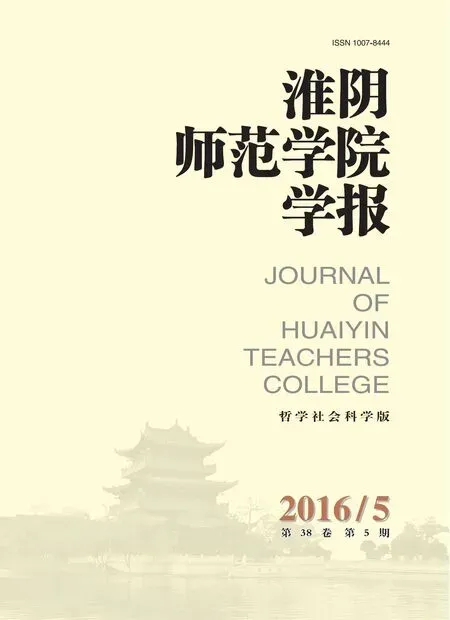“如何认识科学”(二十一):科学与世界观——大卫·凯里对克里斯多夫·诺里斯和玛丽·米奇利的访谈
克里斯多夫·诺里斯, 玛丽·米奇利, 大卫·凯里
【科学哲学·如何认识科学】
“如何认识科学”(二十一):科学与世界观
——大卫·凯里对克里斯多夫·诺里斯和玛丽·米奇利的访谈
克里斯多夫·诺里斯, 玛丽·米奇利, 大卫·凯里
诺里斯认为,虽然世界确因人类的干预受到影响,但无论如何,这个世界在非常大的程度上都是坚实地独立于我们对世界所知道或声称所知道的存在;那些认识上相对主义、怀疑的后现代主义的反实在论思想,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道德上是极具腐蚀性的;实在论绝对必要的根基是这样的观念:使我们的陈述、假说和理由正确或错误的东西是事物立于实在中的方式。米奇利认为,我们的全部思想不得不处于一种富于想象和充满情感的状态,我们就在这样的状态中理解事物;科学只要试图表达,就带有这种叙事手法和情感色彩;科学家即使只承认赤裸裸的事实,依然是在讲述一个自我演绎的故事,他们已失去对自己思想局限性的良好意识,他们给予的是他们自己的道德和政治偏见;科学将永远不可能强大到不再需要神奇。所以,科学家在选择他们想要告诉的故事时,要更有意识和更为小心;只有首先改变我们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我们自己是什么的思想,我们才能改变现实。
实在论;相对主义;比喻;局限性;表达方式
肯尼迪:我是保罗·肯尼迪,这是《思想》的“如何认识科学”节目。在作家萨缪尔·约翰森(Samuel Johnson)生活的18世纪,他与詹姆斯·博斯维尔(James Boswell) 之间有一场关于他们同时代的主教贝克莱哲学的对话。按约翰森和博斯维尔的理解,贝克莱的哲学持有这样的观点,我们实际拥有的关于世界的所有知识都是我们的观念。博斯维尔对约翰森评价说,这种观点虽然是错误的,却不可能加以反驳。博斯维尔还说,“我不可能忘记,约翰森敏捷的回答”。他用他的脚非常有力地踹向一块大石头,在被反弹回来时,他喊道:“我这样就反驳了它。”今晚我们的第一位客人是哲学家克里斯多夫·诺里斯,他持有的观点与约翰森博士相同。他相信最好的科学哲学是稳健的实在论。
诺里斯:有一个客观的和存在着的世界,其相当大的部分完全脱离于我们有关它的知识或对它的干预而存在。世界确实会因人类的干预而被影响;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世界在非常大的程度上,都坚实地独立于我们对它的理解或声称对它的理解而存在。
凯里:今天,在《思想》节目中,诺里斯将讲述为什么他认为实在论会导致最好的哲学和最好的政治学。在该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向你介绍另一位英国哲学家,玛丽·米奇利,她将论证:科学总是用确立某种导向的新闻报道镜头的方式来看世界。
米奇利:我们所有的思想都必然有想象的和情感的成分,并且其简单的要求是,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理解世界本来的样子。这必须使用比喻的说法。所有科学都使用比喻说法;并且,这必定有一些情感背景,一些……导致其产生的指导。
凯里:在“如何认识科学”系列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讨论有关科学知识的两种不同的观点。我是《思想》节目的制作人大卫·凯里。
凯里:克里斯托夫·诺里斯并不一直是一位科学哲学家。他是作为一个对法国后现代主义特别感兴趣的文艺理论家而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不过,在那时,他不喜欢在他所研究的一些人的作品中看到的对现实的一种逃避。一个特别令他讨厌的人是已故的鲍德里亚,后者声称,现代传媒已让世界变成他所称为的“一个假象”,在其中,实在不再可能从它的许多假象中被清晰地区分出来。结果,诺里斯从文学转到哲学,并且开始写文章保护哲学的实在论。现在,他是威尔士卡迪夫大学的哲学教授。2006年的秋天,我在卡迪夫大学他的办公室采访了他,他从他的观点是如何转变的开始他的谈话。
诺里斯:一些怀疑主义的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以后现代主义的名义所论述的一些事情,让我越来越生气。这一状况达到了一个……是的,不是一个危机点,那有点夸张;但它在如下的情况中达到紧急关头:在鲍德里亚臭名昭著的关于第一次海湾战争的两篇文章中,其中一篇的题目是“海湾战争将不会发生”,在其中他说,海湾战争将是一个如此超现实、被吞没了的伪实在,那将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它将不可能告之来自实在的形象,或者来自其背后的假定的真理的形象,我们根本不能谈论一场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谈论一次战争仅仅是进行宣传。所以,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不应该认真地做这样的事情。关于这事,我们应该走向反实在论的观点。在我看来,这近乎就是非常糟糕的观点了。
但是,后来,就在战争之后,他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也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不可能知道——无论我们是否观看制造商增加了的影像资料或战争期间事件的及时真实概况报道。这两种如此既不负责任又得过且过的宣称,实实在在地打击了我,促使我开始写一篇论辩性的文章,并把它扩展为一本书。该书用“不加批判的理论: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和海湾战争”(Uncritical Theory:Post-Modernism,Intellectuals and the Gulf War)书名出版。从这时开始,我就决定,我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从事教学了。于是,在某个阶段,我发展了我在科学史方面的兴趣,用科学哲学的方式提出问题,把我所想的用于对实在论的辩护。因此,这是我对过去较早阶段所做的一些事情的真正的反抗,并且我想,这也帮助我形成一种观念:它们不仅仅在哲学上被弄糊涂了并依然在糊涂着,而且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也是相当有害的。
凯里:你是否允许[我提]一个很天真的问题,什么是实在论?
诺里斯:实在论就是这样的基本信念:有一个客观的和存在着的世界,其相当大的部分是完全脱离于我们关于它的知识或我们对它的干预而存在的。它有确定的客体;这些客体依次拥有性能、结构和位置,以及因果属性、能量,等等,确实能因人类的干预而被影响,并且有时能从粒子加速器、超铀元素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中导出。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都坚实地独立于我们对它的理解或声称对它的理解而存在。
凯里:按诺里斯自己的说法,他被实在论所吸引导致他进入科学哲学领域。在这一领域,他遭遇了比其他人更具影响力的人物托马斯·库恩。库恩于1962年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该书在许多方面,为后来对自然科学的历史和哲学探索提供了一些术语。库恩声称,科学知识是在他称为的“范式”中被组织的,范式是协调各个个体知识要素的主导结构,并随时间而改变。16世纪尼古拉·哥白尼从地球中心说转向日心说的天文学,是范式转换的经典案例;但是,库恩也在牛顿的物理学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之间进行了对比,在牛顿物理学中,空间和时间是绝对的,而在爱因斯坦物理学中,空间和时间却是相对的。库恩说,范式是不可通约的。它们由不同的标尺所衡量。不同的范式挑选出不同的客体并用不同的术语描述它们。换句话说,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识,是相对于我们使用的范式而言的。这对于诺里斯来说,几乎相当于说:我们关于什么存在的观点——用哲学的术语说就是“本体论”——完全是由我们的知识系统、我们的认识论所形塑的。
诺里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第一版中的一些陈述认为,他是一个相当强的相对主义者,不仅是一个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本体论的相对主义者。有一个著名的关于世界改变的句子(作为科学的改变),它可以恰当地翻译为:事物的外部特征因科学家生活于其中的一个主要范式的前后改变而改变。但是,该书突然走红、造成相当的狂热、变得如此的流行和富有影响,原因是人们对它过强的解读。在第二版的《后记》中,库恩相当低调地处理它,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他对第一版的反响深感震惊,并且他说: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指字面意义上的世界改变;我的意思说,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觉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头脑里,并且不同的知觉能改变事物的外貌。正如他所说的,你可以持有不变的感官数据,但我们对通过科学观察所显示给我们那些感官数据的知觉,将会根据我们的理论或我们的先入之见而改变。所以,在认识论的相对主义与本体论的相对主义之间,有一个相当微妙的界限。
凯里: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刚才在这里再一次把它翻译成日常语言——就是用我们知道它的方式制造一个我们完全知道的关于模型、比喻和机械的产品。按诺里斯的评价,它与本体论相对主义之间,仅仅有一个相当细小的差别,因为,如果我们完全被我们的范式所限制,那么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至少在实践上就相当于说我们认为它是的样子。无论托马斯·库恩的观点最终是什么,诺里斯决定采用库恩第一版的这一强观点——科学中没有积累的进步,只有范式之间的更替。诺里斯选取航空业中从螺旋桨动力飞机发展到喷气动力飞机的变迁,作为验证范式转换的一个例子。
诺里斯:这是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有一些关于它的亲身实践知识,因为我有多年在一种竞技的状态上驾驶模型飞机的经历。所以,我选择查看空气动力学及其围绕它的各种技术的发展为例子,特别是机械技术,如被称为“涡轮喷气飞机革命”的技术。并且它有非常丰富和详细的文献资料。那是相当令人吃惊的文献——相对于日趋高深和晦涩难懂的抽象哲学层面上的科学哲学文献,我认为使用它在许多方面会更加有趣。技术哲学的书时常由退休的工程师来写,他们自身处于一种退休状态:他们坐下来去写一本书。并且取像“机械师所知道的和他们是如何知道”之类的文字作为书名,像琼斯·霍普金斯的系列丛书的书名一样令人惊奇。丛书中有一本非常好的书叫“涡轮喷气飞机革命”(The Turbojet Revolution),在这本书的基础上,你可以为科学进步给出一个非常棒的、详细的历史和哲学说明——科学被发现的方式、理论有时先于实践起作用的方式;但就空气动力学而言,更为常见的是,实践先于理论而起作用。在人们有了如何运用空气动力学规律的观念之前,他们已获得了如何飞行的观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当然,一个反实在论者,或者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可能会说,这仅仅是一个特殊的、有益的驾驶技术实践的例子,它产生于一定的文化和经济的利益,科学可能拥有不同的方法并发现相当不同的事物。但这也是一组发现,并且你可以展示其中的进步和连续的样式。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路径,可以用来回答库恩的不可通约性难题,以及从当前观点看在科学史中先前时期某些方面的重建难题。我认为,当你查看空气动力学和航空工程学史的一个实例时,范式之间突然中断的思想,就会很快失败。
凯里:库恩声称,范式之间有不可通约性——在一个范式中所谈论的不能与在另一个范式中所谈论的进行比较。这是库恩在其后期加以修正和妥协的强版本。对此,空气动力学的历史会说些什么?
诺里斯:这说明有时会有相当大的突破;但与此同时,这些突破与先前的发展一起在持续发展。在我前面提到的、爱德华·坎斯坦(Edward Constant)的《涡轮喷气飞机革命》一书里,有一个非常有用的措辞,他说,改变主要是通过他所说的“推定的反常”而发生的。你所获得的是已有技术的一个连续的发展,比如,像活塞动力飞机。你得到动力非常强劲的发动机、加速非常高效的发动机。在螺旋桨技术上你获得了发展。螺旋桨事实上不是一个适当的词,它应该被称为“空气螺旋桨”(air screw)。螺旋桨是一种推进器装置。他们不叫它为“空气螺旋桨”的原因是,在战争期间他们会通话或说,派遣另外一个“air screw”,代表存在一个并将获得一个空中编队。所以,他们开始就叫它们为螺旋桨。当然,这是一个趣闻。关键点是,你可以只发展活塞发动机和空气螺旋推进器到一个确定的点上,因为当螺旋桨旋转快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叫“螺旋桨顶端气泡”的现象。你在螺旋桨顶端周围获得许多涡流。飞机穿过声障而快速飞行。你获得了所有类型的湍流模式。
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认识到:可以使空中的飞行器更为快速和更加流线型,可以使发动机更为强劲;但是,已有的螺旋桨技术阻止飞机飞行得更快。这就是他所称为的“推定的反常”。还有一些事情是从一些另外的可能和可以想象的进步阶段中获得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突出地展示科学确实是进步的例子。科学通过适应而开始,通过从其他技术和科学分支中预感到和激发出来的东西而确实在进步。但是,它不是库恩所主张的完全不连续过程中的进步。无论如何,在库恩早期的、对非连续型进步强有力的说明的意义上,你根本无法从事科学史工作。关于我们是如何获得从托勒密到哥白尼和伽利略的进步,或者从前达尔文到后达尔文的生物学的进步,或者从前拉瓦锡到后拉瓦锡的化学和物理学的进步,你不可能给出任何一种理性说明。所以,我认为,关于库恩的强理论,有一些事情基本上是难以置信的。
凯里:你刚才提到的例子也是他的例子。
诺里斯:是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处理得很好。你知道,库恩谈了不连续性和从我们现在持有的观点去看完全重建一个先前范式的不可能性;但是,他做了,用相当大的确信和很健谈的力量做了。就是说,当他比较它们时,他获得了能站得住脚的一些理由。并且,假设这个其他范式完全不同于你自己的范式,关于在这个其他范式中发生了什么,你一定能通过这些表征给予读者或者至少为你自己获得一个好的观点。所以,你不可能在不损害你自己实例的情况下,在范式之间去解释任何确信的、关于不可翻译性或不连续性的实例。
凯里:诺里斯说,空气动力学提供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去反驳范式不能交流的观点。进步可能有不稳定性,但连续性对他来说似乎是相当明显的。他决定举一个更为困难的威胁实在论的例子:现代科学中的量子力学。工作于20世纪最初20年的物理学家,取得一系列奇怪的发现,其中之一是,根据光被观察的方式,它的性质似乎会改变;在一种测量方式中它显示像粒子,而在另一种测量方式中像波。诺里斯用一个对波/粒二象性的重要证明的描述,开始他关于挑战实在论的讨论。
诺里斯: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它从一个思想实验开始而后逐步被引导做出。你可以在现在的任何一所中学实验室里做这个实验。它涉及展示这样的光线,当光线通过两个缝隙射到感光屏上时,它可以凭借独特的光子束——正在通过缝隙并被检测器上滴答声所记录的——光单元或光包而被观测到。但与此同时,即使光线以一个相当低的发射频率通过,它慢到能让你观察到单个的嘀嗒。这样最终就建立了一个波模式,一个在荧屏上的干涉模式。所以,它是粒子,但它的行为像波。在一种意义上,粒子正在通过两个缝隙。按照传统的解释,这似乎完全颠覆了适用于普通人的、貌似真实的、常识形而上学的一类看法——奥斯汀(Austin)称之为“中等大小的干货(纺织物)”(medium-sized dry goods)。
凯里:“中等大小的干货(纺织物)”是哲学家J.L.奥斯丁对我们每天所感知世界的客体——事物在我们人类尺度上的存在——在常识意义上的描述。量子力学似乎在亚原子的尺度上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事物不仅在同一时间内可能有不相容的性质,而且它们可能看起来似乎同时在两个地方。
诺里斯:粒子可以被捆绑在一起然后在分离的方向上各自分离和离开,还能在任何空间之类的距离上相互联系或相互作用,现在这完全可以建立起来。所以,如果你对其中的一个进行测量,这将同时损害对另一个的测量。这是同时的,这意味着它比光还快,这显然违背狭义相对论的一个核心原则。根据一些著名量子物理学家、特别是天体物理学家的看法,这本身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回到过去。所以,如果你把射电望远镜指向所显现的某个我不知道的超新星或者一些遥远的、几百万光年之外天空中的物体,那么,依靠装在你望远镜上的测量仪,你会发现事件要么发生要么不发生。即使波包(the wave packet)的塌陷只能在观察者实际测量时发生,情况也是这样。直到那时,被观察的现象也是不确定的。
凯里:波包的塌陷?
诺里斯:是的,包既是一种波也是一种粒子,要看你采用一个种什么样的测量。如果你在它的路径上放一台粒子测量仪,那么它将作为一种粒子的一段历程被记录;如果你在它的路径上放一个台示波器或波形记录仪,它将以一种波形出现。结果将依赖于测量工具——源自于传统量子物理学家的观察者的行为破坏了观察结果的启示,现在转变为破坏了事物被观察的性质。
凯里:观察者的行为破坏了观察结果,转变为观察者的行为损害了事物被观察的性质这一结果,诺里斯称它为“量子物理学的传统解释”。但是,这并未被所有的物理学家所接受。爱因斯坦不愿意放弃“一个世界的存在独立于我们的观察”的观点。而一些知名的量子物理学家,如薛定谔也持同样的观点。事实上,正如诺里斯所陈述的,薛定谔发展了一个思想实验来展示相信“除非他们被观察到否则事件没有确定的特征”的荒谬言论。
诺里斯:有一只猫被关在一个盒子里。在盒子里,连同猫一起,有一块易分裂的物质,它有50%的可能性要么放射一个粒子要么不放出一个粒子,粒子将打破一个小玻璃瓶,而小玻璃瓶要么释放出要么不释放出一些有毒的蒸汽。于是,无论猫是否死于中毒,都将依赖于这一纯粹可能性事件是否发生。根据传统理论的看法,它不可能既发生又不发生,除非它被观察到,因为波包将不可能被减少或塌陷,就是说,猫处于一个生和死的重合状态,或者你处于既不能活也不能死的状态,直到盒子被打开一个观察者向里面瞄了一眼。有人也指出,观察者也必须处于二者之间的量子重合状态——观察它可能活着或观察它可能死了的可能性,直到被一个第二个观察者所观察到,如此等等。所以,事实上,薛定谔试图把它看做一种完全归谬法的想法,被许多流行评论者作为一个是其所是情况的证明而接受。他们说,多么奇怪,那猫在那盒子里既活又不活。想想看,它不可思议吗?
部分规范“规定过于原则,往往只是一个概念或者一个具体要求,通常是禁止性要求”[2]14,一方面过于抽象、笼统的规定,欠缺具体的权利义务分配模式;另一方面,仅仅禁止性要求缺乏相应法律责任的设定,而难以对管理对象形成有效处置。例如:《网络安全法》第四十条规定了用户信息保密义务,但是在规范下文并未有直接对应的法律责任设定。缺乏“法律后果“的规范,大幅度降低义务人违法成本,这不但难以形成对公众有效引导,而且容易使规范变得不具可行性。
凯里:薛定谔的猫的故事作为归谬法而起作用,因为猫在奥斯汀“中等大小的干货”的规模上存在,在这样的规模上,事物要么活着要么死去,不可能同时是二者。但是,在亚原子层面上的事物可能在被称为“重合”的状态中存在,无论是否荒谬,它确实显现了。他们可能既是波也是粒子,直到一个测量决定它们的呈现方式。这导致了被称为“哥本哈根解释”的出现,哥本哈根的尼尔斯·波尔和维尔纳·海森堡给出了最初的构想。这就是克里斯多夫的“诺里斯释义”。
诺里斯:这就是说,我们不能给量子现象贴上任何本体论意义上的标签。我们不得不依附于测量——预测的数据、经验的结果、观察——并以实用主义的方式运用它们。对于所有以实用为目的而言,真理就是如何进行工作。我们不需要走得更远。我们不需要冒任何对关于实在的基础成分进行假设或量子现象的本体论假设这样的风险,因为,至少对我们来说,他们就是化约的局外人(bong)阻止理性的解释。所以,这是一种极端的实验主义。你知道,只要结果是正确的,只要技术运用实现了,那么,我们的头脑就不会被现象背后的实在所困惑。这就是天主教会向伽利略所劝说的:看,不要坚持你的观点;我们不会在火刑柱上烧死你,只要你说这仅仅是制造结论的一种方式。不要说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只要说,你知道这只是解释观察和测量的一种方式,还有其他方式。所以,这是实验主义。今天,它被称为“建构经验主义”。
凯里:诺里斯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他持有的观点在他2000年出版的一本叫“量子论与逃离实在论”的书里,他支持物理学家大卫·波姆的观点。波姆死于1992年。波姆在麦卡锡时代因其政治观点被驱逐出美国之后,曾经是爱因斯坦的朋友及其对话者。像爱因斯坦一样,他不能“咽下”哥本哈根的解释。他提出一种可选择的实在论,主张“在事物被观察之前似乎是不确定的”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描述从某种角度看是不完备的。诺里斯在他的书中吸收的正是这一观点。
诺里斯:在该书中,我试图证明波姆实在论的解释观点的正确性。就是说,所有量子力学的困惑——波/粒二象性、量子重合、观察者对观察结果的影响,等等——应该通过人类的无知——技术的局限和我们知识上的局限——来解释。你不应该跨区域地把它们转移到本体论的领域,并认为在最本质的层面上,它们是不可化约的神秘现象。它们是粒子,它们确实具有确定的位置,仅仅是我们不能确定它们罢了。所以,这是一种恢复量子力学实在论的本体论的解释方式。这与所有存在着的测量和传统理论的预言是一致的;并且,它确实还提供了一个貌似可信的本体论的额外功效。正如这个德国人所说的,它就是直观。你可以形象地感知它,你可以有一些关于它状况的智力图片,它在理论上处于优势。就是说,如果在所有其他方面它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种类直觉知识的一些其他理论,那么从平衡的观点看,追求这样的做法是不好的。
凯里:从诺里斯的观点看,大卫·波姆试图恢复量子力学的实在主义观点,是一个带来重要结果的计划。物理学的反向发展超出了自身的界限。牛顿定律固化了现代社会的秩序,同样也固化了知识的新秩序。诺里斯最后说,今天人们不再会说物理学不再能达到事物的底层。
诺里斯:今天,在文化理论中,游荡着许多流行的、怀疑的相对主义观点,确实,它们从物理学的极度混乱和量子物理学以某种方式证明了客观实在的非存在中获得勇气。这就是我猜测的、量子物理学哲学正处于小混乱中并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理由。
凯里:那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诺里斯:这部分是兴趣方面的原因。我喜欢辩论——一种辩解的渴望。还有部分原因要归于我前面所谈到的思想。如果你放弃它并说,好的,我们不需要坚持现象背后有一个实在的观点,或者我们不需要坚持现象背后有因果律的观点,那么,我认为,你把这样的观点应用于比如说政治事件,这将再一次非常迅速地引起流行的怀疑主义,并且它离鲍德里亚的观点就不远了。同时,我也认为,还有一个伦理问题,可以追溯到伽利略与宗教权威之间的问题。我认为,在因果关系的、实在论的解释上,真实地提出否定的观点,可能有点太强制了。它可能是一种领人们入行的方式。我认为,你确实需要真理的操作标准,这在有关历史的争论中特别地显现出来。如果你去我们大学的图书馆,看看放在书架上的本年度历史哲学书籍,你会发现众多的复本——有30/40册现代作家写的书的复本,倾向于后现代和怀疑主义的相对主义观点,我认为,它们都是用现行的术语写成的,并认为历史最终是一种叙事。我们根据现行的规则和意识形态视角制造过去的观点。没有进入历史真理的通道。没有客观性。阅读一本历史著作本质上像阅读小说一样。不同的谋划将产生不同的突出情节。不同的观点将提供不同的解释并聚焦于不同假定的原因,诸如此类。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处理历史哲学问题的极具腐蚀性的方式。有善辩、因果关系、解释的中肯、按年代顺序排列结果的标准,可应用于历史的写作而不是虚幻的写作。你可以用年代学的方式播放所有的比赛,在小说中展示因果关系。并且我认为,在我正在谈论的历史真理问题上,流行的后现代怀疑主义与科学实在论的整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在那些流行的时髦和被认为是最前沿的思想中,其中的一些思想在道德上具有真正的腐蚀性。我想,我的意思是,这方面最为戏剧性的例子是对大屠杀的否定。如果你真的采纳历史真理是由现代的观点、根据当前的喜好、带有意识形态叙事模式而被建构的观点,那么,这将很难看清,你如何维护自己而反驳允许历史修正主义极端形式存在的指控呢?
凯里:但是,只有两种态度吗?
诺里斯:不,不,不是这样的。这是许多学术争论的一个无法摆脱的缺点——走极端。所以,你听到后现代主义者说:任何相信真理的人必须相信一些绝对的主宰;而“没有问题的真理将终结所有真理”肯定是实在论观点的一个绝好的漫画式表达。并且,对于实在论者来说,事实上,正像我所拥有的观点一样,如下陈述当然总是他们极具诱惑力的说法:任何一个持有关于客观历史真理、甚至是温和的怀疑论观点的人,将允许一些左翼修正主义更为恶毒的形式观点的存在。因此,是的,我同意,它可以显而易见地归于相互争论或漫画式争论的方式。但是,我也认为,为了维护你可能称为的“适度的实在论”,你至少要维护一些可以进行工作的差别意识——一方面是信念与知识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是当前我们知识的最好状态与真理之间的区别。这就回到前面我所说的,实在论观点的绝对必要的根基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事物立于实在中的方式使我们的陈述、假说和理由正确或错误。
凯里:诺里斯所关注的,是源自于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中的实在论争论和他视之为一个“逃离”的有害后果。
我们今晚第二个受访者的谈话始于一个相当不同的起点。当然,我认为它并不与诺里斯称的“温和实在论”对立。玛丽·米奇利是一位英国哲学家,在她工作的核心处,她把我们带到地球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关系上来。她在生命后期开始写作生涯。在她建立第一个家庭的30年之后,她的第一本书《男人与野兽》才面世;而现在她安好地进入她第9个10年。她还一直在写作,并且为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而大声疾呼。吸引我去关注她工作的那本书叫“作为拯救的科学:一个现代神话及其意义”(Science as Salvation:A Modern Myth and Its Meaning)。该书内容涉及现代文明中科学给自己指派的有时是英雄、有时是预言的任务,也涉及科学家讲述的关于他们事业的故事。2006年秋,我打电话给她,她在英格兰东北部纽卡斯尔的家里,首先招待我吃了中饭,之后安排了我们之间的采访。我问她把科学说成是一个现代神话的感觉。
米奇利:我的意思显然不是指撒谎。一个人可以用“神话”这个词只表示撒谎,但这并不是一个有益的用法,并且也不是我要谈论的。我的意思是指能让人着迷的、富于想象的一个图景、一件戏剧性的事情、一个梦想。我们思想的全部必须处于一种富于想象的和充满情感的状态。我们就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中来理解事物,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使用比喻的手法。所有的科学确实在使用比喻的手法,并且它肯定有来自于它的某类感情背景、某类……指向。
凯里:米奇利认为,科学只要试图表达自己,就带有这种叙事手法和情感色彩。当一个像斯蒂芬·霍金那样的科学家“穿上”预言的外衣并告诉我们说“完全和统一的物理学将在某一天揭开‘上帝的智慧’”时,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按照米奇利的观点,科学家即使冒险地拒绝所有的意义而只坚持在空洞的宇宙中只有赤裸裸的事实,也依然是讲述一个自我演义的故事。并且,她说,这种讲故事的倾向完全可以追溯到现代科学的开端17世纪。
米奇利:我认为,发生在17世纪的事情制造了巨大的不同,并且我们今天还坚持那时发明的思维方式。我的意思是,在17世纪发生的、且自那以后还在真正实际地被强化的一件事情,就是对科学同样的极度尊崇,以及那让人难以置信的高希望值:寄希望于科学能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为什么17世纪的人们投入如此的热情,为什么他们如此急切地认为世界有一个简单的结构,我认为这是相当有趣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发现如此这般的原因,那么所有问题将有正确的答案。所以,看起来似乎极为美丽、简单的牛顿钟表装置式的世界,只不过是人们想要的样子。现在想想,对我产生冲击的是,17世纪所发生的事情非常混乱,特别是宗教战争,直接而真实地搞乱了人们的生活并破坏了他们感觉到的他们站立其上的基础,因为如果你对你的宗教有怀疑那还有什么不能怀疑的呢?这种深度混乱的观念成为用总的秩序和总的简单性来认识问题所引发困扰的根源。
凯里:这一对总秩序的追求,正如17世纪的自然哲学家所理解的,是一项明确的男性事业——玛丽·米奇利讲述的“着色”科学的另一个例子。
米奇利:对于17世纪那些理论家而言,一个不幸的事实——如果现在他们知道它看上去多么可怕,那么他们会很疑惑,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十分明显的——是他们确信:科学是一项男性的活动并且它就应该如此,这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男性活动所做的就是去搜寻一个叫“自然”的女性——到处去寻找她,发现她的秘密,而且不能容忍任何胡说——你知道的,就是把她从她的藏身之地挖出并揭露她以便提供那最后的真理。我的意思是,他们使用极度野蛮的男性想象力并且他们并不知道这样做是何等的粗鲁。并且,他们正在做的——这值得认真思考——是他们反对那个时代其他喜欢“母性自然”和“地球灵魂”——Animamundi——观念的科学家派别,不是吗?这些学派会说,比如引力是各种客体、物理客体的爱,是对事物之源泉——它们的母亲的感觉;并且自然是一个提供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所有种类事物的母亲。信仰培根哲学的人和皇家学会的人认为,它们是极其迷信的东西,我们不能拥有任何这样的东西,我们不想让情感进入科学,虽然他们会说他们自己写的东西极富情感。只有在涉及柔软和深情一类的事情时,他们才承认情感的作用。他们并不反思他们自己作为一个有情感的存在物、具有侵略性和毁坏性的思维方式。并且我认为,这是一种至今还在继续起作用的谈论方式。如果你抱怨对待猪的方式,人们会说你感情用事。但是,如果某人维护这种对待,其理由是我们需要我们的利益,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吗?这不是感情。所以,这是极为无意识的。这就是我要说的。他们必须使用这些比喻手法。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使用这些特殊的比喻手法——这总是有趣的问题,但他们不问。
凯里:科学家们,按米奇利的理解,不倾向于关注可接受的比喻手法,但与此同时,又对不可接受的讲话者表达了强烈的反感。她说,这种想象的、与一些像他们那个时代的东西产生共鸣的结构的使用,一直持续到我们自己的时代。一个例子就是出版于1976年理查德·道金斯的书《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它很快成为一本在那个时代被广泛阅读和广泛讨论的科学著作。
米奇利:这是戏剧性的一幕,不是吗?一个个人主义时代的喜剧。在这个时代里,许多渺小的个人,仅仅局限于自身之内和事物的表面,每个人都只追逐其自身利益并进行无尽的竞争。你知道的,《自私的基因》一书变得流行,是因为它使用了巨大的极富想象力的力量来书写。它给出这样的一幅画卷:那些可怕的、真正不朽的小生物,在每一次竞争中辛勤劳作,把那些包括我们在内的有机物描述为像受那些可怕的小生物摆布的“缓慢移动的机器人”一样工作。我说的意思是,这对于一个个人主义时代来说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就是说:不仅在你的经济生活中是这样行动的,而且生活中每件事情也是这样行动的。我认为,像许多神奇的事物一样,在其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真理——在生命世界里有许多竞争,但是,这还不及达尔文所声称的一半。正如后来的人所指出的,你不可能有竞争,除非在开始时就有大量的合作。确实,在生命世界里,有大量的合作。所以,如某个人曾说过的,这是一个合作的世界,这将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它应该是竞争的”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时期真正想听到的。所以,你看,我现在正在说的是,虽然那些神话总是把一些真正的科学事实和人们需要知道的事物视为神圣的东西,但它们也被那个年代的一些愿望所强化;因此,人们确实应该注意这一点。这就是我要说的。当然,时常发生的事情是,一个神话可以用来反驳另一个神话。我们不应该仅仅选择它们中的一个。我认为,在17世纪,比如,上帝的目标是比我们的目标要大得多的一些事情、我们将永远不能理解它们的思想,为如下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十分健全的平衡:我们将很快获得所有事物的最终答案。我认为,正如人们已经失去的,他们已经失去了对我们自己思想局限性这一现实的一个良好意识。
凯里:按照玛丽·米奇利的观点,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一书属于科学著作的一类,它在不知不觉中从科学滑落到制造的奇迹,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时常在非同寻常的情况下实现广泛的传播。另外一个同样著名的例子是一本叫《机遇与必然性》(Chance and Necessity)的书,1971年它首次在英国出版。作者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雅克·莫诺,一个杰出的法国遗传学者。
米奇利:莫诺写的这本《机遇与必然性》很有影响,书中有关于娱乐场这样的奇迹的描述。生存就是一场游戏。它完全就是碰运气,你看,我们在这儿见面就是这样的一次运气。每一事物[发生]完全是运气。一个游戏并不是中性一类的模型。它完全是一个有强烈感情的模型,不是吗?你感觉你被无助地抛进这个赌场里。这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思考方式。它不是黑白分明的,是高度色彩化的。同样,《自私的基因》也是高度色彩化的。当然,莫诺所确认的色彩是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建立起来色彩——“野蛮的自然”。
凯里:用玛丽·米奇利的表述,她把雅克·莫诺的《机遇与必然性》看做“一个存在主义者的小册子”。但它自身代表了一本科学著作,也是米奇利反对的基础。她认为,像《机遇与必然性》一类的书,对于某一自大和无知的、不承认他们哲学和意识形态偏见这二者来说,都是一种罪过。
米奇利:如果更多的科学家意识到更多的重要的哲学问题,更多地意识到他们用一种或另一种带有偏见的思想去看世界而又不对之进行思考——就像他们所做的那样直接报告这个世界;那么这将是非常不好的事情。认为“一个人自己拥有的形而上学是科学的一部分”这种迷惑已经在相当的范围内扩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困扰我的不是科学自身是分裂的,而是这样的科学家:从总体上看,通过他们被教育的方式,他们倾向于拥有非常特殊的观点,并且不特别在意于许多较重要的问题。当今,在欧洲大陆——除了莫诺——受过教育的科学家不及一半会是这样的。他们确实倾向于做一些哲学和历史,就像他们做科学专业一样。这是科学从文化的其他方面分离的结果,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幸的。我认为,这一点在我们国家显得特别糟糕;这种观点的诱惑是相当大的。因此,他们就会对诸如上帝是否存在的事情作出武断的判断。我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
凯里:玛丽·米奇利不喜欢这种她称为由科学家发出的“武断的意见”。从她的观点看,雅克·莫诺所断言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的观点没有科学证据;并且,理查德·道金斯所声称的“人类是由他们的基因所控制的机器人”更是如此。但是,在这些陈述被它们的作者抛出时,它们却好像是科学的一部分一样。按照米奇利的观点,科学和意识形态的膨胀,常常加剧了公众反对科学的反应。对米奇利来说,当前,文化论战在美国的演变,就是一个例子。很明显,在科学与《圣经》的文字阅读之间,有一种真正的不一致;但她认为,这一问题已经被争论所呈现出来的进展方式极大地加重了。所有这些形式都可追溯到19世纪美国的情形,当时达尔文主义以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野蛮的自然”“适者生存”等——的形式传入美国大众。
米奇利:赫伯特·斯宾塞创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80年代,他去了各州并在所到之处鼓吹他的思想,使得他的思想在美国接下的10年中比其他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都更为畅销。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像自来水供给一样普及。这就是我认为的被一个达尔文主义者或科学主张所震惊的基督教信仰者所思考的内容——“野蛮的自然”和游乐场。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对那些奇迹的不负责任的使用,已经有一个可怕的效果,那就是,科学家时常迷惑他们自己,认为他们给予人们的仅仅是科学,而事实上他们给予人们的是他们自己拥有的道德和政治偏见。
凯里:玛丽·米奇利写道:“每一思想体系,在其核心中都有一个引导性的神话、一个虚构的幻象,用来表达我们本性最深处的诉求。”这一思想一直根植于她的观念中,她认为,科学将永远不可能强大到不再需要神奇。出于这一理由,她只希望科学家在选择他们想要叙述的故事时,要更有意识和更为小心。但她也认为,科学需要一个新的神奇,她推举的一个候选者就是同乡詹姆斯·洛夫洛克的“盖亚”理论。事实上,她已就该书写了一本小书叫“盖亚:下一个重要思想”(Gaia :The Next Big Idea)。“盖亚”理论主张:地球的生物圈作为一个整体是自我调节的系统——比如,地球周围不稳定的空气是通过发生在地球表面的地质和生物过程的总体而被调节和维持的。它创造了古希腊的地球母亲“盖亚”这一整体象征。玛丽·米奇利喜欢这一理论的一个因素是,它把不同的、有时是敌对的科学——研究地球生命的不同方面的科学——统一起来的方式;另一个是它复活了一个活生生的、有创造性的自然观念的方式。
米奇利:整个生物圈一直在做相当聪明和复杂的事情,如果我们一定要创造那些事物——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这样做,不是吗?——我们就应该始终非常聪明地去创造。主体不是这种呆滞、愚蠢的东西,而是内在地具有巨大潜能、知道去做正确的事情并正确去做的东西。形式的起源来自于对主体自身的摆脱并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所有这些蛋白质和事物都是自我创造的。你看,这并非如莫诺所提倡的那样是一场游戏。它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其中任何事情都绝对可能发生,因为什么将发生将取决于什么适合于你已经获得的分子形式。它们获得的越复杂,它们就越有特别的路径在其中继续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形式。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喜欢理论地观察它,那么[你可以设想]是这些事物中的内在上帝制造了这种发生。你不能用从外部的一个铁锤促使它发生的形式[设想]拥有一个发明家的上帝。
凯里:现代科学所建立的神话虚构了作为不同于本然的人性和作为没有内在目的或方向的、残忍的机械装置的自然。玛丽·米奇利认为,新的神话是,科学是发展着的,非常需要强调自然的创造性的自发性,并用萌芽和进化的世界来定位人性。
米奇利:世界有总体上趋向于更加复杂的趋势,不是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出意识。现在,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完全持续发展的一类事物,然而笛卡尔却说,意识是从外界置于人的头脑中并与人的头脑相当不同的某种东西。我们不必如此认识,确实不必;并且,我从来也不倾向于这样的认识。但在人们谈论有关人类的原理时——宇宙的整体一起产生了我们——我发现这是相当奇怪的。为什么不是长颈鹿原理或大象原理或黑甲壳虫原理呢?所有这些其他生物,差不多和我们一样,需要在这个特别的世界里前行。没有这一世界,它们不能生存。在总体上有一个趋于生命的运动,对我来说是完全明智的;当然,你知道,也有一个生命形式趋于分散的运动,因为有你可以生活的、合适的不同职业和不同地方。我认为,要点一定是,如果事物有获得一定生存方式的机会,那么它就会在其中自然地成长。
凯里:对于玛丽·米奇利来说,人性是与自然的其余部分一起持续发展的,她亲近于每一出现的和将要从其发源地持续出现的事物。但是,一个极为不同的方向被筑入现代世界的制
度里。对米奇利而言,我们如何行动,根本上是建立在我们认识和想象的基础上的——这也是她的哲学为什么不是懒散工作的原因;而且,她最后说,我们正在进入的生态危机,就是现代世界思考方式的产物。
米奇利:大约自17世纪以来,我们就用一种比之前的人们更具剥削性和更自信的态度去对待物理世界,是不是?自然地,他们也就倾向于探索他们能容易发现的东西。当他们发现的东西在出错时,他们就相当快地说,哦,天啊,我们制造了混乱,这不是上帝的意志,诸如此类。不过,他们时常不这样做,因为他们起初就被吓着了。所以,这种西方人从17世纪就接受的、用极为自信的方式对待一切事物的方式,就是他们如何认识世界这类事情,不是吗?这是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所有这类事情的一个结果,是他们相信自己比他们以前的人做得更为重要、更为权威并做出巨大改变的一个结果。我的意思是,在希腊悲剧中,如果你持有某种巨大的主动权,那么你极有可能想到的是悲伤。这在基督教思想中一直是这样的,虽然发生的方式有点不同。而且,自17世纪以来,它一直是这种伟大尝试的结果,不是吗?我们会尝试做所有这些事情并看到所发生的。因此,我感觉我们现在就必须去做——我倒是希望事情变得更糟——以便尽可能快地去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但是,不首先改变我们的思想,特别是我们关于我们自己是什么的思想,我们就不能改变现实。我们能吗?我的意思是,启蒙思想——现在我们摆脱了上帝,我们完全可以接管他的位置——似乎对我来说是不起作用的。
(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荣江译校。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责任编辑:王荣江
N0
A
1007-8444(2016)05-0601-09
2016-03-20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ZX023);2013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3ZXB003)。
克里斯多夫·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卡迪夫大学哲学教授,《反对相对主义》(Against Relativism)和《量子论与逃离实在论》(Quantum Theory and the Flight from Realism)两本书的作者;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哲学家,《男人和野兽》(Man and Beast)、《作为救赎的科学》(Science as Salvation)和《科学与诗歌》(Science and Poetry)等创伤性著作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