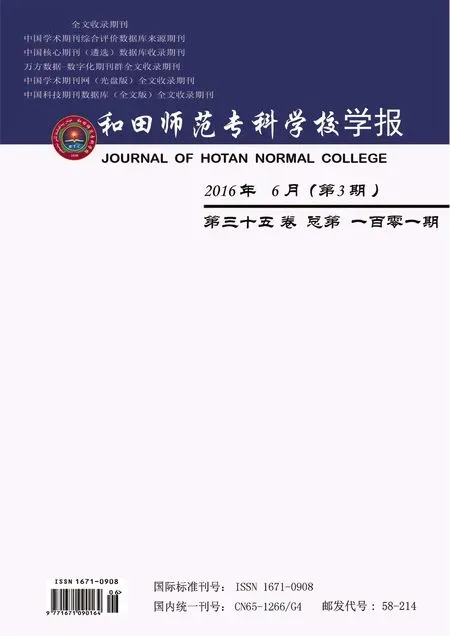“语文学科性质”研究中的问题——以王荣生、于源溟二博士观点为例
王予锋
“语文学科性质”研究中的问题——以王荣生、于源溟二博士观点为例
王予锋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语言学院 新疆 和田 848000)
“语文学科性质”,是指语文区别于数学、英语的其他学科的自身属性。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争论在学术界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专家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尽管新课程标准将语文学科的性质界定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但这似乎并没有就此终结这个难题。本文以王荣生、于源溟二博士为例,关注语文学科性质这个命题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语文学科;性质研究;问题
1.王荣生博士:舍名求实
1.1王荣生博士的主要观点
王荣生博士认为,在我国语文教育研究中,“语文学科性质是什么”这一难题,并没有多少求“知”的迹象,更多的是着眼于“行”,其实是问“语文学科性质应该是什么”。大量语文教育研究所做的是对既没有完全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的改革意见和方案进行的辩护。正如他在书中所说:“但这种辩护太急于进入‘语文科应该是什么’的答题,不但把语文课程目标、语文课程形态、语文教学形态笼统混合,而且跳过了中间一个关键环节。”[1]
在王荣生博士看来,这个跳过的环节就是“语文课程取向”,这也是所谓的“语文学科性质”之争的实质,因而,他放开了所有争论,提出了所谓的“置悬论”。在考察了性质研究的争论后,按照“区别对待”的原则,提出了具体的建议。针对旨在确定“语文学科性质是什么”的“唯一定尊”,树立唯一正宗和终极真理的研究,大概可以看作学力和思力的考量,不是这一路的人,尤其是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一般而言,不应当予以理会。换言之就是让他们争去吧,我们不用搭理。
针对为“我主张”的语文课程取向进行辩护而进行的研究,王荣生博士认为,应当以平常心待之。在语文的价值取向问题上,可以也应该是多元的,但应该“以实证研究为主,重在建设”。最后,他又倡导对语文课程与教学目标、语文课程形态、语文教学形态进行分层面、具体的定性研究。
1.2存在的问题
王荣生博士实质上提倡抛开各种打着“语文学科性质是什么”幌子的研究,“舍名求实”,对语文课程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具体层面进行实证研究。然而,实际上,他也同时否定了“语文学科性质”这个概念本身,否定了语文学科存在一个“性质”。这就必须要谈谈“语文学科的性质”到底有何作用。
实际上,人都是讲究实用的;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是严格的“实用主义者”,相反则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区别在于,实用主义强调的是“工具价值”,而“功利主义”看重的“结果有利”。用詹姆士的话来讲就是“我们思考事物时,如果要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虑它含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做什么样的反应。”[2]此外,美国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所说的“工具主义”在此也可以得到印证。
人类的任何行为基于一定的需要,正如卡耐基先生在《人性的弱点》中所言,驱动他人行动的最好方法是满足他的需要。考察“语文学科性质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否值得研究,只需要用实用主义的方法,看它是否能产生实际的效用,能否成为达到一定目的的工具,能否满足人们的某些需要。倘若有,则值得去研究;倘若没有,就不需要耗费精力。
那么“语文学科特性”这个概念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效用?到底能否成为达到一定目的的工具呢?答案是肯定的。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王世堪先生的论述。他在《中学语文教学法》中这样说到:“作任何事情,都要了解它的性质,谙熟它的非本质属性。我们从事语文教学,当然也应当这样做。”[3]周庆元先生也有相关论述:“语文学科的性质,也就是,语文作为一门课程,它同数学、政治、历史课程有什么根本不同的地方。”[4]
从以上两位先生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语文学科性质”这个概念确实有实际的效用。它的实际效用就在于为语文教学提供学理依据,使“语文学科”始终保持自身本性,不至于变成政治、历史、伦理等学科;使“语文教学”始终是语文教学,不至于成为政治教学、历史教学、伦理教学。
与之类似,辛安亭先生也指出,语文与数学物理等学科不同,政治性比较强,在教学中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发挥语文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作用,体现其道德价值。但是,语文学科的政治性思想性只是从属属性,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根本属性——它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特征——“语文课是工具课,是培养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一工具的课程。”[5]
2.于源溟博士:“属性研究”代替“特性研究”
2.1于源溟博士的主要观点
于源溟先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最后一章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他明确指出“语文学科性质”是一个“学术假命题”。他认为语文没有一门严格意义上的母体学科作为支撑并对其进行限制;课程的设计具有还很大的自由度,是编制主体根据某种需要依据自己的认识进行的个性化创造。没有了语文学科,也就没有了“语文学科性质”的说法,进而完全否定了“语文学科性质”这个概念本身和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
在一系列论述之后,于博士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语文不存在一个“性质”的问题,但是,语文确实存在一个“属性”问题。[6]他认为应该进行转换,将关注的焦点从“性质”转移到“属性”,进而水到渠成地消灭了“语文学科性质”这个命题。
紧接着,于博士站在课程设计的立场,认为语文课程是人为建构的,课程设计就是根据主体的需要,抓住课程材料的属性之间的关系,选择并组成新的属性。课程材料在进入课程时展现所有属性,而有的属性与主体的需要是相悖的,课程设计就是要“尽量求得课程属性组合与主体需要组合相契合。”最后,他又具体阐述了“属性研究”的具体方法:一是研究语文课程材料的属性,一是研究已然语文课程的属性,一是研究“应然而未然”的语文课程的属性。第一类研究的目的是认知语文课程材料的属性,为语文课程设计所遵循的理论和可能的材料;第二类研究的目的是为语文课程设计提供课程材料和课程材料组合的理论;第三类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学生的需要和课程内容的材料属性,为设计者提供理论指导。
2.2存在的问题
于源溟博士的观点看似新颖、严谨,然而,实际上存在很大的问题。
一是,彻底否定了“语文学科性质”这一概念和所有的相关研究。这跟王荣生犯了同样的错误,上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工具性”即便漏洞百出,对抵制语文教育“泛政治化”倾向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思想性”“人文性”尽管错误重重,也有利于纠正语文教育只看重语文的工具价值,忽视思想价值和人文价值。于博士不分青红皂白将其彻底否定,实际上有绝对和极端化的嫌疑,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是不应该出现这种倾向的,因为学术研究不是政治运动,不应产生“文化雅马哈”式的“话语霸权主义”。
二是,将“语文”简化为“语文课程设计”。按照于博士的论述,语文课程设计既然强调“主体需要”,根据主体需要来选择组织材料,实际上就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他在这里强调用“属性研究”取代“性质研究”,实质上是用“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取代了“语文学科性质的认知”,从逻辑上来讲是不应出现的问题。关于这点,还可以从课程论的角度加以证明。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誉教授托斯顿·胡森(Torsten Husen)和前联邦德国汉堡大学教授纳维儿·伯斯特尔斯维特(T.Neville Postlethwaite)主编的《国际教育百科全书》对课程的组成这样解释:“课程由5个方面或5种成分组成,1.对于学生和社会的构想”;2.目标和目的;3.具有选择性、范围和顺序的内容或教材;4.实施方式,如采用的方法和学习环境;5.评估。[7]本书随后又做了具体论述,“学生和社会的构想”就是确定学生的能力、需要、兴趣、动机以及学习文化内容的潜能。“社会的构想”就是说社会旨在训练个人,使用个人。
由此观之,于源溟博士此处仅仅关注这五个部分中的第1个和第3个部分,至于课程的不表、实施方式和评估根本没有设计;甚至连学生第2个部分,他也忽视了学生的兴趣、动机和能力,仍然是按照“我认为”的“学生的需要”进行课程设计,这样的指导理论,恐怕还是不要有的好。
这点在王荣生博士的《语文科课程论基础》里也可以得到印证。王荣生博士将语文教育研究分为七个层面:人—语文活动层面,人—语文学习层面,语文科层面(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层面),语文课程具体形态层面,语文教材具体形态层面,语文教学具体形态层面,语文教育评价层面。其中,文科层面(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层面),指的是抽象的语文课程与教学层面,研究的是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而语文课程具体形态层面则指的在语文科层面“WXYZ”解答既定的情况下,对具体形态的各方面进行研究——也就是课程设计,而在我国则特指在既定课程标准指引下对语文课程组织方式和课程内容的研制。
据此可判断,于源溟博士所谓的“属性研究”,仅仅处理了语文课程具体形态层面的研究,跟语文整体研究相差实在太远,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其后果可想而知。
三是,“主体需要”忽视了社会的需要。于博士在论述课程设计时以“主体的需要”“人的尺度”作为最终标准和依据,实际上这里的“主体需要”主要指“学习者”“学生”的需要,忽视了社会的需要。站在心理学的角度,考察需要,不仅包含个体的需要,还包括社会群体的需要。而就教育来讲,还要考虑国家和民族层面的需要。
关于这个论点,有太多的事实可以证明。先来看博士文中关于尺度的论述“所谓‘人’的尺度,就是以作为学习者的人为尺度”。 “学生作为主体,她的需要决定了课程内容和语文教师的存在。”[8] “课程的属性与学生的需要并非是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很强的复杂性。”[9] “作为‘属性从’的单一‘物’的某一属性与作为主体的学生的多种多样需要的某种需要发生联系就构成课程设计所依循的‘理’,即‘道理’。”[10]
当然,文中也不是一点没有提到社会的需要。比如164页的“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已经很多,诸如要注意语文课程的意识形态守护功能,要选择经典名篇,要注意学生的需要,要注意材料的时代性等等。”然而,将“社会的需要”简化为“意识形态守护功能”和“材料的时代性”,是非常狭窄的。而且,语文是否应当“注意意识形态守护功能”尚需进一步论证。时代的需要也不仅仅体现在语文材料本身的时代性。信息时代对学生语文素养的要求跟工业时代显然是不同的。
3.结论:
尽管关于“语文学科性质是什么”这一命题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新课标也站在国家的层面对其进行了界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语文教学实践上来看,学术界对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和空间。
[1]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基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9.
[2][美]威廉•詹姆士著,陈羽纶,孙瑞禾译.实用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7.
[3]王世堪.中学语文教学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12.
[4]周庆元.语文教育研究概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21-22.
[5]辛安亭,姚冠群.三十年来中学小学语文课教学的回顾[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79,(3):86-87.
[6][8][9][10]于源溟.预成性语文课程基点批判[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4:146;167;168;169.
[7][瑞典]托斯顿•胡森,[前联邦德国]纳维儿•伯斯特尔斯维特.国际教育百科全书(第2卷)[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0:551.
2016-4-3
王予锋(1973- ),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言教育、双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