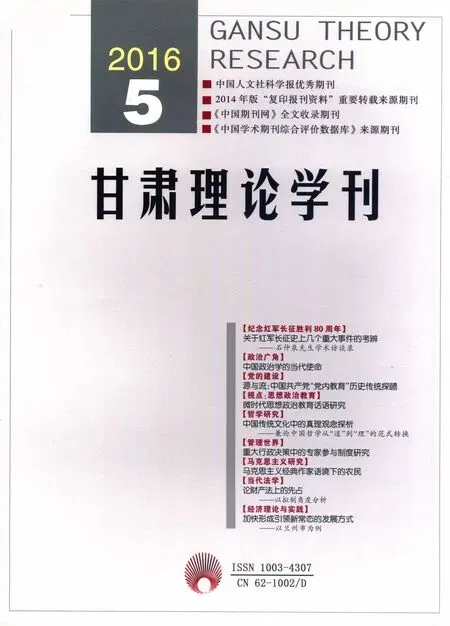红色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耦合
——兼论红色文化生成机制
夏 欢,胡龙华
(1.2. 赣南师范大学 赣州 341000)
红色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耦合
——兼论红色文化生成机制
夏 欢1,胡龙华2
(1.2. 赣南师范大学 赣州 341000)
探寻红色文化的生成有不多不同的视角,本文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出发,以红色文化的文化渊源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以文化比较学为分析框架,考察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其见、对抗与冲突、交流与对话,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耦合的缘起;进而从文化批判学的视阈下分析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科学批判、理性启蒙及在此基础上中华传统文化独立自由精神的回归;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换、爱国主义的精神驱动和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融合三条路径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红色文化耦合的发生机理,形成对红色文化的生成机制的系统认识和再思考。
红色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耦合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种特殊文化样态,其生成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根源。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任何文化的形成都有两大主要因素——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同时,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孤立存在,其必然与其它文化进行交流与对话、碰撞与冲突、对抗与融合。红色文化正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对话的产物,是中西方文化冲突与碰撞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耦合所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舞台上进行深度融合,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正是红色文化生成的内在机理。本文旨在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这一红色文化的文化渊源和马克思主义这一红色文化的理论渊源进行价值分析与机理解剖,把握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与相互区别,探求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动力与话语转换,重新认识和思考红色文化的生成机制,为新时期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传播与推广奠理论基础和思想条件。
一、矛盾与冲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耦合的缘起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条件,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是文化领域的正常现象,只要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发生交集就会出现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既为文化领域所不可避免,也是文化生成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正是有了不同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才增强了文化的传播力度和发展深度,也为新的文化形态的产生准备了存在空间和外源条件。红色文化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中才得以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接受与推广也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正是这一文化冲突过程的“拉锯”,才逐步酝酿形成了红色文化。
(一)差异与歧见:两种不同的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文化土壤,而中华传统文化则是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中、西方两种文化在价值主张、观念态度、思维方式、行动逻辑等方面都有诸多差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西方文化是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文化形态,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歧见。理解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观有诸多视角,这里仅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角度看待中、西方文化观,作此种解释,不仅因为群体动力是文化生成的重要逻辑,还由于在不同文化的比较中,“西方文化的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和中华文化的群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1]76-79。在西方文化观念中,每一个个体都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不受他人的约束,个人利益被视作天经地义,个人意识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个体本位是西方文化观的深层内涵,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观念的价值主张,这种观念催生了追求独立、追逐利益、摆脱束缚、向往自由的个人行动逻辑。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中国文化观念下,集体主义是其最为重要的价值主张,中国文化强调个人服从集体,注重整体内部的等级和秩序,坚持集体内部成员行动一致原则,集体对对个人有着较强的约束力和控制力。文化观念的差异无疑会对个体的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如何运用中国语言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让封建伦理规范、等级制度封闭和武装下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解放学说,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而且是红色文化生成、发展的矛盾动力与内在机理。
(二)对抗与冲突:文化交流矛盾显现
马克思主义自从传入中国之初就伴随着种种争议,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是否契合的争论不绝于耳,有一部分人片面夸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对立面,忽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共通性,因而得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不相容的错误结论,才有了部分爱国志士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或“中间路线”寻求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之道。诚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两种不同样态的文化就其表达方式而言是有其明显差异的,因而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显性”差别,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斗争”哲学,将矛盾的斗争和统一视为事物发展的原因,认为“斗争无处不在”,主张通过主动革命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与此相区别,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中庸”哲学,虽然中华传统文化也有部分学派看到了矛盾的作用,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宗”和“主流”则一直强调“和”,虽然“中庸”文化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一面,但中庸之道片面强调“和”也蕴含着排斥矛盾斗争与阻碍矛盾双方向对立面转化的“保守”成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这些对抗与冲突也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阻碍因素,给一部分中国人民理解与接受马克思主义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这些对立性无法掩盖两种文化的价值主张、理想追求的共通性,如何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成分,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换,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而红色文化正是在这种文化冲突及其消弭的过程中逐渐生成与发展起来的。
(三)命运与反抗:传统文化传承危机
发展至近代,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由于不能适时地根据时代发展变化进行自我革新,从而牢牢地被绑在在封建统治者的战车之上,被印上“落后”、“愚昧”、“封建”的标记,儒家文化被称作“吃人的礼教”,“打倒孔家店”成为无数先进知识分子和爱国仁人志士的共同心声和一致主张,即使有少许主张对儒家文化应当区别看待的微弱声音也迅速地被湮没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中,在这一时期,中华传统文化成为阻碍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遭受了最为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中华传统遭遇了自产生以来最大的危机。在这场文化批判运动当中,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接受者、宣传者最先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不仅对儒家文化特别是封建纲常伦理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学说等科学思想对中化传统文化的专制主义、空想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化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从而使得儒家文化走下“神坛”,国民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不能说不是中化传统文化发展和传承上的重大危机,中化传统文化进入了命运最为坎坷的一段时期。但同时我们这应该看到,正是有了这次对儒家文化的深刻批判和改造,儒家文化吸收了时代精华和先进文明成果,从而增添了新的活力,中化传统文化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历史命运。
二、批判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扬弃
中华传统文化到了近代已经疲态尽显,被蒙上了封建主义的神秘面纱,正如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瞿秋白同志所说,“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2]14,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自我革新的地步,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必须吸收新的时代精华进行自我改造,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不息、传承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外来思想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也必须立足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和文化传统,才能为最广泛的社会成员所接受和认可,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度融合与耦合共生提供了现实可能,中华传统文化亟需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唯物辩证法等先进思想进行反思改造,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扬弃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耦合的产物——红色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崭新样貌以全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批判与传统文化封建桎梏的打破
马克思主义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批判和革新改造就必须彻底清除中华传统文化的封建“毒瘤”,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专制主义思想进行彻底清算。封建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封建宗法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即在封建文化话语体系中,国家是“君主”的而不是人民的,“忠君”就等于爱国,这种名为爱国实质上是排斥爱国主义的以皇权中心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冲击下显得不堪一击,各种“卖国行径”、“丧权辱国条约”充斥着整部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人的地位凸显了出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这就使爱国主义回归本位。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接受者、传播者们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把人从封建专制主义的压制和宗法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赋予其独立地位,同时批判了封建主义落后的历史观,把孔子从“亘古仅有圣人”的“神坛”上拉了下来,主张“考察孔子生活的社会背景与孔子思想产生的关系”[3]359,对儒家文化的落后性进行了深刻批判,将中华传统文化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将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上提供了现实可能。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和独立自由精神的回归
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也有对未来社会美好蓝图的描绘和对理想社会的永恒追求,甚至还被有些学者冠于“古代社会主义”的名词,不可否认的是,这里面确实有着一些百姓“安居乐业”等和谐社会的“积极成分”,但其本质而言仍是一种空想主义,是游离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实际的一种建立在封建伦理基础之上的美好幻想,其目的是让百姓循着封建统治秩序生产生活,这不仅是一种“非理性”的历史观,还是对人民群众独立地位、自由精神、创造思想的压制和束缚,是通过把人的思想囚禁在非理性的未来幻想之中从而消解人民群众对现实封建统治秩序的愤懑情绪与理性思考。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深入分析及其矛盾运动的仔细考察,主张立足社会经济条件、生产生活实际、历史文化传统等具体国情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可能、蓝图设计以及实现路径,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先行者们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陈独秀先生就曾说,“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克思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4],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效消除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成分,重新彰显了中华民族坚持独立、崇尚自由的民族精神。
(三)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科学理性精神的启蒙
“中国传统文化关注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内涵,却推崇尊卑有序和泯灭个体独立的原则”[5]51-57,不仅阻碍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使人的独立地位受到漠视、人的个性受到压制、人的自由精神遭受否定,近代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民族精神的缺失使得近代中国丧失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新鲜血液,重塑民族精神成为传统文化能否继续向前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认识世界,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科学理性精神的启蒙,重新解读了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涵,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促使中华传统文化向先进文化的成功转型,而且致力于改造世界的历史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开启了追求民主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革命征程,伴随这一过程当中,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革命实践的洗礼与考验,不断“去劣取优”、“去伪存真”,回到了科学理性的轨道上,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锻造造了新的中国社会道德,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重新建构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就使得中华传统文化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使得红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获得了持久的精神动力,红色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度耦合中逐渐形成、快速发展起来,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崭新文化形态和耀眼的文化瑰宝。
三、共生与融合: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实践中红色文化的生成
虽然中华传统文化就其语言范式、思维方式、行动逻辑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异,但二者之间仍有许多共通之处。就其对未来社会终极目标的追求而言,儒家追求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笔下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着许多天然的契合,早期共产主义者曾更为直接地说,“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3]44。除此之外,中华传统文化在哲学观上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契合,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古代朴素辩证法有许多地方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光辉,中华传统文化“知行统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有着天然的内在契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存在许多思想契合之处。正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等方面存在理想诉求和思想观点上的契合,才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舞台上共生与融合,逐渐孕育形成了红色文化。
(一)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换与红色文化的生成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要想被中国大多数社会成员所理解、接受和认可,需要立足中国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社会实际,用中国人民能理解的表达方式、话语逻辑进行宣传,这就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化,马克思主义话语转换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过程,这就为红色文化的诞生提供了现实土壤。与此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华传统文化发生了历史嬗变,中华传统文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转向,即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来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种转向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次一次成功“俘获”,也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次主动“就范”,产生的一个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大众化、民族化,并由此诞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话语转换过程之中,在中国革命现实需要的催生下,中华文化的新型样态—— 红色文化应运而生,红色文化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精神和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优秀民族精神,以独特的历史底蕴和话语体系彰显了其重要的文化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换是红色文化生成的必要条件和直接成因。
(二)爱国主义的精神驱动与红色文化的生成
一种文化的形成需要有一定的群体动力,与此相适应的是,文化的传播也要有一定的传播动力,红色文化也不例外。毋庸置疑,红色文化的创造者是中国最广大最普通的革命大众,他们就是红色文化生成的群体动力。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得最普通最平凡的革命群众联合在了一起,又是什么使他们焕发出了强大的力量,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洪流中去?答案是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让中华民族空前团结,也正是爱国主义精神让普通群众焕发出了强大的革命斗志。近代中国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成为那一时代的最强音,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逐渐被唤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征程,红色文化在此过程中得以孕育形成。因此,可以说,爱国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表达,还是红色文化的鲜明标志,是红色精神的核心内容,正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驱动下,革命力量才能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战胜强大的反革命力量,革命形势一次次遭遇困境又“绝处逢生”,在红色文化的激励和感染下,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加入到革命队伍当中,不仅加快了革命胜利的到来,还使红色文化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三)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融合与红色文化的生成
如果说爱国主义精神回答了红色文化文化为何生成的问题,那么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则回答了红色文化如何生成的问题,实践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联结的纽带,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耦合的大熔炉,在革命实践当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武装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发现了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开启了新民主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征程。与此同时,通过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马克思主义找到了适合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从而更加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团结了更多的工农群众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鼓舞了革命群众的革命斗志,也正是在这一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剥削统治、赢得人民解放、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实践中,红色历史不断书写,红色文化孕育形成,红色精神的光芒闪耀在中国五千年革命历史之中,所以说,民主主义革命是红色文化生成的现实基础和实践渊源,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在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熔炉中锻造形成了红色文化。
[1]于桂敏,王艳秋.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因素——中西方价值观念差异[J].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4(3).
[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N].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7-1.
[5]都培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辨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0).
[责任编辑:康继尧]
2016-09-02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高校思政专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内涵及其培养机制研究”(13JDSZ2083)的阶段性成果。
夏欢(1991—),女,湖南邵阳人,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红色文化研究;胡龙华(1964—),安徽安庆人,赣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A8
A
1003-4307(2016)05-01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