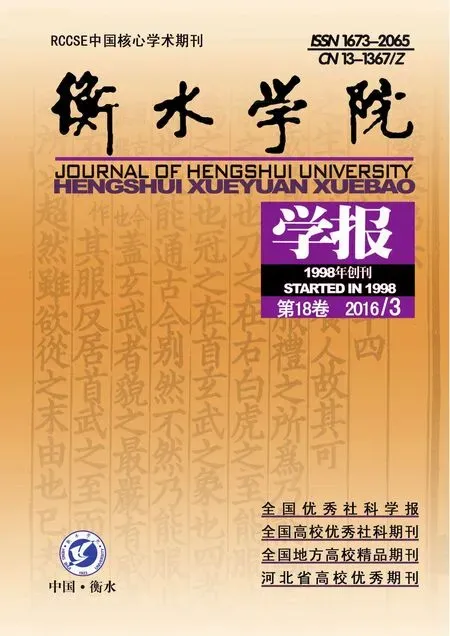儒学伦理与史学主题关系析论
谢 贵 安(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儒学伦理与史学主题关系析论
谢 贵 安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儒学伦理与史学主题之间有紧密的相关性。儒学伦理作为中华文化之根,对传统史学主题起着主导作用。传统史学的叙述者或史书修纂者,在叙事时皆无法摆脱当时主流思想——儒家伦理的影响。无论是尊君、尽孝、旌节、彰义的史学主题,还是编年、纲目、纪传、实录等史书体裁,都深受儒学伦理忠、孝、节、义等观念的辐射和牵引。儒学伦理的变化促进了传统史学发展的阶段和脉络。史学主题形成的原因和背景皆可从儒学伦理及其发展中寻获。然而,以窥探宫闱秘事为己任的野史就对尊君观念形成挑战,说明史学在某些方面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关键词:儒学;伦理;史学;主题
儒学与史学的关系,在学术分类上表现为经部与史部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主导思想与辅助思想的关系,在功能和作用上表现为辐射与扩散的关系。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对传统社会的各种学术和观念都起统治和主导的作用,对史学的影响也不例外。因此,儒学伦理常常成为史学主题,甚至影响史学体裁的变化。当然,非主流史学(野史)的主题,并不总受儒学理论的影响,有时甚至出现与儒学观念相反的倾向。目前或对儒学伦理有密集的研究[1-3],或对史学主题有较多的关注[4-6],本文将二者结合起来讨论。
一、儒学对史学施加的基本伦理
儒学是孔子以宗周的礼乐和宗法制度为基础发展完善而成的学说和思想体系,主要内容包括仁义礼乐思想、尊君重民观念和纲常伦理意识。其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些伦理加以讨论。
1. 正统观念和忠君意识
忠是对君主及其朝廷的尽忠,然而当历史发生歧异时,会出现不同的政权,因此必须选择一个政权来效忠,于是忠的观念又引出正统观念。儒家创始人孔子非常重视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生逢春秋乱世,他深知维护拥有正统地位的统治者权威的重要性,奋起维护周王室的正宗地位,当周王室失去合法性后,他起而维护诸侯的权威,以此维系国家稳定,消弥社会动荡。孔子认为周天子拥有正统地位,因此必须加以维护,指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7]2521在回答问政的齐景公时,特别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7]2503-2504。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8]125。在此基础上,儒家形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的三纲观念。董仲舒把三纲论证为天定的原理,指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独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9]《基义》《白虎通》直接解释道:“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10]唐代孔颖达征引《礼纬·含文嘉》的原文,正式道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提法[7]1540,从此完整地形成了三纲之说。宋代理学形成后,把“三纲”进一步神圣化,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天理,朱熹声称天理“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11]。三纲之首便是君为臣纲,忠是诸伦理之首。孔子在政权歧出的纷乱中,强调正统观念,突出忠君意识,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无论是司马迁的五体形式的纪传体的创立,还是实录对先帝历史的追述,都注入了正统观念和尊君意识。正史中专门立有《忠义传》《诚节传》或《死节传》,便是儒学忠的伦理对史学主题产生的直接影响。
2. 孝顺观念
孝是忠的基础。在家国一体的古代社会,在家行孝,在朝则尽忠,因此儒家特别推崇孝道,认为“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在传统男权社会中,父亲在家中拥有绝对崇高的地位,孝顺成为子女必须遵从的伦理准则。儒家的这种孝顺伦理,必然反映到史学之中,成为史书的主题之一。正史中专门立有《孝义传》《孝行传》或《孝感传》和《孝友传》等,便是孝的伦理在史学中的直观反映。
3. 三从四德和男尊女卑观念
“三从”是要求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谓:“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12]1106班固在《白虎通·爵》中解释:“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三从是“夫为妻纲”的折射和延伸;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12]687,是对妇女的单向度要求。受这种儒学观念的影响,史学的主题打上了重男轻女的深刻烙印。古代史书记载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男人,历史成为男性的历史。历史舞台上活跃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佳人是才子的陪衬和偶尔的点缀。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史书中,几乎都以男人为主角。虽然有些正史中也立有《后妃传》和《列女传》,但就整个史书来看,仍然处于配角地位。只有唐代所修的《武则天实录》和吴兢所撰的《国史·则天本纪》,才书写了以女人为主角的历史,但这种情况不仅罕见,而且在当时即受到卫道士们的强烈反对。德宗建中初,史馆修撰沈既济针对“吴兢撰《国史》,立《则天本纪》,次于高宗之下”的情况。上奏表示强烈反对,指出“则天皇后进以强有,退非德让,史臣追书,当称为‘太后’,不宜曰‘上’”,并且指出“今以周厕唐,列为帝纪,考于《礼经》,是谓乱名”。认为“宜入皇后传,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后》”[13]。宋人孙甫则直接声称“武后僭窃位号,唐史臣修实录、撰国史者,皆为立纪,系后事于帝王之年,列伪国于有唐之史”,是“名体大乱,史法大失”,他要求“正帝统而黜僭号”[14]。《列女传》甚至只是阐释“夫为妻纲”伦理孝条的载体,后来成为忠、孝、节、义四大伦理之一,“节”的贯彻,所录之人基本都是节烈之妇。
4. 民本意识和重民思想
儒家与绝对尊君的法家不同,在尊君的同时提出重民思想,形成“尊君-重民”的政治模式。当然,这种尊君与重民的平衡木,在实践中总是倾向于尊君一端。然而,为了防止因过度尊君导致民变,使统治之舟沉覆,在官方意识形态中,总是不断突出民本思想。在史学中,也经常贯彻重民意识。史书中经常记载地方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和儒臣提出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旱灾和水灾发生时,政府和地方官员对赈灾救民所做的努力。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表明古代史书具有“人民性”。在所有正史中,均没有为当时最主要的人民——农民设立《农民传》[15]。古代史书在贯彻重民观念时,实际上是“义”的体现,体现了君主对百姓所尽的“道义”。
儒学还有其他一些伦理观念,如仁、礼、智、信、廉、耻等,均对史学的记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有时也成为史书主题。限于篇幅,不赘。
二、儒学伦理决定史学主题
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绝大多数朝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对史学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使史学的主题总是受儒学伦理的支配。史书经常贯彻儒家的忠君思想、孝顺伦理、节烈观念和民本意识,形成自己的书写主题。
1. 史学的忠君主题
中国传统史书中,充满着尊君意识和忠君主题。忠是对尊君原则的内心服从。以实录体史书为例,它是皇帝个人及其政权的专史和独有体裁,渗透着儒家“君为臣纲”的伦理和强化皇权专制的思想。
古代实录史书对君主的形象进行过神化、圣化和雅化的塑造过程[16]。所谓神化,就是将皇帝塑造成神圣之君和天之骄子,试图通过儒家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观念,将皇帝及其专制统治说成是顺天应人和天命所归。唐初贞观朝的史臣在修纂实录时,便为唐朝统治者李渊、李世民附会出生时的异象。《唐高祖实录》虚构出武德初晋州人吉善在羊角山遇见乘白马的白衣老父,让他回去告诉李渊将会当上天子的故事;又记载郇州献瑞石,上有文曰“天下千万”的奇象。这些描绘实际上在将李唐王朝之得天下粉饰成早有预兆。《清世祖实录》卷一称,世祖福临于崇德戊寅正月三十日戌时诞生于盛京,“孝庄文皇后方娠时,有红光绕身衣裾间,如有龙盘旋状。女侍皆惊以为火,近视之不见,如是者屡。众皆大异。诞之前夕,孝庄文皇后梦一神人抱一子授之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孝庄文皇后受置膝上,其人忽不见。既寤,以语太宗。太宗曰:‘是异祥,子孙大庆之兆也!’次日,上诞生,视之顶中,发一缕耸然高起,与别发迥异。是日红光照耀宫闱,经久不散,香气弥漫数日。上生而神灵,聪明英睿,志量非常。天日之表,龙凤之姿,仪范端凝,见者慑服。”以此暗示帝生非常和君权神授,达到尊君目的。所谓圣化,就是史书将皇帝描写成“生而知之”的聪明英睿之人。如《清宣宗实录》卷一称道光皇帝“聪明天亶,目下十行”“经史融贯,奎藻日新”。所谓雅化,则是将粗鄙如朱元璋之类的君主,塑造成学问高深的文化人。
此外,史书还将皇帝塑造成道德典范。如《清太宗实录》卷一称太宗皇太极“天赐睿智,恭孝仁惠,诚信宽和,圣德咸备”“又善抚亿众,体恤将卒。无论疎戚,一皆开诚布公以待之”。《清宣宗实录》卷一谓道光皇帝“生有圣德,神智内充”。《清穆宗实录》卷一称同治皇帝“聪明天亶,孝敬性成”。凡此种种,都是儒家强化纲常观念在史书编纂中的具体体现。
忠君的执行者是忠臣。为了表达尽忠观念,古史还特别重视对忠臣的书写和奖励。《宋实录》载,至道二年,合祭天地于圆丘后,太宗下令对“历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有祠宇在,逐处并令精洁致祭”,对于“近祠庙陵寝处,并禁樵采。如庙貌隳坏,令所在量加修葺”。又要求对为王事牺牲的官吏,录其子弟为官生,对于其中有“妻息寡弱不能自达者”,要求“诸司职掌及郊庙行事官等并与加恩”[17]。以此旌恤忠臣。《清实录》记录了顺治六年浙闽总督陈锦的奏疏的内容:“福建福清等二十县士民同心效死守城,忠义可嘉,请免本年丁徭以示鼓劝。”并记载了“疏下部议”的决策[18]卷四三,顺治六年三月戊寅。通过这种记录,表达对忠臣的旌恤。
即使是正史列女传中,也出现了从“夫为妻纲”到“君为臣纲”主题的转变。衣若兰指出:“与元明官修胜朝《列女传》不同的是,殿本《明史·列女传》对于烈女传记的收录,较不特重殉夫,而是强调崇祯朝抗辱死烈者。”[19]这就转向对忠君意识的强调。
2. 史学的孝顺主题
史书还经常贯彻儒家孝道,形成“显亲尽孝”的主题。在正史中,不少列传都反映了孝的主题,如《宋书·孝义传》《梁书·孝行传》《魏书·孝感传》和《新唐书·孝友传》等。
以古代实录史书为例,其修纂的基本主题,除了忠君之外,居然是表彰孝行。实录一般都是继任皇帝为先君所修,修纂的目的就是为了“显亲”尽孝。《实录》是“家国一体”的集中表现,既是国家大典,又是皇家私史,修纂《实录》的目的既是为国家保存史实,更是为先帝显亲尽孝。
北宋侍御史陈次升在《上徽宗论修〈神宗实录〉》疏中明确提出:“圣人之治无以加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显名于后世。”他认为,只有认真为父皇修史才是“显亲之道”,否则便是对显亲之道“未至加隆”,会“有累圣德”[20]。南宋范成大也指出:“追孝莫大于显亲,显亲莫大于述事。”故主张对“御历三纪”的高宗既要记述在位时的“休功盛德”,还要记录其退休后的英明训谟[21]。清皇太极在动员文馆诸臣为其父修《太祖实录》时,显然也受到儒家孝道的影响,指出:“朕嗣大位,凡皇考太祖行政用兵之道,若不一一备载,垂之史册,则后世子孙无由而行,岂朕所以尽孝乎?”[22]顺治帝亲政后,内院大学士希福投其所好,要求将太宗的德业“必载史册,永为法守,用昭我皇上孝思”[18]卷六一,顺治八年十二月戊辰。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古代实录都以突出孝道为己任。《唐顺宗实录》卷一记载德宗与顺宗父子的关系时指出:“德宗之幸奉天,仓卒间,上常亲执弓矢,率军后先导卫,备尝辛苦。上之为太子,于父子间,慈孝交洽无嫌。”以突出顺宗对德宗的孝心。南宋绍兴十三年实录院修撰王赏提议:“皇帝亲享太庙,圣孝格天。前数日阴云欲雪,至日澄霁。伏望宣付史馆,以昭圣孝。”高宗自然“从之”[20]。《明世宗实录》记载了大礼议之争,通过情与理、孝与礼的较量,最终确立了孝的地位,使世宗得以称其生父为“皇考”而不是“皇叔考”。
实录不仅对先帝尽孝,而且对臣民的孝行也同时加以表彰,使实录益显家国一体的特征。《宋太宗实录》卷七六载,至道二年正月辛亥,皇帝制曰:“孤老惸独不能自给者,长吏倍加存恤。”《明神宗实录》卷二六八载,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丁卯,“旌表孝子周勃。勃,湖广奉新县民,幼失母,事父至孝。父年八十病疽,勃口衔药洗疽,且尝粪,延其父六年。从御史旌之”。《清仁宗实录》卷二八一载:嘉庆十八年,“旌表孝子,江南等省谢文锦等十三名;孝妇,江苏杨王氏;孝女,江苏李氏等六口”。
对于统治者来讲,尽孝的重要途径是显亲,即让先帝名声得到记载和张扬。刘知几曾说过:“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21]因此“今上”对先帝的事迹通过载诸《实录》而流传下去,以此显亲而尽孝。北宋陈瓘在《上徽宗乞别行删修绍圣〈神宗实录〉》的奏疏中,提出了《实录》修纂的基本主题:“盖以国史、实录皆欲显扬宗庙之美,非人臣之所得私也。”[2衡之所有《实录》,赞美君亲都是十分明显的主题思想。
3. 史学的节烈主题
儒家受时代局限,提出了“三从四德”和男尊女卑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史学中的妇女书写。在正史中,第一次出现《列女传》是范晔的《后汉书》,当时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儒家独尊地位动摇的背景下,故所记女性既有节女,也有才女。但随着儒学复兴和程朱理学兴起,正史的《列女传》所述女性向节妇和烈女方向转变,亦即突出“三从四德”和“夫为妻纲”之主题。
章学诚对《列女传》的伦理化倾向有清醒的观察,指出:“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节烈之烈为《列女传》,则贞节之与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义妇,更不相入,而闺秀、才妇,道姑、仙女,永无入传之例矣。夫妇道无成,节烈、孝义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学,岂谓不及方技、伶官之伦,更无可传之道哉?刘向传中,节烈、孝义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鲁女,无所不载;及下至施旦,亦胥附焉。列之为义,可为广矣。自东汉以后,诸史误以罗列之列为殉烈之烈,于是法律之外,可载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议之。”[23]衣若兰指出:通过各史《列女传》的考察,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文献,记载人物重在辨其郡望、世系,论其人品、口辩;而宋元人撰史则侧重于叙述历史人物的忠孝节义。这一变化导致“《列女传》道德标准的窄化约从十至十一世纪开始”,其结果使“历朝列女传记所强调的女性角色,贤能辅助的色彩,渐为贞烈所取代。历代诸史《列女传》收录女性慷慨捐生的传记,在比例上有渐增的趋势,动机却走向集中于贞操一项”。她还指出,元明两朝是《列女传》走向“烈女传”的关键,元人所修的辽、金、元三史《列女传》,“因贞节而死的烈女(尤其殉夫者),比例大增”[19]。程朱理学获得统治地位,正是从元代后半期开始的,此时所修的《列女传》,正好突出了夫为妻纲的主题。衣若兰还注意到,在列女传多样性窄化之前,记录女性死烈的原因尚有多种:一基于孝亲,如《后汉书》的曹娥殉父等。二本于爱国,妇女报国的行为见《魏书·列女传》北魏孝文帝时的孟氏与刘氏,《晋书·列女传》的荀灌、张茂妻陆氏为夫讨伐沈充等,“然这些传中,一是为子,一是为夫守城,另一更为报夫仇而举兵,所显现的替夫、子而非出于己身爱国的意涵,亦不得不注意”。她敏锐地观察到:“这样的忠勇行为与忠诚之心,虽符合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然仍源自于女子三从的基本架构。”因此,这些列女的记事主题,仍然是儒家的“三从四德”。
4. 史学的重民主题
古代史书以儒家的民本思想为指导,不断记述农民的苦难和民间的灾害,以及朝廷对抒困和救灾所采用的措施,反映了朝廷对民瘼并非漠不关心。重民思想的贯彻,实际上是儒家“仁义”观念在史学上的表现。
以《明实录》为例,该书中记载了许多赈济灾民的活动。《明英宗实录》表彰了漕运总督王竑所开展的大规模赈济灾民的活动。据该书卷二二九载,景泰四年五月甲戌,“直隶徐州大雨水渰没禾稼,民饥愈甚。巡抚、巡按官右佥都御史王竑等各具以闻”。代宗“诏命竑悉以改拨支运及盐课粮赈济之”。这次水灾,在王竑等人的赈济下,安然渡过。卷二三二载,景泰四年八月乙未,总督漕运右佥都御史王竑奏:“比因直隶凤阳并山东、河南荒歉,民多流徙趁食。臣委官于河上每遇经过舟船,量令出米煮粥给之,赖以存活者一百八十五万八千五百余人。又多方劝输殷实之家,出米麦榖粟二十五万七千三百四十石有奇,银三千六百七十余两,铜钱绵布半之,给与被灾者五十五万七千四百七十九家,其缺农具种子者七万四千三百九十七家,臣亦以官物给之,流入外境而招抚复业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外境流来而安辑之者一万六百余家。即今人颇安业,盗贼稀少。”奏入,代宗颁令嘉奖。对于赈济所剩银两,王竑从民本思想出发,建议代宗将剩银二万四千六百五十两留在灾区,继续济民[27]卷二三四,《废帝郕戾王附录》第五十二,景泰四年十月庚子。水灾刚过,雪冻之灾接踵而至。王竑又忙于救济雪灾。据英录卷二三八载,景泰五年二月丁未,总督漕运左副都御史王竑奏:“山东、河南并直隶淮、徐等处,连年被灾,人民困窘。去岁十一月十六日至今正月,大雪弥漫,平地数尺,朔风峻急,飘瓦摧垣。淮河、东海冰结四十余里,人民头畜冻死不下万计,鬻卖子女莫能尽赎……身无完衣,腹无粒食,望绝计穷……皇上端居九重,无由目睹。设若一见,未必不为动心。大臣居处庙廊,少得亲视,使或视之,未必不为流涕。”要求朝廷设法赈济。对于上述史事的记载,反映了史学对儒学伦理重民和仁义观念的贯彻。
同时,史书还经常记载朝廷官员对吏治的整饬和对贪官污吏的整肃。《明英宗实录》记载了漕运总督王竑减少冗官,减轻民扰的行为。英录卷二○八载,景泰二年九月甲辰,“初自济宁至徐州设管河主事三员,至是以官多民扰减一员,从总督漕运左佥都御史王竑请也”。同时,治理违犯官吏。英录卷二二一载,景泰三年闰九月乙亥,“监察御史王珉被命巡河,数于济宁诸处奸淫,微服至所淫者家,拜其父母,所索运粮军官馈赠尤多,为右佥都御史王竑所奏”,谪充开平卫军。王竑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和贪官。景泰五年,总督漕运左副都御史王竑奏:“运河自通州抵扬州,俱有员外郎等官监督收放粮、收船料钞及管理洪闸、造船、放甑,此等官员辄携家以往,占居公馆,役使人夫,日需供给,生事扰人。又南京马快船有例禁约,不许附带私货及往来人等,近来公差官员每私乘之。宜通行禁约,违者治罪。其掌船官吏,妄自应付者,一体罪之!”[27]卷二三七,《废帝郕戾王附录》第五十五,景泰五年正月己未王竑曾经一次就奏黜了 78个不称职的官员。据宪录卷五载,天顺八年五月辛未,“总督漕运、巡抚淮扬等处左副都御史王竑奏黜老疾、庸懦、不谨官监运司同知刘曦等七十八员”。实录还记载了王竑解决粮长科害小民问题。景泰六年三月,巡抚淮安等处左副都御史王竑奏:“江北直隶扬州等府县粮长,往往科害小民,乞准湖广例,尽数革罢。粮草令官吏里甲催办。”[27]卷二五一,《废帝郕戾王附录》第六十九,景泰六年三月丙辰从之。王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舒缓民困。史书对这些史事大书特书,表明了它对民本思想的重视和贯彻。
与此相应,史书还记载了朝廷任命官员,有时还以百姓的口碑和心愿为标准的历史事实。据《明英宗实录》记载,巡抚王竑保留了任满离任却为百姓不舍的巢县知县阎徽。该书卷二一五载,景泰三年夏四月辛巳,“升直隶庐州府巢县知县阎徽于本府通判,仍理县事。徽满九载当去任,属民五百九十余人保留。巡抚右都御史王竑审实以闻,故有是命”。这些史实的记载,反映出史书的民本思想,是儒家重民观念和仁义伦理在史学上的体现。
三、儒学伦理确定史学体裁
史学体裁是表达史学主题的载体。如果说史学主题代表内容的话,那么史学体裁就代表其形式。中国历代产生的史学体裁,基本上是史学主题在形式上的反映,都是为了更好地突出儒学主题,以反映儒学的时代变化。下面逐一分述。
1. 编年体突出君主的独尊地位和君事的纲领性质
编年体是最早的一种记事形式,也成为最早的史学体裁之一。一般认为编年体的滥觞是孔子删定的《春秋》。孔子在该书中,通过微言大义强化尊君意识,“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8]155。孔子在删定《春秋》时形成的“三讳”原则,正是尊君、敬长和睦亲等儒家观念的直接反映。所谓“三讳”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28]。这些原则,在编年体史书中得到完全的贯彻和落实。
编年体以帝王或君主的年号为线索,突出了君主的主体地位,是尊君的绝佳体裁。宋人认为,编年体以帝王为中心,而国之治乱尽系于帝王之心,故编年体易于认清历史盛衰与帝王之心的关系,于是编纂了不少有影响的编年体史书。司马光撰成了继《左传》后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他秉持尊君的观念,决意为皇帝提供资治的镜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均是编年体的鸿篇巨制,皆以北宋和南宋的每位皇帝的年号为线索,叙述北宋和南宋的漫长历史。虽然宋代皇帝多有荒淫行径,但这些编年体史书均对之加以隐讳。两宋实录一修再修,一改再改[29],就反映出史书对儒家尊君意识和讳饰观念的忠实执行。
除了编年体外,在纪传体的本纪(本纪用编年形式)和“编年附传”体的实录(大类上属于编年体)中,都秉着尊君的观念,以皇帝的年号为主线,铺叙历史事实,凸显皇帝的中心地位。在编年中,对于君主持粉饰或隐讳的态度。实录虽为专记皇帝事迹的史书,但据现存的《唐顺宗实录》《宋太宗实录》和明、清两朝《实录》来看,都对皇帝作正面歌颂,连篇累牍地收录反映皇帝光辉形象的史料,很少有揭露其阴暗的一面。偶有像《明武宗实录》这样的实录,直接暴露皇帝的丑行,但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它是信奉道教的明世宗朱厚熜报复“大礼议”中敌对势力刻意而为的。朱厚熜上台后,将自己忌恨的武宗“留中不报”的八百六十余本奏疏,全部“宣付史馆”,让史臣“据实直书”[30]。但这种现象仅得一见,在实录中成为绝响。
到宋代,编年体演变成纲目体,更鲜明地突出了正统观念和尊君意识。为突出尊君意识和正统观念,宋代儒臣将编年体创造性地发展为纲目体。编年体易于表达《春秋》的微言大义,而难于像纪传体论赞那样直接表达对历史的评判。宋儒创立纲目体正好将二者结合起来,符合宋人笔削褒贬和驰骋议论的特点。在纲目体的发明上,南宋朱熹厥功至伟。他用“天理”标准衡量《资治通鉴》,发现“帝曹魏而寇蜀汉,帝朱梁而寇河东”,不尽合于《春秋》劝惩准则,同时认为《通鉴》按年系事,线索不明,难以检寻,因而将《资治通鉴》改编成《资治通鉴纲目》,创立了“纲目体”,最后由其门人赵师渊完成。朱熹在《序》中指出,纲目体“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31]。纲目体把历史叙述与历史评论结合了起来,其特点是“质诸人心而无疑,参诸众论而无愧,信夫可以接《春秋》之坠绪也!”[32]它的出现,是儒家伦理进一步强化的结果。
2. 纪传体确立忠君意识和大一统格局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国一直在向尊君和中央集权方向发展。但是,儒家的尊君与法家有较大的不同:法家尊君是绝对的,认为君主是主子,臣子是奴仆;而儒家尊君则是相对的,强调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儒家在贯彻忠君思想的同时,竭力做到君臣共治,明良相得。在此背景下,史学体裁的发展,反映了儒家伦理和政治观念的变动趋向。
纪传体是西汉司马迁创立的影响巨大的史学体裁,成为后世承传不辍的官方史学的首选形式,并被长期冠于“正史”之名。它正是在从黄老道家的无为政治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转折时期横空出世的,适应了儒家的尊君观念和大一统格局形成的趋势,具有既尊君又重臣的儒家特点。
司马迁用纪传体撰成了他的宏伟巨作《史记》。该书问世之初,曾被视作子部杂家,称为《司马子》或《太史公书》[33],但在官方认可的正史目录中,却被视为经部春秋类的著作,被附入《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即经部)的“春秋家”下,反映出它所具有的类似《春秋》的记事特点和儒家意识。
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其体裁是一种适应忠君意识和大一统格局的史书形式。《史记》的第一部分就是本纪,共有十二个本纪,代表一年十二个月,本纪编年为史,记载帝王的事迹和一朝大政,为全书之纲,属于史书的核心部分,代表君主对整个历史的统摄;然后是三十个世家,表明一个月有三十天,在政治上的含义则是世家对帝王的拱卫,属于历史的中层部分;然后是七十列传,代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五分之一,是次于世家的众多的大臣列传,属于历史的外层部分。从本纪,到世家,再到列传,表现了儒家“君君臣臣”的等级有差的社会秩序,是儒家“礼”制社会的表现。后两个部分构成了对代表帝王的本纪的环绕和拱卫。凸显了司马迁确立的“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34]的主题,这显然是对儒家尊君意识和大一统格局的绝佳印证。《史记》的列传,先大臣,而后众臣,最后是《四夷列传》,表明由内及外、由中心到边缘的书写模式,是大一统国家格局的鲜明写照。
3. 实录体强化忠君意识和中央集权制
实录体属于编年体之一种,但较编年体有进一步的发展,成为“编年附传体”(元清两朝除外)。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到隋唐统一全国后,统治者决定重新树立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不仅在经学上组织人员大规模从事《五经》的注疏活动,而且在史学上也大规模地修撰正史,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八种正史都产生于此时。并且在史学体裁上还作了适应于儒家忠君观念和大一统思想的创建,这就是对实录体史书体例的改进。实录史书本来出现于南朝萧梁时期,但其体例已不可考。从唐代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纂实录活动,将实录发展成“编年附传”体裁。实录体的创立和盛行,本身就是与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发展相适应的,是为了突出儒家君为臣纲的观念。
实录体同时兼有帝王编年与大臣列传,与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有相通之处。不过,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其本纪与列传分属不同的部分,虽在内在结构上是列传环拱帝纪,但在外在形式上列传与本纪却是并列的两个部分。实录体虽同时具有帝王编年和列传,但帝纪与列传却以编年的形式混编在一起,使列传无论从内在结构上还是外在形式上,都附属于帝王编年,表明尊君观念的发展和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的进一步强化。以帝王编年为主线的实录融入传记后,在保持记事的同时,增加了记人的份量。实录的最大传主是皇帝,同时又融入众多的大臣传记,形成众星捧月之势,使实录体成为更加适合中央集权制的史书体裁,从而获得迅猛的发展。自唐以后,五代、宋、辽、金、明诸朝均修有“编年附传”形式的实录体史书,自成一系,绵延不绝。由此可见,实录体裁的形成与发展,与儒家的尊君观念和大一统思想有密切的关联。
然而,也需要指明,有些史学体裁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在表达儒学伦理的变化,如南宋袁枢在阅读《资治通鉴》时,因编年体在叙事上时断时续,难以掌握完整的历史线索,而另创纪事本末体,就与儒学伦理无关,纯粹是史学体裁自身发展需要所致。此外,野史以窥探宫闱秘事为己任,“人臆而善失真”,但却能够“征是非,削讳忌”[35],显然也脱离了尊君思想和“三讳”原则的轨道。鉴此,我们不能过于夸大儒学伦理对史学的无限影响。
总而言之,儒学伦理作为中华文化之根,对史学主题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传统史学是以叙事为其基本形态,叙述者或史书修纂者在叙事时,无法摆脱当时主流思想——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对于传统史学而言,无论是尊君、尽孝、旌节、彰义的史学主题,还是编年、纲目、纪传、“编年附传”等史书体裁,都深受儒学伦理忠、孝、节、义等观念的辐射和牵引。儒学伦理对史学主题的影响,既有正面效果,也有不良倾向,作为历史现象和既成史实,今人已无法干预其中,只能接受这种历史的结果。然而,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却能对儒学伦理的主导地位产生更加深切的认识,也更能认清传统史学的发展脉络,了解史学主题形成的原因和背景,从而增进对中国传统史学史的探究。
参考文献:
[1] 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2] 刘彦生,梁晋华.从儒学伦理到儒学哲学──孔子儒学与朱熹儒学的比较[J].思想战线,1997(4):42-47.
[3] 刘红叶.汉代儒学伦理政治一体化特征的形成[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8(4):86-89.
[4] 屈小强.论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主题[J].天府新论,1996(6):76-80.
[5] 汪高鑫.董仲舒与汉代历史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6] 方同义.论浙东学术之史学主题[J].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05(11):43-47.
[7] 阮元.十三经注疏: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9] 董仲舒.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0] 班固.白虎通[M].丛书集成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410.
[11] 朱熹.晦庵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383.
[12] 阮元.十三经注疏: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 宋祁,欧阳修,范镇,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539.
[14] 孙甫.唐史论断:卷上,不称武后年名[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62.
[15] 谢贵安.史记人民性悖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6):64-70.
[16] 谢贵安.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J].学术研究,2010(5):97-105.
[17] 宋太宗实录[M].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卷七六,至道二年正月辛亥.
[18] 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 衣若兰.女性入史——正史列女传之编纂[EB/OL].[2015-11-23].http://www.douban.com/note/291897035/.
[20] 陈次升.谠论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38.
[21] 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94.
[22] 清太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一六,天聪七年十月己巳.
[23]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5.
[24] 刘知几.史通[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82.
[25] 陈瓘.上徽宗乞别行删修绍圣《神宗实录》[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3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29.
[26]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829.
[27] 明英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卷二三四,《废帝郕戾王附录》第五十二,景泰四年十月庚子.
[28] 四书五经[M].陈戍国,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1:1298-1299.
[29] 谢贵安.宋实录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94-453.
[30] 谢贵安.明实录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18.
[31]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序例[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
[32] 何乔新.椒邱文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3-24.
[33] 李纪祥.《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J].文史哲,2008(2):65-90.
[3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319.
[35]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53.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fucian Ethics and Historical Themes
XIE Guian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Confucian ethics has close relavance to historical themes. As the root of Chinese culture, Confucian ethics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theme of th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Both the narrators of th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the compilers of historical books in their narrative can not get rid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mainstream thought at that time, Confucian ethics. No matter whether they are the historical themes such as respecting the emperor, doing one’s filial duty, commending man of integrity and honoring man of righteousness in the Tang Dynasty or the historical genres of chronicle, compendium, biography and memoir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oncepts of Confucian ethics such as loyalty, filial piety, integrity and righteousness. The change of Confucian ethics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onal historiography. The reasons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themes may be got from Confucian ethics and its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unofficial history that takes prying into the secrets of palace chambers as their duty challenges the concept of respecting the emperor, which shows that historiography i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in some aspects.
Key words:Confucianism; ethics; historiography; themes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6)03-0026-08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6.03.006
收稿日期:2016-01-04
作者简介:谢贵安(1962-),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国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