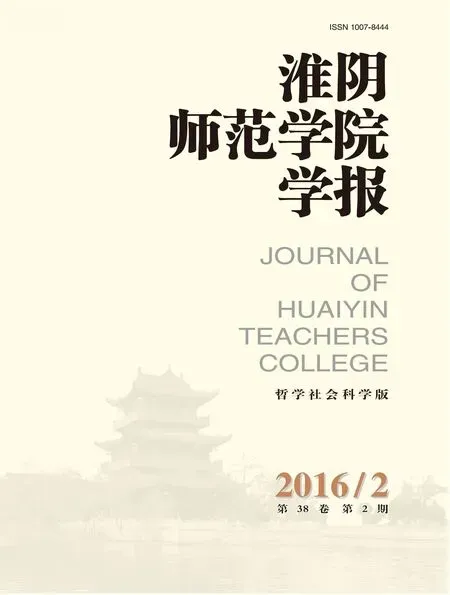“如何认识科学”(十六):科学知识与社会建构——大卫·凯里对史蒂文·夏平的访谈
史蒂文·夏平, 大卫·凯里
“如何认识科学”(十六):科学知识与社会建构——大卫·凯里对史蒂文·夏平的访谈
史蒂文·夏平,大卫·凯里
摘要:史蒂文·夏平认为,有一个独立于我们思想的世界;但当我们开始描绘这个世界和谈论这个世界时,我们是在谈论文化的实在。科学在所有的方式下都是社会性的;这绝对没有破坏其真理的断言,真理同样以自然的、社会的方式存在。在《利维坦和空气泵》中,通过重现波义耳和霍布斯之间关于科学知识可靠性的争论,作者挑战了科学革命作为一个简单和大一统事件的标准形象,展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维度。在《真理社会史》中,夏平继续为撼动被认为是标准的科学观念作出努力,挑战“科学是建立在普遍怀疑的基础之上的”观点,认为科学不是依赖于系统的怀疑而是依赖于系统的信任。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已变得非常重要,它被权力机构和制造财富所包围,这是科学获得巨大成功并获得不断增加的影响力的标志;但这也导致人们相信其中有某些危险。因此,我们有必要理解:科学知识是什么类型的知识,与科学判断有关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确定性,在公共事务中科学能够起到和扮演什么样的作用。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秩序;社会建构;科学文化;科学危险
肯尼迪:我是保罗·肯尼迪,这是《思想》栏目的“如何认识科学”节目。
夏平:我当然相信有独立于我们文化的、独立于我们社会秩序的、独立于我们语言的物质实在;但我也同时相信,当我们陈述事实时,那些关于事实的陈述属于我们的文化。所以,我完全相信:有一个独立于我们思想的世界;但当我们开始描绘这个世界和谈论这个世界时,我们是在谈论文化实在。它们还能是什么呢?
肯尼迪:几年前,哲学家伊恩·哈金编辑了一部系列丛书,使用的标题是“社会建构”:差异性、性别、高血压的社会建构——诸如此类。在哈金创办的丛书中,有大量的这类标题,但大都采用同样意图的表述:削弱据说是社会地建构的范畴的实在性。就是说,这样的知识仍然时常是通过社会过程而形成的;这样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协商的结果。某一事情要么是真实的,要么是社会地建构的,但不是二者;历史学家史蒂文·夏平认为这是错误的认识路径。他在如《真理社会史》和《科学是文化》等书中论辩说,科学在所有的方式下都是社会性的;这绝对没有破坏其真理的断言,真理同样以自然的、社会的方式存在。在今天的《思想》栏目中,史蒂芬·夏平与我们分享他科学史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方面的思想,以作为我们持续进行的“如何认识科学”系列节目的继续。这是《思想》栏目的制作人大卫·凯里。
凯里:1996年,史蒂芬·夏平出版了一本简明地称为《科学革命》的书。科学革命,根据已得到确认的历史传统来看,大体上说包含了从尼古拉·哥白尼到伊萨克·牛顿这一时段。人们可能会更为准确地说,科学革命可以扩展到从哥白尼论证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1543年到伊萨克·牛顿公布了他的运动和引力定律的1687年。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柯瓦雷称其为“由人类的头脑实现的或经历的最具深刻影响的革命”。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同样夸张地写道:“科学革命胜过自基督教诞生以来的每件事情并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降低到只不过是插曲的地位。”史蒂芬·夏平在他的书中以一种更为模棱两可的阐释开始他的书写:“没有像科学革命这样的事情”,“并且这是一本关于这样的事情的书”。这是精确地捕获夏平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看法的精妙表达。“科学革命”这一措辞——以优雅的、合适的、常见的方式——显示:首先,我们已经都知道的事情;其次,可能被建构成为一个紧凑的、始终如一事情的事件:一个革命。而这正是史蒂文·夏平所反对的设想,但不可否认,一本书能写什么,这一直是件有趣的事。
他已经试图以某种比更早期的历史学家允许的、较少视为当然的、更为浑浊和更有争论的方式写17世纪的自然哲学史,并试图打破围绕在一般科学实践上的显著光环。
这种打破旧有习惯的做法在20世纪60年后期和70年代早期就有其根源,当时夏平刚开始他的学术生涯。他完成遗传学方面的毕业论文后转入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领域。1973年,他加入位于爱丁堡大学——用一种新的方式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正在形成的地方之一——著名的科学论小组。2007年春天,我在哈佛大学——在那里史蒂文·夏平作为一名现任科学史教授——他的办公室采访了他。他回想起他和他的同事在爱丁堡试图挑战有关科学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被认为是标准智慧的变化。
夏平:在我进入学术界的时候,被称为知识社会学伟大传统的是,一个人被要求去做的就是弄清楚社会和社会的因素在什么程度以及会带来什么结果的意义上影响知识。社会被认为是一类事情,知识体被认为是另一类事情。并且问题是,一类事情在什么程度上、带来什么结果的意义上会影响另一类事情呢?就知识体被认为是柔性的而言——比如,政治意识形态——知识社会学家认为他们有可列举的案例,比如,像社会利益和社会职位一类的事情会影响你如何认识社会的正当秩序和政府的恰当角色,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就知识体被认为是硬性的而言——它将包括数学、逻辑和科学陈述——许多人把这样的知识社会学视为一种不可能,原因是科学毕竟是关于世界、关于实在的知识。这是真实的知识,并且社会的因素只能侵蚀这种知识。所以,像我自己一类的人曾获得的传统是,把科学知识社会学自身视为一种不可能。
凯里:为什么你认为你和你的同事将能够挑战在那个时期你也持有的那种观念呢?
夏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作者在他们的职业或工作上罕有是专家的。但是,我们在爱丁堡科学论小组中的每个人都有一些重要的科学背景,我认为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认为伴有科学背景,就有一种心愿,不去理想化或者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怀疑过去被告知的关于科学的一些理想化的故事。所以,当在我的同事中有人说我们要把科学当作一种社会制度来理解、我们要把科学当作一种文化的特殊形式来理解时,我们倾向于去经营的试验是,这种对普通科学实践的描述是历史的还是当下的?比如,下雨的周一在一个化学实验室里所研究的是怎样的科学,面对这样的实验科学要给出一个解释吗?与这种标准科学相对立,我们认为,已被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有时被退休的科学家所告知的许多故事是理想化的故事。我们要讲的是有具体气息的故事——把一个更加实际的、更加自然的科学感带入学术界。
凯里:想把一些不同的东西引入科学史理想化叙事中的愿望,导致史蒂文·夏平和他同事的研究走向不同的方向。一种策略是近距离地观察正在工作的科学家:在一个下着雨的周一下午,在实验室里工作的科学家是什么样子?另一种是对科学争论的研究,不论其中的事实是否已经被建立、作为结果的知识是否被固化成教条。这两个方面的探求在史蒂文·夏平与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弗尔(Simon Schaffer)合著的、出版于1985年、名叫《利维坦和空气泵:霍布斯、波义耳和实验生活》这本著名的书中得以进行。
夏平:如果我现在还没记错的话,该书内容的第一行是:什么是实验?人们已经记录的是作为现代化的科学和促使科学进步引擎的实验方法;而我们想获得的是“你是怎样做实验的”“它们真的有用吗”“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你是如何从实验的发现去理解全部自然的秩序的”等这些问题的某种感观。然后,当然还有下面的问题:为什么你做实验?比起做大量实验,有其他达到安全的自然知识的方式吗?以便我们在其他事情中尝试对许多人所说的制造现代世界科学革命时期的理解作出贡献。我们不仅尝试表现一些被做了的事情方面的每一天,而且尝试展现出在17世纪关于人们如何着手生产安全可靠的自然知识的各种观点。并且,我们想展示的不仅仅是那些观点的变化,而且包括论战。
凯里:占据《利维坦和空气泵》一书的是罗伯特·波义耳和托马斯·霍布斯之间的争论。波义耳是一位英裔爱尔兰的自然哲学家和于1660年建立的英国第一个现代科学学会——皇家学会——的创始人。在同一年,波义耳出版了《新实验、物理力学、触摸空气弹性及其效应》一书。他与罗伯特·胡克一起建造了更为早期的大陆模型——一台空气泵——那个时代的科学奇迹。这个装置中的空气可以被排出从而产生一个真空——大致的真空——他实施实验以便他能证明空气压力或者如他更为诗意地称为的“空气弹性”的存在。他发现在许多其他事物中,空气对于声音的传播是必需的并且某一气体的容积与其压强之间反方向变化——今天仍然为人们所记得的波义耳定律。波义耳遭到他同时代的托马斯·霍布斯的反对,后者的书《利维坦》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开创性著作之一。霍布斯论辩说,只有绝对确定的知识才可能平息异议和维持公民的一致;实验永远不能达到这样确定性的程度。霍布斯说,空气泵无疑是昂贵的和有独创性的,但它最终仍然不过是“孩子们用的玩具枪性质的”东西。按霍布斯的观点,用这样的玩具产生的结果并用只不过是私下的少数几个老百姓去证明它,根本不能提高毫无疑问的知识的尊严。这一争论以及双方有趣和吸引人的辩论,为史蒂文·夏平和他的合作者西蒙·沙弗尔进入17世纪的社会背景、它散乱的和未解决的复杂事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我与史蒂文·夏平的谈话从罗伯特·波义耳研究计划的性质开始,并相当详细地谈论这本书。
夏平:他的计划是为建立自然哲学——在一个安全的基础上理解自然的总体秩序——提供一个模型并通过详细说明的实验方式在桌上模型或像桌上模型之类事物的规模上模拟自然。只有当人们人工地制造出大量的实验发现物,他们才可能在那些安全的实验发现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关于自然像什么或者自然的某一部分像什么的假说。这有时被称为与“演绎的”方法截然相反的“归纳的”方法,或者与自上而下的方法截然相反的自下而上的方法:首先是确保你的经验知识、你观察的知识、你实验的知识的安全,然后在这些安全的观察和实验知识的基础上建立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像什么的理解。不是做思想实验,而是做真实的实验,做大量的真实实验,然后从那些大量的实验中归纳或推断出你的自然界的图景。
凯里:为什么波义耳和他的同事觉得他们需要安全的知识?
夏平:在17世纪、特别是在17世纪的中期,有一种遍及欧洲的危机感。它是一种涉及社会秩序的危机。在几十年内战之后,在君主政体复辟的同一时期,皇家学会于1660年成立。在作为整体的欧洲,宗教战争、特别是从1618年到1648年的30年战争,许多人确信欧洲当时所经受的混乱和暴力开始于知识上的危机、信仰上的危机。只要人们能达成共识,只要他们能在推理的正确规则上取得一致意见,这是那时的想法,那么,一个安全的社会秩序就可以得以恢复和维持。所以,在宗教中、在哲学中和科学中,都有对这一知识问题提供解决办法的积极性,以便让每个人在形成、确认、传播和修改知识恰当的方法上达成一致。这就使得哲学和科学比我们习惯上的认识更多地与大范围的秩序问题相关联。
凯里:那么,波义耳的结果是怎样影响社会秩序问题的呢?
夏平:他们提供了一个象征。在欧洲某个村庄附近谈论一个空气泵以展示恰当的知识是如何被建构的观念,是一件滑稽的事情;但是它提供了有关可靠的知识如何能够被制造的一种象征或肖像。并且我认为,对于像波义耳一类的人和他的英国同事更为重要的是,实验结果也提供了在知识的确定性上其限制是什么的模式。所以,比如,在以罗伯特·波义耳为代表的传统内,你可能拥有观察和实验事实的可靠知识,但是你可以从那些事实归纳出来的自然定律至多是可能性的知识。因此,有关被波义耳和他的许多同事接受的、被植入该计划的自然秩序的知识,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作为被他和他的同事忽视的知识问题之一是,要以更多的确定性为目标。
凯里:那么霍布斯制造了什么样的反对的理由呢?
夏平:霍布斯认为,不确定性为混乱开了方便之门。他更倾向于一种自上而下的或演绎的方法。他认为,只要人们在定义、公理和解释了经验或观察过的现象的定律上达成意见一致,那么他们就能达成共识。对于像托马斯·霍布斯和法国的雷内·笛卡尔这样的人而言,知识的问题不得不用巨大的确定性来解决。知识方面的任何弹性、任何维度都可能打开通向异议和最终发生内战的通道。所以,他们在什么是知识应该是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上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它应该是严格地约束人的还是应该允许有弹性或有维度的?波义耳相信后者,霍布斯和笛卡尔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前者。他们每个人对他们视为一个信仰的危机、一个知识的危机的问题都作出了回应,但修正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
凯里:所以在霍布斯那里有一个宽松的因素……
夏平:确实如此……
凯里:……虽然霍布斯时常更多地被当作一个自由主义传统的鼻祖。
夏平:我认为确实如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为如早期皇家学会一位国际法学家所称的“相反的想象力”留有空间。让我们找到在基本原理上人们取得意见一致的方式以及让他们拥有一种对比如全部自然秩序的争论的真正的权衡方法吧。也让我们限制知识吧。又如皇家学会的一位国际法学家所说的,让我们在没有“以教会和国家事务”——这是他们使用的措辞——的名义干预的实验和观察事实上人们可能取得意见一致方面达成一致吧,因为它们会使人们产生分歧。让我们在能证实秩序的基础上创建秩序吧。实验科学能保持一致;但是,一旦你开始谈论形而上学问题,一旦你开始谈论基本的宗教教条,那人们就将吵来吵去。
凯里:罗伯特·波义耳和他的同伴打算在一个大家同意的和实验能核实事实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秩序。不过,虽然这一计划被视为对分裂的宗教和形而上学争论的一种矫正方法,但史蒂文·夏平认为,它使自己也成为一个宗教维度的观点。新的自然哲学家,如波义耳把他自己设想为的,将通过走出社会和阅读自然这本书的方式识别一个可复原的真理。并且,夏平说,这一运动是一种对一个陈旧宗教角色的重塑。
夏平:在宗教中(尤以基督教为典型),教义的提倡者或接受者,要让自己离开社会走向荒原,成为一种在荒野中的呼喊,从社会公约和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信念中脱离出来,置身于孤独之中,只有这样才是对宗教教义的接受。孤独和离群索居被广泛地看作产生和接受本真知识的条件。所以,把社会和特定的知识放在相反两级的宗教知识观念,有长期的传统;并且我认为,这种传统通过我们外在于社会的科学观念被继承。我认为,我们无论何时谈论作为被特定的科学所限制的社会影响、我们无论何时以这种二元论者的方式思考,我们都一直在继承一种作为外在于社会和公民国家的宗教知识观念的修正版本。
凯里:所以,你试图用从事一项社会事业的方式重新描绘波义耳的肖像。
夏平:确实是这样。
凯里:这样做对你而言怎么就是显而易见的呢?
夏平:这样做,不是出于对作为知识概念的毁损,而是为了更大限度地摆脱社会与特定的知识、科学的知识之间的二元论的观念。我们想展示波义耳是如何使用他那个时代的文化材料,去制造、维持和修改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的科学知识体的。对于我们而言,社会不是从外部进入科学的一组影响。在解决被他们视为特定的知识问题中,他们把它当作一个社会秩序问题来解决。你怎样构建一组为了制造和维护知识而认同那些规则和约定的人群?它是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一个办法,同时也是解决被视为特定知识问题的一个办法。所以,社会二元论者的语言处于知识之外、进退之间,我们在描述知识的社会建制中所谋求的变革就是对这种语言的变革。知识是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方法,我们想理解知识问题的解决方法。
凯里: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波义耳是如何建立他的可信性的呢?
夏平:他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并且只取得部分的成功,因为在17世纪许多自然科学家当中——比如托马斯·霍布斯——根本不赞同这种解决知识问题的办法。但是,波义耳所使用的无论什么样的资源,就是当今科学家所使用的。他使用文学技巧,用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谦逊的目击者”的方式记录试验;他在他能弄到的公众范围内使用公众的证明去展示科学是在公共空间中被制造的。不像炼金术的知识,它不是私密地进行的,而是公开进行的——的确特别地公开,你能来并能看到在皇家学会展示的实验。并且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他利用了他个人的权威,因为他是一位极为富有的贵族,一位没有用唯利是图的诱惑去曲解真理的绅士科克伯爵的儿子。所以,某人在实验科学和靠动手做的实验科学中像波义耳那样去做,是知识权威性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象征,并且在当时被广泛地视为当然。
凯里:我想就公共与私人的问题占用你一分钟的时间。我相信霍布斯所声称的:波义耳和他朋友组建了一个私人俱乐部,他们的实验,准确地说,不是公开的。
夏平: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凯里:那么其中的关键点是什么呢?为什么波义耳所声称的是公众的和有证人的活动不被像霍布斯这样的人所接受呢?
夏平:正如我们已经谈论的,沙弗尔和我在这本书中试图去做的事情之一是展示解决知识问题办法的竞争和争论。波义耳和他的同事认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公共领域,在它上面他们可以建造一个可靠的知识体。霍布斯争辩说他们没有做到。那些人是谁?任何人都能来看那个实验吗?当时每个人都关注相关公共领域的某个见解。当时并没有大量的伦敦工匠涌入去看空气泵的演示。波义耳尝试组织的是相关的绅士公众——能够可靠地见证和证实他们所看见的哲学家们。霍布斯不是皇家学会成员,他明显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任何人都能来吗?”——指知道“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答案的人。我想任何一位该书的评论者会说,皇家学会以像豪华宾馆对外开放的同样方式对外开放。
凯里:托马斯·霍布斯和罗伯特·波义耳有很大的不同,并且双方都提出了强有力的辩论。从同时代人的立场看,一个人可能同情波义耳对不确定性的忍耐;然而与此同时,霍布斯认为,实验科学没有造成社会的一致。
通过在《利维坦和空气泵》中生动地重建他们的争论,史蒂文·夏平和西蒙·沙弗尔能够破坏科学革命作为一个简单和大一统事件的标准形象。夏平在他于1994年出版的名叫《真理社会史:17世纪英格兰的礼仪和科学》一书中,继续为撼动被认为是标准的科学观念作出努力。在其中他提出的挑战之一是这样的观念:科学是建立在普遍怀疑的基础之上的;科学家所拥有的,如波义耳的朋友约翰·洛克说的,“只有他才真正知道得那么多”。相反,史蒂文·夏平所要证明的是,科学不是依赖于系统的怀疑而是依赖于系统的信任。
夏平:关于科学的一个重大事情是,你可以从书架上获取大量的知识。你可以在相信装有各种反应物瓶子上注明它们盛有物知识的标签的基础上伸手去拿那些瓶子。你可以在拥有许多科学设备的运行知识的基础上,安全地操纵它们——如果它们有离心分离机的话,那么其运行标准就写在其标签上。在科学文献中,你可以依赖于庞大的体系,即使不是依赖所有的每一项。科学家修改知识、对知识体怀疑的真实能力,取决于他们在现场信任地接受的几乎其他每样事情。
所以,在我所做工作的各个不同部分中,我想去详细阐述科学中得到信任的财富。这种被视为一种古怪断言的对信任的强调的状况,如你指出的,是个人主义的。科学家据说是不依赖于权威的。皇家学会的座右铭是“nullius in verba”,即“不要相信权威”。许多科学革命的现代主义修辞把古代的权威与任何人都能理解的证据或者本质上任何人都能做的实验对立起来。并且他们所捕捉到的就是发生在17世纪的重要事宜;但是,我想要指出的是,建立在科学家拥有的、超过许多其他学术从业者非常多的知识稳定性的真正怀疑能力,能够被信任地采用。科学的荣誉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值得信任的活动。它建立了可靠的知识体、标准、程序、方法,这些是可以广泛地从书架上获得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当你谈论科学中信任的重要性时,你是在将科学作为一种相当独特和强有力的社会制度来加以展现。
凯里:这种信任的观念在17世纪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吗?
夏平:我想它很可能是这样的。由对被称为“学校知识”——在大学里教授的、建立在像比如亚里士多德一类权威之上的传统知识——的病理分析广泛地所构成的一个诊断是,学者、哲学家、科学人都是爱争辩的。他们就基本原理相互争吵;他们用修辞学的技巧和逻辑相互挑战。在其他事情中,被波义耳和他的同事提倡的是,在学术研究生活、特别是自然哲学研究生活中,输入了某些世俗的交谈技术、形成某种礼仪并维持某种礼仪争论的行为。所以,在我的叫《真理的社会史》的另一本书中,我尽力去争辩的事情之一是两种技术之间的关联:一方面是某人连同波义耳和他的同事在皇家学会发现的做科学的技术;另一方面是绅士地交谈的技术——当人们进入学术研究、特别是自然哲学中时,作为一种新的做事方式在他们身上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行为。
凯里:史蒂文·夏平在他的《真理社会史》一书中写道:“真理总是一种集体的优点和一种集体的成就。”在17世纪新科学的例子中,他展现了为实验发现物的可靠性提供担保的礼仪和诚实绅士的密码。罗伯特·波义耳再次是一个核心人物,一个冷静的、值得信赖的真正科学家原型。
夏平:他以一个端庄的、谦逊的、虔诚的人的形象来展现他自己,一个绝对正直的人,一个不会以谋利或者金钱为理由去歪曲真理的人。在自然哲学生活中,像罗伯特·波义耳一样的人的参与是一件极为新鲜的事情。在17世纪及其之前,学者并不是典型的绅士。我们现在还使用的词语“一个绅士和一个学者”,来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公学。波义耳也许是第一位绅士学者。结合学者生活、特别是结合科学生活的一个绅士所拥有的正直智谋,是一个相对新的事物。他个人的正直、与他是谁和人们理解他是谁相联系的正直,在很大程度上赋予科学以前所缺乏的正直气息。
所以,现在的科学家不是绅士。许多人不是先生。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不再轻易使用这样的语言。但是,作为还基本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从他或她的职业性质看不会歪曲真理的人——的现代科学家的形象,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形象。并且,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为科学欺骗的众多例子深感不安的事实,是一个重要的记号,一个我们放在作为一个正直的人的科学家身上的价值记号。
凯里:罗伯特·波义耳作为一个绅士的可信赖性,对于他的方法和他的发现的公众展示是很重要的。他是谨慎的,只公布了部分结果,因为他说其他人“恳求他要镇静”。他是明智的,对他的发现没有断言太多。并且他是可信的;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不仅被要求他要告诉真理,而且允许他自由地去做。在这个意义上,新科学建立在对存在的社会密码进行重新调动的基础之上。并且这也是为什么史蒂文·夏平反对一个科学革命的形象和为什么他能写出我在这个节目的开头所引的那个著名的句子——“没有作为科学革命这样的事情,而这是一本关于它的书。”——的一个原因。
夏平:在“没有作为科学革命这样的事情”的句子中,我试图展示的是:在17世纪所发生的,包含了与在它之前所发生的和在它之后预言发生的同样多的事情;世界不是以你打开电灯的开关的同样方式制造了现代;并且特别是,在17世纪科学中发生的许多重要改变中,有许多异质性的观点。人们在如何从事科学研究、什么是可靠的科学知识上意见不一。这就是没有作为科学革命这样的事情的含义。
凯里:史蒂文·夏平当然知道,没有像科学革命或者启蒙运动或者中世纪一类的分类手段,历史学家是不能做什么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不想被那些总是有点武断的名称所迷惑。并且,他确实成功地展示了科学革命一直是一个比它曾经被设想的更为复杂和有争论的事件。他已经证明科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系列社会性嵌入式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像早期的历史学家所说的“一种头脑的作用”。他已经据理反驳了曾经流行的把科学作为一种处在社会之外的文化形式的观点。
但是他说,他的观点一直经常地被误解。在他的观点里,这种误解的基础,是一种使科学和社会处于势不两立中的错误的二分法以及人们所持有的如下观点:如果真理是一种社会的产物,那么我们将永远也达不到对不由社会所决定的自然的理解。他持有两种观点,而不是二选一的观点。
夏平:我当然相信有独立于我们文化的、独立于我们社会秩序的、独立于我们语言的物质实在。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我相信科学家不伪造自然秩序;但同时我也相信,当我们陈述事实时,那些关于事实的陈述属于我们的文化。它们来自我们语言的约定。为了制造、修改和证明关于世界的陈述,它们被嵌入到我们的实践中。因此我相信,科学的方法、类型、所偏爱的社会制度完全被嵌入在它们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中。所以,我完全相信,有一个独立于我们思想的、独立于我们语言的世界;但是,当我们开始描述这个世界、当我们谈论这个世界时,我们是在谈论文化的存在。它们还能是什么呢?所以,当许多人听到短语“科学的社会建构”或者“知识的社会建构”或者“社会建构”时,他们就把它放在与独立于我们世界的并排的位置。我认为这不是思考那类事物的正确方式。换句话说,我认为,知识的社会建构的思想在任何方式上都不隐含有:没有一个独立于我们、给予我们感官感受的世界;没有一个。在世界中有一些东西就存在在那里。
凯里:史蒂文·夏平关于17世纪科学的书,探索了科学实现权威地位和在现代西方文明中占据信任的社会进路。在这个计划中,他谈到了罗伯特·波义耳如何借助他的社会声望和个人美德的断言,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可以信赖的权威;他描述了科学家如何采用带有僧侣式的和预言家式的、作为孤独的真理探寻者的形象;并且他也展示了这一步骤是如何作为如他说的“可靠的知识”来回应社会秩序的危机的。
但是,今天的科学又怎样呢?我问他。现在,科学在许多方面是社会机构,它有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危机吗?
夏平:历史学家会最糟糕地说,在天底下从来没有任何新的事情发生,每件事情都在以前发生了。但是,一些事情改变了,并且在这些改变的事物中,科学从过去的一种业余爱好转变成一种职业——这就带来了是否可能有科学知识的一个新危机的问题。你对业余爱好有这样的两种感觉:一种是关于召唤——你在其他语言中可以得到同样的词汇,像德语中有“beruff”,意思是“召唤”、犹如神圣的召唤;另一个是,关于业余爱好的感觉是职业的。现在大量的人为了报酬去做科学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从20世纪到现在,如其发生的,不在大学里,而是在政府实验室和工业中。所以,科学已经变得重要了。它已经被权力机构和制造财富所包围。这是科学获得巨大成功的标志。这是科学在现时代获得不断增加的影响力的标志。这是不同于罗伯特·波义耳所生活的世界的现代世界的实质性事实。
同时,那些变化的一些方面已经导致人们相信,有一个危险或者在科学知识方面将有一个危机的危险;因为如果科学家不再以真理的名义而是以默克制药公司或者辉瑞制药公司的名义说话,或者如果科学家是政府的雇员,那么什么是科学的真呢?所以,谈论科学的偏见、科学的欺骗、角色,比如科学的正义在与制药公司之间的妥协中所扮演角色,无论我们何时发出这样的言论,这些言论在报纸、电视和广播中的科学版块中确实不断增加,我们都是在从另外的观点谈论现代科学伟大成功的标志。问题是,科学共同体的信息传递有他们曾经声称具有的同样透明的正直吗?这是许多人要问的问题。我们能相信科学吗?或者当评估科学家所说的貌似有理的话时,我们不得不把他们的资金来源作为因素计入评估之中吗?
凯里:史蒂文·夏平在他最近出版的书《科学的生活:晚期现代职业道德史》中专注于这个问题。它追溯了他已经谈到的——贯穿20世纪整个过程的科学从作为召唤到作为职业——的改变。但是,他对我强调说,这本书不是一支挽歌。对科学天真无邪的失去唱挽歌,就是想恢复消耗他职业生涯第一阶段去挑战的科学革命的神话。他说,在我们可以谈论我们已经失去什么之前,首先必须小心地表述当代的情况。更早期的历史学家像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声称,科学产生了典型的“现代意识”。但是,史蒂文·夏平问,说科学创建了现代文化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呢?
夏平:从马克思·韦伯时代以后,许多评论家把科学描述为“制造了现代世界”、科学就是现代世界中典型的和最强大的文化形式。如果你查看盖洛普民意调查(Gallup polls)或者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s),你就不这样认为了。科学是受尊敬的,但科学知识的权威是有分歧的——这里说的革命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虽然不是唯一的例子。当我们谈论科学的权威时,我们不相信科学事实或科学理论已深深融入世俗文化。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它们没有做到这样。我们的意思可能是,科学观点有一些权威,人们认为科学拥有一种确保可靠的知识产生的方法,并且这是个有趣的观点,除非证据不只是外行人的;但科学家们自己对方法——科学的方法——可能是什么却有巨大的分歧。所以,我们的、关于说“科学是现代性的典型文化”的可能意思,仅留下一个谜题可以关照了;并且我愿意留下这个谜题加以关照,因为我想在我们能谈论科学和现代世界的条件下激发更多的兴趣。宗教,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有巨大的权威。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特别是在这个国家,无论宗教是否在增加它的权威,它都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宗教没有死去,宗教没有被科学杀死。尽管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的评论家都如是说,但他们错了。宗教活着并且活得很好。
凯里:宗教持续的生命力、对科学知识权威的纷争、对曾经著名的科学方法实际上是什么的详细说明的困难——这些是史蒂文·夏平称为一个“谜题”的要素。并且在他的观点中,它们是对这个谜题的解决所急需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在科学家们的掌控中。
夏平:现在我们思考科学家们的什么呢?我们思考他们与每个其他人一样是道德的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如我所建议的,当科学家们传递的是他们知道的那部分世界的知识时,我们信任科学家们并且我们没有选择只能信任科学家们,那么,我们不得不就他们是否是值得信任的人、他们在其中工作的机构是否是以正直和大公无私为特征的问题,提出一些观点。所以,我们在这儿谈的是语言的功效,并且在我的书中我认为要做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要表明,知识的权威问题没有免除那些在实在的名义下谈论个人美德的观念。它事实上也没有。我们可以对一位科学家或者一群科学家所说的有一个合理程度的怀疑,不过我们不得不把他们说的与另外一群科学家的陈述并置。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如果我们不信任一群科学家,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信任另外的一群科学家。科学作为一项按现实定义的事业,在某些意义上、但不是所有的意义上,继承了宗教的风格,而且这一点在20世纪又一次被广泛地谈论。关于它,有巨大数量的条件你要去作决定;但是正如基督教是一项按现实定义的事业一样,因此我认为,人们不得不说,科学对于我们也是一项按现实定义的事业。并且什么是科学家权威的基础的问题依然存在。
凯里:史蒂文·夏平说,今天的公民不可避免地不得不去评估科学陈述的权威性并研究那些能够帮助他的、他要思考的一些东西,以便检验那些判断。与他谈论这个问题,使我回想起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评论,大意是,文学评论家的地盘在文学之内。弗莱的大致意思是说,因为文学不说明自身,批判性的说明是文学事业的一个固有和必要的部分。我想知道,作为科学意义的一种展开的科学研究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科学之内。史蒂文·夏平以这个问题……结束我们谈话。
夏平:就个人层面而言,我的许多最有价值的对话者是科学家、反思的科学家、对科学的故事感兴趣的科学家,不仅试图对他们做的科学而且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是什么样的事业加以理解的科学家——这是第一位的事。第二,我认为当代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并没有被大量的那些科学家、特别是以英语为母语环境中的科学家所继承。元科学(Meta-science)或者反思科学性质的尝试,不是反思实践科学家通常意义上所做的或者想去做的;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我所做的工作不在科学之内。
我认为,像我自己和我的同事一样的人,在向受过良好教育的外行人讲述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机构在形塑他们生活上日益变得重要方面,已经取得很有价值的功效。这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一种教育功能。艺术史或体育社会学同艺术、音乐、体育同样重要,与所有这些方面相比,上述的事情与它们不是一回事并且非常重要。科学、技术和医学正在根本性地改变事物并形塑我们生活的结构。自有原子弹以来,通过教育,人们已经认识到,受过教育的人最好能实际地明白科学是一种什么的事情或者我们的民主社会正处于麻烦之中。这与知道许多有机化学知识并不必然地是一回事。我正在谈论的是理解:科学知识是什么类型的知识,与科学判断有关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确定性,在公共事务中科学能够起到和扮演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理解的我和我的同事作为学者在我们的学科之外确实取得的一些作用。这就是我最为渴望拥有的作用:交流的作用、教育的作用。
(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荣江译校。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责任编辑:王荣江
How to Think about Science (XVI):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Steven Shapin, David Cayley
Abstract:Steven Shapin thinks that there is a world independent of our thoughts. But when we start to represent and talk about the world, we’re talking about cultural entities in fact. In any way, science is social, which is no negation of its character of the truth. The truth also is existed in the way of nature and social. In Leviathan and the Air Pump, by recreating the controversy about the reliabilit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proposed by Thomas Hobbes and Robert Boyle, the writer challenges to the standard image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s a simple and monolithic event. Shapin continues his efforts to change the concept that the science is standard in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One of the challenges is to the idea that science stands on a foundation of universal doubts. He thinks that science is based on the trust of the system, while not the doubt. In modern society, science has become very important. It has been enfolded by power and wealth, which is a sign of the great success and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science. But this also leads people to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risk about it. Because of this,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scientific knowledge belongs to which kind of knowledge, which kind of certainty about scientific judge is, and which role science can play in public affairs.
Key words:Scientific Knowledge; Social Order; Social Construction; Scientific Culture; Scientific Risk
作者简介: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利维坦和空气泵》的作者之一,《真理社会史》和《科学的生活》的作者,2014年萨顿奖获得者。
基金项目:2013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3ZXB003);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ZX023)。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2-0198-08
收稿日期:2015-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