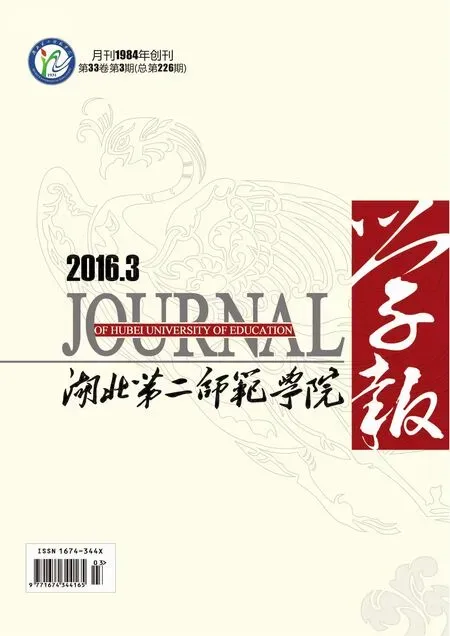墓葬“胡汉战争”叙事画像探析
高梓梅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郑州 451100)
墓葬“胡汉战争”叙事画像探析
高梓梅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郑州 451100)
摘要:近些年,山东、河南等地出土了多幅“胡汉战争”画像石、画像砖,从画像叙事的角度看,人物、地点、事件叙事元素具备;从故事情节发展看,有的选取情节高潮快达到顶点的顷刻,有的选取情节高潮刚刚达到顶点后的顷刻,最富感染力。汉代先民在“视死如生,厚葬尽孝”的观念支配下,不惜资材,将“胡汉战争”故事画像刻画于墓壁,用意在于给死者以精神的慰藉,了却对死去亲人尽孝的心愿。
关键词:墓葬; 画像; 胡汉战争; 尽孝; 保平安
一、汉墓出土的“胡汉战争”叙事画像
“胡汉战争”是汉代墓葬画像的重要题材之一,各地出土的画像砖、画像石不乏胡汉交战的激烈场面,让今人直观地看到了西汉时期汉人与北方胡人的战争场面。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 “最美好和崇高的事情总不外是征战和狩猎。”[3]18列宁说:“一切战争都是对民族使用暴力,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者赞成革命战争”。[4]3“胡汉战争”就汉王朝来说,是为了保卫边境、抗击掠夺的战争,既是暴力,也是美好和崇高,值得后人称颂。
西汉建立,北方匈奴族日益强大,特别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武力更为强盛:“兵强,控弦三十万。”[5]3275“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这个好战的游牧民族,自秦到汉不断犯边,对中国北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边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汉朝建立到武帝执政,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国家实力强盛,“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6]3928有能力对匈奴用兵。于是汉武帝决心挫败强胡,大动干戈与胡交战。“胡汉战争”进行了近五十年,旷日持久,可谓是汉代先民生活的支配现象。近几年,各地汉墓出土了多幅“胡汉战争”交战图,无声地叙说着胡汉交战的故事。
山东苍山出土的“胡汉战争”画像石中画的中央是一座桥,桥右边飞奔的战马为汉军,冲上桥梁的战车为指挥官,后边的轺车只露出马和半个车身,表明后边还有兵马。左边戴尖顶帽、拉弓的为胡兵,前边的胡兵已与汉军交上火。其中二胡兵在汉兵的猛力攻势下跪地投降。后面二胡兵正弯弓搭箭。从马的飞奔、战旗飞扬的情况看,汉军气壮山河,奋勇杀敌,势不可挡;大有挫败胡兵之势。观者似乎听到了战马的嘶鸣,将士的冲杀声和“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呼喊声。这幅画像叙事元素完整,人物为汉军、汉军指挥官、胡兵;事件为胡汉交战,辅助元素有桥梁等,它的叙事情节为:北胡犯边,汉军为御边进军杀敌;汉军战车、兵马行进在象征胡汉交界的桥梁上,与胡兵接火;冲上桥梁战车上的指挥官运筹帷幄,指挥汉军与胡兵作战;汉军战马飞奔,来势凶猛,与胡兵厮杀,有步战、骑射等;二胡兵在汉军强力攻势下败阵,跪地投降,后边的胡兵弯弓搭箭,负隅顽抗;汉军击垮胡兵,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这幅画选择的是情节高潮快达到顶点还没有到达顶点的那一刻,极富韵味。
徐州出土的是一复合场景胡汉交战叙事画像,选取的是情节高潮刚刚达到顶点后那一顷刻。画面上右下角为山包状,正中间是从山包后冲出来的汉军骑兵,前边的两汉军骑兵,一人提起长枪,一人端着长枪,看来是刚从敌阵营冲杀出来,根据画面人物的身材和所居的显要位置,这两位可能是战斗的指挥者和主将。迎面一骑兵手指身后,似乎向主将报告战况。身后一人骑的马前蹄跳起,似乎嘶鸣。画的上方右边一排四人双手被绑缚背后,向左行走,后边似乎有汉军押解。左边五人同样双手被绑缚背后呈跪姿,这些战俘是从山包后押出来的,标明这次战争已接近尾声,汉军冲破敌营取得胜利。这幅画像的叙事情节为:胡汉交战,汉军已冲进敌营;两汉军骑兵一人提起长枪,一人端着长枪,从胡军阵营冲杀出来;一骑兵冲出敌营向主将报告战况;战马嘶鸣,前蹄跳起,战斗激烈;汉军冲破敌营战胜胡兵,从山包后押解出战俘。
作为图像的叙事,仅此一个画面,不可能把战斗的全过程叙述出来,但艺术工匠匠心独运,采用复合式表达结构,再现了胡汉交战的战斗场面和战争状况,令人赞叹,具有里程碑意义。
南阳七孔桥出土“胡汉战争”画像石则是战争凯旋归来受到家乡亲人欢迎的场面:画面上正中刻一骖车,车上并排坐二人,左边可能是一主将,右边是一驾驭者。骖车前有三引领导骑,导骑辔骖驭马,后边一人回首弯弓,射击后边追击的诸骑兵,似乎战争仍在继续。画面的左边是欢迎凯旋者举行的舞乐百戏:二人吹排箫,一人吹埙,一人击铙,一人挥长袖踏鼓起舞,一人扛鼎,一人倒立等,热闹非凡。从乡亲们的欢迎状况看,这是一次正义战争,并且取得了胜利,值得欢庆。画像的叙事元素完整清晰:人物是将士、乡亲、百戏艺人,地点是河南南阳,事件是欢迎凯旋归来的将士。
除此,还有河南新野汉墓出土的“胡汉战争”画像砖、山东滕州的“胡汉战争”画像石等,无论画像石还是画像砖,大都叙事元素完整,选取的情节清晰,最富感染力。
“胡汉战争”叙事画像在全国各地频繁出土,标明“汉王朝与匈奴之间这种长期不间断的战争显而易见地给汉代艺术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艺术家们形象地把胡汉战争的题材描绘于砖石等不同的载体之上,从而创造出一幅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胡汉交战图。”[7]胡汉交战图像形象地叙说着战场上金戈铁马双方对决的残酷。在残酷的对决中,涌现出了一批英勇善战的名将,如李广、卫青等,司马迁赞叹李广“惜哉名将,天下无双。”[8]赞叹大将军卫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馀级。”[9]匈奴在霍去病的沉重打击下,发出“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捕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9]的悲叹。战争的残酷无疑给广大人民带来和平,给国家带来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因此“战争推动了历史,历史现在正以火车头的速度飞驰前进。”[10]76
二、墓葬“胡汉战争”叙事画像内涵探析
“汉画像作为墓葬的建筑材料与装饰,本身不表现汉代社会的现实生活。它不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写照,恰恰相反,它创造的是一个神鬼世界,反映了对墓主生后(在阴间)生活的理想追求,是当时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民风民俗的集中体现。”[11]80由此,战争题材刻画于墓葬,并不是像有的学者认为的是为了表现墓主人生前的战斗经历,以颂扬他的军事才能和功德;或认为不是反映墓主人生前战功,而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其一是被为了扫除升仙或进入死后世界上的障碍,其二是用来歌颂死者在‘武’的一面符合允文允武的官员典型。”[12]234笔者则认为墓室刻画战争画像内涵一是事死如生,厚葬尽孝;二是驱敌护主,保护墓主在另一世界平安。
(一)事死如生厚葬尽孝先民在“万物有灵”的观念影响下,认为人为二元结构,即躯体和灵魂。当人在阳间的气数耗尽时,就要到另一世界——阴间生存,这种观念一产生迅速盛行,到了汉代尤为炽热,先民相信灵魂不灭:“人死为鬼,有知。”这是因为亲情难舍,不愿亲人永远离去。正如《太平经》所说:“人由亲而生,得长巨焉。 见亲死去,适无复还期,其心不能须臾忘。生时日相见,受教劝,出入有可反报,到死不复得相亲,訾念其悒悒,故事之当过其生时也。”于是把死者当做生人看待,幻想出另一个世界。为了让死者在另一世界过上舒适、安稳的生活,墓室建构仿生人,随葬物品生人只要有的,死人一应俱全。“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13]极尽所能为死者建造一个如生前一样的地下家园。《汉书·霍光传》载:大将霍光死后,朝廷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壁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奏各一具,枞木列藏椁十五具”,并“发三河卒穿复士,起冢祠堂。”[14]厚葬成为一种风俗,就连贫穷的董永,父亲去世,只好卖身葬父。除了厚葬,还要为死者建祠堂按时祭祀。祭祀的意义《礼记·效特性》说得很明确:“人死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厚葬成风,祭祀也成为惯制,有节日祭,周年祭;王公贵族祭祀,下层贫民也祭祀。汉武帝时的朱买臣家贫,靠打柴为生,养活不了妻子,妻子另嫁他人,但仍然“上冢”祭祀。“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其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15]先民认为厚葬、祭祀是孝道的表现。汉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策略,褒奖孝行,并且以孝取士 ,举孝廉,“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于是孝道深入民心,发展到顶峰,出现了无以数计的孝子贤孙,厚葬炽热,陵中“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藏之。”[16]在先民看来,除了吃的用的物质用品,死者在另一世界也需要精神生活,墓壁上雕刻的画像就是让死者在另一世界欣赏故事,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了却生人对死者精神关怀的心愿,是尽孝的表现。战争军事故事刺激憾人,是工匠艺人选取绘画的主要内容,特别“胡汉战争”在汉代是具有纪念碑式的史实,是汉代现实生活的写照,艺术工匠选取刻画的画面内容,大都是故事的时间流程即将到达顶点还没有到达的“顷刻”,在复合式的叙事画面上,胡汉两军的激战场景,汉军将士杀敌擒敌的英勇,入侵者跪地缴械的狼狈,汉军获胜的趾高气扬,最能给欣赏者精神上带来快感。听故事、讲故事是人的天性,人们在说与听中得到乐趣,精神得到慰藉。就像有些人爱听战争故事一样,刻画战争故事画像的墓主人生前也许爱听战争故事,到了另一世界同样喜欢,亲人们了解墓主人生前的嗜好,在事死如生厚葬之风的影响下,不惜代价雕刻画像于墓壁;而且墓葬“胡汉战争”故事呈现的总是我胜敌败,凯旋归来的场景,战争胜利的结果是人们所向往的,给人以正能量,生者认为当墓主人欣赏画像故事时,会和生者一样心情愉悦、精神振奋,起到了世人精神享受的同等功效,尽到了孝道。因此,墓壁上刻画战争故事是生者事死如生观念的体现,更是厚葬尽孝的具体形式。
(二)驱敌护主,永保平安先民在事死如生的观念影响下,在墓室刻画胡汉战争还有扫除阴间的强敌侵犯,保护墓主平安的用意。战争是残酷的,流血、惨死,尸横遍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们惧怕战争,最不愿意看到战争。但在现实生活中战争频繁,时有发生,从西汉到东汉末,几百年间战争频繁,一是外敌犯境,边民无复宁日。二是对敌用兵旷日持久,民众深受其害。不管是外敌侵犯,还是对敌用兵,抗击侵略,给百姓带来的都是灾难和痛苦,战争残酷的阴影深深烙在先民的心灵深处,他们惧怕战争,幻想和平,渴望生活稳定。
在先民信仰中,将士、豪杰具有阳刚之气、正义的力量,不但有御敌的本领,还有辟邪的灵性。怯弱是人的本性,杀人的战争,吃人的鬼怪,(如灾异、恶人等),时时吞噬着人类的生命,在科学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人们是被吓怕了,希望那些英雄豪杰们镇邪压惊,保护人民的平安。如春节的门神先是桃符,王充《论衡·订鬼》引《山海经》记载:“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18]后是战争中将士英雄,如尉迟、敬德、张飞等,用意在于让他们把守门户,用其强悍和正义的力量驱邪逐鬼;先民赋予了他们排除消灭各种鬼怪的功能,虽然是迷信,心灵却得到了慰藉。在灵魂不灭观念的支配下,生者不愿让死去的亲人在另一世界再受战争的痛苦和鬼怪的侵扰,把取得战争胜利的画面和英雄武士们刻在墓室中,以求强盛的武装力量在另一世界消灭来犯之敌,保护墓主平安生活。战争叙事画像刻绘的位置足以证明生者的用意,如沂南北寨村汉墓胡汉战争交战图就刻在墓门横额上,画面上刻有大批手执刀、盾、矛、斧的汉朝步、骑兵;嘉祥出土的胡汉交战图刻在门楣上,画面上汉兵以排山倒海之势杀向敌人,胡兵则头断陈尸于地。徐州、南阳等地出土的战争画像中的武士则刻在墓门的石柱上等。先民之所以把具有驱敌杀敌将士绘置于墓门的关键部位,其用意正如汶河岸堤的博客中所阐释的:墓室画像中墓室主人或设计者首先考虑的是对死者的保护,其措施就是安置大量护卫和辟邪的题材。墓室的出入口和中轴线,既是死者灵魂的必经之地,也是鬼怪邪恶出入的所在,所以其正门、前室直到寝室后壁都被作为最重要的部位予以考虑。显然先民对战争叙事图像战斗场面和将士赋予了神圣意义,相信他们的强悍和正义在阳间战胜了侵略者,在阴间同样能够战胜、消灭来犯之敌,保护墓主人,使墓主人生活的世界平平安安,同时强悍的军事将领和战争中的激战场面刻画于墓门等重要位置,如同门神一样,来辟邪镇墓,驱除鬼怪,给墓主人以安定的世界,这些不惜钱财厚葬行为体现的仍是生者的孝道思想。
总之,“胡汉战争”叙事画像告诉后人,先民相信阴间是客观存在的,死去的亲人像生前一样也会面临战争,活着的人理应考虑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安定,才为尽孝。于是赋予战争题材的画像神圣意义,以作为墓主人在另一世界生存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其守卫、防范、镇邪,让墓主人生活的另一世界安定平稳,了却生者尽孝的心理愿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2]朱浒.汉画像胡汉战争图的叙事性研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3,(3) .
[3][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M].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 1997.
[4]列宁.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司马迁.史记·刘敬列传[M].北京:台海出版社,2002.
[6]班固.汉书·西域传下[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7]李卫星.两汉与西域关系在汉画中的反映[J].考古与文物论,1995,(5).
[8]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M].北京:台海出版社,2002.
[9]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M].北京:台海出版社,2002.
[10]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1]陈江风.汉画与民俗—汉画研究的历史与方法[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12]邢义田.汉代画像胡汉战争图的构成、典型与意义[C]∥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桓宽.盐铁论[C]∥诸子集成(第八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14]班固.汉书·霍光传[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15]班固.汉书·朱买臣传[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16]班固.汉书·贡禹传[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17]李卫星.伦两汉与西域关系在汉画中的反映[J].考古与文物,1995,(5).
[18]王充.论衡·订鬼[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责任编辑:胡栩鸿
马克思论战争时说:“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1]790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战争促进历史的发展,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从远古部落,到文明社会,战争不断,人类历史几乎是一部战争史。近几年各地出土了多幅汉代墓葬“胡汉战争”叙事画像,反映了汉代与北方少数民族(胡)的战争状况。从叙事的角度看,画面通过以“时间为中心的‘故事性’ 和以空间为中心的‘情景性’的营造实现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过程。”[2]构成完备的故事元素即人物、地点、事件,叙事过程清晰生动地再现了胡汉双方激烈的战斗场面及汉代先民经历战争的痛苦。先民在“视死如生,厚葬尽孝”的观念支配下,不惜资材在墓室石壁上刻画“胡汉战争”故事画像,用意在于给死者以精神慰藉,了却对死去亲人尽孝的心愿。
Probe into Descriptive Tomb Portraits of the War Between the Hu People and the Han People
GAO Zi-mei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pplied Technology, Zhengzhou 451100, China)
Abstract:Recently, several descriptive tomb portraits of the war between the Hu and the Han have been unearthed in Henan and Shand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rtrait narration, there are enough elements of characters and also narration. Furtherm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lot, some portraits choose the moment before the climax, while others choose the moment just after it, which are both very impressive. Motivated by the ideas of “seeing the dead as alive; an elaborate funeral reflecting the filial piety”, the Han people, spending a lot of money and materials, have drawn the story of the war between the Han people and the Hu people on the tomb walls to give the spiritual comfort to the deceased.
Key words:tomb; portrait; the war between the Hu people and the Han people; filial piety; ensure safety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2016)03-0039-04
作者简介:高梓梅(1954-),女,河南南阳人,教授,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
收稿日期:2016-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