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杜兰特:漫天群星,我为哪颗
毛旭
1913年夏天的哈德逊河上,一个28岁的青年坐在独木舟里艰难地向前划着,狂风暴雨大作,他不能前进一步,并且随时有翻船的可能。几天前他作别恋人,说自己需要一周的时间思考一下是否把这段关系进行下去。他爱她,但他想成为哲学家,而哲学家是不结婚的。这些日子里,他骑车250公里从纽约到了奥尔巴尼,然后又从奥尔巴尼划船回来,用疲惫来麻醉自己的忧虑。爱情与野心在争夺他的心……
上帝的天国
威尔·杜兰特于1885年11月5日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贫穷而虔诚的工人天主教家庭,后来全家搬到新泽西州的卡尼和阿灵顿。他的母亲常常祈祷上帝,不为舒适的生活,只求几个儿子中有一个能做神父。威尔在5岁的时候经常听母亲讲圣经故事,他最喜欢耶稣,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眼睛发亮,母亲则喜上眉梢,认为自己的祈祷终于有了回应。

威尔从小就崇拜英雄,他其实并不在乎基督的神性,他喜欢耶稣,因为他只身反抗世界,有勇气为真理而牺牲。因而,上帝神性的震慑并没有让他成为老实孩子。相对于上学和去教堂做礼拜,他更喜欢玩弹珠,或者和同学打架。有一次上课,老师不得不把他绑在椅子上,他却站起来在教室里到处走,椅子还粘在屁股上。11岁时,因为他玩弹珠输了,便和一个同学决斗,差点被人家打死。
在12岁步入青春期时,爱情和文学让威尔变得内向,并复苏了他的信仰。威尔喜欢上了班里的尖子生艾琳,他每天陪她回家,还送她一篮子自己采的草莓,艾琳则借给他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威尔带回家,不顾家人的反对读到了凌晨1点。读完后,他问艾琳还有没有别的书,艾琳说爸爸答应送她《大卫·科波菲尔》作圣诞礼物——圣诞节还有几个月,威尔等不及了。他攒了14美分,走了5公里路,买了本860页的《大卫·科波菲尔》。他爱上了文学,忘记了艾琳。后来艾琳出家当了修女——她始终是威尔圣洁的偶像。
卡尼教堂新来的神父穆尼喜欢威尔的敏感、好学,他应威尔母亲的请求,致力于把他培养成教会的栋梁。15岁的威尔在穆尼的安排和帮助之下进了泽西城的圣彼得学院,从此他成了家乡父老的骄傲,大家认定他会成为耶稣会修士。
圣彼得学院兼具高中和大学的职能,威尔在那儿上到22岁,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法语等等。这段时间是他一生的奠基时期。一本保留下来的读书笔记显示,他在两年左右读完了1909本书,并且曾在42天里读了48本书,都是 《罗马帝国衰亡史》那样的大部头。从19岁起,他就下定决心要写一系列的文人生平:“我要读完这些先圣的著作,然后加入他们,成为文字中的不朽者。”
此时,达尔文的进化论让他又一次信仰动摇。他从市图书馆借到了《物种起源》,看了看目录觉得没意思,准备还回去,恰巧遇到了穆尼神父。穆尼告诉他这属于教廷禁书,对信仰有害。威尔反而不打算还了,试着读了一半,接着他读了《人的来源》以及斯宾塞的著作。一时之间,他既成了无神论者,又成了社会主义者。
从圣彼得学院毕业之后,威尔对是否进神学院犹豫不决。他在报社实习了一段时间。那时媒体刚刚步入黄色新闻时代,报纸抛弃了以往的严肃,开始用大字标题报道各种骇人听闻的无聊事件来博人眼球。四周之内,威尔报道了四起奸杀案,他感到恶心,在经过一年的考虑之后,决定进入西顿霍尔大学的神学院,在那里他将被培养成耶稣会修士。信仰有其心理需求的根基,所以进化论并不能取缔威尔心中的宗教。达尔文退场了;斯宾诺莎登场。
作为神学院图书管理员的威尔在一小堆书里发现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一个异教徒的书竟会在神学院里——仿佛是伊甸园里的蛇。斯宾诺莎否定人有自由意志:如果他是对的,那么人通过自己的善行得到上帝的褒奖就是荒谬可笑的。既然连是不是自己的想法都不知道,何谈善恶?
对威尔冲击更大的是斯宾诺莎的人格。斯宾诺莎也曾在青年时期对宗教产生疑惑,但他没有掩盖什么,而是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被所有亲人朋友排斥。他诠释了“自由即除了自己什么都不想要”:朋友给他遗产,他拒绝;国王给他年俸,他拒绝;海德堡大学给他教授职位,他拒绝——他就要过忠于内心的日子。他撼动了上帝的宝座,王公贵族在他面前股栗。面对这样一个人,威尔为自己的懦弱感到羞愧。
一年半之后,他退出了神学院,开始在纽瓦克的公立小学当代课老师。为了填饱肚子,他还在纽瓦克社会科学俱乐部给人讲斯宾塞哲学。名声传到了纽约市,费勒中心邀请他来就“宗教的起源”做演讲。为了五块钱的酬金,威尔抱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信念,集中强调性在宗教起源中的作用。听众们都是些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说法让他们非常满意。然而演讲的内容却传到了教会那里,纽瓦克主教在《晚间新闻报》对威尔施行了处罚:任何天主教徒都不许与之来往,“经天使评判和圣徒判决,我们诅咒威廉·詹姆斯·杜兰特。白天诅咒他,晚上诅咒他;在他躺下的时候诅咒,站着的时候诅咒;在他出去上厕所的时候诅咒,回来的时候也诅咒”。阿灵顿教堂的神父严厉地斥责了威尔的母亲,母亲回到家后情绪失常,几乎死去;父亲把威尔赶出家门。在这些穷苦人的眼里,一个人如果不是信教人士,那他一定就是酒鬼或流氓。
摇摆不定的人最终被逐出了上帝的天国。这下他可真成了斯宾诺莎。
人间的乐园
1912年,在威尔走投无路之际,费勒中心的无政府主义者们正在进行教育方面的试验。他们以“三无”(无纪律、无考试、无成绩单)为理念开办现代学校。威尔的学识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他被雇来做学校的校长和唯一的老师,以自由主义的方式教育十来个孩子。上午,他们在教室里学习“太阳底下的一切知识”。威尔有传记方面的癖好,在教地理时,他不谈高山平原,而是讲哥伦布的冒险;讲进化论,他不解释自然选择,而是讲达尔文的生平。他惊讶于孩子们对于英雄有着和他一样的热爱,要是他结束一个故事,孩子们便会抗议,或要他再讲一个。下午他们去公园,坐在草地上学习。在公园里闲逛的人也会坐下来一起听。每当上学和放学时,孩子们有的搂他的脖子,有的抱大腿,有的拉胳膊,连家长都很嫉妒。后来,这种讲故事的习惯贯穿于他的作品之中:《哲学的故事》《世界文明史》《英雄的历史》……
教了半年之后,他在贵人阿尔登·弗里曼的资助下去欧洲旅行,由寇拉·斯蒂文森小姐代课。某天下午,寇拉带着孩子们在中央公园的草地上讲课,从公立学校逃课出来的14岁的犹太小姑娘艾达坐在不远处的长椅上唉声叹气。艾达爱读书,极其讨厌上课。她听到了草地上传来的欢声笑语,有些畏缩地慢慢向孩子们靠近,问她们在干什么。寇拉说她们在上课。第二天,艾达就转到了现代学校,成了那儿最大的孩子。
9月份,在欧洲处处留情的威尔回来了,发现班上多了艾达。她总是捣乱,破坏课堂纪律。艾达不喜欢威尔,他个头不高,只有1.65米,脸上有不少红疹,而且还总是害羞,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威尔努力讲课时,她就带头嘲笑他。
然而没过多久,爱情的魔法就起作用了。艾达发现威尔完全不同于她在贫民窟里见到的男人,他很温柔,而且有诗人气质——她爱上了威尔。她变得文静了,老师有什么需要她总是及时帮助;在院子里做游戏时,她想拥抱他,威尔批评了她。思索良久,她写了封情书表达爱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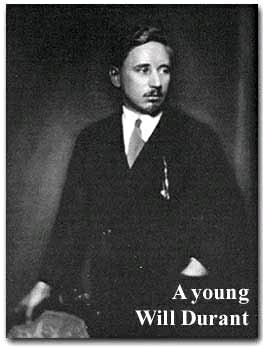
威尔也喜欢艾达,艾达是如此活泼好动,和她在一起时,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但威尔认为13岁的年龄差距是个问题,而且之前他已有独身的念头,因为他肚子里孕育着一大部史书,不知能否有时间享受家庭生活。威尔回信说他很感动,但考虑到青春期的孩子多变,他建议两人必须先等上四个月再决定是否恋爱。
然而两周之后他们就在一起卿卿我我了。在哈德逊河上犹豫了一周,威尔觉得“自己是否适合婚姻”这个问题不是思考所能解决的,然后就放手爱了。他给费勒中心的领导写信辞职,一是出于教师的道德感,二是长期当孩子王对自己的理想无所助益。
半年之后两人就结婚了。万圣节那天,艾达一手提旱冰鞋,一手抱着书(她最终要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和威尔一起到市政厅登记结了婚。出了市政厅,他们拥抱在一起,威尔念出惠特曼的《大路之歌》:“我们会彼此忠诚至生命的尽头吗?”艾达笑了。从此,艾达成了威尔的“艾丽尔”——那是威尔用莎剧《暴风雨》里兴风作浪的小精灵的名字给她起的昵称。
结婚后的四年时光,威尔由弗里曼资助,追随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博士学位,艾丽尔也跟着一起蹭课。为了支持家庭,也为了攒足钱实现自己著史的计划,从28岁起,威尔在美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夜校及夏令营讲哲学、艺术史和科学。作为听众的农民和工人只有小学水平,连苏格拉底的名字都没听说过,稍稍讲难了就使劲眨巴眼,威尔不得不避开术语,把晦涩的命题用各种实例讲清楚,这对他形成《哲学的故事》中那种语言风格是很关键的锻炼。
1922年的一个周日下午,一个叫伊曼纽尔·豪得曼—朱利叶斯的年轻人偶然间听了威尔关于柏拉图的讲座,提出要威尔整理讲稿,作为第159号小蓝皮书发行。“小蓝皮书”是伊曼纽尔印发的一种小册子,可以放在牛仔裤的后口袋里,旨在教育工人和农民。威尔答应下来之后,又写了亚里士多德、培根等共11篇。伊曼纽尔提议把这11篇结集成书出版,由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1926年《哲学的故事》诞生,西蒙-舒斯特公司很快也发展成为世界四大英语出版社之一。
《哲学的故事》是披着传记外衣的哲学史,一经发行就登上了畅销书榜首,威尔从此成为国际知名的作家。《哲学的故事》在1929年引入中国,目前有至少6种汉译本。根据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统计,此书出版后,馆内哲学类书籍的流通量上升了7倍。书中的11章每篇都十分精彩,“两斯”(斯宾诺莎和斯宾塞)的两章尤为重要,是打开威尔哲学观和政治观大门的“芝麻”。
女儿艾瑟尔出生时,艾丽尔21岁,威尔34岁。艾丽尔由于怀孕期间营养过剩导致难产,差点死去。结婚以来威尔的家庭生活是非常幸福的。33岁,他开着新买的敞篷车,载着艾丽尔回阿灵顿,父母立刻原谅了他。他和艾丽尔感情甚笃,虽然出门在外讲学,但每天必一封信。为了排遣孤寂,艾丽尔每天晚上哄孩子睡下之后,读书到凌晨两三点,后来还在刚兴起的格林威治村开了家沙龙餐馆招待艺术家。不过日久天长终不是办法,嫌疑和猜忌偶在滋生。艾丽尔怀疑威尔长期在外能否保持忠诚,而威尔也对艾丽尔把几千元借给那些从不还钱的画家们耿耿于怀。他们的矛盾在1929年达到顶峰,甚至一度想到离婚。好在威尔温柔,艾丽尔明理,两人总是开诚交流,而且幸运的是,在这一年,威尔的资金终于攒足,“文明工厂”开工了,机器的轰鸣声盖过了夫妻的争吵——威尔压缩在外讲学的时间,开始了《世界文明史》的写作,婚姻也得到了拯救。
历史的星空

威尔认为自己是作为哲学家在写史,在他眼里,历史是“举例子的哲学”。威尔想做第一个写“完整历史”的人。早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他就在课堂上对“完整历史”做出了阐释。他为同学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伯里克利带着情妇阿斯帕西娅和友人苏格拉底一起去看戏。这里就涉及政治、哲学、经济、风俗(两性关系)、艺术、建筑(舞台的建设)等等。以往的历史学家只关注政治和经济,而威尔想写一部政治、历史搭台,哲学、文艺唱戏,社会风俗伴奏的全体历史。东西方史学家都喜欢描写枭雄们的战争和政坛角逐,而在威尔这里,理论天才(哲学家和艺术家)的地位高于实践天才(政治家和军事家)。这是一种古代文人自豪感的复苏,正如贺拉斯所说过的:在阿伽门农之前也有很多伟大的将军,但他们没有荷马。不朽的不是帝王的业绩,而是诗人的笔触。
威尔写作原初的计划是五部分:亚洲、古希腊和古罗马、中世纪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到现代。朋友阿道夫·克罗赫建议他只写一卷,因为没有人会花钱买任何五卷的东西。威尔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于是写了11卷,每一卷都比《三国演义》还厚。那些赌咒发誓只买一卷的读者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契诃夫吃煎饼的境地:“发面煎饼真是太好吃了,你拿起一张吃下去,鬼知道怎么回事,第二张就自动钻到你嘴里去了。”
不难想象,威尔的后半生是平淡无趣的,他把时间几乎全部给了历史写作。
45岁—50岁:《东方的遗产》;50岁—55岁:《希腊的生活》;55岁—60岁:《凯撒与基督》;60岁—65岁:《信仰的时代》;65岁—68岁:《文艺复兴》;68岁—72岁:《宗教改革》;72岁—80岁:理性时代三部曲(《理性开始时代》《路易十四时代》《伏尔泰时代》);80岁—82岁:《卢梭与大革命》;85岁—90岁:《拿破仑时代》。原先计划中“拿破仑之后的世界”最终没能完成。
《东方的遗产》的准备工作最多,因为东方——尤其是包括中国和日本的远东——并不在威尔以往的知识领域之内。所以,1930年1月11日,他带着艾丽尔和女儿一起去做环球旅行。3月11日到达中国,在胡适的陪同下游览上海。他评价说中国人是最世俗的民族,他们供奉成百上千个神,但骨子里还是无神论者。他们没有上帝的震慑,却能靠孔子的学说维持伦理道德。他预言不久之后中国会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
回国之后,他立马投入了《东方的遗产》的写作。这11卷书的写作流程是这样的:首先读书,在纸片上做笔记,每一卷能用掉3000张纸片。然后是分类。这是最费工夫的活儿,威尔撰写好大纲、每一章的大标题和小标题,然后对成堆的纸片进行分类。这项工作一开始由他自己来做,后来开始交给艾丽尔和秘书来做。第三步,在家里写第一稿,因为在家里参考资料可以随手拿到,书房的大桌子上铺着字典、参考书、分好类的纸片以及带壳的花生。第四步,到目标地点旅行,把第一稿带在身边,写第二稿——把初稿一段一段地全部重写一遍,目的是把风格和修辞加进去,工作地点是火车、汽车、飞机、轮船……再后是第三稿,用打字机打印出来。最后交给出版商,校对,把旅行时拍下的图片插进去。

《东方的遗产》由威尔全权负责。有一次他在火车上给纸片分类,一个好奇的乘务员从背后看到日本哲学的内容,问道:“你读过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吗?”“没读过,”威尔回答,“但我写过。”乘务员快步走开了,告诉同事杜兰特是个和纸片坐在一起的学术怪物。
《东方的遗产》是本让人大开眼界的必读书。原始部落的风俗伦理各异,读者不得不对自己旧有的观念做出反思:比如女性的贞洁(菲律宾的有些部落非常嫌弃处女,新郎在结婚当天专门雇人来替他抢夺新娘的童贞),男性的忠诚(在赤道非洲,如果一个男人不肯讨小老婆,他妻子就会骂他是小气鬼),审美观(在尼日利亚,最完美的女人是胖得走不动、要骆驼驮的女性),等等。
《希腊的生活》和《凯撒与基督》受到诺贝尔奖得主梅特林克的盛赞,他说威尔仿佛在那个时代生活过一样。那些英雄们的传奇是有趣的,但最有趣的还是当时的风俗,比如尼禄皇帝的情人波帕埃娅发现驴奶可以养颜,“无论她旅行到何处,都有驴子跟着,有时她赶着一大群驴”。
在写作《信仰的时代》的过程中,发生了杜兰特夫妇一生中最激烈的争吵。艾丽尔想搬回纽约(他们此时定居在洛杉矶),因为那儿有热闹的格林威治村。威尔想不通交友怎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不过,这并不是意味着他们的感情有了裂痕,相反,他们越往后感情越深。如果威尔在家,那么他一定等艾丽尔一起入睡;如果他出门在外,他就每天订花让人给艾丽尔送去,附信常常是“每天必须听到你的声音,否则生命没有意义”“我爱你比结婚时加深了100倍”“我终于相信婚姻可以是幸福的”。说这话时,他已经66岁了。
《理性开始时代》标志着杜兰特夫妇的首次合作。1956年,宅文化最终战胜了社交文化。58岁的艾丽尔愿意安定下来了,她在给威尔的信中引用老子对孔子说的话,“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并把这句话解读为:只有语言的世界才能使人不朽。艾丽尔也开始参与稿子的撰写,尤其在威尔犯高血压的时候,她能在他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下去。威尔比较理性,喜欢撰写哲学家;艾丽尔比较感性,负责写著名的女性和沙龙文化。最后文章的润色工作仍由威尔负责。
由于留声机和收音机的出现,他们更少外出参加音乐会和聚会,除了到目标地点做旅行考察,基本都宅在家里。威尔在二楼每天工作10小时,艾丽尔占据着一楼。威尔从18岁起就是素食主义者,艾丽尔为他准备好早餐之后,到姐妹家去吃,回来之后应答各种信件。中午她和威尔一起吃简单的素餐。威尔午睡一小时,醒后到花园劳作到3点,作为身体锻炼,然后继续工作。6点吃晚饭,饭后他和艾丽尔比对各自的读书笔记。
《理性开始时代》的书评是最友好的,然而紧接的《路易十四时代》却是最受打击的一部。剑桥大学的历史教授普拉姆把整套《世界文明史》贬得一文不值,理由是:不重视当代学者的成果;科学和哲学都被人格化了,历史降格为一群传记的集合。威尔做出回应:在枯燥的学术领域中数据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而我们则只对人感兴趣。
1966年,威尔夫妇认为自己来日无多了,于是就此打住,把《卢梭与大革命》作为最后一部。然后,应读者的问询“你们从历史研究中学到了什么”,他们用一年的时间写了《历史的教训》一书,探讨“哪种政府最好”“历史是否真的有进步”等话题。
然而死神未能如约而至,于是他们靠读书和写闲文为乐。最后,被解放的囚犯眷恋当年的锁链,他们又一次开启“文明的车床”,在85岁和72岁的年龄上开始了5年工程的《拿破仑时代》。

1981年,威尔96岁,艾丽尔83岁,仍在忙着写最后一本书《英雄的历史》。这年秋天,威尔心脏病发作入院,艾丽尔由于之前中过风,所以留在家里。她觉得威尔此去肯定回不来了,就拒绝进食,于10月25日去世。威尔的手术很成功。女儿和孙女都对威尔瞒着艾丽尔的死讯,但他还是从电视新闻中知道了艾丽尔去世的消息,几天后他也辞世了。
威尔·杜兰特是个绅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很随和,他经常教育孩子要做到“外表谦和,内心骄傲”。如此庞大的《世界文明史》,不可能由一个没有雄心的人来完成。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有幸听到上帝的召唤,从而拥有一种使命感;上帝的使徒们往往被剥夺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就这点来看,威尔能拥有艾丽尔,实在是最幸运的。
“在那个时代里,伟大的人物似乎都已倒下,而叔本华再次举起英雄崇拜的大旗……他也成功地跻身英雄的行列。”这是《哲学的故事》第七章的最后一句——威尔也是在夫子自道吧。东西方都相信世间的豪杰本属天上的星辰,所以我们这样总结威尔的一生:“把崇敬留给天上的星星,把信仰还给星空之上的神明,对人间则报以温情的微笑。”
我们为历史牺牲得越多,离死亡就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