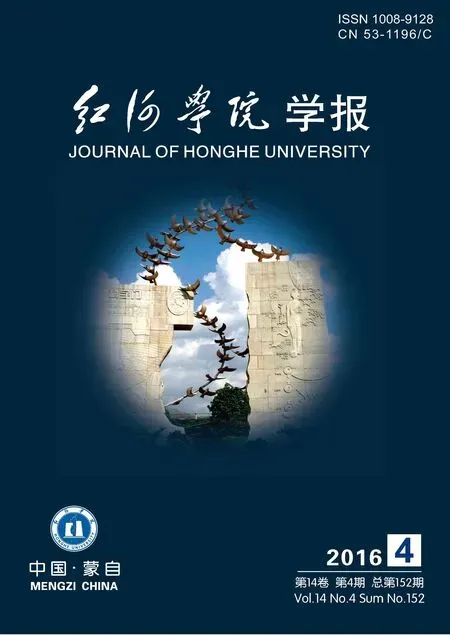云南少数民族民间乐舞的艺术人类学诠释——以哈尼族、彝族乐作舞为例
胡益凡
(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昆明 650500)
云南少数民族民间乐舞的艺术人类学诠释——以哈尼族、彝族乐作舞为例
胡益凡
(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昆明 650500)
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拓展和深化了少数民族民间乐舞理论的研究视野、理论范式以及研究方法,对于高速变迁、消亡的各少数民族民间乐舞文化研究至关重要。文章以艺术人类学为学理基础,以哈尼族、彝族乐作舞为研究个案,在深入民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整合了云南少数民族民间乐舞的普遍现象,记录个案的文化变迁现状,探索民间乐舞与周遭文化因子的内在关联,多视角剖析民间乐舞的文化内涵。
少数民族;民间乐舞;艺术人类学;乐作舞
DOI:10.13963/j.cnki.hhuxb.2016.04.003
一 问题的背景
“跨越了千年历史的波涛,作为‘人类活态文化财产’的中华民族民间乐舞文化,一直在传承、创新、发展着。它以一种可视的、活态的、动态的、运动着的非物质的‘活的文物’,展现着各民族祖先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1]各民族民间乐舞以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喜闻乐见的内容形式、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与节日庆典、宗教仪式紧密的依存关系,体现了民族传统、民族文化、民族历史,反映了民族心理、民族信仰、民族理想,在各民族文化体系中举足轻重,在各民族人民生活中意义悠长。然而,强势文化、现代文化的深入冲击,让各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举步维艰,部分民间乐舞面临着流失和消亡的危机。近年来,政府通过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文化艺术进行保护,虽取得了进展,但情况仍不容乐观。
云南是一个民族大省,古往今来,各民族人民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创造了璀璨富饶的民族文化。傣族“孔雀舞”、佤族“木鼓舞”、彝族“烟盒舞”、哈尼族“棕扇舞”、藏族“锅庄”、景颇族“目瑙纵歌”、傈僳族“阿尺目刮”、普米族“搓蹉”等少数民族民间乐舞成为维系和深化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精神纽带;是世界民族文化舞台上不可比拟和复制的艺术瑰宝;是我们建立民族自信,走向文化复兴之路的重要基石。随着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强省”宏伟目标的实施,商业运作和文化投资将传统文化纳入生产资料中,文化产业运动也随之兴盛。《云南映象》、《丽水金沙》、《印象丽江》等成为云南最为响亮的文化品牌,杨丽萍、李怀秀等名人符号让云南各民族民间乐舞愈加辉煌。但是,据葛树荣参照1981年11月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对比20年后云南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现状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时入卷的 24 个民族(回族、满族未收集到民族舞)的183个舞种/节目,现在有的已经消失,有的长期没有活动,有的流传范围逐渐缩小,有的不断扩大,有的发生了明显变化。与当时的入卷数相比,现存舞蹈有 168个,消失了 15 个。”[2]
在传统与现代、停滞与发展的矛盾中,少数民族民间乐舞文化逐渐流失、消亡,“非遗”的保护、传承以及艺术实践也陷入了原地打转甚至误入歧途的境地。如何做到对少数民族民间乐舞文化有深刻的认识、有自知之明,如何在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浪潮中掌握自主权利,尚显稚嫩的少数民族民间乐舞学理建设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通过对人性普同性和文化多样性的系统探索,考察人类文化的起源与变迁,解释人类自身及其文化的异同。近年来,运用人类学学理研究艺术,成为诸多学者的共识,进而引申出艺术人类学这一学术研究倾向。在艺术人类学的视野下,人们更多地关注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方法,强调整体性、语境性的研究倾向以及局内人视野和平等主义立场。我们在面对传统少数民族民间乐舞时,不再仅关注其本身的动作、动律、队形等形式的记录和探索,或是对其功能、意义的研讨。而是将其反置于整体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它与人类,以及与人类的文化、历史、社会、生活、情感、心理的错综关系。[3]概括而言,艺术人类学研究视角的引入,将拓展和深化少数民族民间乐舞理论的研究视野,补充理论范式,完善研究方法,对于高速变迁、消亡的各少数民族民间乐舞文化研究至关重要。本文以艺术人类学为学理基础,以哈尼族、彝族乐作舞为研
二 哈尼族、彝族乐作舞概述
乐作舞集歌、舞、乐为一体,是由红河哈尼族、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历史悠久、流行广泛、影响深远的传统民间乐舞。同属古代氐羌人后裔的哈尼族、彝族部分先民于汉、唐时期迁入滇南哀牢山地区,经过艰辛漫长的迁徙和数千年历史进程逐步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力及丰富文化内涵的乐作舞文化。乐作舞无人数、地点、时间限制,围圈起舞是它原始基因的重要标志。乐作舞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绿春、元阳、金平等县均有跳乐作舞的传统,且呈现出不同风貌。2008年6月,哈尼族、彝族乐作舞被收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红河县隶属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南部,红河流域中游南岸,横断山脉纵谷区南端,被哀牢山脉盘踞全境。2006年5月,云南省政府认定红河县为“乐作舞之乡”并进入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11月,红河县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称号。乐作舞作为红河县的“县舞”,多次在全国各地及美国、法国、日本等进行展演交流,“红河乐作”已然成为红河县的标志性符号。基于此,本文遂以红河县哈尼族、彝族乐作舞为田野视角。
红河哈尼族和彝族跳乐作舞的历史由来久远。作为文化持有者,两个民族在对乐作舞概念的界定上习惯统称“乐作”,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认同。作为局外人的文化研究者亦是如此。首先,“乐作”是当地汉族根据哈尼族“拢纵撮”的音译。随着汉文化的深入影响,汉语得到普及,“拢纵”的发音逐渐音变为“罗作”“乐作”,之后在频繁的文化交流和推广过程中,“乐作”得到了广泛认同。其次,乐作舞的概念界定。《红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一书对哈尼族乐作舞和彝族乐作舞的套路进行了明确的表述:哈尼族乐作舞以“腊瑟”(踩荞)、“拢纵”(撵调)、“诺比”(斗脚)“瑟然”(找对象)四个套路为主;彝族乐作舞则以“踩荞”“撵调”“斗脚”“三步弦”“经线”“找对象”“擦背”“游调”“翻身”“摸螺蛳”十个套路为主。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辞典》和《哈尼族百年实录》则认为乐作舞并非单纯特指乐作舞套路,而是一个大的舞蹈体系。此外,对于乐作舞的起源,哈尼族和彝族也持不同看法。《哈尼族民间舞蹈》中记载:“哈尼族聚居区的群众认为乐作舞是哈尼先民传下来的。根据有二:1、乐作舞中有一个动作叫“龙泽登”,是因为过去思陀土司第二十六代祖先的名字叫‘龙泽’而得名。2、在过去,哈尼族以种苦荞为主粮……现今的哈尼族乐作舞还被称作‘阿腊磋’,意思正是‘得吃荞子,高兴跳起来’。然而,哈尼族、彝族杂居地区的群众则认为哈尼人跳的乐作舞是从彝族那里学来的,其依据是哈尼族乐作舞与彝族的非常相似。”这一记述恰好体现了哈尼族、彝族乐作舞相互独立又交融相生的文化现象。但是,据阿扎河乡老艺人的讲述,乐作舞产生于红河县阿扎河乡垤施、洛孟的彝族部落,是彝族先民生产生活的模拟和有形记录,由最初的“踩荞”“撵调”舞步发展成为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乐作舞。[4]
三 哈尼族、彝族乐作舞的艺术人类学诠释
笔者在2014年至2015年多次赶赴红河县阿扎河乡垤施上寨村(大部分居民为彝族)、甲寅乡甲寅村(哈尼族占总人口的85%)及周边乡镇走访、调查了哈尼族、彝族乐作舞,对乐作舞所具备的原始性、功利性、群体性、交融性等云南少数民族民间乐舞的普同性进行了整合分析,从表现内容、呈现方式、功能意义、传承主体结构等方面记录了乐作舞的重构变迁,通过反思“非遗”保护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来阐释“文化自觉”对于云南少数民族民间乐舞传承保护的重要意义。
(一)彰显的生命秩序
少数民族民间乐舞,是各民族人民的生存本能在生活中的艺术表达方式,作为一种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文化形态,它充溢着旺盛的生命力,有着无可替代的生活价值和生命意义。“围圈起舞,连袂踏歌”是史前先民生活情境和意识行为的珍贵记忆,也成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舞蹈的共性特征之一,它透视出古老的氐羌民族从游牧向农牧生活的转化过程。[5]红河哈尼族、彝族同属藏缅语族彝语支,学界多数认同他们是由古代氐羌民族与云南土著民族融合发展而来。乐作舞继承了这一遗风,舞时,手拉手,面对面,共向圆心,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统一的节奏,和谐的流动,踏歌而舞。舞群将个体整合形成强大的集体能量,意识的高度统一造就了稳定的整体。而这种群体的感应力,让孤独的个体获得归属,释放激情,也为社会的秩序、和谐构建了基础。格罗塞曾在《艺术的起源》中感慨“再没有别的艺术行为能像舞蹈那样转移和激动一切人类”,他认为传统舞蹈能够团结、激励人类,具有“统一社会的感染力”。
哈尼族、彝族乐作舞在“大分散、小聚居”的文化生境中独立生长,将沉淀着生活、情感、行为之类复杂的信息以“身体体验”的方式孕育;又安置于两个民族和谐交融的文化生态中,造就了“和而不同”“多元统一”的独特民间乐舞文化;在共同的文化认同、平等的交流借鉴、近似的行为喜好中确立了哈尼族、彝族共同的价值取向,促进了地区民族文化核心凝聚力的构建。红河哈尼族和彝族长期以来保持着稳定、频繁的交往,同源血脉的呼唤让这现象更易产生,生活的互动,文化的交融,逐渐显现了两个民族的民间文化共性。“摸螺蛳”是乐作舞中极具哈尼风格的舞蹈套路,来源于哈尼族的劳动生活中,其中探身、拔泥、摸螺蛳等动作将收集食材的场景精妙再现。而这一套路被应用于传统彝族乐作舞中,其动力腿向上勾抬,重心向下的态势与彝族多强调踮步、重拍向上的风格显得格格不入,却被彝族乐作舞人生动表现,广泛认同。无独有偶,甲寅乡哈尼族所跳乐作舞包括“三步弦”“五步弦”“勾脚舞”和“瑟然”四个套路,其中“五步弦”的主体动作与阿扎河乡乐作舞中的“游调”基本相同。此外,红河县甲寅乡和阿扎河乡群众所跳的乐作舞还存在诸多共性,如“三步弦”皆是以撵步为主体动作、都采用了“三”的节奏单位等。[6]53-54其实,这共生、共融、共流的云南各少数民族民间乐舞,印证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也为我们探索民间文化的内涵真谛、价值意义谓以佐证。
(二)记忆的发展变迁
云南各民族先民在漫长的寻求生存和发展出路的征途中,在不断迁徙、愈加频繁的交流融合中创造了今天各具特色、灿烂多姿的民族文化,虽饱经沧桑,仍充满勃勃生机。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负载着人们价值取向、影响着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传统文化基因依然在各民族社会中嵌刻珍藏。然而,时代变迁的巨大浪潮推动着非物质文明由内而外的深度变革,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在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变迁。
在乐作舞的产生阶段,红河县哈尼族、彝族还处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下,生产力水平较低,劳动力严重不足,靠种植水稻、荞等维持基本生活。出于对日月嬗递、季节迁移、洪水滔天、山崩地裂的畏惧无知,亦或是生活中的“意外关照”,大地山川、日月星辰、云雨草木等都成了哈尼先人崇拜敬仰的“神”。[7]哈尼族乐作舞一招一式中总能体现出人们对五谷丰登、人丁兴旺的殷切祈盼。相传,哈尼族、彝族乐作舞是在“撵调”、“踩荞”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此时还没有固定的呈现媒介和活动场合。“撵调”是人们农闲时分自我休闲的极好方式,在嬉戏、逗乐中缓解劳作疲惫。“踩荞”是人们对生产生活的模拟再现和美化提炼,它以一种轻松愉悦的方式让经验得到传承。
随着哈尼族、彝族生产方式出现质的进步,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随之而来便是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迫切需求。乐作舞文化渐成体系,进入了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时期。这一阶段,乐作舞表现出了以下特性:1、呈现组织性。人们在传统节日、婚丧仪式中展现乐作舞,丰富的平台推广促进了乐作舞结构的完善和组织的构成;2、功能复合性。此时的乐作舞已经应用于祭祀先祖、缅怀亡灵、驱邪祛病、庆贺丰收、喜迎节日、自娱娱人、凝聚人心等多个层面,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3、文化独立性。哈尼族和彝族以及各个村寨在同一个母文化系统下建构了拥有各自独立完整套路、动作、风格、功能特征的乐作舞文化系统。
近年来,乐作舞所依附的传统文化场域面临消失,人们对于传统乐作舞实用意义的追求逐渐淡化。而文化自觉意识的普及,让不同领域开始关注传统文化流失危机,并不断地投入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工作中。在当地政府的倡导下,红河地区旅游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乐作舞成为旅游展演重要项目。经济的刺激,行为的认同,为哈尼族、彝族乐作舞的传承、保护提供了必要支持,也选择了一条发展之路。云南省各高校舞蹈院(系)将乐作舞纳入课程,专业教师在田野采风的基础上对乐作舞元素进行提炼、加工、整理编创成教学组合,传统民间乐作舞的传承主体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迁。此外,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当下乐作舞最为重要的功能之一。由群众自发和政府组织的文体活动中有来自各个村寨文艺队的乐作舞表演,“和而不同”的动作套路促进了各民族、村寨间的相互交流。成为国家级“非遗”以来,乐作舞作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乃至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代表与各个国家、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增进了相互的友谊和了解,为长久的合作、共赢建构媒介。
(三)亟需的文化自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步开展以来,红河县政府以推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发展、建设为根本目的开展了一系列的挖掘、整理、普查和展演活动。自2013年便开始对红河县“非遗”保护项目进行系统、集中地发掘记载,于2014年6月出版了《红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开创了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新方法。2014年,红河县广播电视局和文化体育局对全县11个乡镇的乐作舞进行普查,全面收录了红河县境内哈尼族、彝族乐作舞的相关资料,并以文字、视频等形式进行保存,进一步完善了乐作舞的数据信息。自2011年,逢哈尼族“十月年”期间,红河县都要举办“红河乐作”的展演活动,届时红河县各乡镇哈尼族演出代表队齐聚一堂,精彩的表演吸引了八方游客,也推动了乐作舞文化的广泛传播。[6]71-72
近年来,“非遗”保护工作在我国政府的主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通过一整套的法律体系和相关工作机制逐步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和支持。然而,一些问题的出现也让保护工作陷入两难:政府至今未能设立统一的领导部门,导致许多工作分工不明、责任不清;目标和利益的差异也致使各级政府、文化持有者、商业资本以及社会职能部门的相互博弈,如何协调好各方矛盾,成为保护工作中不得不重视的问题;政府的强势地位导致“非遗”保护成为某些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主观意志的横行以及不切实际保护手段的实施,反致“非遗”遭到极大破坏;[8]地方群众(文化持有者)按照政府的决策行事,却只能在保护成果中得到可怜的一点收益,本拥有对自己文化的绝对解释权,可是在被保护之后成了名义上的主人,极大的反差和“彻底的失语”导致群众文化自觉意识的淡漠消失,他们甚至希望挣脱这一传统文化“枷锁”,学习一门新的文化,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权。[9]红河县民族文化传习馆(乐作舞传习所)馆长吴志明对云南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前景表示忧虑,他希望“无论是政府、学者、媒体还是个人,对于传统民间文化的关注应更多地出于尊重,一味地考虑功利只会误入歧途”。
云南各少数民族民间乐舞用“人的身体”承载了各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记忆”,它的传承和发展从未真正停止过。强势的干预和要求是否真的能够化解传统文化的尴尬局面?若将其送回民众生活中,把工作重心放在唤醒人们的文化自觉意识上,一旦人们自觉、自愿、自然的参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许多问题或许就迎刃而解了。
[1]罗银伟.少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探索——浅析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非遗进校园”[J].大舞台,2011 (12):197-198.
[2]葛树蓉.云南民间舞蹈现状调查报告[J].民族艺术研究,2010(4):9-16.
[3]李修建.论艺术人类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4(4):20-26.
[4]殷志勇.乐作舞之乡[N/OL].云南日报,2013-06-02(7)[2015-05-13],http://yndaily.yunnan.cn/html/2013-06/02/2content_?11923.htm?div=0.
[5]贾安林.“篝火之舞”与“连袂踏歌”——藏缅语族圈舞文化特征和功能[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5(2):60-64.
[6]周庆.红河县哈尼族彝族乐作舞研究[D].昆明:云南艺术学院,2015.
[7]胡益凡,李生福.哈尼族地鼓舞的文化渊源与风格特点[J].青年作家,2015(8):75-76.
[8]李富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自觉——对于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反思[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1(12):37-41.
[9]方李莉.谁拥有文化解释的权力?[J]. 艺术评论,2005(8):4-9.
[责任编辑 龙倮贵]
Interpretation of Art Anthropology Minority Folk Dance in Yunnan——Hani, Yi dance music as an Example
HU Yi-fan
(School of Dance, Yunnan Institute of Arts, Kunming 650500, China)
Art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expand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field,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research methods Minority Folk music and dance theory, the speed changes, the demise of the vital research folk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dance. In this paper, art anthropology theoretical basis, Hani, Yi dance music as a case study, in-depth fieldwork civil analyzed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Yunnan folk music and dance with Cape phenomenon, recording the status quo cultural changes of the case, Folk music and dance to explore the intrinsic association with the surrounding cultural factors, multi-angle analysis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folk music and dance.
Ethnic Folk; Dance Art Anthropology; Music for dance
J722
A
1008-9128(2016)04-0008-04
2015-09-28
胡益凡(1991-),男,河南周口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究个案,在深入民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整合了云南少数民族民间乐舞的普同现象,记录个案的文化变迁现状,探索民间乐舞与周遭文化因子的内在关联,多视角剖析民间乐舞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