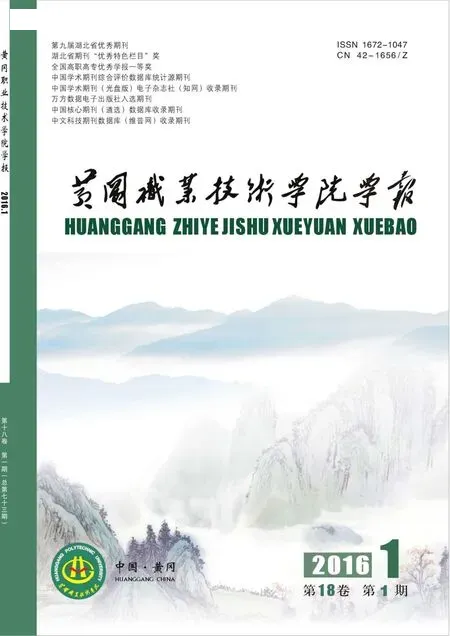超然物外:苏轼人生思考成熟的标志
王启鹏
(惠州学院 中文系, 广东 惠州 516007)
超然物外:苏轼人生思考成熟的标志
王启鹏
(惠州学院 中文系, 广东 惠州 516007)
摘 要:苏轼是个智者,他从小就对人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他青少年开始直至密州任上提出超然物外思想为止,分析研究他在各个时期对人生思考的言论和行动,得出了“超然思想的提出是他人生思考成熟的标志”的结论。文章还阐述了超然思想对于认识人生的作用。
关键词:苏轼;人生思考;超然物外;寓意于物;思想成熟
王水照、崔铭两先生合著的《苏轼传》书名冠以“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这就道出了苏轼的一大特点:智者。这个评价十分确切而又非常有意思。所谓“智者”,就是指有智慧的人,或是说智力超常的人。这些人对许多问题都有独特的见解,而苏轼确实是这样。
据《宋史苏轼本传》记载:“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轼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1]2828可见苏轼从小就是一个智力超常、不同于一般人的人。用现代话语来说,苏轼是一个思维早熟的人,他在少年时期的思维就非常活跃,知道许多令成年人都未能弄清楚的事情,尤其是他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也显得很老成,很有特色。至“超然物外”思想(简称为超然思想)的提出,已显出其思考的成熟,贬居黄州时期更促使其包罗万象、海纳百川思想特色的形成。
一、苏轼在青年时期就不断地探索人生
苏轼之所以会在青少年时期就不断地探索人生,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关,正如他在《密州谢上表》中所说的“臣家世至寒”。苏轼自小生活在农村,经历过“少年辛苦事犁耕”(《野人庐》)的生活,遭受过“小人自疏阔”(《答任师中家汉公》)的冷遇,目睹了“野人喑哑遭欺谩”(《和子由蚕市》)的凄惨情景,所以,他对贫民百姓的生活出路就一直关注。表现得最为集中的是,嘉祐四年(1059)十月,在家服母丧后启程还朝,父子三人一起坐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凡与耳目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其中苏轼的好些诗文就是和人生联系起来的。如《夜泊牛口》诗就最为典型:
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煮蔬为夜飧,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儿女自咿呦,亦足乐且久。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1]9。
苏轼看见山中居民的生活虽然清贫,但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显然是“足乐且久”的;而自己呢,却要为生活而“汲汲强奔走”。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所以,为了追求“富贵”的生活,就要劳碌奔波了。
进入忠州地域,苏轼看见屈原塔。苏轼认为:“在忠州,原不当有碑塔于此,意者后人追思,故为作之。”他想到了屈原的为人,想到了屈原的死,最后认为:“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屈原塔》)[1]23在这里,苏轼对“名声”与“富贵”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名声”是长久的,而“富贵”是短暂的。
走出了黄牛峡,也就是走出了长江三峡的激流险滩,苏轼又发一通议论:“入峡喜巉岩,出峡爱平旷。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出峡》)[1]23走完了长江,到达浰阳时,苏轼好像要对自己旅行心得来个总结似的写道:“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嚣嚣好名心,嗟我岂独无。不能便退缩,但使进少徐。”(《浰阳早发》)[1]70苏轼自己也承认,“富贵本无定”的,但自己也免不了世俗,还是要去追求的,只不过不要太疯狂就是了。
这是苏轼尚未进入仕途时对人生思考的第一阶段。
二、入仕后对人生的思考
嘉祐五年(1060)二月,苏氏父子三人抵达京师。苏轼授河南福昌县主簿,不赴。与弟苏辙寓居怀远驿攻读,准备参加制科考试。这时,苏轼献《进策》和《进论》各25篇,应制科试,取为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十一月前往赴任。
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从小在一起玩耍,一起读书,形影不离,感情十分深厚。现在两人要分开了,自然不习惯,显得十分痛苦和无奈,所以子由要送他去赴任。当送到郑州,刚出西门作别时,苏轼的内心就十分痛苦,在《辛丑十一月十九日……》诗中说:“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1]96当苏轼一个人来到当年他们赴京应举曾住过的渑池时,看见接待过他们的老僧已经死了,曾经题过诗的墙壁也已经损坏了,于是感慨万分。当接到弟弟的《怀渑池寄子瞻兄》诗后,马上和诗《和子由渑池怀旧》一首: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1]97。
从苏轼的这2首送别诗我们就可以看到,苏轼对人生确实有独到的认识。他把人生比作“飞鸿踏雪泥”,这是非常形象而又深刻的。既然人生在世只不过是“偶然留指爪”,所以就应该“慎勿苦爱高官职”了。两人尚未正式为官,就相约早退,共为闲居之乐了。
苏轼到了凤翔履行人生的第一次任职,有幸看到了凤翔的8件宝物,当他看到了仰望已久的周朝石鼓时,忍不住写道:“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1]105由眼前的石鼓想到时代的变迁,再想到人生。他在给子由的和诗中亦说:“薄宦驱我西,远别不容惜。方愁后会远,未暇忧岁夕。强欢虽有酒,冷酌不成席。”“人生行乐耳,安用声名籍。胡为独多感,不见膏自炙。”所以,他和苏辙约定:“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1]120不久又说:“辞官不出意谁知,敢向清时怨位卑。万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霜髭。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1]157由此可见,苏轼离别了弟弟到凤翔来任职是不得志的,所以他又写诗劝子由要看淡名利和富贵:“人生百年寄鬓须,富贵何啻葭中莩。”“下视官爵如泥淤,嗟我何为久踟蹰。”[1]180苏轼虽然认为自己与“官爵”和“富贵”无缘,但为了生存还是要去做官。
苏轼虽然为生存而奔波操劳,但他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心中有着自己的远大志向。当他罢凤翔任还朝,路过秀州时就说:“鸟囚不忘飞,马系常念驰。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1]235甚至还说自己“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1]275可是,现实并不是如苏轼的愿望那么完美的。是时,宋神宗正在支持王安石变法,而苏轼又有自己的不同看法,于是乎苏轼只能“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1]290甚至发出了“我生飘荡去何求”[1]291的慨叹。
在苏轼踏入官场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些身心疲惫,对官场并不热衷和留恋,但为了生存又没有办法,只得违心地干下去。
三、在王安石变法中受挫后对人生的思考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苏轼、苏辙在川居父丧后还朝。是时,“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三年,又让苏轼“权开封府推官”,企图用具体的事务缠住苏轼,不让他参与朝廷政务。四年,王安石大肆推行变法,但苏轼都持不同意见,并提出批评。于是,“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诬苏轼兄弟扶父灵柩回川时贩数船苏木入川),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1]2820苏轼在《与张君子书》中谈到他请求外任的原因也说:“而为郡粗可及民。又自顾衰老,岂能复与人计较长短是非,招怒取谤耶?若缄口随众,又非平生本意。计之熟矣,以此不如且在外也”[2]1649
苏轼一到杭州,就遇到严重的蝗灾:轼“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2]1396加上此时又实行手实法和免役法等新法,苏轼感到十分无奈,他给弟弟子由写诗说:“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1]314还自嘲地说自己“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1]325是年苏轼才37岁,正是年轻力壮、大有作为之年,可他却说“如今衰老俱无用”,这显然是对时局大大的不满。所以,他在《送岑著作》中说:“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拙于林间鸠,懒于冰底鱼。人皆笑其狂,子独怜其愚。直者有时信,静者不终居。而我懒拙病,不受砭药除。”[1]329还坚持说自己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人生各有志,此论我久持。他人闻定笑,聊与吾子期。”[1]384既然是改不了不向改革派屈服的性格,那应该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做个“中隐”之士:“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1]341
什么是“中隐”?白居易在他的《中隐》诗中写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樊丘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日有俸钱。……惟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这种“中隐”的实质就是:不做京官,做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官;不再以隐作为实现独立和价值的途径,只以隐作为隐姓埋名、自我潜藏的一种手段;不抛弃隐士的名称,以隐逸作为虚幻的精神寄托;做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拿一份不薄不厚的俸禄,过一种不紧不慢的生活,讨一份不喜不忧的心情[3]117。所以,“中隐”这一观念在唐宋时期的官场上是得到认同的。
但是,苏轼决不是这种人,当他看见江浙农民“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的现状,看见新法给农民带来的伤害时,就“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并写了一些反映新法的诗歌,如《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目的是让皇帝看到了,能了解新法的弊端。所以,这时的苏轼在农村巡视时的感受是:“身世悠悠我此行”,但“惟有悯农心尚在”,所以他才能事事都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并为农民的利益鼓与呼。
当然,此时的苏轼对人生的感触也是颇为深沉的。他说:“人生如朝露,要作百年客。喟彼终岁劳,幸兹一日泽。愿言竟不遂,人事多乖隔。悟此知有命,沉忧伤魂魄。”[1]509甚至写出了这样的诗句:“已向闲中作地仙,更于酒里得天全。从教世路风波恶,贺监偏工水底眠。”(《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首》)[1]586可见他在杭州通判期间的思想是十分矛盾的。
四、知密州时对人生思考的成熟
通判杭州届满,熙宁七年(1074)五月移知密州。为什么他要主动请求调往经济落后的密州去呢?是不是如他在《密州谢上表》中所说的“携孥上国,预忧桂玉之不充;请郡东方,实欲昆弟之相近”[2]651呢?不是的。苏轼通判杭州,本来就是为了避开朝廷的斗争而自请外任的。他原想在外地等待有利时机再回到朝廷。可是,三年过去了,朝廷中的斗争却更加激烈。在韩绛、吕惠卿主持朝政下,继续大力推行新法,对欲动摇新法或起用旧党人的举措、建议,都坚决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要回到朝廷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为了远离斗争漩涡,等待时机,他才自动请求调往密州[4]289。正如他刚到密州时写给王庆源的信中说的:“新法严密,风波险恶,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谓‘居闲食不足,从官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正此谓矣。”[2]1812
苏轼请调密州不仅是为了避祸,更主要是要等待时机。他在赴密州的路上写给苏辙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词就说得很清楚:“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5]132在这里,他把他们兄弟俩比作西晋时期才华横溢的陆机、陆云兄弟,且说致君尧舜之事何难?但在这个时候,苏轼兄弟俩就应该保重身体,“袖手闲处看”了。这样说,还不是有明显的等待时局变化的意思吗?
当时的密州,经济发展本来就落后。苏轼到任那年,正好遇上严重的天旱和蝗虫灾害,苏轼要全力带领地方官员和百姓投入到灭蝗斗争中去。由于地方经济落后,密州官员的生活也非常艰苦,正如苏轼在《后杞菊赋并叙》中说的那样:我“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2]4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对人生怎样看待呢?庄子的齐物论思想马上涌现出来:
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3]4。
庄子在《齐物论》中就说过:“夫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6]12庄子把世间的任何事物都看成是无差别的,而苏轼也是一样,把“贫”与“富”,“美”与“丑”,“粱肉”与“糠核”都看成是一样的东西,并且认为吃这些粗糙的食物也许能长寿呢。这是他初到密州时所形成的超然物外思想的基础。以后,他在《和蒋夔寄茶》诗中将他赴密前后的生活作了对比:在吴越时,“三年饮食穷芳鲜”,吃尽了高档的食品;到了密州后,就只能“厨中蒸粟堆饭瓮,大杓更取酸生涎”了。苏轼近似总结地说:“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人生所遇无不可,南北嗜好知谁贤。死生祸福久不择,更论甘苦争蚩妍?”[1]654这就说明苏轼是具有牢固的“随遇而安”思想的。
随着苏轼对人生思考的深入,他在到密后的第二年便重新修整了西城台(后称超然台),作为登眺游息之所。于是,便借机向友人广泛征集台名。而对家兄有深切了解的弟弟苏辙,则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耶!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7]821苏轼则欣然同意,并大加赞赏。所谓“超然”者,就是“超然物外”之简称也。超者,高超脱俗;物外者,世外之谓也。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超出世俗生活之外,不受外界物质的诱惑。
苏轼在《超然台记》中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2]351这就是“超然物外”思想的表述。这一思想的提出,说明了苏轼已经将他过去对人生思考的心得体会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形态,并提出了观察外物的方法,从而使这一思想具有普世价值。因此可以说,“超然”思想的提出,标志着苏轼对人生思考的成熟。
五、超然物外思想对于认识人生的作用
《超然台记》的思想非常丰富,笔者在《超然:苏东坡思想的精髓》一文曾作了具体论述,认为此文表达了苏轼透彻的人生哲学思想,旷达的处世思想和强调神似的超然艺术观。[8]20-28如果仅从人生哲学角度来研究,苏轼最大的贡献就是给后人提出了人类认识和处理外界事物的思想方法,要求人们要“游于物外”。二年后,苏轼在徐州任上又将这一思想作了具体的发挥,他在《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2]356
“寓意于物”和“留意于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意义是完全不相同的,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寓意于物”,就是说每一种事物都可以寄托人的思想感情,让人从外界事物中感到快乐。人是以一个观赏者的身份来看待事物的;而“留意于物”呢,则是“在意于物”,即斤斤计较一物之得失。在这里,人是作为物质的获取者来看待事物的,人变成了物质的奴隶。为什么说“留意于物”不对呢?因为“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从现代心理学来看,世上的种种纷争,无非是为了财富,为了名誉,都不外乎利益之争。人们身处其中,不免把它们看得很重。但是,如果用“超然物外”的眼光来看,就会发现,人们拼死拼活地追求的物质享受和名誉地位是十分可笑的,不值得的。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43年发表的《人类激励理论》中就提出:人类生存需求分成5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亦称为社交需求)、尊重和自我实现,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人类的生存,物质东西多一些固然好,但能保证基本生存也就可以了。至于对精神财富的追求,由于各人的素质不同,成就当然也就不同了,所以人与人之间根本上不存在冲突。由此看来,人世间的东西,有一半是不值得去争的,还有一半是不需要争的。况且,在终极的意义上来说,或是用庄子的“齐物论”思想来看,人世间的成功和失败,幸福和灾难,都只是过眼云烟,二者并无实质上的区别。所以佛教教我们“得不喜,失不忧”,要人们用平常的心态来看待事物,千万不要斤斤计较一时的得失。我国古语也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应是苏轼“超然物外”思想应有的内涵。它对于人们正确地看待人生,并用于战胜人类在生活中遇到的苦难是十分有用的。
六、余论
由于苏轼在密州时期就树立了“超然物外”的思想,为他以后遭受到三次贬谪的痛苦遭遇做好了思想准备,使他能够从贬谪的“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的困苦生活中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在黄州东坡种植小麦、茶树和果树;在惠州也种菜、种茶。又由于他有了一颗“无区别”之心,就使得他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做到“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所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9]3。更由于超然物外的思想,使得苏轼能够忘掉自己的痛苦,始终保持着一种热爱生活的心态;不论是做官还是遭受贬谪,始终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把“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东坡文化现象。后人对此现象百谈不厌。这就是“超然物外”思想所产生的神奇效果。当然,苏轼能够做到这样,也离不开宋代文人普遍高扬主体精神的社会大环境。他们不肯屈从官方或世俗的观念体系,他们看重自身的修身养性;不屑于官场的进退,追求“自得”其“乐”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境界。正因如此,才能形成“超然物外”的思想,苏东坡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
参考文献:
[1]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冷成金.隐士与解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4]李增坡.苏轼密州作品赏析[M].济南:齐鲁出版社,1997.
[5]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6]王先谦.庄子集解[M].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7.
[7]李增坡.苏轼在密州[M].济南:齐鲁书社,1995.
[8]王启鹏.苏轼寓惠探幽[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9.
[9]林语堂.苏东坡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郭杏芳]
作者简介:王启鹏,男,广东惠州人,原《惠州学院学报》主编,编审。研究方向:写作学、苏轼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2
DOI:10.3969/j.issn.1672-1047.2016.01.01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47(2016)01-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