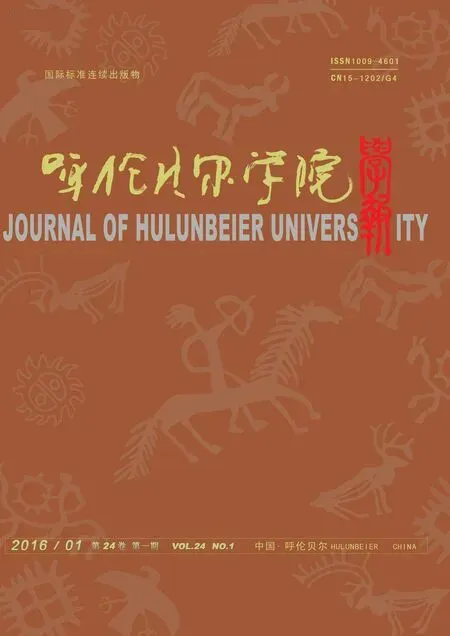青春的艰难与成长
——双雪涛小说的成长叙事分析
吴 玲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辽宁 沈阳 110034)
随着当代文学轨迹的不断向前发展,继60后、70后提法之后,文坛上对于80后的提法从新鲜与争议逐渐进入探讨与研究的过程当中,而这实际上暗含了目前主流文学界对80后这一文学现象的认同与接纳,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主流文坛对于80后作家作品的扶持与滋养。但是自“80后”声名大噪以来,其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维度:一种是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大语境的影响下,对当下都市生活中时尚摩登的着意书写,表达着作家青春的快意与梦幻的体验,他们的文学空间里充斥的是数不尽的现代元素:街头巷尾闪烁不定的广告牌、透明落地橱窗里陈列的琳琅满目的时尚奢侈品、匆匆来往的车流与人群、高耸入天的建筑群……当下都市的浮华烂漫在他们笔下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另一维度的写作则是在浮华骚动的都市中坚守本心,可称为是一种“变中守常”的写作,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传统人文关怀的脉流在他们的叙事方式、人物塑造以及思想内涵中缓缓流动,在全社会追逐新潮的“变”守住那一份“常”,表达了作家们对文学传统理想难能可贵的执拗坚持——其中,东北作家双雪涛以他的创作向学界及读者表达了他坚守的决心与勇气。
生于1983年的双雪涛如今恰逢初卅的年纪。其实,时至今日,“80后”基本多已年近三十或已然年过三十,马上就要度过这初卅的年纪步入人生的中年阶段。而此时,恰又是一个人的巅峰时期,无论是身体还是事业。但是世事并不总是遂心如意的,这些人中自然有人春风得意,亦有人一筹莫展。只是此时无论是否功成名就,面对渐长的年岁与物是人非的境况,难免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与地点生出怀旧情绪,追忆似水年华,怀念已逝的旧日时光。他们或感慨万千、或伤感怀旧、或为过去幼稚的所作所为仰天长笑,或因未完成的心愿黯然神伤。对这种情绪,国内很多作家与导演都有所表达,那些流淌在笔尖、闪烁在镁光灯下的青春记忆,被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些青春记忆中,少年时的校园生活,被作家与导演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极为深入的表现。如作家李师江的《中文系》、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及赵薇投拍的同名电影、导演陈可辛执导的《中国合伙人》等。双雪涛也以他冷峻简练的笔触写出了《安娜》、《聋哑时代》、《跛人》、《我的朋友安德烈》等校园青春题材的作品,这也是本文进行分析的对象。
新世纪以来,青春叙事在文学市场上出尽风头占尽风光,小说、散文、电视、电影等都对之进行大量的集中创作,其风头可谓是一时无两。究其原因,大抵可以概括出三个方面: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城市市民基本完成了“独生子女”的规划,随着“421”家庭结构而来的家庭问题日渐突出;二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不断涌向城市,“留守儿童”问题被残酷地摆在大众面前;三是在现代化大语境下,商业文化的驱使,当下商业文化的消费力量可以消费一切,当青少年问题以文学的形式被作家表现出来的时候,它也就变成了一种奇观现象被展览与消费。
一般来说,青春叙事往往内在地包含有“成长”的主题,也可以将其说成是成长小说。但是,成长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历来不甚发达,已经被列为“经典成长小说”的《青春之歌》、《芳菲之歌》、《欧阳海之歌》等红色作品,并不能当做真正地成长小说。那里虽然也详尽描述了主人公的成长故事,但是主人公的成长都是在革命导师——也就是意识形态的教导与规训下完成的,他们对于世界、自我以及人生的观念与价值体系都不是自发形成的。如评论家孟繁华老先生所称:“成长小说是通过主人公自己在成长过程遭遇的失败、挫折逐渐成长并形成对世界和他人的看法和价值观念的。”[1]在这种意义上,双雪涛的青春题材的短篇小说是当下的青少年成长小说。
一、家庭的缺席
如前所述,青春意味成长,然而,正青春的年龄并不知道如何度过这热血沸腾的青春,成长的旅途中不可避免地会充斥着不完满。而这些不完满如果得不到良好的解决,于青春生命而言,就会引发心理的磨难与精神的创伤,给青春期带去苦闷与彷徨,焦虑与痛苦。对于这种青春期的悲剧,双雪涛在《安娜》、《大路》与《跛人》三个短篇中淋漓尽致地将之展现了出来。在这几篇作品中,安娜、“女孩”以及刘一朵都是正青春的少女,而且她们家境优渥,享有同龄人并不拥有的物质享受。但是,在这如花般鲜活的年龄,她们却选择自残、自杀与离家出走这种极端的方式逃离现有的生活。这显然印证了孟繁华的论断——现实不止是我们置身的外部环境,同时更包括我们的心理和精神处境。这些少女们所处的是优越的物质环境,但是她们的精神与心理却处于蛮荒,而双雪涛则自由地书写她们身处蛮荒中的叛逆与创伤。
《安娜》中的安娜童年压抑、父亲软弱、母亲独断,生于长于这种环境下的她过早地了解了成人社会的阴暗。她憎恶这一切却无力逃脱,为了释放心灵重负她早熟早恋,屡屡自杀(皆未遂)。《大路》中的“少女”将生命置之度外唯求一死,“三天之后的清晨一支送葬队伍从别墅区中缓缓驶来,灵幡从车窗里伸出,有人向外撒着纸钱。我看见有人在副驾驶座抱着一幅黑白照片,我看见了,看见那照片上的容颜。”[2]这段描写与后文“我”多年后的幻觉,暗示着少女生命的陨落。《跛人》中刘一朵与安娜有些相像,叛逆、早恋,唯一不同的是她逃离的方式是义无反顾地踏上离家出走的火车,将一切不愿面对的抛在身后。
她们何以是此般结局呢?这不但是小说中讲述人“我”的疑问,亦是作者双雪涛和整个社会的疑问。这个疑问,双雪涛在这些作品中已经初步给出了答案。如《大路》中“我”与“少女”的一段对话——过了好久,我感觉到自己就要睡着了,屁股也没了知觉,说:“你不用回家吗?”她说:“家里没有人,他们都很忙。”……我说:“亲人是什么样的?”她说:“和你很熟但是和你不相干。”[3]她们并不是生来就是坏女孩儿,她们同样聪明、天真、善良,在濒临绝境时依然抱有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但是她们的成长却是一种几乎完全个人化的成长,父母的缺席使得她们的成长之路没有指引与导向,而父母的矛盾、离异或者“冷暴力”则在她们的心灵上抹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期望破灭,绝境降临,她们脆弱的心灵只能在不能承受的成长之痛面前支离破碎。《跛人》中刘一朵在离开前的火车站广场问“我”是不是能赚钱养家的那种人,无疑是对安稳的家庭生活的期许。《安娜》中安娜哭着说的那句“我就知道,我死了谁也不会难过,一个难过的人都没有。”[4]无疑是一种对家庭与亲情缺失的绝大讽刺。
二、教育的失责
成长小说概念源自于德国的教育小说,而教育小说整个是围绕着少年的教育问题而展开的。在通行的观念中,教育是直指人的心灵的,一个真正的教育者应该是学生们成长道路上的心灵导师,如伟大教育家韩愈所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育应该塑造学生的精神灵魂、唤醒学生的信仰、信念、陶冶学生的学生品格情操,以及发掘学生潜在的智慧与创造力。“教育的责任,十有八九究竟是应该由校长教师们担负的。”[5]从古至今,教育的问题与教师有着直接的关联,学生的成长发展要靠教师来培养,教师的知识水平和教育理念将直接影响到学生个体的成长。
除了教师的个人素质与教育理念将会影响到学生的成长之外,教育体制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古至今,中国的教育体制一直在经历着变革,历经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征辟制、魏晋南北朝时的九品中正制,定型为隋唐及后期的科举制,毋庸置疑,科举制度无疑是我国人才选拔史上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种。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以来,新式学堂不断发展壮大而成为今日的九年义务教育以及高考系统。然而,科举制度千年的影响依然余声不衰,“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观念依然普遍存在,孟繁华指出:“在传统文化那里,虽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学而优则仕’才是真正的目的。”[6]努力学习、升入高等学府依然被当成改变命运和前途的一种手段,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教育便越来越具有功利的目的,而偏离了关乎灵魂的指向。这些弊端,在双雪涛的成长小说中有着全面的表现。
双雪涛出生于1983年,本科就读于吉林大学法学院,2003年入校,2007年毕业。在《小说家的时钟》中他如此写道:“作为幼儿我度过了7年,作为学生的时间较长,17年,作为银行职员,5年,作为写小说的人,1年零5个月。”[7]作为学生的17年占据了他大半生命,无疑是他日后进行校园青春写作的绝佳资源。在他一系列校园青春题材的小说中,他对中学校园的日常生活、生态、学生、老师、学校制度以及教学风气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描写,使读者身临其境般地体验到了90年代的校园氛围。而在这些描写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异彩纷呈的少年学生形象,深入人心。双雪涛却并未止步于此,而是通过这些少年学生的形象深刻揭露了学校教育制度与教师的鄙陋,表达了一个作家以一己之力担当社会道义的普世情怀。
在我们国家目前的学校教育体制中,被老师与家长看好与欣赏的是所谓的“好学生”,这种学生成绩好、性格温顺、对学校的一切言听计从。在《聋哑时代》里,双雪涛就塑造了丹凤陈就是这样一个“好学生”——除了学习心无旁骛,并且是班主任老师的心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学生最终却在学习上迷失自我而被学校驱逐——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双雪涛在作品中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因为成绩好并且长得漂亮,她受到班级内大多男生的追求,但她是好学生,自然要把这些追求报告老师,而那位她“一心效忠”的老师却因惧怕承担责任而开罪她——这是“好学生”丹凤陈内心变化的开端;接着她被老师打入冷宫,转而一心向学,因压力过大而内心浮躁,这个时候本应耐心开导的老师却责骂相加,从而导致丹凤陈心理防线溃决而迷失自我。
与丹凤陈相对的,双雪涛又在《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坏学生”安德烈。安德烈家境贫寒,成绩不好,与老师对着干,而且衣着邋遢,极不招师生的喜爱。但是在那个校园里,他却是最敢坚持自我、最特立独行的“那一个”。为了表达对学校暗箱操作的不满,他敢于在校长室门上张贴大字报以捍卫和“我”的友谊,却因触犯校长与老师的权威而被逐出学校……而他的这种结局很大程度上是学校造成的:因为与老师顶嘴,被永远的安排在最后一排角落并无人与之同桌(所以他才会分外珍惜与“我”的短暂友谊);作为教书育人的老师却私下开办补习班并因此将课程内容只讲一半,并且让学生为之“拉皮条”(此处拉皮条三字讽刺之意尽显),罔顾上级文件暗箱操作,被揭发后不思反省,反而迁怒于学生(对隋飞飞的责骂难道不会再造一个丹凤陈出来吗?)……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曾指出:“人作为主体都具有可塑性,而青少年尤其大,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等外界刺激,往往会形成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8]我国传统观念也认为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阅读双雪涛的这些小说,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主人公们并不是天生叛逆,他们也有梦想,也曾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如安娜曾热爱弹钢琴,获得过各种大奖),然而这种期待却遭遇到家庭、学校、社会阻力,家庭的缺席与学校的失责,使他们发现自己的期待被抛弃、被悬置,但他们又无力改变现状,索性以叛逆的面孔与之对抗。而在这些作品中,少年主人公的叛逆往往以无效或失败告终,面对这种失败,他们选择了自杀、叛学等极端的方式以期完成青春的突围。无论是安娜、刘一朵,还是丹凤陈、安德烈,他们作为孩子时已足够强大,强大到敢于与整个社会做抗争;但是作为成人,他们又太过弱小,他们渴望着来自家长、老师以及社会的呵护与交流。但是这种渴望在双雪涛笔下是不能实现的,于是他们的成长便有了不可磨灭的伤痛。这一现象难道还不足够引起作家、评论家社会的深刻反思吗?双雪涛站出来了,他写出了他的观察与思考,他的讲述喻示了他的文学才能,也喻示了他作为一名文人的现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