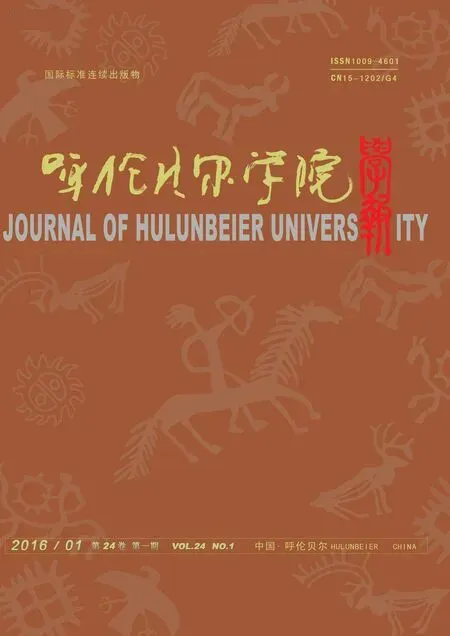青海蒙古语地名文化学解读
吉乎林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 青海 西宁 810000)
地名研究是属于语言学范畴的。既是社会语言学要涉及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语言文化学所要研究的对象之一,既不是单纯的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也不是单纯地属于社会语言学和文化学研究的范畴,更不是历史学的研究范畴。而是语言、社会、文化、文化相交叉的一种历史语言文化学研究的领域。既是语言的、又是文化的,是与语言紧密结合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地名的产生和语言的产生时间应该是一致的。刘盛佳先生指出:“人类为了认识、了解、利用和改造周围的地理环境,需要命名一定的名称,使组成地理环境的个别因素,个别特定地域得以区分,于是便产生了地名,”一个地名的产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最初只是被提出来但并未被所有的人认可,后来在频繁交往中才得到社会的承认并被普遍使用,这样它就按照人们约定俗成的方式由少而多、由简而繁、由近而远、乃至由过去延续到现在、将来,代代传承下去。地名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发展,它是人类认识和籍以识别其居住、生活的自然和社会坏境的符号和标志。”①
一、青海蒙古语地名与蒙古族迁徙
“地名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确定某一类型名称的分界线。这些界线构成了类型或构成分布区。研究地名分布区对确定居民地的迁徙有极大的帮助。分布区的形态可以是各种各样的,通过它们可以圈定某一民族过去历史的分布区,分布区的界线很少与现代的政治行政界线重合,而是反映过去的相应关系。”②地名虽然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变迁、政权的更替、族群的融入或迁徙等都是地名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有的民族或族群已经迁移或者消亡,但他们所创造的地名还依然存在,而被后来者改变了他们所命名的地名,情况复杂,不一而论。但不论怎么说,总会有历史的遗迹,或者留下一定的蛛丝马迹,是我们研究某个民族或族群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例如,从某一语种地名的分布或变化,可以反映出民族迁徙的足迹和民族分布的历史概貌,从历史文献典籍或者民间传说中可以追溯到地名的历史演变。青海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交融、更迭的大舞台。公元13世纪,南宋理宗元庆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进军洮、河、西宁州,青海东部地区纳入蒙古汗国版图。忽必烈即位初,在河州设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青、甘一带吐蕃部落。至元十八年(1281年)设甘肃行中书省,辖西宁诸州。明中叶,东蒙古各部陆续进入青海游牧。16世纪初,蒙古族厄鲁特(即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和硕特蒙古移牧青海,建立和硕特蒙古汗廷,统辖藏、青、川、甘等藏区。清雍正初年,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反清斗争失败后,清朝为了控制和管理该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蒙藏分治”,“抑蒙扶藏”等政策的推动下辉煌一时的青海蒙古族走向了衰败。此前的蒙藏居住格局主要以黄河为界限,除黄河以南有蒙古五旗外其余蒙古各旗均游牧于黄河以北的广阔地区,随着青海蒙古族的衰败和黄河以南藏族各部的强盛使得藏族各部陆续迁往黄河以北的蒙古地区,形成了蒙藏混居状态,自此也开始了大量蒙古族的藏化。
青海境内的大量蒙古语地名的形成和蒙古族几次大规模迁入青海的历史事件有密切的联系,元朝、明朝、清朝都有蒙古族徙居青海高原,并与藏族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和频繁的来往,于是藏族称蒙古人为“索布”或“索乎”(与原霍尔人加以区别),在他们居住过的地方相应出现了许多以“蒙古”(有的写作“索布”或“索乎”,也有的写作“索卜”、“索合”、“索寨”等,汉文书写不统一)命名的地名,这些地名也正好可以印证蒙古族在青海的活动轨迹。
例如:a.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索卜”(蒙古人,今居民系土族)、“索卜屯”(蒙古人居住的村落名)、“索卜沟”(蒙古人居住的地方名,以地貌特点命名,今居民全系土族)、“索卜滩”(蒙古人居住的村名,以其地貌特点命名,今居民亦为土族),甘德县 的“索乎”(蒙古人牧业点,今居住的全为藏族牧民)、“索合勒”(大蒙古人,牧业点,今皆为藏族牧民),
b.共和县的“苏合拉”(蒙古人的牧圈),
c.囊谦县的“索寨”(蒙古人的村寨),
d.久治县的“索合日麻”(蒙古人的帐圈),
e.循化县的“苏合沙”(蒙古人的地方),
f.果洛州久治县的“索乎日麻”(蒙古人的新居),
g.例如有许多以“霍尔”命名的地名:互助有“合尔川”、“合尔滩”,贵德有“贺尔家”民和中川有一庙叫“霍口盖日灭”意为霍尔人居住的地方等等。上述的“合尔” 、“父尔”、“ 霍日”都是藏语“万引”的音译。“霍尔”在藏文史籍中或通指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或指蒙古族。但清代藏文中的“霍尔”多指土族。今天皇源县还有称“胡尔丹度”的地名,意为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居住过的地方。但如今这些地区已经是藏族、汉族、回族等其它民族居住地,很少有蒙古居住了。但是,地名依然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由此可知,这些地方曾是蒙古人居住或游牧过而留下的地名,上述有些地区的人们在交谈中认为自己是蒙古人的后裔,如今,这些地方已经成为其它兄弟民族的主要居住地了,原来的蒙古族或改变民族身份融入到藏族、土族之中,或者迁往别处后仅留下了地名而已。由此可见,从地名中可以窥测出青海多民族和谐共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状况,同时,也可以从中探索蒙古族的历史轨迹。
二、青海蒙古语地名与蒙古族历史记忆
地名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记录。因此,它与历史以及现实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透过地名可以知道很多历史事件及有关历史人物的事迹。地名与历史文化遗迹。例如;从上古时期至近代活动在环青海湖周围的少数民族对当地地名的命名方式多种多样,并且地名在形式上从以前比较单一的地名演变成多元地名,从范围上地名从以前的大范围演变成近代的小区域。地名的出现也和一个家族的家系一样,沿着一条主干分成很多个小枝干。比如,“鲜海”、“伏俟城”、“祁连山”等等,根据史料记载这些地名出现于上古时期。
从地名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不少地名是当时的人民为了记住某一事件或某一历史人物而有意的把自身的某种心理寄托于某一地理实体而予以特定的命名,于是会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甚至编成故事、传说、歌谣等代代传承下去。例如乌兰县的köke “柯柯”这个地名,原意为“青色的地带”。据说,卫拉特蒙古人从天山南北移居青海,在此游牧时,因为此地牧草丰美,最先到达的仙遣军是12名骑着铁青马的勇士,因此,将该地称之为为“柯柯”,此地原为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柯柯贝勒的驻牧地。又如,在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境内有一地名,叫 “tu˜ü˜ügür”、“图格山嘴”,意为“立着旗杆的山嘴”。据说当年罗卜藏丹津反清失败,向西逃亡的时候将军旗立于此地,因此得名。诸如此类的地名很多,如海北州有两个山名分别叫 yeke ula˜an qoši˜u“大红和硕”和 ba˜-a ula˜an qoši˜u“小红和硕”两座大山,即大小“红山嘴”。相传固始汗受藏传佛教格鲁派之邀来到青海之后,以一万军队打败格鲁派之敌喀尔喀却图汗的四万军队,并擒杀却图汗,在此两座山之间激战惨烈,血流满山,染红了整个山嘴,故称此地为大小“红嘴山”。③“tugtut”意为“有旗帜的地方”,此地在今都兰县巴隆乡境内的青藏公路旁的一座高山,据说,罗卜藏丹津反清失败后向西逃亡准格尔的途中经过此地,走到上顶上回望故乡并将军旗插于此山顶上,以表难舍之情,从此这座山称之为“tugtut”,从此地再往西北方向就是有名的嘎斯的芨芨草滩,据说,罗卜藏丹津反清失败后途径此地发现这里的芨芨草异常的高、茂密,将他乘骑的白骆驼都被掩盖时,心情异常沮丧,于是创作了德都蒙古民歌“嘎斯的积极草滩”,此歌歌词里面就有“gas in cagan deresen ni denjin degree haliguragad gagca baigsan danjin ni huitu juge tegen juril-e ”,大致意思为“嘎斯摊上的芨芨草在风中荡漾、唯一的一个丹津赴向了西方”。
河南县有一地名叫“da˜an tala”意为“马驹滩/原野”,据说:1669年土尔扈特部的博师各图汗率领部众一万五千户来到了今河南、泽库等广阔地区,此时,汗王的马驹群跑满了整个草原,故此地,称之为“da˜an tala”。
这些地名和民间传说、故事基本都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依据,并赋予不同的情感因素而命名的,虽然可能与真实的历史有一定的差别,我们研究的目的在于去伪存真,化模糊为清晰,揭示其合理的核心,提供参照。青海很多蒙古语地名和地名故事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一些历史事件或者某个历史人物的事迹,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是研究青海地方史,青海蒙古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的借鉴资料。
三、青海蒙古语地名与民族心理
“任何民族都有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支柱,包括政治、伦理道德精神、传统文化、宗教等等,一个民族的社会心态不仅有伦理观念而且还有社会价值观、社会共同心理,甚至有宗教精神。从文化伦理的角度来审视,地名不仅反映地理自然景观的种种特点,而且反映人文地理景观的各种特点,甚至还反映民族的社会心态。”④蒙古族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萨满教的主旨是长生天主宰一切,蓝色是天的代表,所以特别崇敬蓝色。罗布桑却丹在他的《蒙古风俗鉴》中说:“蒙古人判断年景,蓝色为昌盛,白色为起始。所以蒙古人视蓝色和白色为各色之首。”特别崇尚白色和蓝色,青海蒙古语地名中,以蓝色和白色来命的地名的特别多。例如:ča˜an na˜ur “ 察汉诺 ”(属海西州乌兰县)意为“白色的湖”,ča˜an ˜ool“察汗河“(属大通县)意为“白色的河”,köke“柯柯 ”(属乌兰县)意为“青色或蓝色”,kökena˜ur“库库淖尔”(青色的湖)等等。
在青海蒙古族传统习俗和文化心理中,“白色”象征圣洁美好,“蓝色(青色)”是志高无尚的象征,“黑色”象征力量、权利,也是艰难的象征,“红色”是流血事件、红色政权的象征。如:qar-a na˜ur哈拉湖(属海西州德令哈市辖区,“哈拉”,即蒙古语的“qar-a”。意为“黑、黑色”,全名是“黑海子(湖)”。从命名中可以知道,此湖水深而清澈。ula˜an ˜an˜a “乌兰干沟”(村名,属德令哈市柯鲁克镇辖区)“乌兰县”(属海西州辖县)中的“乌兰”是蒙古语ula˜an,即“红色”的意思,因为它们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红色政权的建立或为纪念牺牲的革命烈士而命名,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意义。
所以这种色彩的表达不仅仅是出于美感的需要,而且也说明蒙古族对于色彩的选择常受传统观念的制约和影响,这其中寄存的祖先的思想观念和深厚情感的表述。⑤
四、青海蒙古语地名与蒙古族社会建构
“族称是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外在符号标志,它往往对内具有认同性,对外则具有相当的排斥性,因此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族名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认识民族的产物。从族名上能够看到人们对某一民族的认识,以及民族关系上的某些特点。”⑥青海蒙古族历史上有29旗,“旗”是青海蒙古族古代社会的重要行政单位,青海蒙古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组织形态。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态在清代,由旗扎萨克按清政府有关规定总揽一旗军政事务。一直延续并应用至新中国成立,“旗”不仅是行政单位,又是清廷赐给封建领主的领地。所以在青海蒙古族中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例如,克鲁可旗、柯柯旗、宗家旗等等,现如今很多旗已不复存在了,但是以当时的旗名命名的地名被保存了下来,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族称地名来研究某些部落,尤其对已经消亡的部落的历史情况等能够提供重要的历史线索。例如,今青海大通县默勒乡,历史上属青海蒙古南左首旗牧地,俗称默勒扎萨克旗,后因诸多原因使得该旗已经消亡,但以此旗名命名的地名依然存在。还有今湟源县有一地方加群科,原属青海蒙古南左末旗牧地,俗称群科旗,后来该旗也因人口流失、牧地缩减等等诸多原因使得该旗名存实亡,但是以该旗名称命名的地名依然沿用至今。还有柯柯镇,原属青海蒙古西后旗牧地,即柯柯贝勒旗,现如今青海蒙古族盟旗制度被取代,但以旗名命名的地名依然被延续。历史上青海海西境内有蒙古八旗,有着固定的地域界限,并由不同的王公贵族来管理,在民间这种传统建构一直被延续了下来,现在还有很多人自称是某某旗人。如,柯柯旗人,台吉乃尔旗人,宗家旗人等。
此外还有“qota ”,“delekei hote”(德令哈市)“˜oolmod hota”(格尔木市)在现代蒙古语中,也是一个多义词,有“放牧最小的单位”、“牛羊群卧的地方”也指称“城市、城镇、市、城、都市”等。在汉语里,用作“城市、市”义是,往往意译为“市”或者音译为“浩特”,如“格尔木市”、“德令哈市”;“呼和浩特”,“乌兰浩特”等。这与古代蒙古族的游牧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延续至今且赋予了新的概念。
五、青海蒙古语地名与青海自然生态
地名文化是与其命名者所处的生态环境及人文语境和相应的经济形态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本民族的生活方式、社会生产方式、传统文化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典型的例证是,中原地区的汉语地名群中,主要是与农耕社会有关和反映农耕文化有关的地名众多。这与青海地区的蒙古语地名形成鲜明的反差。逐水草而居则是青海蒙古族的生产方式,他们是在广袤的草原、山川、河流间不断的游动迁徙,狩猎和游牧,这就意味着要和大自然的山川、河流、野兽、畜群、草木等发生密切关系。这些客观事物和环境,必然会影响其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观察事物的方式。例如,在青海蒙古语地名中就有“哈尔盖”(属海北州祁连县),意思是“有柳沙的地方”,海西州有 bö˜öngtu“野兔岭”地名,意思是有“兔崽子”的地方。还有činw-a daba˜-a(野狼沟)地名,即“野狼常出没的地方”,等等枚不胜举。此外,还有用植物命名地名的。如 arča-tu(柏树山),即长满“柏树的山坡”,ča˜an deresün“白芨芨草滩”,即长满白芨芨草的滩地,诸如此类的地名非常丰富。从这些地名中,我们就可以推测出当地的地质地貌特点和生物状况,为我们研究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和地形地貌,提供必要的事物证据,也是我们探索当地自然环境变化规律的途径和依据。
六、青海地名与宗教信仰
地名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而且与命名者所赖以生存的的自然环境及其在那里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他们所形成的民风民俗、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等有着密切关系。萨满教是蒙古族古老的原始信仰,但是,自从俺答汗会见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和后来的和硕特蒙古部首领固始汗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以后,青海蒙古族基本皈依藏传佛教,随之传播到蒙古各地。所以,在青海蒙古族的思想意识中,藏传佛教格鲁派信仰一直居于崇高的地位,也影响到了对于地理实体的命名。今天,我们每提到青海蒙古语地名,就可以看到许多反映蒙古族原始宗教信仰萨满教的地名和大量的藏传佛教文化色彩的地名。如青海海西有一地名叫eke köndei “母体阴腔”(形状类似女性生殖器),“eke”是个多义项词,有“母、母亲;起源、来源”等意思,“köndei”是“空的、空心的;隔离、山谷、洞穴”等意思。两者组合在一起,构成复合词,意为“母石”。据说人们从中穿过,可驱除灾害,这是原始宗教中生殖崇拜的遗存,“柯柯”属海西州乌兰县的一个乡的地名,意为“青色”,这与蒙古族原始信仰“长生天”有关。青海省天峻县境内有一垭口叫“关角山”,蒙古语意为“˜an˜uur -un kötöl”(甘珠尔梁),“˜an˜uur”是大藏经名,“-un”是属格附加成分,“kötöl”是“山梁、山坡”的意思,组合在一起构成述体结构,作地名。“burqan bodi a˜ula”(万佛山),其中,“burqan”是“佛”的意思,“bodi”是“菩提、正觉”的意思,即宗教用语,指“觉悟的境界”。dula˜an sükeid“都兰寺”、köke keid“柯柯寺”、“altan delekei keid“阿力腾德令哈寺”等寺院,都是以地名命名的寺院名,这些寺院都是在藏传佛教传入青海蒙古族地区后修建起来的寺院。
结语
青海蒙古语地名的许多内容与蒙古族乃至青海各民族社会文化、社会生活、民族迁徙等相联系。因此,在研究青海蒙古语地名的时候,也必须对青海地名作综合考察研究,必须坚持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考察,不可臆断,特别是对于那些地名的读音、意义不够确定的地名,更需要进行语言学、词源学、语音学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论证,作出客观、正确的解释。例如今天的祁连县的“祁连”一词,有的学者说是匈奴语,有的学者说是吐谷浑语,有的学者说是蒙古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都没有离开蒙古语族语言的范畴。因此,只有在充分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仔细认真地考证,才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再现各地的真实历史,加深地名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解,当然,对于了解青海蒙古族思维特点、宗教信仰、社会生产方式、自然地理特征.,民族间文化交流和民族关系等,也同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总之,通过对青海蒙古语地名的研究,“能够更多、更深层地了解蒙古族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即物质生产、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等。正像冯骥才先生在《地名的意义》文章中所提示的“地名决不仅仅是一个称呼,一个特定地域的名称”,一个地方有了“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有一个和生命一样丰富而深刻的含义”,“渐渐地在地名里形成它独具的历史文化”,这个“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独具的历史文化”⑦便是青海蒙古语地名所蕴涵的地名文化。青海蒙古族在青藏高原这块沃土上创造的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也同样蕴含在蒙古语的地名之中。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青海蒙古语地名作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价值不仅在于其语言学意义,还在于其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深入研究青海蒙古族社会历史文化的“活化石”。通过对它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深化对青海蒙古族的历史、语言、文化的全面认识。
注释:
① 王东茜、汉语地名的文化特征、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② B.A茹克维奇著,崔志升译:《普通地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年,119页。
③ 据《安多政教史》及《青海历史》据《青海史》记载:“固始汗在青海湖西北方向的乌兰和硕地方以一万军队击败却图汗的四万军马,并擒杀却图汗,战争十分惨烈血流成河使此地染成红色古称此地为“乌兰和硕”意为(红色山嘴)。”
④ 郭金桴著,《汉语地名与多彩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46页。
⑤ 鲍冬丽、凉山彝族尚色组合的象征文化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3期
⑥ 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年,72页。
⑦ 王东茜、汉语地名的文化特征、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