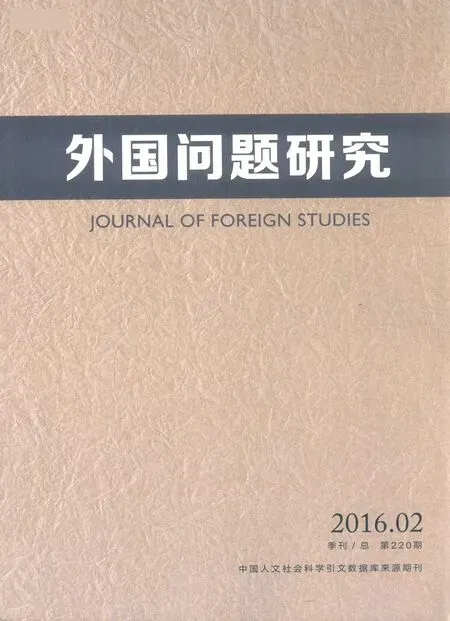古代雅典的城邦与宗教礼仪制度
魏 凤 莲
(鲁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古代雅典的城邦与宗教礼仪制度
魏 凤 莲
(鲁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古代希腊的宗教礼仪制度与古代埃及和古代中国的不同,其作用不在于提升统治者的权威,而在于促进集体之间的情感交流和融合。从雅典的情况看,城邦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处处充斥着宗教礼仪制度,城邦通过神庙、圣地构建自己的政治边界,公民通过宗教礼仪制度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获得公民身份认同。宗教礼仪制度强化了城邦的统治方式,构建了城邦文明的核心和基础,从而在深层次上决定了城邦的政治走向。
宗教礼仪制度;祭祀仪式;城邦;雅典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军事史,但在阅读这部历史的过程中,读者会经常想到政治和军事事件之外的事情,那就是为古希腊历史铺陈了整体背景的宗教。在雅典的历史上,为弑杀僭主的英雄竖立雕像和建立崇拜、十个部落英雄的崇拜机制、崇拜提修斯的活动、帕特农神庙的建设,诸如此类的事件中都带着强烈的宗教色彩,说明雅典的民主政治显然是在宗教的氛围中产生的。而追问苏格拉底被审判、赫尔墨斯神像被毁案、阿吉纽西海战后因未能打捞和救援水手所引发的群情激愤,也迫使人们思考希腊宗教与城邦之间的关系,并从宗教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古希腊人所创造的文明。
正是由于城邦发展与宗教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早在19世纪后半期,法国学者古郎士在其名著《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中,就把宗教礼仪制度看成是城邦社会组织结构和城邦政治的基础。*古郎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近年来,学者们对古郎士的这部著作做了重新翻译,有多个版本。李玄伯的译本是民国时期的重新翻印,但对原著的把握仍然精准。德·波利亚克在《崇拜、圣地和希腊城邦的起源》中,明确提出城邦形成的标志就是宗教崇拜的确立。*Francois de Polignac, Cults, Territo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康纳和古德黑尔等学者强调了宗教庆典(如城市酒神节)在构建雅典民主氛围和城邦意识形态中的作用。*W. R. Connor, “City Dionysia and Athenian Democracy, Classica and Mediaevalia”,vol.40,1989,pp.7-32; Simon Goldhill, “The Great Dionysia and civil ideology”, in Winkler and Zeitlin, eds. Nothing to do with Dionysos? Athenian Drama in its Social Contex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97-129.这些学者对宗教与城邦关系的研究成果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但必须注意的是,他们在对宗教礼仪制度的研究中,往往拘泥于希腊多神教本身的历史,或者拘泥于其他精神因素,试图用文化来解释宗教,而不是从城邦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明宗教问题,常常陷入到琐碎的考据中。国内学者对宗教礼仪制度与古希腊城邦政治之间的关系早有关注,如黄洋的《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古代希腊的城邦与宗教——以雅典为个案的探讨》等论文。*黄洋:《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00—109页;黄洋:《古代希腊的城邦与宗教——以雅典为个案的探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6期,第90—99页。对希腊城邦中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其他学者也有针对宗教节庆和献祭仪式问题的著作和论文,但是探讨宗教礼仪制度与城邦构建之间内在联系的成果还不多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拟以雅典为中心,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为理论依据,围绕四个问题来探讨宗教礼仪制度的内涵及其对城邦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
一、“宗教礼仪制度”或“仪式”?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对宗教礼仪制度的含义和解释始终存有争议。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对“礼”以及“礼制”进行了细致和生活化的阐释:“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人为什么要有规范的行为?是为了配合社会各分子获得各自的生活所需。在古代社会中,人们要向环境获取资源,必须相互合作,并且要有方法。这种方法是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我们说‘灵验’,就是说含有一种不可知的魔力在后面。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而“如果我们在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因此,“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23页。以费孝通的解释反观古希腊的社会生活,可以发现那些保证希腊社会运行的传统也可以用“宗教礼仪制度”来表达。
古希腊的宗教礼仪制度涉及了宗教观念、家庭责任、伦理道德、个人的过渡仪式(如与出生、成人和死亡相关的仪式)、献祭、祈祷和净化仪式等内容,其中对各种仪式的遵守是最重要的。从总体上看,古希腊宗教是一种社会的、实践性的宗教。它“不是关于内在的问题,也不热衷于个人与神之间的交流。古希腊人对神的虔诚,基本上是通过行为,是通过他们尊崇神的行动表达出来的”。*John Boardman, Jasper Griffin and Oswyn Murray,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13.古典学家芬利在《希腊的遗产》一书的前言里也持相似的看法:“希腊人的虔诚,希腊人的宗教以及不可胜数的书文主题似乎表现的是仪式、节日、游行、比赛、神谕、献祭(简单地说是行为),而且其传说与神话的主题是关于诸神活动的实例,而非抽象的教义”。*芬利:《希腊的遗产》,张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页。正如费孝通对中国社会中的仪式的解释,希腊人也将正确的行为视为“仪式”。古代希腊人不用多神教和宗教来解释虔诚和不虔诚的行为,而是用虔诚(eusebeia)和不虔诚(asebeia)来说明遵守祖先的习俗,看自己的行为在时间、对象和方式上是否合适。对雅典人来说,尊崇城邦保护神雅典娜的祖先习俗能从政治上解释他们自身,而城邦公开的仪式能够表达雅典人的自豪,使他们产生了优于邻邦的优越感。
但是,构建古希腊社会的宗教传统还不仅仅是仪式,不能用“仪式”来代替宗教礼仪制度所能表达的全部内容。有学者认为,“宗教仪式是信仰的行为方式,对于大多数的信徒来说,所谓的宗教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仪式生活”。*吴晓群:《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页。这种把宗教生活看成是仪式生活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因为仪式不能概括古希腊宗教生活的全部。仪式作为一种行为,自然要有支配行为的观念、规范和制度。古希腊宗教虽然“缺少一套系统规范出来的信条,一种教义和信仰”,*芬利:《希腊的遗产》,第4—5页。但也具有与行动相匹配的神的故事和传说,这些故事和传说,实际上表达了对神的理解和对传统习俗、社会规范的认可,也能判明哪些是亵渎神明的言辞或渎圣的行为。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史诗汇集了最基本的宗教礼仪制度,尤其是《工作与时日》中大量的格言,是出于对神的敬畏而形成的各类生活禁忌,无疑也是宗教礼仪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正因为有了这些宗教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规范和禁忌,希腊历史上才能出现我们在此文的开头所提到的种种事件,这些事件反映的是希腊人对宗教的反思,是希腊人的宗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他们进行仪式崇拜的动力和源泉。
与此同时,由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与宗教生活纠缠在一起,城邦对宗教事务做了很多相关的规定。从公元前6世纪的梭伦改革到公元前4世纪的吕库古改革,雅典实际上出台了相当多与宗教事务相关的法律,从神庙的选址、建设,到葬礼的各项安排等,都形成了制度,指导着人们的宗教实践。比如下文是一条简单的法令,对献给神的供奉品做了相关规定:
不许把任何供奉品带出圣所,不许毁坏任何供奉品,不许重新安排饰版的位置,也不得在未经祭司允许的情况下带进来任何饰版。*Simon Price, Relig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78.
类似的规范和为了指导宗教实践活动的法令,让我们看到,在古希腊人的宗教生活中,不仅有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还有以法律形式出台的宗教制度。显然,如果把这些制度和规范也都称为仪式的话,“仪式”这个词是装不下这些内涵的。所以,我们把宗教观念、仪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法令制度统称为“宗教礼仪制度”。
二、宗教礼仪制度为城邦构建了发展框架
雅典是希腊唯一没有突然中断与迈锡尼时代联系的地方。*让·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2页。公元前8世纪之前,阿提卡地区汇集着一些不甚重要的小村落,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村落里的人有了分化,贵族一般在雅典城居住,却占据着阿提卡乡间的大量土地,也担任祭司职位,掌握着与某种神力的特殊联系。在向雅典城邦发展的过程中,有两件事值得关注,其一是宗教圣地成为雅典人标志边界的一种方式,其二是以神话传说构建雅典城邦的创始人。
圣地包括土地、祭坛和神庙。乡村通常会有圣地,早在雅典崛起为帝国之前,雅典就控制了阿提卡地区距离其他城邦较近的圣地。比如位于东部海岸布劳戎(Brauron)的阿尔忒弥斯圣地、在阿提卡南端苏尼翁的雅典娜圣地和波塞冬圣地、西部与麦加拉(Megara)接壤的厄琉西斯的德墨忒尔圣地,以及北部与彼奥提亚交界处的安菲阿拉俄斯(Amphiaraus)圣地。*Nancy Evans, Civic Rites: Democrac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Athe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p.20-21.在早期,阿提卡边界上的这些圣地都是地方崇拜,在政治上独立于雅典之外,但是随着“居地统一”运动,整个阿提卡合并成为雅典城邦之后,崇拜仪式虽然还在边界的圣地举行。但这些崇拜的官方控制权已经转移到了建在雅典城市中心的新圣地。这种转移的意义在于,“城邦兴起时,把原属于某些氏族、标志着这些氏族与某种神力的特殊关系的祭祀职能夺了过来,变为官方的城邦祭祀。以前只有受神恩宠的人才能得到神的保护,现在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得到神的保护”。*让·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第45页。古风时代对这些边界圣地的重新安排,使雅典的政治和宗教权威向城邦的边缘辐射,同时,雅典官方与古老的乡村崇拜之间建起的宗教互动重新解释和确认了政治边界。
构建雅典创始人的神话可能与英雄崇拜的发展有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雅典国王厄瑞克透斯(Erichthonius)的传说。根据阿波罗多洛斯的记载,雅典娜想让工匠神赫菲斯托斯为自己打造武器,却遭到后者的性侵。在雅典娜的强烈反抗中,赫菲斯托斯把精液射到了她的腿上。她擦掉精液厌恶地扔到地上,结果从地下生出了一个男孩就是厄瑞克透斯。*Apollodoros, The Library, translated by J. G. Frazer,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1995, 3. 14. 6.作为雅典娜的儿子,厄瑞克透斯成为雅典的建城英雄,厄瑞克透斯的子孙——雅典公民——也就成了雅典娜的后代。这样的神话旨在构建雅典城邦与其保护神雅典娜之间的亲密关系,为城邦的起源和发展笼罩上一层浓郁的神佑色彩,后来的僭主庇西特拉图在夺取权力开进雅典城时,专门找到一个高个女人扮演雅典娜,希望雅典人认为他获得了雅典娜的保护和支持,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I. 60.
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雅典的民主化进程经历了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和克里斯提尼改革,在此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宗教礼仪制度伴随着政治变革所发生的变化。从狄奥尼索斯崇拜的演变这一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民主政治与宗教礼仪制度之间的互相借用与提升:梭伦改革前后,狄奥尼索斯的形象大量地出现在瓶画等艺术作品上;庇西忒拉图时期,建立了城邦集体共同庆祝的城市酒神节;克里斯提尼改革,把酒神颂歌比赛作为融合各部落团结的重要手段。而在雅典民主政体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城邦对狄奥尼索斯崇拜活动也进行了细致的管理,城市酒神节成为表达城邦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魏凤莲:《狄奥尼索斯崇拜与雅典民主政治》,《世界历史》 2015年第6期,第74—85页。论文围绕狄奥尼索斯崇拜的发展变化,以大量史实和铭文及瓶画资料,反映了雅典民主政治与宗教礼仪制度之间的关系。
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城邦特别利用了宗教节日在公民认同和提升城邦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节日(heortē)这个词通常与“宴会”(eranos)和“聚会”(panēguris)相关*Daniel Ogden, ed., A Companion to Greek Relig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190.,也就是说,宴饮和聚会才是节日的两个中心特征。所以,古希腊的节日在祭祀神灵的同时,常常会伴随着大量的食物、民众、娱乐活动,是一种愉悦的宗教体验。而诸神、仪式、起源神话和其他因素所构成的独特节日数不胜数,雅典的节日被记录保留下来的比较多,在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日历中,每年都有144个节日*P.E. Easterling and J. V. Muir, Greek Religion an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98-99.。诺伯特(Elias Norbert)在《符号理论》一书中说,“仪式及其包含的符号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个人成其为个人,社会成其为社会,国家成其为国家并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通过文化、心理的认同而构成的,而这种认同又是通过符号和仪式的运作所造就的”。*Elias Norbert, The Symbol Theory, London: Sage, 1991, pp.123-124.显然,雅典众多节日的存在也构建起了个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而另一方面,众多节日促使雅典公民的生活被日益仪式化。我们不知道公元前6世纪公民大会或400人议事会具体是如何运作的。但在古典时代,从抽签到选举财政官,仪式化的现象已经非常明显,并且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Robin Osborn, “Ritual, Finance, Politics: An Account of Athenian Democracy”, Robin Osborne and Simon Hornblower ed., Ritual, Finance, Politics: Athenian Democratic Accou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p.2-6.比如公餐成为献祭仪式的延续。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每个部落中的50个人的议事会主席团(prytaneis,或部落代表)就在圆庙(Tholos)吃公餐饭,时间为1个月。因为议事会成员是抽签产生的,所以每个雅典公民都有机会吃公餐,在圆庙的餐桌上享用公共献祭(每天都在进行)所产生的肉。其他的城邦官员及城邦的客人也会在圆庙或者是在议事厅(Prytaneion)用餐。用餐的人员还包括因为特殊荣誉而由城邦公共基金供养的人。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之所以激怒了陪审团的成员,是因为他不仅声称自己无罪,而且还要求赋予他在余生享受议事厅公餐的荣誉。*Nancy Evans, Civic Rites:Democrac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Athens, pp.59-60.
雅典虽然没有抽象的教义,但是具有基本的宗教观念和宗教禁忌,他们能够认定哪些是亵渎神灵的行为和思想。当雅典人认定国家宗教受到威胁或遭遇挑战时,保护宗教事务的意识特别明确。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的亵渎秘仪案、赫尔墨斯神像被毁案以及著名的审判苏格拉底等事件中,雅典法律惩罚了亵渎神灵的行为,对传播诽谤神的思想给予了坚决抵制,表现出雅典人对宗教礼仪制度的坚守。所以,民主的雅典并不是绝对自由和宽容的,针对那些违背宗教礼仪制度的行为和观念,雅典人会动用国家力量进行控制和应对。
三、宗教礼仪制度是公民获得身份认同的保证
在雅典,宗教礼仪制度将社会秩序(特别是城邦及其更小的共同体)与超自然能力联系起来,为雅典“提供了城邦的框架和象征中心”。*C. Sourvinou-Inwood, “Whaot is Polis Religion?”, in O. Murray and S. Price, eds., The Greek City from Homer to Alexande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322.在这个框架里,参加祭祀和各种仪式活动的资格是拥有公民权的重要标志,被拒绝参与这些崇拜意味着脱离城邦。家庭、德谟(demos)、“宗族”(genos)、“兄弟会”(phratry)和“部落”(phyle)等城邦各级组织通过各种宗教活动和仪式参与公民身份的确立,由此编织了城邦的社会、政治与宗教崇拜的结构,构建了城邦共同体的认同。
古希腊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单位是家庭(oikos),其含义贴近于英语household一词,*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颜一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在某种程度上说,家庭是一个共同居住的群体,其成员之间具有血缘关系或者姻亲关系,因此具有独特的宗教认同。一个希腊人提到“家”或灶火时,指的是家庭祭祀的地点。在灶火旁祭祀的责任属于一家之主,他往火焰上奠酒,在每顿饭前,往灶火里扔进少量的供奉。灶火熄灭,意味着家庭中的某个成员死去了,重新点燃灶火要有相应的祭祀*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Archaic and Classical, trans. by John Raffa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255.。孩子出生后的第五天,其父亲会抱着他围着灶火跑一圈,之后举行庆祝孩子出生的聚会。新娘出嫁,会被带离自己父亲家的灶火,领至夫家的灶火旁,在这里,她将被培养成新家的女主人。
“宗族”(genos)是家庭的扩展单位,在雅典,宗族是在同一个“庭院的宙斯”(Zeus Herkeios)祭坛前进行崇拜活动的一群人。这个“宙斯”是保护家庭的宙斯,也是好客的宙斯(Zeus Xenios),监督着与外界建立友谊。在希腊,好客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联系着城里的个体家庭,也为城邦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框架。城邦通过宗族组织分配祭司职能,宗族祭司代表城邦与神明进行沟通。*Christiane Sourvinou-Inwood, “Further Aspects of Polis Religion”, in Richard Buxton (ed.),Readings in Greek Relig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8—55.所以,宗族同样具有重要的宗教崇拜功能。
“兄弟会”(phratry,与拉丁语frater“血缘兄弟”同一词源) 被认为是有亲缘关系的团体,有共同的祖先。每个兄弟会都崇拜自己的祖先,也会崇拜所有兄弟会共同的神,特别是兄弟会的宙斯和雅典娜(Zeus Phratrios 和Athene Phratria)。兄弟会控制着获得公民权的渠道,原因是祭祀宙斯的阿帕图里亚节(Apatouria)由兄弟会举办。这个节日是雅典的国家节日,在爱琴海周边的伊奥尼亚人中间和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各城邦中非常重要,它不是全体公民共同庆祝的节日,而是城邦的各个“兄弟会”在各自的崇拜中心进行的。节日持续三天,成员们将举行杀生献祭,并集体共餐,费用源于会费*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Archaic and Classical, p.255.。阿帕图里亚节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父亲将在这个节日上介绍年满三岁的儿子进入“兄弟会”,使其成为“兄弟会”的一员。同时,“兄弟会”的其他成员也可质疑其是否为合法婚生子,是否具有合法身份*Robert Parker, Polytheism and Society at Athe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3.。女孩儿有时也将被父亲展示给“兄弟会”的成员,但她不会像男孩那样获得“兄弟会”成员的身份。*Simon Price, Relig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p.90.新入会的人将被带到祭坛前,并进行献祭。公元前396/5年,属于德科利亚(Dekeleia)德谟的得莫提翁德伊(Demotionidai)兄弟会颁布了一项法令,因为是在徐洛克勒斯(Hierokles)的提议下通过的,因此被称为徐洛克勒斯法令,法令显示出兄弟会要对其成员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
任何未按照得莫提翁德伊兄弟会的法律进行判决的人都要由兄弟会的成员进行判决。他们要在宙斯前宣誓,并从祭坛里拿到自己的选票。如果有人还没有获得兄弟会成员的权利,却已经被允许非法进入兄弟会,他的名字会被祭司和兄弟会领袖从得莫提翁德伊所保存的登记册及副本中删除。他的介绍人将被罚款100德拉克马,献给宙斯。*L. B. Zaidman and P. S. Pantel, Religion in the Ancient Greek 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p.87.
德谟(demos),即村社,是雅典城邦的基层组织,负责审查和登记公民身份,年满18周岁的孩子能否正式成为城邦的公民,“兄弟会”的认可是重要的依据之一*Nicholas F. Jones,The Associations of Classical Athens: the Response to Democrac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Chapter 7.。在雅典,即将上任的执政官在接受资格审查时,为了证明自己的公民权,他不仅要说出父母和祖父母的名字,还要说出他们的庭院宙斯和阿波罗的祭坛以及他们的家庭墓地在哪里。因为这些崇拜地是不变的,能够牢牢地维系男人与城邦之间的关系*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Archaic and Classical, p.256.。另外,村社也有自己的祭祀事务,“村社公民大会需要讨论节日与祭神的事务,村社长则需要负责祭祀活动”。*Robert Parker, Polytheism and Society at Athens, p.64.比如托里克斯德谟的祭祀日历对每个月的节日都有类似详细的规定,并由村社具体实施。
部落(phyle)是最后一个基层组织。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雅典建立了十个新的部落,分别以十个英雄的名字为之命名,每个部落都与自己的英雄之间形成了某种宗教上的联系,比如为自己的英雄建造圣地,在特定的宗教节日里祭祀他们。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提尼改革虽然被认为是激进的民主改革,但是出于宗教祭祀的目的,四个古老的血缘部落并没有被完全废除,依然组织实施某些宗教仪式。*Simon Price, Relig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p.79.
通过家庭、德谟、“宗族”、“兄弟会”和部落,城邦被构建成为一个祭祀的共同体。城邦的保护神护佑着城邦的发展及延续,神和城邦相互依存。有关神的事务也是城邦事务的一部分,由城邦进行全面管理:雅典集市上,公开展示的最大的铭文就是宗教日历。节日规划了一年的结束和一年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活动是从属于宗教活动的:公民大会在开始之前,都要进行净化仪式,包括献祭一头小猪、祈祷和咒语*Robin Osborne and Simon Hornblower, Ritual, Finance, Politics: Athenian Democratic Accou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2.;政治会议的安排受宗教节日日历的影响,而不是相反;城邦历法的制定主要是为了适应公共宗教活动;城邦组织的大型节日,如泛雅典娜节、城市酒神节等,都由专门的官员管理和安排。即使是许诺来世幸福的厄琉西斯秘仪、狄奥尼索斯的疯狂仪式也都被合并进雅典城邦的公共宗教里。城邦不仅比任何团体或个人具有更高的宗教权威,而且为宗教思想和宗教体系的表达提供了基础平台。
四、宗教礼仪制度是城邦文化的核心和基础
与城邦相关的宗教活动通常发生在神庙、剧场、运动场等公共建筑里。这些公共建筑属于城邦的公共空间,它们所承载的公共宗教崇拜活动也都属于城邦的政治活动。而这些活动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促进了城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宗教礼仪制度构成了城邦文化的核心和基础。
首先,宗教礼仪制度本身是城邦文化的一部分。各种形式的献祭、奠酒、净化、游行、舞蹈、节日里的比赛、颂歌和祈祷以及占卜无疑都是城邦文化的展现,尤其是节日。节日构成了希腊人日常生活的节奏,是城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节日带来的休闲以及妇女在节日上担任重要的角色,缓解了社会对人的束缚和压制。德谟克利特曾说,“没有节日的生活就是一条漫长的路,沿途却没有酒馆”*Daniel Ogden, ed., A Companion to Greek Religion, p.201.。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记载了伯里克利在烈士葬礼上的讲话,“我们为从劳苦中放松我们的心灵提供了最多的机会,建立了比赛、祭祀等多种多样的习俗”*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2.38.1。。普鲁塔克也提到伯里克利给了人民很多情感,经常设计一些节日的壮观场面或者城邦中的游行,娱乐人民*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伯里克利》,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1.4.。
其次,宗教礼仪制度是古希腊人强有力的教育力量,他们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社会生活教育多数是在宗教氛围中完成的。这首先得益于父母的言传身教。柏拉图曾生动地描绘了孩子们自襁褓始,就开始听母亲或保姆讲神话故事。青春仪式、订婚和结婚、怀孕、生孩子以及葬礼,在这些人生中至关重要的过渡仪式中,希腊人自有一整套宗教礼仪制度与之相配合。在祭祀仪式上,他们听祈祷词,观看相应的动作和程序*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archaic and classical , p.260;在众多的仪式中,他们经历自身的过渡仪式。可以说,男童和女童的启蒙教育基本上都与宗教节日相关。
以女孩的启蒙为例。在雅典,每四年选出一批5—10岁的女孩子,参加祭祀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的“熊仪式”(bear-ritual)。每一年选出两名7—11岁的女孩,在雅典卫城照看神圣的橄榄树,并为雅典娜缝制一件新袍,时间长达一年,这段时间她们被称为“阿勒福拉”(Arrhephoroi)*Simon Price, Relig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pp.90-94.。之后,女孩子们可能会作为“磨面者”(Grinder),在厄琉西斯秘仪中帮助准备献给女神德墨忒尔的蛋糕。*Yigun Zhou,Festivals,Feast,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Ancient China and Goe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es,2010,p.162.最后,还是在泛雅典娜节的游行中,已成为青年的女子扮演提篮子的角色。所以,女性在成长的不同阶段,将在宗教节日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责任,学习各种技艺,从而为结婚后成为合格的妻子和母亲做好准备。
第三,某些宗教崇拜活动衍生出新的文化形式,促进了城邦文化的发展。希腊早期的各种颂歌,是在祭祀神的过程中,为赞美神而做,作为一种抒发情感的文学形式影响了希腊人,出现了品达、萨福等能代表古代世界诗歌水平的著名诗人。另外,对狄奥尼索斯的崇拜产生了希腊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明确说明戏剧就是对狄奥尼索斯崇拜及其祭祀仪式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1449a。而悲剧的内容、形式以及目的都始终保持着其最初的宗教意味。*魏凤莲:《古希腊悲剧文本中的狄奥尼索斯因素》,《齐鲁学刊》 2013年第1期,第157—161页。
城邦世界充斥着古希腊人独特的宗教礼仪制度,在民主政治的雅典城邦中,这种情况尤甚,民主政治体制需要仰仗于宗教实践活动在生活中各个层面的运作。雅典公民之间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关系,也通过宗教礼仪制度建立彼此之间、他们与子孙及祖先之间、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参加宗教祭祀活动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而对宗教传统的遵循也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雅典的政治和历史。
由此,我们看到,古代希腊的宗教礼仪制度与古代埃及和古代中国的不同,其作用不在于提升统治者的权威,而在于促进集体之间的情感交流和融合。古希腊的宗教礼仪制度与希腊各城邦共同体相伴产生,并在城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强化了城邦的统治方式,确保了公民获得身份认同,构建了城邦文明的核心和基础,从而在深层次上决定了城邦的政治走向。
(责任编辑:郭丹彤)
2016-06-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宗教礼仪制度与古希腊城邦的构建研究”(编号:12BSS006)。
魏凤莲(1969-),女,河南郾城人,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A
1674-6201(2016)02-0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