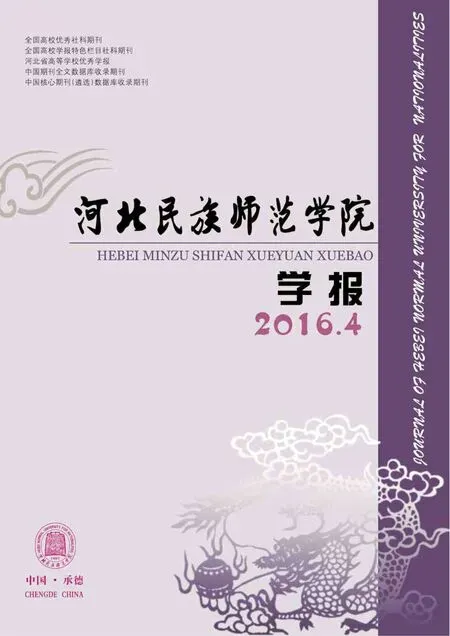灵魂病症自我疗救的药方——评爱斐儿的《非处方用药》
张 翼
(福建警察学院 基础部,福建 福州 350007)
灵魂病症自我疗救的药方——评爱斐儿的《非处方用药》
张 翼
(福建警察学院 基础部,福建 福州 350007)
散文诗集《非处方用药》构成篇篇独立而又内具整体想象的文本世界,于传统题材与古典诗性语言中注入现代审美因子,将中药的表层意义与哲理情思深层勾连,以纯熟的诗艺在本草的叶脉上张举灵魂的纲目,谱写心灵图景与时代风情。诗人将传统医学文化中的药性药理与生命情感、社会意识熔铸,使其在现代文化背景中获得多元化表达。题材的推陈出新,拓展了文学创作的素材与领域,彰显个性化写作的同时又秉具普世的价值关怀,实现审美独特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爱斐儿;非处方用药; 灵魂病症;传统元素;现代性
作为医生,爱斐儿①爱斐儿,本名王慧琴,1966年出生于河南许昌,医生,诗人。作品散见于国内外多种报刊,入选多种诗歌选本。积极救治患者肉体上的疾病;作为诗人,她深知人们心灵的痛楚,执着于精神上的疗伤。爱斐儿的作品坚持对生存意义的拷问,对灵魂皈依的追寻,对心灵残缺的救赎。她以大夫的冷静清醒地意识到:每个人都有病患的可能,当然,也包括诗人自身,如她在诗中所言“不存在不患病的肌体,不死的生”(《茵陈》②本文所引的爱斐儿散文诗作品都选自散文诗集《非处方用药》。)。同时,她又凭借诗人的敏感与热情,抒写个体的生存体验与忧患,实现对存在意义的审美领会。爱斐儿根植于自身的医科职业,以大夫与诗人的双重视角,将身体伤痛与心灵病灶艺术化地呈现在散文诗的创作视境里,在对自我心灵创伤的修复和希望的再生过程中也为当下社会的各种精神乱象把脉,开具一剂剂灵魂的处方。诚如诗人在《非处方用药》序中所言:现在,我只想把这副具有温和疗效的方药呈现给你,它已经经过了我灵魂的炮制,以生命为“君”,以灵魂为“臣”,以思考为“佐”,以热爱为“使”。它的药效以温暖抚慰为主,以寒凉提醒为辅。[1]
医学上,“非处方药”是指那些不需要持有医生处方就可直接从药店购买的药物。一般公众凭自我判断,按照药品标签及使用说明就可自行使用。诗人把散文诗集取名为“非处方用药”,是祈望身体和心灵携带“毒素”的人们能根据自己的病症,自行服用,自我拯救,至少,引起患病灵魂疗救的注意。作者以良善之心,坚信人们仅凭常用药物即能治疗自身;社会确有病症,然尚未病入膏肓,只要对症下药是可以痊愈。德国解释学哲学家伽达默尔曾指出:“通过一部艺术作品所经验到的真理是任何其他方式不能达到的,这一点构成了艺术维护自身而反对任何推理的哲学意义。”[2]通过审美,可以更好地自我认识,自我复归,领受存在的意义。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美是作为无蔽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3],人通过审美体验,不仅可以洞悉自我、感知他人,还可以更好地认识社会。试看爱斐儿如何从药典中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智慧的精华,挖掘中药植物性、药理性背后的文化意蕴,以诗性的语言构筑存在的家园,使读者能够诗意地栖居其间,锻造强健的魂魄以应对周遭各种“现代病菌”的侵袭,借助于审美意识化解当下存在的主体性危机与意义的不确定性。
一、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性重塑
本文阐述的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性重塑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是指爱斐儿不仅揭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本草里药理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赋予每一方药草的诗性内涵,即从药草的实用性中挖掘其审美性的意义。另一方面,从散文诗集中可以看出其在传承中华文化 “观物取象”的思维特性和“草木皆诗”的文学传统上,有所拓展与重构,其本草意象中既沉淀着深厚的历史人文意识,也渗透着强烈的时代关怀和现代意识。
爱斐儿的整部散文诗集《非处方用药》与李时珍的药典《本草纲目》一样,都以入药的植物为书写对象,只是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本草的药理特性,而是在药材的形态与药理上衍生出诗意、诗性。她以艺术的视角挖掘本草中的人文意蕴,勾画出一幅幅人与自然、社会、文化相连的“药性人生”。清代诗论家叶燮认为“变能启盛”(《原诗·内篇之三》),爱斐儿在烙印着民族符号记忆的中草药里注入当下社会文化与人生历程的主体性思考,拓宽了散文诗的创作题材,完成审美意识的现代性发现与建构。文本中传统意象在现代意境中被换位、唤醒,历史典故与当下感悟相融、再生,古典诗学与现代美学相互点醒、深化,在接通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时代精神病症展开治疗,实现对存在意义独特的审美领会。
爱斐儿的散文诗创作既能对外来现代文化合理利用,又能对本民族的诗学传统和其他文化资源进行吸收与创造性融合,为古老的药材注入时代新鲜的人文血液,以探索者的勇气从传统中推陈出新。传统不是轻易就能获取,需要花上巨大的劳动才能得到。美国诗人艾略特在著名的诗学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传统是具有广泛意义的东西。传统含有历史的意识,是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4]爱斐儿的创作实现了艾略特提倡的这种“历史意识”,也许正是这种意识使她敏锐地认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序列,意识到自己与当代的关系。在《非处方用药》中,她充分发挥身为医者的独特优势,将传统文化中用来医治生理病痛的中草药引入创作,并成功将其升华到艺术精神层面,用以解决现代社会中个体存在的心灵困境。诗人选取《本草纲目》中的99种草药,开掘不同药材植物性、药理性背后的文化意蕴,并赋予其浓厚的诗意和人性光辉,使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草药得到全新的现代性的人文诠释。这99味草药,每一味都被爱斐儿以诗性的思维和精巧的语言生发为散文诗的题材,在诗人饱满的情感笼罩与睿智的哲思指引下,一株株中药植物走出古朴、严肃的药典,获得了灵动、活泼的艺术展现。爱斐儿在草木的药性中昭示人性,将人性里的种种邪恶与精神困境寄托在不同植物药性的医治中,以期获得心灵的抚慰与审美的救赎。如“天麻”主要有性平、味甘,祛风湿、止痛、行气活血等药用功效。它的药理作用据《神农本草经》记载可归纳为“三抗”、“三镇”、“一补”,三抗即抗癫痫、抗惊厥、抗风湿;三镇即镇静、镇痉、镇痛;一补即补益。爱斐儿将天麻的自然属性与诗的艺术性融合,赋予草木以文化的社会属性与时代的精神属性,对伤痛、惶恐乃至癫狂的心灵进行镇定、止痛:
总是把你的背影当成诗稿一读再读。
看你笔走尘沙、气吐瀚海,虽然你浪漫的气质有些冷。
只因那些带给你长痛或短痛的爱情,让你的病情深埋诱因。
“天若有情天亦老。”渐老的光阴,让重若千钧的爱,手捧药方进入你的命运。
为你驱除每一场阴雨留下的风湿、创伤留下的剧痛、生离死别留下的气滞与血瘀。祭起镇静的法宝,舒缓你心中的麻木,剔除你骨头中的寒冷,抚平你噩梦中的痉挛;捻亮一根灯芯,用一只照心烛台擦拭浮尘,阻断那一缕发生在你胸膈间的放射状疼痛。
总是面临别无选择的选择,站在唯一的路口,直通苍茫夜色中你那颗孤独的心灵,倾尽一生挚爱。
“她已耗尽一生蓄积的内功。”
---《天麻》
“天麻”所蕴涵的审美意蕴和精神疗效来自作者独特的现代生存体验和生命哲学,其诗质内涵超越了医学上的药性及功效,达到了爱尔兰诗人叶芝所言的感情和理性的结合,使原来普通的药物“焕发出难以言述的智慧的闪光”[5],爱斐儿也借此完成了一个诗人力所能及的现实承担和精神拯救。
又如“苦参”,据《本草纲目》记载:“苦参之苦寒,皆能补肾,盖取其苦燥湿,寒除热也。热生风,湿生虫,故又能治风杀虫。”诗人抓住“苦参”味苦,性寒的植物本性和治疗热病狂邪的药理特性,赋予其人文的书写,使苦参在冷峻寂寥的外表下裸露出除暴安良的情怀——与人性中的邪恶力量进行殊死搏斗:
不能拒绝这个残缺的世界,一次只能面临死亡的一生。
苦与寒与生俱来,炎与凉伴生伴行。你无法抗拒苦寒的命运,亦无法改变自己的性味与归经。
一颗心因为沉重而深陷厚土,举出泥土那部分,却枝叶青翠、花朵幽香,它无意泄露你灵魂的真相。只因高蹈的生命必定携带旷古的孤独与寂寥,在面对沧海的时候展眉一笑。
你过重的心事可比苍茫夜色,忧伤一贯高过夜莺的歌声。无论向上还是向下,神经的突触总是避不开灵魂的呻吟,护佑血液运送人间温暖。
注定在没有回路的曲径,与毒风恶癞和豺狼狭路相逢,唤醒豢养在你左心房的精神虎豹(你磨砺的一把苦寒的宝剑)。你会选择拔剑相向,取敌人首级如探囊。
然后,潇洒转身。
在《本草纲目》之上,留下最后一个侠客式的背影。
----《苦参》
爱斐儿借助文字的津筏渡过古代与现实的关隘,让富于诗意的情感穿梭于古今时空、中外想象之间,使“苦参”潇洒的侠客形象豁人耳目,具有深层的历史文化语境与现代精神内涵,展示了千古“侠客”的核心精神——“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6]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就是当代的“侠客”,他们以语言、文字、思想为武器,批判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为弱者发声,敢于对威权“选择拔剑相向”。
金银花,自古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药性论》记录其性甘寒气芳香,甘寒清热而不伤胃,芳香透达又可祛邪。诗人利用药名的一语双关,写出生活的缤纷色彩。只是诗人不满足于此,从草药名的引申,马上跳转到对药物性能与搭配功效之药理说明的诗性阐释。金银花作为清火败毒的药剂,因病灶与体质的不同,还需对症下药。针对现代灵魂中虚浮、急躁、麻木、虚无、欲望膨胀等不同文化症候,诗人开出不同的配方:
听,用金属的听觉;看,以花朵的眼神;思,以治病的路径……
以右翼炼金,以左翼打造纯银器皿,以月中玉桂研磨人世浮躁病因。
牵手连翘、薄荷与荆芥,用春水一盏,煎盛夏八分,加诗酒半盅,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滚二三沸,热服,解世间温热虚浮表症。
以芳香率野菊花、蒲公英、紫花地丁、紫背天葵子组成五味消毒饮,调制金花银蕊的济世药汁,化孤独痈疽、寂寞肿毒、谎言疮癣。
注定这一生我只能以清风梳头,露水洗瞳仁,以普世心肠挥霍命中的金银,气血同清,三焦同治,用一味药的冷静覆盖灵魂的轻盈。
----《金银花》
让我们循着大夫的叮嘱,“牵手连翘、薄荷与荆芥”,用“春水”的水温,“盛夏”的火候,加入“诗酒”的浸泡,来诊治“世间温热虚浮表症”。对于那些被孤独、寂寞和谎言缠身的病魂,爱斐儿改变了配药,发挥金银花的“芳香功效”,让它与“野菊花、蒲公英、紫花地丁、紫背天葵子组成五味消毒饮”,辅以“清风、露水”般爱与美的“普世心肠”,驱除人心的寒凉,温暖灵魂的孤单。
如上所述,爱斐儿没有拘泥于中草药表层的固定形态和药理性,而是将主体的生命情感融入到草药的物性、药理中,赋予中药以生命,诗化其医治病痛的属性,表达一种抚慰苦难,召唤灵魂的仁爱精神。以药入诗,以诗写药,二者有机结合,谱写一部本草诗典。这不是常人能参悟的,需要长期的医学研究与人文思考才能挖掘出中医药里凝聚的中华民族辩证、虚实、相生相克的智慧。《诗经》伊始虽有“草木皆诗”的文学传统,但传统诗词中的“草木”一般是作为某种情感、情操的寄托,最著名的莫如“松、竹、梅、兰”。然而,从草木的药理性出发,挖掘每一株草木之恰如其性的审美内涵,从而赋予各种草木疗效灵魂与精神的意义,扩大了古典文学里意象的审美内涵和精神境界,使之具有现代性的审美体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在传统承续中进行现代性意义重塑的创造性尝试。南朝评论家萧子显指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爱斐儿正是对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有所吸纳,又能加入当下的思考,挖掘中药文化的诗性品格和散文诗的艺术潜质,才使作品具有了广阔的表现领域和形态无限的可能性。
二、中药的植物性、药理学与哲理情思的深层勾连
散文诗是一种近代文体,是适应近代社会人们敏感多思、波动不居的复杂心理特征而发展起来,“揭橥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内心的深层意识和情感潮汐,成为个体对自我冷静沉思,对社会反省批判以及美学旨趣深厚的文学读本”[7],是审美情感模式内在结构变化在文学创作上留下的烙印。爱斐儿的《非处方用药》穿透具体药物的所指,以各种本草的意象代替生活中的物象、景象、事象,增强作品的诗性功能。通过意象的建构、象征的妙用和意境的创设,引导人们由中药的表层意义进入深层的文化、情感哲思,引发读者对各自人生境遇的丰富想象,通过感兴体验实现身份认同与审美想象,使作品向一切主体开放,获得最普遍的理解。试看《甘草》:
迎风就想流泪,转身就哮喘咳嗽。
症状与冷热、与阴阳、与金木水火土无关。
你眼中的火星,你指尖的烟草味道,能止咳平喘,息风定惊。
注定这一生将被你缠绕,病因和秘方都是你。
今夜,谁似我倒提影子,灵魂出窍。
用自己的眼看清灰烬中抟火的心;用诗歌的手指抠出灵魂深处的灰尘,搬开西西弗斯的石头。
坐在一旁,发烧,寒颤,流泪,咳嗽。
你埋下了病根,带走了草药,一遇分离就复发。
那个病得不轻的人,一定是爱上了白天的星星,夜空的太阳,继发了症状多变的后遗症。
使君啊,一个“念”字,怎能拯救病中的世界重回太平。
“甘草”这个意象新颖且丰富, 诗人借助于主观幻想对这幅具补脾益气、润肺止咳、缓急止痛的草药作了“陌生化”处理,使客观自然之物和人生情感取得诗意性的关联。首句直接切入对病症的描写“迎风就想流泪,转身就哮喘咳嗽”,随后告知以上症状与“冷热、与阴阳、与金木水火土无关”,唯有“你眼中的火星”与“你指尖的烟草味道”才能让“我”—— “止咳平喘,息风定惊”。众所周知,咳嗽、哮喘之人最怕香烟味道,烟草的气味会让患者的气管受到刺激,引起呼吸系统的不适。为何火星与烟草味道却能止咳平喘、息风定惊呢?诗有别才、别趣方能引人入胜!艺术不适用概念,不进行判断、推理,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和直觉体验,创造艺术形象。南宋诗论家严羽曾言:“诗有别才,非关书也;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 诗辨》)。审美意象的创造、联结和转化,只遵从审美自身的规律,不受形式逻辑规则的制约。审美意识对逻辑规律的超越,实际上是人对现实世界限制的超越,无理却甚妙!正是这种非逻辑性,让读者洞悉一位与爱失之交臂的痴情女子的内心。因为“病因和秘方都是你”,“一遇分离就复发”,只有与心上人重逢,爱的伤痛方能治疗。否则,只能继续“发烧,寒颤,流泪,咳嗽”。作为病根的你,带走了“草药”,导致“那个病得不轻的人”,“继发了症状多变的后遗症”。爱之殇非亲历者不能体会其痛。“一个‘念’字,怎能拯救病中的世界重回太平?”“爱上了白天的星星,夜空的太阳”,这种非常态情感的发生,有时非得一些意外的动作“倒提影子,灵魂出窍”,方能正视内心深处的渴望,“用自己的眼看清灰烬中抟火的心”,愣怔之后,自我解密,“用诗歌的手指抠出灵魂深处的灰尘,搬开西西弗斯的石头”,或者根本无法解密,又有多少人类的情感与行为至今仍停留在无法破解的黑暗里。
诗无达诂,对这章散文诗还可以有多种解读。“用自己的眼看清灰烬中抟火的心”,可理解为灵魂里各种欲火的不调和,贪欲之心、嫉妒之心、抱怨之心,甚至是害人之心,而人类往往缺少正视自身的勇气,不愿面对生活的真相与人性弱点,不能直面灵魂的困扰。那让我们借助艺术手段,“用诗歌的手指抠出灵魂深处的灰尘,搬开西西弗斯的石头”。为了静观生命的本相,唯有搬开执念的负累,借助艺术来完善自我的修为,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齐物论》)。爱斐儿对“甘草”意象的选取塑造与诗中情境的创设,使散文诗的含义摆脱单调性而生成丰富多义的复调。意象是现代诗语的要件,它的显现与组合、熔铸与深化,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与审美感染力。如《菊花饮》:
写下这个名字,我看到低首走来的菊香。她的美,已越过诗歌的东篱。
如今,它以随时准备入药的情态,立于秋风渐凉的季节。
她面对的风热来自四面八方,云翳来自雷雨的深处,疔疮肿痛则遍布生活的肌肤。
她披肝沥胆的气质还在,只是风骨略显甘苦。
天凉之后,许多事物将不再以音色的形式发声,包括一枚菊花在庚寅之年的咏叹。
此时,她允许自己坐在渤海之滨,面对永不平息的潮水,像一座岛屿沉潜在在一亿年光阴里。
这多么好!生活总是在山穷水尽之处,给我们留下一星半点峰回路转的余地。
供你零星回味,供你悠长荡漾,供你模仿大海的样子毫不犹豫地清空自己,就像潮汐清空体内的尸体与残骸。
潮起又潮落,又一些事物阻挡不住外力的作用成为空留余音的贝壳与海螺。
而一些菊花,则放弃了风光的枝头,把收敛的光华交给一杯清水,像一盏氤氲药香的菊花饮,忠于生活所赐,含香地活着,或者带香死去。
《菊花饮》里一如既往地感受到诗人浓郁的古典语言风格以及对“草木皆诗”文学传统的秉承,只是加入更多的象征暗示以承载哲理情思。个体存在的主体性危机成为现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当“现代性”问题尚未解决时,世界又已进入了“后现代”时期,谁也无法逃离消费性、物流性、虚拟性等后现代元素的包围,人们被笼罩在挥之不去的“匮乏感”中。作者凭借对“菊花”荣枯轮回的诗意阐释把读者从自然之相引入哲理思考的层面,为现代社会个体生存的困境搭腕把脉,开出疗救的方药。
“菊花”经历了春、夏的萌芽、繁茂的生长过程,终于等到绽放的季节:迎来了生命中最绚烂的时刻!尤其在“秋风渐凉的季节”,能耐寒的花已然不多,正是其傲视群花的机会。然而,菊花却“放弃了风光的枝头”,“它以随时准备入药的情态”,“把收敛的光华交给一杯清水”。生命的美,可以有多种形式,“她的美,已越过诗歌的东篱”。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收获并非都要“获得”,有时“付出”是另一种“得到”。生活中曾“披肝沥胆”地面对过“来自四面八方的风热”、“来自雷雨深处的云翳”,“疔疮肿痛遍布过的生活肌肤”让她“风骨略显甘苦”,此刻生命到达舒展通达的阶段和风淡云清的状态,“毫不犹豫地清空自己”, 抵达道家倡导的“唯道虚集。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忠于生活所赐,含香地活着,或者带香死去”,没有纠结、遗憾,生命最高价值的实现应该就是这样“善与美”的和谐融合吧!诗人用丰厚、善良、纯净的心灵面对自然、人生,用“菊花”这个核心意象为读者营造出独特而曼妙的心灵情境,消解了建立在自我核心基础上的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让主体生命在“氤氲药香的菊花饮” 中优美地完成个体纵向的生命感悟和宇宙洪荒的横向交感。在文学艺术领域“去审美性”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的当下,这样的审美创作尤显可贵。
爱斐儿《非处方用药》的99首散文诗里,都力求将中草药的表层意义、药性药理与个体生存之情感、境遇等进行深层换位、叠加、关涉、勾连,正是这种艺术处理过程中的审美情绪推移,让读者通过“草木”深入自身,感同身受地触及一道道“非处方”的灵魂药效。诗人以纯熟的诗艺在本草的叶脉上张举灵魂的纲目,在药理的适配中追寻诗性的成分,展示心灵的图谱,镜映时代的风景,让内容自身真正触及到个体生命与当下生存的深层关联。
三、审美独特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个体审美意识越独特,个体越能发现、创造独特的美,这种美就越深刻、充分,越能被普遍欣赏。爱斐儿善于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激荡起的强烈情感或瞬间意绪营造独特而深远的情境,使古典美的意境与都市生活融为一体,用审美意象的诗情美为现代人提供一种超越现实视域的更为广泛的心灵疆域,使读者不仅可以徜徉于含蓄隽永的古典诗境,还能静默观世,超越现实生存的体验,回归存在本体,从而穿越表象世界,使“存在”显现,实现海德格尔对艺术的期待:“艺术的本质或许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置入作品。”[3]例如《可待因》:
所有的等待都有原因。
菩提等如来。拈花等微笑。因果等轮回。
我等你,今生的命运。
等到羊群找到了牧人,琴弦找到了知音;
等到金秋穿越了绿色的森林,时间不改变速度的一贯;
等漫山遍野的野罂粟找到了病因般的美,等到真理般的诗歌成为一种瘾。
我等在文字的那端。
等不来被爱就去爱你。
天色尚早。道路上的人间正行走着微暖的春寒。
打扫完前尘往事与来世轮回,剩下比虚无更真实的余生足够等一次美景重现。
无论早晚,伴随恍惚的清醒与醒后的麻醉。
症状必须是爱到痉挛,疼到不能忍。
剂量是关键。适量的等是药。
过量的等是毒。
不宜久服。成瘾难戒。
诗人以“菩提等如来。拈花等微笑。因果等轮回”的排比句式将追寻、等待、回响等人生重大命题一气铺排于眼前,让人不由思考“命运”这个沉重的话题。不同的追求,会面对不同的命运吗?“羊群”找到“牧人”;“琴弦”寻觅“知音”;“森林”等候“金秋穿越”;“野罂粟”绽放出“病因般的美”。“羊群”、“森林”、“牧人”、“琴弦”、“知音”、“野罂粟”这些具体可感的意象选取与情境描绘,聚合了传统与现代多种复合的文化心理和美感因素,将抽象的人生命题形象化,同时又利用这些意象群内在复杂的关联呈现人生选择与命运安排错综而微妙的关系,以主体独特的审美眼光去发现、表现它,赋予现实以个性化的审美意义。
沧海可以变桑田,然而,有些事情却改变不了,正如“时间不改变速度的一贯”,有些时候,有些人躲不开冥冥之中的注定。“爱到痉挛,疼到不能忍”时,不得不接受宿命的安排——“等不来被爱就去爱你”。孤独,是现代人的生存常态,即使美好的事物或情感,也只是暂时的幻象——“无论早晚,伴随恍惚的清醒与醒后的麻醉”。诡谲不定的都市生活,纷扰难辨的世相人心,都使现代人心智与情感上的困扰有增无减。如何认识自己,把握自我?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谢林认为:“艺术家的职责就是挖掘他自己,最重要的就是挖掘他自身里面黑暗的无意识的力量,通过痛苦而暴烈的内部斗争把无意识提升到意识的层面”[8]。面对内在的某些无限精神的悸动、痉挛,需要麻醉、镇静,但“剂量是关键”。审美意识超越了现实意识的局限,是对世俗生活的升华,让人的无意识与自觉意识完全同一。作为大夫同时又是诗人的爱斐儿深知“可待因”这种麻醉药物对肉体与精神的药效与副作用。“适量的等是药。过量的等是毒。不宜久服。成瘾难戒。”人类虽卑微,但也还有精神向往,渴望灵魂的救赎与超越。
《非处方用药》体现了爱斐儿极强的自我表达欲望,其作品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个体审美意识间并不互相矛盾、排斥,每个人尽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但并不否认他人的美感。艺术品的独特性与普遍性是统一的,美感往往具有共通性。审美意识是对现实生活和意识形态的超越,是对生存意义的直接体验,达到哲学意识的高度。波德莱尔认为优秀的作品肯定是含有哲学感的],是深邃的哲理意蕴与生动艺术的统一。诗人从草药名字里引申开来,在传统药材中注入现代的情思,完成个人之情到人性之爱的升华。诗人不排斥重大的社会题材,从中发现它对个人历史命运的影响;作者也不排斥社会理想,把它内在地包含于个体价值追求中,展示对生活具有韧性的全面救赎。
散文诗集中的99种入药植物,每一种都是对生命与自然最质朴的表现与象征,每一种或几种配合同用,都关涉灵魂不同病症的疗救。如弥漫清苦花香的艾草能“苦燥辛散,理气血、温经脉、逐寒湿”,具有治疗神经疼和过敏的功效。现代社会中,自我不是理性的主体,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也不能主宰社会。自我是不确定的身份,人格分裂,神经过敏,内心脆弱。人们如何面对自身的主体性失落?不妨让“比岁月香,比时光暖”的艾草来护佑,它“善炙人间冷暖寒疼”,“那些找不到方向的风湿和神经疼病因,那些被失血带走的江河气脉,那些诱发变态反应的世纪性过敏源,以及一切症状之后留下的忧伤空白,被一颗本草的心紧紧抱在胸前。(《艾》)”政治的黑暗,礼法的虚伪,才华无法施展的苦闷,内心的彷徨,这些不仅是人心纠结所在,也是时代的症候,“风邪侵袭,也不是哪个朝代独有的病症”。紫苏虽可解表散寒,行气宽中,但有时也需要与其他药材配伍,方能解“胸闷不舒,脾胃气滞,气滞痰结”的沉疴痼疾。人生,需要知己来共同抵御世间的风邪冷气,“生姜,前胡,藿香,三两个知己走出《本草纲目》,和你一起纵论世间风邪,在寒温间摆渡。”象孟浩然与故人“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如“竹林七贤”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排遣胸中气闷。并非时刻都能与好友喝酒、品茗、纵歌来寻求精神寄托,气滞之时更需要自己内在的调理运化来平息“内心的风暴”,以至真至善的终极价值来抵御世间秽恶之气的侵袭,“而你不只需要从容的琴弦,还需要嵇康那种生死度外的定力”(《紫苏叶》)来化解灵魂深处的气滞与血瘀。香燥、寒湿症的患者需要“轮廓温婉、淑静,剑胆琴心”的木香“轻挽剑花如墨迹,不动声色逼出他体内虚寒。(《木香》)”那些焦虑而抑郁的灵魂是这般“让焦虑控制的中枢神经,怎不让忧郁从病因脱颖为症状”,不妨让性善通达的“远志”来帮助开心气而宁心安神,感受“岁月的静好”,“留一份闲情,给自己温一壶酒,添一只结霜的青梅”(《远志》)。江湖中躲不开“明枪暗箭,跌扑杖疮”的受伤肉体只能留给三七 “呕心沥血”去“每天甄别伤口的质地,腐烂的成色”,“对一切不可能复原的新伤旧痕清创缝合,对危机四伏的衄血、崩漏殚精竭虑”,而让这些灵魂“冷却了三分癫狂,七分燥热”,三七也不由要“打了一个小小的寒噤”(《三七》)。
每一味药都有独特的药理特征与功效,但却有共同的追求“一颗仁心,要拯救的不是对错,奸雄。只是,命与非命”(《云南白》)。缘于此,《非处方用药》构成篇篇独立而又内具情绪串联的文本世界。这种内在的贯连,是对日常生活以及精神世界幽微的洞察和体悟,是对人类共有经验的思考与超越。爱斐儿推陈出新的题材拓展了散文诗可撷取的素材与可接触的领域,体现了个性化的写作风格。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认为:“一个创造者,他知道如何深刻和真实地表现完全属于个人的经验,同时又超越个人的或社会的领域……文学没有必要四处搜寻政治现实,或甚至为那些换来换去的制度烦恼;他可以超越它们,同时依然可以回答制度在人们心中唤起的问题。”[9]爱斐儿超越性的个体书写,为陷入精神困境的人们寻找出路,对时代的心灵病症进行拯救,她的个人小我经验可以涵盖甚至超越国家的大我经验。也就说,诗人从社会的“大叙述”里抽身而出,“深刻和真实”的个性书写依然可以使其作品秉具普世的价值关怀,实现审美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综上所述,爱斐儿在传统医药里灌注对个体生命的思考,打破中药与药性、药理单纯的对应关系,将传统的普通药材引入文学的创作视野。诗人笔下的药材经过审美经验的淘洗与润泽,带上了主观的人文色彩,一方面仍具植物属性与药理性,另一方面又与主体情思相通。每一种药从物理视角审视仍是药材本身,但情绪逻辑上都应和着作者的情思,加之中医术语的诗性传神表达,更增添了阅读的趣味性,延展了主题与意境的丰富性。诗人将传统医学文化中的草药与生命情感、社会意识熔铸,使其在更广阔的现代文化背景中获得多元化的欢欣表达,正如艾略特评论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时所说:“诗里引进了某种新东西,某种在现代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使用了普通生活中的意象”,“使意象达到了最大的强度——将意象按原样表现出来,却又使它代表较它本身为多的内容”[10]。爱斐儿凭借诗人与大夫的双重身份,力图为现代社会灵魂病症开出自我疗救的精神良方,开启诗歌——这种深植于人们血脉深处的艺术以潜移默化的功效,为心灵郁结的人们辛温散寒,治愈内心深处的顽疾。这应该是爱斐儿《非处方用药》创作的动因,也是其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在。
[1]爱斐儿.非处方用药[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2.
[2](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8.
[3](德)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3、21.
[4]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0.
[5](英)戴维·洛奇.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M].葛林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58.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722.
[7]张翼.20世纪上半期中国散文诗的审美现代性发现与建构[J].福建论坛,2014,(1):139.
[8](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M].吕梁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8.101.
[9](捷克)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M].景黎明,景凯旋译,台北:时报出版公司,2003.75.
[10](美)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M].王思衷编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113.
Self-Treatment Prescription for Soul Disorders:Comments on Aifeier's Non-Prescription Drugs
ZHANG Yi
(Foundational Course Department, Fujian Police College, Fuzhou 350007, China)
In the prose poem collection Non-Prescription Drugs, the chapters are separate but constitute a whole world of imagination. The poet injects modern aesthetic factors into traditional themes and classical poetic language, connects the surface meaning with the deep philosophical emotions for Chinese medical herbs, and with skillful art of poetry, writes compendium of soul on the veins of leaves, describing the soul of modern man with the style of the times. The poet combines the medicinal properties in traditional medicine culture with emotions of life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which makes the poetry diversified in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With theme innovation, the poet expands the field and material of literature and creative writing, highlights personalized writing style and at the same time has the value of universal care,and achieves the unity of aesthetic uniqueness and universality.
Aifeier; prose poem; soul disorder; traditional elements; modernity;remodeling
I206
A
2095-3763(2016)04-0048-08
2016-09-02
张翼(1975— ),女,福建福州人,福建警察学院基础部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散文诗的文体学研究”(项目号15YJC751062)成果;2016年度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人才计划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