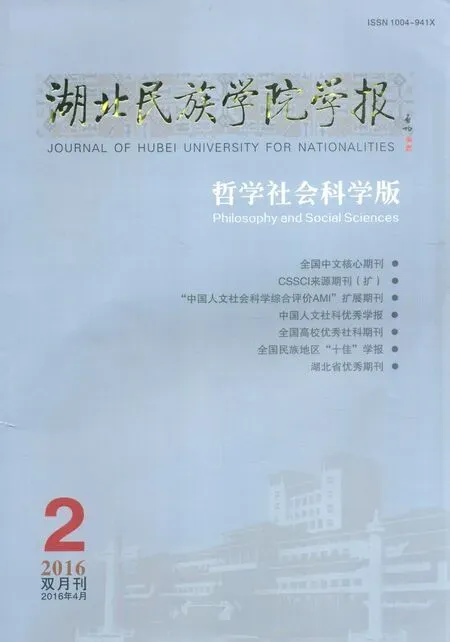勒奎恩作品中的海德格尔语言哲学观
肖达娜
(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四川成都610066)
勒奎恩作品中的海德格尔语言哲学观
肖达娜
(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四川成都610066)
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Le Guin,1929-)最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作品,莫过于其奇幻系列代表作《地海传奇》。由于作者从小便接触了老子的《道德经》,且故事中体现了中国传统老庄哲学精神,于是引发了评论界对该作品中的东方道家思想略显偏执的定性及推崇。在笔者看来,除了对道家思想的运用,作者在该系列作品中还表现出极具哲理的语言哲学观,而这些语言哲学观与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语言的运思有诸多相通之处。通过对勒奎恩奇幻系列作品的创作背景及内容的分析,探索并证实作者的语言哲学观与海德格尔语言哲学观的契合之处,以期获取对作者语言哲学观的准确解读。
勒奎恩;海德格尔;语言哲学
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Le Guin,1929-)是美国著名的科幻、奇幻、女性主义以及青少年儿童文学作家。她至今作品不断,创作门类跨度甚广,包括文学评论、诗歌、散文、小说、童书及剧本。她撰写的跨世纪奇幻代表作《地海传奇》部曲由一系列发生在想象中的群岛的故事构成:《地海巫师》(A Wizard of Earthsea,1968)、《地海古墓》(The Tombs of Atuan,1971)、《地海彼岸》(The Farthest Shore,1972)、《地海孤雏》(Tehanu,1990)、《地海故事集》(Tales form Earthsea,2001)、《地海奇风》(The Other Wind,2001),故事构思奇妙、语言优美,深受读者喜爱,与托尔金的《魔戒三部曲》(The Lord of the Rings,1954-1955)和刘易斯的《纳尼亚年代记》(The Chronicles of Narnia,1950)共享“西方奇幻三大经典巨作”的美誉。由于勒奎恩曾在访谈中表示中国道家思想是该系列作品的灵感来源之一[1],于是评论家们花了大量笔墨去挖掘其中蕴含的东方哲学;也有学者从女性主义、女性生态主义等视角下工夫,议论西方性别观与道家阴阳观的结合;更有甚者,将作者的语言观也全全归于老庄话下,似乎整部作品惟有老庄元素的存在。
诚然,道家思想对勒奎恩的成长颇具影响,她14岁时就开始接触《道德经》,后花了整整40年的时间与人合译《道德经》,表现出她对道家世界的向往和追求。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其语言观仅仅是受老庄思想影响而形成的。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的特征,而语言观的形成,与一个人的成长历程、生存环境以及社会关系密不可分。从其所处的年代和创作背景来看,勒奎恩在作品中显现出的对语言的感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20世纪语言转向的影响,其深邃的语言思想远不是两千年前便已成形的传统的道家哲学所能涵盖的。本研究以作者本人为观察的中心,立足其自身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分别从哲学、文学思潮和同时期作家作品的影响以及勒奎恩自己作品文本分析入手,探索其作品所体现的语言观的形成动因与具体表现。
一、语言论转向及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
20世纪初期至60年代可以说是世纪哲学发生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最兴盛的时期,也是大家们积极建构语言乌托邦的鼎盛时期。阿佩尔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总结西方哲学的发展:古代哲学的研究重点是本体论,近代哲学重视的是认识论,到了20世纪,语言成了哲学所关注的重点。在阿佩尔看来,哲学归根到底就是对语言的思考[2]。20世纪初期,哲学史上发生语言论的转向,使作为语言的哲学逐渐取代作为认识的哲学而成为世纪哲学的中心。从世纪初弗洛伊德从心理分析角度创作的《梦的释义》(1900),本雅明的《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1916),卡西尔于1923年在《象征形式的哲学》卷一的《语言》一文中所谈到的语言的象征及寓意,到30年代英加登从现象学解释学入手创作的《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海德格尔于1936年首次发表的关于诗性的语言《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继而进入40-50年代以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观,50-60年代以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1954)与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1960)为代表的视觉语言学,以及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在《写作的零度》(1953)中提倡的语言与文学的互训,无不呈现出语言在哲学世界中的繁荣之势。语言哲学不仅成了20世纪哲学家们最重要的研究领域,还促使西方后现代哲学、文化观念和方法论发生了巨大转变,与此同时,文学批评观念和文学创作也受到了极大影响。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现实世界变得荒诞、混乱却也充满希望和幻想。战争摧毁了旧生命、旧观念,新生事物接踵而至,在这样一个精彩纷呈却又悲喜交加的时代,各种文学思潮纷至沓来,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改变,文学不光是一种单独的文学存在,还同作者、读者、媒介、社会等产生了联系,逐渐演变成一种文学复合体。从前现代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20世纪西方文学衍生出诸如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其中后现代主义发展最为深远,体现出较现代主义更加彻底和决绝的反传统精神。对于后现代主义,学界争论颇多,不断出现新的观点,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家伊哈布·哈森就曾评说:“后现代主义的内涵与当今许多术语有某种亲缘关系,而那些术语本身的内涵就是不确定的。”[3]它主张无中心、无权威;提倡多元化的创作方法;否定构建任何文学规则。于是,在作品的内容、意义被消解之后,将创作重点转向了写作自身,语言也因此而成为创作的中心[4]。深受“语言论转向”以来西方学术文化范式转换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坚信语言本身就具有意义,认为语言就是目的。他们不断在语言文字、技巧手法、叙述话语方面创造新的花样。有的钟情于对传统文学和经典作品的模拟戏仿,以期达到消解神圣、解构经典的意图;有的则以纯粹的文字排列组合、词语搭配为乐,把玩各种语言实验、话语游戏,从中获取创作的乐趣。可见,在大半个世纪中,语言论转向对现代西方哲学和文化研究甚至文学创作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语言学也因此而成为西方人文科学的领头学科。[5]
如果说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叔本华、帕格森、尼采、弗洛伊德等人高深的思想哲理,那么后现代主义则主要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智者们的运思。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海德格尔相继作了六篇关于语言的演讲报告《语言》(1950),《诗歌中的语言》(1952),《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1953),《语言的本质》(1957),《词语》(1958),《走向语言之途》(1959),并于1971年英译成集,名为《诗·语言·思》,其间他致力于让语言挣脱形而上学的牢笼,将语言在哲学中的地位推向了极致。
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来源驳杂,亚里士多德、歌德、哈曼、海贝尔、黑格尔、赫尔德尔、洪堡特、胡塞尔、康德、老子、尼采、柏拉图、席勒、苏格拉底等学界的大家们都曾先后成为他在语言的研究过程中所引证或辩驳的对象。他集大家之所成,运思逾半个世纪,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诗性语言观。仔细阅读这半个世纪中有关语言的论著,会发现大家们的语言思想相互影响,互为佐证,存在不少相通之处。譬如海德格尔、巴尔特对于语言本质的阐释就与20世纪初卡西尔的看法暗中契合。卡西尔认为语言是“隐喻”,海德格尔主张语言是“诗”,而巴尔特极力证明语言的本质就是文学。卡西尔钟情于从原始神话中探索语言的隐喻与象征意味,相信“语言”是艺术,是象征的基石;海德格尔倾情于诗歌的深层内涵,认为诗是思,是歌唱,是语言,是存在的原初本质的现象学显现;而巴尔特则强调“文学是美的化身,文学的写作是对语言至福境界的一种热切的想象,文学语言的清新象征一个新的亚当世界的完美,也即是说,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6]。三者的看法都特别侧重语言的清新及完美,隐现出语言的乌托邦特质[7]。实际上,他们关于语言本质的思想是基本相通的,因为自古以来,神话就是以诗为载体来传达世界的隐喻及象征,来体现文学的至美。而歌唱即是诗歌,诗歌即是隐喻,同时诗歌又是文学的发端。神话由诗而来,歌曲为诗而唱,文学以诗而起。“诗”中所展现的语言,便是语言的真实显现,语言的原初本质之所在。如此一来,我们又回到了海德格尔的诗性语言观中。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中国老庄哲学给予了颇高的认同,曾与中国学者肖师毅合作翻译老子《道德经》的部分经文。他用德文的“道路”来翻译老子的“道”,极好地分析了汉语思想中的“道”与“道路”的异同。海德格尔大胆猜度“道”就是指开辟道路的道路,一切皆道路。主张“道”这种“道路”高于理性、精神、意义等形而上学的规定性。《庄子·齐物论》中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8]、老子《道德经》25章中“寂兮廖兮”、73章中“不言而善应”[9],也都被海德格尔一一吸收,融入到自己对语言的探索之中,突出了语言的寂静之声的重要内涵。
在《走向语言之途》中,海德格尔对洪堡特所作的“语言的最初始的状态就是歌唱”的定论给予了肯定。洪堡特认为:人类是“歌唱的生物”,其他动物虽然也会歌唱,但只有人类的歌唱是伴随着具体的思想内容的[10]。海德格尔提出,诗即是思,是歌唱,是语言。他同时还特别关注洪堡特1836年《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对洪堡特的“语言即精神”的观点做了深层的分析并得出结论:洪堡特的语言之途是以人为指向的,经由语言而导向另一个目标:探索和描绘人类精神之发展。但是如此理解的语言本质,却没能把语言的本质显现出来。他说:“我们不再能寻求那些普遍性观念,诸如活动、行为、作用、精神力量、世界观、表达等;我们不再能在这些观念中把语言处置为那种普遍性的一个特殊情形。我们应该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这就是要向语言的固有特性靠近。”[11]249
总的来说,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可归纳为:命名在召唤,召唤使物显现;名称即词语,词语让物存在,词语具有神秘的支配作用;沉默更胜于言谈,寂静之声就是本质的语言;诗就是歌唱,歌唱也是语言,歌唱就是把道说聚集到歌中。
二、勒奎恩作品与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
仔细分析勒奎恩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勒奎恩对语言的思考及运用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运思不无相似之处。首先,海德格尔认为名称是具有描绘作用的词语。它们将已经存在的东西送达表象性思维。凭借它们的这种描绘力量,名称,也就是词语,“证实了自身对于物的决定性的支配及领导地位”[11]223。他的这一观点在勒奎恩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在奇幻世界中,魔法施行的三大要素包括咒语、仪式和巫师的礼仪状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咒语,亦即语言,通常由一个或若干词语组合而成,具有召唤万物及启动超自然的能力。在小说《地海巫师》中,巫师只要知道一物的真名,便可召唤此物,使物呈现,就如同词语对物的支配作用。格得的师傅欧吉安,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法师,他也是通过对弓忒山说话来让一座城池免于震灾,他用语言安抚它,如同镇服一只受惊吓的猛兽,平定了高陵的崖壁颤动[12]33。后来格得到柔克学院系统地学习巫术,包括万物之名、符文、咒语等也都由词语构成。小说中很多诸如此类的关于名称、词语的作用的描述都影射出海德格尔对于词语的定义:“词语突兀而起显示出一种不同的、更高的支配作用。”[11]223
地海世界中的一切生物的存在都始于语言创造者为万物命名。海德格尔通过对格奥尔格诗集《新王国》(1928)中的《词语》一诗的分析,反复验证了词语与存在的关系,强调只有词语才赋予在场,即存在——在其中,某物才显现为存在的状态。如同《地海巫师》中,要想成为人,必先经过命名,获取真名,才得以存在。故事主人公格得便是在其成年礼中由大法师欧吉安赋予其真名的。在地海世界中,人的真实自我和生命本质就存在于其真名之中。所以人们之间一般不会相互透露真名。因为知道一人的真名,便掌握了这个人的本质,从而掌控他的命运。相反,因为黑影没有名字,所以终究只是一个“非生非死”的无形之物,只能借寄于他人的身体,以尸偶形体存在,占他人之嘴说话。所以尸偶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人的声音,倒像是没有嘴唇、粗声粗气的野兽勉强在说话[12]139。又如《地海古墓》中的黑暗力量“累死无名者”(Nameless ones)即是代表黑暗、毁灭和疯狂,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神圣力量,先于光明而存在[13]。这生动地揭示了地海世界中名字与存在的关系。
其次,海德格尔指出,道说作为显示而居于大道之中,是成道或居有的最为本己的方式。大道在沉默中展开世界,万物在寂静之中演变进化。他认为“道说(sagan)”和说话不是一回事,说话单纯是指语言之发声,而道说是神秘(Geheimnis),甚至是无需表达的。小说《地海巫师》以《伊亚创世歌》开头:唯静默,生言语;唯黑暗,成光明;唯死亡,得再生:鹰扬虚空,灿兮明兮[12]1。其中的第一句“唯静默,生言语”,便是指一切都在静默中得以显现。在小说的结尾,格得与黑影合二为一,目击者维奇又再一次响亮地唱起了《伊亚创世歌》,首尾呼应,揭示了故事的主题思想及世界的自然运行之道。这种静默的召唤极好地应和了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本质的看法:语言之本质是属于使四个世界地带(大地与天空、神与人)“相互面对”的开辟道路的运动的最本己的东西。语言保持和维护着世界诸地带,语言本身,即是道说,它作为无声地召唤着的聚集而为世界关系开辟道路。而这种无声召唤的聚集,正是“寂静之音”——本质的语言。[11]212
欧吉安大法师也拥有沉静的性格。他教导格得不要急于学习法术的施展,而应先观察、了解事物的本质,学会倾听寂静之声。欧吉安是一位沉默的智者,他喜欢在丛林里散步,喜欢观察、聆听,话很少,因此被人们称为“缄默者”。《地海孤雏》的“欧吉安”一章回忆了欧吉安寂静的一生,恬娜陪伴他走过了最后的人生,她说:“如果有人要为他写歌谣,……,他曾是沉默的人,而现在他完全地沉默了,只有沉默。”[14]小说中法师欧吉安的生活状况极像晚年的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晚年隐居于黑森林地区,树林中有许多小路。沿着小路走,每到一个转折处,就会有新的景象映入眼帘,每个新景象仿佛一个新的世界。他领悟:人生恒走在道上,沿着道,可以领略不同的风景。人所需要的,只是静默的观察,欣赏。”[15]
最后,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因为作为道说的语言乃是大道之方式。此所谓方式(Weise)与其说是模式(modus)和样式(Art),而不如说是歌、曲调,即吟唱着进行道说的歌[11]268。勒奎恩亦在《地海巫师》中穿插并介绍了多首传世歌谣,体现诗歌的魅力与作用。故事主人公格得的成长总是少不了歌曲的陪伴。从成人礼上《龙主行谊》的诵唱到重大节庆之际师徒们齐唱《少王行谊》《冬日颂》《厄瑞亚拜行谊》等歌曲,再到岛民们为纪念格得的屠龙奇迹而编唱的《雀鹰之歌》,以及师傅欧吉安通过念诵漫长的咒语和吟唱《英雄行谊》安慰受伤的格得,处处展现着歌唱的纪念、颂扬及鼓舞作用。最后格得反追黑影,在无边的黑夜里航行,他大声吟唱《冬日颂》和《少王行谊》等诗篇,为自己打气,给自己力量。他还专门教导“手岛”上年轻的诵唱人《莫瑞德行谊》与《黑弗诺之歌》,让岛民们了解英雄的故事,通过雄伟的歌谣记事来传播文化,增进岛屿之间的文化交流。好友维奇亲眼目睹格得与黑影最后的搏斗以及光明与黑暗的相遇、交会、合一,他一边航行,一边大声的诵唱《伊亚创世歌》:唯静默,生言语;唯黑暗,成光明;唯死亡,得再生;鹰扬虚空,灿兮明兮。《地海彼岸》中更是多次强调歌唱的作用:莫瑞德之子亚忍,也是未来的王者,善以歌曲明志,在群岛区的长舞节上,大家以歌唱来抵抗恐惧,当众歌者尖细的声音有如远处海鸟的鸣叫般消逝时,亚忍高唱《伊亚创世歌》为全岛人民驱散恐惧[16]。这显现出歌曲对人类的开化及教导作用。在《地海故事集》的“黑玫瑰与钻石”一章中,钻石虽拥有巨大的巫师潜质,却坚持放弃巫术的学习,坚持追求歌唱事业,陪伴自己的爱人做一位流浪的歌手[17]。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诗即是歌,而歌中道说的即是一种赞美,一种颂扬,laudare(赞扬,赞美)是歌的拉丁文名称。把歌道说出来就是吟唱(singen),歌唱(Gesang)就是把道说聚集到歌中。”[11]225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的诗性语言观对勒奎恩的奇幻系列创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故事从命名与存在的意义、词语的支配作用、寂静之声的道说、歌唱对道说的聚集等多个方面都呼应了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在奇幻世界展现出语言的力量,见证了语言创生的奇迹,使其作品丰满且富有哲理。
综上所述,勒奎恩的奇幻文学创作,除了目前学界较为关注的受到中国老庄哲学影响外,还顺应了当时语言论转向的学术思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同时代其他女性文学创作的影响。仅从《地海巫师》这一作品的奇幻风格和语言元素便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一点。其中多项语言元素的运用恰好充分体现出海德格尔语言哲学的深刻影响。因此,勒奎恩的文学创作不排除有东方道家哲思的痕迹,但是也绝不可忽视其所生活的时代西方哲学与文学思潮尤其是海德格尔语言哲学的影响,而这一点正是目前研究的薄弱之处。
[1]Ursula K.Le Guin.“Dreams Must Explain Themselves,”The Language of the Night:Essays on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 [M].ed.Susan Wood.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2:44.
[2]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
[3]伊哈布·哈森.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12.
[4]亢西民,李家宝.二十世纪西方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47.
[5]龚翰熊.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102.
[6]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09.
[7]王一川.语言乌托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172.
[8]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7.
[9]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11.
[10]胡明扬.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4.
[11]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2]厄休拉.勒奎恩.地海巫师[M].蔡美玲,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0.
[13]厄休拉.勒奎恩.地海古墓[M].蔡美玲,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88.
[14]陈荣华.林中路(Holzwege)[J].台北:时报,1996(V).
[15]厄休拉.勒奎恩.地海孤儿[M].段宗忱,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81.
[16]厄休拉.勒奎恩.地海彼岸[M].蔡美玲,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81.
[17]厄休拉.勒奎恩.地海故事集[M].段宗忱,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81.
责任编辑:王飞霞
H0-05
A
1004-941(2016)02-0169-04
2016-03-11
肖达娜(1981-),女,四川安岳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