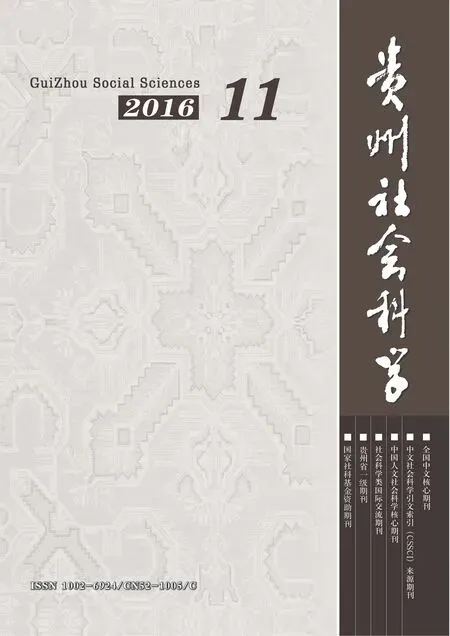1935年抵制暹米风潮及其历史困境
周石峰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1)
1935年抵制暹米风潮及其历史困境
周石峰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1)
20世纪上半叶日益激烈的暹罗排华问题,深刻影响了中暹关系的历史走向。1935暹政府强行取缔华校,中国舆论鼓吹“民众外交”、“武力护侨”和“经济绝交”。付诸实践的抵制暹米运动,沿袭了“民众台前、党部幕后”的一贯模式,目的是促使暹方取消排华苛例,并与我国订立商约和建立邦交。暹方撤换教育部长是唯一成效,两大目标均未实现。抵制暹米重创华侨经济,有悖护侨初衷;粤省高度依赖暹米,经济抵制则缺乏物质保障,双重经济困境决定了运用经济抵制手段实现政治目标的低效性。
暹罗排华;抵制暹米;历史困境
20世纪10年代以降,暹罗民族主义勃兴,①排华问题愈演愈烈,深刻影响着中暹关系的历史走向。1935年暹罗强行取缔华校,我国朝野则互为因应,采用外交交涉、抵制暹米和赴暹考察等手段,与之进行角力,以期促使暹罗取消排华苛例。目前,暹罗排华问题,学界已有不少讨论,但多集中于排华事件的梳理或排华原因的分析,而我国之应对问题则稍显薄弱,尤其是抵制美货、抵制英货和抵制日货的成果已经非常丰硕,②但抵制暹米问题则尚无专文论及。③本文首先厘清抵制暹米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而从华侨经济和粤省民食两方面,重点探讨抵制暹米成效甚微的经济困境,期望拓宽中国抵制外货史的论域。
一、暹罗排华与抵制暹米
1910年拉玛六世登基,下令征收华侨人头税,华侨罢市相抗,“嗣因暹政府用威力压迫,不得不屈服,自此以后,暹人乃惊觉华侨在经济上之势力伟大,而取缔华侨之手段,亦从此开始矣”。除在政治与经济上压迫华侨之外,对华侨文化亦“常怀消灭之心”。1918年颁布《民立学校条例》,1932年颁布《强迫教育条例》,“渐改渐严,已使华校成为教授泰文之学校,失去其存在之意义”,“迨新军人秉政,连此有名无实之学校,亦不容存在”。④1935年1月,暹教育部宣称施行“十年教育计划”,勒令华侨所办中、小学自4月1日起一律停办,强迫华人接受暹罗教育。且据暹罗教育部长及秘书解释,此一政策乃“专施于华校”。各华校接到此一“突如其来之通告,无不惊惶失措,慄慄危惧”。⑤在联合抗争的同时,华侨代表陆续归国,不断吁请我国政府和民众予以援助,以期迫使暹政府取消各种排华苛例。此即“华侨教育事件”,或简称“华教事件”。
兹事体大!既牵涉“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又关乎中暹两国“文明声索之争”。⑥华侨反对暹罗排华之诉求同中国政府与暹建交的意图高度耦合,因而“华教事件”演绎为两国之间的角力。针对暹罗当局强行取消华校一事,中国舆情汹涌,有关应对方策亦甚嚣尘上。《益世报》社论声称“欲达到外交胜利,则仍赖于民众之后盾”,主张由政府与暹罗折冲樽俎,而民众进行经济抵制,“定可刚柔互济”,取得外交实效,⑦亦即近代中国颇为盛行的“民众外交”。而《独立评论》则鼓吹“武力护侨”,认为“蕞尔暹罗,胆敢侮辱中国”,“暹政府若再执迷不悟,原供人做摧残华侨傀儡,则我们最后唯有用武力以实践护侨政策”,即使此举引起国际纠纷,甚至“掀起世界大战亦在所不惜”,因为“情势险恶至此,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冒险以求生”。⑧
对南京国民政府而言,“武力护侨”论显系纸上谈兵,而“民众外交”则自可采行。南京当局在与暹进行外交交涉的同时,并密令民众团体抵制暹米,以期运用经济抵制手段逼迫暹罗与我建交。早在1933年,广东拟征收洋米入口税,向以中国为大宗出口市场的暹罗当局迭开国务会议以为因应,而其舆论亦指责政府不与中国订约为失策。我国商务委员遂电外交部,建议趁机电令我国联代表设法与暹代表提订商约,以保护侨民权益。顾维钧主张提高暹米入口税率,迫使暹方就范,建议电告驻日公使蒋作宾,如暹使主动谈及米税问题,不妨趁机要求中暹早订商约。1935年3月30日,广东粮食统制会率先通过“禁止暹米入口案”,作为暹罗当局压迫华侨的反击手段。⑨而南京政府政务院则转请中央党部密饬各地党部指导民众团体抵制暹米,并建议禁止暹米入口,作为对暹谈判之筹码。⑩5月1日,外交部等再审此案,认为实行禁止暹米进口困难重重,暂时缓议,但为促成暹罗与我早日订约,可先提高暹米入口税率。
4月下旬,上海粮食界承诺不再采购暹米,认为暹罗“不能善其邻”,对我侨民施以种种苛例,我国商民惟有予以经济上之打击,如果暹罗当局拒不改变态度,“当绝对不再购进暹米”。28日,上海华侨联合会召开第5次整理委员紧急会议,讨论联合全国有关团体、筹谋大举抵制暹米之办法,认为广州、厦门、香港、汕头和上海系暹米运销的主要商埠,决定分别联系五地商会及米商公会,以期一致行动。5月上旬,上海华侨联合会继续敦促粮食界践行抵制之议。6日,该会委员与旅暹侨胞回国请愿代表,由潮州驻沪米商介绍赴杂粮业同业公会、豆米业同业公会,报告暹罗政府压迫华侨的各种非法行为以及侨民所受痛苦,呼吁沪市米商抵制暹米进口,“俾促该国之觉悟”。9日,杂粮公会全体执监会议强调,对暹罗政府颁布苛例摧残华侨“万难漠视”,电请中央当局与暹政府积极交涉,倘若暹罗政府再不修改条例,该业将对暹实行经济绝交。11日,南京市商会、工会、农会电请政府速颁禁止暹米入口令,呼吁全国拒用暹米。汕头华侨团体决定停购暹米,“作有效制裁”。汉口国货运动委员会则明令禁止暹米入口,“以示抵制”,同时通电全国,呼吁一致声援暹侨。北平商会亦有抵制暹米计划的初步酝酿。
6月上旬,抵制暹米逐步由舆论宣传落到实处,其中转机无疑是党政力量的介入。广西《博白县政府公报》载有“训令各区查禁暹米入口由”,标记为“秘字第3554号”,日期为6月6日。该密令谓:“旅暹华侨代表纪宏良等呈为暹罗实施排华政策苛待华侨请从速采取有效对策与暹订立邦交一案到院,当叫外交财政实业三部及侨务委员会会同审查,旋据报告,经提出本院第209次会议决议,转请中央党部密饬各地党部指导民众团体发表我侨在暹受虐待如教科书不准用中文等,应实行禁止暹米入口,先作此种宣传,以期暹政府反省,改善华侨之待遇,相应抄录原呈,函请查照,转呈密饬各地党部遵照等由。广西省执委要求各县党部会同政府,查禁暹米入口。”《商务月刊》亦刊载“奉闽侯县党务指导委员会令禁绝暹米严行抵制转请査照由”,“案奉闽侯县党务指导委员会训令开:顷阅报载暹罗政府封闭华侨学校,强迫同化,摧残华人工商业,钳制华人言论等等,显系实施排华政策,揆其用意,实欲置侨胞于死地,噩听之下,深为愤慨,似此目无公义之排华手段,凡我同胞自思有以对抗。兹查暹米运售我国各口最为大宗,如能一致禁绝,亦可制敌人之死命,为此除普遍宣传外,特令该会(县商会)迅即转知各米商禁用暹米,以为有效之对策。县商会分函各米业公会和各米商,务希一体遵照禁绝暹米,严行抵制”,日期是6月12日。
6月2日,上海华侨联合会代表声称,闽粤二省及沪市米业对禁止暹米入口一事“咸表赞同,现正积极进行,最近期间,即可实现”。18日,广东商联会致电上海市商会等团体,呼吁“全国商人一致奋起,实行与暹经济绝交,先拒销暹米,以作有效之制裁,并望各团体一致主张”。上海米业公会于7月4日正式宣布禁销暹米,“即行通知本市各米商,开始一体禁销。在暹政府未能改善各种苛例前,绝不开禁”。在6日召开的上海各团体援助旅暹华侨联合会常委会上,潮州同乡会提出,“昨日报载某洋行有大批洋米进口,应切实调查,如有暹米,本埠各米商应严厉拒绝批销”,决定由各常委负责严密调查。中华国货维持会则建议向广州、香港、厦门、汕头各地米商及相关团体电告上海自动抵制暹米经过,“并请一致抵制到底,俾收最后成效”。
上海等地抵制暹米,并未促使暹罗改变排华政策,“沪上暹米早已绝迹,无如暹政府夜郎自大,冥顽如故,以我侨胞为可欺,不但待遇毫无改善,且变本加厉,加紧压迫,苛例迭增”。上海援助旅暹华侨联合会决定分函港、粤、闽、汕、厦有关团体,呼吁切实施行抵制暹米,并派员赴沪,共商组织全国援助旅暹华侨联合会。援助旅暹华侨联合会提倡抵制暹米后,各地纷纷响应。厦门海外华侨公会主席谢镜波复函表示:“暹国蛮横,虐待华侨,同深愤慨。业由本会联络商会及米业公会实行抵制。”甚至越南华侨总工会亦表达了类似主张:“拒买暹米,在暹侨胞、固不无一时损失,然须忍一时之痛,始克谋久全之计。”
1935年8月1日,暹罗将教育部长调任农务部长,其国务院将“取消华侨强迫班”一案暂缓施行,此则我国抵制暹米的最大成效。据熟谙暹情者之观察,其意图显然在于缓和我国抵制风潮。10月中旬,西南政务委员萧佛成由暹返粵,认为国内盛传之暹罗排华问题言过其实,而取缔华校问题,经广东教育厅长赴暹疏通,暹罗政府已承诺完善相关条例。但是,撤换教育部长显属权宜之计。就在新任部长履职当月,即下令禁止华侨学生身着华服,并拒绝潮剧“中正顺”班创办童伶学校的要求。9月中旬又颁苛例,规定华资米垄每年须将一半盈利拨充军费;旅暹华侨不得有侮辱日本人之事件;华侨学生不准着中国服装;华资米垄暹籍工人须占70%。
早在6月20日,军统局据其情报密函外交部,认为暹罗排华系其国策,绝无改变可能。如果华人抵制暹米,暹罗即渐值棉花,并借款发展工业。关于中暹商约问题,军统局指出,暹罗政府缺乏与华订约之动机,中暹商约决难订立。因此,我国外交部知难而退,遂于该年11月命令驻日公使转告暹使,阐明中国政府维持中暹贸易之旨趣。而以抵制暹米为手段,意欲迫使暹罗与我订立邦交的政治意图遂告失败。因此,纵观此次抵制风潮的成效,诚如《密勒斯评论报》当年的观察,无论是政府禁止暹米入口还是民间自动进行经济抵制,均非“根本之解决办法,盖此种杯葛手段,只可目前使暹政府和缓其政策之推行也”。
二、抵制暹米与华侨经济
暹侨经济势力在南洋各地居于首位,按照陈序经的说法,华侨被暹罗民众称为“远东犹太人”,甚至认为“远东之所以无犹太人,就是因为有了中国人”。因此,抵制暹米,首由暹罗华侨代表倡议,但倘由言论层面落到实处,全体暹侨的经济利益势必先遭重创。
国内舆论的主流大肆提倡禁止暹米入口、抵制暹米或与暹经济绝交,但亦不乏理性的主张,积极反思经济抵制的负面效应。有人指出,如果实行禁止暹米入口,“受打击最重者不是别人,仍是华商”,提出抵制方策施行之前,必须考虑如何抵制暹米问题。有人认为抵制暹米势必导致四大恶果,即加剧国内民食恐慌、打击华侨经济、阻塞侨汇来源以及隔绝国货销路。时人敏锐洞悉世界经济大萧条背景下抵制暹米给华侨造成的特殊影响。暹罗华侨的火砻业亦即碾米业,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本已风雨飘雨,相继倒闭者甚多,并且“山巴农民,也因谷价低贱,生活困难”,甚至在1933年至1934年的两年,由于谷价太低,售价不够抵偿运输费用,“僻壤农民,多有愤而自焚其谷者”。而1933年广东征收洋米进口税,暹米业更受严重打击,“破产者颇不乏人”,故而华侨“颇有争持,后来争持无效,怨言殊多”。因此,倘若抵制暹米成为事实,华侨生活大多立即“失其常态”。外交部要人亦提醒国人:禁止暹米入口一旦发生实效,“不独碾米厂家蒙其损失,碾米华工亦有失业之虞”,米商及碾米工迫于生计,势必起而反对,甚至引发华侨的内部冲突,或者滋生对祖国的怨恨之心。在他看来,禁止暹米入口之策,事实上“殊多窒碍”,作为因应暹罗排华之报复手段,“行之有效,利害参半;行之无效,则只见其害而不见其益”。
强调抵制暹米对华侨造成的损害,其理由无非是华侨在暹罗米业中拥有重要地位。据暹罗政府1929年的调查,华侨商务以米业为大宗,木材、锡等大规模工矿业则几乎操诸西人之手,如英人之婆罗洲公司、英暹公司、孟买缅甸公司、路易公司、丹麦人民亚细亚公司等,华侨经营的工厂仅有民生火柴厂、利民工厂,以及十余家小规模铁厂、肥皂厂等。其他各业虽有华侨参加,多未具规模。据其次年调查,华侨有米业141家,运销暹米输华者则“尽数华侨,绝无一外商”。具体而言,暹罗米绞即碾米工厂,约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大火砻,资本自100万至300万铢者七八家,以黉利、老长发、振盛、亚细亚为最;二是中火砻,资本自40万至80万铢者67家,以顺成利、锦泰盛、宏兴隆等为最;三是最小火砻,资本自5万至20万铢者600家左右,遍布于湄南河流域和其他河流与内港,除亚细亚之外,其余全为华侨创设,资本总额超过3000万铢,每日出米除供给全暹民食之外,余即全数出口。另据日本人调查,曼谷80个华侨碾米工厂,固定资本高达1200万铢,每年碾米能力约160万吨,其余各地尚有800个左右小工厂,固定资本大约800万铢,每年碾米能力约为120万吨。这些工厂雇用了2万名华人。暹米年出口数量高达百万吨,出口价值则高达1亿3千万铢左右,其中60%由华侨自雇外国船舶,或由华侨经营的轮船公司,通过香港、海峡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等地华商输出。华侨经济势利深度介入到暹罗米业产销的全部环节。各地华侨零售商店向当地农民支付预付款收购稻米,加工后按计划出口,从而成为碾米业的“先锋”。每年五六月青黄不接时,农民食米不足,农业资金缺乏,在当地经营小杂货店和饮食店的华侨,“对平时接触的农民的性情、生计、耕作、收获等十分熟悉”,通常预付每一农户50铢左右的的“适当金额”,在当年12月或次年1月的收获期,收取20石左右稻米作为利息,并收取预付款项。“若换算成时价,经七八个月时间,相对于本金可获得一倍以上的高利润。”而这些小商店的预付款多从曼谷等地的碾米业者或其直属经纪人处融资,月息3分左右,但对收购稻米收取一定数额的手续费。华侨在暹罗米业占有重要地位,故而成为该国制订农业政策时无法回避的力量。1930年底,由于米业不振,暹罗农务部讨论救济问题,该部大臣特向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征询意见。
暹侨不仅在米业中拥有重要地位,在其他行业的力量亦不容忽视,并且各个行业之间的联系极其密切。根据暹罗政府1930年的调查,除了米业之外,华侨还拥有输出入商84家、银行3家、批馆(银信局)40家、保险公司10家、木材商20家、机器商41家、木器商18家,而杂货商则多达1325家。这些行业多以米业为轴心,而华侨也或多或少与米业存在关联。据估计,如果每家火砻的工人、船夫、杂工、驳艇和办事人平均为80人,则依赖火砻业领取工薪者超过6万人,如果每家以平均4人计算,这6万人的家庭人口则高达24万人,而依附于火砻业的批馆、保险业、米行、经纪人以及他们所负担的家庭人数,则超过50万人。因国内天灾、匪祸、兵燹而赴暹耕作的农民,加上旧日原有农民,其人数也有30万至40万。因此,“暹罗一切事业,均依赖米业以为转移,而米业仅赖出口销路,方有活力。倘国外贸易畅旺,火砻业自蒸蒸日上,其他各业也呈活跃状态,否则米业衰疲,其他各业也日形凋落。……若火砻一蹶不振,牵连所及,则各业受累不浅。暹罗国际贸易,除少数木材、山货之外,三分之二是米,而米的销路,是以香港和中国最多,卖出的资金购买洋货和中国货,各业赖以支持,否则金融完全无法周转,不独火砻立刻停工,即其他各业也当宣告搁浅”。
暹侨代表承认经营米业者多系华人,但却认为中国如果禁止暹米入口,对华侨业主并不会造成重大损失。原因在于,世界经济萧条已使米商损失巨大,倒闭者不少,不顾亏蚀而继续营业者,则希望度过难关,以图来日。若禁暹米,粟价亦随之而跌,“远大眼光米商早已得粟贱米贵居奇的机会”。同事,暹米绞工多为华人,米绞停工不免失业,“惟侨胞素重义气,纵令一时失业,亲族朋友辈尽可周全,不至冻馁”。但是,即使是抵制暹米的鼓吹者,也不得不承认经济抵制将使华侨“陷入绝大困难”,只不过“凡事有大小之分,缓急之别”,我国实行经济抵制,目的在于运用国家政策促使暹罗觉悟,“救侨胞于水深火热,是其大者急者也”,为了全体侨民利益,“不得不忍痛牺牲局部利益”。而且,我国如果放弃经济抵制这一武器,暹方对与我订立邦交一事,则“更无兴趣”。
三、抵制暹米与粤省民食
南京外交部要员曾对中央社记者谈及禁止暹米入口之困境,认为广东食粮大部分向恃西贡米及暹米接济,如果中央禁止暹米入口,势必造成粤省食粮供应紧张,“该省当局是否认为施行无碍,殊为疑问”。此种消极论调遭到舆论强烈批评。有人指出,暹罗排华苛例颁布以后,暹侨“奔走呼号,力尽气嘶”,我国朝野竞谋应付之策,“对暹经济绝交”、“禁止暹米输华”等主张方才应时而起,故而斥责外交部要员的消极言论“没有抓住问题的重心”。也有人认为,暹罗与我“同洲同种”,竟对我侨胞施以苛律,我国才以抵制暹米作为报复,以期“促其反省”,此举结果虽难预料,但以政要身份而公开强调抵制暹米并非善策,“已属大上其当”。
若从外交技术层面着眼,或以民族主义为视角,外交部政要的消极论调确有可资非议之处,但与舆论宣传的激进高调相比,却更加切合历史真实。暹米在华的市场格局明显呈现南重北轻的态势,则所谓“暹罗盛产米,故米价常贱;粤闽则缺米,故米价恒贵,因以暹米济我之穷,清初已然”。暹米“销于粤港者为多,厦门上海次之,北方之天津,所销亦无多”。暹米质高价贵,上海虽为洋米的巨大市场之一,但是“能食价高之米者宁食粳米,不能致者,又宁取价贱之西贡小绞诸米食之”。因此,北平商会对抵制暹米的响应,纯属应景之议,并无实际价值,而抵制呼声最为激烈的上海,因非暹米主要销售区,自然失却抵制的标靶。
与上海等地不同,对于粤省而言,暹米与民食则关系甚密。据近代粮食专家黄菩生的看法,广东粮食之所以不能自给,主要有六大原因,一是多山,不如长江下游诸省平坦,并不特别适宜种植水稻;二是“民蛮杂处,每每发生冲突,农业定居生活屡被骚扰”;三是与海外通商最早,商业资本比较发达,民众热衷商业,习于外出谋生,农民改农习商者日众;四是深受外国商业影响,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致使农民改种桑茶与果木;五因山多林少、河面浅窄,“水之灾患,常有被及农村,致使稻田被洪水所淹没,谷物失收成为常有之事”;六因近山之田旱灾不断,“北江一带,常遭此患”。在他看来,广东稻作发展与洋米入口恰好构成“互相对立的消长形态”。也就是说,广东粮食多仰给于广西及江浙数省,但这些省份的米粮输入,亦不足以满足粤省需求,因此洋米输入逐年增加成为“必然之趋势”,同时洋米输入增加,反过来又导致广东稻作逐渐减少,该省粮食则进一步不能自给,“农村劳动者大批流出外洋,农地一天一天增加,农村经济一天一天破产”。
广东是洋米或者暹米消费的主要省份,因此1933年粤省决定征收洋米税,洋米商极力反对,理由是广东全省米粮产额仅敷4个月之需,洋米征税显然妨碍民食。而潮梅各县大为震动,因潮梅15县及闽赣边20余县,每年产米仅敷3个月之用,其余9个月全靠洋米接济。因此,潮汕市商会、南北港杂粮同业公会和米行等,均致电西南政务委员会、省政府和财政厅,恳请撤销洋米税,米商派代表则赴省力争。但在汕头市长翟宗心看来,征收洋米入口税旨在“救济农村经济”与“复兴粤省农业”,“凡稍有爱护国家社会之心与稍具经济常识者”,均当“力图赞助”,指责洋米“奸商广布谣言”,“冀耸观听,贪图个人小利,罔顾公众利益”,并且援引海关数据,认为粤产米粮足以供给11个月,米商所言4个月之说“不攻自破”。因此,尽管官民之间的申说动机虽然截然对立,但粤省粮食不能自给,则系不争之事实。
“九一八”事变之后,邹韬奋曾经呼吁全国民众“毁衣、毁食、毁住、毁行”以及“造产、造物、造材、造兵”,以此作为抗日救国之道。关于“造产”问题,他沉痛指出,尽管中国系农业国家,但米来自暹罗,棉花小麦来自美国,煤来自日本,糖来自南洋。若无暹米,国人陷入挨饿之窘境,而缺乏美棉与美麦,工厂则面临“无事可做”之难题。他乐观地预期,政府一旦重视发展经济,仅仅上海一埠,即有大量农矿人材分赴各地,运用其专业才能从事“造产”工作。但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暹米进口数量不断增加,1931年暹米占中国大米进口总额的6.5%,居第5位,1932年占28.62%,居第3位,1933年占35.25%,居第2位,而1934年占44.8%,跃居首位。1912—1932年,广东洋米进口担数年均占全国总量的65.2%,而1915—1919年的5个年份,该省洋米输入均超过全国洋米进口总量的80%,即使是1931年和1932年,也超过了60%。
禁止暹米入口,难免导致粤省食粮供应紧张,无疑需要斟酌权衡。抵制论者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期望民众的爱国之心和同胞之情,可以克服粮食紧张问题。《新生活周刊》承认,禁止暹米入口“不免要使粤省食粮发生问题,不能不加以考虑”,但是广东人的爱国心“素来是很热烈的,这回为爱护侨胞起见,总不能说除了暹米,就无米可吃”。《申报》刊文指出:“为力保国族起见,虽有牺牲,亦在所不惜。”也有人希望民众从降低国家入超的角度,改变偏好洋米的惯习,声称”吾国工业落后,物产不能发达,以致入超日增,此原为暂时无可如何之事,至于食粮,则我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且广土众民,非英之三岛可比,何至依赖外产,或谓灾象使然,但旱灾之烈,乃去年事,而外米输入,则不自去年始,或又谓一部分人惯食外米者,不能更易,此则更不成理由,将谓价廉可取,然财力榨尽之时,何以为继,与饮鸩止渴者何殊”。在暹侨看来,禁止暹米输华对国内部分民众,“表面虽有损失,但为维护整个华侨将来利益计,自不能不作一时牺牲,否则暹罗同化政策完成,侨胞均变暹人,财产尚得为中国所有乎”。
其二是购买其他国家或国内其他地区米粮作为替代。暹侨在电告香港华商总会时提出,我国洋米进口,除暹罗之外,尚有安南、缅甸等处,暂时禁绝暹米,尽可多购缅米、越米作为替代,不至于影响民食。南洋问题研究者梁鸿认为,抵制暹米一事,只要全国民众同具决心,“大可以虚声而收实效,不必至于实行抵制地步”。针对抵制暹米影响民食问题,他强调,“事前如能统筹善策,亦非绝对无办法补救”。我国粮食生产分布不均,存在粮食供给“过剩”与“缼欠”之矛盾现象,应由政府统筹解决,同时限制“奸商”利用供需矛盾而乘机营利。他举例说,广东食粮缺乏,但竟有商人由广东运米至芜湖销售,“利用免税以图非得利”。
但是,暹米一经抵制,缅米和安米供少求多,势必抬高价格,“国内一般奸商亦可趁机渔利”。况且,暹米中之米碌价钱廉贱,与普通民众购买力相适应。以潮州而论,每年土产米粮仅足维持4个月至6个月,其余则需仰仗外米进口,此地多数平民都购暹米中的第三、四号米和小米,购食芜湖米者亦众。但由于先年芜湖旱灾,“芜米来源既绝,洋米腾贵,本以不堪负担,一朝暹米也被隔绝,痛苦的情形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广东方面抽收洋米税,每包超过3元,较之其他各地,米价尤显昂贵”。即使国内米商自觉抵制暹米而改销他国米粮,亦很难禁止日商销售暹米。在汕头,由于凭借特惠商约而无需缴纳农产品特税,正常米价为每元12斤,日商暹米则可降至每元18斤,而购买者多属贫民,甚至有自澄海等地远赴汕头购买者。私米源源运入汕头,市面米价大跌,国内米商被迫亏本销售,暂停进购米粮,故而迫切希望当局早日妥善解决暹罗排华事件。
解决粮食“过剩”与“缼欠”这一矛盾,则有赖于交通运输的便捷顺畅。交通瓶颈恰恰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难题之一。1935年新年前夕,胡适乘火车长途旅行,途经安徽符离时,他观察到:“火车站两旁的空地上满堆着一袋一袋的粮食,一座一座的小山,用芦席盖着,在那漾漾细雨里霉烂着,静候车皮来运输!站上的人说车辆实在太少了,实在不够分配”。胡适将每年进口两亿元粮食与交通部新官邸落成的盛大典礼之间的巨大反差相互勾连,认为铁道、交通两部如果合而为一,则可节省行政支出用于车辆购置,从而解决粮食运输困难。他指出,为了应对1933年广东开征洋米进口税,暹罗政府则免除大米出口税,结果暹米入口仍未衰减,湘米与暹米竞争仍处劣势。因此,他对即将到来的新年充满了期待,“梦想”政府能够充分运用关税政策和交通政策解决民食问题,希冀实现全国粮食产需协调,从而避免出现“某一区域丰收成灾而某一区域嗷嗷待哺的怪现状”。如果来年我国粮食进口额从2亿多元减少到1亿元以下,他“不枉负又痴长一岁”。
1936年,马寅初主张实行粮食统制政策,对先年的抵制暹米问题曾有简略反思,并将抵制暹米的经济困境作为申论的例证。他强调抵制暹米“非空言所能奏功,必须事先统盘筹划,平日积谷,足供三年之食,则虽遇荒年,尚可维持;否则一遇米量缺乏,不得不订购暹米,则我未能抵制暹人,暹人反可居奇不卖,还以抵我。此必须统制粮食之又一证也”。对于我国抵制日货,马寅初亦曾担忧遭遇日方的经济反制,但暹罗与日方因应我国经济抵制的强硬策略迥然有别,既派遣考察团赴华,以期消弭纷争,又坚持其既定政策,甚至禁止华报入口,封杀我国舆论。
1905年,美国排华法案的出台,引发我国民众抵制美货而“寻求正义”,且并非全无所获,此后,经济抵制成为民众抵御外侮的常用手段,其中以抵制日货最为频繁,多达十余次,国民党对动员民众进行经济抵制,亦可谓得心应手。针对暹罗排华一案,中国社会又重拾此一武器,甚至将其视为“极具神效的当头棒”。南京政府与暹进行外交交涉,而国民党党部则沿袭反日运动的模式,秘密发动民众团体进行经济抵制,以期解决暹罗排华问题,并同时实现中暹建交的宏大目标。
毫无疑问,近代民族主义观念,或曰爱国主义情感,显然是抵制外货运动频频勃兴的思想资源。民族—国家观念的型构离不开与“陌生人”的比较,而国民意识的生成,与“他者”的敌对性存在密切相关。作为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广州成为抵制洋货的一个重要策源地。但是,抵制暹米可能重创华侨经济,从而有悖护侨初衷和本旨,同时受制于粤省对暹米的高度依赖,经济抵制则难免流于空谈,沦为“吓人”之策,即所谓“我国抵制外货,无一次不是虎头蛇尾,自清末抵制美货至前年抵制日货止,中间不知有若干次,而能收抵制之效者,迨未之前闻。民众凭一时之情感,以抵货为武器,必不能在外交上得胜利也,明矣。……在此次之抵制暹米声中,受之者固未必因之着急,施之者未始不自知其为吓人之政策也”。近人对我国抵制外货的这一反思,堪称至论。进而言之,在殖民主义时代,中、日、暹保持了独立地位,在此三角关系中,中国渐弱而日本渐强,暹罗转而疏华亲日。历史业已证明:暹罗的国策转向实则与虎谋皮,终而自食其果,但中国与暹建交之意图,数十年间始终是一厢情愿,难成正果。
注 释:
①泰国古称暹罗,1939年改名为泰国,1945年又改为暹罗,1948年又采用泰国之名,为切合历史语境,本文多称暹罗,而援引文献时,亦间有称之泰国者。
②抵制日货问题的研究概况,可参阅拙著《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1908—1945)》之导论(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
③李道缉的《泰国华人国家认同问题(1910-1945)》(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999)曾有简略涉及。
④《外交部关于暹罗政府1910年以来排华事件报告 (1946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五)》,凤凰出版社1999年版,第543—544页。
⑤《暹政府决定封闭华校》,《申报》,1935—2—11(8)。
⑥分别参见张启雄:《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清末民初中暹建交的名分交涉》,《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Wongsurawat,Wasana.Contending for a Claim on Civilization: The Sino-Siamese Struggle to Control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Siam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2008(2).
⑦《由商民抵制暹米到民众外交(社论)》,《益世报》,1935—5—24(6841)。
⑧君泽:《中暹问题我们应有的态度(续)》,《独立评论》,1935年第159期。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21辑(1935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页。
⑩李道缉:《泰国华人国家认同问题(1910—1945)》,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999。
[责任编辑:翟 宇]
周石峰,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中外关系史。
K205
A
1002-6924(2016)11-062-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