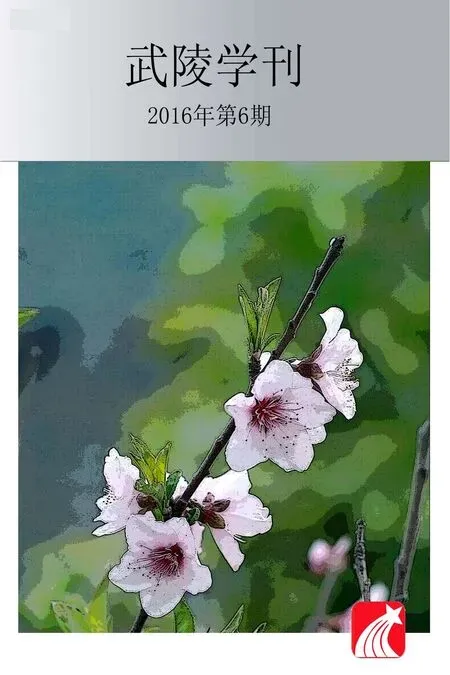重思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伊恩·汤普森教授访谈录(一)
高海青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420)
重思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伊恩·汤普森教授访谈录(一)
高海青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420)
目前,对海德格尔的研究,特别是对海德格尔技术思想的研究正在逐渐退出技术哲学界考察的视野,海德格尔思想的研究似乎已经有了定论,即从理论上讲是神秘主义的,从实践上讲是寂静主义的。但事实是否确实如此,针对此问题,美国海德格尔思想研究专家、技术哲学家伊恩·汤普森分别从理论方面就海德格尔技术思想与传统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从实践方面就海德格尔技术思想与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答。在第一个访谈中,汤普森以本体神学这个概念为核心对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作了更本质的解读,把技术问题转化成了存在之技术的领会问题,从而把技术与现代性联系了起来,并且提出了一种新的存在之后现代的领会。
本体神学;技术批判;存在之后现代的领会
伊恩·汤普森(IainD.Thomson)是美国著名的海德格尔思想研究专家、技术批判理论家,新墨西哥大学哲学系教授、荣誉顾问,被誉为最著名的后海德格尔评论家,本体论教育的守卫者,极力诉诸于后现代性以及艺术与诗来领会存在的当代哲学拥护者,其代表作有《海德格尔、艺术与后现代》(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海德格尔论本体神学:技术与教育政治学》(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5),曾与技术批判理论家安德鲁·芬伯格多次交锋,是芬伯格特别重视的一个学术对手。但有意思的是,国内学者关注芬伯格比较多,对芬伯格技术批判思想的研究也比较深入,而对芬伯格极为重视的这位思想对手却较少关注,甚至几乎很少提到。正是这种疑惑让我产生了直接约访汤普森的想法,于是,我在2016年初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对汤普森做了一次访谈。我根据他的著作提了很多问题,他经过两个多月的思考回答了我的全部问题,但我在翻译他的复信时,我对他的某些表述又产生了新的疑问,如此反复近4个月的时间,在他的耐心帮助下终于完成了这次访谈。从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恩·汤普森教授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独辟蹊径,他以本体神学为核心概念把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纳入了更宏大的西方思想轨道,并且不同于大多研究者对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研究。他认为,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解读蕴含着实践的维度,而不是宿命论似的寂静主义。关于这一点,在此次访谈中,汤普森作了十分详实的回答。
高:汤普森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问。在研究海德格尔思想的过程中,我碰到了很多疑惑,遇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海德格尔后期关于技术的追问以及海德格尔对技术问题的克服,所以特别想请您这位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专家给予帮助。现在,海德格尔的思想已经传至世界各地,并且给20世纪乃至当前都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像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芬伯格等很多学者关注的那样,我想问的是,海德格尔这位参与过纳粹的伟大思想家是否应该被看作反现代主义者呢?
伊恩:高海青您好!首先,感谢您对我关于海德格尔的思考如此感兴趣,也感谢您能够耐心地等待我的回答。您也许知道,安德鲁·芬伯格是我的老师(此外,还有休伯特·德雷福斯和雅克·德里达等重要的后海德格尔思想家),因此,您提出的这些问题,涉及到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激进批判这个永恒主题,还涉及到他因该主题而与马克思等备受赞赏的现代哲学家、芬伯格及其声名卓著的老师马尔库塞等重要的当代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争论不休的关系,对此,我努力思考了很长时间。
我想首先声明的是,我们最好不要把海德格尔理解成一位反现代主义者,而是把他理解成一位坚定的后现代主义者。尽管,他对现代各种不容质疑的形而上学原理(包括主客二元论,事实与价值二分)极为不满,但是,我认为海德格尔对现代性批判的深邃性使他的作品成了我们绕不过去的晚现代哲学的试金石。因为,海德格尔是一位从现代性最深处的预设到其最终的结局来思考现代性的思想家,所以,他帮我们开创了一条道路,而该道路既超越了现代性最具破坏性、最虚无主义的要素,也保留了它最为关键的、无可替代的进步要素。
因此,我不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位反现代主义者(他反复地教导我们,反现代主义者总是试图反对某些东西,但却依然陷入了它潜在的逻辑中,这种使傲慢的无神论者依然陷入有神论的传统逻辑的思想方式都有一个预设,即自己能够认识超越于可认识之外的东西,实际上,肯定上帝存在的有神论者与否定上帝存在的无神论者都有这样的预设)。相反,我认为,他是一位具有原创性的后现代思想家,我所坚持的这个观点能够得到大量尽管肤浅但却直接的事实的支持,即几乎所有重要的当代大陆哲学家都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不仅阿伦特(Arendt)、巴特曼(Bultmann)、伽达默尔(Gadamer)、哈贝马斯(Habermas)、马尔库塞(Marcus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萨特(Sartre)和蒂利希(Tillich)等公认的“现代”哲学家,而且阿甘本(Agamben)、巴迪欧(Badiou)、鲍德里亚(Baudrillard)、布朗肖(Blanchot)、巴特勒(Butler)、卡维尔(Cavell)、德里达(Derrida)、德雷福斯(Dreyfus)、福柯(Foucault)、伊利格瑞(Irigaray)、拉康(Lacan)、列维纳斯(Levinas)、朗西埃(Rancière)、罗蒂(Rorty)、泰勒(Taylor)、瓦蒂莫(Vattimo)和齐泽克()等这些公认的“后现代主义者”,也都把海德格尔的思想当作自身哲学的基本出发点。他们想借此试图超越这一海德格尔的起点(必须说,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最终看来,所取得的进步确实比他们自己预料的少很多)。因此,这些重要的思想家都普遍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学着“沉默地”(即批判地、谨慎地、有保留地同时有选择地保持开放状态)倾听海德格尔对其所讨论的问题的观点(就像他自己经常强调、称许的那样),才能像海德格尔这样的解释学现象学专家一样思考。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讨论中发现让我们自身回到至关重要的事情本身(die Sache selbst)的道路(而不是纠结于没完没了的术语辩论,仅仅纠结于“语义学的”错误,而忽视了真正的分歧)。如此一来,我们最终就会思考其思想中讨论的问题,就会比海德格尔本人终其一生的思考走得更深入——或者按照我们现时代的关切,按照我们对我们这个时代与我们这代人、我们的地球与世界、我们的过去与将来、背景与视野、空间与时间影响最大的事情的特殊领会方式,至少以我们自身的方向与语调对他的问题作稍稍不同的阐释。
不是有位中国的圣人曾经这样说过吗?“智者手指月亮,傻瓜却望着手指。”(Whenthewiseman pointsatthemoon,thefool staresatthefinger①)海德格尔与这位圣人相呼应,他多次抱怨道:“少有人能充分体验到学术对象与问题思考的差别。”易言之,“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充分思考事情本身的内容[或者‘思考事情本身的问题实质’,die Sachverhalte der Sachen selbst zu durchdenken],并且逐渐熟悉其中那些值得质疑的内容,而不应该是借助于另外的思想家来打倒这个思想家。”②这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一定程度上占有海德格尔思索的问题,揭示它们对现时代问题和关切的适用性、相关性与重要性——避免将注意力放在一些微不足道的有关海德格尔本人可能思考些什么的争论上,而是要学着比他本人还要更进一步地思考他思想中利害攸关的重要问题(通过“思考他尚未思考的问题”,即那些他本身借以思考问题但却几乎很少进入他成文的思想前沿的洞见)——这也正是我在著作中一直致力于做的事情。
另外,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比海德格尔本人更进一步地思考他所思考的问题,以海德格尔的方式思考并超越他对将来的思考,或者,揭示逗留于将来(Zu-kunft,A-venir)的东西,未来的未来性(futurity),尚未到来的敞开状态,这种创造性的解蔽会从对海德格尔作品及其利害攸关问题的深刻理解中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phusis-like),纵然这样一种理解需要10多年的时间才能赢获,需要一生的时间(毫无疑问,不能仅靠某个人的一生)去阐发(即使似乎总是有强力反对该思想的继续阐发,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理由,合理的反对都是正当的,但却决非如我们相信的那般正确)。因此,海德格尔思想与后海德格尔思想有着深刻的代际(generational)联系。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在把“generational”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您要确保两个层面的联系,一是本体论层面的生成关系,二是时间意义上的世代关系,即(1)真正的教师通过给予或激发一种有效促进存在之意义涌现的动力并最后将其展现出来以帮助“生成”(generate)思想的方式,和(2)这些在一段历史时期聚在一起来发现、辩驳和揭示存在之意义并因此作为“一代人”结合起来的群体在短时间内的聚集。我特别好奇您该如何把“generational”翻译成中文?您能确保这两层联系吗?正如海德格尔所评论的那样,任何翻译都是一种解释,我希望您允许我说,我不禁想更全面地知道在您的翻译中会收获什么又会遗失什么,哪些精微的差异会被保留下来,哪些细微之处又会被随意丢弃,哪些新的解蔽会涌现出来,哪些又会受到妨害?这些也都是代际的问题,原因并不仅仅是这项艰难的翻译工作总是充满了创造性,还因为这项理解它的任务只能开始于未来的那些人,即像您一样栖居于语言世界之间,在各领域之间架起输送洞察与理念的重要桥梁——倘非如此,各领域就会被无知的鸿沟分裂开来——的那些人。当然,关于这方面的看法远不止于此。
高:中文一般把“generational”翻译成“代际”,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之间的代际传承,从这点来看,无疑您所说的第二个方面绝对能够得到满足,但我不敢确定“代际”是否有第一个方面即“生成”的意味。您为何专门讨论“代际”呢?这和您在研究现代性问题的过程中选择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有什么关系吗?
伊恩:对海德格尔思想与后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代际师承关系的考虑把我带回至您的问题,即我为何选择研究海德格尔。以兼具利弊的后见之明回首过去(正如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早晨令人欢快的希望可以在暮色黯淡的傍晚的反观凝视中得到充分的理解,但这一点还远不够明朗),可以说,我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段令人陶醉的日子里最初喜欢上后期海德格尔的诗化哲学的,当时我是德雷福斯的学生。他是我的第一位海德格尔思想的老师,必须说的是,尽管他的学说对我产生了影响,但却是在弗洛伊德、马克思、尼采以及其他伟大的现代哲学家等几位优秀的导师(此外,某些决定性的个人经历)首先使我自身的思想变得足够深刻、足够开阔以后,我才开始把海德格尔的思想变成了我的思想,简言之,我才开始直接去领会它,才开始理解和真正地思考他不断讨论的话题。诗人这种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就我个人而言)具有父系继承性(我父亲,我祖父等等,他们都是诗人),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因此开始逐渐成为自我)被海德格尔诗化的思想及其挑衅性的宣言——只有诗歌的光芒才能把世界从我们晚现代技术虚无主义愈来愈阴暗的黑幕中拯救出来——吸引住了。稍后我会对这些要点作些解释。
高:谈到您的老师德雷福斯,我们知道德雷福斯曾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会长,被誉为海德格尔作品最精准、最完整的解释者,他对欧美世界海德格尔思想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您与德雷福斯之间在理解海德格尔上有哪些区别呢?您做了哪些方面的推进?
伊恩: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我也有些担忧,因为完整地回答该问题可能需要一篇文章,所以我只能极其简单地回答一下。对德雷福斯来说,存在就意味着“可理解性”。海德格尔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在《存在与时间》中把存在定义成了“存在者先已得到领会的基础”。此外,德雷福斯还以人的“背景实践”(background practices)来理解存在,比如,在与某人交谈的时候,与其保持适当的间隔距离。此种背景实践通常是非概念的,它因文化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而我的存在之领会更为宽泛,我倾向于认为,它“构成并溢出了”可理解性,是一种前概念的给出,一定程度的诗的概念化和超出概念的部分。我与德雷福斯还有一点不同,我认为“存在者之存在”持有极其明显的概念成分,还属于本体神学[即形而上学是以何种方式通过把握存在者“本身”(本体论)和存在者“整体”(神学)把“存在者之存在”概念化的]。
由此看来,德雷福斯受《存在与时间》的影响更大,因为在那里“,存在”通常是“存在者之存在”。而我更倾向于后期海德格尔,极力强调“存在者之存在”(Sein des Seienden)与“存在本身”(Sein als solche)之间的区别。《存在与时间》在探索“基础存在论”或“领会一般存在意义”的过程中海德格尔始终求索的正是存在者之存在,但海德格尔在后期作品中将其作为“形而上学”抛弃了。后期海德格尔认为,根本没有唯一的、从西方历史中可以得到恢复的、统一的“存在”概念,他还认为,试图为存在问题提供这样一种最终答案的尝试是形而上学最根本的错误(更确切地讲,这是本体论层次的本体神学的错误,根本不可能获得能够将单一的概念阐释与纷繁多样的存在者维系起来的最终普遍共同的根据)。对后期海德格尔而言“,存在本身”既构成也超越了(因此有可能招致)这一系列不同的形而上的(即本体神学的)理解“存在者之存在”的方式,而正是后者暂时地巩固和稳定了西方存在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
我认为,德雷福斯不会否认“存在本身”与“存在者之存在”之间的这一重要区别。实际上,他一直以来都特别支持我的作品,而在我的作品中,这个区别是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区别的关键所在。但由于德雷福斯总是太过关注早期海德格尔,所以他一直都不强调这一重要的区别(据我所知),他不认为该区别在其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中具有重要意义,换句话说,在德雷福斯看来,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MIT Press, 1990)才是关键。对此,我在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但是,关于德雷福斯为何特别关注早期却忽视后期海德格尔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却一直都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估,其实,这与他成功的、在早期海德格尔的启发下对人工智能的批判密切相关。在他还是麻省理工大学的年青教授的时候,他就成了最早借助海德格尔来批判人工智能的学者,并且这一批判帮助他赢得了许多主流分析哲学家的尊重③。因为我更关注海德格尔整个作品的总体轨迹,以及我们还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学到哪些东西?所以我特别强调其前后期著作的这一重要区别,而相对于海德格尔前期的工作,即他在《存在与时间》中阐释的观点,我认为,这一区别可以说是他的一大进步。对我而言,海德格尔后期对形而上学所作的本体神学的理解极为关键,因为它不仅统一和深化了他的思想(解释了为何形而上学沿着它前后相续的理解“存在者之存在”的本体神学的方式永远只能部分地占有“存在本身”),而且它还为其富有洞见的对技术虚无主义的批判提供了先前未曾被认识到的支持。
高:您能谈一谈您对海德格尔作了哪些回应吗?
伊恩:现在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对海德格尔的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我还将其称作海德格尔的希望——作了深刻的回应。如此看来,30多年前在伯克利的那段热情洋溢、令人陶醉的日子现在就好像是一个早期的暗示,一次深刻但却未得到充分领会的与早期存在主义会面的迹象、某种令人心动的征兆这样的东西,但是,它决不是一个物,而是无着(nothing)或存在本身在其持续不断的涌现与无蔽中的尚未成为物的状态[not-yet-a-thing-ing]——我一直不停地把它当成我的生命并在我的生命中将其展现出来——的相遇。我谈论的不是某种遥远过往的无名的“已经—总是”(always-already)而是我们自身个体“命运”(Geschick)的生存论建构,而命运,就是我们神秘的、不确定的但却适时而至的生命,是不断馈赠的礼物,是一个事件,而在该事件中,我通过使某种统一的意义藉由我具体化而碰巧产生或成为自我,因此,持续存在的自我意识,我还称其为具体化的“我”,它通过解蔽我自身的实存(回顾过往)似乎自始至终都具有的形式——该形式纵然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变得完全不同——而恰好具体化。即使把所有特殊的细节都提取出来,这样的描述也是近乎疯狂的,然而,无论我们何时想要试图解释我们自身内在同一性随时间而具体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存在在我们的生命中具体化为我们的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一种现身方式也许在所难免。“生命”是本体的时间性绽出,它绝不仅仅是属人的;而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或者如果这是您追问的问题),那么我认为,我可以对“命运的遣送”(Destinal sending)这一存在的历史现象作出更清晰、更严肃的解释(事实上,我在已发表的作品中经常谈到这些方面)。
高:我非常乐意倾听您关于“命运的遣送”的解释,因为这涉及到后面会提及的“技术命运”的问题。
伊恩:“命运的遣送”是一个复杂的观念,但却特别重要,它与存在本身以巨大的超出部分给出自身的方式有关,而该超出部分只有经过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得到理解,因为经过一段时期后,此一存在的遣送才会把意义创造出来、统一起来。这就是我现在经常说到的“真理事件”。关于这样一种命运的遣送,海德格尔列举的最主要的例子就是“本真的居有事件”(the authentic event,die eigentliche Ereignis,以单数的形式),即在西方历史“最开始”的古希腊时期“存在本身”给出自身的方式,而该方式只能藉由相互关联的在场状态(presence,Anwesenheit)、涌现(emergence,Anwesen)、自然(nature,phusis)和真理(truth,alêtheia)等理解存在的方式来得到部分地把握。这些引起强烈共鸣的理解存在的方式都被错误地物化了,并因此被隐藏了起来,而它们就这样在其整个帮助构建的西方历史中延续了下来(如同一个“遗忘存在”的历史)。经由本体神学,存在的充满活力的在场状态变成了静止的、持存的“物质”(而它至为关键的涌现也因此被遮蔽、被遗忘了);自然(phusis)的“自我展现”变成了可以定量计算的自然(natura);作为人类富含意义地参与其中的本体论层次的解蔽事件,原初西方对真理的理解已变得“主观化”,已从存在转移至我们自己,因此,“真理”的场所从存在自身不断溢出的涌现转移到了我们狭隘的表象能力。
这个存在的“命运之遣送”问题——即它在西方历史中,并且作为西方历史,它的到来势不可挡,但却又不断消失、缩减——是后期海德格尔“存在之历史”的关键所在,因此,他经常会阐发一些细节,只是他的阐述太过粗略了(而我在《海德格尔论本体神学》的第1章与《海德格尔、艺术与后现代性》第3章对此作了详细的讨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海德格尔认为,德国的命运(或者说共同的天命)就来自这一原初的西方的“遣送”。他认为,德意志“民族的诗人和思想家”就是要帮助完全恢复已被遗忘的存在之意义,并因此帮助开创一个新的西方历史时代。正是这一筹划把他引向了纳粹主义(他愚蠢地相信,通过把纳粹主义与他自己的思想联系起来,他可以彻底改变纳粹主义,而他后期认为这个可怕的误解是他“最大的错误”)。但我始终认为,这一筹划的核心从哲学层面上讲仍然很重要,尽管出现过如此可怕的联系(我曾经很长一段时期都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并写过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确实,对后期海德格尔来说,通过更完备地理解存在来重新开启历史已经不再是德意志的专属职责;传播存在之后现代的领会并因此不断改变世界这个目标成了一切思想家——不分国籍——的任务。
当然,还有更多值得讨论的地方(比如,海德格尔对东方思想所作的复杂难懂的理解),但这些都没有脱离对西方“存在之历史”的牢固把握,我认为,“坠入爱河”是另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简单地理解命运之遣送的例子。无论是迅速地还是缓慢地“坠入爱河”,只有当我们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把它的意味与意义呈现出来之后,我们才能理解这样一个重要事件的意义。而一辈子本身通过把爱情的意义呈现出来也因之充满了意义(至少部分地)。不管是爱的历史显现,还是存在的历史显现,实际上,所有的这一类的真理事件或命运的遣送,对它们而言,物化的危险始终存在。因为,我们这些有限的存在者在我们自身确定的界限内往往感觉不自在,总渴望以安全与控制来补偿,而这就会诱使我们把给定的错当成真实的,把现实的错当成可能的,把现行的错当成整体的。但是,不管对存在来说,还是对爱(仅仅是存在的一种样式)来说,我们只能藉由持续不断地生成才能持续不断地存在,也即是说,只有藉由持续不断地呈现“存在”的意义才能持续不断地存在,亦或,只有藉由持续不断地呈现在“相爱”的意义才能持续不断地“相爱”。确实,海德格尔早在《存在与时间》中就已经承认“高于现实维持着可能性”;浪漫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lres Baudelaire)也写道:“阳光的每一粒原子都可能带来累累硕果。”由此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海德格尔从早期到后期的转变就可以被看作是其简单洞察——成为我们自己就是成为此在,即积极参与创造我们世界的可理解性,而当我们帮助把真正的意义引入世界(并由此消灭虚无主义)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就做到了最好——的革命性意义的展开。
高:您对“命运”的解释,让我对海德格尔的理解有了更深的体悟。关于这个问题与技术的关系,我后面会深入地向您讨教。在此,我们更想知道的是您的研究概况,即您对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的哪些方面作了深入探究?
伊恩:今天,在我暂时放下我的工作来对我的思想进行概述并想真正深入地回答您的问题的时候,我专门搜索了谷歌对学术的说法,它们以令人感兴趣的方式对哲学家的作品及其影响作了评价,尽管它们的断言看起来很客观,但却是成问题的。在它们看来,我似乎成了最著名的(或至少影响最广的)批判由我们的存在之技术的领会所带来的虚无主义后果的后海德格尔评论家,成了本体论教育(更确切地说,该教育是一项“完美主义”的事业,它致力于“让我们成为我们自身”并因此使我们成为引领有意义之生活的人类)的守卫者,成了极力诉诸于海德格尔的(后海德格尔的)后现代性以及持续相关的艺术与诗来帮助我们学会按照真正有意义的、后现代的方式理解存在的当代哲学的拥护者。我目前最常被引用的作品致力于解释和说明:(1)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本体论批判;(2)从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理解为本体神学来把握其技术批判的根源;(3)把技术批判和本体神学批判与海德格尔重要的教育观点——即我们人类如何成为我们自身,以及如何过上充满意义的生活——连接起来的关系;和(4)艺术的作用在于帮助我们学会超越我们晚现代的虚无主义,过上充满意义的生活。我认为,这也正好表明,我的工作主要聚焦于思考后海德格尔的技术、本体神学、教育、艺术与后现代性,也即是说,追随、藉由和超越海德格尔。
高:您的意思是,海德格尔开启了后现代,把思想潮流带向了后现代性,那么海德格尔与现代性是什么关系呢?
伊恩:在我看来,海德格尔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深刻、复杂而且迫切重要的问题,很难作出简要回答。我最近的著作《海德格尔、艺术与后现代性》(Heidegger,Art,and Postmodernity,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11)阐明了海德格尔在向现代性最深层次的预设上所发起的激进的哲学挑战,也解释了他通过运用某些重要的关于世界从艺术与诗歌中绽出的洞察阐释一种具有本真意义的后现代替代方案的尝试。极其简略地讲,海德格尔认为,现代(从笛卡尔到康德)可以作这样一个明确的定义,即人类把“存在者之存在”理解成了现代受“主体”主宰与控制的“对象”;而在晚现代时期(从康德到尼采),我们越来越追求甚至控制现代自我吹嘘的主体(及其主体性)并使其客观化,因此,我们逐渐把全部存在者之存在仅仅理解成了无,即无内在意义、随时准备被有效优化的“资源”(Bestand,持存物)。与此不同,后现代对存在者之存在的理解对“无”有不同的领会和体验,没有把“无”理解为“最后一缕正在蒸发的现实”,正如在尼采把存在化入无,也即是生成的时候那样,是把“无”理解成了存在本身早期的召唤,理解成了“无着”,而“无着”不是尚未绽出,而是不断地将其自身提供给我们充满创造力的解蔽。
这种存在之后现代的领会,或者,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以“存在本身”为依据的“存在者之存在”的领会,有助于我们学着不要把一切物都经验为“现代”受主宰和控制的对象,或者“晚现代”无内在意义、随时准备被优化的资源(因此,存在者最后全然成了潜在力量的临时构形,而不是其它什么东西),而是经验为始终饱含意义的东西,它们远远超出我们的概念表达能力之外,更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固定于某种单一的本体神学,即一些包罗万象的通过把握存在者最深处、微观的内核与其最外层、宏观的实现来维系我们对存在者的理解的宏大叙事或大一统的理论。
高:谈到本体神学,我想起您的著作《海德格尔论本体神学:技术与教育政治学》。乍看起来,您的书名让人非常疑惑不解,您能就此简单说明一下吗?这个书名到底有哪些内在的蕴含呢?
伊恩:实际上,我这个书名受到的启发主要来源于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理解,他把西方形而上学理解为“本体神学”,而这是开启他“后期”另一个潜在的统一性思想的主要线索,也是解释他如何深邃地、连贯地把技术批判、政治(西方自由主义,东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教育联系起来的主要线索。其中海德格尔一个最深刻但却常常被忽视的洞察是,我们晚现代,尼采的本体神学引起了虚无主义的技术化,而我们也被卷入了这股潮流。
我们晚现代的本体神学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集置”(Gestell),如同存在之历史的其它时代那般,它围绕基础层面的存在之领会具体展开。我们的存在之“技术”的领会就直接来源于尼采的本体神学;我们倾向于把整个存在者之存在理解为强力意志的永恒轮回,也即是说,力的无止境的分解又无休止的聚集,不断地超越力本身的持存。如果我不断地逼问您,这个桌子到底是什么,您最后可能会说,它是飞速运转(但桌子看起来却很牢固)的亚原子粒子的排列组合,而事实上,它毋宁说只是这些潜在的力所具有的短暂的、空虚的形式。只要我们毫无保留地通过这一本体神学框架来理解“是什么”(what-is),我们不但会把存在消解为生成,还会把所有存在者与纯粹的“持存物”(Bestand)联系起来,并因之把所有的存在者都转变为“持存物”,即以效率最大化来优化、订造及提高本质上无意义的材料。
如同尼采式的说法,技术本体神学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存在者向纯粹资源的这一历史性转变变得越来越普遍,因此按照现象学第一原理即切近,它也就逐渐地避开了我们批判的目光。实际上,我们这些晚现代的人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我们自己的,而这构成了我们对世界进行技术重构的基础。现代的主体已经不再谋求去做客观世界的主人,我们逐渐转向了用以控制客观世界继而返身控制我们自己的技术,而主体的这一客观化逐渐把我们也变成了另一种以效率——不管从美容方面、精神药理方面、基因方面、审美方面、教育方面,还是其它“技术方面”——最大化来优化、订造及提高的本质上无意义的材料。现实的这种“技术化”带来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隐藏在现实背后并且驱使着现实的存在之虚无主义的领会:尼采的本体神学把存在化入了无(nothing),但却招致了“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生成”,即无穷无尽的力的轮回,这样一来,它就否认了事物的一切内在本质,否认事物具有的一切能够抵御滑入虚无主义的本真的意义,一切质上的价值,比如,不能纯粹以“价格”来量化和表征的价值,但也因此,无成了无价的(nothing is invaluable)④。
高:本体神学是您这本著作的核心概念,海德格尔主义者对这个概念阐释较少,您为何把它摆在了一个显要的位置,您能否谈谈自己的理解?这个概念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伊恩:您可能注意到了,我那本书《海德格尔、艺术与后现代性》的第一章开头的那句话:“海德格尔要通过本体神学表达什么——我们为何要关注?”⑤在此,我只能作极为简略的回答:如果,像巴门尼德一样,我们也把可理解的现实当成一个球体,那么本体神学要做的就是既从内到外又从外到内来掌握这个球体。换句话说,海德格尔以本体神学来命名的就是这一通过既掌握现实最深层次的内核又掌握它的最终表现并且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以使整个可理解的秩序(或意义空间)稳固下来的尝试。
本体神学开始于泰勒斯与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泰勒斯是通过追索把以各种方式存在(is)的万物统一起来的本质核心(他称其为“水”)这个最深层次的基础来理解本原(archê)的。因此,泰勒斯通过发现现实最内在的基础,即统一并因此解释了一切万有之存在的最终根据,他为西方哲学传统提供了给一切现实奠定基础并把它们统一起来的最原初的本体论道路和基础主义的尝试。不同的是,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却把万物的基础理解成了阿派朗(apeiron),即“无规定”或“无定形”,它是一切具体实存得以产生的本原,而一切具体的实存不再是或者放弃它们具体的存在时,它们就要复归它们最初得以形成的本原。对阿那克西曼德来说,作为分离的特殊性,具体的个别实存是无意义的;只有通过运用上帝之眼来观察整个宇宙,实存的意义才能得到理解:在概念上,分离的个别的实存与无限这一所有个别的存在者得以形成——为了以分离的个体的形式存在——的本原相矛盾(因此,按照他的说法,是“对立”)。因此,我们在死亡中与无限的重新结合是一种适当的报应,它恰好能够偿还(在某种程度上)让人内疚的以特殊个体形态存在的罪恶。按照这种最初的神学观点,个体存在本身是无意义的;只有整个的宇宙循环才是合理的。只有通过以万物最终得以涌现的终极理由为条件来理解现实,整个宇宙的意义才能得到辩护,而(海德格尔认为)这仍然适用于所有追随阿那克西曼德足迹的神学思想家,从柏拉图直至尼采,适用于整个本体神学传统。
柏拉图是第一位将这些用于设定智思(可理解的)世界基础的本体论与神学的方法结合起来的哲学家。他的理念或形式学说把泰勒斯通过把握现实最深处的内核(其它一切实存的共同的本体论基础)来思考现实的原始的本体论方法与阿那克西曼德(通过极力把握现实的最终“神学”表达,即仅此就能为整体实存的意义辩护的最高的表达)思考现实最终根据的方法结合了起来。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将同一实体的不同实例统一了起来(比如,美的形式可以解释各种不同的美所普遍具有的共性:一切美的实例都是美的理想形式的不完美的体现),柏拉图的形式同时还是这种实体的最高的表现形式(因此,美的形式是您所能模模糊糊感觉到的最美的东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见的东西与其相比,都会黯然失色,但正是这一模模糊糊的感觉,它能促使我们领会到宇宙的终极秩序)。因此,正如海德格尔经常说的那样,柏拉图是最早的形而上学家,其实就是说柏拉图是最早的本体神学家。在柏拉图之后,按照我在著作中详细阐释的存在的历史,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由一系列不同的通过把握现实最内在的微观核心与最外在的宏观表现及其在亚原子物理学中第一因与终极的宇宙论表现以使整个的智思秩序稳定下来的本体神学尝试构成。
这不仅仅是哲学史的运动,原因是,海德格尔教导说,西方本体神学传统确立了西方人理解万物“存在”的意义的导向,因为,一切可理解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存在”,所以,西方形而上学的本体神学传统一直都在塑造、改变以及引导西方历史。海德格尔极其反感形而上学,从他下面这个观点可以看出,即当本体神学发挥效用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存在的意义,“从两方面奠定时代的基础”。成功的形而上学本体神学塑造并且改变了西方历史关于存在“是”什么[“是者”(Isness)本身是什么]的导向,因为万物都存在(is),所以,它们塑造并重塑了我们对万物的理解。伟大的形而上学本体神学通过把握现实最内在的核心与其最外在的表现并将这两方面和唯一的“本体神学”理论联系了起来,暂时地阻塞了流动的历史性。
换句话说,本体神学只是暂时地回答了一个时代的存在问题。通过确立存在的意义(或“是者”的意义),本体神学将一个“时代”用圆括号括了起来(暂时地防止一个时代免受本体论层面的历史性所具有的其它漫无目的的生成的影响)。如此一来,本体神学就会对万物是什么以及如何形成与确立给予一致的理解。任何可理解的事物都以某种意义“存在”,因此,一旦本体神学允许一种新的对“存在”的意义的理解固定下来、传播开来,就会促使我们对其它事物的理解的历史性转变稳定下来。海德格尔把西方历史上这三种不同的理解“存在者之存在”的方式称为“存在的历史”。本体神学为这一具有不同的理解存在者之存在的方式的历史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或脚手架。在西方历史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存在者之存在的方式,它们分别产生于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然而,正如我早先曾提到的,现代可以被进一步分为真正的现代与晚现代时期,古代可以分为前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至柏拉图时期以及后柏拉图时期,而海德格尔最大的希望就是传播存在之后现代的领会,他认为这种理解早已在荷尔德林(FriedrichHlderlin)的诗、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艺术作品以及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哲学思想(如,海德格尔从正反两面对尼采本体神学所作的深刻解读)中具有了早期的形式。
高:那么,海德格尔的本体神学与他对技术的追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他是如何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与技术联系了起来的呢?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对技术与强力意志的关系有过讨论,但是语焉不详。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在《海德格尔论尼采之虚无主义》(Heidegger on Nietzsche on Nihilism)中曾批评道:“海德格尔一经‘攻击’尼采(自1936年之后的演讲,他的这种转向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他便开始指责尼采为虚无主义者,将其与主体性的形而上学联系起来,并将其牵扯进现代技术‘集置’的存在之意义的问题,他不仅曲解了尼采,而且错失了更好地利用尼采之诊断以解决核心问题的机会。”接着他又强调:“海德格尔没帮我们把握为何他认为[强力意志的]这种‘无目标状态’将要求‘人对于地球的统治’。”您是否同意皮平的观点?尼采的虚无主义与海德格尔的技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伊恩:需要重点强调的是,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可直接地从他对本体神学的理解得出。实际上,这两方面的联系非常紧密,即他的技术批判根本无法完全独立于他的本体神学思想。我最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本体神学是后现代技术集置时期隐藏起来的形而上学脚手架。早在1934年,海德格尔就曾指出尼采的两面性(事实上,他的思想既支持优生学的观点,服务于纳粹的技术最优化,却也高于纳粹对其思想的运用),但是在他是纳粹党员及其随后受余波影响的这段时期,海德格尔倾向于抑制他与尼采在激烈“争—辩”(alter-cation,Aus-einander-setzung)中积极的一面,相反,为了间接地推进他对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纳粹主义的批判,他一直都在批判尼采,并且持续到海德格尔痛苦地放弃他在哲学上所抱有的帮助纳粹主义“第二次、更深刻的醒悟”——在此,他想成为“领袖的领袖”,希特勒哲学上的大臣,他想教导纳粹党如何超越他们晚现代的优生学理论,如何像“诗人和思想家”那样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希望后。海德格尔曾希望以此方式来招致存在之后现代的领会,而他最初就是想把该理解当成德国对世界史的独特贡献,然后再逐渐将其全球化,但这只是一个幻想,不过藉由撰写和传授他的充满诗意的思想,他一直都在努力促成这一幻想。
高:该如何理解您所谓的“尼采的本体神学是后现代技术集置时期隐藏起来的形而上学脚手架”?您能否更清晰地把您的断言表达出来?
伊恩: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本质上不是特殊的技术装备,而是存在之技术的领会,只是这样的装备通常能够把该理解清晰地表达出来。此一存在之技术的领会也是尼采对“存在者之存在”的理解,他把“存在者之存在”理解为“永恒轮回的强力意志”,而这一传播开来的理解只把万物理解为各种以力量本身最大程度的持存为目的而展开相互斗争的力量。这种尼采并未认识到并将其投射到世界上的存在之领会,不是出自某种私人的创造性的洞察力,而是出自达尔文对生命和亚当·斯密对经济等存在的理解,但之后却变成了对宇宙本身及宇宙中万物的全面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是尼采的信徒;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把存在含蓄地理解为无意义的、随时准备优化的力量,我们采纳和传播的都是存在之技术的领会。海德格尔本人早已意识到,此种理解已经在像横跨德国高速公路的蝶形的立交桥这一雄伟的因技术革新而带来的工程壮举——藉此,遥远的距离被尽可能快速且高效地连接了起来——这样的物中具身化,而为了更快、更有效、更无缝地将我们连接到无尽的信息流通之中,这种最优化的逻辑通过我们当代的“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通过我们每个人口袋里、手腕上以及将来的脑袋中随身携带的越来越多的小型技术神殿,得到了更直接的表现。
此种存在之技术的领会变成了我们借以领会现实的透镜,即使在我们没有使用谷歌智能眼镜而只是按照存在的技术化来理解现实的时候,我们也会趋向于把物理解成以备我们将现有的计划与设计强加于其上的无意义的材料,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我们可以学着有创造性地、有责任感地呈现出来的最初提供给我们的隐约闪现的意义迹象。比如,想一想米开朗琪罗是如何认真思考那块有名的使其从中创造性地把“大卫”呈现出来的大理石的,想一想伐木工在决定用木块制造什么东西的时候是如何毫无神秘性地思考特定木材的形状与纹理的,再想一想工业刨花板厂是如何——为了把磨好的碎木屑重新粘合成规格一致、可替代的平板,从而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方便使用——将木板不加选择地磨成粉末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未曾察觉到的存在之技术的领会愈来愈倾向于利用刨花板厂这样的技术来处理一切事物,藉由技术,被强加到本身被认为无意义的材料上的是现存的形式,不像是那种我们在艺术与诗中明显遭遇到的创造性的解蔽,而藉由艺术与诗,我们学会了对最初以别的方式隐藏在物质中的迹象保持敏感,我们学会了按照我们自身的方式携手物质谋求创造性地、负责任地呈现这些迹象。
对海德格尔而言,强制和解蔽抑或技术强制和诗意解蔽之间的区别,是我们对存在毫无意义可言的技术领会和我们自身与世界富含意义的相遇这一后现代领会之间的主要区别。我想再举一个可能更贴近我们生活的例子,即两种教育方式之间的区别,第一种教育方式设法帮助学生识别和培养他们自身固有的天赋与能力,帮助他们学会培养自身独特的天资与技能,使其有能力回应他们这一代人眼中最紧迫的问题;第二种教育方式试图把预先确定的结果强加到所有学生身上,该教育方式有可能会强调“优秀”,以便高效地造就现行经济体系及其不断变化的需求所需要的工人,它也有可能会遵循最优化的律令,试图以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多的回报。对海德格尔而言,真正的意义,即我们可以绕此构建令人满足的生活的意义,并不能通过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世界之上来获取(正如克尔凯戈尔所教导的那样,这会使我们变成无何有之乡(a land of nothing)的最高统治者。在这里,一切意义都不确定,因为意义来自我们,来自我们自己的意志,因此它很容易被设定,也很容易被废除);相反,真正不朽的意义是通过学着把那些至少部分独立于我们而存在,并因此容许我们发现各种参与和服务于比我们自身更大的东西的方式(即使这有可能带来无法回避的危险和回报)的意义展现出来才得以形成的。
(未完待续)
注释:
①译者在《楞严经》卷二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译者注
②参见Heidegger,Poetry,Language,Though t,trans.A.Hofstadter, New York:Harper&Row,1971,p.5;Heidegger,Aus der Erfahrung des Denkens,Pfullingen:Neske,1954,p.9;另参见“A Letter from Heidegger,”trans.W.J.Richardson,in Manfred Frings, ed.,Heidegger and the Quest for Truth,Chicago:Quadrangle Books, 1968,p.19,21。
③关于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参见德雷福斯在2005年美国哲学协会西部分会上的主席报告:Overcoming the Myth of the Mental: How Philosophers Can Profit from the Phenomenology of Everyday Expertise。
④nothing is invaluable,原意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无价的,但汤普森在此想驳斥的正是这种观点,并且考虑到前面提到了无(nothing),因此,译者对该短语作了意译,不过,这种翻译可能更符合海德格尔与汤普森的观点。
⑤参见Thomson,Heidegger,Art,and Postmodernity,New York 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7。
(责任编辑:张群喜)
B516.54
A
1674-9014(2016)06-0025-09
2016-09-2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技术时代的精神状况:在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之间”(15YJC720008)。
高海青,男,山东滨州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技术批判理论和技术现象学。